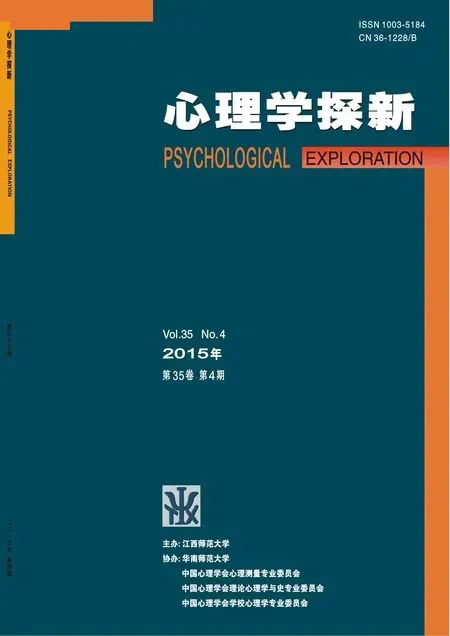恶与菩提心:佛教慈悲观在心理治疗中的运用
2015-02-26张鳅元,杨韶刚,王兴华等
*通讯作者:申荷永,E-mail: shenheyong@ hotmail.com。
摘要:“菩提心”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础,其核心内容便是“慈悲心”。文章由分析心理学中的“阴影”概念引发出对“恶”的临床水平意义上的探讨。总结并发展了“恶”的心理学含义,阐述了对“恶”的理解和认识在心理治疗中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将佛教中的“菩提心”引入现代心理治疗领域,阐明了治疗师在心理治疗中对待“恶”的态度及方法。“阴影”与“恶”是人类内心及人性中无法被忽略或否认的部分,需要以“慈悲”的态度去面对和抱持,这是一切心理治疗的基础。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5)04-0307-05
早前,詹姆斯、弗洛伊德、弗洛姆等其他心理学家及心理治疗从业者们就曾展开过关于佛教冥想及禅宗与西方心理学的讨论(Andersen,2005)。而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兴起,佛教思想在心理治疗领域中的引入与应用受到了越来越多地关注(王求是,刘建新,2007)。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禅宗与心理治疗(Chan et al.,2012; Kalliel,2003;谭素芬,吴希林,邓云龙,2012;王求是,刘建新,2007;魏吉槐,唐秋萍,邓云龙,2012;姚瑞,唐秋萍,邓云龙,2012),正念疗法(Mindfulness -based Therapy)在心理治疗中的使用(Ames et al.,2014; Bruce,2010; Coelho,Canter,&Ernst,2013; Khourya et al.,2012; Singh,2012;李英,席敏娜,申荷永,2009;石林,李睿,2011;庞娇艳等,2010),冥想(Meditation)与心理治疗(Condon,2013; Hussain&Bhushan,2010; Young,de Armas DeLorenzi,&Cunningham,2011;任俊,黄璐,张振新,2010),以及其他佛教核心思想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Andersen,2005; Chiesal&Malinowski,2011;石文山,2013;石文山,叶浩生,2010;姚萍,2012)。
综合现有的佛教与心理治疗的文献,不难发现无论是禅宗与心理治疗、正念疗法还是冥想,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佛教的“无我”的自我观之上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都是从“自身关系”的角度出发,解决“自我”的内在冲突。包括对佛教其他核心思想与心理治疗的探讨,如“般若”思想与心理冲突的缓解(石文山,2013),也都是从“自身关系”这一角度来思考的。然而,心理治疗是一个在治疗师与来访者建立起治疗联盟之后才会产生治愈效用的过程。所以,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人我”关系更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关于佛教之中的“人我”关系在心理治疗中的运用,却尚未被谈及。在这一方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都是空白的。而在探讨佛教的“人我”关系与心理治疗之前,一个同样需要被重视的问题是,在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人我”关系中,治疗师所面对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来访者以及自己。本文关于“阴影”、“恶”以及“菩提心”的探讨,都是围绕以上问题展开的。
1 阴影
“阴影”(Shadow)是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荣格(C.G.Jung)这样阐述它,对于人性中那些被我们判断为“恶”的,那些被我们否认、压抑、抑制的部分便是“阴影”(诺伊曼,1998)。荣格认为阴影是一个道德问题,挑战着整个自我人格,因为,如果没有相当多的道德努力,就没有人能意识到阴影。要想意识到它,就要承认人格的黑暗面是存在和真实的。但是,荣格并没有直接描述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恶”,他只是提到,善与恶本身就是原则,在人类生命存在之前就已存在,并且是每一个心理治疗师都必须要处理的问题(Jung,1995)。同时,荣格还指出,由于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一种原则,心理冲突便会产生,而这种心理冲突也是一切的心理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治疗师所要解决的是来访者情绪过度的冲突情境。并且,荣格把这善与恶的原则归结为道德判断的原则(Jung,1995)。但是,荣格也强调过,阴影并非只是人格中阴暗的或被压抑的部分,还包括那些从未被察觉的和生命中最原始的部分,因此,面对阴影的态度,荣格更强调整合,使之与其对立面人格面具以及意识自我相整合,最终体验人格的完整性(McNamara,1994)。
可以说,“阴影”是每一位心理治疗师、每一段治疗关系都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而要想更清楚地理解“阴影”是什么,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恶”。
2 恶
2.1当代与近代心理学中对“恶”的阐述
对于“恶”这一问题众多心理学者及临床治疗师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或认识,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必要探讨的形而上学的问题(Hoffman et al.,2011)。然而,斯考特·派克(Scott Peck)直接且充分地探讨了“恶”这一主题。虽然,他并未对“恶”给出一个严格的心理学定义,但在他的著作People of the Lie一书中,他对“恶”作了一个生动并贴切地诠释:“恶”(evil)倒过来写就是“生命”(live),“恶”与“生命力”恰恰相反,互为对立面,正如,“恶”总是与对生命的“杀害”、“杀戮”息息相关(派克,2007)。并且,派克(2007)进一步补充到:恶是存在于人类外表与内心、企图扼杀生命力或活力的那股力量。
比派克更早,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姆(Fromm)也对“恶”给出过充分的注解。在The Heart of Man一书中,弗洛姆(1989)用非精神病性的暴力行为来证明他的性恶论。其中包括,为了娱乐而进行的搏斗、互相残杀(娱乐型暴力行为),为了捍卫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利益等所采取的攻击(反应型暴力行为),为了挽回自尊或是因信仰崩溃而有的破坏性行为(报复型暴力行为),为了平衡自己原有的无能或软弱而依附于有权势的团体并为协助其作恶的行为(补偿型暴力行为)。同时,他还通过恋尸癖、自恋和恋母固结(即“退行综合症”,the syndrome of decay)这些病态行为,来说明恶的本质。在弗洛姆(1989)看来,“恶”的本质与根源是人性中的对死亡与毁灭的渴望,即“死本能”,以及被驱逐出外在客体又全部指向自我的力比多。不难看出,派克与弗洛姆笔下的“恶”的共通之处在于对生命的破坏以及非人道主义的暴力,而弗洛姆在秉承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学说的基础上,更认为“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性。
2.2存在主义心理学对“恶”的阐述
除此之外,对“恶”给以更多注意及更全面解读的是存在主义心理学。其中包括最为重要的几位存在主义心理学家,Rollo May,Ernest Becker和Stephen A.Diamond(Hoffman et al.,2011)。对于Ernest Becker来说,“恶”是对死亡的否认,而Ernest Becker所谈到的死亡,不仅只是生命的终结,还包括死亡的象征意义,即人类自然性中的各种极限,比如知识上的、权力上的以及影响力上的。所以,Ernest Becker的“恶”可以理解为对人类各种有限能力的不能接纳(Becker,1985)。罗洛·梅(Rollo May)对“恶”的阐释与荣格所讲的“阴影”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认为除了人性中破坏性的一面,“恶”还包括原始生命力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是创造力、活力与健康的来源(2010)。罗洛·梅(2012)认为“恶”中蕴藏着哪些潜能取决于个体如何对生命原始性的运用。Stephen A.Diamond对“恶”的注解也是建立在“原始生命力”这一基础上的(Hoffman et al.,2011)。而这一“原始生命力”与精神动力学派的无意识是有关的,同时还意味着极限与掌控。关于“原始生命力”与掌控,在Otto Rank精神分析的论述里也早涵盖(Rank,1978)。在Otto Rank的基础上,Ecker 和Hulley(1996)对无意识给出了更清晰的定义:无意识在更广的范围内包括觉察以外的一切认知的、情绪的、躯体的感受、状况以及过程。使个体们受控的往往是这些觉察不到的部分。而Rank这里的无意识对个体的控制与Diamond所提到的“原始性的管控”很相似。罗洛·梅(2010)对这一“原始性的掌控”有如下的定义:任何归结于无意识范畴的本能的过程都可以叫做原始性的控制。而这里的“原始性”常与压抑(repression)和束敛(constriction)同时出现。压抑是否认原始性力量的影响作用,而束敛则是指降低生理心理的觉察能力(Hoffman et al.,2011)。而Diamond(1996)认为面对这一“原始生命力”,我们应该做的是承担个人责任、行诚德之行以及保持自我觉察。所以,概括地说,存在主义心理学是以交汇的视角对“恶”、个体责任与伦理进行思考的,它不仅融合了精神分析学派的无意识观点,也包含了分析心理学中“阴影”所涉及的道德问题。
2.3关于“恶”的存在整合的观点
进一步地,在已有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对“恶”的阐述的基础上,Hoffman等(2011)结合了社会心理学,特别是金巴多(Zimbardo)的理论,发展了关于“恶”的存在整合(existential-integrative psychology)的观点。从金巴多(2008)的环境论观点来看,“恶”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与文化,在于社会体系中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system)。而存在整合的观点则认为在“恶”的发展中,既有环境(situational)因素,如人际关系、社会与文化,同时也有性情(dispositional)因素,即如存在主义心理学所提到的,人的原始性、破坏性以及对生命极限的否认。
所以,与其他关于“恶”的阐述相比,存在整合的观点相对更为完整。而综合上述所有对“恶”的解读,“恶”可以被阐述为:包括意识性的非精神病性的暴力、破坏行为与意图,以及对死亡及其象征的拒绝接纳;也包括无意识中的生命的原始性,它既常常被压抑,体现出“原始性的掌控”,同时也是创造力与活力的来源。当把“恶”放到集体水平上的时候,社会与文化都会影响“恶”的形成与发展,这便使“恶”具有了道德性与伦理性。在心理治疗中,每一位治疗师与来访者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几乎都是围绕着“恶”展开的。比如,来访者对失控事件(如死亡、权利、能力等)的恐惧,或者因人伦情感问题而产生的自罪心理,甚至还包括意识自我与原始创造力之间的冲突与连结等。而心理治疗中的“菩提心”的运用,以及由菩提心衍生出来的“慈悲观”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提出来的。
3 菩提心
3.1菩提心与慈悲观
“菩提心”源自印度佛教的bodhicitta,指“觉醒的心”、“证悟的心”,其两大基石便是慈悲与智慧,特别是“慈悲”被看做是“菩提心”发起的根本所在,甚至很多时候被等同于“菩提心”(济群法师,2009;徐光兴,2013)。而慈悲观作为佛教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佛教一切教义的根本准则。
中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学者王学富(2011)曾提出“直面”心理学的观点。他认为,我们要“直面”,即面对生活中的不幸、创伤及恐惧。他认为,“直面”是一种使自己从“生存主义”(survivalism)超越到“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人类能够发现并理解各种消极事件的意义。诚然,“直面”也可以作为一种对待“恶”的态度,而“直面”心理治疗中所倡导的“不逃避”与“面对”也可被理解为“不否认”。但是,更值得强调的是:对待“恶”,特别是“恶”中的消极部分,不仅仅需要“不否认”以及“面对”,更要“接纳”与“抱持”。而对“恶”的“接纳”与“抱持”的基础是“菩提心”。
然而,“菩提心”中倡导的“慈悲”,并非简单地“我要利益他人”的想法,其慈悲观是建立在佛教的最根本的自我观之上的。这一自我观包括两部分,“无我”与“同体”(彭彦琴,沈建丹,2012)。“无我”是指“五蕴” *的无常与不恒存,心理学的理解即,无常的、不恒存的物质之我和精神之我。对“无我”的认识则是破除佛教所谓的“我执”和心理学中的“自我中心”的前提,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慈悲心”是指,在由己度人地认识到物我无常之苦之后,生起的慈爱与悲悯之心。“同体”则是指华严宗中的“自他不二”的人我关系,即个体与其他众生是一体的,利益他人即利益自己,损坏他人即损坏自己,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恤,即为“同体大悲”,对一切有情(人与动物)等同视之,对众生苦乐感同身受(彭彦琴,沈建丹,2012)。由此可见,建立在“菩提心”基础上的“接纳”与“抱持”是一种最深广的慈悲。一如文章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所言,内心和人格之中的“阴影”以及人性之中的“恶”往往是产生心理冲突的症结所在,而治疗师的由“菩提心”衍生出的“慈悲观”则是建立在对来访者的“阴影”与“恶”的深层认识的基础上的“接纳”与“保持”。
3.2菩提心与心理治疗
“菩提心”在心理治疗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应用便是“共情”。罗洛·梅在一次题为“受伤的治愈者”的演讲(1984)中曾指出:我们是通过自身的伤口来医治他人的……正是通过我们与自身问题的斗争而获得的洞察,引导我们发展出对人类的共情和创造性——以及慈悲。同样地,徐光兴(2013)也认为心理学中的“共情”(empathy)与“慈悲”有共通之处。他认为,“慈悲心”的本质并不是怜悯者与被怜悯者之间的上下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在共同的痛苦经验上建立起来的,施予他人的同时也是在施予自己,对他人的慈悲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慈悲。可以说,在“慈悲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情”,是一种建立于在意识层面上对来访者最深切地认识的基础上的“共情”。这种认识不仅仅是建立于“无我”与“同体”的自我观之上,还包括对来访者的“阴影”以及人性之“恶”的理解。而在此“慈悲心”基础上产生的“共情”,才能使来访者卸下防御,从而与来访者建立心灵交流的桥梁。所以,在治疗师的“慈悲心”面前,一切“阴影”与“恶”都是可以面对的、被接纳的、被抱持的。而也只有在这样的“面对”、“接纳”与“抱持”之中,治疗师才能为来访者创造出一个安全而受保护的空间,并和来访者在这一空间中建立起治疗联盟,从而使来访者获得转化以及治愈。
除了“共情”这一点,“慈心禅”也可以看做是“菩提心”的理念在心理治疗中的一个运用。曾祥龙、刘双阳和刘翔平(2013)对慈心禅有较详尽的研究。在佛教中,“慈”、“悲”、“喜”、“舍”被认为是“四无量心”,是面对一切众生的四种态度。“慈”,是指对一切众生的无条件与无差别的善意,且不受亲疏分别或利益关系的影响;“悲”代表悲悯,既包括对他人的,也包括对自己的;“喜”,是为一切众生的快乐或成功感到喜悦;“舍”,表示保持不带执著的接纳与内在的安宁。“慈心禅”可以理解为,以“慈悲”为基础,逐渐提升到“喜”与“舍”的境界。“慈心禅”是佛教中“止禅”的一种,其练习方法是将注意指向和维持于某一特定对象,以训练注意的专注并暂时止息内心烦扰的过程,和专注呼吸的禅修相似。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慈心禅”训练能够提高积极情绪体验,缓解消极情绪反应,能有效提高自我同情和对他人的共情能力。所以,可以说“慈心禅”是一种以“菩提心”为基础的可应用在心理治疗之中的可操作方法。同时,治疗师本身也可以通过练习“慈心禅”来提高自身的觉察及共情能力。而心理治疗从业者们需要认识到的是,无论是以自我提升的目的来练习“慈心禅”,还是对来访者施以“慈心禅”,其源头都是“慈爱”与“悲悯”。而需要从业者们以“慈爱”和“悲悯”来面对的,正是“阴影”与“恶”,既包括来访者的,也包括治疗师自身的,甚至还有社会与文化中的。
4 结语
可以说,由佛教“菩提心”衍生出来的“慈悲观”与人本主义心理治疗中治疗师首先要具备的素质“无条件积极关注”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当“慈悲观”被运用到心理治疗之中的时候,它为“无条件积极关注”补充了许多实质内容,包括,(1)治疗师是在对什么“无条件关注”,那就是本文所谈及的“阴影”与“恶”;(2)治疗师如何“无条件关注”,那便是“菩提心”中的“慈悲”态度,而这一“慈悲”是建立在“无我”和“同体”的观念之上的。所以,把“恶”与“菩提心”以结合的方式提出,可以看作是西方心理学与东方哲学的一种融合,特别是对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和补充。虽然,针对心理治疗中的“阴影”与“恶”,而在佛教“菩提心”基础上提出的“慈悲观”并不是一种具体的实操方法,但是,这是比任何一种具体的治疗方法都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心理治疗师首先要具有的态度。面对千变万化的精神及心理症状,心理治疗的方法也是多样且各有千秋的,但是,当一位心理治疗师具备了“慈悲观”这样一个前提态度后,即便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且棘手的案例,相应的治疗方法也会应运而生。而这在实际工作中,也屡见不鲜。正如佛教中的八万四千法门,便是由以“菩提心”,即“慈悲”,为基础而生起的智慧所产生的(笔者补充)。回到心理治疗上来,事实上,对于“阴影”和“恶”的探讨,是值得每一位心理从业者,特别是临床心理从业者首先并继续思考的问题。而与之对应的“菩提心”与“慈悲观”更是治疗师们应具备的素质和前瞻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