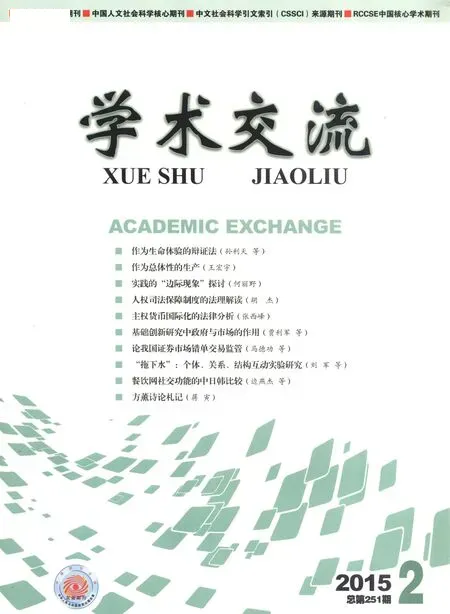《时时刻刻》中现代知识女性的“牢笼”之惑
2015-02-26王佳英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空间闭合与解域:《时时刻刻》中现代知识女性的‘牢笼’之惑”(12532410);齐齐哈尔大学校级重点课题“英语专业英美文学作品赏析中文本细读及空间理论的应用策略研究与实践”
《时时刻刻》中现代知识女性的“牢笼”之惑
王佳英
(齐齐哈尔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摘要]迈克尔·坎宁安的《时时刻刻》是一部跨越时空的女性小说,揭示了三位知识女性积极探寻的精神家园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她们来自20世纪不同年代和不同城市,面对禁锢身体和心灵的“牢笼”,却承受着同样的挣扎、困惑、恐惧和绝望的命运。虽然每一位主人公冲破“牢笼”的方式不同,但她们的选择及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苦苦求索都诠释了女性找寻自我的艰辛历程。
[关键词]迈克尔·坎宁安;《时时刻刻》; 现代知识女性
[收稿日期]2014-11-13
[作者简介]王佳英(1970-),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士,从事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2-0192-04
20世纪初,英国著名意识流作家、女权主义运动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了全人类女性自己的独立宣言:“一个女人,第一需要是独立”。她以女性特有的直觉、细腻和机敏关注“女性”这一“隐形”的群体,通过自身的经验和“生命写作”,将《达罗卫夫人》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女性经典作品奉献给人们。针对伍尔夫在《达罗卫夫人》这部小说里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女性精神世界及生存状态,美国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通过《时时刻刻》这部小说给出了回应。小说勾勒出了20世纪女性艰辛的自我认知过程,同时也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一次女性被奴役灵魂的独白、一部女性成长的史诗。
《时时刻刻》出版于1998年并于2002年被好莱坞搬上荧屏。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另外两位虚构人物布朗太太和达洛维夫人一起构成文本叙事的三条主线,同时坎宁安选择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经典意识流小说《达罗卫夫人》的曾用名《时时刻刻》作为小说的名字,这些显而易见的互文特征必然使读者在解读《时时刻刻》时与《达罗卫夫人》及伍尔夫的女性思想联系起来。小说聚焦于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中三位女性一天内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世界。讲述六月阳光明媚的一天里所发生的平常事件,而这“实际上是表面的;作家大胆而无情的笔触伸向人物内心,使她们处于剧烈的矛盾、冲突之中,经历了强烈的、骤变的过程之后,简单之下所有的矛盾和复杂呈现出来”[1]。
一、伍尔夫太太:精神疾病是束缚身心自由的牢笼
英国现代著名意识流作家、女权主义运动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小说中三位女性主人公之一。复杂、敏感的内心世界及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她的身心备受摧残,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1923年,在伦敦郊区里士满的霍格思府养病的伍尔夫感觉不到乡间生活的恬适和惬意,医生的安排、丈夫无微不至的呵护和监督没有带给她丝毫的心灵安慰和些许的安全感,只有窒息。她认为:“这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都被你们偷走了!我住在一个我不想住的镇上,我过着一种我不想过的生活。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挣扎,深深的黑暗,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选择不住在这个令人窒息的郊区”[2]60,她被“囚禁”在这里,就像一只笼中之鸟,丰满的羽翼不能完全展开。里士满的霍格思府是伍尔夫在现实生活中无法逾越的藩篱,成为束缚她身心自由的空间表征。
伍尔夫向往自由的生活,她渴望回到伦敦,那个能够让她感到生命灵动的“混乱喧嚣的都市……这是我的选择。即使最卑微的病人,也应该允许她对自己的药方有一定发言权……你不能通过逃避生活来寻求平静”[2]60。她痴迷地幻想着伦敦的生命脉动,幻想着自己的生命融入其中。而这些快乐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她身患精神疾病,发作时歇斯底里,曾经几次试图自杀,所有关心她的人都认为她需要静养,郊区的平静生活对她有好处。她觉得自己完全被排斥在美妙的生活之外,“世界是一个整体,而我则在这个整体之外”[3],疾病的束缚和对自由的向往成为伍尔夫精神世界痛苦的根源。
疾病对肉体无休无止的纠缠,被“囚禁”的生存境遇让伍尔夫感到越来越强烈的抑郁、孤独和无助。封闭的养病环境切断了她文学创作的源泉,丈夫的严格监督侵犯了她自由生命的选择权利,佣人的愤慨和敌视剥夺了她作为女主人的尊严和自信,这些身体自由的桎梏和精神自由的压抑像一张无形的网将她牢牢罩住,让伍尔夫感到忍无可忍,她渴望被理解,却无处倾诉。她想冲破缠绕着她的无形的藩篱,却无能为力。“如此生活下去她会死,慢慢死在玫瑰花盛开的床上”[2]145。在这种绝境中,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悄悄地溜上楼”,将自己束之高阁,隔绝外界喧嚣,备下纸笔,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达罗卫夫人》这部小说中的同名女主人公达罗卫夫人表达自己的心情。
她对这部小说寄予厚望,希望它是“一部最好的小说”,能够蕴含自己所有的遭遇、苦闷及希望,能够探索女性幽深敏感的内心世界……这位备受精神疾病困扰的天才女作家用女性特有的直觉、细腻和机敏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荆棘和杂草的女性内心世界。这是一个惶惑、迷茫的世界,女主人公达罗卫夫人借举办聚会来掩饰和排遣内心的孤寂。她茫然地走在买花的路上,可心却早已失去了活力和方向。在匆匆的人流中,她悄然穿过,游走在现实世界的边缘,脑海里翻涌着无尽的思绪,试图解读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价值。突然,自杀的枪声惊醒了她游走徘徊的灵魂,从战场上归来、罹患精神疾病的赛普蒂默斯以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绝望与无助。“有人必须要死,是为了让剩下的我们更加重视生命。这是一种对比。”这是弗吉尼亚与丈夫伦纳德在探讨《达罗卫夫人》时的对话。无奈地结束自己生命的人给了世人以警醒,活着,需要活着,人应该活着。达罗卫夫人的生存选择也是伍尔夫要求自己作出的选择。对伍尔夫而言,活着本身就是一场搏斗,与缠扰自己肉体的病魔搏斗,与控制自己精神的癫狂搏斗,与束缚自己思想的传统观念搏斗……伍尔夫通过达罗卫夫人的心理活动进行“生命写作”,捕捉那些影响和决定生命选择的特殊时刻,即“存在的瞬间”,思考女人、呼唤女人、探秘女人对于生命的认识、对于死亡的思考。这是伍尔夫灵魂发出的声音,这个敢于质疑和否定主流社会观念的勇敢的、伟大的同时也是敏感的、脆弱的灵魂发出的无言控诉。
但是,尽管伍尔夫拼尽全力去厮杀,她仍然感觉到了病魔张牙舞爪,狞笑着向她袭来。二战即将开始,伴随着战争而来再次发作的疾病吞噬了伍尔夫的希望,她彻底崩溃了,再也无法面对那比死亡更加可怕的命运。带着对丈夫和姐姐的深深歉疚,伍尔夫选择负石沉水,结束了自己痛苦、煎熬和拼搏的一生。
二、布朗太太:家庭生活是束缚个性自由的牢笼
《达罗卫夫人》的痴迷读者劳拉·布朗是二战后迷惘的家庭主妇的典型。像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达罗卫夫人一样,劳拉有就业能力和选举权利,却随着社会的潮流主动退回到家庭,意欲成为新一代的“房屋中的天使”。可悲的是,劳拉不但没有成为一位“天使”,却变成了世人眼中的“恶魔”,她自杀未遂,在生下女儿后抛夫弃子,离家出走,致使原本“快乐温馨”的家庭遭遇灭顶之灾。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位被丈夫挚爱的妻子、儿女心目中天使般的母亲如此决绝、冷酷地选择离开呢?
在成为战争英雄丹的妻子之前,劳拉“从未被人追求过,也未被人珍爱过,总是孑然一身,孤孤单单地读书”,可是丹却深深地爱上了她,“于是,她现在成了劳拉·布朗,而劳拉·齐尔斯基,那个孤独的女孩,那个成年累月死读书的女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便是劳拉·布朗”[2]40。称呼的改变标志着她作为一名女性身份的改变,也标志着社会身份和家庭责任的变化。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认为,“命名是确立主体身份的方式”[4],劳拉·布朗这个称呼意味着责无旁贷的义务。作为女主人,她应该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应该让丈夫感到家的温馨幸福、应该让儿女感到安全快乐,成为二战后美国社会大力宣扬的“快乐的家庭主妇”。表面上看,她应该感到骄傲和幸福,事业有成、体贴入微的丈夫,聪明、乖巧的儿子,宽敞的房屋,富裕的家庭生活,即将到来的第二个孩子,这种大多数家庭主妇梦寐以求的生活却成了她的深渊和噩梦,“劳拉·布朗正试图隐匿自己……从而离群索居,不与他人来往。”[2]37
劳拉的自我处于不断的失衡和激烈的斗争之中,真实的我和伪装的我脱了节。她试图发现生活的美好,竭尽全力地感受家庭的幸福,无奈魂系别处。心底深处那个真正的自我渴望逃离无聊、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她终日恍恍惚惚、心神不宁地生活在这座房子里,浮现在她眼前和心里的是生活的琐碎和了无生趣。在丈夫的生日这一天,她希望为丈夫做一个美味的蛋糕,希望“这蛋糕将显示出仁爱与欢愉,诚如一所宅第予人以舒适与安全之感……充满希翼。”[2]76可是,做好了的蛋糕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精美”,她不仅是一个“失败的工匠”,更让她在她怀有同性恋隐匿情结的朋友基蒂面前感到“难堪”和无能;乖巧、懂事的儿子也没有让她充满爱意,儿子的依赖和爱慕让她不知所措,有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她在家庭生活中感到的是无尽无休的窒息,没有自己的空间,无法找到属于自己自由世界的出口。“除了丈夫、孩子和家以外,我还想要更多的东西。”[5]唯一能让劳拉身心愉悦并给她带来精神慰藉的就是逃离现实。她开车来到偏远、僻静的诺曼底旅馆,要了十九号房间,一个“自己的房间”,尽情享受只有自我的时光,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只有在此时,她的身体和精神世界才完全属于她自己。怀着轻松自由的心情,劳拉继续品读《达罗卫夫人》。故事中女主人公的生活和经历引起了劳拉的共鸣,她从达罗卫夫人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压抑、悲伤、茫然,她开始质疑现实生活。她痛苦地反思自己的生活,从了无情趣的日常琐事开始索问生活的意义和自身的价值,此时此刻,就在这种狂乱的思绪之中,她甚至想到了死亡。死亡,似乎触手可得。此时,劳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灵魂的诉求,她的灵魂要从这被家庭生活羁绊的肉体里超脱出来,超越社会之我与家庭之我,在无拘无束的精神世界里感受生活、享受自由。由此可见,劳拉的社会及家庭身份与内在自我处于分裂状态,无法建立起稳定、和谐的自我身份认同。
最后,劳拉听从了内心的声音,“克服了来自公众舆论对她的压力又战胜了她自身内在的阻力”[6],选择离家出走,作出了一个自己最痛恨又无可奈何的决定,“抛弃孩子,这是一个母亲能做的最恶心的事”。劳拉宁愿背负种种罪孽也要摆脱社会及别人强加在她身上的所有“身份”定义,“妻子”、“母亲”,抛弃社会观念和伦理规范的所有“无形的镣铐”,逃脱“灵魂的奴役”。褪去所有光环和卸下所有责任的劳拉,就像她曾经渴望的那样完全回归自我,成为一名远离社会、远离亲人的孤单的人。她是“多伦多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一位生活的观察者,一个“被生活遗忘的人”;一个在儿子理查德的诗作中开始被奉为“天使”,而后又成为“恶魔”的女人;一个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于肝癌,女儿被撞死,儿子罹患绝症、苦苦挣扎、艰难度日却毫无所动,静静地、冷漠地等待“结局”的女人;一个“隐匿”于人世,孑然一身、无牵无挂,一个纯粹的、无知无我无他的“自由”的女人。
三、达罗卫太太:情爱责任是束缚生命自由的囚笼
克拉丽莎·沃恩是一位中年女编辑,因为与伍尔夫笔下的达罗卫夫人同名,被其男友理查德称为“达罗卫夫人”。“尽管她想叫自己伊莎贝尔·阿切尔或者安娜·卡列尼娜,还与理查德争过一番,但理查德仍坚持说,达罗卫夫人这一名字显然是她唯一的选择。”[2]3因为这关乎着她的命运问题。
克拉丽莎事业有成,与同性伴侣萨莉和借精生养的女儿茱莉亚生活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她拥有一切构成幸福的要素,可是她的真情和挚爱却在她罹患艾滋病的前男友理查德身上。多年来对理查德无怨无悔、无微不至的照料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作为理查德曾经的女友,她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他的全部生活,包括精神上的支持。当年才华横溢、俊美潇洒的理查德与克拉丽莎一起度过了他们一生中那段最浪漫的快乐时光。在那美妙的感觉中,他看到晨光中克拉丽莎美丽的身影,称她为“达罗卫夫人”,而她就成了他最甜美的“达罗卫夫人”。当理查德昔日的同性恋男友路易斯拜访她时,克拉丽莎突然情绪失控,泣不成声。她觉得自己就像生活在牢笼之中,甚至觉得有点委屈,因为自己仅仅拥有一个夏天的回忆。现实淋湿了温馨、砸碎了幻梦。盛极一时的女权运动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克拉丽莎的人生抉择:“对异性恋的摒弃是向男性统治最直接的挑战,对男性中心社会更具冲击力,是对男人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的拒绝,而女性之间的爱恋才是构建女性自我意识的直接而有效的方式。”[7]克拉丽莎是一位追求独立自由的新女性,热衷于阅读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并因其新潮思想与挚爱的男友理查德发生争吵,最后导致分手。
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变成了如今永恒的追忆。对于克拉丽莎而言,她的眼角眉梢、身体和灵魂都镌刻着对理查德绵绵不息的爱恋。她的生活只存在于过去,永远地凝固在理查德站在她身后时灵魂的悸动中,永远地停驻在理查德深情的凝视时飞升融化的身体里。在生活中所有代表成功的一切都会在瞬间让她感到沮丧和不安,她不断地质疑自己的人生选择及现在的生活——平庸的岁月、朋友的忽视、叛逆的女儿、不平等的同性婚姻、这座窒息她灵魂的房子及所有的一切——是虚妄、无果和失败。而她生活的重心、曾经的男友理查德却正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这让她心如刀绞。有时,克拉丽莎疑惑如果她当初没有离开理查德,两个人是否能有一个美妙的未来?有时,她又希望逃离现在的生活,抛弃所有的烦恼,回到儿时与父母度假时窗外有树影婆娑的房子里。可是,现实是理查德需要她,她愿意也必须承担起不断唤醒理查德濒临死亡的生命之魂的责任。克拉丽莎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担负着对理查德日复一日、持续多年的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支持。可理查德却痛苦难当,他为自己的爱人克拉丽莎而活,无以言表的情感铸就了啼血的诗篇,这部获得卡鲁塞斯奖的诗集凝聚了理查德生活的全部。当他完成夙愿,在与爱人做最后的道别后,从窗口倾身而落,他带着欣慰的笑容、满足的笑容、胜利的笑容,他摆脱了枯朽的肉体,却铸就了一颗圣洁、感激的自由灵魂飞升而去。
理查德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此之后,“她已不再是达罗卫夫人。现在已经没人再叫她达罗卫夫人了。”[2]216克拉丽莎面临着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建构自我的困境,她需要割舍过去,从曾经是她生命和灵魂的理查德的世界里走出来,把那个世界的门轻轻关闭,把美好的回忆和憧憬、时时刻刻浸润心灵的爱和侵入骨髓的痛化为一种感觉,珍藏起来,细细咀嚼、慢慢回味……可理查德没有真正离开,他的爱和希望熔铸在克拉丽莎的生命之中。克拉丽莎理解理查德的抉择,她知道理查德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为了归还她的自由之身和自由之魂,希望她拥有一个完整的自我,而不是一个被他所累,穿梭于同性恋人和昔日男友之间情感困惑的女人。理查德用生命诠释的对克拉丽莎的爱及临终时的幸福、满足将激励克拉丽莎珍视生命,快乐前行,使克拉丽莎成为理查德所希望的,一个事业有成、拥有幸福家庭的人,“魅力无穷,前程似锦”[2]9。
克拉丽莎是伍尔夫的幻想和劳拉困惑的终结。她没有像伍尔夫一样疯癫、绝望,最后走向自杀和毁灭,也没有像劳拉一样迷茫、自私,最后选择逃避和冷漠。她选择了希望和努力,她的身上体现了女性对爱的渴望、对家庭的需求、对女儿的期冀、对自由的追求与对责任的担当。虽然迷惘犹在、困惑依存,但她已经完成了女性丰富多彩的一个人生阶段,卸去了达罗卫夫人的灵魂依附,以全新的自我面对未来。
《时时刻刻》是一部关于现代知识女性的小说,三个女人、三个时代、三种完全不同的处境,却同样面对“牢笼”之惑。作者迈克尔·坎宁安像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是一位卓越的心灵捕手,巧妙地运用《达罗卫夫人》将三位女性的命运连接在一起。达罗卫夫人在家庭中的苦闷、彷徨及隐秘的同性恋情结由完全回归家庭的劳拉演绎,而达罗卫夫人超越时空的自由梦想和她同性恋之欲的实现则由20世纪末女权运动影响下独立、自由的新女性克拉丽莎来呈现。可见,《时时刻刻》延续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罗卫夫人》这部小说里所关注的女性内心世界,并对女性复杂、隐秘的自我进行了多维阐释,通过对伍尔夫女性思想的冷峻反思、批评和颠覆,将现代知识女性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置于历史和空间维度上去考察,引导读者思考并深入挖掘女性“牢笼”之惑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现实意义,引发社会正视女性对自我发展空间的诉求。“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之一”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了“女人后天形成论”。这一观点令欧美乃至世界震惊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是传统的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造就了女人。”[8]世界是男性与女性共生共存的地方,在一个禁止具有独立自我意识女性发声的失衡的社会里,受伤的不仅仅是女性自身,男性同样也是受害者。同时,女性的绝境也反衬出世界的残忍和社会的扭曲。经历了二十世纪战争的洗礼和各种哲学话语的碰撞涤荡之后,人类社会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刻,女性将在新的世纪里理性又充满希望地发现一个新的自我。
[参考文献]
[1]Virginia Woolf. Granite and Rainbow[M].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8.
[2]Micheal Cunningham. The Hours[M]. New York:Picador USA,2000.
[3][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海浪[M]. 曹元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13.
[4]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7.
[5][美]贝蒂·弗里丹. 女性的奥秘[M].巫漪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32.
[6]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94.
[7]葛尔·罗宾.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M].李银河,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192.
[8][法]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曹金钟孙琦〕
历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