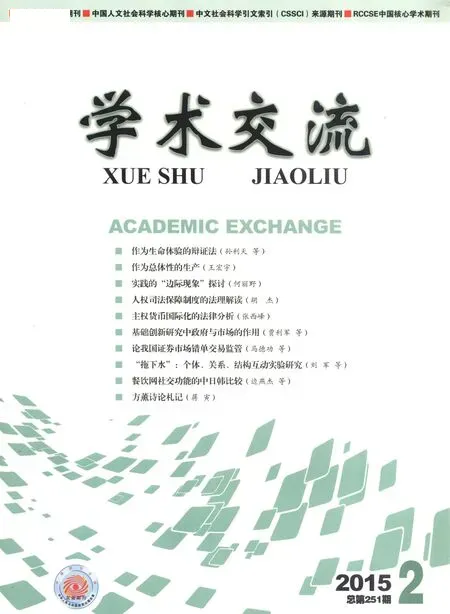“美丽中国”语境下“旁观者”现象透析
2015-02-26秦文,郭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和思想状况调查研究”(14ZDA059);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阶段社会公众的精神生活水平调查研究”(12AZD00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营造全面深化改革的良好社会环境研究”(2014XAE001)
“美丽中国”语境下“旁观者”现象透析
秦文,郭强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现代性的展开,既昭示着科学技术的伟大变革带来人们生活世界的日新月异,也显现出工具理性的大肆扩张造成人的主体性丧失与主体间疏离的负面后果,“旁观者”现象便是其衍生品之一。随着世俗主义、自由主义的纷至沓来,自然的神秘面纱被揭除,曾经坚固的道德信仰消散于无形,价值规约失去载体,在理性与常识的控制下,受情感支配的道德冲动被抑制,移情唤起的动机被搁浅,“旁观”成为理性计算与常识判断后的选择。在相互依存的生活空间,“旁观”不仅是一种耻辱,更是一种罪恶。因此,从旁观者向行动者转化,既应在理论的维度上重塑道德信仰,重建主体间的信任与关怀,在社会共同体中形塑自我,还应着眼于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中,大力培育和谐、友善、互助的核心价值信仰,通过公民性社区的建立增进成员间团结,并发挥司法的能动性,最大限度地维系伦理道德底线。
[关键词]美丽中国; 旁观者; 道德
[收稿日期]2014-05-14
[作者简介]秦文(1978-),女,山东济宁人,讲师,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社会学研究;郭强(1965-),男,河南商丘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2-0160-07
Abstract:The expansion of modernity not only shows the ever-increasing changes that great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ing about our colorful daily life, but also illustrates the negative result caused by adults' loss of subjectivity and their alienation among subjects after over-expanded instrument reason, so "bystander" comes to be one of its derivatives. With the coming of secularism and liberalism, mysterious veil of Nature is revealed, strong belief in morals dissipated, regulation of value lost. Under the control of reason and common sense, emotion-controlled moral impulse is dominated, and motive evoked by empathy is stranded, "bystander" became the option after reasonable calculation and judgment from common sense. In the mutually-depended living space, "bystander" means both a kind of shame and an evil. Therefore, conversion from bystander to actor needs a rebuilding of morals in theory and that of trust and care among persons, as well as a reshaping of social communities. During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beautiful China", we should take efforts to foster the core value of harmony, kindness, mutual assistance.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citizen communities, their members can enhance solidarity; judicial activism can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to maintain the bottom line of morals.
鲁迅先生曾用“一群鸭子”鲜明刻画了“旁观者”的冷漠形象。面对世风日下、国将不国的社会现实,梁启超先生也曾发出“四万万国人无血性”的悲恸之声。当今时代,从臭名昭著的美国吉娣·格罗维斯案,到中国佛山小悦悦案,对于旁观者的情感冷漠与人性异化的讨论从未停歇。社会学家鲍曼在探讨旁观者现象时,引用心理学家佩特卢斯卡·克拉克森对旁观者的定义,即当他人需要帮助时,他并没有积极地行动起来。进而他论证道:“如果一个人见证了一个有种族歧视、厌恶妇女或憎恶同性恋者的笑话而没有对抗它,那么,他就是旁观。让一个朋友酒后开车就是旁观。如果你没有面对或帮助因精神紧张、精疲力竭或吸毒而伤残或受损的同事,那么,你就是在旁观。”[1]215因此,通常所谓旁观者,即那些对于身边发生的不幸,选择消极观望,退避三舍,没有积极采取行动的人。在拥挤的世界中,人们之间彼此相互依存,一旦否定了这种存在,或贬低这种存在的实际意义,或拒绝它的打扰,声称我们无能为力,就是采取了“旁观者”的态度。网络信息化时代,人们彼此之间的依存度更加紧密,无论是否承认,责任就在那里,邪恶与不义所造成的现实危害已不局限于个人。选择了旁观者立场并不会令我们每一个人感到幸运,而是深陷道德焦虑与困惑,一种由羞耻感和无助感引起的痛苦油然而生。面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越发感觉到自我能力的欠缺,人际关系的疏离,不确定性与不信任感令我们感到巨大的生存压力。我们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我们面对着一个无法控制的世界。
一、 “旁观者”现象的理论观照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物质财富极大增加的同时,个人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为利益厮杀的漩涡中,道德情感沦丧的危机向人们袭来,基督教以“仁慈”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体系受到世俗的、功利的学说的挑战,市场经济的勃发与工商业的繁荣,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伦理道德的衰退、道德情操的沦落。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哲学家表达了对正义、美德的极大关注。“旁观者”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角度,以独特的思维与视角,对“旁观者”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
(一) 亚当·斯密的同情理论
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以“情感、秩序、道德”构建起一个广义的道德哲学体系框架,并由此奠定了美德伦理学的基础。斯密对于“旁观者”现象的分析,集中于从人性的角度来探讨。他认为同情心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敏感的旁观者甚至能对当事人的任何一种遭遇都感同身受”[2]3。当他人处于不幸或痛苦的状态,我们会心生怜悯或同情,即使我们不是亲身遭遇,但与生俱来的同情心会令我们如同置身于他人的不幸遭遇中,也会感到沮丧与悲伤。斯密认为,即使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或者藐视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的罪犯,也同样具有同情心,只是感性的、善良的人会更加敏感。每一个人在遭遇逆境的时候,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关心,而一旦这种希望没能付诸实现,则会陷入失望的痛苦。得到爱和帮助,令人感到快乐。斯密倡导旁观者能够将心比心地体谅当事人的心情,一个铁石心肠、麻木不仁、自私自利、对他人的欢乐和痛苦无动于衷的人,是面目可憎的。“人性的至善至美就在于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在于克制我们的私心,培养公正无私和慈善博爱的情操。唯有如此,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上的沟通才能和谐,也才能有情绪的优雅合宜可言。”[2]14斯密从人性角度阐释的同情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美好生活图景,令我们看到从旁观者转化为行动者的人性基础。
(二) 施托布的社会行为理论
施托布以社会行为理论来解释亲社会行为是怎样产生的,社会行为理论是把价值取向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试图形成道德行为的综合理论。社会行为理论认为,人在发展中形成了各种动机,而人的行为多数是以目的性为特征的,所以应侧重于探讨追求期望的目的动机。目的是个人追求的最终状态,是由相互联系的认知网络组成的,其中包括与对结果的评价相关的信念、思想和意义。目的是潜在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激活。目的处于潜在状态时,依据其对个人的价值或重要性,按层次排列。环境(包括内在的环境)条件可以同时激活一个、两个或多个目的,并且激活的程度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把价值取向看作是道德领域中的个人目的,亲社会价值取向则是利他和不伤害他人的个人目的。研究发现,人的亲社会价值取向越强,在特定情境中被激活的可能性就越大。亲社会价值取向体现为两种动机源:一是作为利他的无私行为的动机源,其目的在于帮助他人,是以他人为中心的;二是以规则为中心(rule-centered)的道德取向为特征的动机源,目的在于坚持行为规则。所以,两种道德取向的目的不同,并且对行为产生不同影响。亲社会行为多数是由利他主义引起的,移情是利他主义的直接根源,移情的唤起有助于利他行为动机的产生。做出移情反应的个体更加聚焦于他人的幸福。亲社会行为不全是利他主义引起的,助人行为某些时候也存在隐蔽的利益计算。知识、职业、社会适应、自我防卫、提高自尊以及价值表达都可以成为助人的动机,而只有价值表达才可以被称为真正的利他主义。
因此,根据亲社会行为理论,旁观者转化为行动者在心理动机上存在高低之分,或者可称为高参与度的行动者与低参与度的行动者。尽管二者都表现为助人的行为,但是在动机方面却有着利己与利他的区别。高参与度的行动者具有更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更为完善的道德人格。
(三) 拉尔夫·费尔夫的常识理论
拉尔夫·费尔夫认为,人类社会的非道德化倾向在于常识代替了情感,因而变成了错误场合的理性。常识成为人们说话做事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遵从情感、美德与信仰的热情为冷静的分析、理性的判断所取代。“确信常识、情感、科学和宗教可以相互替代的论点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它认为理性取代了宗教道德,也取代了情感道德。”[3]207个人在现代生活中的困境与“非道德化”过程中所特有的疑虑、困惑和不确定性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对人对事,常识引导人们小心翼翼、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常识拒绝情感的介入,也同样拒绝恪守信仰的必要性。常识珍视感觉,并且明确地赋予物质很高的价值。当常识战胜情感、宗教、道德,成为指引我们行动的准据法则时,人们彼此之间的界限会更为清晰。常识的独占上风,使得基于情感的同情、移情唤起动机逐渐退隐,人们变得越来越功利化、行为也越来越谨慎。扮演“旁观者”的角色,成为符合常识判断的理性选择。
二、 “旁观者”现象产生的社会机理
(一) 原子化个体与陌生人社会
现代性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将人类从家庭、村落、宗教和弱小的共同体的严格控制下解放出来,为个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机遇,开辟了灵活多变的生活道路。[4]85传统社会温情脉脉的人际网络被精于计算的、冷冰冰的货币关系所打破。个体所赖以依存的共同体濒于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原子化个体的独立存在。分享、互助、相互允诺的和谐社群关系破裂,社会生活场域成为陌生人的聚集场。现代人生活的归属感与意义感逐渐丧失,在快速切换的生活场景中,精神的重压与失落感、紧张感、焦虑感向人们袭来,个人生活失去开阔的视野,内心越发孤独与充满危机感,原子化个人终被抛入冷酷而又充满敌意的黑洞。封闭的内心陷于平庸、狭隘,极少关注他人与社会。“肤浅、情感和凡俗的单调、时间的拼接汇成了不连续的碎片”[5]148,陌生人之间飘忽不定、没有承诺的关系,使得社会场域中个体的每一次相遇都是偶然的,交往是浮于表面的,相互间保持戒备,小心翼翼地计算着自己的每一步行动。齐美尔曾在对孤独症候人群缺乏的道德良知分析后认为:“在极为孤独之时,不管是某种上帝的戒律也好,也不管是自己的幸福也好,不管是某个其他人的意见也好,也不管是历史的形势也好,都一点儿也谈不上深入道德的良知。”[6]354在陌生人的社会体验中,无私的爱与包容,以及基于这种情感而产生的同情、关怀,便无从产生。在现实处境中,常识提供的行为准则代替道德规范控制着个体行事方式,冷漠与理性代替了温情与感性,道德规范变得空洞无物,人们的共同情感日益衰败,神圣的信仰与传统伦理规范被不断贬低,人们的自我存在感与社会归属感渐趋衰退。
(二)非确定性与信任缺失
鲍曼对布尔迪厄所描绘的“永恒的不确定状态即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某些人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和强烈的‘无法控制现在’的感觉”有如下观点:“不确定性萦绕在流动的持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因此团结起来形成一致的对抗行动,而是不断裂变成分化的个体。”[7]53伴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到来,曾经紧密结合的共同体纽带逐渐分裂,在流动的持续变化的社会中,人们生存的稳定感与安全感在自我的确证与自由的追寻中受到挑战。缺乏人情味的和随随便便的交往,代替了从前浓厚的、面对面的关系。当上帝的神圣感被驱散,自然的神秘面纱被揭除,曾经坚固的道德信仰消散于无形,价值规约失去载体,人与社会间的张力不断加大,人们处于无根基的生存状态,生活中的可控制性、确定性和安全性的理念濒于崩溃,社会交往中的不信任危机陡增,人与人之间赖以维持信任关系的基础发生动摇。鲍曼曾对信任评述道:“信任是一切理性的筹划和满怀信心的行动必须具备的不可分割的条件,但是它却飘忽不定,寻求足够坚实的基础以求稳定是徒劳无益的。”[8]53面对彼此之间的信任危机,人们时刻提示自己保持清醒与冷静,对他人、对社会充满了防备与戒心。一种排除情感干扰,时刻保持理性的行为准则支配着个体的行动与人际间的交往。借由产生同情与关怀的情感冲动被理性所抑制,而这种冲动恰恰是移情唤起的本源,是利他行为产生的动机,也是履行道德责任不可或缺的正能量。理性时刻提醒社会个体保持克制,压制情感。当面对非确定的社会、非确定的他人、非确定的行为结果时,不要轻易相信他人,并且也不要期望自己被他人所信任。于是,人们不自觉地成为他人和社会的“旁观者”,同时也帮助他人扮演“旁观者”的角色。持续的不确定性和无助会产生大量的攻击性能量,并渗透进社会纽带网。团结与协作、温馨与友善在攻击性能量的作用下濒于破碎。
(三)工具理性的主导与道德视野的褪色
旁观者现象所透射出的工具理性主导模式,是指行动者在理性的支配下,出于功利与效率的目的展开行动,而人的情感与精神价值被行动者漠视。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人们积极追求利益与效率最大化的目标,工具理性被推向极端,人们日益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困境,道德责任变得可有可无,关心社会与他人的初始情感被陷于极端的工具理性所摧毁。社会学家查尔斯·泰勒在论及现代性的隐忧时将工具理性列于其中,其所指的工具理性,是一种我们在计算如何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是工具理性成功的度量[9]6。理性地计算得失成为行动的准则,而几乎或根本不用顾及这些活动对他人生活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鲍曼表达了社会学家对社会现实的担忧,即一旦人类走上(或被迫走上)追求秩序和理性化的道路,事物的终极价值就会被忽视。韦伯极其担忧个性受到缓慢而无情的摧残,涂尔干也同样极其忧虑道德规范受到的威胁[1]10。皮特林·索罗金、基思·泰斯特等社会学家集中探讨的“非道德化”在现时代有了更为充分的表现,与泰斯特的表述相契合的是,现代学者对于“非道德化”的关注,在于“非道德化”使人类变得更加残忍,对他人漠不关心,这一现象的产生源于理性的错位。在理性的控制下,受情感支配的道德冲动被抑制,没有了相互间的道德义务与长期承诺,行动的有效性与最终意义被认真地计算,对自身的生命意义与现实处境周密考量,拒绝承诺性的行动成为理性计算的结果。拒绝承诺并不费力,旁观者总能为否认罪恶找到一个适当的借口,然而事实上,逻辑的完美根本无法消除良心的谴责,困惑迷茫的自我面临道德上的极大困境。正如鲍曼所说:“陷入旁观者的角色并不是令人满意的状态。道德忧虑就是旁观者要承受的巨大折磨。”[1]19
三、从“旁观者”到“行动者”的理论构建
(一)践履美德,塑造德行人格
亚当·斯密在论及美德与个人幸福的关系时,提到三种美德,即正义、仁慈与审慎。“正义使我们不去伤害别人,慈善鼓励我们为他人的幸福而奉献,审慎则让我们自行约束,从而使我们免遭各种伤害。”[2]188当我们秉承内心的良善与公义行事,并对自己的行为作客观裁判时,我们会自觉践履这三种美德,并会为适宜时机奉献他人的精神与行为感到幸福,为未尽到道德责任而深感愧疚,这本质上是行动者的德行人格体现。在这三种美德中,正义是最为基本的道德义务。遵循正义准则,是人最基本的品德,尽管不会受到过多褒奖,但违背正义准则,则会受到严厉制裁。仁慈与同情、怜悯、慈悲大致相同,对他人悲苦与不幸产生的情感共鸣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敏感的旁观者能够对他人的快乐或痛苦感同身受,并产生类似的情绪。相比正义而言,仁慈是高位阶的道德义务,仁慈的品行,会受到较高的道德褒奖,缺乏仁慈的行为,只能引起厌恶和反感。相比前两种美德,审慎则较为中立,当审慎与仁慈、正义相结合表现出来的时候,则是最为完美适宜的美德,是将缜密的思维、智慧的头脑与高尚的心灵结合为一体的美德。然而当审慎与恶行或不良品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则会加剧后果的恶化。如果说正义与仁慈的美德具有利他性,那么审慎的美德则更表现为利己。正义使我们不去伤害他人,仁慈鼓励我们为了他人的幸福而奉献,审慎则让我们自行约束、谨慎行事,从而使我们免遭伤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旁观者”转化为“行动者”,要求我们时刻关注自己以外的人或事物的处境,因而需要具备同情心或仁慈的美德。美德的结果有时符合人们的意愿,有时则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在利益动机的驱动下,行善者践履美德可能遭遇违背初衷的后果,然而人们对美德的赞许不会因此而衰减,在一番关乎道德的激辩之后,美德的感染力会得到进一步升华,而践履美德的行动者则令人们充满敬意。因此,无论行动的结果怎样,受惠者是否理解并有所回报,高尚的行动者都会义无反顾地践履美德。人们赞扬美德,是因为它带来幸福与愉悦的感受,并给每一位社会在场者创造了安全感与信任感,让人们感受到共同体的温馨与安宁。与无私奉献的仁慈相比,审慎受到的尊重与赞美逊色不少。缜密的思维与谨慎的处事风格,往往会抑制情感,成为行动的障碍。但当正直的人将仁慈与审慎的品德结合在一起,也自然会塑造出理性适度的美德。
(二) 重塑道德信仰,实现社会有机整合
随着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趋于崩溃,神圣的宗教信仰从公共生活领域撤退,世俗化社会的突进,使得共同体及根植于共同体中的道德与风俗陷于崩溃,个人与自我之间的分裂、社会的分裂以及人与自然的分裂继而展现出来。与社会的分裂相关,价值观与信仰领域的分化成为现实,价值多元化成为现时代的表征之一,社会制度不再是人们共同体会到的信念和价值的表达。社会中的个体犹如散落的沙子,相互间的交往陷于利益化与程式化。因而从“旁观者”转化为“行动者”,需要激活社会个体的共同体意识与集体观念,这是产生同情与移情功能唤起情形的基础要素,当休戚相关的共同情感战胜工具理性与科学常识时,行动者才能正式出场。维系个体共同情感的绳索是爱、同情、关怀及彼此间的承诺,这便揭示了道德的开端,即“对他人的关怀——直至做出牺牲,甚至为他而死的关怀”,“与听到那无声的求助呼叫时的震惊时相同,他者的无助和脆弱,在裸露的面孔中暴露无遗”,“震惊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戏剧性地使所有那些理性考虑——在习俗和契约义务的世界中,沐浴于自我彰显之下——都失去了意义。道德人的诞生,是这样的自制:他/她是我的责任,而且只是我的责任。这就表明,我,只有我,应该为他/她的完整和幸福负责[5]61。将他者视为感情的目标,不只是同情或怜悯,而是建立在道德责任之上,承担着对他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在承担责任的同时,自我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在对他者关怀、担责的同时,自我的存在意义也得以体现。彼此间的承诺与互助,是搭建爱与信任共同体的基石。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应只是在常识和认知上被生产出来,而是从情感上被体会到。社会制度因人们的积极热情赞同而得到支持,社会的整合规范和行动导向表达了饱含深情的、集体创造的共同性,当个人成功的自我实现与社会整合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时,可以产生一种特别的能量:只有当个人在社会共同体中把自己的能力表达出来的时候,他才能与自己实现和解。而当个人在社会制度中从情感上重新发现他自己,这个社会才与他自身实现和解。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共同体的形成不仅自在地是目标,而且作为目标也必然是密切相互联系的[10]11。在个体化、世俗化的生活中,每个存在者面临诸多的选择自由,有机会尝试多样的生活方式,可以有多元化的价值追求,但同时也产生难以摆脱的孤独感与难以抑制的不确定感。一个凭借共同的道德信仰与公共意识建立的依赖、互助、关怀与支持的共同体成为个体找到归属感和存在价值的栖息地,人与人之间相互承担责任,尊重作为他者的个人,彼此间交互感知与承诺,努力将共享的多样性转变成人类团结,在共同理解与信任的集体中,每一个人都是积极参与的行动者。
(三) 惩罚道德罪恶,坚实从旁观者到行动者的转化路径
鲍曼曾提到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斯坦利·科恩的研究贡献,即科恩通过大量的制度选择及意识形态的注解,揭示了旁观者和作恶者具有极为隐蔽的、近乎不可见的共同点[1]212。邪恶的犯罪与冷漠的旁观者,从形而上的罪恶或道德罪恶的范畴而言,侵犯了绝对的人类团结,而这是所有道德的基石,因此,罪行与受难者的直接因果关系的缺失并不足以消除罪恶,因为无论何时,每一个人都要为他人承担责任,人不仅是生命意义上的存在个体,还是道德意义上的集体成员,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利益相关,共同维系着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克拉克森在诗作中称旁观者的道德冷漠行为无异于“仁慈的杀戮”。实证案例不断验证了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判断,旁观者的冷漠助长了作恶者的气焰,当旁观者面对施暴行为或者受害者的求助时,既不大声抗议也不予以积极的帮助,邪恶的行为与悲剧的结果终于难以避免。鲍曼列举雅斯贝斯、列维纳斯关于道德罪恶与形而上的罪恶的论析,认为前者论证了旁观者的道德冷漠与受害者的痛苦之间因果关系缺失,但不足以消除罪恶;后者则认为因果关系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每个人都要为他人承担责任[1]217。旁观者的道德冷漠不仅需要面对助纣为虐的指控,也面临着蜕变成作恶者的危险。雅斯贝斯指向的绝对的人类团结与列维纳斯论证的对他者的责任,都已成为现时代最为严峻的事实。将旁观者的过错予以法律的惩罚,明确旁观者因其道德冷漠而致的恶劣后果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谴责,是在利他的动机源丧失时,通过制定行为规则而明确的行动模式。相比价值表达的助人动机而言,依照规则的助人者并不是积极行动者,但是为了避免作恶者的行径得逞,也为了使受害者免于侵害,制定强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则成为必要的选择。在全球化的时代,面对他人痛苦的信息,每个人都是旁观者,以“我不知道”、“我力所不及”、“我尽力了”为托词否定自己的责任,并拒绝成为行动者是耻辱的,甚至是一种罪恶。“在相互依存的生活空间里,旁观者与同谋、帮凶、从犯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1]215
四、“美丽中国”语境下从“旁观者”到“行动者”的实践路径
(一)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提升大众精神境界与道德修养
现代生活的图景伴随着“社会性的终结”与个性的张扬展开。每个人都被赋予了专属自己的自由规划个人的生活,探寻自己心中的价值追求。价值的个体化和独立化确证了现代社会的进步,每个独立的个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价值观念并付诸行动,任何机构或个人无权干涉。然而这并不是说个体所做的价值选择都是合乎高尚道德的,尽管不能干涉价值选择的自由,但是从旁观者转化为积极的行动者,需要崇高的精神境界与坚定的意志力。讲信修睦、扶危救困、和谐共进既体现了人性之美,也体现了社会之美;既是我们应着力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准则,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美丽中国的题中之意。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念是从“旁观者”转化成为“行动者”的精神动力,因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实现这种转化所应依赖的主导路径。
鉴于此,我们应将中国五千多年灿烂文明中的传统文化所赋予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承下来,充分汲取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道德因子,倡导“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人文关怀精神,以“言忠信,行笃敬”的教导律己待人,以“知恩图报”的训诫回报行动者,从而夯实和谐社会、美丽中国的文化基底。其次,网络化、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离不开社会舆论与媒体的引导与传播,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与道德情操,在人际交往与耳濡目染中得以形成。“逐渐把别人视为‘我们之一’,而不是‘他们’,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详细描述陌生人和重新描述我们自己的过程。承担这项任务的,不是理论,而是民俗学、记者的报道、漫画书、纪录片,尤其是小说。”[11]7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加大道德榜样的宣传力度,将“见义不为”的道德冷漠与“恩将仇报”的丑恶行径公之于众,是鞭策“旁观者”转化为“行动者”的助推力。
(二)加强公民性社区建设,增进社区归属感与成员之间的团结
涂尔干面对社会成员分散、集体道德缺失及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失范现象提出“社会团结”的目标,并提出恢复社会秩序,建立社会团结。除了普遍的道德化之外,需要建立社区组织,将个人整合进这一组织和群体中,从而使个人不再孤立无援,在社群成员友善的关怀与帮助下激发个人的德行,发挥人性中最大的善,关爱他人与社会。涂尔干将社区类型划分为传统的乡情式社区与现代的公民性社区。从“旁观者”转化成“行动者”,潜在的支持力量来自于公民性社区的建立与社区成员间的有机团结。公民性社区突破了地域性的乡情社区,激发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以民主参与、履行公共义务为宏旨,推动现代市民社会与道德共同体的建立。
旁观者的道德冷漠与孤立的原子化个人可悲的自我关注直接相关,当全部视线聚焦在个人利益得失,无视他人及社会的切实利益时,成为行动者的参与热情全然消失。在庞大的现代世界里,每一位个体都是渺小的、脆弱的,面对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面对快速切换的生活场景,每一位个体都是孤独无依的。一个温暖、舒适、充满道德关怀的团体为我们所依恋。托克维尔曾就公民依靠集体的力量应对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的不公平现象提到:“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部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12] 636-637公民性社区的建设,使每一位个体进入到集体生活中,分享彼此的快乐,履行各自对集体的承诺,并由此获得自我认同感与集体归属感。在社区成员彼此守望、关系融洽的共同体中,每位个体都是积极的行动者,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入公共生活领域,在社群成员友善的呵护下激发出人性中的善与同情的本能,践行完美的道德人格。
(三)维护社会正义,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能动性
市场经济的理性人假说,为个人主义的现时代存在提供了充分的合理性,人性中的“自利”、“自私”之“恶性”被不断放大,甚至成为判断个体行为的“常识”。行动者的道德支援行为,在所谓依据“常识”的逆向推理下被否定,这已成为现时代社会公众扮演旁观者角色的无奈选择。在多数情况下,面对弱势的求助者,人的“同情心”在那一特定时刻极易被唤起,当情感战胜了常识,人们会自觉地选择成为行动者。如果借由所谓的“常识”,否定了行动者的善良动机,势必为旁观者的道德冷漠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从而致使社会个体间的疏离状态及个体与社会间的张力不断加大。因此,鼓励旁观者转化为行动者,不仅要大力弘扬社会正气,还应为旁观者向行动者的转化创造良好的道德舆论和法制环境。
在程序正义的维度下,最大限度地体现实质正义,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制裁和惩罚非正义的行为,就会严重削弱公民的法律信仰,使意志薄弱者突破道德底线,从而助长不义者的嚣张气焰。从法律角度而言,行动者与受惠者之间存在无因管理法律关系。无因管理法律制度,即在于通过法律确认无因管理的合法性,充分保障无因管理人的合法权利,因而体现了法律维护公平正义、倡导社会美德的价值追求。同时,对于社会上屡次出现的受惠者图赖行动者的恶劣事件,依据民事诉讼法律“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原则,受益者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利用司法的能动性捍卫道德底线伦理是有迹可循的,只有将人们的社会交往及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纳入秩序化的轨道,降低无因管理行为的风险,提高不义者的悖德与违法成本,才能有利于培育友善的群际关系,将“非如此不可”的道德强制性力量转化为“自愿性”的道德行为动机,激发个体道德中的“善性”得到充分发挥,进而推己及人,群起响应,建构和谐、美丽的生活家园。
五、结语
在纷扰喧嚣、充满利益冲突的现实中,面对脆弱与无助、侵扰与蛮横,很多时候人们选择了“旁观者”的立场。这充分透射出社会公众道德冷漠、人际关系功利化、社会沙化的时代病症。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道德的不确定性不断扩散,现已成为唱响和谐主旋律中最不和谐的音符。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甚嚣尘上,使道德的“道义感”、“义务感”日益淡化,“利益”成为个体自我建构的核心,旁观者的“明哲保身”、受惠者的“反诬图赖”、社会成员的集体良知麻痹,成为时下社会共同体瓦解、公共道德衰退的突出表现。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社会公众的道德风尚与文明素养,既关乎国家富强与社会安定,也是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每一位社会个体都应力争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行动者,社会成员之间应互相尊重、和睦友好,努力形成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将“友善”的个体道德行为规范内化为社会公众的核心价值信仰,心系社会、心系国家,互帮互助、诚信友爱,从而增进社会成员彼此间的理解与信任,在自我、自然以及他人之间建立共享、互助、宽容的合作关系,塑造崇高的生活境界与美丽的生活空间。这不仅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实现“美丽中国”伟大梦想的精神支撑。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杨程程,廖玉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1.
[3][英]费尔夫R W.西方文化的终结[M].丁万江,曾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4]吴玉军.非确定性与现代人的生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英]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郁建兴,周俊,周莹,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6][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M].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8][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M].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9][加]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M].程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10][德]阿克塞尔·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M].王晓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1][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2][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Probe into the "Bystander" Phenomenon in the Context of "Beautiful China"
Qin Wen, Guo Qiang
(SchoolofMarxism,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
Key words:beautiful China; bystander; morals
〔责任编辑:常延廷黄琦〕
语言文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