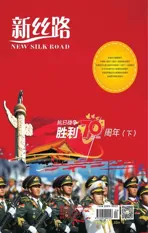试析托尼莫里森的叙事艺术风格
——以《宠儿》为例
2015-02-25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李 丹(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试析托尼莫里森的叙事艺术风格
——以《宠儿》为例
李 丹(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在叙述语言运用方面独树一帜,她的作品《宠儿》通过碎片化的叙事,魔幻的手法,音乐性的语言,相互映衬的场景,重现记忆,深入揭示了蓄奴制度下美国黑人肉体和精神上难以忘却的伤痛,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本文以该作品为例,试分析托妮·莫里森的叙事艺术风格特点。
托妮·莫里森; 叙事特点; 艺术风格
托妮·莫里森是一位杰出的非裔美籍黑人女性作家,199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她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出版于1987年的《宠儿》。在这部作品中,托妮·莫里森对1856年发生在逃亡黑奴玛格丽特·加纳身上真实故事进行了巧妙的重新加工,把一个陈旧的历史片段加工成了具有新的主题深度与内涵,充满艺术魅力的作品,展示黑奴的内心生活,从新的角度揭露奴隶制对黑人民族尤其是黑人女性心灵的戕害,表现了那些不曾诉诸文字的黑人女性的内心世界,深深打动了众多的读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本文拟从《宠儿》的叙事结构、叙事手法、叙事语言等方面对托妮·莫里森的叙事艺术风格作以分析。
一.叙事的碎片化
《宠儿》这部小说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方式,没有线性地展开情节,而是把不同时间、地点组合交织在一起,在现在与过去之间自由穿梭,让读者通过一个个叙事的碎片,拼凑、还原出完整的故事。
小说开始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一所整天闹鬼的房子——蓝石路124号,一位每日努力把回忆赶跑的黑人妇女塞丝,以及一个孤僻的女孩丹芙。与现时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的是多种层次的过去:有作为历史回忆的贩奴船的故事,有不同人物在昔日的农场“甜蜜之家”的种种磨难,有塞丝于逃亡途中生下丹芙的情景,有塞丝逃到辛辛那提后二十八天里黑人邻居们相聚的热闹以及从此后124号的孤立等等……这些过去的故事时而出现在人物的回忆中,时而杂糅在现时的故事里,仿佛成了正在发生的故事。这种过去与现在并置、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叙事手法巧妙地增加了小说的纬度与涵盖面,强调主人公塞丝等昔日黑奴在获得人身自由后,苦难却并没有结束,她的心灵仍然被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中,奴隶制使她的肉体饱受摧残,而为反抗奴隶制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痛苦的回忆就像老房子里的鬼魂,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她的心灵。这种碎片化的叙事方式能让读者感同身受,把这种痛苦总是围绕着主人公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碎片化叙事模式还体现在对小说的主要事件——塞丝杀婴的叙述中。小说的开头只提到124号有个被割断喉咙的婴儿鬼魂在作祟,提到“油一般浸透手指的婴儿的鲜血”(第5页)[1],让人不明原委;随后保罗·D和塞丝的谈话中,零星提到塞丝坐牢,那里的耗子什么都咬,却不碰塞丝的幼女丹芙,为什么坐牢却不得而知;丹芙的回忆中曾闪过童年伙伴的询问:“你妈妈不是因为谋杀给关起来了吗?她进去的时候你没跟着吗?”(第125页)[1]对于牢房的模糊回忆使丹芙意识到某种可怕事实的存在,于是双耳自动失聪,读者也因此和丹芙一样无法听到答案。直到把整部小说读了将近大半,读者方才明了,十八年前面对奴隶主追捕的塞丝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宠儿。
碎片化叙事手法在《宠儿》中的运用则巧妙地契合了小说的主题挖掘和人物塑造。首先,零星的碎片式叙事,避免了读者对塞丝杀婴过早做出判断,把这个充满复杂感情因素的行为和过去的故事交织叙述,使读者对这一骇人之举的历史及个人背景有了更深的了解。其次,整篇故事在叙述与逃避叙述不断交错,一方面增加了小说的悬念,另一方面也对应小说人物对不堪回首的往事的极力回避,吻合记忆压抑与恢复的心理机制,展示了“回忆重现”的真实过程。
二.故事的魔幻性
小说开始就描述了蓝石路124号闹鬼的场景:镜子一照就碎;蛋糕里出现了两个小手印;一锅鹰嘴豆堆在地板上冒烟;苏打饼干被碾成碎末,沿门槛洒成一道线;泔水桶被倒扣;在人身上冷不丁击上一掌……这些魔幻的场景几乎每天出现在屋子里,像是一个小孩的恶作剧,屋子里的女人“就像知道光的来源一样明晓这些暴行的来源”(第4页)[1];当塞丝一度向婆婆提出搬家建议时,贝比·萨格斯回答道:“在这个国家,没有哪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黑人死鬼的悲伤。我们还算幸运,这个鬼不过是个娃娃……我生过八个……我估计,个个儿都在谁家闹鬼呢。”(第6 页)[1]当一个自称宠儿的姑娘出现在124号时,不但丹芙和塞丝认为她就是还魂的宠儿,很多黑人邻居也断定这个没有掌纹的姑娘就是十八年前塞丝杀死的女儿还魂。显然,超自然和魔幻的东西被小说中的人物视为自然和日常的现象了。
成长于“熟知超自然”并且有着讲故事传统的黑人家庭的莫里森,从孩提时起就熟悉黑人民间文化中这些超自然和魔幻的成分。在她看来,超自然和魔幻反映了一种宇宙世界观,是黑人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其了解事物的另一种方式,源于非洲古老的宗教文化:死者与生者可以沟通,灵魂可以被召唤回阳间,生死之间没有界限。《宠儿》中运用的魔幻手法也是基于上述黑人民族宇宙观以及非洲古老的宗教文化,在西方主流文学创作中显得别具一格,匠心独具,具有独特的魅力。托妮·莫里森把自身的本土文化融入小说创作,以魔幻的表现手法抵抗权威话语提供的现实,对抗其文化殖民,以唤起本民族被湮没的种族记忆。
三.语言的音乐性
托尼·莫里森认为,音乐除了给处于底层、边缘的黑人以灵魂慰藉的原始功用外.还应担负着更多的作用。在她的创作实践中音乐成为了一种叙述策略,她常把自己的小说比作音乐,音乐与文字结合起来,引领读者进入声色俱全的阅读体验。而托尼·莫里森最熟悉的,莫过于爵士乐的重要分支——布鲁斯音乐。
布鲁斯音乐起源于过去美国黑人奴隶的圣歌、赞美歌、劳动歌曲、叫喊和颂歌,是南北战争后产生的一种民间演唱形式,它与黑人的种植园歌曲(劳动时集体合唱的无伴奏歌曲)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托尼·莫里森在《宠儿》这部小说中运用的语言也不时呈现出布鲁斯音乐的节奏感,如描写保罗·D和其余四十多名黑奴被拴在一条锁链上干活的情景就形象地模拟了音乐的鼓点:
在“嗨师傅”的带领下,男人们手抡长柄大铁锤,苦熬过来。他们唱出心中块垒,再砸碎它;窜改歌词,好不让别人听懂;玩文字游戏,好让音节生出别的意思。他们唱着与他们相识的女人;唱着他们曾经是过的孩子;唱着他们自己驯养或者看着别人驯养的动物。他们唱着工头、主人和小姐;唱着骡子、狗和生活的无耻。他们深情地唱着坟墓和去了很久的姐妹。唱林中的猪肉;唱锅里的饭菜;唱钓丝上的鱼儿;唱甘蔗、雨水和摇椅。
他们砸着。砸着他们从前曾经认识、现在却不再拥有的女人;砸着他们从前曾经是过、却永不会再是的孩子……(第130页)[1]
文中反复出现的“唱着”、“砸着”产生了鼓点似的节奏,恰似铁锤的一次次抡起、砸下,回荡着黑奴们的愤懑和对自由生活的期盼。同时,这段描述又一次展现了启应式轮唱的魅力,描摹了黑人们依靠音乐的力量在逆境中求生存的生动画面。
布鲁斯音乐歌词中一般会包含诗一样的语言,并且不断反复,然后以决定性的一行结束。旋律的进行以和弦为基础,使人有着苦乐参半、多愁善感的感觉冲击。《宠儿》的叙事语言深受布鲁斯音乐的影响,多处呈现音乐的美感。例如《宠儿》后半部分大段的内心剖白,叙述方式十分独特:
宠儿
你是我的姐姐
你是我的女儿
你是我的脸;你是我
我又找到了你;你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你是我的宠儿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我有你的奶
我有你的笑
我会照顾你
你是我的脸;我是你。你为什么离开本是你的我?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再也不要离开我
你再也不会离开我
你走进水里去了
我喝了你的血
我带来了你的奶
你忘了微笑
我爱你
你伤害了我
你回到了我的身边
你离开了我
我一直等着你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259页)[1]
这段内心剖白,全段没有标点,类似歌词,以塞丝、丹芙、宠儿三人不同的口吻,反复吟唱,最终使三人的情感完美交融在一起。这种表达方式类似布鲁斯音乐的即兴演唱风格,如泣如诉,随性而凄美,像是音乐中几个演唱者分别演唱着自己的声部,互相唱和,达到和谐的效果,使得读者能更真切地感觉到几个主人公内心的爱与痛。
四.场景的映衬化
塞丝杀死女婴的场景,是本文故事叙述中的重要环节,托尼·莫里森使用独特的叙事方式,用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叙事角度来叙述,并分布在小说中不同的位置,这些场景相互映衬,一点点地还原,让读者印象深刻,产生深深的共鸣,对书中人物的遭遇产生深刻同情,同时,对叙事者的内心世界进行一层层深入的剖析和了解。“每个人虽然讲的是同一事件,但都不是完整故事,而是以不同层面为故事提供和积累了互为补充的信息。”[2]
塞丝杀婴事件首次叙述时,读者首先看到的是追捕塞丝的奴隶主“学校老师”的叙述场景:
“一个发疯的老黑鬼拿着把斧头站在木头堆里。你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疯子,因为他在咕哝着——发出低沉的、猫一样的呼噜声……”
“里面,两个男孩在一个女黑鬼脚下的锯末和尘土里流血,女黑鬼用一只手将一个血淋淋的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手抓着一个婴儿的脚跟。她根本不看他们,只顾把婴儿摔向墙板,没撞着,又在做第二次尝试。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就在这群人紧盯着面前的一切的当儿——那个仍在低吼的老黑鬼从他们身后的屋门冲进来,将婴儿从她妈妈抡起的弧线中夺走。”
“事情马上一清二楚了,对‘学校老师’来说尤其如此,那里没什么可索回的了。”(第178页)[1]
接着,斯坦普·沛德叙述这一场景。读者了解了事件发生前的宴会,看到了塞丝当时“怎样飞起来,像翱翔的老鹰一样掠走她自己的孩子;她的脸上怎样长出了喙,她的手怎样像爪子一样动作,她怎样将他们个个抓牢:一个扛在肩上,一个夹在腋下,一个用手拎着,另一个则被她一路吼着,进了满是阳光,由于没有木头而只剩下木屑的木棚屋……那里除了铁锹什么也没有——当然,有锯子。”(第188页)[1]
最终,读者又看到了塞丝本人的重现这一场景,“她蹲在菜园里,当她看见他们赶来,并且认出了‘学校老师’的帽子时,她的耳边响起了鼓翼声。小蜂鸟将针嘴一下子穿透她的头巾,扎进头发,扇动着翅膀。如果说她在想什么,那就是不。不。不不。不不不。很简单。她就飞了起来。攒起她创造的每一个生命,她所有宝贵、优秀和美丽的部分,拎着、推着、拽着他们穿过幔帐,出去,走开,到没人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去。到那里去。远离这个地方,去那个他们能获得安全的地方……”(第195页)[1]
以塞丝的视角重现这一幕,使读者对当时场景中塞丝所做的反应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一骇人之举正是一位母亲在剥夺黑人做人、做母亲权力的强大制度下,一次不顾代价的反抗,一种深沉的母爱的表达。
莫里森使用多个场景为故事提供多层面解读,目的是为了消解白人主流话语对黑人历史的叙述,补上缺失的黑人话语。在对杀婴事件的叙述中,读者首先被迫接受奴隶主的话语,在这个话语中,塞丝等黑人表现出“发疯”的动物般的表征,其行为无法用“人”的标准衡量理解,带着明显的种族偏见。相比之下,黑人男性斯坦普·沛德的视角更具同情性,更接近客观,但它仍然缺乏从深层次的心理感受上挖掘蓄奴制对黑人女性的戕害。只有当塞丝打破“失语症”似的沉默,直面惨痛的过去,参与叙述时,这个故事才获得完整的叙述,它的深层内涵才彰显出来。
五.象征的多重性
莫里森还善于使用象征的艺术手法,并且她笔下的象征意象是多重的,复杂的,善于表现出多种感情,引起读者多重揣测的,具有深意。例如,本文中的主人公宠儿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
第一重,还魂的女儿。
她像宠儿死而复生的冤魂。“她的皮肤是新的,没有皱纹,而且光滑,连手上的指节都一样”(60页);“丹芙看见了那个东西(指锯痕)的一端”;“在阴间我的名字就叫宠儿”;“你回来干啥?”宠儿莞尔一笑。“看她(塞丝)的脸。”(88页)[1]她知道塞丝有一对水晶耳环,正是曾经逗着那个叫“都会爬了”的小女婴玩的东西。这样前后印证的描述,让人更加相信宠儿就是那个还魂的女儿,增加了故事的魔幻性,同时也加深了读者对宠儿的悲悯。
第二重,塞丝的母亲。
宠儿“也就十九、二十岁,长的又苗条,可她行动起来却像个更重更老的人:扶着家具,用手掌托着脑袋休息,好像它对于脖子来说太沉了。”(66页)“宠儿埋怨一句,塞丝道歉一声。那年长女人的格外努力所博取的欢心也减少了。”(287页)[1]正如文中所示,塞丝母亲的脾气从未好过,因为塞丝从来没有见过她笑;宠儿的撅嘴与无法识辨的微笑与塞丝母亲戴过马嚼子后撅嘴形成的“笑脸”也像极了。宠儿的形象总是步履蹒跚,但对塞丝颐指气使,脾气暴躁,这个形象也象征着塞丝的母亲,被侮辱、被奴役、被吊死,要通过身体上的烙印才能被认出的老黑奴。
第三重,黑人的过去。
宠儿还象征黑人的过去。当丹芙问宠儿“那边什么样儿,你过去呆的地方?”宠儿回答“漆黑”,“滚热”,“没法呼吸,也没地方呆”,“哪儿有好多人。有些是死人。”当丹芙问她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宠儿回答:“我等啊等,然后就上了桥。”(第89页)[1]众所周知,奴隶贩子从非洲把黑奴贩卖到美洲大陆,要通过海上长时间的漂泊,为了节约成本,尽可能多的搭载黑奴,他们强迫黑奴紧挨着躺在黑暗的船舱里,不见天日,直到上岸,很多黑奴在贩卖的途中就因为环境、疾病等原因死去了。宠儿与丹芙的对话,运用的象征的手法,精确的用词,寥寥数笔,仔细读来,既象征18年前被母亲所杀的宠儿、被奴役的塞丝的母亲,又代表着当年被贩卖到美洲来的死在船上的“六千万甚至更多”的黑奴。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描写,实则是对白人的历史罪恶的血泪控诉,饱含愤怒和哀伤,让人对黑奴的血泪史感同身受。
作者通过宠儿这个人物形象,勾连历史的记忆,勾连其他的人物回忆,完成宏大的历史叙事,使人物的象征意向与魔幻式叙事手法完美结合并相得益彰。
再如,“甜蜜之家”也有多重象征意义。
第一重,甜蜜的爱情诞生之地。
在甜蜜之家,塞丝遇到了自己的爱人,相恋、结婚,有了爱情的结晶,正是这一连串甜蜜的幸福为小说中的悲剧情节做了很好的铺垫。
第二重,充满邪恶与压迫之地。
和“甜蜜之家”的名字相反,处在南方种植园区的“甜蜜之家”并非黑人的乐土而是一座地狱,在这里,奴隶们过着非人的生活,白人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在这个地方,塞丝的背上留下了“苦樱桃树”疤痕,被夺走了乳汁,丈夫黑尔目睹这一切变得精神崩溃……奴隶们意识到,“甜蜜之家”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它代表着邪恶与压迫。
另外,“甜蜜”代表着黑人奴隶对以往幸福生活的回忆,也代表着黑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这种对甜蜜幸福生活的追求,才促使塞丝带着儿女逃亡,正是这种对自由的渴望,才有了塞丝为了儿女自由所做的“解脱”。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托妮·莫里森在《宠儿》这部小说中,汲取了黑人民间口头文学、布鲁斯音乐所特有的营养,结合西方主流文学的叙事模式和叙述话语,用碎片化的叙事、魔幻的故事、音乐性的语言、相互映衬的场景、多重的象征表达了她作为非洲裔黑人女作家的独特体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叙述风格。她用沉痛、悲郁又充满诗意叙述语言来表现美国黑人的历史与文化,站在鲜明的民族立场上展示了黑人在过去和现在所遭受的奴役、歧视。“尽管她的作品往往表现最痛苦最阴暗的主题,她流光溢彩的文笔却使她的每一本书都诗一般富于激情和韵律。”[3]
[1]托妮·莫里森.宠儿.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2]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
[3]心航.纽约纸不贵:莫里森其人其书[J].读书,1994,(1).
李丹,女,出生于1979年12月,籍贯为陕西省汉中市。2002年毕业于陕西理工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本科,文学学士学位。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在职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陕西理工学院发展规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