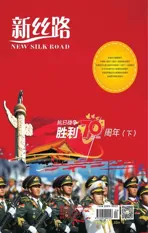《宠儿》之美与殇
2015-02-25孙博超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孙博超(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宠儿》之美与殇
孙博超(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托妮·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文学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她的第五部作品《宠儿》以其独特的艺术创作特点和语言表达方式斩获1987年“美国普利策小说奖”,以《宠儿》为代表,更使其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美国《纽约时报》曾评价这部小说是“一部闪耀当代、不可思议的非凡之作。”本文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及意境表达方式入手,探讨《宠儿》之美与殇。
宠儿;残缺;意境;美;殇
托妮·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文学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她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当今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位非洲裔作家和第二位美国女作家,她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作品《宠儿》便是其最具代表的作品①。该书于1987年一经问世,就立即轰动了美国文坛,次年即获得了在美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普利策小说奖”,2006年,《纽约时报》召集美国125位知名作家、评论家、编辑以及文坛泰斗等选出自己心目中的“25年来最佳美国小说”,《宠儿》以最高票数名列第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其为“一部惊世之作,难以想象没有它的美国文学是什么样。”阅读《宠儿》,一幅汇聚着美与殇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一、蓝池路一百二十四号的残缺
《宠儿》全篇以蓝池路一百二十四号为主要场所,这本是一个代表着自由的地方,南方的奴隶们来到了废除了奴隶制的北方,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与自由,这座房子原本应是充满希望和幸福的。然而,托妮·莫里森却剑走偏锋,小说首句即以“一百二十四号充斥着恶意”来开头,带给这座原本五彩斑斓的房子一片灰白的色彩。
与读者的期待不同,一百二十四号是残缺的,因为这里面居住着一群残缺的人们。这些人们虽然已经获得自由,但长年非人般的待遇与压迫使他们都患上了严重的“记忆缺失症”,他们的记忆是残缺的,而这些“残缺”与刻意的“遗忘”,变成了小说叙事的中心,是小说的主要意涵所在。
1.塞丝之残缺
塞丝是《宠儿》的主人公之一,也是牵引全故事的主要人物。这个有着“铁一般眼睛”的女孩是“甜蜜之家”里唯一的女奴,在“甜蜜之家”里的塞丝始终像一个骑士般捍卫着内心中对人格和自由的向往。于是,她在与黑尔结婚之时自己缝制“嫁衣”,在“学校老师”的蹂躏之下选择以逃跑的方式去对抗。在逃亡蓝池路一百二十四号的路途上,艰辛绝非常人可想,托妮·莫里森用女人特有的细腻语言来衬托现实的残酷,仿佛越是华美的句子,越是滴着带血的墨汁。塞丝的出逃是成功的,来到了一百二十四号的她虽然已经九死一生,但在贝比·萨格斯的照料下逐渐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时的塞丝对于新的生活是充满了憧憬与向往的,然而这种平静与美好转瞬即逝,“学校老师”和猎奴者的出现彻底敲碎了这个女人眼中“铁”,塞丝疯狂了,她对自由的绝望和对孩子们的爱让她亲手杀死自己不到2岁的女儿,这个已然“疯癫嗜血”的女人用惨无人道的惨烈方式击退了“学校老师”,也彻底撕裂了她自己,从此之后,她变得残缺不堪。
纵观小说,塞丝的残缺散落成无数的碎片,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属于在“甜蜜之家”的生活,这是在这里生活过的黑奴们共同之殇。“甜蜜之家”里最开始的主人加纳先生却给了他们对人格与自由的期待。塞丝在这里“自由”地选择了她的丈夫,孕育了他们的孩子,那时,她的眼中有着铁一般的光芒。然而,一切都随着加纳先生的去世和“学校老师”的到来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加纳先生曾经许诺给这些黑奴们的希望也变成了最终杀死他们的利剑,“学校老师”用他的方式诠释了人性最丑恶的样子,撕碎了塞丝所有的希望,坚硬的铁在塞丝的眼中日益黯淡起来。然而,最终摧毁她的,却是在第二个阶段中。
第二阶段即为塞丝来到蓝池路一百二十四号到她杀婴之后的时间里。在短暂的自由面临破碎的时候,塞丝选择了同归于尽。她残忍的杀害了自己不到2岁的女儿,杀婴的过程是惨不忍睹而又惊心动魄的,她充斥着塞丝对女儿绝望的爱以及长期在奴隶制度的摧残下已经“病变”的人性。她的癫狂与残忍将自己彻底击垮,从此这个女人再也无法直面自己的破碎。这种残缺的碎片,有对曾经非人生活不堪回首的记忆,更有着对无法面对亲手弑子真相的绝望。
2.保罗·D之残缺
保罗·D是“甜蜜之家”中浓墨重彩的第二个人物,也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他的残缺大多来自“甜蜜之间”的记忆。这些残缺相对于塞丝来说,是幸运的,也许没有经历过塞丝杀婴的震撼,保罗·D在整个故事里始终是一个斗士的形象。在“甜蜜之家”里,他与命运抗衡,向着自由的方向追逐。然而,他的出逃并不像塞丝一般幸运,先是被猎奴者擒获,目睹了西克索残忍被害,随后又经历了采石场的非人经历。一切的苦难与仇恨让保罗·D对自由的向往更加迫切,让他那抗击命运的拳头握得更紧。于是,在他再次从采石场出逃后,循着花的方向,他突破了各种生理上的极限去挑战命运的宣判,在他到达兰池路一百二十四号时,与精神已经残破不堪的塞丝相比,保罗·D拥有着的,是更多的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期待。尽管在小说末尾,保罗·D曾经也因为了解了塞丝的“残缺”而一度退缩,然而,他斗士一般的执着也最终使他战胜了自己的心魔,重新回来与塞丝共同面对寻找希望的人生。
3.贝比·萨格斯之残缺
贝比·萨格斯并没有让托妮·莫里森耗费大量的笔墨去粉饰,然而她也无疑是在兰池路一百二十四号中一个重要的残缺的人物。贝比的一生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与塞丝类似,我们可以将她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中,蕴含了贝比·萨格斯的残缺碎片:
第一个阶段是她的前半生。贝比·萨格斯的前半生与众多女奴一样,是破败不堪的,被当作是牲畜或者货品的生活充满了她的命运,她亲手丢掉了她被白人蹂躏后所生的孩子,用近乎冷酷的方式昭示着她对命运的不满。在这个阶段里,她的生命是黑色的。
第二个阶段是在她被自己的儿子黑尔赎出之后到塞丝杀婴之前。这段日子也许是贝比·萨格斯人生中最为自由的日子,她有了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也正因为这样,蓝池路一百二十四号才应运而生,贝比·萨格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除此之外,她还创建了“林间空地”,成为了获得自由的黑人们精神寄托的传播者。在这个阶段里,贝比的生活是彩色的。
第三个阶段发生在塞丝杀婴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贝比·萨格斯同塞斯一样,被彻底摧毁了,她心目中的“林间空地”,她所搭建的自由与梦想之家,都在塞丝滴着鲜血的双手中失去了颜色。
4.“甜蜜之家”后代们的残缺
如果说在前段提到的人物角色生命中的残缺碎片里都有“甜蜜之家”的影子,那么丹芙却是蓝池路一百二十四号中没有“甜蜜之家”记忆的一个人物,然而,这样一个本该拥有完整人格的小姑娘也有着属于她的残缺。丹芙对塞丝的爱是狭隘甚至自私的,她排斥一切塞丝可能去爱的人,包括保罗·D,甚至宠儿。丹芙最喜欢听母亲讲的是她出生的故事,因为那段故事中只有她和塞丝的存在。她排斥保罗·D的出现,为了赶走保罗·D她甚至期待着“鬼魂娃娃”的作怪。这种残缺的心理和性格,扭曲了这个本该天真烂漫的女孩。看到丹芙的残缺,总会不自觉的为一百二十四号冠上一份“咒怨”的标签,貌似这里真的是被上一辈人的残缺带来的怨气充斥着,使得但凡身在其中的人们都受到了“诅咒”。丹芙的记忆里没有“甜蜜之家”的非人生活,也没有塞丝杀婴的血腥画面,然而,她的残缺看上去既毫无根据又貌似水到渠成。归根到底,丹芙的残缺来自于一个时代的造就,没有经历过那些残忍画面的她却真实生活在这些拥有残缺记忆的人群中,被这些遗忘的碎片割伤了的丹芙,受到了一百二十四号的“诅咒”,而宠儿的出现,也使丹芙和塞丝一般,在自己的残缺中越陷越深。
5.宠儿的残缺
宠儿是全书的主角,这个塞丝用生命保护和摧毁的孩子。历来对于宠儿的形象就有着各种说法,最为主流的有三种:第一种,宠儿的现实层面形象是一位长期被白人幽禁蹂躏的黑人女奴;第二种是在超现实主义的魔幻层面中,宠儿被塑造成塞丝还魂的女儿;第三种则是历史层面的,死于中间通道的六千万黑人奴隶的代表。这三种形象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宠儿这个人物角色,但无论哪一种形象,归根到底依旧是残缺的。宠儿在整偏篇小说里多以无厘头的形象出现,无头无尾地贯穿在整个人物形象中,不论是她的出现和消失,还是她在一百二十四号中的所作所为。宠儿在小说中更多的其实是一种精神,一种非人的奴隶制度对一个种族在精神、文化和心灵上的扭曲、摧残与灭绝之后的产物。宠儿似乎是一个吸收了塞丝、保罗·D、贝比·萨格斯以及丹芙等千千万万个黑奴人性方面残缺之后凝聚而成的产物,托妮·莫里森用魔幻的手法将奴隶制度下对黑人种族的璀璨拟人化的表现出来,具有极强的震撼效果。
二、《宠儿》之美与殇
如果前文赘述的是《宠儿》的残缺,下面的分析则是从托妮·莫里森的语言意境与现实情感入手,欣赏《宠儿》之中的美与殇。
托妮·莫里森说过,“我想显示我们语言的美丽,她的韵律,她的比喻,她的诗意”。在莫里森的作品中,《宠儿》是最能体现她的语言艺术的一部作品②。整部小说语言诗意唯美,处处可见女性特有的细腻,然而,正是这种细腻优美的语言,恰恰衬托出了故事人物本身的绝望与殇逝。
1.追花的人
这段描写出现在保罗·D寻找北方道路的文段里。保罗心中的北方是“自由的”、“神奇的”、“好客和仁慈的”。这几个排比句将保罗·D对自由和希望的向往展露无遗,切罗基人微笑告诉他:“跟着树上的花儿走”。于是,保罗·D开始了他的“寻花之旅”。“他从山茱萸跑向盛开的桃花、苦楝花、山核桃花、胡桃花和刺梨花。最后他来到一片苹果树林,花儿刚刚结出小青果。春田信步北上,可是他得拼命得奔跑才能赶上这个旅伴。从二月到七月他一直在找花儿。当他找不到它们,发现再没有一片花瓣来指引他,他便停下来,爬上土坡的一棵树,在地平线上极力搜寻环绕的叶海中一点粉红或白色的闪动。他从未抚摸过它们,也没有停下来闻上一闻。他只是簇簇梅花指引下的一个黝黑、褴褛的形象,紧紧追随着它们的芳痕。”
这段对保罗·D寻花之旅的描写在语言运用上可谓精湛,在花海中寻找自由的方向,在这种意境里都飘着一股淡淡的花香。托妮·莫里森将这段故事镶配上花儿的美丽,从文字中还原出的画面是精美绝伦的,然而,当我们感叹过这种美丽的意境之后,却也可以强烈体会到这幅美景画卷背后的感伤。保罗·D那黝黑褴褛背影追逐着花儿的芳痕寻找着自由方向的画面竟是那样刺眼,自由对于他来讲,蕴含着更多因为迫切期待而又小心翼翼的情愫。这种感情体现在段落中使得保罗·D甚至不敢抚摸它们或者停下来闻一闻,只有拼命地奔跑去寻找自由的闪动,这种意境之美下的现实之殇融合得如此完美而凄美,不得不让人为之折服。
2.梧桐叶的记忆
对梧桐叶的回忆出现在塞丝的印象中:“猛然间,'甜蜜之家'到了,滚哪滚哪滚着展现在她眼前,尽管那个农庄里没有一草一木不令她失声尖叫,它仍然在她面前展开无耻的美丽。它看上去从来没有实际上那么可怖,这使她怀疑,是否地狱也是个可爱的地方。毒焰和硫磺当然有,却藏在花边状的树丛里。小伙子们吊死在世上最美丽的梧桐树上。这令她感到耻辱——对那些美妙的飒飒作响的树的记忆比对小伙子们的记忆更清晰。她可以企图另作努力,但是梧桐树每一次都战胜小伙子们。她因而不能原谅自己的记忆。”
梧桐树下挂满了吊死的黑奴们,风吹梧桐带来的沙沙声响伴着这些屈死的亡魂们原本是那么的阴森与晦涩,然而在塞丝的记忆中,托妮·莫里森却用柔美的语言勾画出了一幅唯美的油画作品,这种唯美的景色与现实的残酷仿佛无法相提并论,但在此处却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仿佛只有这样美丽的画面才可以缓解塞丝心中难以重现的伤痛,意境之美与现实之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出《宠儿》特有的艺术展示魅力。
3.苦樱桃树的印记
这个画面出现在塞丝的背上,是学校老师残忍的“艺术品”。书中描述出这是带着树干、树枝还有树叶的一颗苦樱桃树,她是塞丝永远不能够愈合的伤痛。就像塞丝的残缺一样,它们一点一滴黯淡着这个女孩儿眼中的光芒,最终为她蒙上了一层灰色的绝望。也许任何一个画师都无法描摹出这样的一幅画卷,这种带着绝望和枯败的苦樱桃树就像有毒的罂粟花一样闪着暗媚的光,投射在塞丝的心中变成一片永远不能碰触的禁地,它昭示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提醒着塞丝永恒的伤痛。托妮·莫里森用这种唯美的语言风格结合着现实残酷的伤痛构建出一种沉痛、悲郁而又充满诗情的意境。
综上所述,《宠儿》是一部关于忘却痛苦与罪孽,重新找回失落的东西并用爱将它们编织进新生活的小说③。它将所有的美与殇最终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中,并赋予了它们爱与希望的定义。正如小说的结尾中所述的场景一般:“渐渐地,所有的痕迹都消失了,被忘却的不仅是脚印,还有溪水和水底的东西。留下的只有天气。不是那被遗忘的来历不明者的呼吸,而是檐下的熏风,抑或是春天里消融殆尽的冰凌。只有天气。当然再不会有人为一个吻而吵吵闹闹了。”
[1]《试析托妮·莫里森<宠儿>中的人物宠儿》,张慧,哈尔滨工程大学,2007
[2]《<宠儿>中的黑人男性奴隶话语分析》,章汝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3]《走出历史的魅影》,王湘云、朱磊,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2007
[4]《宠儿》,托妮·莫里森著,潘岳、雷格译,南海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