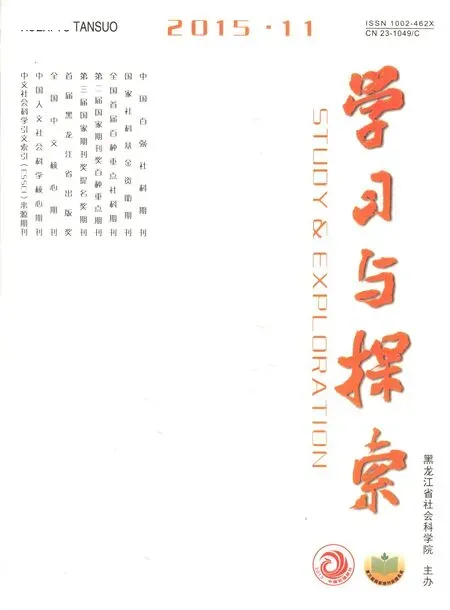秩序情结与无讼思想
2015-02-25郑莉,张辉
郑 莉,张 辉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01)
秩序情结与无讼思想
郑 莉,张 辉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01)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理想是“太平盛世”,这一政治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主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孕育的秩序情结,塑造了传统中国人追求和谐的品质,建构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同时也影响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这一情结在法律实践中的表达便是“无讼”。在加快法治建设的中国,对“由秩序情结而衍生的无讼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秩序情结;无讼思想
引 言
秩序,是指在自然状态或社会状态下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确定性和稳定的具有连续性的一种状态。社会秩序是指由社会规则所构建和维系,行动者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结构和状态。
香港学者张德胜教授在《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一书中说:“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的文化发展,线索虽然很多,大抵上还是沿着‘秩序’这条主脉而铺开。用弗洛伊德的术语,中国文化存在着一个‘秩序情节’,换做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说法,中国文化的形貌(configuration),就由‘追求秩序’这个主题统合起来。”[1]110李约瑟先生在对中国的研究中也明确提出,“和谐”是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2]马克斯·韦伯在对中国的研究中也提到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秩序问题”,尽管他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但他也认为中国“子民的幸福正显示上天的满意与秩序的运行无误”[3]61。可见,“秩序”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线索,值得关注。
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无讼”的研究,不难发现:一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无讼思想进行研究,考察其演生、发展及转向[4];二是从文化内的角度,考察无讼思想的建构[5];三是从法律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探寻中西法律文化的原理[6]。此外,还有的学者将“无讼”“健讼”“禁讼”“厌讼”“息讼”等进行全面考察,为构建现代诉讼观做尝试性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出的秩序情结,展开无讼思想的研究,探寻秩序情结为无讼思想所注入的文化因子,以及秩序情结在文化、社会以及法律实践中的表达。
一、秩序情结:无讼思想的本源
“秩序情结”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皆有迹可循:人充当何种角色、承担何种责任、履行哪些义务、处于何种等级、分属哪个阶层、过着何种生活,皆体现着“家国同构”之中的等级与秩序,这种“等级秩序观”与“和合文化观”“有序和谐政治观”的融合,催生了中国人的“秩序情结”,而“秩序情结”正是“无讼思想”产生的关键所在。同时,“无讼”也是“秩序情结”在法律文化中的实践表达,也可以说,“无讼”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传统中国人的法律价值观。
(一)秩序情结的文化表达——“和合”
金耀基先生认为,“秩序情结”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追求秩序,避免祸乱的一种突出的文化取向,在“趋避动乱”这一层面上,他也将之称为“动乱情结”,主要是想突出中国人向往和平、追求和谐的文化理念[7]2。
中国传统文化对宇宙万物和谐的关注由来已久,诸子各家不同研究进路的终极关怀是秩序的建构。儒家的“克己复礼”、法家的“以刑去刑”、墨家的“非攻兼爱”,皆体现出传统文化中追求和谐的“秩序情结”:法家任刑重刑,以“主人翁”的姿态干预和谐秩序的建构,是为了使民无争;墨家的法律观以“非攻兼爱”为核心,注重“法、法度”的作用,强调“方圆”和“规则”;儒家则以积极入世的态度,以其“礼治”思想的包容性,在秦汉以后,一跃而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并将“无讼”的法治理念与“修身和教化”融合起来,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如果说,法、墨两家可以让我们从诉讼形态上把握无讼思想的话,那么儒家的学说则为无讼思想的衍生及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养分,并有力地证明了其在传统法律实践中的核心作用。抑或说,在功能方面,形成了“阳主阴从、先礼后法、德主刑辅”的局面,并以此维系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秩序。
马克斯·韦伯在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研究中,将儒家称为儒教,他认为,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儒教的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格[3]235。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指出先秦思想家的共同文化取向是:一个宇宙界到人事界中的“秩序优位性”(primacy of order)的概念。中国文化重“和谐”的价值观贯通于个人的生活与社会:讲家庭生活,曰:“以和为贵”,讲生意,曰:“和气生财”。中国的大城,称西安,延安,长安;中国之北京城门亦称天安。中国以最好的政治为“国泰民安”,而政治社会之最高境界则是“大同”,意即盛世大和平也[7]。在中国老百姓的心里,“家和万事兴”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这种和谐的文化观不仅体现在礼乐上,在中国古代的建筑上也得到了验证。“房屋和城市由儒家的意念所形成:规则、对称、直线条的,等级森严,条理严明,重视传统的一种人文的形制。花园和风景由典型的道家观念所构成:不规则,非对称的,曲线的,起伏和曲折的形状,对自然本来的一种神秘的、本源的、深远和持续的感受。”[7]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社会生活都把自然和谐奉为最高准则,这种文化的性格以人道和天道结合,人性与天性相通为基础,也就是经汉儒董仲舒系统阐述的“天人合一”理论。正如张岱年所言:“但认为人含有宇宙之本根,天人相通不隔,则两家无异。两说都认为宇宙之本根乃道德之最高准则;人之道德即是宇宙本根之发现。本根之理,即人伦日用之理;在人为性,在物为理,在事为义,都是宇宙本根之表现。此种天人合一的理念,是汉宋儒家哲学中之一个根本观点。”[8]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在超越性的体现。
除此之外,“秩序情结”在法律文化中的体现尤为值得关注。瞿同祖先生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与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具有密切联系,研究法律必须将其放到社会中去。瞿老从家族、阶级、宗教、巫术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开展研究,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做出解释。他认为,“生活方式的差异既如此重要,与社会秩序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认为这种差异必须严格维持,绝对不容破坏,否则,必致贵贱无别,上下失序,而危及社会秩序,其推论实有其理论上的根据。于是不仅将这些差异规定于礼中(礼即所以分别贵贱尊卑的行为规范),图以教育、伦理、道德、风俗及社会制裁的力量维持之,且将这些规定编入法典中,成为法律。”[9]162这种“以礼入法”的做法,是儒家用来维持秩序的方法论。“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实质上就是身份群体的统一性,后者乃是官僚制古典文学教育和抱有前述君子理想的儒家伦理的载体。这种身份伦理的功利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强有力的约束,因为巫术宗教及其礼制被公认为身份惯例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因为对祖先和父母恪尽孝道的义务得到了公认。正如家产制源于子女对家长权威的虔敬一样,儒教也是把孝道的基本美德作为官员对统治者、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尤其是臣民对官员和统治者的从属关系的基础。”[10]儒家看重“礼”,主张社会地位差异性的存在,强调等级秩序,反对同一的“法”;而法家看重“法”,主张以同一的法维持社会秩序,以法治世。尽管两家的进路不同,结论各异,但均是为了达到理想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治世工具。孟德斯鸠在谈到中国问题时也说:“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生活。他们要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11]
(二)秩序情结的社会表达——“和谐有序”
要考察秩序情结的社会表达,就不得不谈及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国的政教俱以伦常为本,所以政治与家族的关系密切无比,为政者以政治的力量来提倡伦常,奖励孝节,是人所熟知的。”[9]99韦伯从人类历史经验中归纳出了三种支配的类型:卡理斯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在其对社会历史形态的分析中,分析了传统的家长制和现代的理性制度。他将秦统一后的中国作为典型的家长制的代表。他写道:“在中国,和西方一样,家产官僚制是个强固且持续成长的核心,也是这个大国形成的基础。”[3]91“中国的政治及其担纲者日益发展的官僚体制结构,已在整个中国人文传统上刻画下独具特色的印记。”[3]158台湾学者林端在对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的研究中,也明确写道,“韦伯眼中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主义笼罩下的社会,作为西方理性主义社会的对比类型,中国社会的整套文化设计都在不理性的、传统主义的笼罩之下:在宗教领域内,儒家深受传统仪式的制约,是一种仪式伦理;在政治领域内,是所谓的家产官僚制、传统型的支配结构;而在法律与司法领域内是所谓传统型的法律,亦即实质的——不理性的法律、家产制的司法、卡迪审判;而在经济领域内,经济组织深受传统与宗教束缚,并不区分家庭与企业。”[5]183尽管林端批判韦伯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方式” 落入了“规范式的欧洲中心主义”*林端认为,韦伯从文化间进行比较,是想说明西方社会所独有的法律是可预期的、高度形式理性化的。本来是一种“启发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即为了说明西方现代法律的特点,却不自觉地落入了“规范式的欧洲中心主义”来体现“形式理性”的法律是法律发展的高级阶段。的陷阱,但这并不能否认中国传统社会政治领域的特征是家产官僚制。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家国同构”,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是“父权家长制”的一种延伸,是父权从家庭到家族再到国家的一种延伸,是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特征。
中国自秦朝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来,“皇帝”就成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即所谓的“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显然,“皇帝”成了“家国同构”之中国的最高家长,普罗大众和精英阶层都寄希望于这位最高家长建构其“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希望最高家长成为“圣王”。在这种新的秩序里,家的伦常自然上升为治国的理念或纲领,尤其是自汉儒董仲舒“春秋决狱”以来,儒家以其价值体系重构了社会治理的理念,即众所周知的“以礼入法”到“礼法融合”,再到“礼主刑辅”,使“礼”成了治世方略的主导。“礼”:左边从“示”,指上天对人间所呈现的吉凶之兆;右边从“丰”,即祭祀之器皿。礼最初是带有宗教性质的原始习俗,是原始社会人们祭祀时遵从的行为仪式。而宗教或“神学”往往是祭祀文化产生的根源,在中国,祭祀表现为对祖先的崇拜,祭祀中的“禁忌”以否定的方式来规范人类的活动,逐渐形成了规矩,进而成为礼仪式秩序,这种秩序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人的行为,人也渐将其作为行为的规范,并自觉遵循。这种经过教化,使人们主动服膺的习惯,便是儒家思想中的“礼”。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礼既足以节制人欲,杜绝争乱,又足使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完成伦常的理想,自足以建立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而臻于治平。禁绝争端原是一切社会维持秩序的最低限度,也是一切行为规范所同具的目的。五伦则是儒家思想的中心,政治最高的鹄的。”[9]320规范着人与人行为的“礼”,成为儒家维护其秩序的工具,也成为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而儒家认为社会是存在差异性的,礼也是具有社会等级性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是入世的,是整体的,是王道的。这是因为“儒家根本否认社会是整齐平一的。认为人有智愚贤不肖之分,社会应该有分工,应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儒家认为这种存在于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异和存在于社会中的贵贱上下的分异同样重要,两种差异同为维持社会秩序所不可缺。儒家心目中的社会秩序,即上述两种社会差异的总和。礼便是维持这种社会差异的工具。”[9]309-311
此外,“礼”还特别强调国家间的关系准则是“和睦共处”,作为调整诸侯国关系的准则,“礼”注重的是王权,而非霸权,不崇尚武力,而热衷于和平。《左转》中记载的典故“郑伯伐许”,郑庄公戒饬守臣,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郑庄公戒饬守臣》隐公十一年《左传》)。可见,君主关注的重点在于以相对合理有效的方式保证其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和谐有序,以强化其统治地位。
在“家国同构”的传统中国,由礼培育出的道德观和政治观,必然带有父子有亲、君臣有义、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秩序情结,这种情结渐渐内化为一种民族精神,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成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换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维持主要靠礼治,注重道德教化,强调内在超越性,以适应现世,已达致伦理化的普遍主义。
二、无讼:秩序情结的法律实践表达
“无讼”源于孔子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顾名思义,“无讼”即为“没有诉讼或者不发生诉讼”。翻译孔子的话便是:“听断狱讼,我和他人一样,一定要使狱讼不再发生。”而非后人所理解的并付诸司法实践的意识形态化的“无讼”,即“禁讼”;也不仅是靠教化达到狱讼不生的目的。孔子所说的“无讼”是预防狱讼,消除百姓的讼争。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思想,显然,也是“以和为贵”的秩序情结在法律文化中的实践表达。文化对于社会如同性格对于个人,中国传统文化所注重的内在超越性已经将这种情结内化于心,传统中国人并不把法律看作是外界的东西,绝不像西方文化中“摩西的金牌律”是神授一般,而是认为这种礼法来自于他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来自于人们心中认同的普遍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
诚然,催生“无讼思想”产生的因素众多,除了前文提到的文化上“天人合一”、政治上“和谐有序”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稳定性和“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以及司法不公、诉讼成本均是导致“无讼思想”产生的因素。基于此,试着推演“无讼思想”的演绎路径:生活在自然经济下农耕社会中的人安分守己,具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秩序情结,人与人的交往不多,商品经济欠发达,社会关系也相对简单,过着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乡土生活,形成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一张人际关系的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大致分为三类,即“生人、熟人和家人”;或如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人分为“我群”和“他群”一样,这种社会关系是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特征的。因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12]32。这种社会关系的差别自然引起了不同的处事原则和救济方式:家人一般为血缘关系圈,彼此之间更多的是尽义务,一般不要求获取对等的利益回报;熟人多为地缘关系圈,彼此之间属拟亲化关系,一般讲人情,交往多采用大家默认的人情交往模式,以促进情感交流,但也期望获得程度稍低的利益回报;生人之间既无血缘关系,也无人情关系,彼此交往存在着利害关系或工具性关系,对利益回报的要求也非常精确,至少要得到对等的利益回报。人在各自的圈里生活,必然会发生纠纷,当纠纷发生时,不同圈里的人解决纠纷的方式也不一样:家人之间一般采用“自力救济”,如忍让、宽恕、和解等;生人之间一般采用“公力救济”,如诉讼、法庭调解等;熟人之间一般根据纠纷发生的程度不同采用不同的救济方式,由轻到重分别采用的救济方式是“自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典型的是复仇、战争)。当然,这三种关系可以相互转换,三种救济方式也必然适用于转换后的关系。然而,就一般意义上而言,“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12]57-58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所言其体会到孔子曰“必也使无讼乎”时的神气了。
纠纷是不可能靠“自力救济”就完全解决掉的,必然存在其他两种救济方式,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诸如“复仇、战争”之类的救济方式鲜少使用,百姓为解决纠纷无奈借助于“公力”,“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周礼·地官·大司徒》)在中国传统社会,凡走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一般分为重案要案和自理案件。重案要案按照当时的诉讼程序和法律条文,依律论处,签字画押,交由最高司法部门或最高家长裁定后行刑。自理案件一般交由州县审理,州县在堂审之前,一般会采用官方和民间的互动方法,也就是黄宗智先生所讲的“第三领域”,这种半正式、半制度化的模式,尽力促成“和解或私了”,这种行政方法黄先生称之为“集权的简约治理”。经过上述程序后坚持到堂审的案件,一般不再适用调解,州县最终也只能依律论处。在关于是否“依法(律)判决”的问题上,滋贺秀三和黄宗智的观点不同。滋贺秀三认为:“探索中国诉讼的原形,也许可以从父母申斥子女的不良行为,调停兄弟姐妹间的争执这种家庭的作为中来寻求。为政者如父母,人民是赤子,这样的譬喻从古以来就存在于中国的传统中。事实上,知州、知县就被呼为‘父母官’、‘亲民官’,意味着他是照顾一个地方秩序和福利的‘家主人’。知州、知县担负的司法业务就是作为这种照顾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方面而对人民施与的,想给个名称的话,可称为‘父母官诉讼’。”[13]黄宗智根据其对清代四川巴县、台湾淡水新竹和顺天府宝坻县档案研究,认为清代官员是按律办案的。不管是滋贺秀三的“情理说”还是黄宗智的“法律说”,都不可否认官员在堂审时,都会用道德教育子民,并适时采用教化的方式和父母教育子女的语气“问案”、“听讼”,尽管这里存在着“刑讯逼供、口供主义、贪赃枉法”的事实,但最后还是以官僚支配手段进行裁决。“不过,在中国,裁判的非理性,是家产制的结果,而非神权政治的结果。”[14]这种家产官僚制的支配和儒家的“仁政、礼治”密不可分,不管是乡土社会的“自力救济”还是于无奈时求助的“公力救济”,都是统治阶级以维持社会有序和谐、政治稳定的手段。把“以和为贵”的观念意识形态化,让其成为百姓的价值观,辅之以“讼则终凶”的恐吓,再加上诉讼成本的性价比不高,从而使百姓生发和谐稳定、反诉讼的秩序情结,并将此转化为一个具体的原则,即“无讼”。可见,“无讼”不仅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实践表达,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的理性诉说,更是中国人“以和为贵”秩序情结的实践表达。
三、无讼:走向法治理性化
“无讼”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与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结合的产物,是官方维持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实践表达,韦伯认为中国传统法律具有“实质非理性”的特征,充满自由裁量和不可预期性。不可否认,对实质公平和正义衡平的追求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神的体现,“无讼”便是这种文化的历史性的理性选择。时至今日,“无讼”早已不再是法律文化的核心表达,但“无讼思想”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它融合了社会力量和国家力量,是传统社会解决民事纠纷较好的方法,其制度之完备,经验之丰富,实施之广泛,在世界古代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评价一种法律的价值在根本上应视它对文明的促进程度[15]。那么“无讼”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无讼最大的价值就是其以灵活的方法调处讼争,减轻讼累,以至和谐。这与西方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所追求的社会正义性和生活秩序化殊途同归,这显然也是现代法治的追求,而实现这一追求的途径便是当今司法中的“调解制度”。调解制度是由以“无讼”为价值取向的传统法律文化演变而来的,秉承了“和合”的文化观、“有序和谐”的治理理念,以及无讼思想中的道德教育和礼治的“息讼”理念,体现了中国人所践行的“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有机融合的产物,抑或说是西方法思想植入中国法文化的成功典范。“中国的调解制度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甚至在1980年9月拟定了一项《调解规则》草案。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16]可见,正是调解制度的出现,使人们对“形式理性”的法律认识褪去了僵化和形式主义,迎合了现代法治的精神。正如庞德所言,“法律制定必须完全符合道德的倾向,道德理念随之进入法律理念的进程,以及将没有法律制裁内容的道德转化为有效的法律制度。”[17]换言之,法律与道德共存是可行的,调解制度在坚持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摒弃了泛道德化和家父长制的成分,兼顾着风俗人情,消除了对抗性,为国家法和民间法的互动搭建了平台,填补了实体法与民间习俗的空缺。让人们不再认为“现代法官是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18]。不难看出,以实现无讼为理想的“调处”演变成了现代社会的“调解”,带来的却是人们内心深处对法律内在权威的认同,也是人们对和谐的理性追求,很有可能使法律成为人们自觉而又坚定的信仰。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语境中谈“无讼”,人们很自然地体会到“实质合理”的意蕴,对实质公平的追求通过对个案的调处以达致和谐。回到现代法治的语境中,现代人的法律与权利意识与传统的无讼观截然不同,现代法治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还要体现程序的合理性,即形式合理。如前所述,调解制度是现代人对无讼的创造性转化,既体现了对社会秩序和谐的追求,又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在无讼的创造性转化中,并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法律中成型的诉讼制度,而是摒弃了义务本位的法律观、人治的自由裁量、德治的伦理性和等差性以及诉讼程序的不严明;并将伦理、道德和中国的“理”巧妙地融到了法治中。进而言之,由无讼思想中继受的因子,并没有忽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髓,葬送自己的社会文化,而是避开了“法律万能主义”的认同模式,为“法律多元主义”找到了出路。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创造性转化,可能是现代法治追求实质合理和形式合理的成功典范,也使无讼走向了法治理性化的道路。
[1] 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 李约瑟.李约瑟文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338.
[3] 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5] 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6] 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7] 李允鉌.华夏意匠[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306-307.
[8]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76-177.
[9]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0]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上册[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1194.
[1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73-374.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3] 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J].比较法研究,1988,(3): 25.
[14] 韦伯.法律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33.
[15] 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5.
[16] 梁治平.新波斯人札记[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48.
[17] 庞德.法律与道德[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5.
[18] 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张乃根,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62.
[责任编辑:高云涌,张斐男]
2015-09-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韦伯与中国文化研究”(14ASH002)
郑莉(1973—)女,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理论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张辉(1982—),男,助理研究员,从事理论与文化社会学研究。
C91
:A
:1002-462X(2015)11-00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