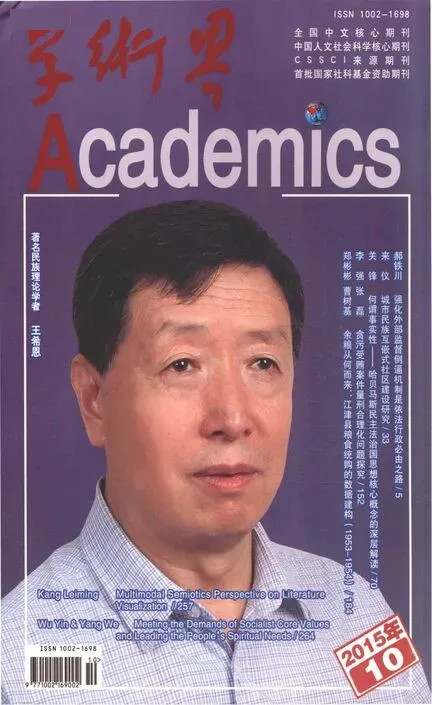撩开神秘的面纱〔*〕——《神秘的河流》的殖民书写
2015-02-25王小琼金衡山
○ 王小琼,金衡山
(1.合肥学院 外国语言系,安徽 合肥 230601;2.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62)
一、引 言
殖民题材得到澳大利亚小说家的青睐与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1788年,英国一支船队历经八个月的航行终于在澳洲登陆,澳洲的历史进程从此被改变。1968年,人类学家斯坦纳在演讲中用“澳洲历史上流血的神秘河流”来描述英国殖民者对澳大利亚土著人残忍的种族灭绝的屠杀行为以及随后对此种可耻行为的历史性掩盖。〔1〕2005年,澳大利亚当代女作家凯特·格伦维尔的聚焦澳洲殖民历史的小说《神秘的河流》,一经发表即获得高度关注,斩获2006年英联邦作家奖。该小说站在回顾殖民历史的高度,讲述了早期英国移民与澳洲土著居民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极具历史沉重感与深邃的思想内涵。格伦维尔通过对主人公——殖民者索尼尔个人命运的刻画来审视澳洲土著的苦难经历及澳洲殖民历史。在帝国霸权面前,被视为劣等民族的土著居民,不仅失去祖祖辈辈对土地的拥有权,连话语权也被剥夺。依据斯皮瓦克、萨义德、霍米·巴巴等人的后殖民批评理论,文章从帝国镜像的建构、帝国叙事的物质实践、帝国飞散者家园意识等方面出发,对小说的殖民书写进行解读。土著居民的悲惨遭遇暴露了帝国霸权和殖民主义暴力的特性,殖民地成为帝国权力掌控的空间,所彰显的是与帝国、种族相关的霸权性权力,但是主人公索尼尔却整日陷入“无家可归”的焦虑和恐慌之中,主人公索尼尔边缘人的形象设计,解构了帝国中心的权力,批判了帝国的霸权意识与殖民主义叙事。
二、帝国镜像的建构:失语的属下
“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另一个与其相异质的且与其竞争的另一个‘自我’(‘他者’)的存在。”〔2〕而“存在只有在他性的映衬下才具有意义。他性就是与宗主国相对的殖民地他性……”〔3〕所以,帝国的形象离不开殖民地“他者”的存在。为了建构帝国的镜像,格伦维尔在小说中塑造了殖民地的他性——失语的属下。属下,源自葛兰西《狱中札记》,指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受统治阶级霸权控制的社会群体。后来,古哈等印度批评家用“属下”概念特指殖民地印度本土居民,特别是“贱民”。1985年,斯皮瓦克在其《属下能说话吗?》这篇文章中又对“属下”进行了阐发,把古哈等人的特指扩展到女性群体,特别是被殖民女性。〔4〕从此,“属下”成为后殖民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意指那些在第三世界中受殖民主流文化压迫,没有话语权,不能表达自己的群体,尤其是殖民地的女性群体,在殖民霸权话语的绝对统治下,变成了沉默和黯哑的“他者”。〔5〕“属下”的概念表征了澳洲土著居民在帝国霸权面前“他者”的生存样态。仅仅因为肤色的差异,澳洲土著被类型化、异化为“黑鬼”“异类”,成为缄默的从属阶层。
小说中,白人殖民者自诩为“文明人”,而土著黑人在白人的眼中则是“光着身子,不知廉耻,到处乱跑的野蛮人”〔6〕。“像蠕虫一样四处徘徊,像蛇和蜘蛛一样,令人防不胜防,是寄生虫”。(第88页)尽管索尼尔与其他大多数殖民者都是被流放的囚犯,但他们的白人身份第一次让他们觉得自己比土著黑人高人一等。出身卑微的索尼尔在白人绅士面前卑躬屈膝,但在土著黑人面前却表现出明显的种族优越感。索尼尔利用疤子比尔跳舞来招揽生意,“……看着那个比他们身份还低劣的黑家伙在自己面前活蹦乱跳,欢呼声此起彼伏”。(第87页)对斯麦舍来说,鞭子和狗是对付野蛮黑人的强有力的便利武器,他甚至还将黑人的耳朵割下来,挂在腰间,说能保佑他交好运。政府公告上说,“任何当地黑人……都不得侵入任何英国公民的农田,一旦侵入,法律则令黑人首先离开该农田。如果他们坚持不离开,移民过来的人有权利使用武器把他们驱赶出去。”对此,罗夫迪的解释是,“这规定讲得很清楚,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开枪打死那些黑鬼。”(第261页)“白色”赋予了这些来自文明世界的殖民者天生的种族优越感,而“黑色”将土著黑人异化为白人眼中的“黑鬼”。18世纪的“伟大的生存之链”就将黑色人种置于人类发展的最原始阶段,紧挨着猿类。但是,对于黑人到底是应该属于人类,还是应该归于猿类的争议,爱德华·郎认为,白种人与黑种人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7〕肤色成为种族间明显的一种差异。对于人类差异的科学理论将会引起怎样的政治和文化后果?德国的人类学家西奥多·韦茨于1895年就曾清楚说明,“如果真的有属于不同物种的人,那么就会有一个自然的贵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种族来统治那些较低等的种族;如果低等种族证明对白人无用,那么就一定要任由他们停留在野蛮状态。无论何时只要因为那些低等种族挡了白人的道,所有那些灭绝性的战争就不仅是可以原谅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8〕据史料记载,澳洲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人在白人入侵后遭到了灭顶之灾。岛上的土著人几乎全部被消灭或被迫迁往他乡。〔9〕
小说从殖民者的视角描写土著黑人,但小说中没有对土著言辞的描写。当索尼尔第一次与土著头领哈利相遇时,尽管哈利滔滔不绝说了一大段,可索尼尔“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一个字儿都听不懂”。(第138页)索尼尔曾躲在树后偷看土著居民跳的战阵舞,可索尼尔觉得“声音听起来没有任何意义,跟昆虫的叫声没什么两样。”(第237页)当土著们在离索尼尔岬岬角较远的一边安营扎寨时,索尼尔去土著人的营地,十分坚决地告诉他们“这块地现在是我的。你们最好离开这里,离开我的地盘。”这里刚刚进行了一场交谈,有询问,也有回答。“但是,询问了什么,又回答了什么呢?他们看着对方,各自的言语就像挡在他们之间的一堵墙”。(第190页)在与土著居民的交流中,唯一能明白的,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一种语言里,都有表示相同含义的那个手势——滚开,即使是一只狗都会明白。”(第141页)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活吗?》中指出,“发言”指一种发言人与听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发言者不仅可以说话,而且所说的话要能被听见,只有当说和听都能充分实现的情况下,语言行为才得以真正完成。否则,即便“属下”是在发言,她的发言也无意义。〔10〕在殖民者面前,土著黑人却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化、自己民族的情感和意志。土著黑人无法与白人殖民者实现平等的交流、对话。在欧洲移民没有进入澳大利亚之前,土著居民的语言有三百多种。〔11〕但是,在小说中,格伦维尔没有以地方英语(english)的形式让殖民者听到黑人土著的抗议之声,而是以这种特殊的书写方式反映土著居民在帝国霸权面前“失语”的困境。在殖民时代,“帝国压迫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对语言的控制”。〔12〕语言是民族文化特性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建立民族意识形态的媒介之一。语言的作用不仅仅是用来描述事物,语言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行事”的重要功能——以言行事。殖民者禁止使用土著语言,强迫殖民地土著居民使用殖民者的语言,意味着殖民地土著居民无法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确立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只能用殖民者的语言及其文化来确立自己的被殖民者的身份。在殖民地,语言,与武器一样,是彰显帝国权力的强有力的工具。谁控制了语言,谁就掌控了话语权。“话语与权力从来是不可分的,因为话语是每一个机构控制和发号施令的媒介。话语决定什么是可能说的,谁被允许有权威说话,在什么地方有可能说这样的话。”〔13〕由此可见,属下不是不能说话,他们可以说话,只是在帝国空间里因话语权被剥夺而不能以自己的主体语言来言说。
小说对殖民统治下的一个特殊群体——黑人女性属下——的生存与地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叙述了女性土著居民——女性属下在帝国霸权下的境遇。小说多处从白人男性的视角描写黑人女性裸露的身体。“……年轻的女人们浑身赤裸,尚未发育完全的乳房和修长的大腿,让男人们眼花缭乱……丝绸般肌肤的光泽在肩头和尚未发育完全的乳房周围滑动着。丹贪婪地盯着那群女人们,丹的眼睛放着光。奈德开口了:快看那些姑娘们,好好看看那些姑娘们吧!接着咯咯笑了起来。”(第194-195页)在白人男性掌控性的、好奇的凝视目光之下,黑人女性及其身体成为白人殖民者凝视的客体,成为男性欲望的能指。这种凝视既蕴涵种族意识,也蕴涵性别意识。这种“男性—凝视、女性—被看”,“本身就是一种不对等关系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话语,一种意识形态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14〕亦如福柯所说,身体是权力运作的场所。黑人女性身体成为帝国得以施展其霸权的对象和目标,遭遇规训与征服。黑人女性的身体被色情化,成为白人男性的臆想对象、性目标。种族主义压迫下的澳洲黑人女性,不仅遭受白人的种族歧视,还遭受白人男性的性暴力,成为他们泄欲的工具。当索尼尔来到斯麦舍住处挑选狗用来对付土著人的时候,“强烈的阳光下,屋里的东西模糊不清,只看到一团黑影,还传来一阵锁链声,以为是条狗。忽然发现原来是个蹲着的人:一个黑女人,缩在墙边痛苦地喘着气,身上有好多处锁链磨破的印记。‘拖着你的黑屁股给我滚出来’,斯麦舍的鞭子抽在她的背上。‘赛吉提和我都干过,都从背后干的。想试试吗,索尼尔?’斯麦舍问”。(第245-246页)澳洲女性土著居民,不幸的是她们是黑人,更不幸的是她们又身为女人。斯麦舍用锁链将一名黑人女性像狗一样栓在屋里,使之成为他的性囚犯,随意用鞭子抽打,不仅占有她,还邀请其他白人一起玩乐。黑人女性面对白人男性的羞辱、折磨、玩弄和杀戮,无力反抗,成为帝国霸权和男权统治的双重牺牲品,无法逃避肤色与性别给她们的生存带来的厄运。在小说结尾描写的驱逐土著黑人的战斗中,手无寸铁的黑人女性被血腥杀戮,一个都不留。
在殖民语境下,“类型”(stereotype)替代了真实的种族身份,被殖民者不能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地位,而沦落为被征服和被控制的客体,即他者,既被视为欲望渴求的对象,又被视为嘲笑的对象。澳洲土著居民,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却被殖民者用武力驱赶,土地也被殖民者侵占,成为霸权表征的历史和政治暴力的受害者,沦落为帝国文明的“野蛮他者”。这些“野蛮人”“愚昧、落后、残暴”,在帝国霸权面前自始至终都处于弱势地位,处于失语状态,尤其是黑人女性。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施暴象征着殖民主义者对被殖民者的征服,声音的缺席则象征着被殖民者话语权的丧失。殖民主义权威话语及其声音的单一性是殖民主义权力运作的基础。“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作为被殖民的民族,土著居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机会向白人主流社会发出抗议之声。”〔15〕小说反映了霸权话语对属下话语的压制及属下无从发言的历史处境。〔16〕
三、帝国叙事的物质实践:索尼尔岬
18世纪大英帝国所进行的海外扩张和殖民征服使得帝国成为文学作品中无法回避的话题之一,而且,18世纪英国航海小说的兴起及《鲁滨逊漂流记》的诞生,使得大海成为殖民扩张的象征,水手亦成为帝国使者的象征。小说《神秘的河流》正是帝国海外殖民扩张、征服、掠夺的真实写照。主人公索尼尔在小说中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在殖民话语中,“帝国霸权和男性话语往往是合二为一,帝国通常被表征为男性,而且是白人男性。”〔17〕索尼尔,英国白人、男性、水手,从泰晤士河出发来到澳洲,扬帆探险、安家落户,最终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澳洲绅士,反映的正是帝国海外扩张的殖民史。对索尼尔来说,占有土地意味着寻求财富和新生活的机遇,是实现欲望与希求的手段,所以索尼尔对澳洲大地所能做的,亦如鲁滨逊所做的,就是征服、掠夺、占有、控制和改造。小说通过对索尼尔与土地间关系的描写,反映殖民者对土著居民表现出的强烈的帝国优越感和霸权意识,讲述两种文明的冲突,突显澳洲大陆上的种族问题。
当索尼尔站在澳洲广阔的大地上时,一个疯狂的欲望已经吞没了他——“一定要占有它。一定要让自己说这是属于我的”。(第101页)于是,索尼尔们仅仅通过“命名”的方式就占有了土地。“只需找到一片还未被别人占有的土地即可,种上庄稼,盖所房子,称那片土地为史密斯之地或弗拉纳根之地,然后旁观别人众说纷纭。”(第116页)当索尼尔大声喊着“你们最好离开这里,离开我们的地盘”(第188页)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他到来之前,这里其实早已是土著黑人的聚居地。小说中,索尼尔询问布莱克伍德是如何得到百亩土地的,布莱克伍德瞥了他一眼,“这地盘根本就不存在向谁提要求的事,伙计,坐在地上,挺直坐好就行了,这就是他们要求你做的全部的事。”(第100页)受布莱克伍德启发,索尼尔心想“自己眼之所见全归我所有”。(第146页)“要拥有一片土地,居然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真令人诧异”。(第127页)布莱克伍德的回答、索尼尔的想法听起来匪夷所思,却反映了当时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态度,无视生于此、长于此的土著居民的存在,暴露了帝国征服、掠夺的殖民本性。索尼尔对土地表现出占有关系,视自己为土地的主人和所有者。面对土著居民的长矛,索尼尔依然指着那些峭壁,还有河流,大声对长胡子哈利说,“这里是我的地盘,你再找别的地方吧”。(第138页)小说结尾告诉读者,黑鬼溪已经改名叫索尼尔溪了。亦如萨义德所说,“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关于土地的争夺。但当涉及谁拥有这片土地?谁有权力在上面居住工作?谁建设了它?谁赢得了它?谁规划了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反映、争论,有时被故事所决定。”〔18〕
殖民者索尼尔对索尼尔岬完全占有的标志是他种上的玉米。玉米地是索尼尔梦想的象征,也是殖民欲望、殖民统治的象征。土著黑人摧毁玉米地,不仅意味着索尼尔的梦想受到了威胁,也意味着帝国的殖民统治受到了威胁。只有解决了来自土著黑人的“威胁”问题,索尼尔才能坚守自己的梦想,帝国在澳洲的殖民统治才能顺利进行。对索尼尔岬强烈的占有欲望导致索尼尔最终参与了对土著黑人的血腥屠杀。战斗中,索尼尔开枪打死了长胡子哈利,将声称“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土著黑人头领的脑袋割下来,意味着土著文化在霍克斯布里的消失、帝国殖民统治的开始,索尼尔岬完全属于索尼尔了。终于“没有黑人再来惹麻烦,新来的居住者们在河流的每一个转弯处都划定了自己的土地。”(第307页)索尼尔拥有一千镑现金,三百英亩土地和一张土地所有权证明,有一座气派的房子。“俯瞰索尼尔的房子,眼前的景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英格兰。”(第323页)小说充分证明了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精辟判断:“帝国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土地的问题。帝国主义意味着对不属于你的、遥远的、被别人居住了和占有了的土地的谋划、占领和控制。由于某种原因,它吸引一些人而时常引起另一些人不可名状的苦难。”〔19〕“土地”是贯穿小说的文脉、反映作品主题的宏大意象。索尼尔最终将“索尼尔岬”变成了自己的地盘,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泰晤士河上的穷水手成功转型为受人尊敬的“澳洲绅士”,成为上等人——拥有居高临下权力的上等人,彻底颠覆原来的身份。在新的身份建立的过程中,帝国的权力如影随形,同时权力的运作,也通过特定的意识形态主体得到合法化。索尼尔宛如帝国的使者。小说站在殖民者索尼尔的视角,而不是土著黑人的角度进行叙事,打破了传统的叙事策略,突显了支配与被支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以展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白人男性与黑人女性之间的权力机制。
殖民总是与战争、种族冲突这些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早期的殖民者需要在澳洲安家落户,建立自己的家园。于是,殖民者凭借先进的武器消灭土著人,凭借暴力霸占土著居民的土地。澳洲的土著居民因为殖民者的到来,则要被从已生活了几万年的家园里撵走。殖民地成了帝国权力控制的地域,所彰显的是与帝国、种族相关的霸权性权力。据有关史料记载,澳洲土著居民“从原来三十多万人降到上世纪中叶的四万余人。很多部落已经不复存在,有的人种(如塔斯马尼亚人)已经灭亡。正是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和种族虐待破坏了土著人的生存环境,把他们逼上了种族灭绝的边缘。”〔20〕
四、帝国飞散者的家园意识:非家幻觉
索尼尔因为帝国的扩张来到澳洲,从而成为一名“帝国飞散者”。〔21〕飞散者(a diaspora or a diasporan)不仅仅是指在自己的故土家园以外生活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和家园的联系或是在跨民族的关联(transnational networks)中实现的。〔22〕家园是文学中的一个古老主题,但20世纪90年代的家园政治理论认为,家园不再指一般意义上的固定居所,而是一个通过“权力”,以一系列“表征”性符号为媒介通道所建构的“主体想象物”,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家园建构都是“政治性的”,它涉及身份、地点之间的基本联系和流动、变迁之间形成的更为复杂的关系。〔23〕由此可见,家园政治是一个主体不断建构的问题,其内涵具有丰富的指涉。
对索尼尔这样被判流放至澳洲大陆的囚犯,家园意味着“流亡或放逐”。另一方面,早期的殖民者对土地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以索尼尔对“索尼尔岬”的强烈依恋为例,“索尼尔岬”对索尼尔来说代表着机会、活力和成功,是满足个人欲望、实现梦想的媒介。索尼尔对“索尼尔岬”的情愫主要是因为漂泊异乡的生活经历导致他对身份、对归属感产生强烈的诉求和探寻。“‘我是谁?’是二十世纪流行的问题。我们想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想知道我们是谁?希望自己的身份被社会所接收,想在地球上找个特定的地方安个舒适家。”〔24〕人文地理学鼻祖段义孚认为地方首先是人身份认同的源泉,而且,这种对大地的依恋类似于对家庭的依恋,所以这种依恋感又被称为家园感。〔25〕索尼尔之所以对索尼尔岬具有强烈的情感体验,是因为索尼尔希望通过占有索尼尔岬——土著黑人的土地,以建起属于自己的房子,建立属于自己的家,追求他在英国社会无法确立的身份,即财富、社会地位与名誉,重新找回了因与泰晤士河的割裂而失去的归属感,以实现自我认同的身份建构梦想。因此,家园意味着人人为之奋斗并被建构为“排他性”领地的充满欲望的地方。〔26〕殖民主义对自我与他者总是表现出无穷的欲望。
欲望是拉康理论,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关键词。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欲望最初来自婴儿与母亲身体的分离,即母亲身体的缺失。对于母亲身体的缺失我们不得不寻找替代品。拉康追随柯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认为欲望永远是对他者的欲望,要求他者的“爱”或“承认,被他者承认的欲望永远没有尽头。〔27〕索尼尔一生都在从“边缘”到“中心”的世俗欲望中挣扎。索尼尔们被自己的母国抛弃来到遥远的澳洲,最大的梦想就是建立自己的家园。科巴姆大楼的建立意味着索尼尔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与身份。但是,索尼尔全然没有胜利的感觉。在索尼尔们到来之前,对土著黑人来说,这片土地是“诗意栖息地”,他们与这片土地物我相征,在这片土地上享受着惬意和自由的生活。虽然索尼尔将科巴姆大楼建立在刻着鱼的图案的那块岩石上,索尼尔一家却无法体会土著人的惬意与自由。科巴姆大楼高高的围墙将澳洲原野挡在了外面,意味着索尼尔们与这片土地的疏离与隔阂,只能游走于“诗意栖息地”的边缘。杰克的存在也提醒了索尼尔,索尼尔岬并非是他的。“这是他没有的:一片与他血肉和灵魂融为一体的土地。”(第323页)每一天快过完的时刻,索尼尔会坐在阳台上,手拿望远镜,看着夕阳金红色的余晖洒在山崖上。“每一次,都多添了一份空虚。”(第327页)骨子里,他仍然还是那个站在寒冷的泰晤士河里向着贵族奴颜婢膝的水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身份是互相依存的,殖民者优越的文化身份的确立需要从被殖民者那里得到心里确认。当殖民者从被殖民者的凝视中得到一个扭曲的自我形象时,殖民者的身份的自我统一感即受到了挑战。亦如拉康的镜像理论所说,个人自我身份的形成最初是依靠认同于他者。但是,当主体意识到他永远不可能站在他者的位置上看待自己的时候,深刻的自我分裂感就出现了。〔28〕
以索尼尔为代表的殖民者是道义上的失败者,并不能享受胜利的喜悦,反而生活在一种莫名的恐怖之中。主人公索尼尔是殖民者,但厌恶野蛮暴行,故而未能进入白人主流,但他也未能被土著居民接纳。于是,对索尼尔来说,家园虽是给人以归属和安全感的地方,但同时也是一种囚禁。在科巴姆大楼,索尼尔整日陷入“无家可归”的焦虑和恐慌之中。巴巴曾明确指出,殖民主义的要求(demand)永远表达一种没有穷尽的欲望与焦虑。这些欲望与焦虑正是殖民主义者对于殖民客体爱恨交加的矛盾情感的来源。〔29〕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原住民对土地权利的主张是奇怪的,而忽略那里的土地本来就不是欧洲人的,这正是一种“不熟悉和熟悉并存”的“非家幻觉”〔30〕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非家幻觉”是“家和世界位置对调时的陌生感”,或者说是“在跨越地域、跨越文化开始时期的一种状态”。〔31〕索尼尔的困惑正是对澳洲土地所有权的“非家幻觉”的“家园意识”的表现。对索尼尔来说,家园意味着栖身于两种文明冲突之中且被两种文明所抛弃的“无家”之感。
五、结 语
“种族”的划分使得“白人”以“优等民族”自居,而“黑人”则被视为“原始野人”的“劣等民族”。文明开化的白人要占据那片土地安家落户,而尚未开化的黑人则被武力从祖祖辈辈的家园中驱逐。不仅如此,“黑色的异类”在“白色神话”中没有话语权,生来没有任何权力,成为在各种差异性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属下”,遭受帝国强权的支配与压制,成为“缄默的他者”。更为悲惨的是,作为“黑人”又作为“女性”的“黑人女性属下”,肤色和性别让她们更是面临“双重危险”——成为白人男性“凝视的客体”和性暴力的受害者。殖民统治让殖民者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利益和刺激,但是,在以暴力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家园,殖民者陷入“无家可归”的焦虑之中,“非家幻觉”如影相随,也有其逻辑必然。殖民者索尼尔的命运结局显然是作者的用意所在。
格伦维尔为什么将小说的主人公——殖民者索尼尔塑造成一个边缘人?2009年,在一次采访中,格伦维尔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向土著居民说一声‘对不起’”。〔32〕“对于澳大利亚小说家来说,殖民主义题材无疑可以用来构建一种政治社会母题,直奔澳大利亚社会最为敏感或许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土著人和其他种族的纠纷。”〔33〕在小说中,格伦维尔将困扰着澳大利亚人200多年的种族问题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索尼尔们从遥远的帝国中心来到澳洲,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镜像昭示,他们可以征服,可以成功,但他们在澳洲历史上所留下的不光彩的一页,也使他们成为永久的“外人”。“白人至上”与帝国的优越感,令“劣等民族”摆脱不了被征服、被掠夺的悲惨命运,但被殖民者权利意识的觉醒、对权利的主张与抗争,终将影响帝国权力的走向。
注释:
〔1〕王丽萍:《评凯特·格伦维尔的新历史小说》,《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
〔2〕〔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426页。
〔3〕陶家俊:《文化身份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0页。
〔4〕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5〕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8页。
〔6〕〔澳〕凯特·格伦维尔:《神秘的河流》,郭英剑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以下该书引文只在括号内标明页码。
〔7〕Robert J.C.Yong,Colonial Desi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7.
〔8〕Waltz,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转引自 Robert J.C.Yong,Colonial Desi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7.
〔9〕〔15〕〔20〕〔33〕叶胜年:《殖民主义批评:澳大利亚小说的历史文化印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90、56、111、28页。
〔10〕〔16〕马广利:《文化霸权:后殖民批评策略》,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69、70页。
〔11〕〔32〕冯元元:《关于〈神秘的河流〉的对话》,《外国文学动态》2009年第3期。
〔12〕阿希克洛夫特等:《逆写帝国》,任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1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红樱译,三联书店,1999年。
〔14〕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诗性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17〕蒋玉琴:《书写政治》,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8页。
〔18〕〔19〕〔美〕萨义德:《文化和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3、6页。
〔21〕〔22〕〔30〕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117、115、123页。
〔23〕〔英〕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24〕〔25〕Tuan Y F,Rootedness versus Sense of Place,Landscape,1980,pp.45,47.
〔26〕费小平:《家园政治:后殖民小说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27〕〔28〕〔29〕贺玉高:《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9、73、79页。
〔31〕Gelder,K.D.,and J.M.Jacobs,The Postcolonial Uncanny:On Reconciliation,(Dis)possession and Ghost Stories.Uncanny Australia:Sacredness and Identity in a Postcolonial Nation.Carlton: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1998,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