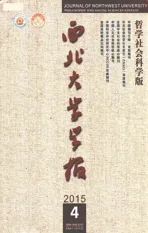人性的反思与诗意的创造——重读《夹缝中的历史》
2015-02-23吕刚
吕 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55)
一
一部好书是经得起重读的。朱鸿《夹缝中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好书[1]。近来,我把这部历史文化散文集重读一遍,仍然感触良多。书中发人深省的挚烈情思和充满诗意的文字叙述,又一次深深地刺激、打动了我。
朱鸿在此书的《后记》里说:“到现在为止,在我的所有写作之中,这一组系列散文的写作,是我最为重视,也是最为用心的。”时间证明,作者的用心和努力没有白费。这本书于2001年1月,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首次印行,至今已刊行3版,印刷达14次之多,近期又将推出第4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大众读物甚嚣尘上,出版商唯利是图的当今,一部纯文学作品集还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印行?
还是那句老话——“人间要好诗。”《夹缝》不是诗集而是散文集,但它却比一般的诗集更富诗意。梁实秋在《论散文》中说:“‘诗’时常可以用各种的媒介物表现出来,各种艺术里都可以含着诗。”[2](P28)余光中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有些散文,本质上原是诗。”[2](P197)我理解,这里所谓的“诗”,强调的是优秀散文作品所内涵的高贵的精神品质和优雅的美学境界,而这恰是《夹缝》所体现的质与相。
《夹缝》所收的14篇文章,每一篇涉及的都是中国历史之重大事件及重要的历史人物。其独特之处在于,作者的笔触无不是从“人性”的角度切入,对历史事件及人物命运进行描述与分析,从而揭示传统文化尤其是专制政治对于人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荆轲是中国历史上刺杀嬴政的英雄,自古及今受人尊敬,朱鸿却“怀疑荆轲”。首先,他不相信荆轲“失手”的原因是“剑术偏差”。荆轲是人,是人就会“贪生”“不想死”。中国人当然讲“士为知己者死”,但燕太子丹实在算不上荆轲的知己[1](P63)。朱鸿以为,荆轲的“失手”,完全在于行事的瞬间心存“杂念”。这是一个破天荒的推理,也是合乎人性的判断。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接受别的原因。只接受剑术偏差的原因,甚至不愿意认真分析荆轲失败的原因”呢?朱鸿认为,这是一个民族可怜的“精神胜利法”——“指秦始皇之桑,骂自己所憎恶之槐”。由于长期的集权专制统治,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理,无可奈何地落到了敢怒不敢言的地步,荆轲因之成为“苦闷的灵魂得以出气的洞口”。这种对“英雄”的崇拜心理,是人性长期受压抑而寻求的一种平衡[1](P66)。在《怀疑荆轲》中,朱鸿从人性角度切入审视荆轲内心甚至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便提出了启人深思的问题,也给出了足以服人的答案。
商鞅变法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影响深远。朱鸿从这次变法对于民众权益的影响落笔,写下《成功的罪孽》。他以为商鞅在改革政治、强大秦国的同时,完全不顾及民众的利益。为了凝固人们的意志,商鞅竟然以“法”的形式确立了“告奸”——即人揭发人的正当性,这是“对人所有的基本的生存权利的威胁和侵犯”。朱鸿说:“商鞅的方式,充满了集权统治的倾向。商鞅通过变法,为中国的集权统治建筑了一个基本框架,甚至是他的变法产生了中国集权统治的雏形。”[1](P43)指明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不是同时着眼于社会与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共同发展,人们很难发现商鞅成功背后所隐藏的罪孽,至少会忽视这种罪孽的恶果。事实上,这种由“人揭发人”演变成“人诬告人”的肆意践踏人权的恶行,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
中国以往社会发展之缓慢,可以在传统文化的根上找原因。其实,梁漱溟早就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3](P259)但这并不等于伦理文化在设计之初就要取消个人之价值,真正限制个人思想、剥夺个人权利、妨碍人性与社会发展的是皇权下的专制统治。这一点,我们比较一下《我在孔庙的所见所想》与《司马迁之残与苏格拉底之死》两文,便不难理解。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之际,诸侯竞争,政治权力相对分散,客观上为个人的思想与行动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孔子讲“仁爱”,曾经周游列国,寻求从政的机会,但是“孔子的精神是独立的”。在《我在孔庙的所见所想》中,朱鸿赞美了孔子,指出孔子的“愿望是进入权力机构,并按自己为人类的设计直接地改造社会”[1](P10);孔子“活着恓恓惶惶,仿佛丧家之犬”,但他的言行是自由的。可是司马迁就不同了:作为史官却因为“说错话”而致罪,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性”都被剥夺了。专制统治者不把人当人,而要把所有的人都驯服成任意驱使的工具。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开始两千余年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标志性事件。其实汉代统治者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并不契合孔子精神的实质,而是对孔子思想“修正”的产物,统治者以此“僵化全体中国人的思想,并封禁中国人探索与发现的激情”[1](P6)。从此,所有的人都要颤颤兢兢,在皇帝手下讨饭吃,人之为人的尊严与资格丧失了。这种结局当然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却严重损害了民众的权益与社会的进步。正如西田几多郎所言:“只有生活在一个社会里的每个人都能充分地活动,分别发挥他们的天才,社会才能进步。忽视个人的社会绝不能说是个健全的社会。”[4](P145)
在《司马迁之残与苏格拉底之死》里,朱鸿把司马迁与苏格拉底放在一起比较是深有意味的。两位东西方哲人都因“说错话”而致罪,其命运不无相似之处,但结局却大不相同:苏格拉底用他的死捍卫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司马迁在忍辱完成《史记》之后悄然辞世。“司马迁之残”不仅是专制统治的耻辱,更是人权遭践踏、人性受摧残的见证,它给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永难抹去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创痛。
如果把皇权专制统治的社会比作金字塔,那么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自然是皇帝,处在金字塔最下层的无疑是广大的女性。即使那些身处皇宫,有幸能够接近皇帝的女性也不例外。与社会各阶层女性不同的是,宫中女性是仅供皇帝一人驱使的“尤物”而已。
王昭君就是这样一个“尤物”。但是在许多国人的记忆中,这个薄命的女子似乎至今身上还绕着许多光彩四射的光环。但朱鸿不这么看:“我关注的是王昭君这个人的生存状态,这个女性的基本欲望及其丧失。”[1](P166)作为一个被选入宫的女子,王昭君等待君王宠幸的愿望是万分渺茫的。与宫中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她们作为女人的基本权利,被一个男人凭借手中的特权剥夺了。后来王昭君远嫁匈奴时,没有表明此去的“真实”想法。虽然王昭君自己没有说,后来的人们还是替她说了许多,有的不免大言堂皇。朱鸿虽到底也没有在字面上指明这一点,但读者清楚他的意思:嫔妃制度是有悖人性的,王昭君远嫁而去,至少暂时“逃离”了戕害人性的处所。
《苏三监狱》是一篇具有象征意味的作品,它揭示了专制统治下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人的智慧与才能没有用来创造有效的价值,而是无止境地用以制造人与人的对立情绪与紧张关系。人性在长期的紧张对峙中,一面因受压而扭曲,一面因放纵而异化。这种情形既使人养成了对权力的屈服与崇拜,也激发了人对权力的向往与争夺。
在《追究吴三桂》中,朱鸿不相信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浪漫说法。他以为“一束缥缈的爱情之光,不但照花了吴伟业的眼睛,也照花了历史的眼睛”[1](P310);其实“吴三桂是想有自己的江山的”[1](P325),他想成为专制中国的大“禁子”,不想成为别人治下的“囚徒”。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吴三桂的反复“叛变”了。权力可以用来压制人性,也可以从内部扭曲或者异化人性,使人从生活的主体,蜕化成权力演变的附庸。
朱鸿对过去时代的人与事细心甄别,努力挖掘被历史尘埃遮掩了的普通而又普遍的人性,意欲打通古今人类的心灵通道,以历史之光烛照现实。他深深懂得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我的思路是,迂回到现实的背后去,以深刻地进入现实。”“已经过去的人类生活,便是历史,从历史之中生长出来的新的人类生活,则是现实。”而“文化把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接到一起了”[1](P1)。于是,《夹缝》中所描述分析的历史与人物,沿着朱鸿的眼光与思绪,顺着古今共通的人性的“管道”,与那些尚不失锐敏的读者的心灵产生激荡,引发多方面的积极效应。
二
朱鸿曾经说过,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夹缝》便是他长期思考中国历史的结晶,具有一种既凝重又绚美的力量。诗人废名说,“思想是一个美人。”[5](P432)的确,思想着是美的。朱鸿散文既远绍了韩愈“文以载道”之主张,更近承着鲁迅“为人生”之艺术精神。但朱鸿强调的“道”,是人的理解与沟通、人的文明与进步的人性之道。他有过这样的自道:“作为人类的成员,我艰难地生存在同胞之中。”“我用自己忧郁的眼睛注视其他成员,而且设法将我的目光投向历史,投向各民族、各地域、各时代的生活。”“我首先望着周围的人,我在发现他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生存状态,我特别敏感人的痛苦,我经常思考人的痛苦的原因。”[6](P56)因此对于专制政治文化的批判,对于人之自由精神的张扬,必然构成朱鸿散文充满内在张力之两极,这正是朱鸿散文的“文气”之所在。韩愈谓为文“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7](P1163。鲁迅的《野草》大多篇幅短小,朱鸿的《夹缝》皆为长篇大论,但是前者读过不觉其短,后者读来不嫌其长,都给人以力的鼓动,美的享受,只不过美与力的程度有别而已。
人们的阅读经验往往有一个误区,以为强调思想性的文章,一定是不甚注重修辞,只有思想平庸的作者才肯在辞章上劳费功夫。这种认识所致的结果之一,是很多人仅把鲁迅看成一个“思想者”,读其文只注重他“说了什么”,而忽视了鲁迅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怎么说”。李长之早就指出:“鲁迅在文艺上乃是一个诗人;至于在思想上,他却止于是一个战士。”[8](P136)有人可能不完全赞同这种看法,但说鲁迅内心里有着强烈的感情,在艺术上有着执著的追求与巨大的创造,总是不错的。
朱鸿也是一个内心里涌动着强烈的感情、艺术上有强烈的精美化追求的作家。《夹缝》既是用心深思的文字呈现,又是苦心经营的艺术作品。其后记云:“我还借鉴了诗人的办法,这便是注意我的句和字。”[1](P328)的确,读者与《夹缝》的思想沟通与情感交流,是在美妙语词构成的艺术世界中展开的。
《灰堆》写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事,作者“对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一直有物伤其类的隐痛与激愤”[1](P72)。在渭河以南,他找到了那次焚书留下的巨大的灰堆。接着有这样一段文字描写:
当我默默站在它面前的时候,二十世纪最后某年的夕阳,以自己无奈的光芒照耀着这个沉积物。锥形的灰堆,孤立于晚霞停滞的旷野。黄昏之中,它似乎有一种高耸之感。这灰堆周围,到处都是呐喊的麦苗和蔬菜,还有呐喊的树木[1](P80)。
这些描述性句子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感情的抒发不是直接、空洞的,而是有控制地转移到了对周遭物景的描写与对气氛的营造上。作者无形的情绪浸染到具象的闪着“无奈的光芒”的“夕阳”“停滞”在“旷野”的“晚霞”“灰堆周围”“呐喊的麦苗和蔬菜”以及“呐喊的树木”之上,创造了物我浑然、贯通古今的艺术意境,充分表达了无奈而又无比愤懑的情绪,产生了震颤读者心弦的审美效果。
《怀疑荆轲》是一篇独具见解的文章,它让我最难忘的是对荆轲刺秦王的瞬间的想象性描写:
他瞪着眼睛望着匕首,他看到匕首在咸阳宫漂亮地飞旋着,可它却碰在了一根铜柱上。秦王及其文武百官都听见了尖锐的金属之声,我也听见了,因为它一直沿着历史跋涉的方向尖锐地响着[1](P61)。
这样的的文字,将读者的视觉、听觉、触觉甚至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调动了起来。其诗意尤其在于最后三句,显示着的巨大的空间转移与漫长的时间跨越,而这一切都是在作者的想象及对想象的准确表达中完成的。
汪曾祺曾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其实,写散文又何尝不是呢?文字不仅是表达思维的工具,本身也是一种目的。特定的语词使用,不惟传达特定的思想,也往往会形成特定的美学风格。朱鸿对一些词语的独特运用,就收到了这样的效果。如写孔庙的环境:“孔庙也有槐树和银杏树、海棠花和梅花,当然还有别的种种珍贵而美丽的植物,然而孔庙的主流却是柏树。”[1](P1)用“主流”来描绘孔庙的柏树,真是生动之极,也准确之极。谓之“生动”,是因为“主流”一词不仅写出了柏树之多,而且写出了柏树枝叶在风中摆动的感觉。这个词语人们一般习惯在社群的意义上使用它,移诸写植物,便产生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谓之“准确”,是因为这里似乎又有以树写人的意思,“主流”的柏树与“主流”的人群之间,有着一种暗中呼应的关系。那么,槐树、银杏、海棠和梅花等别的珍贵而美丽的植物,也可说成为各色人等的象征了。
再举《成功的罪孽》为例。文中引秦孝公的求贤令,有“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的句子。朱鸿大概特别喜欢“光美”这个词了,随之一用再用“光美之事”“感到光美”等词语,造成一种古雅而又大气的美感效应。
我还要特别提到朱鸿写唐代诗人命运的《诗人多难》一文。其活泼而有趣的句式,引起了著名语言学家沈家煊的注意。沈先生说,他读“闲书”时,看到这篇文章,于是把全文25个段落中写诗人“出场”的句子拿来分析,撰文讨论“话题的引入与象似原则”。朱鸿的文字无意间成为语言学家研究句法问题的材料,可见其笔墨之活脱与法度之谨严。
三
作为一部富有“诗性”的散文集,《夹缝》深刻的思想与作家对其思想之艺术传达是水乳交融、光雪互映的。深挚的思想不借助睿智的修辞无以传达,睿智的修辞离开深挚的思想则近于聒噪,真正的艺术追求必然如孔子所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9](P61)。
朱鸿确是一个有着强烈感情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但我以为,朱鸿首先是一个文学艺术家。强调这一点,并非轻忽其文章对于读者思想上的影响。我想说的是,朱鸿用诗一样光美的语言,创造了一部直抵人心的艺术作品,同时也就创造了诗意的生活。朱鸿时常对现实不满,但他不否定生活,而是积极地创造着生活,做他想做的事,写他想写的文章。像一切优秀的艺术家一样,朱鸿只是觉得现实世界应该更加完善一些,美好一些,人性应该充分地闪耀出智慧和道德的光辉。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宁愿把艺术家的创作首先看成个人自我完成的过程——艺术家不单是在创作艺术作品,同时也是在创造自己的艺术生活。
法国哲学家福科说:“难道每个人的生活不能变成为艺术品?为什么应成为艺术对象的是一盏灯或一座房子,而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把自己创造成艺术品。”[10](P423)我想,这正是朱鸿所向往与努力实现的人生境界。
[1]朱鸿.夹缝中的历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2]王锺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散文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4]王海明.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6]朱鸿.药叫黄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9]沈家煊.李白和杜甫:出生和“出场”[J].语文研究,2008,(2).
[10]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0.
[11]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