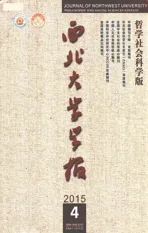存在、价值、境界—— 二程“儒佛差异”之辨新探
2015-02-23申冰冰
申冰冰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西安 710069)
儒学发展到北宋时期,有了重大的转折。“援佛入儒”是北宋理学的一大特色,显示出这一时期儒学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但理学也面临着重要的理论问题——儒家伦理体系的阐扬和回应佛学的挑战。早在二程之前,韩愈、孙复、石介、张载等人,都曾进行过判定儒、佛差异的工作。但程颢、程颐有别于其他学者的是,他们没有对佛学采取排斥的方法,而是从“理”的本体角度出发,集中从理、佛二家的精神境界、意识环境、伦理路数上的不同来叙述和阐发理学的精妙之处,取得了新的成效。
宋代理学、佛学二者有何差异①在北宋以前,很多士人主张“融合儒释”的思想。不仅儒家汲取佛道理论,外来佛教也在积极吸收儒家思想。到北宋时期,儒佛交融蔚成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儒士参禅蔓延开来。正是在二程等学人的倡导之下,北宋统治思想始终以儒家为主导,显示出了儒学在这一时期巨大的生命力。?面对这个困惑儒学研究的问题,程颢、程颐开创出有别于张载“气”的最高范畴——“理”,并坚定地回答了世人:“自家体贴出”的理学“援佛但非佛”。本文认为,二程以儒为宗进行的理、佛的差异之辨,不是为了实现批判佛教的单向目的,而是为把落脚点放在阐发北宋儒学本体理论之精妙和回应佛学挑战的双重目标上。
一、“佛学善诱”与二程“以儒为宗”的观点
理学思想开启于北宋时期,与程颢、程颐对儒学道德价值的反思关系密切。程颢、程颐察觉到,自汉唐以来的儒家经学虽然精妙,但拘泥于文字训诂,缺少义理之魂魄在其中,这也是佛门兴盛、儒门式微的重要原因。而有精深理论体系的佛学,经过唐代“三教并尊”政策的提倡,至北宋时期已经开始弥漫天下。面对“极乎高深”并逐渐在中原大地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佛家理论,二程也肯定“佛说直有高妙处”[1](P425)。为使儒学走出衰落与僵化之困境,二程开始克服保守而努力“尽用其学”[1](P425),对儒学进行既有创造又有发展的文化会通活动。
二程在理学奠定的关键时期,以创造性的思维“援佛入理”。在世界本原方面,二程将华严宗的“理事”总结为“万理归为一理”。他们在“佛学影响下对《易》学改造,为世界安上了一个头——即‘理’或‘天理’”[2](P589),认为万物蕴含着共同的宇宙道德之理,开启了宋代以“理”范畴为形而上学的本体体系。其次,二程在阐发养心、体悟等“成圣”之说时提出的“主敬”之道德涵养理论,其实带有佛学的影子,其语“心存诚敬耳”就脱胎于禅宗的“坐禅入定”说。显然,二程撷取了儒家的人文、宇宙道德观,并借鉴了佛家的修养境界学说及其佛性观念,使先秦时期孔子、孟子在道德层面上的心性之学,获得了“性与天道”上的构建,从而使儒家文化获得了心性与本体、道德与天道的联结,实现了儒家学术会通佛学文化的重大变革。
可见,渗透着佛学思想的理学很大程度上已经有别于早期孔孟之学,但在深蕴“理”之道的二程看来,尽管佛学善诱,理学毕竟是以儒学“门庭”来自居的。面对时人常发“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感慨(《蒿庵闲话》卷二),二程不甘理学被世人认为是“披着儒学外衣的佛学”,认识到宋代儒学要“当自明吾理”,才能达到“彼不必与争”的目的[1](P38)。在汲取佛家理论的同时,二程强调理学必须摆正孔孟之学的地位,其精髓即儒家义理的渊源不能被忘却。正因立场坚定而又深明儒学之理,他们“出入佛老几十年”,而能“返求诸‘六经’”[1](P638),逐渐使儒家思想向重本体化方向发展。也正因此,面对急需解决的“儒(理)佛二学差异”问题,站在理学门庭之内的二程不为佛所“乱”而心中甚为分明,他们旗帜鲜明地表达出理学是儒学一脉的思想,并进行了有着独特眼光的儒佛差异之理论分析。
二、二程的儒佛之辨的理论角度
(一)“修养境界体系”差异:理学强调居敬之修养工夫
作为理学的奠基人,二程学说体系虽没有脱离早期儒学的伦理道德特征,但比之前更重视境界修养,可说是一种“内圣”之学。宋代以前,人们称佛学、道家为境界内学,而儒学为事功外学,但到了北宋理学时期,因儒学亦主“内修”而使这种区分标准有所改变。理、佛二家主张的“敬”与“静”,皆是一种冷静的人生态度和理性的“内倾”心理结构。虽然二程没有否认儒、佛在“思绪集中”的身心修养方法上有一致性,但在“敬”与“静”修养的心理内容上,他们认为两家有根本区别,从而在“理佛之辨”上迈出了第一步。
面对世人由于对“敬”与“静”之间的认知偏差而形成的理佛境界修养差异的问题,二程做出了坚定的回应并以此来标榜理学修养之法的精妙:
才说入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不用静字,只用敬字[1](P189)。
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1](P169)。
毕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焉,“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1](P74)。
从第一条可以明显看出,二程一言点破如果无法体会到理学“居敬”与佛学“持静”境界的差异,就会陷入理与佛修养上的歧义,这也是许多理学家没有辨别出二字的差别而陷入佛道之学的关键,所以二程才指出“才说入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为了与佛教有所区别,他们修正了周敦颐“主静”的内圣修养方法,而从“涵养须用敬”[1](P24)的层面上,阐发对明诚的修养工夫——居“敬”的基本认识意图。二程说:“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作敬。”[1](P11)这样的言论承认“敬”与“静”一样需要思虑,但强调二字背后的企图和目的不同。二程认为在修养境界问题上,理学主“敬”异于佛学主“静”。理学之“敬”与“诚”相联系,乃以人伦道德为内容的诚心之义,佛家之“静”却要求忘却俗世之烦忧,以抛却人伦纲常为本意。何谓“敬”?请看第二条:二程强调“敬”不能离开孔孟纲常伦理之道德境界,忘却此人伦纲常,就不是“敬”。但这种“敬”不是对待圣贤的“敬畏”“尊敬”之心,而是源于心之本初的状态——“诚”,此字可理解为“使自己的思想专注于一人或兢兢业业专注于一事”[3](P4)。《中庸》指出:“诚者,自诚也。”程颢对此解释:“诚者自诚,如至诚事亲则成人子。”(《二程粹言·论道》)无疑,二程说的“敬”是指在内心专注、慎重的基础上,对待君主、父母、兄弟应有的不虚假之虔诚态度。
从第三条可以看出,二程十分赞同《易经》“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说,指出佛家所重“静”是“忘”,即忘却心中一切“七情六欲”之世俗根,所以“义以方外”是佛家所不具备的。二程强调,理学之“敬”表现的并非只是箴言警句的空洞形式,而是有具体道德内容的修养工夫,由此他们倡导的“敬”,是一种“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的内外兼备的修养方法[1](P74)。“直内”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工夫,更近一步,二程提倡要通过个体内化于心的道德本性来行“方外”之仁义。这样的“直内”与“方外”结合的修养理论指明:儒者应持有一种以居敬、明诚为方法的内、外兼具的和谐存养工夫。程颐认为“持敬”就要“闲邪则诚自存”[1](P149),“闲邪”就是要自觉防止邪恶浸入体内,他强调儒者在修养的过程中,要将“仁”内化于心,同时也要认识到人与外界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据此提升人之道德修养境界和社会责任感。显然,二程试图将儒家的“成圣”道德论和知识修养论相融合,这种目的使得其理学的修养工夫实际而不显空洞。显然,二程的践履道德观点与佛教没有社会实践的内容而只追求精神之过程迥然有别。
可见,佛家的“静”虽也具有“诸如调息、静思等操持……但却是没有任何社会行为的纯粹的精神过程”[4](P443)。而二程明晰理学的“敬”之涵养工夫,是“自我”在与“他人”“他物”的实践过程中,避免外物干扰牵绊依然维持伦理纲常的工夫,故“格物”修养是恢复天理、修养心性的必需。如此,二程一方面将“敬”的修养规范化成为了一种更有普遍意义、绝对性的“天理”律令,另一方面又使得“敬”的修养没有脱离人们的日常道德生活。理学“此严整的道德意识下”,更加强化了“内圣之教的‘精微’”[5](P166),二程鲜明地指出儒者的修身与佛教的修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法。
(二)“意识认知环境”差异:倡导世界存在着本体之实理
作为理学之奠基人,二程明白儒佛修养方法上的差异,乃是根源于二种学说对世界存在状态上的认识迥异。佛教将意识之外的世界看作是虚灵、宁静的“空”境之状态,认为如果个体过于追求物之“实”就是“执著”。相反,二程强调世界呈现的是万象更新的人伦景象,万物是真实存在的,一切伦理道德离开人伦社会乃不可言说。
二程从“认知”和“本体”的两个层面,就儒、佛二家对世界“来龙去脉”看法有何不同,做出了特有的辨析。
第一,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在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上,首先反驳了佛学认为世界的存在是“四大皆空”的理论。二程认为:“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1](P73)在他们看来,佛教把外缘(外在事物)看作是如梦似幻之空、无、假,虽对破除人心痴迷尘世有用,但又容易使人陷入认识上的狭隘性。因为佛家“在观念上和行为两个方面都将道与物隔成两截”,这样的佛家意识“不是整体的,而是分裂的”[6](P343)。二程提倡“格物穷理”来体认外物,他们认为不去和世界外物接触,就谈不上成圣之“理”。所以,二程认为世界不是简单的“有”或者“无”的存在,而是一种永恒而真实的伦理道德呈现状态,而不像佛家所认为的世界是脱离现实生活的“虚幻”。程颢《春日偶成二首》其一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诗中描绘出的生机盎然的“近午”,川流不息的“前川”,是一个充满人的流动生命之世界,置身这样的人伦世界,诗人“乐在其中”。
其次,在认识到世界“实有”状态的基础上,从最高范畴——“理”之层面,阐发了对佛教“诸法刹那生灭”没有永恒不变之主体的反驳观点。儒学发展到二程,最主要的特征是把“理”的概念升华,摆脱了汉唐天命观的虚妄,使“理”与“人”真实地联系起来,具有了既有宇宙论又有本体论的意蕴。而在佛教看来,万物的一切活动乃至生与死,都是“一切皆空”的表现。针对佛教之“空”的认识理论,二程指出:
物生死成坏,自有此理[1](P3)。
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实有是用,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终而言也[1](P116)。
可以看出,“理”在二程体系中作用之重要。程颢、程颐最高的哲学本体范畴是“理”,他们的“理”之范畴虽借鉴了佛学的本体论,但正是以此“理”来回应理学和佛家差异之处。何谓“理”?“理”乃“天地万物普遍存有的根据,也是最深层的价值源泉”[7](P36)。程颐指出:“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说皇天震怒,终不是有人在上。”[1](P290)因此,能被“人”感觉的世界无处不是理。二程认为充满流动生命之世界背后,是一种本体实“理”;有“理”则有气、象以及天下万物的繁生不息。可见在二程这里,“理”或“天理”已经从认知的范畴上升到了具有本体性内涵的范畴。在二程看来,理学本体与人之生命相关联,落脚点在人性论,而最后的归宿则在社会的人伦纲常上。二程构建的理学之根基恰是社会中存在的君臣、夫妇、兄弟之伦理,离开这些实实在在的社会伦理,就脱离了儒家入世的本质,“理”之本体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人生价值观”差异:主张体认“理”要躬行践履
二程承认世界是真实的“有”,并在此基础上,充满热情地在社会之“理”中追求道德纲常。孔孟就曾经提出人只有致力于追求仁义道德,才能发挥出有限生命的熠熠光辉。二程在孟子良知、良能论的基础上有所继承与发展,以凸显人的社会价值本性,从而在“理佛差异”之辨的理论中,迈向了更高一层,即理学是以追求天下“人”与“万物”生生不息的和谐之道为终极目标的。
首先,儒、佛二家对“人应该追求什么”问题的不同回答,其实与对待生死观的不同态度有关,二程认为:
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死生。佛之学为怕死生,故只管说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惧,易以利动。至如禅学者,虽自曰异此,然要之只是此个意见,皆利心也[1](P3)。
这些语句鲜明地道出了儒学与佛教的生死观的区别,即“儒家生死观的特色在人伦,佛教生死观的特色在破执”[8]。人活一世,难免要面对死亡。佛教的心理因素是对死的恐惧,它的宗教目标在于“彼岸”,可见佛家重视死要过于生。但儒家给出的是相反的答案——死亡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死后人们对自己的评价。在孔孟看来生前对“他者”做出的一切,能够对身后产生重要的影响。虽然,二程上承周敦颐重修养的理论,减弱了早期儒家奋发有为的政治思想,但为家国天下践履的道德方向却依旧没有迷失。二程赞同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认为“死生存亡皆知所从来,胸中莹然无疑,止此理尔”[1](P17),也就是说生与死是分内之事,人生完满的终结是以人伦道德的实现为标准的。
其次,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不同,亦决定了二种学说人生追求的目标的不同。二程虽然认同儒者应该有“留芳百世”的追求,但反对“徇名为虚”而以务实的治平为己任。如程颢就是以仁人的追求为人生目标,他在《识仁篇》中云:“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1](P83)在程颢的话里,我们可以体会出:仁是包罗义、礼、智、信之理,“识仁”是人之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首要源泉与基础,而程颐以充盈万物的“仁者”情怀来体物,贯穿了《周易》中“天地之大德谓生”的理论(《周易·系辞传》)。二程指出:“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认为宇宙万物的创生过程是道德实践的过程,与万物同源的人身上也应该具备道德。人如能在修养的基础上以仁者之心关怀万物,便能实现一种完满的人生。
在“识仁”的理论上,二程进一步指出理学、佛学在人生追求本质上的差异:
圣人致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各当其分;佛氏总为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1](P142)?
君子之志所虑者岂止一身,直虑及天下千万世[1](P41)。
可以看出,程颢以公与利来定义“人之为人”的本分,他指出的“圣人致公”,与佛家的“一己之私”直接对立,这是从二者的现实功效上做出的立场差异之辨。程颐进一步强调:“佛逃父出家,便绝人伦,是为自家独处山林。”[1](P149)也就是说他们反对佛家从一己的个人私利来思虑人生,认为儒者不能枯槁山林,不能像佛家一样抛却个体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相反,应该在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中努力去完成人之应尽之“分”。而以“直虑及天下千万世”为实质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的追求,在二程看来就是人之为人的道德本分。这种观察立场和结论所内蕴的人伦内容和道德品性,就是程颢所说的“圣人致公”。所以,从追求的本质上看二程的“存天理,灭人欲”,就会发现他们灭的是自我私欲,追求的是对家国、天下的“大无我之公利”,而不像佛家所说的斩断一切人世间牵绊之“七情六欲”而为“自我”找寻归宿。同时,二程把孔子“推己及人”的范围扩大化了,把对人的仁爱之心,扩大到万事万物,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展现出了一种更广阔的仁者胸襟。
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否定佛家全是为“私我”而无“利他”的价值观。佛家在发展中也显示出不同脉络,如小乘佛教与儒学的宗旨虽异,但也显现出一种“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以拔一切众生苦”慈悲为怀的精神(《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面对小乘佛教的“大慈大悲”之理论,二程以“公”和“私”的人生目标来判定儒、佛两学之区别,这样的的理论是否成立?其实,理学的追求虽是以“为己”开始,但“为己”境界必须环绕“趋于道”的儒家伦理标准来进行,即以“推己及人”“推己及物”为目的,实与小乘佛教从“为己”的烧香祈福到“为己”大获福利的“私”的循环有着根本区别,所以,从追求终极的社会目标上来说,二程的阐述是能够成立的。
三、二程的“儒佛差异”之辨的价值
二程重视“内圣之道”甚于“外王事功”,但没有忘却以孔孟的伦理道德思想作为理学的灵魂,认为理学独有的修养境界、意识环境、人生价值观与佛教迥然有别。那么,二程辨析二学性质差异的意义是什么?
一方面,北宋理学力排佛学,但其学说又难免沾染佛家理论,所以既融合又有所创新是宋代儒学的特征。然而,面对佛学之袭,出现了“儒者而卒归异教”的“释氏盛而道学萧索”之局面[1](P156)。因此,重塑儒学“信仰”地位的责任意识,激起了二程的儒者本位意识。二程思虑到“惟当自明吾理”,才能重新燃起理学家的儒者基调,因此他们虽“援佛入理”以使自己的理论更加精妙,但还是没有忘却对儒家思想的重新整理,终于“完成了为儒家伦理建造哲学理论的使命”[9](P144)。
另一方面,二程看到士人在亲近佛学中出现的“忘却身外之人伦”的精神状态,无益于改变北宋时期社会“积弱”的局面,因此他们发出了对佛家“卒归乎自私自利之规模”的痛斥之声[1](P152)。他们看重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希望更多的时人不要沉浸在佛学的忘君、忘父、忘兄弟的人伦虚无之中,而更多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这样的“忧国忧民”以治世的责任呼唤,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促进北宋时期社会的改良。惟其如此,二程才以异端称佛。
带着坚定而自信的儒家观,二程云:
今言当世之务者,必曰所先者:宽赋役也,劝农桑也,实仓廪也,备灾害也,修武备也,明教化也。此诚要务,然犹未知其本也。臣以为所尤先者三焉,请为陛下陈之。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谓也[1](P143)。
这些话虽是对君主所说,但流露出的是对儒家仁义道德说的崇敬。话语深处,已经揭开了“理学”特有的儒家精神实质,其中包括“仁为王道之本”的仁政观、“以厚民生为本”的民本论、“择任贤俊”的人才思想等。从二程的理佛之辨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们面对佛教理论的挑战,希望冲破佛教思想笼罩,扭转北宋时期的虚妄之风,而倡导一种济世的儒者情怀,因此在重新树立宋代儒家权威方面,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在他们的带动之下,后世理学家无论是朱熹“理学”还是陆九渊“心学”,都依然高扬儒家之道德思想并续续不绝地影响着世人。二程奠基的理学思想在和佛学交锋的过程中,逐渐如日中天,成为了宋代的主流思想。
[1]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张岂之.中国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
[3]葛瑞汉.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4]崔大华.儒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蔡仁厚.宋明理学北宋篇[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
[6]卢国龙.宋儒微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7]许总.宋明理学与文学[M].上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8]刘立夫,张玉姬:儒佛生死观的差异——以二程对佛教生死观的批判为中心[J].孔子研究,2010,(3).
[9]李书有.儒学与社会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