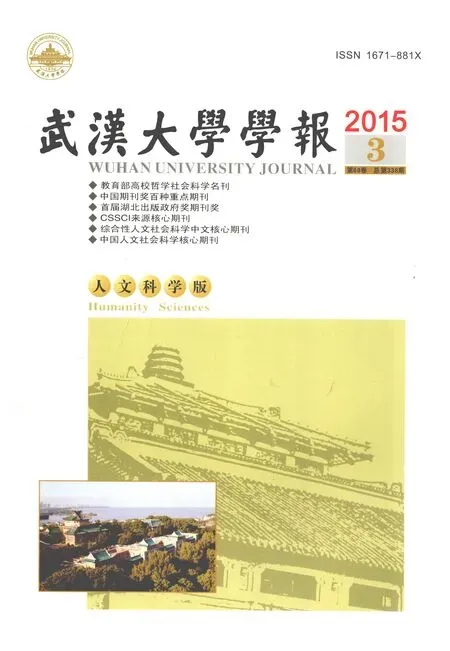王朝文治与清代御定宋诗选——以康熙《御选宋诗》、乾隆《御选唐宋诗醇》的编撰为中心
2015-02-22谢海林
谢海林
王朝文治与清代御定宋诗选
——以康熙《御选宋诗》、乾隆《御选唐宋诗醇》的编撰为中心
谢海林
摘要:从某个角度来说,探究占有主体性的选家也许比诗选、读者更重要,因为他是选本生成的施动者。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对选家编纂诗选以及刊行等一系列活动都有显性或隐性的干预和掌控,凭藉专断的王权来争夺选家的话语权力,规训选家;另一方面亲自裁定体例,厘正选目,删削内容,改动版本,藉助御定选本直接来宣示符合皇家文治的权力话语。皇权介入选政,以诗教维护政统,节制了选家握管操觚的主体自由,也影响了宋诗学建构的文学空间。反过来,选家一旦脱离官方权力的掌控而退居民间,在私编诗选或和其他选家交往时,也会作出一些诗评家本色甚至背离官方话语的诗性反应。
关键词:《御选宋诗》; 《御选唐宋诗醇》; 选家; 诗教; 话语权力
一、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设想
辑纂诗歌选本乃名山事业。选本的最终旨向,就在于“选者之权力能使人归,又能使古诗之名与实俱狥之”*钟惺:《诗归序》,李先耕、崔重庆标校《隐秀轩集》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通过编纂诗选,选家可阐述一己之见,表达诗学主张,还可借助选本的典范作用以求得桴鼓相和的集体效应,影响到个体之外更广阔的人群,延宕到更久远的时空。明末艾南英就把选家、评论家的权力比作皇帝的权力。因此,不论私人选家还是官方机构甚至君主、藩王等权贵对此青睐有加,或亲自裁定,或主持选政。表面上,清人所编宋诗选本由于选录对象相隔较远而非当代同好,摆脱了作者的各种影响,选家应更能专注评选,施以己意。“虽选古人诗,实自著一书。”*钟惺:《与蔡敬夫》,载《隐秀轩集》卷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69页。那么,辑纂宋诗选本的选家是否真的是一个纯粹的编创主体呢?
从编者的身份构成着眼,大体可分为官、私两类。从编者的人员寡众来看,又有群体与个人之别。从选政的运作模式来考量,既能以个体一己之心力操觚染翰,还可藉助群体力量联手共襄。从诗选的生成机制来讨论,既有选家“闭门造车”式的“专断”,以一人之意餍服众人之心,同时也存在选家受到诸多外力因素,尤其来自官府、学界、出版业的干扰,最终达成群体“合谋”。由此生发,不管是官方主流权力的染指,还是民间文士精英的倡扬;无论是纂辑总集而不著一语的隐性批评,还是遴选作品而施加评语的显性品鉴,编者的话语、权力都能作用到选本的辑录、编排、评点、刊行等流程之中。正由于话语、权力对编选活动影响甚巨,因此官私双方常藉助选集来表达自身的思想与立场,申诉自我的话语和权力。由此看来,选诗是彰显选家话语权力的重要活动形式,诗选是演绎选家权力话语的有效传播载体。选家的话语/权力与选本之关系极为密切。清人所编的宋诗选本康、乾两朝是最多的*谢海林:《论清代宋诗选本发展历程及其特征》,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不可否认,清代民间私家所编宋诗选本占了绝大部分,皇帝御定的两部含有宋诗的大型选本《御选宋诗》和《唐宋诗醇》不容忽视。学界关于这两部御定宋诗选的研究寥寥可数,且只限于版本异同、编选宗旨和选家观念等方面*莫砺锋:《〈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胡光波:《从〈唐宋诗醇〉看乾隆的唐诗观》,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王苗苗:《〈唐宋诗醇〉诗学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卞孝萱:《两本〈唐宋诗醇〉之比较研究》,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李靓:《清代御选宋诗研究》,2010年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重要的是,帝王或行政干预,规训选家;或亲自题序,擅作准则。百般钳制之下,编者在选录运作中并不是艺术价值判断的纯粹主体,其甄选评骘自然难以出于公心,而是更多地打上了君主专制思想的烙印。故从诗选编纂的文化考察出发,通过权力/话语等角度来探讨选本的生成机制和审美旨趣,着眼康乾两朝宋诗选集的编者,关注权力场与文学场的离合,尚有可拓展的空间。
二、 政统·诗教:康、乾御定宋诗选的文化考察
(一) 编校人员的际遇、身分与皇权钳制
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大肆招揽名士,尤其是东南俊彦入朝为官,一方面鼓吹休明,润色鸿业,安抚遗民,调和冲突,另一方面借辑书撰史之名,笼络江南士子,阴行怀柔之术,极尽羁摩之事*张宪文:《清康熙博学鸿词科述论》,载《浙江学刊》1985年第4期。。参与《御选四朝诗》的编校人员,大都有如此般的际遇。据《御选宋金元明诗》卷首所附参编校勘37人名单,有以张豫章、魏学诚为首的纂选官6人,以吴士玉、张大受、顾嗣立等为主的录选官22人,以及杨瑄、查昇、陈壮履、钱名世、汪灏、查慎行等校勘官9人。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顾嗣立、张大受、吴士玉为首的数十位纂校人员特召入朝编书。康熙四十四年(1705)帝南巡,四月十二日驻跸苏州,巡抚宋荦疏荐张大受、顾嗣立、吴士玉等人。十四日,召试举贡监诸生和山林川泽之士,顾嗣立一干人等被录选。十月,康熙开设“四朝诗馆”,选址怡园,从十二月一日开始纂修,已到的录为翰林,未到的“在家纂选”,“人授一廛,岁有俸米,月给百金”,赏供纸笔*顾嗣立:《闾邱先生自订年谱》,载《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9册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80~81页。。纂修人员在生活待遇、工作环境、仕宦前途等方面备受优待。破例擢用淹蹇落拓的江南士子,一跃而跻身馆阁,修校秘府书籍,这是康熙朝后期右文政策的常式。他如查慎行,四十一年(1703)康熙南巡,李光地以学问人品引荐查慎行。查氏和后来一同参与《御选四朝诗》编校的汪灏、查昇,“每日进南书房办事,先是内廷皆词臣轮班入直,专命之荣,盖自此始”*陈敬璋:《查他山先生年谱》,载《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丛刊》第86册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恩遇特重,罕有同侔。此后,查慎行开始奉旨编纂《历代咏物诗》、《佩文韵府》及校勘《四朝诗》。像查昇、陈壮履、钱名世、汪灏等编校人员亦在此列。此外,尚有陈鹏年因遭弹劾而被康熙召京修书之特例。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时任江苏布政使的陈鹏年被两江总督阿山系狱,康熙诏谕免死,命其“抵京师纂修《宋金元明诗》”*李果:《家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64,载《清代传记丛刊》第153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789页。。五十一年(1712)十月,总督噶礼诽谤苏州知府陈鹏年游虎丘诗,康熙又加以回护,再召入京修书*《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64,载《清代传记丛刊》第153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735页。。他如校勘官杨瑄,四十二年(1703)春康熙南巡驻跸杨瑄故里松江,念其学问甚优,诏复原职,充馆修书。乾隆朝编纂《唐宋诗醇》时,诸如梁诗正、钱陈群等编选校刊人员也可作如是观。梁诗正,雍正八年(1730)探花及第,后归家守制。乾隆元年(1736),谕曰:“向来翰林丁忧者,有在京修书之例。梁诗正著来京,在南书房行走。”*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20《梁诗正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1529页。九年(1744)翰林院修葺完工,乾隆临幸,诸臣毕集,赐宴赋诗,“十一月命(诗正)选《唐宋大家诗醇》。”*王昶:《行状》,《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3,载《清代传记丛刊》第138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693页。由此可见梁诗正际遇非凡,至于钱陈群,更不消细说。他如陆宗楷、陈浩,亦有此般眷遇。
概言之,参与编校群籍、修书纂史的人员,多为翰林院、詹事府属官,和一小部分超擢任用的举人、贡生及国子监监生。据《清实录》所载,从康熙到乾隆,不止三番五次申谕翰詹职任紧要,乃亲近天子之臣,必由文学淹通、众所推服者充任。但果真如昭梿所说,君臣“无异同堂师友”*昭梿:《啸亭续录》卷一“南书房”条,中华书局1980年,第398页。吗?身份的显贵,并不意味着获得了皇帝的认同。他们的角色逐渐发生转变,而沦为帝王加强统治、附庸风雅的工具。比如经筵会讲。康、雍、乾通过一系列改造,帝王的听众角色转变为评论者,士君教化角色已悄然逆转*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91~102页。。昔日讲官的“帝师”地位也随之动摇,道统的掌控能力彻底位移到专断的帝王手中。回到本文所关注的辑纂诗选上来,皇帝对文学弄臣的优渥,迫使选家在握管操觚中逐渐丧失诗学批评的审美自主权力,转向鼓吹隆平,成为帝王文艺政策的代言人。选家承受着皇权的无限压制和干预,话语权力也逐渐被侵蚀剥夺,甚至消失殆尽。
不可否认,康熙、乾隆对汉文化尤其是诗赋格外喜好。但是,清帝嗜好诗文的背后掩藏着汉文化侵袭满族习俗的担忧。“八旗入关以后渐弃旧俗,满语和骑射日益荒废,康、雍、乾三朝屡次下谕要八旗子弟熟习弓马,并规定必须能马步箭才准作文考试。”*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86~187页;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显例如乾隆,三令五申告诫宗室子弟勿失满洲旧俗,万万不可专事文学,废弃紧要的骑射技艺。早在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乾隆明确地指出,写诗作赋应根柢经术,“关于世道人心”*《清实录·高宗实录》(五)卷352,中华书局1986年,第860页。。御选《唐宋诗醇》之际,乾隆十年(1745)“李慎修尝谏乾隆勿以诗为能,恐摛翰有妨政治”*徐世昌:《晚晴簃诗话》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乾隆特作诗《李慎修奏对,劝勿以诗为能,甚韪其言,而结习未忘焉,因题以志吾过》云:“慎修劝我莫为诗,我亦知诗可不为。”*《御制诗集·初集》卷二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如此一来,帝王干预诗坛、操控选政自是意料之中。
康熙对诗风的钳制,学界屡屡称引的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翰詹大考,徐乾学、韩菼等因学问、文章加以赏赉奖励,而周之麟、钱中谐等“文理荒疏,未娴体式”*《清实录·圣祖实录》(二)卷119,中华书局1986年,第251页。,难胜厥任,不是降调,就是他用。升降褒贬判若云泥,这固然与康熙的审美趋尚极有关联,同馆中人毛奇龄曰:“近学宋诗者,率以为板重而却之。予入馆后,上特御试保和殿,严加甄别。时同馆钱编修以宋诗体十二韵抑置乙卷,则已显有成效矣。”*毛奇龄:《西河文集·诗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213页。可看出康熙干预诗坛,整饬翰詹,推行文治的铁腕手段。这也波及到选坛。康、乾钦命“儒臣选择简编,皇帝亲为裁定,颁行儒宫,以为士子仿模规范”*《啸亭续录》卷一,第400页。的各类书籍,经史子集共达147部。《御选四朝诗》虽无康熙直接干涉选家、把持选政的证据,但从校勘官查慎行等人奉勅编纂其他总集的活动来看,可旁证出康熙在操觚染翰中的无上权力。现以《佩文韵府》为例详论之。是书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二月设局始纂至五十年(1711)十月告成,而《御选四朝诗》正编刊于此时。四十八年(1709)四月,“二十四日,上谕云:‘汝(查慎行)学问好,可赴武英殿督纂《韵府》。’受命后,即偕钱亮功、汪紫沧两同年,竭力蒐采,每卷帙排日进呈,一字一句俱依旨定夺。”*陈敬璋编:《查他山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丛刊》第86册影印本,第346页。词臣辑纂典籍,每日进呈,编纂之体例、择录之字句均须依旨定夺,可谓事无巨细,干预之迹昭然若揭。有查慎行《武英书局报竣奏折》为证:“《韵府》一书,尤宸衷所注意,钦颁体例,御定规模。每卷每帙,排日进呈,一字一句,遵旨定夺。其间繁简去留,尽由指授;源流本末,咸奉诲言。诸臣采掇弥年,而皇上披览一过,皆渊衷之所熟记。诸臣广搜众籍,而皇上开示片语,悉愚昧之所未闻。”*范道济:《新辑查慎行文集》卷一,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页。六月二十三日“进呈分类诗《凡例》及选诗,五类俱称旨,今日发下,命照此例编辑”*陈敬璋编:《查他山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丛刊》第86册影印本,第247~248页。。不单是选政的掌控,康熙对编纂人员也极为关注:“所奏《佩文韵府》告成,知道了。这折内修书人员,谁修的多?谁修的少?走了几年?谁勤?谁惰?可令查慎行、钱名世、汪灏等查明,即注在名单之下,再奏。”*范道济:《新辑查慎行文集》卷一,第22页。钱名世、汪灏、查昇也是《御选四朝诗》的校勘官。即便康熙在位最后一部钦命编纂的《御选唐诗》,也是“命儒臣依次编注,朕亲加考订,一字一句,必溯其源流,条分缕析;其有征引讹误及脱漏者,随谕改定”*《御选唐诗序》,《御选唐诗》卷首,康熙五十二年(1713)刊本。。
至于《唐宋诗醇》,虽说署名称“乾隆帝御选”,而乾隆坦言“去取评品,皆出于梁诗正等数儒臣之手”,“所选六位诗人的名单是乾隆帝‘御定’的”,“是一部乾隆朝馆阁文臣的集体著作”*莫砺锋:《〈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乾隆没有染指具体的编选吗?莫砺锋认为,“虽然全书总的编选宗旨并无歧异”,但“此书在定稿时肯定经过一番整合的工作”*莫砺锋:《〈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此种推定不为无据。其中所辑录的苏轼诗评,即出于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王友胜认为:“乾隆御编的《唐宋诗醇》选苏诗10卷,诗500余首,不仅选目与汪氏之作大同小异,诗前总评几乎径抄汪氏《苏诗选评笺释叙》,而且连对所选苏诗的评语也与汪评如出一辙。”*王友胜:《苏诗研究史稿》(修订版),中华书局2010年,第241页。惜未有深论。这个问题早在1928年9月29日,汪辟疆考证“苏诗选本”时已有详察。
钱塘汪韩门尝选《苏诗选评笺释》六卷,即世所传《唐宋诗醇》底本。乾隆九年甲子诏选《诗醇》,梁文庄实董其事,御制序所谓“去取平品,皆出梁诗正等数儒臣之手”者也。韩门未与修纂之役,而与文庄为乡人,且同居京师。文庄即以苏诗一卷相属,此书即其原稿也。……《诗醇》既为御定,词臣草创底本多不敢出,或即焚弃以灭迹。……即原稿评语亦与《诗醇》本互异,则此稿进呈后之窜改可知矣。*张亚权编:《汪辟疆诗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9页。
“以爱憎加入”窜改原稿,并且“词臣草创底本多不敢出”,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只有乾隆了。不只是定稿作过手脚,翻印重刻也有删改。这着重表现在对所录钱评杜诗上。据考证,《御选唐宋诗醇》有内府本(及翻刻本)与四库全书本之不同。内府本于乾隆十五年(1750)编定,次年刻成。此时乾隆尚未公开敌视钱谦益,故编者采录了钱氏评语。此后乾隆二十五年、光绪七年等翻刻本一并照旧。但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写定的四库全书本,已在三十四年(1769)下诏将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禁书毁板之后,《钱注杜诗》自然未能幸免*卞孝萱:《两本〈唐宋诗醇〉之比较研究》,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这缘于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置钱氏于卷首。乾隆干预诗选,这时已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官方御选的《唐宋诗醇》与私家辑撰的《国朝诗别裁集》俱遭厄运。选家黜名,选目删削,底稿藏匿,内容窜改,版权褫夺……选政所关涉的方方面面,赤裸裸地受到了来自上层统治者的干扰,压制,乃至操控。选家的话语权终究敌不过专断至上的皇权。
(二) 官修选本的缘起、体例和政治教化
康、乾祖孙以极高的热情与兴趣直接参与诗歌创作、品鉴活动,并鸠集文臣编纂天下典籍,辑选诗歌总集。众所周知,康熙、乾隆的诗学观念向以唐为主,这两部“御选”、“钦定”的巨帙又缘何而编?
编纂四朝诗并非心血来潮。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到五十二年(1713)《御选唐诗》付梓,是康熙后期钦命词臣辑撰诗词文总集的高潮期,短短八年间共计八部,除《御定全金诗》72卷、《御选唐诗》32卷之外,其他皆逾百卷,多的高达900卷,堪称皇家编书之最。这是《御选四朝诗》诞生的大背景。《御选四朝诗》312卷,其中宋诗部分78卷,姓名爵里2卷,选录作者凡880余人。《御选宋诗》的编纂体例,也可佐证康熙专断的君权思想及其文治铁腕。首先,体例大而全。从帝王贵胄到俊彦硕士,从僧尼道侣到渔卒走贩,无不网罗其中,以诗存史、以史存人的历史正统观念极其明显。这其实就是一种话语霸权。此种以人为纲,先帝王次后妃,余以年代为序,末为僧侣闺阁以及无名氏的编排,肇自于宋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而计著乃一部私人编纂的纪事体诗歌典籍,主要辑录有事之诗,以事附诗,以诗传人。康熙则凭借无上的政治权力将私人著述体例挪用至官方编纂活动中,前有《全唐诗》,后有《四朝诗》等,将帝系权威凌驾于宋代诗史统绪之上,这无疑是官方政治权力对民间私家话语的明争暗斗,并以“话语”形式(总集)来实现官方在意识形态、文学场域中的话语权力,而且竭力去维护、强化和掌控。其次,选目偏重朱熹等理学家之诗。据统计,朱熹入选583首,雄踞第一,近占其诗歌现存总数的一半。其次苏轼558首,陆游483首,而与苏轼并称的宋调代表黄庭坚区区90首。所选诗歌多关注言之无物的宫体诗、咏物诗,粉饰太平的山水诗,而那些感情真挚、辞采高华的遗民诗、思乡诗却难得一觅*李靓:《清代御选宋诗研究》,第20、21、23页。。可见,《御选宋诗》建构的并不是完整而公允的宋诗史,反倒彰显出康熙借助理学、理学家之诗来教化民众,以文治巩固统治的良苦用心。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御选宋诗》的诞生,也与康熙当时的诗学观念以及身边文官词臣的诗学宗尚有关联。康熙贬黜钱中谐等诗学宋体的翰詹是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是时王士禛已完成了《古诗选》的编撰,由宋返唐的气味日益浓厚,至二十七年(1688)辑撰《唐贤三昧集》,“神韵诗说”风靡朝野,这一时期宋调稍衰,唐风转盛。但随着康熙四十三年(1704)秋,王士禛因陷夺嫡之事而罢官归里。宗宋的陈廷敬、查慎行、查昇、汪灏以及入选《江左十五子诗选》的吴士玉、钱名世、张大受、顾嗣立等《御选四朝诗》选校官供奉内廷,入馆修书。为了凸显帝王大一统的文化企图,在主唐的诗学观念之下,兼及宋朝以下,这是文治策略的必然选择。康熙南巡苏州,宋荦进呈为宗宋诗学张目的《十五子诗选》*王兵:《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3~166页。,大获康熙赞誉,随后引荐的一干人等大多效仿中晚唐诗或宋元诗,宗宋诗风渐趋明显,因而康熙钦命其入朝编纂四朝诗,随材录用可谓自然而然。当然,也别忘却宋荦此选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振兴风雅”。这更合乎康熙藉助编纂诗歌选集教化民心,总持风雅,以政教统摄诗教的意图。
文章盛衰,关乎世运。诗韵小书,亦补治道。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八月,康熙谕曰:“文章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骚人词客,不过技艺之末,非朕之所贵也。”*《清实录·圣祖实录》(一)卷43,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572页。《御选宋诗》的前一年康熙四十五年(1706)六月,由查慎行代拟的《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序》略云:“朕于诗之道,时尽心焉。”“昔者子夏序《诗》,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若是乎,诗之道大矣哉。”“将使之由名物度数之中,求合乎温柔敦厚之指,充诗之量,如卜商氏之所言,而不负古圣谆复诂训之心,其于诗教有禆益也夫。”*《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卷首,康煕四十五年(1706)武英殿刻本。推崇温柔敦厚,强调教化功能,这是康熙一以贯之的选诗写诗宗旨和出发点。《御选唐诗序》也说:“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御选唐诗》卷首,康熙五十二年(1713)内府刻本。《御选四朝诗》也不例外,“措之礼陶乐淑之中,被以温柔敦厚之教”,“用以标诗人之极致,扩后进之见闻”,最后“皆本于一人之心”,统归于“思无邪”的诗道*《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序》,《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卷首,康煕四十八年(1709)内府刻本。。“温柔敦厚的唐诗自然最适合表现康熙间国家稳定、政治清明之际的诗歌审美祈向。”*黄建军:《康熙与清初文坛》,中华书局2011年,第218页。为何延及宋以下四朝之诗,包括诗余、辞赋?除了调和唐宋诗论争,笼络天下士子之外,最重要的目的是文章诗赋乃士之性情所发,能窥见本心,陶淑礼乐,鼓吹休明,契合盛世治象,故而帝王若将其化为己用,成为经邦治世的有效工具,不失为诗教之最高功用。前文提及的《御选宋诗》录选官陈鹏年,数次被权要弹劾,但康熙每每为之回护,召其进京修书,也是因为陈鹏年“长于诗,工于翰墨,以文为其政教,可谓得乎天之全者矣”*《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64《陈鹏年传》,载《清代传记丛刊》第153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775页。。陈鹏年嗜好谈诗论艺*余廷灿:《行状》,载《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64,载《清代传记丛刊》第153册,第817页。。康熙三十七年(1698)八月自序诗集,认为文士之诗有纪阅历,咏性情之用。若幸逢如康熙之盛世,进则如词臣“颂扬休明”,退则如草民“歌咏太平”*《陈恪勤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康熙刻本,集部第259册,第513页。。而鹏年“于诗学杜少陵,得其抑扬顿挫沉郁之故,宦迹所至,喜崇奖德义,以彰风教”*《陈恪勤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康熙刻本,集部第259册,第513页。。可见陈鹏年的诗学观和康熙颇多暗合,故能全身而退,入馆修书。概之,从编纂的筹备到人员的网罗,从体例的拟定到宗旨的确立,从具体的辑录到作品的考订,康熙可谓意图明确,计划缜密,布置周详,关注密切,推广有力,在温柔敦厚的诗教外衣下不断地传布王权话语,极大地占据了选家的权力场域。
因文治武功的卓越建树,康熙一直被嫡孙乾隆所效仿。除去前文论及的对汉文化及诗歌的相同态度,在典籍修纂、选诗宗旨以及思想钳制上,乾隆对圣祖康熙可谓亦步亦趋。《御选唐宋诗醇》在选目上无法与《御选宋诗》的大而全相比,但乾隆对选政的干预以及选诗宗旨的宣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先来考察《御选唐宋诗醇》的选目。在乾隆看来,钦命词臣编纂诗文选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彰扬风雅,裨补世道。此选遴录唐宋诗家六人,唐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宋苏轼、陆游。乾隆向来尊尚唐诗,序曰:“文有唐、宋大家之目,而诗无称焉者。宋之文足可以匹唐,而诗则实不足以匹唐也。”*《御选唐宋诗醇序》,《御选唐宋诗醇》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那为何还选及两宋之苏、陆呢?原因是乾隆与康熙在诗歌观念上一样,主张尊唐兼宋,风雅教化。乾隆及选家心中的苏轼,其人“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为之也。惟诗亦然”,“要归本于六义之旨”*《御选唐宋诗醇》卷32苏轼诗卷首小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看中的便是苏轼的志气节义,而诗也合乎风雅六义。而陆游呢?则取其类似杜甫。“观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御选唐宋诗醇》卷42陆游诗卷首小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如此看来,主唐的乾隆兼及宋人,实出于褒扬忠孝贞义,扶植伦理纲常的诗歌功利观。从乾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来看,当时清廷面对的朝局与康熙朝已有较大的差异。乾隆中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堆积,官场痼疾逐渐爆发,为了正人心,厚风俗,化子民,乾隆贬斥清初降将贰臣,又褒奖明末忠臣义士*黄爱平:《清代康雍乾三帝的统治思想与文化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4期。。而四库馆臣亦迎奉乾隆主唐兼宋的观点:“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亦惟两代之诗最为总杂,于其中通评甲乙,要当以此六家为大宗。”*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0《御选唐宋诗醇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1728页。以诗歌正变的角度来解释采唐及宋的选录标准。
其次,《御选唐宋诗醇》旨在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一点,乾隆和康熙是一脉相承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四库馆臣上呈《御选唐宋诗醇提要》,曰:“兹逢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之旨品评作者,定此六家,乃共识风雅之正轨。臣等循环雒诵,实深为诗教幸,不但为六家幸也。”*《四库全书总目》卷190《御选唐宋诗醇提要》,第1728页。辑选六家诗,最先入乾隆法眼的就是风雅正宗、忠君爱国的杜甫。《诗醇·杜甫小传》曰:“昔圣人示学诗之益,而举要惟事父事君,岂不以诗本性情,道严伦纪?古之人一吟一咏,恒必有关于国家之故,而藉以自写其忠孝之诫。……东坡信其自许稷、契,或者有激而然;至谓其一饭未尝忘君,发于情、止于忠孝,诗家者流断以是为称首。呜呼,此真子美之所以独有千古者矣!予曩在书窗,尝序其集。以为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良足承三百篇坠绪。兹复订唐宋六家选,首录其集而备论之,匪唯赏味其诗,亦藉以为诗教云。”*《御选唐宋诗醇》卷9杜甫诗卷首小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杜甫既能得性情之正,又能本于忠孝,君臣纲纪与家常伦理皆备,确实是最合乎乾隆诗歌功利观的不二人选。乾隆首推杜甫,以其为诗教代言人,细观李、杜、白、韩诸人小传,连李白也说是出于其“忠爱之志”,“笃于君上”*《御选唐宋诗醇》卷1李白诗卷首小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与风雅正宗的杜甫相埒。至于杜诗后裔的白、韩,不言而喻。苏、陆前已论及,此不赘述。面对迥异康熙的朝局和诗坛现状,乾隆在诗歌功利观上表现得更加圆通。四库馆臣在上呈《御选唐宋诗醇提要》时说:“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禛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各明一义,遂各倚一偏,论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谓欤!”*《四库全书总目》卷190《御选唐宋诗醇提要》,第1728页。一方面,乾隆主导诗坛的审美祈向,老调重弹温柔敦厚的诗教;另一方面,乾隆也看到了社会现实与诗坛现状,批评宗宋之风不解温柔敦厚之义,又指摘渔洋神韵之风不关注国计民生。如此一来,既调和了唐宋诗之争,也满足了诗歌政治教化的需要。
三、 余论:话语权力与选本的离合
从清代宋诗选本发展的角度来说,皇权介入选政,以诗教维护政统,这的确节制了选家握管操觚的主体自由,也影响了宋诗学建构的文学空间。而这未尝不是好事,最高统治者的关注足以证明了宋诗选、宋诗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尽管康熙、乾隆多主唐音,还能兼及宋调,不能不说这给宋诗带来了“福音”,虽然打上了借助通代诗选来实现在大一统思想,教化民众的功利性烙印。御定宋诗选本的出现,首先调和了唐宋诗之争,催生了一批唐宋诗合选本。比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七月戴第元辑成《唐宋诗本》,自序曰:“《御选唐宋诗醇》一书,至博至精,津梁奕禩。所选者六家,而三唐两宋之精华无不荟萃。第元官翰林时,诵习既久,玉堂清暇,泛览滋多。爰本《诗醇》体例以读唐宋诸家之诗,凡古今诗话、诗评偶有所得,辄抄缀简端,积年遂成卷帙。”*戴第元:《唐宋诗本》卷首,乾隆三十八年(1773)览珠堂刻本。
戴第元可算是较早得以观摩《唐宋诗醇》的翰林,也是受此启发而私纂唐宋诗选的词臣。序中虽然仍沿袭乾隆标举风雅的老调,但明确地提出不可“徒挟偏胜”,抱持分唐界宋之论,调和兼宗的意味不言自明。其次,帝王主唐兼宋的态度,既受到文学侍臣的影响,同时反过来也影响着诗坛风气的走向。比如,康熙御选宋诗时,周边就有像查慎行、陈廷敬等人,地方上则有宋荦等宗宋诗风的封疆大吏。《御选宋诗》部帙浩繁,深藏内府,在民间流传不广。但《御选唐宋诗醇》影响极大。据考察,乾隆年间钱载、彭元瑞分别在乡试、会试策问中都提及到《御选唐宋诗醇》的典范作用*钱载:《萚石斋文集》卷四《乾隆四十四年江南乡试策问五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08页;彭元瑞:《恩馀堂辑稿》卷一《会试策五道第二问》,《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47册影印清道光七年刻本,第453页。,虽然主要标榜乾隆的诗教观,但也间接地促进了宋诗在民间的流布,尤其是苏、陆两家的广泛接受。梁章钜曰:“唐以李、杜、韩、白为四大家,宋以苏、陆两大家,自《御选唐宋诗醇》其论始定,《四库提要》阐绎之,其义益明。”*梁章钜:《退庵随笔》,《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77页。民间的普通士子都已如此,更遑论皇帝身边的翰詹词臣。彭元瑞还以《唐宋诗醇》来教导翰林庶吉士,曾对英和称:“应将《文选》及《唐宋诗醇》《文醇》尽卷熟读,可为好翰林矣。”*英和:《恩福堂笔记》卷下,《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78册影印清道光十七年刻本,第555页。概言之,康熙、乾隆御定含有宋诗的总集,从中央到地方,从士大夫到民间文人,程度不同地受其影响。尤其是康、乾二帝对选家编纂权力、批评话语的掌控,深深地嵌入诗选的生成及其面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沈德潜辑纂《国朝诗别裁集》*王兵:《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第254~266页。。当沈德潜一类的选家脱离政治中心,有时会回归到诗性的选家生存空间,从而导致与官方诗学造成激烈的冲突,反过来促成了帝王直接强制干预选家选政,以推行其专断的王权话语。由此可见,选家的权力遭受来自帝王、权臣等人的凌驾之后,造成了选家话语的失声,选政运作的无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考察到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对诗人作品的窜改、涂抹*黄裳:《谈“全集”》,载《我的书斋》,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43~45页。,而选家这种恣意妄为的编纂活动并没有受到他人的干预。这足以说明话语权力与选家选本是有离合的。在王权的掌控或忽视下,选家的话语权力与权力话语也不断地反抑制和自我超越。
统观康熙、乾隆御选宋诗的选家,也存在像沈德潜一样的离合现象。比如参与御选四朝诗的查慎行、顾嗣立、汪灏等人。被康熙誉为“儒臣冠”*沈廷芳:《翰林院编修查先生行状》,《查他山先生年谱》卷首,《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丛刊》,第86册影印本,第302~303页。的查慎行却常自称“烟波钓徒”。这是内廷清客、文学侍臣对皇家帝王专制政治的心理反抗*严迪昌:《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519页。。一同参与编书的汪灏、顾嗣立也因戴名世《南山集》案而心有余悸,后者旋即辞官归里,著述、漫游以终。而御选《唐宋诗醇》的主要人员梁诗正休致返杭和入仕前一样,与乡梓硕彦、流寓文士如浙派诗群厉鹗、杭世骏、赵信、赵一清等人,包括参与《宋诗纪事》校勘的诗正胞兄梁启心,雅集唱和,诗酒风流。这是诗人的一种诗性回归,跟入朝修纂书籍屈从王权截然相反。总而言之,选家社会身分的尊卑与诗学观念的显晦,选本折射出的权力话语的顺逆离合,官私话语权力的强弱消长,对于清代宋诗选本的编纂、宋诗学的演进来说,息息相关。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3.010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08a052)
●作者地址:吴波,怀化学院中文系;湖南 怀化 418008。Email:wb1265@sohu.com。
●责任编辑:何坤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