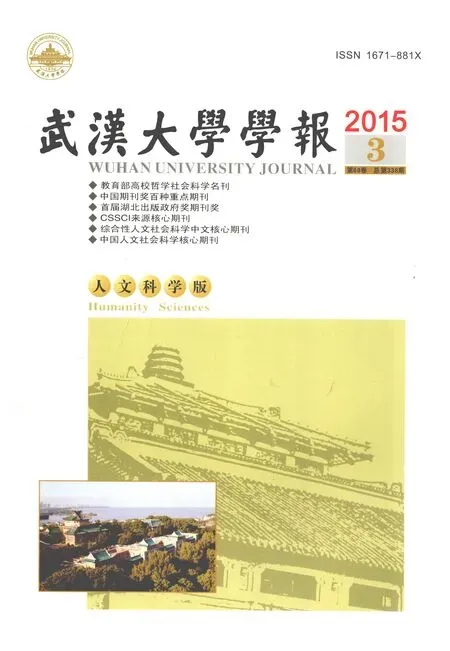“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至“焚书坑儒”——析秦帝国政权与士人关系的演变
2015-02-22刘力
刘 力
“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至“焚书坑儒”
——析秦帝国政权与士人关系的演变
刘力
摘要:在秦构建帝国一统的进程中,曾试图通过“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的文化怀柔而“兴太平”。然而,由于价值取向的分歧,秦帝国政权不断遭遇士人“异说”,最终,帝国威权以“焚书坑儒”回击之。这不仅宣告了秦帝国初期文化怀柔政策的转向,也揭示了士人与政权之间由春秋战国的“为帝王师”向专制帝制内的“为君之臣”的关系转变。
关键词:秦政权; 悉召文学方术士; 焚书坑儒; 士人; 文化政策
在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帝国——秦朝“短命而亡”的批判中,其作为西戎之国的严刑峻法、文化专制往往是首要,而典型的例证则是“焚书坑儒”。其实,在秦帝国构筑大一统政权过程中所择取的文化政策,并非一开始即欲将士人置于政权的对立面。两者之间实则经历了一个从怀柔与期待至冲突、对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有帝国维护威权政治的考量,也有士人在社会已然转型过程中却对自身价值期待恒一不变的原由所致。本文拟从此角度管窥秦政权与士人关系的演变。
一、 秦初“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的文化怀柔政策
成就帝国统一大业之前的秦作为关西一隅之诸侯国,在文化序列上往往被关东六国“比于戎、翟”而耻与之。这一方面源于“内诸夏外夷狄”的认知,另一方面则是因秦重军功、尚耕战的文化传承与法家文化取向所致。随着秦政治、军事上统一步伐日益彰显,其当政者也开始重新思考帝国文化意识上的方略,尤其是应如何将以齐、鲁为代表的关东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传承延揽入帝国政权。具体言之,则是落实为如何对待作为承载诸子百家之学的士人问题。
在诸侯纷争的战国,“士人”对于诸侯而言,可谓是制胜的重要法宝。“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王充:《论衡校注》卷十三《效力第三十七》,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6页。,故战国时期七国虎争天下,莫不以招四方游士为要。其时秦国虽还是地处西隅的诸侯国之一,但“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贤,远求异士”*《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887页。。相较于关东六国,秦国举贤纳士的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洪迈:《容斋随笔》卷二《秦用他国人》,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页。秦重用四方宾客士人最终获得了丰厚回报: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岳麓书社2001年,第511~512页。
最终,因着“听众人之策”,秦实现了“乘六世之烈而吞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所谓的“众人之策”,即来自四方宾客士人的谋略建议。我们可以看见,在成就帝业的过程中,秦国对于各方士人是倚重、礼遇的,即便在因怀疑“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而意欲“请一切逐客”时,最终考量到如若“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而“乃除逐客之令”*《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512页。。作为秦帝国的开创者,始皇还在其幼年之际,亦开始招纳士人,“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秦王……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岳麓书社2001年,第41页。
其时士人在建功立业为帝王师的理想憧憬下,亦是欣然向秦的。李斯,楚国人,却驰骛为秦王“舍人”: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511页。
作为楚人,李斯却毅然前往西戎之秦,缘由在于秦强王贤,可以成就天下一统的帝业,“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511页。成就天下一统的万世之伟业,不仅是统治者的政治憧憬,亦是渴望为帝王师的士人们的政治理想。对于此时秦统治者与士人之间惺惺相惜的关系,有学者以为,“历史的嘲弄常常是双向的。一方面,它固执地将秦的统治者铸于士的对立面,从而与东方那些温良谦逊、恭敬文雅的士的保护人、赞助者明显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自由度相对最大的战国末年,士人们几乎是完全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帮助他完成统一大业,甚至帮助他灭亡了自己的国家。”*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这说明,在相当一段时间,秦政权虽然奉行商鞅重军功、尚耕战的法家思想,但对于士人是倚重、礼遇的,而士人对被视为西戎的秦国亦是心向的。
公元前221年,当秦最终扫定六国,建立起庞大的武功帝国后,为了弥补自身作为西戎之国在文化历史、文化内涵上的先天不足,秦在文化上实行了对关东六国尤其是齐、鲁之士开放、容纳及礼遇的政策。这种文化怀柔政策主要表现在博士员的设置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72页。王国维先生在《汉魏博士考》中指出,秦博士员七十人,“其中盖不尽经术之士……殆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皆立博士,非徒六艺而已。”*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载《王国维遗书》第1册,上海书店1983年。即是说,秦帝国置博士,有儒学之士、亦有方术、道家等其他诸子之士。博士员的设置,是帝国统治者拟图将春秋战国的私家养士制度一变为王朝养士,将以儒生为代表的士人延纳进入大一统的体制之内,从而与帝国政权一统相适应的文化政策上的举措。
除了“广置博士员”外,秦帝国的文化怀柔还表现在最高统治者的不断向东巡游。秦始皇在位十多年,很重要一事项是巡游四方,尤其是向东巡游。在帝国建立后的五次巡游中,有四次是在东南方之濒海地区。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于是乃并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刻石。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至钱塘。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44、46、46、49页。。
在舟车极其不便的古代,这么频繁的出巡,政治目的十分昭显。始皇的这一行为,一方面是彰显了其“对东方宗教文化的一种礼尚之意”,但更“应当是始皇试图文治天下,兴太平,拉拢关东六国士人的政治宣传与举措”*李禹阶:《秦始皇“焚书坑儒”新论——论秦王朝文化政策的矛盾冲突与演变》,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或许正是秦帝国之初的这种文化怀柔,加之其成就的“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统一伟业,故士人们对这一新的帝国是充满期待与认可的。“天下之士”“斐然向风”“罔不宾服”*《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56、44页。。“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43页。此翻称诵者,不仅有法家者李斯,亦有儒学之王绾,“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皆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43页。。一定程度上言之,在帝国之初,政权与士人之间这种双向期待与认知应该算是较为同步的。
二、 士人“异说”挑战帝国威权
历经“周秦之变”,国家—社会从二元一体变为二元对立。“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48页。。这是绝对服从、秩序与专制的政体形式,是一种与“处士横议”的春秋战国迥乎不同的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表现在政治领域是血缘政治的淡化,思想领域的表现则是承担意识形态功能的礼乐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出现意识形态危机*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4页。。
意识形态是社会对自身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表述,是受到权力支持的占支配地位的信仰系统,其功能是为既存的或构想中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作解释和论证,并为之实现提供策略,它是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为此,代周而立的秦帝国需要一套能够论证、支持自己统治的信仰系统,这个系统不强调统治的有效性(实然)而是它的合法性(应然),这就需要从道义层面来解释、论证秦帝国的合法性。然则,其时帝国采纳的用来论证新帝国合法性的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论不仅忽略了对于权力道德来源的论证,且其“五行相胜”的结果是对法家思想的坚持。之所以要强调权力的道德来源,是因为历史地看,经过周秦之变,西周的宗法制在表层政治结构上被郡县制所取代,但在社会的深层结构中依然具有宗法势力继续存在的土壤,宗法制社会形成的民众心理对王道政治伦理还保持着相当的认同感*李军靖:《秦汉之际政治方略的变革与调适辨析——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透视中考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正是这种认同感,造成了秦帝国中的以儒生、方士为代表的士人“异说”。
首先,随着秦帝国的建立,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作为儒生们安身立命的礼乐文化也遭遇为新生帝国立论的五德终始论和法家文化的排斥。在面对 “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秦帝国政权的如何建构上,儒生作为西周宗法礼乐文化的承载者,对于滋养礼乐文化的分封制自然青睐有加。为此,儒生们一再向帝国统治者禀呈分封制的合法性。
帝国之初,作为儒生的丞相王绾就进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儒生们希望新生帝国与故周一样,分封天下。与之相反,作为法家代表的廷尉李斯则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44页。两种体制的择取分歧,实则是各自所代表的文化取向(礼乐文化与法家文化)在政治体制上的显现。而始皇帝最终“廷尉议是”的首肯则明确表明了统治者的择取意向。只是,这并没有让儒生士人就此止步,依旧固执的呈己所见。乃至其后当仆射周青臣进颂“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时,博士淳于越驳斥其为“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47页。。此处,分封与郡县的政见分歧已经演化为政治道德评判。
郡县制并非秦帝国的产物。早在战国诸侯纷争的时候,作为关西一隅的秦国就已经实行之。“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41页。相对于分封制而言,郡县制更能有效的保障最高统治者意志的贯彻与执行,因为在郡县制下,各级官吏不再单纯从血缘亲属中产生,而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官吏与皇帝之间首先和主要的是君臣关系。故对于专制集权的秦帝国而言,这是历史的自然的逻辑的选择。然则,固守西周礼乐文化的儒生士人却依旧沉湎于分封制所带给他们的“处士横议”的价值存在感,在天下已然一统的政治土壤上依旧喋喋不休的宣讲着分封制,这自然成其为“异说”。
儒生们不仅在体制上屡出“异说”,而且还对象征帝国威权合法性的“封禅”讥议之。“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44页。招揽儒生议决封禅祭祀之事,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帝国统治者对于儒生以及儒生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的重视。然而,儒生关于封禅却是人言人殊,不仅“繁琐”,且“各乖异”“难施用”,因而受“绌”,“不得专用于封事之礼”。对此,儒生则以舆论话语的“讥之”回应“既绌”,“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岳麓书社2001年,第163页。。儒生讥议封禅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始皇帝所开创的“自上古以来所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伟业的否认,更是对于秦帝国一统太平合法性的质疑,因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易姓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第163页。。封禅,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宗教祭祀活动,更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昭告。儒生这一继分封“异说”之后的“封禅”之讥,无疑是直接挑战了帝国一统的政治威权。
士人除却对于秦帝国体制、合法性上进行异说讥议外,还对于帝国最高统治者——始皇帝进行道德品评与非议。在帝国统一大业的推进过程中,其时还是秦王的始皇对于大梁人尉缭表现了相当的礼遇,不仅“从其计”,还“衣服饮食与缭同”,可谓“亢礼”。然则,作为士人尉缭的回应却是,“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42页。
而曾经被始皇帝施与重金寻觅仙人的侯生、卢生在任务难遂之时,即开始非议: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48页。
不仅如此,方术之士为逃避惩罚,还借用谶语对于希望“万世而不朽”的秦政权王朝予以诅咒。始皇三十二年之际,燕人卢生因入海求仙不得而还,遂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为破此谶,始皇帝“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47页。。三十六年,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同年秋,又有言曰:“今年祖龙死。”*《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49页。
上述儒生、方术士人的“异说”、“讥议”亦或“黔首刻石”诸种言行,显现的是在大一统帝国体制之下,秦政权与士人之间出现的紧张状态。两者关系出现这一状态,除却个体因素之外,主要的在于双方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上的差异。在以儒者为代表的士人阶层,秉承西周政治道德化的理念,“即认为政治是道德的延伸,权力的基础是道德而不是暴力。这是他们关于政治的最根本观念,其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源于这一观念”*代云:《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载《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5期。。当士人秉承这一观念,并用之对新生帝国进行品评乃至批判的时候,权力却露出了另一面目。对于帝国政权而言,其“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的目的是为了士人们能够认可且论证帝国政权的合法性与长久性,“兴太平”。“当由皇权苦心培植的承担教化功能的士人阶层开始成为皇权的反对派,当士人们开始通过控制舆论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质疑和威胁皇权的合法性时,皇权对于士人的礼遇亦或怀柔便不复存在”*姚静波:《试析东汉末年太学生离心倾向之成因》,载《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因为对秦帝国来说,专制皇权的至上性、绝对性是不容分割和质疑的,“焚书坑儒”即是秦帝国在其威权受到挑战时所露出的权力的狰狞。
三、 “焚书坑儒”:政治威权与士人道义关系的破裂
“焚书”与“坑儒”原本是没有直接关联的两个历史事件。“焚书”由儒、法士人就分封与郡县两种体制的屡次争论所引发,是秦帝国针对“诸侯并作”与“法令出一”、“师今”与“学古”的矛盾分歧所采取的一种文化取向。在李斯“焚书论”主张中可以看到,其之所以采取如此的文化取向,是因为王朝欲以经书文学之士“兴太平”的政治实践遭遇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的“异议”与批判。这与统治者所期望达到的皇权一统,政令出一,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大相径庭。以军功、秩序、服从以及文化禁锢政策而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秦帝国面对这种“心非”“巷议”的社会“异议”与批判,武器的批判必将显露出对批判的武器的专横及专制,秦帝国将此局面归咎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于是,“历史在这里拐了个急弯,即帝国建立初期企图以人文道德,经书文学补‘法’,以此‘兴太平’,倡文教的指导思想,迅速演变为对诸子之学、百家语义禁忌的文化专制政策。秦帝国在文化政策上又露出始于商鞅的‘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一贯政策取向。”*李禹阶:《秦始皇“焚书坑儒”新论——论秦王朝文化政策的矛盾冲突与演变》。
“焚书”后一年的“坑儒”成为秦帝国爆发的又一个重大政治与文化事件。如果说“焚书”起于制度之争,针对的是儒生的以古非今的对帝国大一统政权不识时务的社会文化批判,而“坑儒”却直接起于方士诸生对于始皇帝的欺骗与非议,是始皇帝因对于方士诸生施与重金却遭遇背叛的一种惩戒,“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遂“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48页。。
焚书坑儒的结果不在于具体燔焚了多少诗书坑杀了多少诸子士人。因为就事实而论,历经焚书坑儒之祸后,诗书、儒生也并未就此绝迹于当朝。东汉王充就言:“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王充:《论衡校注》第28卷《书解第八十二》,第560页。在笔者看来,“焚书坑儒”揭示的是秦帝国之初意欲实施的文化怀柔政策发生了转向。 “焚书坑儒”并非有预谋的政治事件。翦伯赞先生认为,“秦代的政府不是一开始就准备对于古典文献,不分青红皂白,非秦者烧;对于知识分子,反秦者坑,他们曾经从六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几乎是全部的古典文献,征聘了七十位老学者,授以博士之官,又召集了两千以上的诸生,要他们在皇家图书馆进行古典文献的复查工作。焚书坑儒并不是秦代政府预定的计划之执行,而是逐渐演进出来的。”*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4~86页。由此可见,秦帝国政权对街谈巷议、偶语《诗》《书》、以古非今者所施行的“焚书坑儒”是与秦统一之初的政治、文化政策有极大差异的。它标志着秦帝国在统一全国后政治、文化取向发生的一个重大转折。这就将秦的文化专制主义施向全国,将帝国的专制、服从、秩序、等级、军功引进文化领域。帝国初始的文化怀柔政策被原西秦的“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文化禁锢所取代。宣告帝国初期企图以怀柔文化而“兴太平”,以文治天下的政策取向的彻底破产。虽然保留了“非博士官所职……”但在全国焚书的高压下,这一权利形同虚设*李禹阶:《秦始皇“焚书坑儒”新论——论秦王朝文化政策的矛盾冲突与演变》。。
其次,“焚书坑儒”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与政权两者相互认可的礼遇关系开始向“威权”政治利用专制体制的强力迫使士人“承意顺命”转化。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人继承了凝聚着三代之治的上古文献,运用阐释权,取得评价现实权力的合法性依据,成为此后中国社会价值的提供者和道义的承担者。其时出现的“处士横议”一定程度上就是士人利用自己掌握的道德文化资源品评时政的社会状态。春秋战国的诸侯纷纷礼遇宾客游士,实则就是为了获得士人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从理论层面观之两者,此时呈现的是一种“道”凌驾于“势”的态势,故士人亦常以帝王师自居。然历经周秦之变,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取代诸侯割据,政治一统也就注定了士人们已经失去了“处士横议”的土壤。尽管秦帝国之初“悉召天下文学方士术”的怀柔与礼遇一度让士人“斐然向风”,但政权统治者的这种怀柔与礼遇是以士人对于新生帝国的认同与归顺为前提的。然而,我们看到,在现实的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道统之间,却呈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从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的言论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对于新生政权合法性的承认,相反的依旧还是拟图以理想规范政治现实的强烈冲动。为此,有学者认为,“焚书坑儒”是始皇以国家暴力夺取舆论控制权、统一意识形态的一个举动。其结果是宣告了儒生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是儒家士人以王道政治理想规范政治现实的失败*代云:《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焚书坑儒表明中国帝制下的文化定位不仅有了“独尊一术”的取向,而且士人群体所承载的“道”与专制政体威权二者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关联维度。春秋战国所有的“以道抗势”在专制帝制下开始向“承意顺命”倾斜,曾经为帝王师的士人必须逐渐开始接受专制政权下为君之臣的身分与现实。其后叔孙通以“圆滑”著称于世,就是士人群体在权势高压下对专制政体所采取的态度与对策。
黑格尔曾说:“在历史里面,人类行动除掉产生他们目的在取得的那种结果——除掉他们直接知道欲望的那种结果之外,通常又产生一种附加的结果。他们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还有潜伏在这些行动中的某些东西,虽然它们没有呈现在他们的意识中,而且也不包括在他们的企图中,却也一起完成了。”*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载北京大学编:《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480页。“焚书坑儒”在形式上钳制士人之口的同时,却也断送了帝国拟欲“兴太平”的最初设想,这或许是始皇帝所始料不及的,同时也开启了在专制集权社会中士人所守持的道义与政治威权之间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3.007
●作者地址:薛国中,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xgz2910@163.com。
●责任编辑:桂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