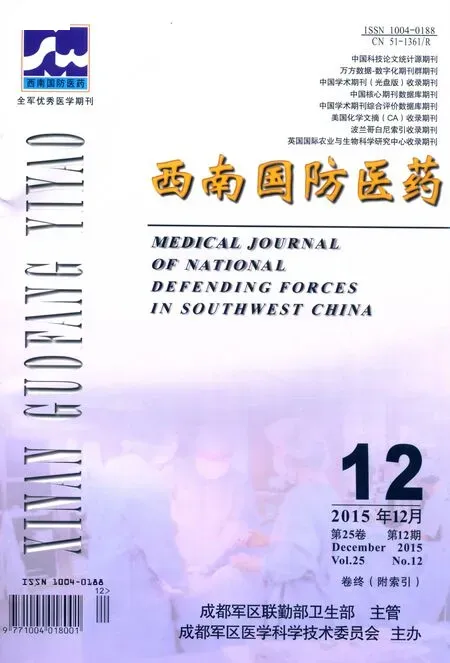木村病导致肾功能损伤的研究进展
2015-02-21马小平杨丽南宋小炜阮一哲段志强
马小平,张 萍,杨丽南,宋小炜,阮一哲,段志强
木村病(Kimura disease, KD)是一种罕见的病因不明的慢性炎性疾病,以淋巴结、软组织和唾液腺损害为主,也有诸多文献报道累及肾脏[1-3],其中约12%~16%的患者可出现蛋白尿,59%~78%患者表现为肾病综合征[4]。 KD 累及肾脏时,可以表现为多种肾病病理类型,包括膜性肾病、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微小病变型、局灶节段硬化性肾小球肾炎、IgA 肾病等。 单纯的不伴发其他脏器损伤的KD 临床表现以无痛性皮下结节为多数,多发生在耳后、头颈部[5],也有发生于眼附属器、肘窝、胸壁、腹股沟、鼻腔等部位。KD 病程进展缓慢, 伴随有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和血清IgE 升高。 KD 分布具有地域性,主要出现于亚洲,好发于亚洲中青年男性,欧洲也有少量报道。
1 木村病致肾功能损伤
木村病最早由我国学者金显宅于1937 年报道[6],最初命名为嗜酸性粒细胞增生性淋巴肉芽肿,后于1948 年由日本学者Kimura 等[7]详细报道描述并命名为Kimura disease。木村病的病因国内外文献均暂无明确报道,但该病特异性地表现出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IgE 水平升高, 这一点诸多文献支持[8-11]。 Iwai 等大样本研究更指出,引起KD高复发率的预后因素包括: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升高超过白细胞总数的50%、血清IgE 表达>1000 U/ml 及唾液腺以外区域出现多个病灶。 病理学上,肉芽肿与周围组织界限欠清,这一点也成为手术切除肿块的瓶颈。 光镜下可见毛细血管大量增生,血管内皮细胞肿胀,故易致管壁增厚、甚至管腔阻塞。 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内皮,嗜酸性粒细胞密集形成局限性的“嗜酸性小脓肿”灶。值得指出的是,华西医院肾内科段睿等[3]指出,部分木村病虽累及肾脏,肾间质却很少出现嗜酸性粒细胞浸润,这一特点提示其肾损害可能并非嗜酸性粒细胞的直接浸润所致,而与其他的免疫因素(如TNF、IF 等)参与相关。 笔者认为,此发现提醒对木村病有兴趣的学者从免疫相关分子角度切入主题, 进一步研究木村病导致肾损伤的确切原因,这对治疗木村病导致的肾损伤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2 预后
木村病属于良性疾病,少有主流文献报告该病有恶性增殖趋势,但邓维业等[12]报道,有1 例既往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伴颈部淋巴结乳头状癌转移的患者,术后4 个月发现颈部淋巴结肿大,行病理活检证实术后肿物为KD。故笔者认为KD 是否有恶性转化的可能,尚需要更多的研究证实。 同时,木村病虽为良性病变,但复发率高,可能与手术切除不彻底、皮质醇治疗周期不充分相关。
对于KD 高复发率的研究,国内中山大学肿瘤中心邓维叶等[12]开展了一项40 例木村病患者的回顾性分析,长期随访木村病术后病患, 将该40 例的手术切除肿物作病理活检,并用Ki-67 行免疫组化,评估其在KD 组织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Ki-67 表达程度与KD 复发相关,复发的11 例中,除了1 例(9.1%)为低表达,其余10 例(90.9%)均为高表达。 而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物个数、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及主要肿块的最大直径均与Ki-67 表达无关联(P >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Ki-67 表达、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及主要肿块的最大直径对KD 患者的复发有影响(P <0.05),而年龄、性别、肿块分布、个数及位置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 将单因素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纳入Cox 模型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i-67 表达及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为影响复发的独立因素。故笔者认为,Ki-67 表达、肿块最大直径等因素,可用于初步判断木村病患者的易复发倾向,为后续的治疗提供指导,可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以提高生活质量,避免木村病继发肾脏损伤。
3 鉴别诊断
值得一提的是,木村病的诊断极易与血管样增生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ALHE)混淆,可能造成对体表有包块且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病患的误诊。 上世纪60 年代,首先报道ALHE 的Wells 等[13]认为,该病与KD 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且KD 是ALHE 的后期阶段,后期一些研究也认同该观点。但目前国内外主流观点[3,11]都否定了两者是同一种疾病的看法, 故笔者认为应严格鉴别两者。 ALHE病理表现出血管增生明显,厚壁血管,伴内皮细胞多形性,嗜酸性脓肿少见; 而木村病病理表现为增生血管常为薄壁,少有内皮细胞的改变,嗜酸性脓肿多见。 ALHE 虽也有颌面头颈肿块等相似点,但ALHE 目前尚无引起肾功损伤的报道。同时,ALHE 多发生于西方,东方亚裔少见,我国罕有报道[14]。在临床上,由于两者表现及实验室指标特异性并不高,故确诊及鉴别仍要以病理活检为金标准。
4 治疗
对于本病的治疗,国内外文献报道的主流有效的治疗方式包括有小剂量放射治疗、手术切除、激素免疫治疗等。由于该病散发、罕见、无大样本分析、合并肾损伤病例更少等原因,首选治疗目前各文献尚未统一。对于单发肿块,肿块体积小,病变局限,保守治疗继发肾损伤效果不佳者,手术治疗首选[5,11],具有治疗周期短、治疗效果确切、病理诊断明确等优点,笔者也赞同此观点。 但手术切除存在易复发特点,可能是因术中肿物界限不清,切除范围过于局限造成。对于全身多发包块、合并肾损伤患者,Othman 等[15]主张初始给予较大剂量皮质类固醇治疗, 稳定后缓慢减量,可有效控制病情,可联用环孢素降低复发率。 2015 年4 月上海同济医学院的Yu 等[16]对1 例45 岁木村病合并肾损伤男性患者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该患者右上臂查见一4 cm×5 cm 包块,肌酐212 μmol/L,电解质水平正常,血清白蛋白水平较低(28 g/L),甘油三酯水平高(3.2 mmol/L),24 h 尿蛋白定量为3.5 g/d,血白细胞8.3×106/L,嗜酸性粒细胞比例高(42% ),血红蛋白(136 g/L),IgE (17 100 IU/ml)。给予强的松口服,30 mg/d, 疗程4 个月。 用药3 个月后,IgE 水平和嗜酸性粒细胞比降至正常水平,蛋白尿消失;4个月后,肿大的淋巴结明显减小。 4 个月后强的松剂量降至7.5 mg/d,疗程7 个月,后随访1 年,无复发。 笔者认为该病例治疗对木村病合并肾损伤患者的激素治疗很有指导意义。 对手术、类固醇治疗无效的复发肿块、界限不清的多发肿块,主张放射治疗,程茂杰等[17]认为,局部放疗效果优于类固醇治疗,且副作用小,缩小瘤体70%以上即可达到治疗效果。 但放射疗法对儿童、孕妇患者的适用性有待探讨。
2008 年Sun 等[18]报道:应用小剂量的伊马替尼,具有缓解嗜酸性粒细胞增多,选择性阻断酪氨酸蛋白激酶的作用,从而治疗KD。 2014 年Nonaka 等[19]进行了一项试验研究, 对3 例木村病患者应用免疫疗法, 即予以抗IgE 抗体——奥马佐单抗治疗,结果肿物明显缩小,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减少。目前伊马替尼用于治疗KD 正广泛被国内外学者接受,前景可观,但国内尚缺乏多中心的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来证实该方法对亚裔患者的有效性。
综上,木村病是一类罕见淋巴组织增生性慢性炎症性疾病,以淋巴节及唾液腺受累最常见,其合并肾损伤这一特点值得广大临床医生警惕。 病因学尚不明确,诊断上表现出局部肿块、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及IgE 水平上升的特点,明确诊断需要病理学支持。治疗上既往包括手术切除、小剂量放疗、糖皮质激素免疫疗法等,效果确切,但近几年也有伊马替尼、奥马佐单抗等新的治疗理念的提出。 尚未解决的方面包括明确的病因学、特效标准疗法、继发损伤的预防措施等问题,这一系列尚未明确的领域有待国内外学者进一步研究证实。
[1] Kaba shima R, Kabashima K, Mukumoto S, et al. Kimura's disease: presenting with a giant suspensory tumor and associated with membranoproliferative glomerulonephritis[J]. Eur J Dermatol,2009, 19(6): 626-628.
[2] Chen H, Thompson LD, Aguilera NS, et al. Kimura disease: a clinicopathologic study of 21 cases[J]. Am J surgpathol, 2004, 28(4): 505-513.
[3] 段睿, 何朝霞, 胡章学. 木村病伴肾损伤2 例[J]. 华西医学,2015, 30(6): 1192-1194.
[4] Matsuda O, Makiguchi K, Ishibashi K, et al. Long-term effects of steroid treatment on nephrotic syndrome associated with Kimura's disease and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Clin Nephrol, 1992, 37(3): 119-123.
[5] 黄石, 吕丹, 郑永波, 等. 头颈部木村病4 例临床分析并文献复习[J]. 实用医院临床杂志,2013, 10(2): 138-139.
[6] Kim HT, Szeto C. Eosinophilic hyperplastic lymphogranuloma,comparison with Mikulicz's disease [J]. Chin Med J, 1937, 23:699-700.
[7] Kimura T, Yoshimura S, Ishikawa H. On the unusual granulation combined with hyperplastic changes of lymphatic tissue[J]. Trans Soc Pathol Jpn, 1948, 37: 179-180.
[8] Sah P, Kamath A, Aramanadka C, et al. Kimura's disease-An unusual presentation involving subcutaneous tissue, parotid gland and lymph node[J]. J Oral Maxillofac Pathol, 2013, 17(3): 455-459.
[9] Katagiri K, Itami S, Hatano Y, et al. In vivo expression of IL-4,IL-5, IL-13 and IFN-gamma mRNAs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and effect of cyclosporin A in a patient with Kimura's disease[J]. Br J Dermatol,1997, 137: 972-927.
[10] Kimura Y, Pawankar R, Aoki M, et al. Mast cells and T cells in Kimura's disease express increased levels of interleukin-4,interleukin-5, eotaxin and RANTES [J]. Clin Exp Allergy, 2002,32:1787-1793.
[11] 王振霖, 张名霞, 刘俊其, 等. 木村病的临床诊断与治疗[J]. 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2015, 21(1): 43-45.
[12] 邓维叶, 高云飞, 陈艳峰, 等. Ki-67 在木村病患者中的表达和复发相关因素分析[J]. 中山大学学报,2014, 35(4): 584-588.
[13] Wells GC, Whimster IW. Subcutanepus angiolymphoid hyperplasia with eosinophilia[J]. Br J Dermatol, 1961, 81: 1-14
[14] 常晓燕, 陈杰. 血管淋巴组织增生伴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与Kimura 的鉴别诊断[J]. 诊断病理学杂志, 2004, 11:119-121.
[15] Othman SK, Daud KM, Othman NH. Kimura's disease: a rare cause of nephrotic syndrome with lymphadenopathy[J]. Pathology,2012, 44(3): 275-278.
[16] Yu G, Gu JY, Sony L, et al. Kimura's disease accompanied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in a 45-year-old male [J]. Diagnostic Pathology, 2015,10: 43.
[17] 程茂杰, 常建民. 木村病[J]. 中华皮肤科杂志, 2010, 43(3): 218-220.
[18] Sun QF, Xu DZ, Pan SH. Kimura diseas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Internal Medicine Journal, 2008, 38: 668-674
[19] Nonaka M, Sakitani E. Anti-IgE therapy to Kimura's disease: a pilot study[J]. Auris Nasus Larynx, 2014, 41(4): 384-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