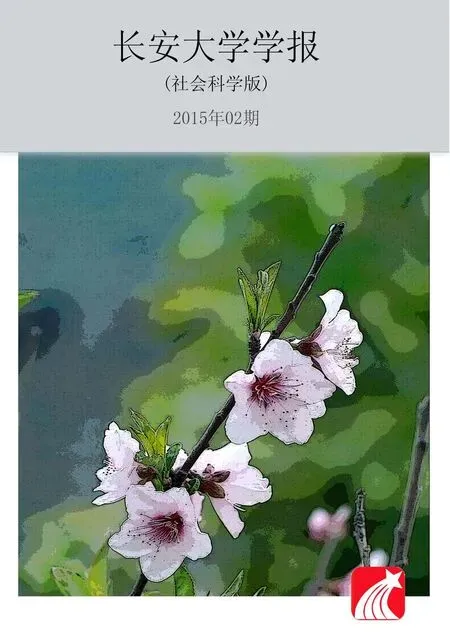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阵法及其影响
2015-02-20王路平
王路平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陕西西安 710041)
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阵法及其影响
王路平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陕西西安 710041)
北宋自太宗朝起,统治者就对阵法高度重视并不断加以建设,以期取得对外作战的胜利。北宋末年,当政者抱残守缺,以防范武将为己任,最终酿成靖康之祸。南宋初年,宋高宗企图通过继承和沿用北宋诸帝授阵图的传统,实现“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然而在消极防御国防战略和“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的影响下,阵法创制流于形式,预授阵图成为统治者控制武将的重要手段,在战场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南宋武将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控制,并自创适合与金军作战的阵法,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宋金议和后,“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再次发挥作用,南宋初名将云集的局面不复出现。
北宋;南宋;阵法;阵图
为避免唐代中晚期藩镇割据、武将跋扈局面的出现,北宋自太宗朝起,统治者就对阵法高度重视并不断加以建设,以期取得对外作战的胜利。然而在消极防御国防战略和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的影响下,阵法创制流于形式,预授阵图成为统治者控制武将的重要手段。由于预授阵图的做法违背了基本的军事指挥原则,以致于北宋在对辽和西夏的作战中频频失利,最终酿成靖康之难。以往,学术界对北宋阵法与阵图的相关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述,然而对于两宋之交阵法创制的探讨则稍显不足[1-5]。本文着重剖析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军事将领可以灵活地创制、使用阵法,并取得战场上胜利的原因。
一、北宋末年的阵法
宋哲宗元祐(1086~1094)初,因皇帝年幼,高太后成为了北宋政权的实际控制者。作为保守派,她贬黜改革派并启用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保守派官员。自此,在宋神宗朝受到压制的保守派又一次控制了北宋政权。他们甫一上台,就废除了宋神宗一生努力推行的变法措施。除了政治、社会领域的政策回归保守以外,在国防上,保守派将宋神宗朝对西夏积极进攻的军事政策,转变为消极防御政策,主动放弃了宋神宗时期费尽心力才夺取的关隘要地。在对待统兵武将的态度上,采取打击压制策略,“握兵将帅相继以罪罢去”[6]。对于司马光采用消极防御,甚至为避免冲突,将宋神宗时的胜利成果都拱手相让的军事政策,即便是保守派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元祐五年(1090),一直对变法持反对态度的给事中孙觉,就朝廷御将之法发表意见,认为朝廷管辖边境将帅过于苛急,致使将领“不敢以便宜行事”,不论政事大小,“悉闻于朝廷”,严重影响了处理边境事务的效率[6]。另外一个“元祐党人”吕陶也同意孙觉的意见,他指出,不论将帅领兵处于何方,都必须听从朝廷中枢的命令,“敌人在境,而一兵不敢辄发”,如此则何谈战场取胜[7]?
在日益严苛的政治氛围下,武将群体士气不断受到打击,尤其是身处对敌前线的边将,因此畏缩不前,又回到了宋神宗改革之前畏懦避战的状态。元祐八年(1093),陕西河东诸路守军每每探听到西夏人即将大举入侵的消息,不是积极筹备抗敌,保国安邦,反而是让当地人民“清野坚壁,专为守计”。西夏摸清了宋军消极防御的策略,要么避实就虚攻其不备,要么集中优势兵力强力突进。宋军固守城砦,不敢出门接战,“而边民被害数已不少”。因此,诚如枢密院奏折所称:“边将不过闭壁自守,坐观焚掠”,军队不敢出击,致使西夏军队在北宋境内“若涉无人之境”[6]。
绍圣年间(1094~1098),宋哲宗亲政改弦更张,在罢黜保守派官员的同时,起用元祐年间受到打击的改革派,又重新走上了改革之路。随着改革派重掌朝政,北宋政府又开始整饬武备,采取积极进攻的国防战略。特别是元祐九年(1094),章惇拜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一职后,力主采取主动进攻西夏的军事政策,在西北前线修堡寨,极大地打击了西夏军队,迫使西夏主动求和。但是好景不长,哲宗皇帝23岁便英年早逝,北宋政局又一次陷入混乱,北宋对外军事活动也随之受到严重影响。
随着政局的不断变化,宋廷使用的阵法也不断出现反复。元祐(1086~1094)初年,在保守派主导下,北宋政府恢复了在元丰七年(1084)就已经被神宗废弃不用的四御阵,“以御阵与新阵法相兼教阅”。绍圣三年(1096),哲宗又把保守派恢复的四御阵废除,仍然使用五军阵。虽然史料上无法确切了解从元丰七年(1084)到元祐元年(1086)再到绍圣三年(1096),这14年里北宋军队三易阵法的反应,但这样仅因为政治观念不同,而不考虑军事实际,频繁地调整军队训练和作战阵法,对军队无疑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宋徽宗即位后,虽然政局动荡,但在阵法的选择上却一直将神宗朝的阵法作为军队的基本阵法。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下诏将五军阵法推行到各路。在稳定沿用五军阵法的基础上,徽钦两朝仍然坚持北宋朝野积极创制阵法与阵图的传统,“当时君臣虽无雄谋远略,然犹切切焉以经武为心”。靖康元年(1126)时任通直郎的秦元向宋钦宗上兵书和阵图。其阵法得到监察御史胡舜陟的称赞,胡氏认为秦元的阵法参考了古今军阵,“博而知要,实为可用”。既然有监察御史的大力推荐,宋钦宗当然对秦元的阵法加以关注,还专门下诏召见秦元[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拥有这样“博而知要,实为可用”的兵书和阵图帮助,也未能延缓北宋灭亡的命运。所以徽、钦二宗的“经武之心”不过是做出自己关心武备,勤勉政事的姿态而已。实际上,宋徽宗时期的国防形势相当严峻,知定州张舜民的奏折可谓一针见血,他认为宋徽宗时河北地区的边防形势,就如同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0)的陕西地区一般: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一旦战争爆发,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守边的大臣因此“预为振举”,则会被“谓之张皇”,“而朝廷亦自不容”。如果在这种形势下“依旧宴安”,反而会被称赞为“无事”。在这样严峻的国防背景下,朝廷内担任将官的人却多半是“膏粱子弟”,“畏河东陕西不敢往,尽欲来河北,百年之间未尝知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路,唯是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7]。在有识之士看来的边防隐患,宋徽宗却不以为意。他抱定“丰亨豫大”的享乐思想,通过花石纲等手段满足自己无尽欲望。朱熹评论“宣政间有以夸侈为言者,小人却云当丰亨豫大之时,须是恁地侈泰方得,所以一面放肆,如何得不乱”[9]。
宋徽宗为建不世功勋,想趁辽国衰弱,收复幽燕地区。他先是与金人签订了海上之盟,后委任宦官童贯为统帅,负责征伐辽国的军事行动。宣和四年(1122),童贯分兵东西两路,每路军分别有前军、左军、右军、后军、选锋的配置[10]。可以看出,当时北宋两支征辽的大军采用的就是前后左中右的五军阵法。然而再好的阵法也不能替代统帅的指挥。刚愎自用的童贯秉承将从中御的原则,多次指挥错误,直接造成了北宋军队在对辽作战中大败。在金人铁蹄前不堪一击的辽军竟然也让北宋军队铩羽而归。宋军面对金兵的强悍攻势,是“来无藩篱之固,去无邀击之威”[11],完全落于下风。面对围困京城的金军,同知枢密院孙傅不组织军民抵抗、反而寄希望于自称能用“六甲法”,可以调动天兵天将的江湖术士郭京身上,自开城门,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荒唐可笑的一幕。
二、南宋初年的阵法
北宋政权在金人铁蹄冲击下走向了终点。但赵宋王朝天数未尽,气运尚存,南宋政权贪偏安于临安。在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南宋初年,中央已经无法实施将从中御的政策,但宋高宗和文人士大夫仍然倾心研究阵法阵图。建炎三年(1129),待政权稍安,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吕颐浩便立即建议南宋军队考诸古之阵图,效仿古法,“仿古阵法常山蛇势”[12]。在金军强大骑兵的冲击下,为了实现以步治骑的目标,南宋大臣们又开始去故纸堆内翻找阵图,“诸将亦皆画阵图,诣殿前司献”。对于无视战争规律,妄想通过发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阵图而达到取胜目标的想法,当时就遭到不少批评,认为战事变幻莫测,如果敌人提前预知我军战阵而“别布它阵,将何以御”[11]。
实际上,只有在正确的军事原则指导下,因地制宜设置的阵法才有意义。无论是岳家军还是对手金军,他们的胜利从来都不是靠照搬阵图、阵法取得的。金军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灭亡了辽、北宋,后来又将南宋打得节节败退。其能成功的原因,除了当时金国新立处于上升期外,关键还在于金军熟练运用战略、战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骑兵的作用。金军骑兵一般以50人为一队,“相去百步”,并且配有副马,平时养精蓄锐,“待敌而后用”。每队前20人为重甲骑兵,“持棍枪”,后30人为轻甲骑兵,“操弓矢”。遇敌,则先派一至两人观察敌人虚实,然后骑兵从前后左右方向猛烈攻击敌人,“百步之内,弓矢齐发”,往往命中率很高,其阵法“分合出入,应变若神。”因此宋人评价道:“其人自为战,战则必胜”。实战中,金军惯用的是“三生阵同命队法”,也就是游牧民族普遍采用的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金兵遇敌,先以圆阵为先锋,“次张两翼,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而且金骑兵小队每队15人,以一人为旗头,余下梯次排列,分别称为“角、从、副、徼”,“旗头死,从不生还,还者并斩。得胜受赏,亦然。故谓之同命队”[11]。
对比宋军的平戎万全阵、四御阵等花样繁多、立意高远的阵法,“三生阵同命队法”既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没有玄妙繁复布局,但却取得了良好的实战效果。名将吴璘对此有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宋军之前与西夏作战,不过一个回合即可分出胜负。而金兵则是“更进迭退,忍耐坚久”,军令残酷,每场战事“非累日不决”,并且金兵“胜不遽追,败不至乱”[8]。
南宋在对金艰苦的作战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军事将领,他们成长于战火中,对于他们而言,通过研究古书,恢复古阵法没有意义,只有通过研究敌人特点,有针对性地自主创新、使用阵法才能够克敌制胜。比如名将吴璘在镇守川陕之时,分析总结金军特点,认为“金人有四长”,分别是“骑兵、坚忍、重甲、弓矢”,针对此,吴璘提出应对之法,“吾集番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分别以“分队法”、“番休迭战”、“劲弓强弩”、“以远克近”来制约金兵的“四长”[8]。在此基础上,吴璘发明了叠阵。他通过将长、短近战兵器与远程武器综合配置,根据敌我距离不同,分别选择不同武器分番迭次地打击敌人。实际作战中,吴璘把长枪军布置在队伍的最前面,让他们坐在地上不要起来,长枪军后面依次布置最强弓、次强弩,这些军士都要跪地备战;弓弩之后再布置使用神臂弓的军士。当看到金军突进到距离宋军阵前百步的时候,令神臂弓首先发射;到距离宋军七十步的时候,强弓齐射;以此往复,下一个军阵也是这样安排。在阵前,摆放以铁钩连接在一起的拒马,一旦有了伤亡就由后面的次阵替代。如果需要前阵和次阵更换位置,就通过击鼓传达命令。在步兵和阵型调整的时候,有骑兵从两翼冲到阵前保护,布阵完成后,骑兵退下。依据步兵武器特点和射程排布各兵种的叠阵,可以在不同的战场条件下,针对骑兵突击,整合各兵种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在叠阵的帮助下,吴璘取得了和尚原、饶风岭等对金大战的胜利。
熟练使用阵法的武将中,大将张威是其中出色的代表。当时张威驻守荆鄂地区,当地地势平坦,非常有利于金军发挥其骑兵机动、快速的战略特点,而“叠阵”就失去了战略优势,所以他创制了“撒星阵”。所谓撒星阵,就是“分合不常,闻鼓则聚,闻金则散”,力求在“倏忽之间,分合数变”,乘金人惊慌失措之时发动进攻,以取得最终胜利[8]。战争经验说明简单实用是实战中最重要的原则,撒星阵将灵活机动与瞬息万变的战场实情相适应,发挥出非常明显的战略优势。从创制撒星阵可以看出,张威能够不拘泥于形式,充分掌握了战争特点,因此才能每战皆克。
南宋名将岳飞对待阵法、阵图的态度更能说明他何以成为一代名将。岳飞“好野战,非古法”,岳飞在宗泽手下为将时,宗泽曾经给他一些阵图让他学习借鉴。岳飞看完阵图后,认为宗泽所给阵图,“乃定局耳”,古今用兵,“岂可按一定之图”,要想在战争中取胜,“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13]。因此岳飞看待阵图的态度是“阵而后战”[8]。岳飞不看重阵图,并不是说岳飞用兵不讲阵法或者不重视阵法。而是岳飞已经将阵法运用得出神入化,早已经脱离了需要依靠固定的阵图去排兵布阵的低级层次。《孙子兵法·虚实篇》说到“能因敌变化者谓之神”。岳飞非常熟悉各个兵种的优点和弱点,依据不同的地形、敌人对各个兵种进行组合布置,从而发挥各兵种的最大优长,取得战争胜利。岳飞对于阵法的运用已经进入了大象无形的境界,明代的何良臣在《阵纪》中称赞“凡用步兵,欲以寡斗众,弱胜强者,无如岳飞之任机势”[14]。正是因为岳飞能够不拘泥于任何阵图,才能够多次大败金军,名垂青史。
随着宋代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到南宋时,火药等新型军事武器在战争中的使用日益广泛,对阵法产生了影响。南宋初出现了围绕火药兵器创制的阵法,其中尤以如意战车阵法最具代表性。如意战车及阵法是南宋初名将魏胜创制的。“胜尝自创如意战车数百两,炮车数十两,车上为兽面木牌,大枪数十,垂毡幕软牌,每车用二人推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辎重器甲,止则为营,挂搭如城垒,人马不能近;遇敌又可以御箭簇。”当布阵时就把如意战车布设在军阵外侧,用旗帜覆盖隐藏,用弩车当战阵的大门,弩车上设床子弩,床子弩用的箭矢大的像凿子一样,一箭能射穿数人,一次可以发射三只箭,射程可以达数百步。炮车被放在军阵中间,可以发射火石炮,射程也可以达到200步。当敌人军阵距离较远的时候,宋军阵里就发射弓弩箭炮杀伤敌人。如果敌人已经突进阵前时,就让刀、斧、枪这些长武器伸出阵外刺杀敌人。当两军开始交战时骑兵就会冲出,两向共同夹击敌人,如果得胜骑兵就拔阵追击,如果稍有不利就回到阵中休息片刻。使用这样的阵法,士兵不会疲劳,进攻和撤退都非常有利。魏胜经过使用后觉得非常好用,把如意战车的样式上报朝廷,朝廷“诏诸军遵其式造焉”[8]。
金军以骑兵为部队主力,擅长快速突击。因此南宋各将领根据敌人特点,因地制宜,制定有效战略战术,取得了不少胜利。如和尚原之战就是吴玠、吴璘兄弟利用地形和弓弩创造出的以步制骑的典型战例。名将岳飞则通过背嵬军与游奕军、马军结合的战术打破金军骑兵铁浮屠,取得郾城大捷。李师颜指挥下的扶风之战则是宋代以骑制骑的经典战例。随着金军控制中原,南宋退守南方后,宋金两国的战局发生了改变。南方由于水网密布,水乡沼泽众多,两军能够进行大规模野外会战的机会较少,多为围绕城市开展攻防争夺战。南宋将领能够迅速改变战术适应战场变化,如刘锜的顺昌之战就是极具代表性的城市防御战。
在南宋初年涌现了样式繁多的阵法,这些阵法对于抵御金军入侵,稳固南宋政权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与北宋时期创造的阵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何以如此?第一,南宋初的阵法既不是不谙战阵的皇帝和文人士大夫们坐在书房里翻查古书得来的,也不是民间隐逸之士凭空设计出来的。这些阵法都是一线统兵将领在实战中总结出来,并能在实战中根据不同的战场条件进行调整、改变,才能取得制敌的效果。第二,南宋初年,政权尚未稳固,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军追击东躲西藏。此时他只希望军队能够全力抗金、稳固政权基础,哪还顾得将从中御的祖宗之法。没有了皇帝和文人士大夫的掣肘,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这些握有重兵的大将才能摆脱条框束缚,取得一系列抗金战役的胜利。第三,南宋初阵法能够有效使用与众将都有私人亲军有很大的关系。南宋初年的众多名将在乱世之中,借助召募和打击各地起义军都各自组建了自己的部曲亲军,如岳飞的背嵬军、韩世忠的铜脸韩家军等,这些亲军与主将关系密切,勇猛善战,能够理解和贯彻主将的战略意图。
以上这些结果都是在朝廷无暇控制军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一旦局势缓和,皇帝和士大夫必将重新夺回对于军队的控制权。绍兴元年(1131),大臣汪藻就指出“今诸将之骄,枢密院已不得而治矣”。侍御史沈与求也认为“今图大举而兵权不在朝廷,虽有枢密院及三省兵房、尚书兵部,但奉行文书而已”[15]。所以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看到内乱已定,外战对金、伪齐战胜之时,便尝试第一次收兵权,结果导致了郦琼之变,宋高宗只好暂时放弃了这一想法。不过,南宋的皇帝与文臣一直没有忘记防范、控制武将。绍兴五年(1135),大臣张守认为“今之大将皆握重兵”,这批武将位高权重,朝廷无法制约他们,长此以往,会造成“朝廷之势日削,兵将之权日重”。绍兴七年(1137),陈公辅向宋高宗上书,认为朝廷难以控制武将,正是由于“御之未得其道”,再次建议加强对诸大将的控制,“愿加之以威,处之以法”[15]。虽然宋高宗没有采纳士大夫的建议,不代表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他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终于,随着宋金绍兴和议的订立,第二次收兵权的时机终于成熟。自此,南宋又回到了赵宋崇文抑武的传统道路上,武将们也回到了被打压、排挤的位置。南宋初武将们创制阵法,连取大捷的荣光从此走进历史,不复存在。
三、结语
整个北宋时期,统治者都非常关心阵法与阵图的研究工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北宋时期朝野上下,不分文武都参与到创制阵法与阵图的研究中来。但是收效不明显,究其原因,皇帝们研究阵法与阵图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将从中御的政策,遥控指挥统兵将领,文武群臣研究阵图是为了投皇帝所好,当时创制的阵法与阵图多是穿凿附会之作,宋神宗也承认群臣所创的阵图“皆妄相眩惑,无一可取”。所以,研究阵法与阵图无法改变北宋军队战斗能力低下的问题,更无法延缓北宋灭亡的步伐。
南宋初年,由于面临灭亡的危险,宋高宗根本无力也不能实施将从中御的政策,所以涌现出大批功勋卓著的将领,他们针对金军战术特点,根据各自实际创制阵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南宋初年的岳飞、韩世忠等名将与北宋的傅潜之流庸懦无能之辈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充分说明宋朝既不缺少将才,也不缺少舍生忘死的士兵,之所以在战争中败多胜少,是因为北宋政府根本没有给胜利创造必要条件。
[1]吴晗.阵图与宋辽战争[J].新建设,1959(4):87-95.
[2]陈峰.“平戎万全阵”与宋太宗[J].历史研究,2006(6):180-184.
[3]周荣.朱利民.北宋仁宗时期的阵与阵图[J].唐都学刊,2010(5):103-107.
[4]陈峰,王路平.北宋御制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J].文史哲,2006(6):119-125.
[5]王路平.宋神宗时期的八阵法与阵图[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05-110.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8]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七十三卷[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10]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熊克.中兴小纪[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6.
[13]岳珂.金佗粹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何良臣.阵纪[M].北京:国家图书馆,2002.
[1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Tactical development of troops and its influencein the last years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year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NG Lu-ping
(The Monument of Xi'an Offic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Xi'an 710041,Shaanxi,China)
Since emperor Song Taizo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rulers had highly valued and constantly constructed the tactical development of troops and expected to win victory.However,at the end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rulerswere conservative and guarded against generals,which led to the Jing kang calamity.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emperor Song Gaozong attempted to observe the ancestor domestic discipline—“Jiang Cong Zhong Yu”by inheriting and continuing using the system of battle formations employed by the emperors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However,under the influence of passive defense strategy and the domestic discipline,the tactical development of troops became a formality and system of battle formations just became an important tool which was used to control generals by the rulers,which led to great harm in the war.In the fierce war environment,the generals were largely out of control,created the appropriate tactical development of troops to fightwith Jin's army and won victories. Besides,after the negotiation of Song and Jin,the domestic discipline played a role again and the generals aggression of the early years of South Song dynasty no longer appeared.
Northern Song dynasty;Southern Song dynasty;the tactical development of troops;system of battle formations
E291;K244
A
1671-6248(2015)02-0130-05
2015-01-07
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4L18)
王路平(1980-),女,河南许昌人,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