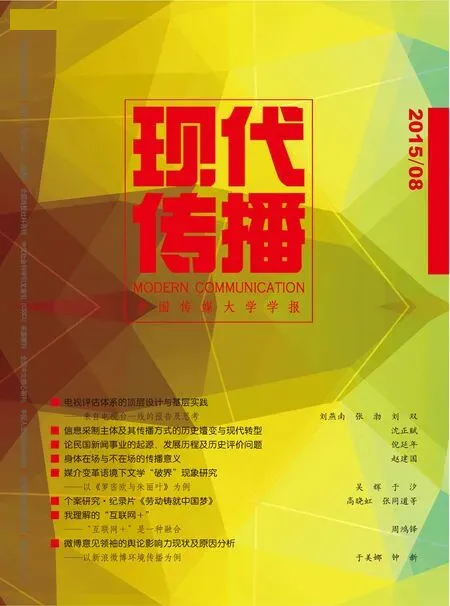论影像政治修辞的历史演进及其内涵扩展*
2015-02-20王晓红
■王晓红
论影像政治修辞的历史演进及其内涵扩展*
■王晓红
政治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对组织和管理人类社会有重要意义。自西方近代政治科学产生以来,政治修辞作为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一直深受关注,其内涵和外延在历史演进中不断扩展。本文以影像修辞为核心,对政治修辞的历史演变及其核心特征进行了概括梳理,提出政治的影像修辞从逻辑性到直观性进而到多元性的发展路径,并且深入诠释了现代修辞情境论的内涵变化,由此导引出本文的核心观点,即:现代修辞已经从文本言说扩展为人的活动,活动成为修辞。这一点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政治活动;影像修辞;政治修辞;修辞情境
政治修辞的目的在于通过表达获得政治认同,其内涵和外延是在政治实践的动态发展中不断趋向丰富的多样性。在前大众传播时代,修辞方法主要表现为语言修辞;大众传播时代,修辞方法从语言修辞向影像修辞扩展,并由此指向了修辞情境;后大众传播时代即互联网时代,由于传播关系的变化,修辞情境发生变化,活动本身成为修辞,同时,手机“在线”进一步促进了影像修辞向活动修辞转向。活动即修辞,这种变化应是当下政治传播中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不过,正如“深刻解释学”方法所指出,对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分析,首先要有历史分析的视角。因为“有意义的对象和表达方式的生产与传播是发生在历史上具体的、社会规定背景中的过程”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特定人类活动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内在意义,从而对研究对象与众不同的特征做出恰当的评判。简言之,我们只有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才能逻辑地把握它的本质。
一、政治修辞的早期历史:从逻辑性到直观性
修辞学始于有雄辩之风的古希腊。古希腊雄辩家善用有力的逻辑论战和巧妙的说服技巧,打动公众、激发行动。亚里斯多德将这种说服技巧定义为“修辞”,即“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②。
修辞学的兴盛与希腊城邦公共生活关联密切。城邦时代古希腊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一体,民主程序初成,城邦事务通过讨论和激辩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家大多都是雄辩家,比如,伯利克里、德莫斯特尼斯等。他们经常面对面地向民众发表演说,展开辩论。为了争取民众的信任和信服,让演说更有说服力,更能打动人心,修辞术逐渐形成。显然,“修辞”自出现起,就已经服务于政治活动,甚至可以说,希腊修辞术源于政治需要,体现为政治修辞。
早期政治修辞主要表现在言说方面。西方著名学者埃里克·哈弗洛克教授(Eric Alfred Havelock)在研究希腊政治的开明气质时发现,格言警句是对政治思想或道德内容的最好修辞,因为它们朗朗上口,简洁易懂,容易得到广泛认同,并且能够被牢记心间,口口相传③。
这一时期,修辞术是“显学”。亚里斯多德写出了第一部修辞学论著《修辞学》。其中,他专门研究了话语修辞的各种机制及其在公共语境下的说服作用,由此奠定了西方修辞学理论的基本体系。
在中世纪,修辞主要表现在经验哲学的文字里。它以严格的逻辑来论证上帝本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表达的严谨性,这是近代科学产生的思维条件。随着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工具理性统治了人们的思维,人们开始质疑“修辞”是“以词害意”,是煽动情感、误导判断之术④。于是,修辞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局限于文学言语的各种修辞格,或者停留于论证的逻辑研究,较少关注受众的接受效果和行动⑤。
借助传播技术的力量,大众传播渗透生活社会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受其影响。日益广泛的传播引起人们对传播修辞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指向了传播效果层面。
传播史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增长、社会教育普及、政治参与扩大以及印刷术降低了平面媒体的传播成本,这些是报纸成为大众媒介的前提条件。表现在政治活动领域,报纸的出现意味着直接的面对面的政治传播有了中介,各种力量开始借助报纸来扩大影响,因而报纸成为了政治修辞活动的主要工具。报纸带来了传播规模化,宣传活动也更为醒目。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广播先后出现,传播媒介增多,并且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政治宣传领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双方都借助报纸、广告、新闻电影、宣传册等传播媒介,运用大量修辞技巧,进行心理战,威力巨大。战后,有一批学者开始从各自领域研究一战中的宣传并且出版了不少成果。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是其中的代表作。拉斯韦尔对战时宣传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且特别关注宣传技巧及其有效的运作机制:“我们知道宣传者是在某个具体环境中社会化的,该环境的具体特征将限定宣传者潜在的观点、想象和行为。而宣传者试图影响的受众,是那些在相似环境中社会化的人”。⑥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是广播时代最成功的政治修辞。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美国经济几近崩溃。为了求得美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罗斯福利用刚刚兴起的广播媒介,在白宫壁炉边,采用“谈话”而非“讲话”形式,进行全国动员。借助无线电波,罗斯福真挚的声音顷刻之间进入了千家万户,其影响广度远胜于古希腊政治家们的广场论辩和口口相传。“炉边”成了巨大象征。听广播的美国公众并不知道罗斯福总统是否在火炉边。其实,他是否真的坐在火炉边,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炉边”两字所带来的亲切感和感召力。在充斥着恐慌、不安、动荡的大萧条时刻,“炉边谈话”就像是冬夜里温暖的炉火,驱散了寒冷,带来了光明,也为罗斯福赢得了民心。今天,人们可能不知道“炉边谈话”的内容,却能够记住“炉边”两字。“炉边”作为一种符号,进入修辞领域,“炉边谈话”成为了政治学和传播学的经典。
在电视时代,政治修辞的内涵被进一步扩展。“当代政治离不开电视,离开电视的政治是难以想象的”⑦,这句话强调了政治、公众和电视之间密切关联。进一步说,政治合法性、社会共识或者利益冲突的公开表达,想要产生最大影响力,都离不开电视。而电视独特的媒介逻辑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现代政治,其修辞方式受到了布勒姆勒(Blumler)所说的电视“现代公开性”影响⑧,即电视影像的直观性和形象性。早在20世纪40年代,电视刚出现时,英美等国已经注意到新兴影像对未来政治修辞的影响。《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认为,“特写镜头不会使演讲者显得很遥远”⑨,这意味着在群众集会上被忽视的一个手势或表情,在电视屏幕上将十分显眼,政治人物的外在形象会更为重要。
综上可见,在古希腊时代和中世纪,人们比较强调修辞的逻辑性。在大众传播时代,报纸、广播、电视相继出现,修辞方式增多,各种符号、形象、场景、道具乃至活动都被纳入修辞范围。除了逻辑性外,人们开始关注修辞的直观性。
二、政治修辞的视频运用:从直观性到多元性
关于电视与政治修辞关系的早期研究文章中,普遍的观点是:传统浮夸的讲究戏剧性的演讲将让位于更随意的且能更好适应电视接近性特点的方式。美国前总统杜威对他的幕僚们说:“在广播时代,你们是对群众说话,而在电视时代,你们是和群众对话”10。到了这个时期,政治演讲越来越凸显简洁、随意而亲切的风格,美满家庭也成了政治演讲时重要的背景符号和修辞策略。
随着电视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电视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受到重视,也有学者称之为媒介范式或电视媒介逻辑。众多修辞学研究分支,诸如总统修辞、战争修辞、选举修辞、媒介修辞等都关涉电视影像逻辑。此时,除了直观性以外,电视影像修辞在政治传播中被赋予了更多内容,是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
美国政治传播学者把电视报道范式的影响因素概括为以下几方面:观众容易获得的接近性、反映事件广度和清晰度的图像质量、内容的视听元素的丰富性和戏剧性、报道所具备的普遍兴趣,以及组合报道的技巧等11,这种概括反映出美国政治活动对“隐藏在影像背后的技巧和技术”的强调。有意凸显人物个性、精心设计视觉形象、选择性提供同期声片段、重视人物出现的形象化场景以及简洁回答复杂问题,以适合电视播出。这一切也是政治活动的影像修辞要义12。甚至,里根前新闻发言人拉里斯皮克,在新闻发布会前,都会准备一到两个适合电视的新闻故事13。还有学者在分析美国新左派学生政治运动时指出:“新左派的行动得到报道是因为他们符合媒介范式,特别是视觉上的有利机会,如游行、标语、夸张的表达等。事实上,这种视觉机会是获得全国性关注的主要因素”14,可以说,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媒体记者,抑或社会团体,都已经意识到“视觉力量比对话和抽象的意义更重要……行为越具有视觉效果,报道就能得到越多的关注和报道时间”15。不可否认的是,为迎合电视戏剧化、娱乐化的范式需要,严肃的政治活动被过度“娱乐”,修辞符号被滥用,这种现象遭到严厉诟病。不过,这不是本文研究重点,在此不复赘述,举这些事例是为说明美国对影像政治修辞的细致研究和广泛运用。
事实上,在政治活动中,人们已经不仅仅只是关注修辞符号、道具的使用,还关注场景、情境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如英国学者布莱恩·麦克奈尔所说“政治修辞在公共场合与私下里存在着潜在不同”,他认为人际政治传播也关乎修辞16,可见,政治修辞已显现其活动性质。从古希腊中世纪到广播电视时代,政治修辞从重视逻辑性拓展到直观性运用,从语言的单一性转向了感觉的多维性转化,现在更拓展到情境、心理、活动等层面。
有学者把电视修辞称为是“一种体制结构”17,因为电视传播是一种权力不对等的传播,掌握传播权的一方,通过选择让观众看什么,对只能被动观看的观众实施软性控制。这一过程不是通过强迫的外在形式来完成,而是利用电视修辞,诸如,故事选择、解读引导、镜头设计等来获得。
在新媒体时代,政治修辞的涵盖面更为广泛,扩展到无所不包的社会空间。由于传播关系变化,每个网民都成了自媒体,传播权力也发生了转移,“这导致政治话语和政治基础的转变”18,互联网及网络视频的修辞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2004年5月,苏珊·桑塔格在《时代》杂志撰文:“影像不会消失,这是我们生存的数字世界的本质。一张照片、一幅画面抵得上千言万语。即使政治领导人选择不去看它们,还会出现成千上万的快照和视频,不可阻挡”19。
桑塔格的这段话表明,在网络时代,视频仍然是传播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并且更具本质意义。视频影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内容,虚拟网络空间开始具有现实空间的特性,人们在网络空间中交往、聚会、讨论进而成为商业、文化乃至政治活动的平台。
美国政治学家班尼特认为,数字时代向传统信息方式提出了挑战,人们更容易摆脱新闻媒体报道,而转向他们真正关注的事情和信息来源,政治家越来越难以控制信息议程,也越来越难以把它的信息传递给人民20,政治信息传播战略技术由此兴起并且趋向复杂。
以政治信息传播战略技术为视角,政治传播学者布勒姆勒和卡梵纳夫(Blumler and Kavanaugh)将西方半个世纪的政治传播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电视出现之前,传媒体现了强烈的政党意识形态;第二时期是通过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来传递政治信息,政治活动对传媒专业人才的需求增加,因为这些传播人才谙熟媒体逻辑,善于利用媒体达到传播目的;第三时期是目前正在形成中的“富”媒体时代(media abundance),因为政治新闻的生产机制充满了不确定性21,所以政治传播的专业主义显得更为重要。
无论班尼特所说的政治传播战略技术,还是布勒姆勒提出的政治传播专业主义,它们都直接关联政治修辞,也导向同一个目标,即在日益复杂的媒介环境中,如何使政治信息、政治活动能够说服公众,为公众所接受。
上述观点还表明,思想家们已经将目光投向了网络时代的政治修辞,但是,他们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诠释。面对一个新的传播时代,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这一问题。如何从修辞的角度理解互联网的变化,我们首先需要回到现代修辞理论研究,从中探寻修辞的逻辑进程。
三、现代修辞认同论:从情感到情境
20世纪60年代,各种媒介已经深入家庭,传播范围大大扩展,修辞学研究走向繁荣,以肯尼迪·博克为标志的现代修辞理论形成。此后,修辞研究吸取了后现代立场和方法,对修辞话语中认知性、意识形态、权力运作过程等进行了研究,这些不同分支理论从不同角度揭示修辞性质或功能。
1.从修辞目标看,从单向劝服转向了互动认同
亚里斯多德的修辞说服论是以行动为目标,以语言为手段,注重直接的目标效果和行动,只要对方接受,并不关心其内心是否真正愿意。现代修辞学则强调心理认同,认为修辞活动的本质和标志都是“认同”,要求受众的心理和行动均符合修辞者的期望。
为什么修辞要强调心理认同?肯尼斯·博克解释说:“在符号活动中,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求认同的情景中”,因此,修辞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发现“潜藏着的认同材料”22。如果修辞者能够抓住获得认同的情境,也就抓住了产生共同思想和感情的基点,从使双方行动真正达到和谐一致。布莱恩特(D.C.Bryant)认为,修辞作用在于向人传达意思,又能够让人传递意思23。的确,任何修辞主体都在传达意思,但是能否让接受者主动再向他人传递意思,则需要以认同为前提。否则,只能有一厢情愿的“传达”,难以赢得接受者主动配合式“传递”。
2.从修辞内涵看,从文本言说扩展到人的活动
现代修辞学将修辞定义为“用话语和象征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24,也就是说,修辞不再只是文本,一切以象征为依托的话语和行为都是修辞。这一定义扩展了修辞内涵和外延,把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都纳入了修辞的范围,因为活动及成果已经具有了符号的性质,用肯尼斯·博克的话来说,“哪里有说服,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说服”25,说服的目标就是对意义的认同,修辞能力决定了修辞的成效。
“媒介即信息”,麦克卢汉的这一命题已经隐含了工具符号的意义属性。他认为,一种新技术的使用往往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环境创造出来了”。以往人们只把媒介视为单纯的工具,它仅为承载和传播信息而存在,而麦克卢汉在使用“媒介”这一概念时,将人类的一切工具都视为媒介,作为人体的延伸,每一种新工具的使用,都为人类活动引入了新的尺度,它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进而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感觉,也改变了人们的语言、文化环境及其生活环境。在这里,重要不是媒介承载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
学者周宪、许钧在解读麦克卢汉媒介观时,特别指出了人类社会工具符号化现象:“人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从符号的角度看,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26,文化体现为符号,人类的一切工具,诸如器具用品、行为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皆是符号,也皆为修辞。
事实上,一旦社会的主导传播媒介变化,符号系统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媒介发展也会不断地丰富修辞内涵。当印刷传媒在社会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时,人们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符号及其修辞的运用,而当电视成为大众传播的主导形态时,图文声像影的视觉元素被纳入修辞领域。因此,在传播活动中,修辞要产生良好效果,必须理解并且符合传播媒介的工具特性,即前文所说的媒介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卫?伯格指出:“修辞学要成为社会分析有用的工作,必须关注媒体对人们交流行为的影响”27,政治修辞同样如此。
西方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注意到情境在政治修辞中的重要影响,其中代表人物为美国修辞学者劳埃德·比彻尔(Bitzer)。他认为“政治信息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情境,是对历史情境的必要反应”。28
袁影、蒋严两位学者在《论“修辞情境”的基本要素及核心成分——兼评比彻尔等“修辞情境”观》29一文中,对修辞情境论做了详细介绍和修正。
1968年,比彻尔在西方最重要的修辞学杂志《哲学与修辞学》创刊号上发表论文《修辞情境》,首次提出了“修辞情境”这一重要概念,它包括三个核心要素,即缺失(exigency)、受众(audience)和一系列限制(constrains)。
袁影、蒋严认为,“一系列限制”是无所不包的要素集合,内涵模糊,于是在比彻尔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修辞情境五要素”,即:缺失、受众、修辞者、场景和时机。除了将“一系列限制”做了更明确的细分外,他们还对“缺失”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分为情礼、信息、理念和行动等。
“五要素”丰富了原修辞情境论内容,使之更为合理清晰。两位学者观点对我们把握修辞情境论富有启示,概括来说,主要有三:1.修辞者与修辞对象(受众)构成了一对主客体关系,修辞者应有角色意识,包括自我社会角色、受众角色以及双方角色的关系认知,同时还应根据修辞对象所处的具体状态,选择合适的表达内容和形式;2.修辞者如能识别情境中所“缺失”的部分,比如信念、行动、信息等,就可以采取相应有效的策略;3.修辞要考虑场景和时机,其中包括事件状况、时间、场所、所处情境阶段等。
关于修辞情境论的研究都是基于一般意义展开的,尚未有学者对互联网的修辞情境进行研究。事实上,互联网改变了传播的主客体关系,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活动空间,进而导引了整个修辞环境的变化。在此情形下,修辞学研究不能仅仅只局限于某个方面、某个领域,而需指向涵盖所有方面的活动情境。这正是未来政治修辞研究所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 [英]约翰·汤普森:《大众传播与现代文化:对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贡献》,刊载于奥利佛·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主编:《媒介研究的进路》,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4页。
② [希腊]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4页。
③ 转引自[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④ 转引自成伯清:《社会学的修辞》,《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⑤ 胡春阳:《修辞分析:另一只眼看传播效果》,《中国传媒报告》,2009年第2期。
⑥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⑦ Jerry L.Yeric:Mass M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2001,F.E.Peacock Publishers,Inc.p.7.
⑧ Gianpietro Mazzoleni: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Television between Old and New Influence,In Maarek,P.&Wolfsfeld,G.(Eds)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New Era: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Routledge,2003.
⑨⑩ David A.Baird:An Emerging Emphasis on Image:Early Press Coverage of Political and Television,American Journalism,20,Fall 2003,pp.13-31.
(11)[美]戴维·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邵志择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12) Hoyt Purvis:Media,Politics and government,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p.67.
(13) Philippe J.Maarek,Gadi Wolfsfeld: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New Era: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Routledge,2003.
(14)(15)[美]戴维·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邵志择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7、64页。
(16) [英]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褀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17) 徐贲:《媒介知识分子手中的文字和图像》,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092sq.html。
(18) Janet Wasko&Mary Ericks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YouTube In The YouTube Reader 2009.http://www.kb.se/Dokument/Aktuellt/YouTube_Reader_Inledning.pdf.
(19) Susan Sontag,Regarding the Torture of others,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May 23,2004.
(20) [美]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杨晓红、王家全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21) Philippe J.Maarek,Gadi Wolfsfeld: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New Era: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Routledge,2003,p.2.
(22) [美]肯尼斯·博克:《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顾宝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 徐贲:《媒介知识分子手中的文字和图像》,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092sq.htm。
(24) 胡春阳:《修辞分析:另一只眼看传播效果》,《中国传媒报告》,2009年第2期。
(25) 成伯清:《社会学的修辞》,《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26) 周宪、许钧:《理解媒介:论人体延伸》中文版序言,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页。
(27) 胡春阳:《修辞分析:另一只眼看传播效果》,《中国传媒报告》,2009年第2期。
(28) 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29) 袁影、蒋严:《论‘修辞情境’的基本要素及核心成分》,《修辞学习》,2009年第4期。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教授)
【责任编辑:张国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网络视频传播与舆论引导研究”(项目编号:09YJA860025)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