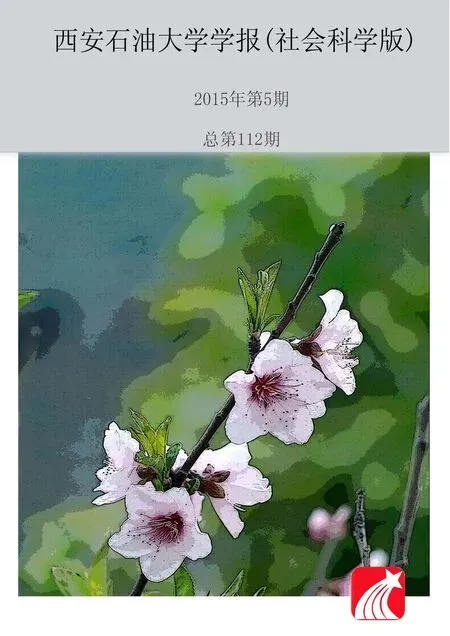论二十世纪新文学史视域下的鲁迅书写
2015-02-20荀睿
荀 睿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论二十世纪新文学史视域下的鲁迅书写
荀 睿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新文学史中的鲁迅书写是了解新文学史编纂的重要部分。百年新文学史发展中对于鲁迅的阐释体系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与书写者立场的不断转化和外界非文学性的干涉密切相关。通过对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新文学史著作中的鲁迅书写样态进行梳理,可明显地看出政治因素在解读作家及文学史重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而探讨如何回归对鲁迅的真实表达,如何以客观的态度突破文学史写作的传统局限,对文学史书写的反思和开掘具有启发意义。
新文学史; 鲁迅书写; 意识形态化; 文学史反思
0 引 言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的百年新文学发展史中,文学景观纵横、思潮迭起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表征。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大环境和文学实绩不断推演变化的事实,一辈辈新文学史家用自己的理解描述着新文学历史潮流。这其中不乏书写体例的不断探索,历史构架的一步步完善,视角立场的多重倾向以及对作家及文学现象的不同解读。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新文学治史的开端,一大批著作多元共生。在为文学作史目的驱使下,文学史写作也随时代变迁和作家个性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点。面对大量的史实,如何挑拣、筛选与描述成为发现新文学史和研究其价值的重要方面。在厚重的历史书写中,不同的作家、流派、作品统统被纳入其中,不同风格的文学史写作也在整合与表现这些内容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其中,鲁迅作为现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从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到支撑民族精神的“民族魂”,从作品到思想,从社会到人心,鲁迅作品及其代表意义在不同时代被发掘和解读的深度各有侧重。对于鲁迅文学家、革命家、启蒙者、战士等一系列定位也均可以在文学史脉络中搜寻到痕迹。不论是个人的对于文学史朦胧的感情还是有意为之的大规模集体“造史运动”,鲁迅书写带给我们的对于新文学史发展谱系的系统认知,文学史受制于社会环境的立场与政治氛围的无可奈何,以及文学造史的迷途和理想,都成为后世解读前代的宝贵经验,同时也催生着新的文学史写作的不断尝试和突破。
1 百年新文学史中的鲁迅
新文学的诞生正如其名一般具有一种决裂和革新的命运。伴随着晚清国门渐开,文学在中西碰撞和古今争驳的夹缝中完成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其转型的特殊性在于并不是由所谓的渐变而是采用革命的激进形式。新文学史的命运也由始至终与文学的革命形式保持着一致性。在这个文化激变的潮流中,最先要提到的便是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的这部著作并不是专门研究文学史的专著,“而是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作的。我的目的只是要记载这五十年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短历史,以备一个时代的掌故”[1]401。胡适是以白话来挑战文言的第一人,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刊发《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章“八事”,到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具体论及“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再到1923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问世,据胡适自述中说自己是一种单纯的“记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三个重要的文章实则是由对白话的新文学由理论倡导到史实依托的渐次深入。其在具体的叙史过程中,详述了五十年来旧文学发展的穷途末路,白话文学羽翼渐丰的实绩,并指明新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五十年中,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文学”,“乃是许多白话的小说”[2]6。这里胡适强调了白话如何优于古文。介绍文学革命的发展时讲到:“近五年的文学革命便不同了”,“他们老老实实的主张现在和将来的文学都非白话不可”[2]8。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争中白话的大获全胜使新文学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扫清了一次障碍。对于当时近五年的白话文学的成绩,以白话文学为核心,以形式的进步为进步。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白话文学的标准筛选史料,“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2]108。鲁迅作为唯一被写入的新文学作家,以出色的白话小说家在新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并独具代表,可以说这是胡适对于鲁迅的一种初步发现。
以白话形式的成功运用作为对鲁迅的描述显然非常局限。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关于鲁迅的部分对其做了修改、补充和更为全面的概述。《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以总、分的形式将文学发展置于一个更为扩大而富有动态的背景下。其在各体裁的分论中,对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进行了精到的分析,从“写实”笔法,“冷峻”文风,“吃人”与“救救孩子”的寓意剖析,以及“新形式”体裁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对鲁迅作品进行了概括。同时,对于鲁迅杂文的地位予以肯定以及另辟专章详述鲁迅及其追随者的情况,对鲁迅“国民性”、“人道主义”和乡土风格的发掘可以说把他真正作为了新文学作家来看待。由此使得文学史撰写的体裁分类格局得到确立,作家鲁迅的面貌得以和盘托出。
作为1933年出版的“第一部具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在小说的讨论一节中讲到:“谈到中国的新小说,没有人不知道鲁迅的”[3]139。在此王哲甫首先对于鲁迅作品辐射范围之广作了肯定。随后其认为鲁迅的成功是从日本小说中获得体裁与语言的“暗示”,《狂人日记》是一种侥幸的“意外”成功,这种评价显然是有失偏颇。而鲁迅的《呐喊》之所以获得“无数读者”赞扬,原因在于鲁迅不但以冷静的笔锋刻画国民的弱点,更是以“嘲讽中含着悲悯”、“冷眼之中含着热情”[3]139来关照当时的中国;他的散文,“以讽刺的笔锋,挖剔中华民族的‘国疮’,对于青年的思想有莫大的影响”[3]141,所以“他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无论在技术上,都已达到最高尚的境地”[3]140。虽然王哲甫这部文学史著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被认为“对作家作品的介绍主次不大分明”,但对于鲁迅作品思想性方面的认识还是有其独到的见解。紧随其后的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出版,将中国新文学史的编纂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小说集导言》的部分由茅盾和鲁迅分别撰写。作为《小说月报》主编的茅盾,出于工作重心和研究方向的特点,将他主写的中心放在了期刊发展并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的作家群。鲁迅撰写的部分则更侧重于以当时共生的流派、期刊为依托勾勒文学发展的线索。篇目开头点出“在这里(《新青年》)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4]80。这些作品,“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对于自己作品的评价怀着十分谦虚的态度。因“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年轻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4]80。他把自己作品的大部分成就归因于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和学习,而自己只是在这条中西交融的道路上“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渺茫”[4]80;在脱离外国作家影响之后,但也因“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4]80。这应该是新文学史编写上少有的对于鲁迅创作个性的定位和对于作品源流的探寻,甚至是少有的对于其创作正反皆有的公允评价。
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进程中,文学史的撰写必然会受到左翼思潮影响而带有时代特点。1931年作为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代替进化论立场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的出版,表明整个30年代新文学史书写进入一个大的转型时期。“用社会学的眼光,定立并说明了中国每个时代的社会形态,以及该时代所产生的作品和社会背景是什么,然后再来估定这一作品的价值”[5]1成为唯物史观的基本态度。因而从社会学阶级理论的角度把“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定义为“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社会意识斗争”[5]227的结果,作为所谓“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鲁迅和他的作品在这部文学史中的评价必然是“先分析他的时代”,由此把鲁迅的创作以1924年、1930年为时间点分为了呐喊、彷徨、转变三个时期。“呐喊”时期的鲁迅是“抨击封建势力最猛烈的”;“彷徨”时期仍旧是暴露封建社会的丑恶,但人道主义悲悯的同情却是他小资产阶级的特质;“转变”的原因是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尖锐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不愿做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要以反封建的精神来与“布尔乔亚”战斗。《中国文学史纲要》对于鲁迅及其作品评价更多的是夹杂了阶级论调与情感,认为鲁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的怒号者,表现了对他的文学的不甚满意,但对其加入“左联”之后转向无产阶级的前途充满期待。可以说《中国文学史纲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统摄新文学史编纂逐渐成为主流,并随着共产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在革命史的地位逐渐重要而又有符合中国革命实情的深化。在抗战时期,周扬在《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将“五四”运动作为政治上的历史分界点,即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分期。新文学史在“新的经济政治基础上且应新的政治要求产生”[6]302,也将服务于中国的基本革命任务,即反帝反封建。所以“五四”文学革命也就被定性为“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并且作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作为新民主主义的一部分被纳入社会主义的范畴。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中,鲁迅成为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着重突出于“精神界之战士”的榜样作用。因他的作品和思想从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变为无产阶级立场,从民主主义思想转变为共产主义思想,这种变化是与社会进化、与阶级理论高度吻合的,所以也无形中符合了战时共产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的探索。
伴随《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新中国的成立,现当代文学学科在新中国政权基础上得以建立,新生政权急于对无产阶级在新文学上的主导地位进行合法化论证。于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文学发展轨迹和发展方向的理论指导下,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应运而生。“中国新文学史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那么“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路线也就规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和方向”[7]5,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首先表现在“反帝反封建精神的彻底性上面”。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从开始创作,他自觉地使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革命服务的目的就是十分明确的”[7]97,代表了新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这部文学史著中对于鲁迅小说进行了农民题材与知识分子题材的分类。《阿Q正传》中精神胜利法的提出,对待革命艰难进程的透视,将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鲁迅对待中国的顽疾是一种“金刚怒目”式的姿态,却又对“老中国的儿女”抱以深切的同情。虽然新民主主义的调子把鲁迅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但在具体的表达中鲁迅创作的复杂性和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舒展。也就是从《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新文学史中的鲁迅以经典化的身份,在文学对革命和政治的从属前提下以及高压的政治环境中不断被加以描述,并在“文革”十年中达到顶峰。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神化”的鲁迅一直占领着主流。只有在“文革”结束、政治和文艺界的思想解冻之后,文学史编纂逐步回归文学正途,鲁迅书写的部分也开始经历由“神”向“人”的转变。从1979年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鲁迅“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8]88的塑造,到1999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对鲁迅“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9]29的定位,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史编纂开始出现更多“去政治化”倾向,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地位开始逐步超越甚至替代其革命者、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就像新文学史开端,将鲁迅作为一个卓越的作家、启蒙者进行书写一样,百年新文学史书写在此竟成巧合。而历史有它不可重复的一面,文学史发展也必然紧跟历史脚步,对于后来者面对“鲁迅”这样一个厚重的文学现象如何把握,如何选择立场与角度进行书写,不但是值得探索的,也更是值得反思的课题。
2 催生鲁迅书写形态多样化的立场
纵观百年新文学发展史与新文学史编纂实践,每一位书写者都试图在历史发展客观性与自身立场的主观性之间寻求平衡。在一次次历史书写的尝试与实践中,尽管每个人都怀着极大的热情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新文学史树碑立传,但很大程度上,“大多数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10]302也许来源西方的文学史评价并不是十分贴合中国新文学史的编纂实际,但通过对于文学史中鲁迅书写部分对比发现,这些著作不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学史风貌,而且暗含着互相区别的文学史立场。从20世纪这个大的时间过程来看,按照文学史一般的每十年作为一个节点来划分,在文学史书写上也可以作为标志性的划分。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作为第一个文学革命的十年的代表性的新文学史著作,势必与胡适的文学进步观念息息相关。按照胡适沿袭的西方进化论思想,“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11]22,因此虽然作为“附骥式”的新文学史还没有得到文学史的独立地位,但在“新旧”“活死”文学对立这样坚决的立场中,他所称许的“白话文学”所代表的新方向不言自明。很大程度上鲁迅作为新文学小说家被提及也是为了证明白话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蓬勃的生命力,而因了文学进化论的立场,形式变革成为了革命的急先锋,自然也就无暇探究鲁迅作品“没有不好的”的其他原因了。鲁迅的作品作为文学进化观念强有力的证明被高举,但毕竟潜心研究文学发展史的其他学者是不能满足于这样粗暴的单线定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与鲁迅的《小说集导言》则是站在一个相对冷静的历史高度来书写第一个十年中关于文学发展的问题。秉持中西文化交融的立场和中国的“朴学”传统,文化发展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与进化论所谓“以新代旧”的断裂相区别的,因而他们的文学史更注重对于作品文学性本身的把握。虽然鲁迅等人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已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发展时期,但编纂者身份多是经由20世纪20年代文学革命的亲历者,他们“身作”和“心构”历史的特色完全有别于左翼文学史的书写,与之同时期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细心描绘文学发展的全貌,虽通过俄国文学在中国被翻译的情况推论出“这可见世界文学的潮流,已趋向于无产阶级的文学”[12]264,这样的分析立论不免有过于牵强之处,但也并非彻头彻尾的阶级论者,因而与20年代文学史立场更有相似之处。
在左翼文学渐成主流,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统摄文学史编纂的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书写迎来了又一个大的转折。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左翼作家团体中被推广以纠正“革命的罗曼蒂克”倾向,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左翼作家并没有完全把‘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当做一种纯粹的艺术方法,而是作为观察和分析事物的一种新的立场和角度”。[13]17就是在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史纲要》等一批站在左翼阶级论立场的新文学史问世。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学目的随革命及政治形势发生着愈来愈不单纯的变化,伴着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使得依附于文学发展的文学史却也无法回避这样的命运。因此,在“左联”成立之前的,不激进的、不代表无产阶级立场的鲁迅及其作品因了这一立场的限制,就不可能得到这类文学史的认可,也只有到“左联”以后,才被提升了地位,被认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作家。这种将鲁迅分为前后两种阶级身份的观点很快在20世纪40年代被取代。为了适应战时宣传鼓动的需要,突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在百年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领导和推动作用,1940年《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赋予新文学一个全新的身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武器的作用参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6]21实际上,周扬并没有采用绝对的阶级划分的方式来分析新文学阵营,他所采用的是社会历史评价的方法,用与封建主义对立的民主主义革命来囊括新文学的内容。“文学革命是经过白话对文言的剧烈斗争”,是“思想上民主主义对封建主义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6]105。在这里关于鲁迅书写的内容,便有了对其民主主义战士的转向,突出了“我们在鲁迅初期思想中所唯一要看取的是那种朝气蓬勃的、凌厉无前的民主主义者的战斗气魄”[6]31。其中列举关于《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一系列早期关于精神战斗、国民性改造、思想启蒙的内容,作为“旧民主主义新文化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先声”。[6]30文学革命的重心在于以新的形式表现新的思想,所以《狂人日记》是“第一次在现代小说的形式上把反封建思想和白话文学真正结合了起来”[6]108。在经历3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大讨论之后,对于《孔乙己》、《药》等作品的评价也受其影响,成为“严峻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对于封建制度和思想最有利的控告”,基本上还没有超出反封建的范围。逐渐地,随着共产党执政前途的逐渐明朗,面对文艺界出现的思想“混乱”局面,整风运动时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使得单纯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析还是无法满足政治上无产阶级对于文艺领导权的掌控,这就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武器来加强这种领导。因此随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便继而提出了政治上无产阶级的新方向,文艺上工农兵方向,观念上新旧民主主义划分等一系列基本要求和经典论断,《中国新文学史稿》据此说明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文学”[7]5。所以,新文学史编写也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依附政治的新文学发展立场。鲁迅因他作品中反封建与革命性的价值以及其自身与“左联”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密切关系能够很充分的说明无产阶级对于文艺界之巨大影响,因此作为文化界领袖和方向的意义被不断放大。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文学史政治化的倾向愈演愈烈,也使文学史书写被迫停滞。在“文革”结束、理论界展开广泛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文学史的思想解冻也渐渐展开。从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虽展新姿仍存旧痕”[8]119的努力,到钱理群等新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出发,尽可能地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出发进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书写。20世纪“所特具的思想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9]7。这样的立论根据很大程度上是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学人的精神追求分不开的。鲁迅以“改造国民灵魂”的事业为使命,这种使命感渗透到了他所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中,因此解释鲁迅的文学活动是从社会及阶级革命以外的角度来予以关照,也是避免陷入历史的强制解说下意识形态要求与审美自由悖论的方法。从这种角度讲“启蒙论”的立场引领着中国新文学史的重生。
新文学史书写者们力图寻找一种全面的更贴合历史真实的书写模式,然而立场的自由选择与政治的实际要求往往让人无所适从。文学史编纂立场的演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是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杂糅的产物,只是在文学史家权衡这些客观条件的同时又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影响书写者的方向,而愈发激进的立场反而让文学走向极端,也只会让文学史的发展陷入僵局。
3 鲁迅书写下文学史编纂的困境与反思
真正的文学应该正如周作人所提出的朝着“人的文学”方向发展,致力于对人的发现和对人生的尊重。真正的文学史也应该是以求得历史真实为目的,饱含对历史的“同情”。因鲁迅在新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往往通过对其在各个历史时期评价的分析,可以更为真切的感受到书写者对于历史和文学的态度。显然,在进化论、阶级论、唯物史观等一系方法和立场的指引下,我们看到的是“鲁迅”变成了一个符号被不断地强化,鲁迅研究在以“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创作和评价格局中单线突进,对于鲁迅在文学史书写的样态也随其文学政治影响力的拔高而随之附和,而真实的鲁迅就在这种有意为之的书写中被遮蔽掉了。不可否认,就像“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家们对待旧文学的态度一样,以革命姿态所进行的“破”和“立”的文化实践在中国的各个领域不断发酵,使得“激进主义”的观念随着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越来越深入。不断强化的政治要求代替了文学的规律和传统的文学观念,这样的畸形发展结果与最初的文化革命方式密不可分。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我们不应对那些文学史书写者一味苛责,历史书写也有其无奈的一面。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不断的批评那些过去的错误的甚至极端的思想,着力在于认清过去的包括观念上和实践上的种种失误,并试图寻找一种新的评价方法来打破原有体制内对于权威历史的解读。事实上,总有人敢于冲破观念的藩篱,正如20世纪80年代对作品的“重读”、对文学史的“重写”,无疑是一个对经典论定的挑战。尽管并没有彻底扭转文学史发展的格局,但重要性在于是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历史的个人创见”[14]4,以“纯审美”标准对文学进行评价的尝试,它试图让人们对历史有一个真正的反思和清醒的态度。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学者N.福斯特所言:“文学史家必须是个批评家,纵使他只想研究历史”。历史与批评在同一个瞬间联系在一起,成为文学史的一个特殊的现象。作为具有文学批评精神的文学史家必须超越纯粹个人感性经验的主观判断,此时就必须要发挥历史的规劝作用。而所谓历史的公正态度又常常是暗合在书写者的思想意识之中,这种潜在的影响,势必会在主观的文学批评之下呈现出强弱的差别。文学书写的客观性长期以来被思想史发展的主观倾向所钳制,因此对于客观历史的考量也渗透着主观的态度。政治标准、意识形态话语成为了解读一切文学、文化甚至社会现象的工具。思想的简单化使得文学史也可以用“对”和“错”这样极端的贴标签的方式进行评价,以至于形成思想的惰性,刻意地回避那些原本复杂的文学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以论代史”等一系列错误文学史书写观念的影响,书写者无视或是“不了解历史上的情况,他将常常误解许多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10]39,也必将大大折损文学史的价值。
客观的历史标准和书写者的批评尺度并不是一场刻意地要求谁服从于或是屈服于谁的博弈,这种矛盾也不是简单的调和论就可以得到解决,二者应是在同等层面上来进行探讨的问题。书写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得对于历史的解读从来就不只有一种方式,正如文学形态的多样化一样,文学史书写也应该在追求客观历史的构架下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就如20世纪之后的文学史编纂中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做出的努力,鲁迅书写应尽量回归历史常态,文学史也应逐渐摆脱“大一统”的局面,在不断探索的标准中寻找新的方向。
[1] 胡适.胡适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M].北京:新民国书局,1929.
[3]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M].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
[4] 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5] 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M].北京:斌兴印书局,1933.
[6] 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J].文学评论,1986(1).
[7]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
[8]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9]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1]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3).
[12] 刘增杰,赵福生,杜运通.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
[13] 黄修纪.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4] 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主持人的话[J].上海文论,1988(4).
(责任编辑 陈红娟)
Luxun's Writ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History in 20th Century
XUNRui
(SchoolofLiterature,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Shaanxi,710119,China)
Luxun's writing in new literature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compil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In one hundred year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history,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s of Luxun's writting are constantly changing,which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writer's position and non-literary interference.Sorting out the various periods of representative work about Luxun's writting in Chinese new literary history,and discussing problems about how to return to the true expression of Luxun's writting and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limitations about writting literary history,both have the inspiration significance in the reflec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literature history writing.
history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Luxun's writing;ideologicalization;reflec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2015-05-08
荀睿,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10.97
A
1008-5645(2015)05-008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