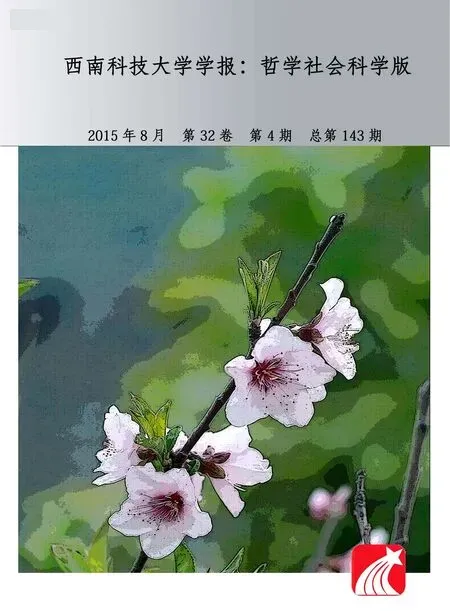吴文英审美人格和审美心理分析
2015-02-20谢盛华
谢盛华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广东广州 510520)
吴文英审美人格和审美心理分析
谢盛华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广东广州 510520)
宋末士人在普遍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之后,走向了对自身人格的消解。在没有任何社会意义的基础上一味地消解,最后走向了无任何目的、无任何中心的人生,无法建立起任何一种人格规范。宋末奔竞之风的矛盾心态;仕不能、隐不能的两难抉择和边缘化的人格,造就了吴文英多变的价值取向。他的词作是苦闷的、感伤的、颓废的、繁复的、隐晦的,唱出了江湖士人漂泊的无奈凋敝和社会转型的压力与阵痛。这些作品在他自己编织的梦幻世界,似一抹浓重的暗影投摄在心灵的最深处,映射出吴文英黯淡的心态以及迥异的变态审美心理。
吴文英;士风;梦窗词;人格心态;变态审美心理
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生活在动荡、险恶的宋末时代。昏君当政,权相专权,造成了“君子在野,小人在朝”的不合理现象,畸形的社会加深了他们对政权的疏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德力量和规范的失守,造成了儒家伦理人格的解构,士人怀着对儒家精神的依恋,逐步走向了对儒家人格的叛逆。党争激烈、权相相争,士人多于夹缝中求生存,少了南渡之初那种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爱国热情,大多低迷颓败,顾影自怜。士人逐渐消磨了自己的责任感,在腐朽没落的政局中自甘堕落,随波逐流,一时间奔竞、奢靡、变节之风泛滥。而正直的士人,大多也采取躲避、漠然的态度,过起了“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隐逸生活。
一、隐逸之风与边缘人格
“在其根本意义上,中国之‘美’(美学)有别于西方,它是一种对付、处理人生的困厄、毁誉、吉凶的手段,是一种体现人生圆满自足的人文精神,因而是中国传统士人人格修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正是有了美学的存在,古代士人的人格才得以完美;而正是有了完美的人格,中国古典美学才更显其独特的魅力,二者相辅相成。”[1]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儒家正统思想逐渐式微,因而人格美学也随之改变。首先,政局的变化改变了士人那种以仕为荣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士人心态。
吴文英以幕僚和清客的身份潦倒终生。在梦窗词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对国事的关心,对仕宦生活的向往,但更多的是入仕不成的失落。他的心中充满了“铜华沧海,愁霾重嶂,燕北雁南天外”的家国之忧以及“浪迹尚为客,恨满长安千古道”的失意悲痛。因为畸形的社会形态、腐朽的科举制度以及个人出身等诸多原因,惨遭时代的拒绝与庙堂的放逐。他只能以幕僚和清客的身份“曳据王门,附声权贵”,算是对不能进入仕途的一种弥补。但是他向往如苏秦、范蠡一样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业,留名青史的梦想却无法实现,只能“灯前倦客老貂裘”似的一事无成。梦窗有对国事的关注和忧虑,但是作为幕僚和清客的他毕竟远离政治中心,没有经纬国家的权利,这样的状态是非常尴尬的。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如上层士大夫那样拥有雍容娴雅的心境与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更多的则是对自身生存处境的伤感和哀怜。于是在隐逸风气的盛行之下,梦窗亦希望在自然山水的抚慰下舒解人生失意的悲哀,寻找心灵的避难所。在梦窗词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决意归隐的表述:
归隐何处?门外垂杨天窄。放船五湖夜色。(《大酺·荷塘小隐》)
以设问的方式写出自己归隐的理想所在——不是门外垂杨那样狭小之处,难以容纳广阔胸怀,而是到范蠡隐居的太湖,月夜放舟,超逸洒脱。
湘浪莫迷花蝶梦,江上约,负轻鸥。(《江神子·送翁五峰自鹤江还都》)
用庄周梦蝶之典,告诫自己不要迷恋官场仕途,人生短促,荣华如梦,不如早早归隐,实践鸥盟之约。
这样的例子在梦窗词中还有很多。可见在社会风气的熏染之下,梦窗亦有归隐的情结,但是仔细研读,却发现这些作品中真正写自然风光和隐居之乐的并不多,更多流露出的是一种对时事的无奈。面对现实,词人无可作为,放任自流,隐逸或许是一味安抚心灵的良药。吴文英在仕与隐之间无奈地徘徊。当然,这种彷徨、苦闷与失落是时代、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吴文英仕不能,隐不能,两难的境地造就了他无奈的心态和边缘化的人格。一方面,梦窗无法敲开权贵的大门,无法挤入政权中心成为上层精英士人;另一方面,他既缺乏隐逸的资本,也没有真正老死埋名乡间的勇气,终摆脱不了被孤立的命运和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于是,他成了这一社会里的“局外人”。而正是这种“边缘化”的人格,造就了他多变的价值取向,使他不会像姜夔那样以名士、雅士的身份孤高自傲、不合流俗;更不会如稼轩那样尚侠任气、率性直言。在末世隐逸之风盛行下他非仕非隐,这是时代凋敝和社会转型的压力与阵痛,两难的处境实非其心甘情愿。因此,吴文英一生都处于不安、焦虑和彷徨的状态,他的作品是苦闷的、感伤的、颓废的、繁复的、隐晦的。
二、奔竞之风与矛盾心态
南宋后期,政治上的最大弊端就是权相专权。理宗时史弥远擅权,度宗时贾似道专政,宰相以个人之好恶掌握百官的命运,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一批士人禁不住利益诱惑,主动加入奔竞的行列。吴文英所生活的理宗、度宗两朝,士风最为低迷。“清高”士人在名利面前成了名副其实的投机者、软骨头,奔竞之风最终使士人人格扭曲、价值观裂变。对新的人生价值观的迷惘,进而影响了一代美学风尚的转变。正如在评论魏晋士人人格美学特征时所说:“结束了先秦两汉时期美学依附于政教道德的狭隘境界,将审美和艺术创作与动荡岁月中士人的生命意识与个性追求熔为一体。”[2]
宋末士人在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之后,走向了对自身人格的消解。他们在没有任何社会意义的基础上一味地消解,最后走向了无任何目的、无任何中心的人生。此时,对儒家人格的解构已成为定局,而士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又使他们无法建立起任何一种人格规范。所以,这个时期士人基本上是在人生中游戏的一群人,正如当代西方的后现代,只是一味地消解,而无法建立起具有建设意义的崇高人格。宋末士人正是中国古代的一群类似当今“后现代”学说的实行者,他们在无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人格解构中,把人性的社会意义也解构了。
由于风气使然,吴文英亦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奔竞的行列。他是权贵门上的常客,以词章出入侯门,结交的朝廷显贵有两浙转运使判官尹焕、权相史弥远的儿子史宅之、参知政事吴潜及丞相贾似道、度宗的生父嗣荣王赵与芮等,梦窗与他们赋词唱和,过从甚密。吴文英没有远离权利中心和政治斗争,却在当时奔竞风气的影响下,不自觉卷入其中,饱受心灵的痛苦挣扎。梦窗与吴潜二人曾共游沧浪亭,梦窗作《金缕歌·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词,吴潜亦有和章。通过这首词,可以看出两人真挚的友谊:
乔木生云气。访中兴、英雄陈迹,暗追前事。战舰东风悭借便,梦断神州故里。旋小筑、吴宫闲地。华表月明归夜鹤,叹当时、花竹今如此。枝上露,溅清泪。
遨头小簇行春队。步苍苔、寻幽别坞,问梅开未?重唱遨头小簇行春队。步苍苔、寻幽别坞,问梅开未?重唱梅边新度曲,催发寒梢冻蕊。此心与、东君同意。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
这首词感慨时事,上篇从沧浪亭着笔,由悼古写起,缅怀中兴的英雄,伤叹不堪回首的往事,面对物是人非,词人潸然泪下。下篇则抒发了二人游园的同优同愁:“此心与、东君同意。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
吴文英也曾在贾似道府酬唱,《梦窗集》中有赠贾词4首,其中有3首作于这一时期。梦窗以词结交权贵,献上的多是寿词或宴饮时即席之作,这在南宋时的上流社会非常流行。他为贾似道写了《宴清都·寿秋壑》与《木兰花慢·寿秋壑》两首祝寿词,以精致巧妙、铺排夸张的语言对贾似道曲意逢迎,尤以《木兰花慢·寿秋壑》中“黄粱露湿秋江,转万里、云樯蔽昼。正虎落、马静晨嘶,连营夜沉刁斗”为最。善于用典的梦窗,把贾似道比做劳苦功高的文太师;比做汉朝大将周亚夫,歌颂其治军有功、国泰民丰。在这些词中,我们看到的是闲雅高华的情调和伪饰生平的语言。梦窗以词章为谋生手段,曳据权贵,为实现个体价值和满足生活需求,他的“边缘化”人格以及时代的谄谀风气恰似一道催化剂,致使他最终选择了随波逐流。
梦窗矛盾的边缘化生存状态,使他矛盾地挣扎着,煎熬着,在物欲与高洁间无奈徘徊。因此,吴文英是一个矛盾的、复杂的个体,也是最真实的个体。在奔竞之风下所显现的矛盾心态,是吴文英悲观个性的体现;是一个文士受士风所左右,人生轨迹被动转变的写照。最终,梦窗潦倒终生,无法逃遁“困踬而死”的结局。这是大的时代环境造成的命运悲剧。
三、江湖风气与凄凉感伤的心境
宋末社会,求仕之路的艰难使得众多士人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他们欲进不能,欲退不甘,只能流落江湖,辗转奔波,饱受羁旅之苦。于是,浓重的江湖风气在宋末文坛弥漫开来,大群奔走在江湖的士人共同构成和推动了这股江湖之风。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委顿江湖的寂寞与无奈,以及流落江湖的奔波劳碌与漂泊无依,吴文英正是宋末江湖士人的典型。他的人生是众多江湖士人的缩影,他的《梦窗词》唱出了这个时代江湖士人漂泊的无奈。
吴文英的一生是奔波的一生。他常常奔波于杭州、吴中、淮安、新邑等地:45岁,梦窗离吴赴杭,46岁,重返苏州,47岁,又返回杭州,50岁后则一直奔波于杭州、越州两地。为生计所迫,他长期处于频繁的旅途奔波之中,在生活和情感的双重压力下,其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漂泊无依之感、天涯羁旅之恨:
自叹江湖,雕龙心尽,相携蠹鱼箧。(《一寸金·赠笔工刘衍》)
东风不管,燕子初来,一夜春寒。(《诉衷情·柳腰空舞翠裙烟》)
霜饱花腴,烛消人瘦,秋光作也都难。病怀强宽。恨雁声、偏落歌前。记年时、旧宿凄凉,暮烟秋雨野桥寒。(《霜花腴·重阳前一日泛石湖》)
算江湖幽梦,频绕残钟。(《江南好·行锦归来》),
一寸悲秋,生动万种凄凉。(《玉蝴蝶·角断签鸣蔬点》)
思渺西风,怅行踪、浪逐南飞高雁。怯上翠微,危楼更堪凭晚。(《惜秋华·八日飞翼楼登高》)
身老江湖,蝶情春飞雁天南。(《声声慢·和沈时斋八日登高韵味》)
在词中,梦窗为我们呈现的自画像多是一个漂泊不定、旅食他乡、身处江湖的落魄文人形象。他深深厌倦这样的生活,将自己喻为一事无成、身心俱疲的江湖“倦客”: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十二郎·垂虹桥》)他慨叹自己孤苦无依的困厄命运:“衣懒换,酒难赊,可怜此昔看梅花。”(《思佳客·癸卿夕》)“窗粘了,翠池春小,波冷鸳鸯觉。”(《点绛唇·和吴见山韵》)他对自己的前景感到迷茫、恐惧,便不停地用回忆与梦幻同自己对话,用年少时的美好温馨消解如今的寂寞:“紫燕红楼歌断,锦瑟年华一箭。”(《谒金门·和勿斋韵》)“玉舟曾洗芙蓉水,泻青冰。秋梦浅,醉云清。”(《花上月令·文园消渴爱江清》)长年的羁旅漂泊意味着动荡、不稳定、不安宁和无归属感,这种无着无依的悬浮状态给梦窗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梦窗词完美的将奔波的孤寂凄苦与人生的失意困顿融合在一起,通过自己的所思、所感,将一番凄美幽怨缠绵地抒发开来。
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人阶层漂泊无依、缺乏归属感的境遇所造成的巨大焦虑,为话语建构提供了强大的心理驱动力。对吴文英而言,宋末日渐衰颓的国势、曾经美好爱情的逝去,都与其浮萍般的生命紧密相连。他如一叶扁舟,游幕江湖,沉沦下僚,扮演的角色仅仅是权贵盛宴上的点缀,这样的生活伴其一生,直至风烛残年,困踬而死。他天生的敏感和多情,将这种浪迹江湖的漂泊之感、绝望迷茫的状态诠释得凄迷感伤;将家国之感、身世之叹、离合之悲3者浑然融合。这种独特的人生审美心态和复杂情感远非柳永、秦观等盛世羁旅词人所能体悟,它只属于末世的江湖士人,属于奔波一生却布衣终身的吴文英。他的一首《永遇乐·乙巳中秋风雨》将这种凄凉感伤之美渲染到极致:
风拂尘徽,雨侵凉榻,才动秋思。缓酒销更,移灯傍影,净洗芭蕉耳,
铜华沧海,愁霾重嶂,燕北雁南天外。算阴晴,浑似几番,渭城故人离会。
青楼旧日,高歌取醉,唤出玉人梳洗。红叶流光,苹花两鬓,心事成秋水。白凝虚晓,香吹轻烬,倚窗小瓶疏桂。问深宫,姮娥正在,妒云第几。
“雨侵凉榻,才动秋思”展示了自己漂泊、凄苦、孤寂的生活;“缓酒销更,移灯傍影”描写自己愁绪满怀,只能以酒消愁。“傍影”写出陪伴自己的只有灯下的影子,突出了形影相吊的孤独意境,而窗外传来了风雨淅沥、芭蕉簌簌的声响,更添离人心中凄苦。在风雨中,“渭城故人离会”,已经没有熟悉的人了,剩下的只有孤独、寂寞、凄苦。下篇写自己悲欢禽合的往事,“青楼旧日,高歌取醉,唤出玉人梳洗。”回忆了昔日那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可是转眼间,“红叶流光,苹花两鬓,心事成秋水。”一事无成的自己已是两鬓斑白,心凉如水;外面风雨停歇,白云凝滞,屋子里炉香将尽,月光黯淡,爱人已不在。这首词充满了人生失意、感伤凄凉之美。
总之,梦窗词所呈现出的凄凉感伤的心境,与吴文英身处末世、寄人篱下、四处漂泊的生活和心态是分不开的。吴文英的这些江湖词作渗透着时代的伤感和自身的困惑,是词人自己真实情感与人生的写照,在一定程度上亦代表了宋末江湖风气盛行之下的士人普遍心态和情绪体验。
四、颓废士风与变态审美心理
法国19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美学家丹纳曾说过:“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3]虽然,我们并不认为时代背景对美学具有决定作用,但又必须重视时代风潮对美学建构所应有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社会的重要转折时期。宋末是中国历史上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频繁的年代。在一个动乱不安的年代里,试图完全抛开社会环境的存在是无法考察吴文英美学观点和审美心理的。
吴文英在强调个体独立的条件下,将自己审美理想的主体性从群体伦理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强烈地突出了其个体在审美心理中的主体地位与重要作用,使个体从群体中独立出来,从某种程度上对建立在儒家伦理人格基础上的美学进行了一次解构。
宋末残酷的社会现实,恰似一抹浓重的暗影投摄在吴文英心灵的最深处,颓废的士风造就了梦窗黯淡的心态以及迥异于人的变态审美心理。在士风普遍颓废不振的情况下,吴文英的心理亦因此而波动。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时代的忧患意识和抑郁情怀,反映出其在特殊的历史时代的痛苦乃至于绝望的心路历程。
变态审美心理,是一个由精神病领域借入到文艺创作理论中的专用术语,“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虚实不分,真假莫辨,混淆现实与想象或幻想的界限,把想象或幻想当成真实,把心理的东西当成物理的东西。他们在内心里建立一个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似乎觉得有充分的信心;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人们所理解的现实的共同因素对他来说是不真实的。他根据自己的感觉来解释一切事物,而不顾也不了解实际的情况 其实做梦也正是一种变态,不过这是常态的变态。”[4]高尔基说:“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的。”也就是说,艺术是想象的产物,创作者在文学生产的活动中以非常态的心理观照事物,使作品显现出怪异的审美亮点。
吴文英混迹江湖,身受离乱、羁旅行役之累、世态炎凉之感,又遭遇情感无归宿之苦,都使敏感的词人对那幽怨缠绵的心灵吟唱不已。面对着国事日非、情感失意,他无法排遣个人内心的痛苦,于是便把自己编织在梦幻的世界里,以获得情感或心理上的某种补偿。吴文英以这种变态审美心理将缕缕情思寄托在自己的词作中,将平生的失意和悲观融入到自己所营造的梦幻世界里,因此他的那些如梦如幻的作品留给人的是消极、颓废的感觉。
吴文英特别精于写梦。据初步统计,在现存梦窗词341首作品中,“梦”字出现的频率高达176次(不包括虽写梦境但是无“梦”字的作品)。梦窗如此钟情于写“梦”,这在以往的词人中是罕见的。“其词的梦幻美主要体现在作品意境的创造上,表现出一种雾里花水中月的朦胧效果。这种美,我们只有用心去体味,才能获得恍然惊喜、真实而新鲜的感受。”[5]吴文英的梦幻心理,“可以看作是对宇宙人生的一种‘虚无’心理,其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态度,一般来说可以表现为两种情况:达观和悲观。因觉梦幻而达观或努力达观,前者是‘道’、‘佛’的境界,后者我们在不少文人的作品中也屡见;因觉梦幻而感梦幻的可爱,苦苦地寻梦、找梦,则难免落入悲观的渊薮。”[6]
事实上,在吴文英的词作中,我们很少能看到词人因幻梦而达观,更多的是词人于梦中的沉醉与怅然若失。梦窗执著于梦幻的写作,虽然充满了一种破灭感,呈现出悲观的心态,但是他却又屡屡主动地去寻找过去遗失的美好,其结果是对现实、对未来的更加失望。于是,他转而再回到梦中寻找寄托和慰藉,如此周而复始地恶性循环,使得他作了一首又一首的词,也做了一个又一个难圆的梦。
吴文英词中有很大比重的伤逝感怀之作,充溢着词人生离死别的生命之恋。一些温馨总是如梦如幻地映现在词人情感的窗口,挥之不去,久久沉浸,令其伤怀不已。如自度曲《莺啼序·春晚感怀》:
残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绣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 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
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 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
幽兰旋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别后访、六桥无信, 记当时、短楫桃根渡。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
在这首词中,吴文英回忆了与杭州亡妾共同生活的难忘时光。在梦幻的境界里,词人似乎又回到当年的西湖,无论是与爱人邂逅相遇还是到后来的生离死别,都写得感人至深。词人仙境般的热恋生活转眼成空,接踵而来的是洒泪相别。斜阳空堤,仅剩鸥鹭。从初相逢到惜别,整个故事恍倘迷离,昔日之情历历在目。忽然间,词人仿佛又看到了爱人的眼睛,于是又重回梦境。吴文英抒写了如梦如幻的心灵颤动以及生离死别的迷离恍惚,可谓今昔交错,大开大合,大喜大悲,荡气回肠。其中,相思的悲情只能寄予琴声,伤心奈何,此恨无期。在这首《莺啼序》中,吴文英如痴如醉地沉迷于往昔的梦幻,梦境复杂深曲与现实交错辉映,缠绵悱恻地抒写了词人心中浓重的苦恋相思之情,饱含了对幸福爱情的热烈追求与渴望,充满了“好景永逝,今不胜昔“的无限哀伤。在颓废、委靡的风气之下,梦窗词亦呈现出颓靡、感伤的艺术特质。吴文英通过虚实相生、如梦如幻的笔法,将这种感伤情怀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反映了词人的真情实感,读后感人肺腑,动人肝肠。吴文英凭借其迥异于人的变态审美心理,在词体创作领域开创出一种全新的审美范式,以炫人眼目之态屹立词坛。
“梦窗词既非单纯的再现亦非单纯的表现,在一个新的更深刻的意义上看它是一种对形式和美的发现。”、“一千几百年的词是一部不断改变和丰富词的风貌,不断扩展其美学领域的历史。尽管不同时代词评家、词选家的价值标准,审美理想因时代潮流而有所变化,致使词人的历史地位在不同的时期升沉涨落,但真正的大家,终会从千峰竞秀、百川争流的词坛上脱颖而出,接受历史的裁决。“[7]
结语
宋末士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的审美人格心态与审美心理,进而影响到文人作品风貌。吴文英词作所呈现的复杂性、梦幻性、矛盾性等诸多特征,是词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受时代风气所左右,自觉或被动做出的选择,进而折射到文学领域的一种表现。正是由于宋末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士风的影响,才造就了这种与衰世相应的,别开生面、戛戛独造的梦窗词。
[1] 刘月.魏晋士人人格美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5.
[2] 袁济喜.六朝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
[3] (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7.
[4] 吕俊华.艺术与癫狂[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
[5] 刘国文,金乃茹.李商隐诗和吴文英词的比较研究[J].时代文学,2014.2
[6] 田玉琪.徘徊于七宝楼台[M].北京:中华书局,2004:26.
[7] 周茜.映梦窗零乱碧——吴文英词艺术价值论[J].南京大学学报,2013,2.
WUW en-ying’s Unique Aesthetic Personality and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Analysis
XIE Sheng-hua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Arts,Guangdong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Guangzhou 510520,Guangdong,China)
After the late Song Scholars in general lost superior social status,their own personality falls into absence.Blind absencewithout any social significance,has at last the trend of lifewithoutany purpose and withoutany center,unable to establish any kind of personality specification.In the Late Song Dynasty the ambivalence of longing for interest and competition aswell as the dilemma that they cannot be an official or hidde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personality,creat WU Wen-ying various value orientation.His works are depressed,sentimental,decadent,complicated,obscure,expressing the itinerant scholar wandering helpless depress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essures and pains.These worksweave in their own fantasy world,like a touch of heavy shadow casting in the deepest soul,and reflecting themind mapping ofWUWen-ying and different aesthetic psychologicalmetamorphosis.
WU Wen-ying;Saxophone;Mengchuang words;Personality mentality;Metamorphosis aesthetic psychology
I207.23
A
1672-4860(2015)04-0025-05
2015-02-13
谢盛华(1975-),男,汉族,湖南邵东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