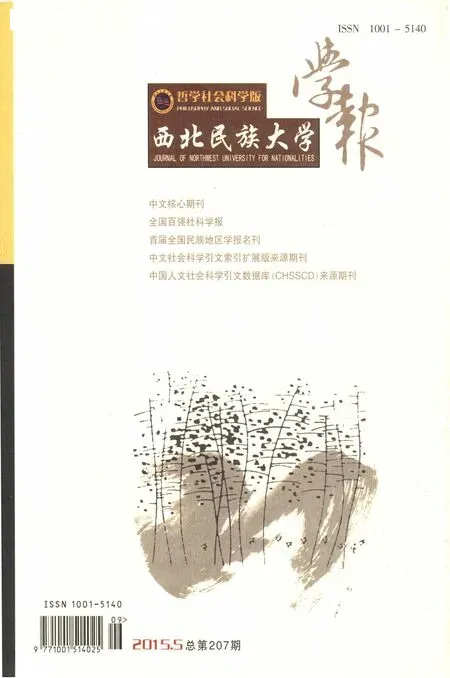在时间信物的引领下——阿来小说《轻雷》的叙述分析
2015-02-20白浩
白 浩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610066)
“这个世界还有另一个维度叫作时间。在大多数语境中,时间就是历史的同义词。历史像一个长焦距的镜头,可以一下子把当前推向遥远。当然,也能把遥远的景物拉到眼前”[1]。时间一向是阿来作品基本主题之一,它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历史的过程,时间是承载深沉历史的载体,也是历史问题解决的方法,正因如此,面对时间的宏观法则,阿来将世事的无常、人的智愚、挣扎与渺小化为面向时间之链的阵阵浩叹,却又能坚定不移地奔向时间的最末端。时间构成阿来叙事野心的一个硕大伞盖,使他可以在企图窥探历史的规律未果时自居为一个时间的记录者,但也使他在即将接近那些历史的尖锐的疼痛和可怕骇人的某些东西时又可以巧妙地滑脱,而这些均在其代表作《尘埃落定》中得以孕育,在《空山》[2]前4卷中继续得以展示。时间与阿来间正犹如罗兰·巴特所说的那个叙事的色情游戏一样[3],在即将抓住与不断滑落间兴致勃勃,他躲在时间的掩体里时不时冒出来放几枪,又躲在时间的掩体里躲避飞过的枪弹。时间,使阿来扮演的是一个史诗的说唱艺人,而非一个战士。然而,时间之链终于走向它的末端,从《尘埃落定》的藏乡近现代史,到《空山》的当代史,《轻雷》是阿来作品中,也是《空山》前4卷以来抵达当下时间最末端的作品,甚至是与当下物理时间同步运行的作品,这对阿来的叙述策略来说是个巨大的风险,因为他终于要跳出时间和历史的掩体,要与真实的现在进行时态作胸膛对胸膛的对话或者搏斗了。这便使《轻雷》格外重要起来,正是《轻雷》的出现,将《空山》这个历史长卷和整个阿来写作史推展到了时间维度的尽头,面对消逝的空间,去寻找时间的信物来记录永恒,而在叙述上,《轻雷》也成为其独立性更强、更具代表性的一个样本。历史如何行进,灵魂如何丢失与寻找,藏乡山水村寨的历史现场正由这些时间信物引领回归。
一
面对时间之链,《轻雷》首先呈现出的是一个下滑叙事,这是一个信物丢失的世界。现实呈现出的是即时性的一个点或面,然而人是有记忆、有未来的,正是这样,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想象将断裂的时间之链接续起来,使它构成一个线性的或立体的叙事,连接这个想象链条的,正是那些正在消失却又或隐或显的时间留下的信物。
这些信物中,首先便是生存于其中的外在自然环境。如果说《尘埃落定》的主题是表现和哀叹一个土司制度的消失过程,那么《空山》则在表现和哀叹一个新的文明形式下,藏区人生存的那个富于诗意和生命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外在环境的消失过程。从这个角度,套用最时兴的话表达,它便是一个生态主题。美丽的森林、繁多的动物、丰硕的粮食,这些供养我们的一切,迅速地消失,是天灾,更是人祸。在《天火》中是政治运动下的狂热引来的天火燃烧掉,在《达瑟与达戈》中是被政治运动的诱惑、文明的诱惑,被情欲和物欲鼓起的屠杀而毁灭掉,在《荒芜》中则是被伐木场砍走,被泥石流卷走。经过重重文明带来的劫难,大森林到《轻雷》时,已经是劫后残余了,“大型的国营伐木场迁走,不是说每一株树都砍光了,只是残剩下的森林‘不再具有大规模化的工业开采价值’”[4]。然而,《轻雷》所做的,便是继续打扫这个满目疮痍的掠夺战场。“那些残剩的森林,对当地政府和机村的老百姓来说,如果只是论钱,还有上亿上十亿的价值。整个地区都为这木材买卖而兴奋,甚至有些疯狂了”。①文中没有标明的引用均来自阿来的作品《轻雷》。“轻雷”这个诗意化的名字到变为“双江口镇”的过程,正是这个打扫战场过程的见证。“轻雷”,这个被遗忘的名字,正是回到时间之链远端的信物——那是“祖祖辈辈进出这个河口的机村人起的”,“过去,因为没有公路,没有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这个世界比现在寂静,几里之外,人的耳朵就能听见河水交汇时隐隐的轰响”。聆听涛声激荡的“轻雷”,意味着聆听自然之声,循自然之法,而“轻雷”的消失,则意味着远离自然之声,毁自然之法。双江口这个从诞生到消失,一共不过20年时间的镇子,正是专为这个打扫残余战场的伐木盗运而生而灭的。“轻雷”是一段时间的信物,双江口则是另一段时间的信物,它们的消失构成一个链条。
与外在自然环境的下降叙事相伴,则是内在人心世界的下降叙事、心灵世界信物的丢失叙事。如同大森林的残余一样,在精神世界,过去那个为神秘宗教法则、自然法则所统领的世界也只留下些残余了。阿来所构建起的那个熟悉的信仰世界,那个世界里的那些熟悉的信物们,寺院、僧侣已荡然无存,佛法、巫术也已祛魅,而轮伐、珍爱敬畏生命的古老乡规民约也已成为历史遗迹。统治这个世俗社会——无神灵世界的“这个法是什么?不是巫师们法术的法,也不是僧侣们佛法的法。而是法律的法”。尚有信仰的人,崔巴噶瓦、驼子支书,都只作为历史的笑话而在苟延残喘、等待死亡,而拉加泽里一家则在懦弱无能中随波逐流。村里那些无信仰的人,更秋六兄弟、铁手、刀子脸,依靠着贪婪、凶残、邪恶而成为文明与富裕的引领者。更为严重的是,与以往的机村叙事不同,《轻雷》的叙事已经转向了双江口镇,如果说机村仍然是一个有信仰与自然遗迹的村庄,那么镇上则纯粹是一个利益、罪恶、阴谋、贪欲的工业时代、现代文明缩影。从机村到镇上的转移,正是这个灵魂下滑叙事的质变。统治这个世界的“法”,如同过去的佛法、巫术一样,时灵时不灵,而人们对待这个“法”,也如同对待过去的神灵们一样,时时糊弄和取巧,而更不堪者,正执掌世界“法”的,由过去的万能的神灵变为了现在的贪婪的人,所以,下滑和崩溃就更加势不可挡。
见证和连接这两个下滑叙事的是拉加泽里,而他本人更是一个下滑的标志。看看他的那些身份吧!辍学者、无能的傻瓜、失恋者、被人“修理”的“胶皮”!再看看,“钢牙”意味着什么,是对罪恶的容忍、纵容,是对纯洁世界被污之谜的保守;“信使”,意味着与罪恶做交易,以此为资本,他获得了入盟和分羹的资格,并进一步变身为“老板”。作为一个纯洁的人,作为一个被寄予家族和村落希望的读书人,他命运挣扎的无效与堕落的迅捷和势不可挡进一步暗示着村落堕落的必然,暗示着希望的断绝。当崔巴噶瓦告诫他“一个男人一生最多可以犯三次错,小子,你一次就同时犯了两个”时,告诫他丢掉了一个好姑娘,一个好前途,而不能再去犯法时,他却只能冷冷地在心里说:“大叔,我也顾不得你那些道理了,我一次就把三个错误犯完了!”他如同于连一样,以人格尊严为代价,与罪恶做交易,拼命跻身于成功人士的“上流社会”,如同浮士德一样,与魔鬼交易,出卖了灵魂。而那次入狱,则更像是一次“冲动的惩罚”,这个惩罚也使他得而复失的成功像一枕黄粱一样虚幻,也更像浮士德的梦幻一样破灭。
自然的下滑、人心的下滑、人的下滑,在时间信物、自然信物、灵魂信物的丢失中,《轻雷》岂止是历史运行的遥远“轻雷”,它失落的焦虑与深沉的忧郁简直如同闷雷,轰击着我们的神经、灵魂。
二
然而,《轻雷》的复杂和富于魅力之处,在于下滑叙事的同时,却又埋下了另一个上升叙事。与丢失的世界相比,这个上升叙事构筑的是一个回归的世界,这是一个寻找回归信物的世界。这个双向的叙事在拉加泽里身上展开,如果说前一个叙事是罪与罚,那么这一个叙事则是救与赎。
拉加泽里作为一个纯洁的人,一个读书的高材生,这些却没有为他带来尊严和生存的环境,于是他来到了双江口镇,在这里,他只是一个补胎匠,一个落魄书生,一只落毛凤凰,然而,双江口也成为他命运的转折之所,成为他的另外一所学校。双江口,是一个罪恶之所、交易之所,但它是真实的社会,它因此成为一个书本中的人,纯洁、稚嫩的孩子变为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成人的技能见习所、养成所。老王对他的胶皮式修理宛如他的一场成人礼仪式,由此为起点开始了他的生命上升过程。李老板这个教父式的人物,成为拉加泽里的人生导师、庇护者,这既是技能的,也是情感的。拉加泽里因此同时在双江口和机村成长起来,他获得了钱,也获得了经验,获得了尊严。而且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好的坏人,在他身上,良性未泯,因此在村里,崔巴噶瓦对他谆谆教诲寄予期望,他成为了一个当了老板而不忘侍弄庄稼的人,因此驼子支书要叫他入党;在镇上,老王、李老板、本佳、刘站长也对他刮目相看,在利益规则之下也真心地帮助他。金钱、尊严的获得与良心的折磨一个上升,一个下滑,两者构成拉加泽里成长的分裂,他是一个成长的人,但他也如同断裂的历史、断裂的时间一样,是一个断裂的人,他在罪与罚间搏斗,也在堕落与复活间徘徊。因此,他并不与更秋兄弟同流合污,他帮助降雨人,他以特殊的砍落叶松方式来感恩李老板,他甚至在崔巴噶瓦圣者式的感召下准备幡然醒悟。这都走向另一个叙事,救与赎的叙事,有了这样的救与赎,那么前一个下降叙事便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如同但丁《神曲》[5]中的炼狱之行,亦如同浮士德[6]的种种堕落只是一种游历,是灵魂的救赎和上升所必备的阶段一样。
这个复活和救赎的上升过程被棒击更秋兄弟事件和落叶松事件戛然中断,然而复活和救赎的真正完成也正是在这两个事件中。与坏的坏人更秋兄弟间的冲突其实是迟早的事,而为维护哥哥这受欺凌者尊严的爆发为拉加泽里彻底赢得了人性与血性的尊严,因此警察老王有言:“好小子,你犯法了,但干得好。”而勇于承担落叶松事件的责任,则更像是拉加泽里要自己把自己送入监狱,他需要对自己的罪恶,也需要为双江口的罪恶做一个交待,也需要一个了结。完成这两件事后,监狱生活对于拉加泽里的灵魂净化和道德升华来说,那不异于是由炼狱之行登入到天堂中去了。他失去的所有那些最圣洁的东西,如同那些圣洁事物的标志——前女友阿嘎一样,失而复得,重焕光芒,阿嘎之于拉加泽里的灵魂,正如同引导但丁天堂之行的贝·阿特丽采一样。在小说的结尾,拉加泽里出狱后,他所看到的那些消失的镇子、消失的人物,都在对他笑笑地说“对,小子,你回来了”,正是赎罪后灵魂的典型归来、上升。
拉加泽里的出狱尽管只有短短几段,但在这里,展示出阿来对上升叙事的期望。拉加泽里,曾经的盗伐者在狱中完成了曾经不可能完成的学业,拿到两个本科学位,其中一个是关于森林环保的,他即将成为一个森林的重新播种者。如果说拉加泽里的得救如同《百年孤独》中坐着床单飞上天的俏姑娘雷梅苔丝一样神奇[7],那么盗伐森林的标志——双江口镇亦如同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整个儿从地球上刮走的马孔多镇一样神奇消失,同是时间的魔法,不同的是,这个镇子的消失却是福音,而机村之根、灵魂之根、生态之根,则得以存活和回归。“你看现在到处都是林子,退耕还林,机村以前开的地,好多都又种上树了”。被破坏的森林即将回来了,轮伐的自然法传统回来了,生态环境、人心、道德都回来了!人、人心、自然环境丢失了,他们又都回来了,这构成了《轻雷》整个下滑-上升的复合叙事。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陷阱,那便是上升叙事是否是廉价的乐观呢,是否会抵消前面下滑叙事中的尖锐锋芒呢?在这里,阿来解决这个麻烦的办法,是重新引入时间这个法宝——12年后,一个未来时态。从叙事上来说,阿来是预支了时间,然而这里是逻辑的结果,也是作家善良愿望所在,同时也是现实的希望之所在。只有有了未来,有了希望,那么过去的、现在的堕落才是有意义的,也才是我们所能够承认和接受的。当然,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未来时态本就是虚妄的,只有现世解决不了的问题人们才会把它投放到来世中去,投放到未来时态中去,时间的距离——未来,空间的距离——监狱既是巧妙回避,但也同时证明其虚幻化,乃至虚妄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阿来的预支时间也便并非乐观,并非消解锋芒,而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对现实的否定、批判、悲观。值得注意的是,与扎西达娃小说所表现出的藏人们佛教的环形循环时间观不同,阿来一直是一个线性时间论者,那些时间线性发展中一旦失去的事物便不可逆转、不可收回,相较之下,《轻雷》中的回归愿望,对他来说,尤其展示出沉痛的批判。
三
那么,一个下滑叙事,一个上升叙事,看似巧妙的深度结合,其实两者在叙事力度和真实性的砝码上并不均衡。一个是板上钉钉的无可阻挡的沉痛现实,一个是善良的虚幻的愿望,一个是锐利的刺刀,一个是使人能承受这锋芒的预支的“和谐”,两者间有内在的危机和混乱。阿来一定为这种混乱而头痛不已,所以,他必须采用另一些方法来搅混清晰的逻辑线,来缓解这种头疼。
一个办法是,将不同语汇系统地混用与互动。在阿来作品这里,一直存在着两套语汇系统:外面的-本土的,本土语汇系统代表着藏区的古老生活方式,如宗教、僧侣、猎人、森林、动物等,而相对应的外面的语汇系统则代表着汉人的新的生活方式的介入,如政治运动、现代文明、工业(伐木工人)等。不同的语汇系统代表着不同的表述方式、命名方式,也代表着迥然有异的生活的存在方式。这两套语汇系统在阿来的藏民世界中不断混杂,彼此间发生着各种复杂的关系,主动-被动,渗透-融入,强力-服从,强力-抗拒,拒绝-消亡,等等,这种分子运动式动态变化也正寄寓着藏人们对自我民族身份的困惑与寻找这样的重大意义。这套方法在以往的阿来叙事中行之有效,宛如所经过的漫长调情过程一样,两个文化主体间的互动既生动活泼,又意蕴绵长。然而在《轻雷》中,尽管也仍然沿用着两套语汇系统的共存与对立痕迹,但事实上却已陷入了失衡之中,图穷匕现,外来的语汇系统已经几乎完全压倒了本土系统。比如尽管仍然存在机村人把一些外界文明事物的新发明归类为“太聪明”的东西,又害怕“太聪明”的东西多了,神灵会被忘记,神灵会生气,因而降下灾难,但这样做的人只是一些“顽固的老人”了。大部分人,尤其年轻一代已经对外来事物安之若素,并已融为一体了,双江口镇这个外来语汇系统的统领地已对机村这个原始村落构成了压倒性优势,并已实现了话语中心的转移,而卖木材、买汽车、赚钱、办厂等也已成为机村内部的话语主流。机村人不再对此话语系统排斥和格格不入,相反倒开始为之辩护起来,因此便出现了新的悖论,一方面这是一个“疯了”的世界,“我已经把自己毁掉了”,另一方面拉加泽里又辩护“这个世道是什么世道,大家都挣得到钱难道不是好的世道”。这样的一边倒情形使过去那种两套系统间有趣地并存和纠缠的温馨局面破裂了,从而走向彻底的焦虑之中。
与上述外来—本土系统混合相类似和联系的另一个办法是,将官方与民间身份的混合。先看看那些公家人的身份吧。老王,他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面孔,在官方规则下,他是一个暴力性的警察,因此他魔鬼般痛殴拉加泽里和其他人,“如同修理胶皮那样”。然而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和善的老头,一个被哮喘折磨的老头,一个富有人性的人,一个好人。在老王这里,典型地是职业-人性分离的人,他是一个坏的好人么?对此,拉加泽里吃惊而又迷茫,熟悉而又陌生,而老王则以“对不起了,这是我的工作”,“恨我?不要恨我。我就不恨你,我只是在工作。破案。……我在破这个案”来开导受刑人,也是以职业道德来开导自己的人性。只是有时候,他也会迷失于自己的这套逻辑,比如面对拉加泽里的追问:“我已经是坏人了。”“你是好人。”“好人会被警察打?”老王对此也困惑,只能以骂道“妈的”来作答。老王应该如同一切执法者一样自认为是好人的,但这个判断有时也会因自己的职业行为而迷茫。对于老王的逻辑深表理解的是木材检查站的人,如刘站长、本佳,一方面他们是执法人员,另一方面是吃黑钱的人,一方面是贪婪的人,一方面又是充满人性的、仗义的人。官方的人是相互理解的,本佳因此开导拉加泽里,老王打他那么狠,因为“那是工作!小子,工作,你懂吗?他打你就是工作,跟你锉那些胶皮差不多”。民间认识的清醒而又含混的逻辑将官方清晰而又尴尬的逻辑巧妙地消解和搪塞过去。而李老板,同样是这两套逻辑了然于心,从而游刃有余地存活于两套逻辑的夹缝之间。
小说另一个含混的逻辑便是好人与坏人价值判断的复合与含混。如同警察老王、木材检查站的人困惑于自己是坏的好人,还是什么一样,同样令他们困惑的问题便是他们手下的那些受刑者、受惠者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比如拉加泽里。在拉加泽里第二次受刑时,一方面老王“老子看你打了坏人想帮你一把”,另一方面又为那小子的钢牙行为而恼怒,阅人无数的老王也最终承认“小子,你把我弄糊涂了,你说自己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吧”。拉加泽里是一个好的坏人,还是一个坏的好人,无法理清。李老板,是一个好的坏人,还是一个坏的好人,同样无法理清。再加上坏的坏人更秋兄弟——然而他们构成了新的生存规则,好的好人崔巴噶瓦——然而他历史地走向没落。好人与坏人的传统与简单价值判断清理只是将线团弄得更加混乱和复杂。
既然外来与本土、官方与民间、职业与人性、好人与坏人、堕落与救赎、下滑与上升的所有逻辑均搅作一团,复合含混,那么,究竟谁应该对森林的消失负责呢?那个老是搞秘密勾当的镇子,那些官方人,木材检查站,它的使命究竟是什么?是阻止盗伐,还是催生和见证盗伐的?机村人,过去那些反感伐木场大面积采伐森林的当地村民如今都成为技术娴熟的伐木人了,在生存与利益之间,他们无法选择,也无法加以拒绝,如拉加泽里所想:“拉加泽里并不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就把路走偏了。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并没有很多道路可以随意地选择,他只是看到一个可以迈出步子的地方就迈出了步子,可以迈出两步就迈出两步,应该迈出三步就迈出三步。他无从看到更远的地方,无法望远的人,自然也就无从判别方向。”山民无辜么?那么要承担责任的是遥不可及的山外文明世界么?“你们不能又要木头,又要水,还要因为没有水怪罪我们砍了木头!”当逻辑含混思绪繁复,面对过程,大家都有理,面对结局,大家都无理,然而又追寻一个简单的承担责任的人都困难时,那么问题的解决便更加茫然。
面对这一场灾难,阿来以预支时间的方式来作结,来给出答案。然而这个答案是虚幻的,因为面对这一切混乱复杂的现象,阿来亦无能为力去理得清楚。所以,他又沿用了一个老招式来缓解头痛,那便是历史现实主义式地记录下来,以一个“记录者”的理性来缓解一个“思想者”的思考,以一个说唱艺人的吟唱来缓解一个战士的炽热和疯狂。正如在“轻雷”到“双江口”的地名变迁间,地名办公室的人“我们只是记录,而不是改变”的自陈一样,作家自我宽慰于在时代名的变迁间一样“只是记录,而不是改变”。当然,这个记录者充满情感的沉郁、思绪的复杂,并最终寄望于时间的改变。时间的信物继续牵引着阿来行走于历史、现实之间,构筑起一个村落史、文化史、人心史。时间信物、历史信物丢失,那便是一个无根的世界、外来的世界、异化的世界,而信物的寻找,则是这个记录者和思想者的使命。
[1]阿来.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J].扬子江评论,2009,(2).
[2]阿来.空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57.
[4]阿来.轻雷[J].收获,2007,(5):156.
[5](意)但丁.神曲[M].王维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6](德)歌德.浮士德[M].钱春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7](哥伦比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黄锦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