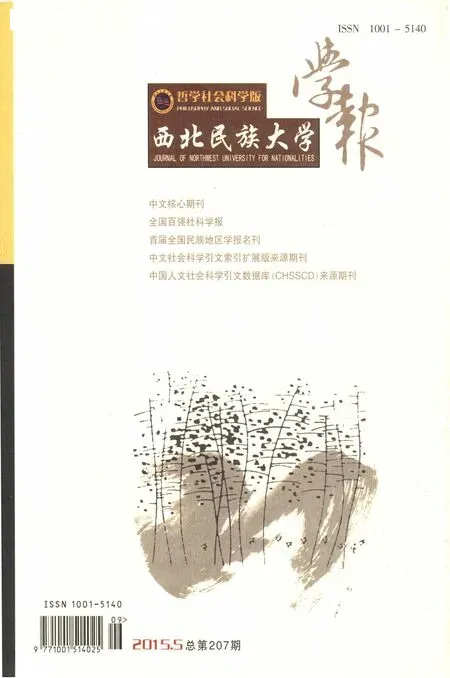作为资源、职业和信仰的佛经抄写——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汉文写经的模式与社会文化动因
2015-02-20周珩帮
周珩帮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211189)
吐蕃统治时期(786年-848年)①敦煌陷蕃的时间,本文用贞元二年说。的汉、藏文写经,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由于藏文文献的丰富和独特,因此,皇室和寺院主持的写经一直是研究重点。近期的几项研究,则丰富了我们对信众写经工作的认识。②主要参见:陈楠.吐蕃统辖敦煌时期之藏文抄经活动考述[J].中国藏学,2013,(S2):32-38;赵青山.俗众佛教信仰的法则——以敦煌写经为考察中心[J].唐史论丛,2010,(1):281-294;赵青山.佛教与敦煌信众死亡观的嬗变——以隋唐宋初写经题记为中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63-69;赵青山.隋唐宋初写经设邑考略——以敦煌写经题记为中心[J].敦煌研究,2014,(1):87-93。将之综合起来,该时期敦煌佛经的抄写,便是一个吐蕃皇室、寺院经坊、职业经生和普通信众共同参与的事业。六十余年间,敦煌内部既有经济流通、语言、佛教界的显著变化,又有未发生变化的一面。[1]而从地方文化连续性上看,汉地佛教仍然通过敦煌向吐蕃本部传播,吐蕃官方与唐朝中央政权保持着联系,唐代文化礼俗一定程度上被吐蕃官方和民间保留与吸收,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亦对唐朝中央政权保持强烈的向心力。[2]这也意味着,尽管社会文化情境有所改变,但自魏晋以来,地方佛教组织通过中央朝廷赠送、寺院抄录、经生和信众抄写,而获得佛经抄本的模式,依然保持着相对的连续。
基于宗教信仰,几种群体佛经抄写的社会动力,是“功德”修持。而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政治和宗教的结合趋于紧密,寺院在宗教和文化教育方面处于垄断地位,佛经和寺学中古代典籍的抄写较为兴盛,同时,普通信众的宗教仪式和需求形式繁多,又有大量经生在题记中以职业群体出现。因此,从地方社会文化结构来看,佛经抄写又往往溢出宗教动因,各自又有获取政治、文化和经济资源或利益的意图。
一、皇室施写佛经与政教权力的守持
吐蕃皇室在敦煌主持一定规模的写经,集中在赤祖德赞主政期间(815年-838年),约始于822年(据P.3966号尾题)。依赞普之命抄写的主要经卷,是藏、汉文《大般若经》和《无量寿宗要经》,经生数量达到千人,内有大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经生,吐蕃经生占总数的20%左右。这种写经模式集中有效,因此,西冈祖秀说,现今收藏在中外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无量寿宗要经》等经卷,“都得到了赤祖德赞王的赞助……当时的写经事业,是按照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地区的统治者戴伦(bDe blon)和沙州佛教团管长下发的通达牌的指示,由沙州的两个僧团和俗人2 700人进行的大规模的活动”。[3]但我们认为,尽管皇室组织的写经规模庞大,抄录的经卷数量可观,但由于持续时间不长,不可能满足敦煌各寺院此前和稍后的经本需求,因此,只能是短时期集中性的抄写。
吐蕃皇室组织写经,一方面是佛教推广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是借助佛教强化政治权力的行为。赤祖德赞是佛教传入吐蕃后的第二位国王,他曾立《兴佛盟誓碑》,明确了佛教在国家统治及王室成员、属臣中的地位:“……所供养之资具,均不得减少,不得匮乏。自今而后每代子孙均需按照赞普父子所做这盟誓发愿。其咒誓书词,不得弃置,不得变更。祈请一切诸天、神祗、非人,同类作证。赞普父子与小邦王子,诸论臣工,与盟早誓。”[4]攻陷敦煌以后,这项举措从两个方面在敦煌得到推进:一是采用“部落”划分等方式对之实施政教管理,在行政方式中体现出浓烈的宗教色彩;二是借助皇室成员祈愿、抄经及大规模的施法大会巩固和提升威望。
在大规模抄经以前,皇室成员祈愿已较为频繁,P.2255、P.2326号《祈福发愿文》,S.2146《行城文》,P.3256号《愿文》,P.2770V0《释门文范》,P.2807《斋文》等就是798-815年之间吐蕃皇室祈愿留下的文献,发愿者有赞普、国夫人、皇太子、十郎、十一郎、太子夫人、公主、诸娘子等皇室成员,有节儿部落使、都督公、部落使判官、瓜沙两州都蕃僧统等属臣,及灵图寺、乾元寺、报恩寺的教授。[5]这种发愿,可以看做吐蕃王朝及其敦煌地方管理者的集体行为,而不仅是个人功德。
大规模写经开始后,不仅写经生的召集、部分纸张和费用的筹措由部落百姓分担(可见于TLTD.2-14、S.5824、S.8698等),[6]而且管理上带有强制色彩。一段藏文题记记载,“在写经任务未完成期间,要没收(写经生的)家畜、财务两倍的价值交给(经典)收集官,监督者若不能压制(写经生的)反抗或未及时收集经卷,(里正)们也要受一卷纸笞10下的杖罚。(里正)们还要想着有机会到捐施者之地去,要好好地考虑捐施者贡献纸张的多少”。[7]可见,西冈祖秀说吐蕃皇室是写经的“赞助人”,①赞助人(patron或patronage),是西方艺术史学者在研究艺术生产(art produced)时使用的概念,主要针对西方中世纪至19世纪下半期的艺术,“赞助人”的基本意义是保护者(protector)、倡导者(advocate)和守护者(defender)。见Jonathan Harris:ART HISTORY:The Key Concept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Taylor &Francis Group,2006.228.并不准确。但也正是这种手段,才使得吐蕃王朝有效介入佛教兴盛的敦煌当地:一是,写经是皇室自身的功德,也体现皇室的虔诚、爱民与团结;二是,所写经卷分赐寺院,可以保持与寺院的联系,强化对寺院的管理;三是,借助汉藏文写经,吐蕃文化渗入敦煌当地,很多当地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并使用藏文,由此确立吐蕃文化导向;四是,借助强制手段,将一部分当地乡绅和文人纳入麾下,为己所用,“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8]五是,经由佛经抄写,吐蕃官员才能获得寺院和民众的认同,获取信任和支持。
同样,借助佛教施法大会,皇室也强化着对沙州寺院和百姓的统辖。写于844年的P.T.999号藏文写卷有一段题记:
先前,为天子墀祖德赞之功德,在沙州缮写汉、藏文《无量寿经》,百姓及各方大施主亦普遍行此善事,所写佛经由龙兴寺经库管理。计汉文《无量寿经》135卷,藏文480卷,总共615卷。鼠年季夏(六月)八日,沙州二部僧伽,为赞磨王妃潘母子宫殿微松之功德,也为沙州地方百姓之功德举行回向供施法会。从宫庭指令及信函、教法大臣及安抚大臣之信函中得知,在2 700人法会之时,教法大布施所奉献之财物,交与长老僧人洪辩和旺乔登记,并由管经僧人云海和李丹贡核对经卷记录和正式凭据付账。以后结算经卷总账之时,以此登记账目和总账本(底数)相核对,如吻合则登记偿付,并发给盖有印章之凭据。[9]
这段文字回顾了之前615卷的写经成果,表明六月八日规模宏大的施法会的目的,是为了赞磨王妃和沙州地方百姓的功德,进而明确了法会所得财物和经书的管理、稽核办法。显然,缮写经本,是祈愿、法会的物质和精神载体,也是吐蕃皇室维护政教权力、管辖沙州百姓和寺院的支点。尽管以功德自持,但抄经的举措,亦暗中促成了吐蕃王室权力资源的获取。
二、各寺佛经的藏写转请与社会地位的体认
佛教教义宣扬、佛学研究必须以佛经为载体,印刷术广泛使用之前,佛经主要依赖寺院内写经僧的抄写和流传。①写于8世纪的BD03907有“弟子王发愿雕印”的题记,表明佛经的印刷起源较早,但8世纪尚不普及。见: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五十三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23.吐蕃统治时期,各寺院藏经不外乎4大来源:一是,吐蕃统治前中央分赐、寺院抄写、经生和信众缮写的经卷积累;二是,吐蕃皇室组织抄经后交付管存的部分;三是,各寺院组织写经僧、聘请写经生不间断地缮写;四是,信众和僧人零散的抄写和供奉。我们知道,这一时期敦煌僧尼寺院新增5座,僧尼数目从之前的310人增至千人左右。[10]无论寺院规模和社会地位如何,佛寺和僧尼增加,讲经、法事活动所用佛经的需求量也会增大。反过来,寺院拥有的僧尼数和藏经量、被官方关注程度、举办佛事活动的规模和效应,又是决定其社会声誉的几个关键因素。
前引P.T.999号中,吐蕃皇室所写615卷佛经,交付龙兴寺管理,表明龙兴寺是这一时期敦煌当地规模和声誉较好的寺院。从BD02295(7-8世纪,龙兴寺寺僧慈定受持)、BD01106(759年,龙兴寺静深写)等零星题记来看,吐蕃入主之前,龙兴寺的写经僧便缮写不辍,故藏经应有相当规模。即便之后有吐蕃皇室的赠送,龙兴寺经坊仍然组织写经,以丰富藏经资源。BD09340为吐蕃时期龙兴寺向“阴法律使者一真”借出共20帙《大般若经》的记录,其中有新写1帙3卷,表明有更新,但也空缺1帙,合缺11卷。BD11874的三个文献,为龙兴寺转《大般若经》付经录,《大般若经》点勘录,及某寺佛典点勘录。②所引文书分见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三十二册、十六册、一百五册、一百十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2009.分册条记目录之12,12,58,36.晚至归义军时期,龙兴寺外借经卷仍未中断:
□…□请龙兴寺藏本:佛华严经,三袟,新写本。三袟内一/□…□卷,并分付法镜勒手拈。法镜。第六袟内欠两卷,法镜。/□…□般若藏本,第六十袟。(BD10785号)[11]
除龙兴寺等少数寺院可获取官方资源,其他各寺院的藏经必须依靠经坊或雇请书手抄写。如BD02574是灵修寺雇张涓所写,BD02745、BD01920是金光明寺请吕日兴和张涓(子)所写,BD02840为永安寺聘张良友所写,BD14983是圣光寺尼真定所写,BD03355号5题“大蕃国沙州永康寺律师神希记”,BD05515为比丘日定于大云寺抄写等。③所引文书分见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三十五、三十七、二十六、三十八、一百三十六、四十六、七十四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2010.分册条记目录之17,12,16,12,14-15,5,10-11.各寺所写的经卷有严格的校勘、清点、库管、转借、报废制度,并有标识所有权的题签或藏经印。如P.3188为“乾元寺前经司藏经数目”:
乾元寺前经司大慈手上藏内经,现分付后经/司广信,谨具数目:/大般若经,六十袟,一部,足。/大般涅槃经,四十二卷,一部,足。/正法念处经,七袟,一部,足。/楞伽经,十卷,共一袟。/法华经,两袟。/大乘无量寿经,十卷,共一袟。/大宝积经,一袟。/大佛名经,一袟。/金刚般若,十卷,共一袟。/都计七十八袟。[12]
寺院佛经的抄写,主要依靠两支力量:写经僧和雇佣经生。然而,文献所见的写经僧不多。所幸,金光明寺经坊的一些信息,可见于S.2711、S.7945、P.3205、S.6028。[13]其中S.2711(G.7842)如下:
金光明寺写经人戒然、弘恩、荣照、张悟真、法贞、贤贤、寺加、金塩、道政、法缘、俗人阴暠、郭英秀、索庭照、索琎、索滔、王英、张善、张润子离名、董法建、义真、惠照、辩空、法持、道岸、道秀、超岸、昙惠、利俗、净真、李峨、张宽、李清清、卢琰、陈璀、∟张润子、张崟、宝器、张重润、翟丘、张献、高子丰、立安、宗广、王进昌、孔爽、薛谦、李颛、张英环、安国照、∟张善、范椿、索奉禄
第一组的18人中,前10人为写经僧,“俗人阴暠”及其下8人为俗众经生;第二组的35人,前12人应为写经僧,其余23人为俗众经生。除却重复的2人,写经僧22人,俗众经生29人。S.7945中不重合的是海、济、惠、崇恩4个僧人组长,另有安国兴、翟今、张贲、张重恩、髙丰、王昌、萨谦、索禄、翟立、张还、左安、李岷12个俗众经生;S.6028的校勘者中,不重合的有惠炬、洪言、慈心、道正、宝良器、像幽、义泉、像海8位僧人,有王文宗、索海、李涓3位俗众经生。这样,负责校写的僧人共34名,俗众经生共44名。姓名重合的校写者则有超岸、贤贤、离名、崇恩、王昌等。但限于片断材料,一些前辈曾疑虑:金光明寺写经人是第一组所列,还是包括第二组?第二组是否为另一个写经机构?[14]当时寺院的写经工作,是否只在金光明寺开展?[15]据年代相同的P.3138可以发现一些重合的人名:①因图版不清,背面录文略去经名和数目。图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7[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5。李正宇先生据正面“禅定寺”确定该文书在蕃占中期。见李正宇.敦煌古代祠庙寺观简志[J].敦煌学辑刊,1988,(1、2):80.
(正面)
龙兴那维汜寺主请第□□□
第六十 第卅九 五十五 五十一 大云维那曇□□□
廿四 第卅三 第卅 第卅四
报恩维那承恩请第卅三 第十八
开元维那谁(?)暄请第卌八 第卌
安国维那请卌九 卌二 卅七 十九 五十八
灵图维那法诠请第廿七 第十三 第六 第五十
莲台维那道凝请第卅五 第三 第十二 第五十(七?)
乾元维那惠(?)光请第廿 第廿九教授放
永安维那请卅六金光请卌一 廿八
兴善维那道通请第七 第九 第十一
灵修维那妙智请第十四 第十五 第卅八 第廿五 第十七
第卌六 第卅二 第卅五 五十三 廿 禅定维那明谦请卅三 第廿八又付定十六 廿七
大乘维那真元请第一 第二 第四 第十
普光维那第卅 第卌四 第廿一 第廿二
(背面)
大云寺:法常、戒荣、道正
报恩寺:酬恩、怀恩、玄法、惠诚、崇恩、怀
灵图寺:法诠、金鼓、法幽、金塩(?)、荣照
莲台寺:志照(坚)、道凝
开元寺:切遇、来、文照、曇秀、□昂、利相
乾元寺:法(?)睿、净真、戒盈、利珍
前见的“道正”出现于大云寺(还见于BD11493“云”寺),“崇恩”出现于报恩寺;活动于蕃占中后期的“荣照”(另见于P.3301V、P.2837V、D162V)出现于灵图寺,“净真”出现于乾元寺,“明谦”还见于P.3336。这表明,以上金光明寺34名经僧中,有其他寺院的经僧,或是根据抄经需要而临时组合。抄写和校勘是写经僧的工作,寺院提供纸墨、原稿,保障日常所需,不存在为其支付报酬的问题;同时,写经是牵涉译经僧、讲经僧、写经僧、藏经僧等众多寺院成员的工作,除表明抄写、校勘责任人而有意注明外,不需要特意署名,故而,未留名的写经僧很多。
以经卷典藏为资源,各寺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往往通过转请自我补充,或共同校勘力求完备。而各种付经录和写经名单,应该是一些集中用经、抄写、整理,寺院间互通有无、彼此补益时留下的文本。前引P.3138正面即是蕃占中期14座寺院的一次请经录,另如BD11493为敦煌佛教界某次勘校经、付经的记录:
亥年四月廿九日勘教经
南寺:《大宝积经》,五袟。
光辩边:《花严经》,八袟,并袟。/
惠达边:《立世阿毗昙》,一卷。贞闍梨边:《佛本行集》,一袟。
如闍梨边:《佛本行》,一袟。/
龙:卅一、卅三、卅八,付惠真。
恩:卌四、廿七、卌九,付崇福。
开:卌、卌一,付法进。/
金:卅四、卅九、卅六,付惠能。
图:五十一,付惠云。
云:卅三、卅,付道正。五十三,付惠。
莲:五十四、五十六,付法清。/
乾:五十七,卌六,付英达。
永安:卅七、卅五欠一,付法清。(后空一行)
修:廿、十七、五十、廿一、廿九、廿六、卌三,付坚真。
普:廿四欠一、五十五、廿八、五十九、廿五欠一,付宝净。/
乘:廿二、廿三、十九欠一、卅五、一十八欠三、卌二、卌五,付坚法。/
五月二日。付孔:卌一、卌二、卌七、卌六、卌五、五十六、五十八、五十七、卌九、五十一。[16]
记录中不见9世纪初新建的安国、圣光、兴善等寺,其年代应在8世纪末。参与这次校勘活动的,除13个寺院外,还有光辩边、惠达边、贞阇梨边、如阇梨边,如果校勘活动是四月廿九日一天内完成,那么参与者必有很多。另如,S.2712号时间不超过800-810年,是大乘、永安、莲台、灵修、报恩、安国、龙兴、金光明、永安、大云、兴善共10个寺院的付经录①其他付经录的研究,见马德.敦煌文书《诸寺付经历》刍议[J].敦煌学辑刊,1999,(1):36-48.,其中,安国、龙兴、金光明三个寺院所付卷帙最多;S.307lv残存大乘、普光、灵修三座尼寺的付经历,且附有写经生的人数:大乘寺6人,普光寺8人,灵修寺12人。[17]
写经需要一定的经费,同时会有新的收入,“是维持敦煌地区十多座大寺院以及数百座洞窟的有力财源”。[18]寺院经坊是否也有相应的经济利益,目前还不得而知。尽管各寺有相应的经司负责典藏,由知藏负责管理,但只有龙兴寺、灵图寺、报恩寺和蕃占晚期的净土寺、三界寺收藏有大藏经。[19]而这些寺院不仅在吐蕃时期文献中大量出现,其发展也与官方和当地豪门的支持有关。[20]可以说,佛经的藏、写、转、请,是寺院佛教资源的一种体现,也是诸寺在宗教界、官方和民间获取声誉,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
三、介于寺众需求与个人生计间的职业写经
吐蕃统治时期汉文写经中频繁出现的署名经生多达几十位,这些署名经生,少部分出现于皇室或寺院经坊写经名录中,如田广谈曾为龙兴寺(BD02200)、永安寺(BD02323)等寺院写经;更多的情况是独立或合作抄写当时盛行的《无量寿宗要经》《大般若经》,是一个较为稳定的职业群体。
以抄经为生的前提,一是皇室和经坊书手匮乏而大量雇请,前文已述;二是不间断的经卷典藏和更新需求,其中僧尼诵读及兴盛的法事活动造成的经卷损耗是主要因素,如BD06359号背3“灵树寺众僧慈灯等”于公元815年为节儿纥结乞梨所作的福田转经:
转《金光明经》一部十卷一遍,《金刚经》七遍,《观音经》十遍,《般若心经》一百八遍,《无量寿咒》一百八遍,《维摩经》一遍,印沙佛两千;为节儿娘福田,转《金刚经》七遍,《观音经》十遍,《般若心经》一百八遍,《无量寿咒》一百八遍,印沙佛一千。[21]
信众所需的宗教仪式名目很多。宋代司马光(1019年-1086年)曾批判性地写道:“世俗信浮屠诳诱,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朞、除丧,饭僧设道塲,或作水陆大,写经、造像、修建塔庙,云为死者灭弥天罪恶,必升天堂,受种种快乐;不为者必入地狱,剉烧舂磨,受无边波吒斫之苦。”[22]灵树寺在文献中所见不多,应为小寺。与之相关的BD06359号背2是开元、图、永(安)、金、龙等寺院行事名录,共计41人,另有当地民众53人,[23]表明重大宗教活动不限于一寺主持。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和不断深入的宗教信仰,促成佛经抄写的需求,为经生的职业化生存提供了保障。
自魏晋起,敦煌的职业经生绝大多数就来自当地,其中,张、索、汜、阴、令狐等,都是常见的敦煌姓氏,该时期亦然。一部分通过寺学或家学完成蒙学教育的“学童”或“学郎”,后来便以写经为业。但由于大量使用硬笔书写,且因敦煌与中原文化一定程度的阻断,经生的代际传承也受到一些影响,而逐渐形成了地方传统,前辈经生书写的本子,无论文字还是书写样式,都成为后继者学习的对象,但也因此出现书写水准的下降与视觉形态的类型化:行笔加快,趋于行楷;夸张提按顿挫,转折和捺笔做程式化重按,较之初唐和中唐,尖峰入笔增多;单字结体变初、中唐的端平方正为左低右高态势;字距缩小,字与字空间局促,行齐列散,单行总字数有2-5字之差,整体章法显密。当然,这些特征的形成,还有最关键的因素,即追求佛经抄写的速度。
从上引S.2711等材料看,皇室和寺院经坊中都有大量俗众经生,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是临时从事抄写,一部分则应是专职于写经机构,收入相对保障,因此留名情况不多。相应地,常见的署名经生,可能是更为职业化的群体,既等皇室、寺院和信众的雇佣,也要自主抄经,待市而沽。因此,他们的题记,是为了写清供养人和供养目的;他们的签名,是为了计算酬劳,也可能是做职业宣传。汉文写经生中“王瀚”的资料较多,以他为例:
A.奉为西州僧昔道萼写记,经生王瀚。(BD00018尾题)
B.已前六卷,纸卅张。王瀚写。眼闇书,不得不放,知之。(BD00099第8纸尾题)
C.佛弟子僧裴法达、樊法林、曹寺主灯奉为十方一切众生,愿见闻觉知,写记。经生王瀚。(BD00244尾题)
D.王瀚经,十卷,共五十一纸。(BD01887尾题)
E.王瀚写,第一校,第二校,第三校;/尽十八纸。(BD02970尾题)
F.社经,王瀚写。(BD05467尾题)
G.王瀚勘了(BD05509《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第16纸尾题)。
H.清信佛弟子屈荣子奉为合家愿保平安敬写。王瀚。(BD15102尾题)①所引文书分见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二、四、二十六、四十、七十三、七十四、一三九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1.分册条记目录之7,10,13-14,8,6-7,15,9,4.
以上A、C、H、F四条材料分别出现僧侣、社邑、信众三类供养者,含有为众生、社区和家庭祈愿三类目的;B、D、E三条材料则注明经生姓名和写经所用的纸张数目;E、G两条兼及校勘工作量;材料B显示了王瀚因常年写经而视力不佳的窘境。综合下文僧道格所说的写经惩罚制度,可以推测,通常情况下,一卷佛经(卷轴装)需要5张纸,受写经惩罚的僧人,一天的任务大约就是一卷经的抄写量,对常年写经的王瀚来说,BD00099(现首残尾全,留8纸)也要花掉他大约6天时间,而且是对同一部《无量寿宗要经》的连续抄写。《无量寿宗要经》曾得到皇室的倡导,篇幅不大,但需求量不小,对职业经生来说,既可独立、连续抄写,以供不时之需,也便于彼此间的短期合作,灵活可行,大概最受经生欢迎。王瀚还抄写过很多大部头的经卷,必有与其他经生的合作。当经生群体协作时,就需要签名以计算酬劳。
经生酬劳的方式,S.5824显示为“得菜”,以“驮”和“束”计量,每人每日所得32或33束,每年4驮稍多,由各部落提供。[24]藤枝晃先生还认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铜钱完全消失,不再流通,代之以粟、麦等等价物的交换,[25]若真如此,依靠这些酬劳,写经生不仅要面临再次交换,似乎也很难养家糊口。此外,该时期汉文BD01199号2,有《五言诗一首?增上》:“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迴面不相看”,[26]这首诗很可能是流传的行业用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职业经生受制于雇主和市场,而无力周转的谋生状况。
四、僧尼信众的施受信仰与零散写经
较之以上三种模式,僧尼和信众的写经相对零散,但也是重要的抄本来源。由于存在集体性的家族和社邑、个体性的僧尼和信众两类主体,有自己抄写、雇人抄写、购买供奉三种途径,这个模式的情况便显得较为复杂。家族和社邑做施受主体,难免有小集体社会文化地位的展示与塑造意图,但最根本的动因,是宗教信仰。
写经施受以除灾祈福的信仰深入人心,来自三种力量的促动:一是,执事机构和僧尼的宣扬,如稍晚于该时期的BD08959尾题说:“书写文书,有一人听受、持念者,得无量福生,不堕三地狱”;[27]二是,佛经本身对写经功德的许愿,如该时期被广为抄录的《大乘无量寿经》第一段就表明:“若有众生得闻名号,若自书,或使人书能为经卷受持读诵于舍宅所住之处,以种种花鬘缨珞涂香末香而为供养,如其命尽复得延年,满足百岁”,[28]之后又在第四部分详述供持佛经的六种功德;三是,知识分子对抄诵佛经“奇迹”的传述。唐代赵璘《因话录》记载,韩弘同僚王某因事被上级刘逸淮杖罚三十,在新造杖具下本该活不过五六杖,王某最终却安然无恙,对此,王某解释说:
“我读《金刚经》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记初被坐时,见巨手如簸箕,吸然遮背。”因袒示韩,都无挞痕。韩旧不好释氏,由此始与僧往来。日自写十纸。及贵,计数百轴矣。后在中书,盛署时,有谏官因事谒见,韩方洽汗写经。谏官怪问之,韩乃具道王某事。[29]
种种写经功德,使不专职写经的僧人,也时常参与佛经的抄写,如:
A.唐贞元三年(787年)十月廿日新造报恩寺僧离烦写毕记,十一月□…□。(BD14622尾题)
B.为亡比丘尼常悟写《法华经》一部,写《金光明经》一部,《金刚金》一卷。已上写经功德,迥施亡比丘尼。承此功德,愿生西方。见诸佛,闻正法,悟无生。又愿现在合家平安,无诸灾鄣。未离苦者,愿令离苦;未得乐者,愿令得乐;未发菩提心者,愿早发心;未成佛者,愿早成佛。巳年六月廿三日写讫。(BD05742号2尾题)
C.施主清信佛弟子诸三窟教主兼五尼寺判官法宗、福集二僧同发胜心,写此阿弥陀经一百卷,施入十寺大众,故三业清净,罪灭福生,莫逢灾难之事。比来生之时,共释迦牟尼佛同其一绘(会)。(BD06035号尾题,本卷年代稍晚)
D.为师僧父母国戒安。(BD01036号3尾题)
E.比丘尼莲华心为染患得痊,发愿写。(BD01952题记)
F.乙丑年(845年)五月一日比丘惠超就于军将寺夏居之,此写竟记之耳。(BD14728尾题)
G.丙午年七月五日,大蕃国肃州酒泉郡沙门法荣写。手恶笔,多有阙错,后有明师,望垂改却。(BD02092尾题)①所引文书分见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百三十、七十六、八十一、十五、二十七、一百三十二、二十九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2010.分册条记目录之15,24,13,13,7,13,9.H.僧道格云:有犯苦使者,三纲立案剿闭。放一空院内,令其写经,日课五纸,日满检纸数,足放出。[30]
以上材料显示的写经目的,或为寺院典藏,或为僧尼祛病,或为众生祈福。材料H中,量化写经成为惩罚手段。同样,出于这些原因,信众也自己抄写或雇人抄写,如:“未年正月社人张庭休写,一心供养”(BD05584朱砂题记);“徐宗云敬佛经一卷”(BD15033号尾题);“辛丑年七月廿八日学生童子唐文英为妹久患写毕功记”(BD04584《观世音经》尾题,821年);“沙州清信佛弟子田进晟敬写此经”(BD01830,871年);“写经书手索押衙兑,龙苟儿家”(BD07431)等。①所引文书分见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七十五、一百三十七、六十一、二十五、九十七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2010.分册条记目录之9-10,12,20-21,10,8.由于民众思想信仰的实用性,敬事诸神与追求个体、同伴、家庭、家族幸福的意图便综合起来,凸显出写经的精神和仪式价值,如:
敬写金光明最胜王经一部十卷。右已上写经功德,并同庄严、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伺命伺录、土府水宫、行病鬼王、并役使、府君诸郎君及善知识、胡使录公、使者、检部历官舅母、关官、保人可韩、及新三使、风伯雨师等。伏愿哀垂纳受功德,乞延年益寿。(BD04072号,年代稍晚)[31]
此外,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与中原交通不便,各地信众到敦煌施写的情形可能大大减少。在此之前,中央和地方官吏、流散文人、商旅,乃至在押犯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天宝三载九月十七日,玉门行人在此襟。经廿日有余,于狱写了。有人受持诵读,楚客除罪万万劫。记之。同襟人马希晏,其人是河东郡、桑泉县。上柱国樊客记。”(BD05671号1)[32]
尽管中原知识分子抄本变少,但当地信众的零散写经,尤其是亲自供写的方式,不仅丰富了经本的书写风格,而且强化着经卷抄写的神圣性,其宗教信仰内涵,成为经卷生产的重要动因。
五、小结
皇室短期集中抄写、写经僧日常抄写、职业经生的专业抄写,和信众的业余抄写,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汉文写经的四种模式。其中,写经僧、职业经生和信众的抄写,是自魏晋以来就形成的写经模式,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传统。在该时期,三种形式均因吐蕃统治而得到了一定的加强,这是因为,吐蕃皇室组织写经,较之唐中央赐经影响更甚:这一立足于佛教事业的举措,不仅是吐蕃信奉、推广佛法的自主选择,也是基于统辖佛教圣地敦煌的必然道路。它促成了吐蕃政教举措在敦煌的顺利实施,保障了吐蕃政权的政治和宗教权力,并有效介入到敦煌各寺院的管理和运行之中,促成了当地职业经生队伍的壮大与稳定,保证了敦煌当地社会的相对和平。对此,“破落官朝散大夫殿中侍郎史臣王锡”的见解是一个恰当例证。他曾上书吐蕃赞普,极陈王者爱民的道理,说服赞普停战修和,同时也将佛教推广看做统治敦煌的最佳选择:“或□惠而广译真经,更建立伽蓝,雕刻素像,交驰驿使,延请僧徒。岂不是弘菩萨之心,启慈悲之愿,精修六度,拯拔四生耶?若如此者,同声闻之”(Pel.chin.3201V0)。[33]而对敦煌来说,虽暂时与中原阻隔,但正是借助佛教事业,地方宗教和儒家文化的主体脉络依然稳固。其间,佛经的抄写,便成为关乎地方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结构的事业,关乎文化生产与实践。故而,佛经施写,既是普遍的宗教信仰,也是各主体附加各自动因的一种社会文化行为。
[1][25]藤枝晃,刘豫川.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中)[J].长江文明,2012,(02):100-121.
[2][5]陆离,陆庆夫.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唐朝中央政权关系管窥[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01):97-107.
[3][7]西冈祖秀.沙州的写经事业——以藏文《无量寿宗要经》的写经为中心[A].李德龙,朴明姬译.陈庆英,耿升,向红笳.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二辑)[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113-128.
[4]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下)[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678.
[6]赵青山.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J].西藏研究,2009,(03):45-52.
[8]赵璘.因话录.卷四[A].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C].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97.
[9]陈楠.吐蕃统辖敦煌时期之藏文抄经活动考述[J].中国藏学,2013,(S2):32-38.
[10][14][17][18][24]藤枝晃,刘豫川.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下)[J].长江文明,2013,(01):84-100.
[11]任继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百八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40-41.
[12][33]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7[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8,146-147.
[13]赵青山.5件文书所反映的敦煌吐蕃时期的写经活动[J].中国藏学,2013,(4):99-104.
[15]吐蕃统治的敦煌[A].山口瑞凤,高然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编委成员.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61.
[16]任继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百九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63.
[19]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诸寺藏经与管理[A].郑炳林.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C].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15-38.
[20]李正宇.敦煌古代祠庙寺观简志[J].敦煌学辑刊,1988,(1、2):76-80.
[21][23]任继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八十五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8-9.
[22]谢应芳.辩惑编·卷二·治丧[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709册[C].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57.
[26]任继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十七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17.
[27]任继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百四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43.
[28]王尧.藏汉佛典对堪释读之三《大乘无量寿宗要经》[J].西藏研究,1990,(2):105.
[29]赵璘.因话录·卷六[M].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C].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02.
[30]仁井田陞.唐令拾遗补[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7.1003.
[31]任继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五十五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17.
[32]任继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七十六册[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