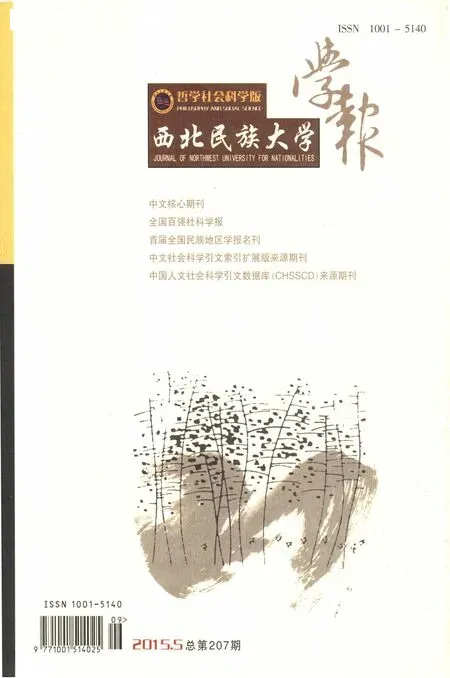清室与民国:清民之际满族贵族的政治认同
2015-02-20朱文哲
朱文哲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思政部,陕西 西安712100;2.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上海200433)
革命党人、袁世凯集团及满族贵族之间的互动角力,最终促成了清民转化。而由南北和谈所促成的清帝优待条件,使清室与民国形成了独特的共生与竞争关系。以往研究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局限已经有了极其深入的认识,此方面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也彰显了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清民之际历史变化的连续性逐步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如对《清帝逊位诏书》在稳定时局所具有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学者从法律史角度探讨了清民转化与民族国家的接续再造,对于重新审视《清帝逊位诏书》在清民转化中的重要意义极富启发性。①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喻大华《<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探溥仪潜往东北的一个原因》,《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杨昂《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常安《清末民初宪政世界中的“五族共和”》,《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2辑第343-371页;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章永乐《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重审清帝逊位系列诏书》,《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杨天宏《“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等等。有关清帝逊位研究的总体情况可参见陈鹏、韩祥、张公政《百年“清帝逊位”问题研究综述》,《清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不过在重新解读这些重要历史事件被忽略的面相时,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被历史“淹没”的群体。②近年来,有关满族贵族和清遗民的研究也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对于理解民国初期的政治生态多有助益。此方面的论著可参见孙燕京、周增光《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的政治心态》,《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如满族王公贵族在清民的共生竞争关系中政治认同的蜕变,有助于深入认识这一群体在民初的进退抉择,以及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连续性与断裂。
一
清民转化对清室而言为清帝退位换取了优待条件,而民国对优待条件的承认则是构成清王朝与民国政权转移的前提,也是“中国”主权连续性的重要保障。这种共生关系通过双方和谈得以确立,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又得到了清帝退位诏书的确认。如《清帝逊位诏书》说:“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民军所开优礼条件,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先皇陵制如旧妥修各节,均已一律担承。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1]与此同时,这些优待条件也构成了清室与民国的竞争关系。如《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之条件》的第一款即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2]尽管此种规定仅限于“礼”,但由礼仪所展现的清帝地位,仍有“外国君主”之礼的特殊境遇,无疑仍赋予了清帝所具有的“君主”象征性作用。此外,从清帝退位诏书来看,清帝辞位推荐袁世凯与民军组建中华民国,其自身仍具有“道统”的合法性。因而在民初政局中,“清帝”与“总统”并立,清室与民国共存,部分对前清抱持好感、对民国现状不满的复辟分子,仍旧以“清帝”归政为其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这无疑又对民国政权的稳固是一种威胁。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清帝退位后,紫禁城虽在实际的政治运作层面退出了政治舞台,但以政治文化的层面观之,紫禁城仍然承担着部分的道统合法性和君位神圣性,而这样一种剥离了政治实权的“中心”象征仍是有意义的。在民国政治的常态运作下,紫禁城不过是一个用宫廷仪式装点的皇城,然而一旦政治异态发生,紫禁城就会成为各类现实政治人物争相援据的“合法”资源[3]。在此情况下,特别是当清室与民国对现实政治资源形成竞争态势时,他们内在的矛盾便会被激化。由此可以看出,清室与民国之间脆弱的共生竞争关系,也构成了民初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内容之一。
清室与民国的此种复杂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民初王公贵族的政治生活样态。就以往对民初满族亲贵的研究来看,主要侧重于探讨宗社党的政治活动[4]。实际上,民初满族王公贵族的活动更为多样,大体可分为四种。一是组织复辟势力,意图恢复清廷的统治。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善耆、溥伟等人,他们联合国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企图颠覆民国,对民国初期的政局形势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也最为时人所关注。二是参与新政府的政治活动,如溥伦、荫昌等人。溥伦还曾担任袁世凯政府中的参政院议长之职;荫昌因“捧袁最力,因此袁对他也最赏识”,担任了总统府侍从武官处的侍从武官长[5]。三是脱离政界,基本上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如奕劻,清帝退位后不久即迁居天津租界,极少与闻政事。四是继续服务于前清逊帝溥仪。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世续、绍英等人。这些人不同的政治生活样态,恰恰反映了在时代变革之后满族亲贵在新政治体系中的困境与选择。尽管民初满族亲贵的政治取向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政治行为背后所展现的对清室认同之蜕变,则呈现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内容。
二
在民初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大多数满族亲贵也认同了现有国家,顺应这种时代潮流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而且在现有政治格局之下,清帝得以优待,自身利益得以保全,很多人反而对此感到庆幸,如1912年元旦,绍英在日记中说:“袁项城已允勉尽临时总统之义务,其优待皇室条件必能有加,岂非大清帝国二百九十余年深仁厚泽之报耶?”“惟祝国运亨通,苟全性命,获免瓜分,是诚五大族国民之幸福也。”[6]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满族亲贵无法出仕民国,也无意复辟清室,不问政治,吃喝享乐,醉生梦死。就如溥杰所述,民国建立之后,“王公贵族们除了讲究磕头请安的繁文缛节,就是比较吃喝穿戴,再不然就是追慕过去和嘲骂现在。”[7]而在清末曾经位高权重的奕劻和载振则退居天津租界,仍然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但基本不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8]。那桐则作对联“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年又过一年春”,称“隐居海滨,消受清福,别有意味”[9]。据金启孮所说,辛亥让国前夕,隆裕太后将府邸旗地赐为私有,王公世爵之财产(公产)有了处分权(成了私产),表面上是没落了,实际上却是畸形的阔绰起来了。而且因为金启孮的父亲恒煦与民国新贵之间的密切关系,得以承袭镇国公之爵,“与民国的关系比宫中接近”[10]。民国建立之后,满族王公贵族没有了前清时期的诸多限制,反倒更加自由,加之清末积聚的财货较多,因而很多人沉浸于声色犬马之中,根本不顾及往日家族的荣光及清室的存亡[11]。恽毓鼎就感叹,“满清无望中兴”,因为“亲贵之心死矣”[12]。
当然,还有些满族王公贵族有机会得以在民初参与北京政府的政治活动,不过疏离于清室,服务于民国,彰显了他们政治认同变异的独特境况,也体现了清室与民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溥仪就曾清楚记得荫昌拜会自己时的情景,“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的举动最为出色,他穿的是一身西式大礼服,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代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就跪在地上磕起头来。”[13]这一仪式所具有的双重意义极为丰富,从某种程度上展现了清民之间的共生与竞争关系,身为满族贵族,对满人之逊帝仍行君臣之礼;任总统侍从武官长,却已入民国之政府。形式上的礼仪与现实中的利益实现了“完美”结合,不过其对旧朝及逊帝的认同已经模糊难辨了。而在民国与清室形成竞争态势之时,满族王公贵族的表现就更为直接,也展现了他们对清室认同与现实政治利益抉择的真实态度。据溥仪回忆,袁世凯准备称帝时,溥伦曾代表清皇室和八旗向袁世凯上劝进表,袁世凯许给他亲王双俸,溥伦还进宫索要仪仗和玉玺。这让溥仪感到“心酸、悲愤和恐惧”[14]。尽管荫昌和溥伦的表现不尽相同,但显然都是屈从时势,服务于新的政治体系。中国历史中“不事二姓”的传统早已被这些本应“规复清室”的王公贵族所抛弃。而自称旗族中人的何志新,其说法也能反映旗人对此的观感,“旗人居军警劳动界为最多,各机关书记錄事次之,教育界又次之,掌参政权者万无一焉!即有一二,亦早为人收买,良心丧尽,不为本族谋也。”[15]另据了解逊清皇室诸多内幕的郑孝胥所说,“皇室愈贫,宗室大臣愈富,且有近支亲贵,串同民国政党中人,设谋分取实物者,人心可知矣。”[16]对民国与清室不同的态度,也见证了满族王公贵族对清室政治认同彻底崩解的现状。
事实上,恰恰也是民国与清室之间的共生关系,为清室存续及满族亲贵政治利益的维系提供了保障和可能,因而满族亲贵也“顺应时势”,与民初的北京政府相互利用。如袁世凯当政时期,民国政府继续允许前清王公承袭爵位,并将之视为优待皇族的重要内容。袁世凯就曾颁布命令:“清皇族私产应遵照前颁优待条件,一体认真保护,并严行晓谕各处壮丁人等,照旧缴纳丁粮,务期同奠新基,各安旧业。”[17]袁世凯意图称帝时,变更政体也受到清皇室的“推戴”。袁氏甚至发布命令意欲将清帝优待条件载入宪法,“政治堂呈称准参议院代行立法院咨准皇室内务府咨称,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承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协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临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等语。现在国体业经人民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此令。”[18]清室及满族王公贵族则依附于北京政府,并利用民初共和政体遭受挫折的契机,妄图复辟。对此有论者就指出,民初的尊孔运动,“既有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以及前清遗老的支持,又有袁世凯复辟集团的襄助,他们抬着孔子偶像招摇过市,把孔子思想吹得震天价响,既聚合了复辟势力,又扩大了复辟运动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是向民主革命力量叫阵示威。”[19]不过在满族亲贵丧失对清室的认同,以及清室与民国之间竞争关系的影响,此种暂时的联盟关系极为脆弱。
与顺应时势、疏离清室的大多满族王公贵族相比,仍有少数满族亲贵并不甘心清廷覆灭,妄图复辟旧朝。溥仪就回忆说,“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和旧臣们的话说,这是‘光复故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帝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止过。”[20]不过就满族王公贵族的复辟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种:其一是以善耆、溥伟为代表的宗社党,妄图利用各种反对民国的势力,以实现清廷复辟;其二是希望维系现有格局,借机实现清帝归政。其中宗社党在清帝尚未退位之前,面对清廷受迫之困境,就主张强硬对付袁世凯及革命党人,以保护清王朝的“宗庙社稷”。如“载泽、载涛二人自初九日(1911年12月28日)谕旨颁发后,颇为忿激,大骂各亲贵各顾自己,毫无心肝。是日即密约善耆等会商,二人情愿各出宝贵物品及资财若干万,由善耆派人携资分赴内外蒙,贿说各王公、台吉及番僧等群起反对共和,以降服外国为要挟之主旨,或举兵勤王,军饷悉由二人筹拨,万一保存君主,事后必予以特别之利益。”[21]不过迅即因为南北和议,迫使清帝逊位。善耆、溥伟等人逃往东北,从而拉开了复辟活动的序幕。他们活动的主要手段即运动前清之藩属,谋求独立,从而规复“旧朝”;或借外人之力干涉中国内政,企图迫使民国归政清帝。他们在民国建立之后的诸多活动,与清帝逊位之前多有关联。时论就说,“宗社党前此反对共和,借外兵图暗杀,种种举动均归无效。现见大势已去,都城地方又有重兵镇压,无可发动之机。忽发生一奇想:欲拥君主前赴东三省,联合蒙古各处,邀请日俄保护,宣告独立。前数日已派数人前往联络赵都督及红胡子,布置一切。闻帕王、泽公等不日亦将出发,彼党以为此举成则不失为偏安之局,败则即以土地送人,启中国之瓜分,亦足以泄逼迫逊位之私愤。”[22]
特别是善耆、溥伟等人,企图借助外人之力分裂中国,逆历史潮流而动,更使自己身败名裂。溥伟在写给川岛浪速的信中就说,“自壬子春出亡海上,追随忠义之士,奔走呼号,惟以救民复辟为宗旨,虽叠经波折,不能稍改此志。今者中国分裂,时机大有可乘,务求鼎力斡旋,急起直追,上报累朝之恩遇,奠东亚之和平,辅我兄弟之不足。他日事成则贵国与先生之义盛,永垂天壤,岂仅我大清臣子没世不忘乎?”[23]溥伟对支持宗社党活动的日人宗方小太郎说:“(德人)实极优待,他们亦深知余志,有约给予援助。然而静思,德人给予援助之真意,和贵国之真意,自当有所区别,余对此深有了解。如借欧美异种人之力,恢复宗社,虽成功心中实以为耻,国民也不愿这样作。余虽不忍却德人之好意,然志实不在此。今虽不能遮离青岛,但贵国若无异议,他日欲迁居旅顺。贵国和我国为同文同种关系,受异族之援助,余所不愿,得同种邻邦扶助,完成恢复大业,则荣幸有加。望先生能将余之心志转达贵国政府(从前我国政府所为,有不少伤害贵国感情之事,此皆朝廷中奸人所为,决非朝廷真意云云)。”[24]从溥伟冠冕堂皇的说辞当中已经辨别不清他到底是大清的臣民还是日本的走狗,视图谋中国的日人为“同种”,却彰显了自己所处的困境。特别是他们保全清室的狭隘目的,致使他们在规复旧朝的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摇尾乞求外人之干涉,不顾时代潮流及民族国家利益,也只能被日人利用作为祸乱中国的工具。
满族亲贵的复辟举动会打破具有法理基础的清民共生关系,置清廷于危险之中,既遭到清室的责难,也激起民国当政者的强烈反对,陷自己于进退两难之境。少数满族亲贵企图颠覆民国,恢复“旧朝”,从“国家”层面自然与清廷退位的条件相冲突,因而看似在维系旧王朝的合法性,却从根本上威胁着逊帝的政治地位。因而民国刚刚建立,隆裕太后三令五申,禁止王公贵族参与复辟活动。如《顺天时报》报道,“清太后近因宗社党屡开秘密计议,实于共和成立大局有碍,特派世伯轩太保、和硕亲王前往抚慰解散。”[25]又据《申报》消息,“北京宣布共和之初,满亲贵恭王、肃王、泽公及铁良等谋在奉天独立,拥戴恭王为皇帝。事为清太后所闻,日前恭王回京时,清太后唤其入内,谓:大势已趋共和,尔等勿在外妄有举动。恭乃唯唯而退。”[26]而民国政府则密令赵尔巽,清剿在东北活动的宗社党分子[27]。袁世凯还致电负隅顽抗的升允,“痛言此次议和之原因及大势之趋向,劝其当以救国为急,不可坚持一人之意见,致陷国家于危亡。”[28]从这些内容就可以看出,在时势变革之际,宗社党既面临“清帝合法道统”延续的强大压力,又受制于“民族国家建构”潮流的逼迫,因而不管是逊清皇室还是民国政府,从舆论到武力都对宗社党大加挞伐。
与秉持激烈手段的善耆、溥伟等人不同,在逊帝溥仪周围的部分满族王公则力图保持现状,借“天机”与“民心”复归以恢复清朝之统治。这种复辟动机,从支持宗社党的宗方小太郎的说辞中也可见一二。“革命以来新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新法,不仅不能取悦人心,混乱的秩序依然不能恢复。新的设施尚未见眉目,旧的恶弊仍在困绕着人们。兴一利而生百害,内外施政经营尚不及前清时代。内地各省常常陷人混乱,生灵涂炭。天下人心已厌共和,讴歌前朝者渐多,复辟帝制的时机似将来临,复辟分子在暗中活动,似一股涓涓暗流,在寻找它的归宿。”[29]此种对清室抱持特别好感的主观取向,既源自于对时代潮流判断的不确,也源自于对现有政治格局的无知,更包含有日人趁乱图谋中国的祸心。即就是面临如此“良机”,很多人并不愿意公然复辟。甚至在1917年张勋复辟时,世续等人的表现颇能反映清室的顾忌,当时“清帝室中,则瑾、瑜等四太妃不愿遽行复辟,以招危险。世太保续亦叩头流血,请斟酌尽善,方可实行。”而“满人之有世界知识者,无不私忧窃叹,甚或慷慨愤激,痛骂辫帅。”[30]随着形势对复辟越来越不利,溥仪也特派某贝勒至荷兰公使馆,向外交团声明,称此次复辟纯是张勋所为,与清室无干[31]。另据《益世报》报道,段祺瑞入京之后,“前清皇族醇亲王、振贝子、涛洵两贝勒及梁鼎芬等极形不安,曾历访段总理、黎黄陂、蒋作宾等,申辩此次复辟与清室无关,恳请保护将来。”不过在时人看来,“然复辟即成,事关清室,无论如何解说,终不能脱得干净。”[32]尽管清帝优待条件得以保全,但此次事件促动了整个社会对清帝地位的重新思考。当民国新贵与前清皇室之间的关系受到时势的冲击越加淡薄的时候,清室的存在就必然受到威胁。换言之,清室主动或被迫参与复辟活动破坏了自身存在的法律基础。受张勋复辟失败的影响,满洲贵族更为谨慎,此种情况从金梁的条陈也可见大略,“今日要事以密图恢复为第一,恢复大计,旋乾转坤,经纬万端,当先保护宫廷,以固根本。”“恢复变法,务从慎密,当内自振奋,而外示韬晦,求贤才,收人心,联友邦,以不动声色为主。”[33]这看起来是简单的“归政”问题,却包含了对共和趋势的否定,而复辟分子对“清帝”道统地位的利用和维护,也反映了他们在清民政治转型时所面临的难以适应的心境[34]。
三
不管满族亲贵的何种复辟形式都与时代发展潮流不合,也多为时人所反对。《申报》的评论,颇能代表时人对宗社党之观感,“从前易姓革命之后,一二孤臣遗老,不胜故主之思,尝胆卧薪,潜图兴复,以彼胜之者固据天下为己有也。今则清廷逊位,非一姓一家之兴亡问题,乃帝政与民主之蜕进问题。一姓之兴亡,可以效忠于一姓而复之,帝政与民主之擅蜕,断不能逆群演之大例而复之。故自今以后,无论为宗社党,为非宗社党,或拥戴他人,或帝制自为者,均逆天演进化之大例而归失败,彼宗社党亦人,奈何愚不可及若此。”[35]事实上,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并不代表人心复归清室。正如有人所言,“夫今言国事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本不可强为画一。但平心论之,国事败坏,由于清季朝政昏谬,则为不可辩之事实。种因悠久,陆续获果,至今未已。二三遗老,犹欲戴此一姓,而不肯蔽以误民之辜,亦太昧昧矣。”[36]钱玄同也针对社会上泛起的复辟论调说到,“一、依世界人文之进化原则,中国必为共和;二、一度建设共和之国,即使恢复帝政,亦不能持久;三、特中国尚不为真正共和,虽终局最后必为共和,于此过渡期间有无变化,则不可一一逆睹。”[37]而在1917年的张勋复辟中,面对其代表要求归政清室的逼迫,黎元洪态度非常坚决地说:“予一人进退不成问题,惟民国政府乃受国民之付托,非国民有正当之表示,予决不能私相授受。”[38]冯国璋的讨伐电文更有意味,“国家以人民为主体,经一度之改革,人民即受一度之苦痛。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孝定景皇后禅让于前,优待条件保障于后,共和国体,民已安定。约法谋叛民国者,虽大总统不能免于裁判。清皇室亦有倡议复辟,置褚重典之宣言。诚以民生不可复扰,国基不可再摇。虑共和国体之下而言帝制,无论何人,即为革命。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所以保民国,亦所以安清室。”[39]从这些时论述评就可以看出,希图清朝复辟根本不符合人心大势,反倒破坏了辛亥之际所形成的清民共生关系。
实际上,清民共生关系的维系是需要清民双方共同遵守的,而双方的竞争关系则使清民之间的矛盾难以根本消除,特别是在民初复辟势力仍然比较猖獗的情况下,民国政府对清室政治活动做出限制成为必然趋势。1914年宋育仁等人倡言民国政府要归政清室,肃政史夏寿康进行了批驳。“清廷本以失民去位,民心断难再复。徒使反侧之徒,用其阴谋,搆煽内乱,而他国且利用此收渔人之利,中国之危亡,将万劫不可复。是争一姓之权利,陷五族以沦胥,不独为世界公例所不容,亦且背孔、孟大同之经义!况清室宗庙陵寝,永受优待,载在盟册;设因此等谬论,致满人皇族中或有一二无知之辈,误入迷途,妄生枝节,其祸何可胜言?更恐其说倡扬,国本因之动摇,清室亦随以倾覆。”民国参政院议员则指出,“民国既成三载,而清室种种举动一仍前清之旧,奄然在民国中又别有一统治权”[40],因而要求惩处提倡复辟论调的守旧分子。1914年12月26日,袁世凯主导下的民国政府与清皇室商定了善后办法,其中第一条就规定:“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41]随着革命形势再度高涨,优待清室条例的修改和废止也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由此也彻底打破了清民之间的连续性[42]。
综上可见,民初亲贵之取向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特别是民族国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得满族王公贵族对清室之认同面临难以调适的困境。大多满族亲贵在民国建立之后不问政治,依靠以往所积聚起来的财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甚至投身民国政坛,清室之存废已经无关紧要。少数满族亲贵试图借外人之力颠覆民国,既不顺共和之趋势,也损害国家利益,为人所不齿;还有一些人“总觉得清王室列祖列宗深仁厚泽,人心思归,清朝不该就这样灭亡了,将来还有好起来的一天,等待着‘否极泰来’”[43]。这些鲁莽举动和天真幻想,在清民转化的时代大潮中都无实现之可能。因为“复古主义”政治活动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困境,正如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所分析的那样,“复古主义由于其事业的性质,常常被斥责为企图调和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而这种主张中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正是复古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弱点,因而复古主义者便陷入一种不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摆脱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倘若他丝毫不顾现实,而试图恢复过去,一往无前的生命冲动就会把他的脆弱建筑打成碎片。另一方面,如果他听任复古的热情屈从于改造现实的任务,那么他的复古主义将被证明是一场骗局。”[44]这就意味着在民初剧变的时代大潮中,满族亲贵退出历史舞台已成为必然趋势。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32-433.
[2]共和关键录(第一编)[C].上海:上海著易堂书局,1912.
[3]冯佳.“国”与“君”:政治文化视角下的隆裕太后葬礼[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4]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114.
[5]唐在礼.辛亥革命以后的袁世凯[A].杜春和.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C].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81.94.
[6]绍英.绍英日记(第2册)[Z].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282.
[7]爱新觉罗·溥杰.溥杰自述[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总101辑)[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86-187.
[8]爱新觉罗·溥铨.我父庆亲王载振事略[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145.
[9]北京市档案馆.那桐日记[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765.
[10]金启孮.金启孮谈北京满族[M].北京:中华书局,2009.193-253.
[11]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365-422.
[12]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593.
[13][14][20]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97,65,59.
[15]何志新.旗族之将来(续)[N].京华日报.1918-11-28.
[16]云台.清皇室衰落之内容[A].聂其杰.家声选刊(第一辑)[C].上海:有正书局,1925.50.
[17]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1912-1928)第二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1392.
[18]政府公报.第1279号,1915-12-17.
[19]张艳国.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复辟与尊孔关系探讨[J].学术月刊,2002,(6).
[21]诱致内外蒙反对共和[N].新闻报,1912-01-11.
[22]宗社党愈趋愈下[N].申报,1912-02-09.
[23]恭亲王溥伟书简川岛浪速[Z].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资料编号2286.
[24][29]宗方小太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总48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95-96,89-90.
[25]派王大臣劝解宗社党[N].顺天时报,1912-02-28.
[26]专电.申报,1912-02-21.
[27]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3册)[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243-245.
[28]专电[N].申报,1912-02-24.
[30][31][38]许指严.复辟半月记[M].上海:交通图书馆,1917.9-60,79-80,9.
[32]清亲贵洗刷复辟[N].益世报,1917-07-16.
[33]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条陈三事摺[A].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C].故宫博物院刊行,1929.
[34]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向下的清遗民[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364.
[35]姜.宗社党[N].申报,1913-01-04.
[36]黄溶.花随人圣庵摭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2.
[37]钱玄同.复辟论之评判[J].正谊杂志,1914,(6).
[39]存萃学社.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C].上海:大东图书公司,1977.18-19.
[40]万仁员,方庆秋.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四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512-525.
[41]政府与清皇室商定善后办法[J].东方杂志,1915,(2):6.
[42]杨念群.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J].近代史研究,2012,(5):20.
[43]爱新觉罗·溥杰.溥杰自传[M].叶祖孚执笔.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20.
[44][英]汤因比(著),萨默维尔(编).历史研究[M].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