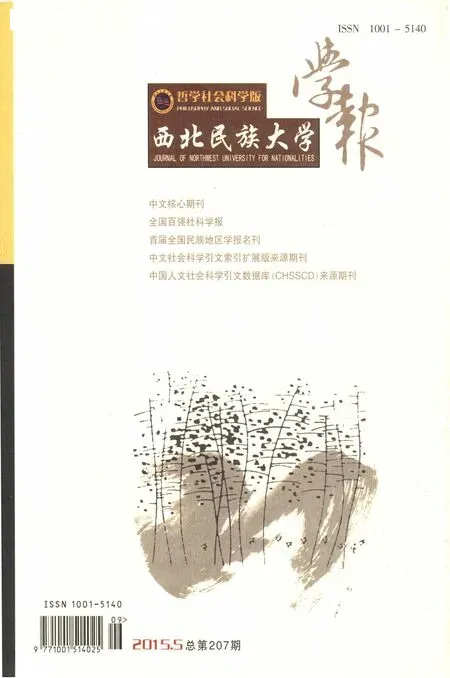青海和硕特部蒙古与康熙末期“驱准保藏”
2015-02-20刘锦
刘 锦
(广州行政学院 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广东 广州510070)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军远侵西藏,终结了青海和硕特汗庭对西藏75年的统治。准噶尔的入侵打破了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而其控制达赖喇嘛号令蒙古诸部的企图则令清朝、青海和硕特蒙古深感不安,清朝、青海和硕特及准噶尔等三方势力在西南边疆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八月,清军拉拢青海和硕特蒙古联军入藏,成功地驱逐了在藏准噶尔军队,学界称其为“驱准保藏”。关于这次平定西藏的准噶尔之乱,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但学界多为侧重研究其背景、经过、影响及意义。饶有趣味的是,档案、文献中常提到的青海和硕特蒙古,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有所述及[1],但缺乏深入的分析探讨。曾经控制青海、西藏及其整个周边藏区,并与准噶尔、西藏僧俗高层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青海和硕特蒙古,清朝是如何争取、利用其实现“驱准保藏”事业的?本文在分析西南边疆局势及清朝与青海和硕特关系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青海和硕特的内争及其影响以及探讨清朝拉拢青海和硕特联合入藏,以企厘清实现“驱准保藏”的动态过程。
一、西南边疆形势与清朝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昭莫多战役中俘虏的罗垒厄木齐,即青海和硕特博硕克图济农派往准噶尔处的使者,向清廷供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道出五世达赖喇嘛已殁多年的秘密,二是青海和硕特蒙古支持、参与了噶尔丹与清朝的战争。此消息震惊清廷,康熙帝立刻调整对青海、西藏的政策。自此,青海和硕特、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为理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有必要了解清朝与青海和硕特之关系的发展演变及其西南边疆的形势。
1636年,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1582—1654年),受西藏佛教格鲁派之邀请,率军南下并征服了整个青藏高原。之后,顾实汗分封诸子,长子达延一系继续驻扎拉萨,成为达赖喇嘛的保护者,其他诸子则驻牧青海,以“青海厄鲁特”或“青海和硕特”而著称。早在崇德七年(1643年),青海和硕特与清朝之间开始建立联系[2],顾实汗之子多尔济达赖巴图尔向清朝贡马[3],此后青海和硕特向清朝遣使贡方物渐多。顺治六年(1649年)十月,清朝敕谕青海和硕特鄂木布、墨尔根、和罗木席部,请求出兵助其攻打喀尔喀蒙古,试图与青海和硕特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关系。其敕书内容如下:
上谕鄂木布卓礼克图巴图鲁济农、鄂木布土谢图巴图鲁戴青、和罗木席巴图鲁额尔得尼戴青:本朝于旧好之国,初不愿加兵,若当交好时,土谢图汗、丹津喇嘛、硕雷汗无故出兵,两次拒敌,惟天降罚,使之败畔。二楚虎尔又无故侵我巴林,杀人掠畜。俄木布额尔德尼又无故加兵于我,及闻我出师,始还。巴尔布冰图又来侵我土默特部落,杀其人民,劫马二千匹。此辈每起兵端,朕能默然处之耶。朕前此遣使,尔诺门汗云,我虽老,我诸子兵卒尚未老也,凡有征讨,我当以兵助之。尔等欲如何?[4]
上述内容显示,顾实汗其实早已想与清朝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我虽老,我诸子兵卒尚未老也,凡有征讨,我当以兵助之”。而清朝的请兵,一是试探青海和硕特与喀尔喀蒙古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试图打破一般意义上的遣使朝贡关系,与青海和硕特建立政治盟友的联系,此次清朝的请兵最终失败。然而,清朝还是试图拉拢青海和硕特,这从《清世祖实录》的其他记载可知:“以破回逆,及招降西宁城功,峨木布车臣戴青为土谢图巴图鲁戴青;和罗木席额尔得尼戴青为巴图鲁额尔得尼戴青;墨尔根济农为卓礼克图巴图鲁济农”[5]。青海和硕特鄂木布、墨尔根、和罗木席三部,曾帮助清朝镇压甘州回族米喇印、丁国栋起义以及招降西宁城有功,清朝分别赐予封号,以此来笼络和巩固彼此之关系。
顺治九年(1652年),顾实汗成功劝导五世达赖喇嘛赴京朝觐,青海和硕特与清朝之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期。清朝非常重视此次达赖喇嘛赴京朝觐,借此机会争取与青海和硕特结为相互依赖之势力,遂赐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并颁予金册、金印[6]。自此,清朝在政治上正式承认了顾实汗及其子孙在青海和西藏的统治地位。遗憾的是,此好景不长,顾实汗死后,青海和硕特诸部互争雄长,频频掠边,常与清朝发生有关争夺牧地、牲畜和属民的边境纠纷。后顾实汗时代的汗王,已渐失驾驭青海诸部的能力,应如何处理青海和硕特事务?清朝几经周折后开始选择让五世达赖喇嘛参与青海蒙古世俗事务的处理[7]。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十三日,清朝从俘虏中获悉“噶尔丹言,青海诸台吉并俄罗斯国人,与彼同攻中国,又潜通中国回子,从中助彼,计得中国后,立回子为中国主,彼则取其赋税,是以至克鲁伦”[8]。此奏报显示,青海和硕特暗中支持、参与噶尔丹东侵喀尔喀,与清朝作对等。知此消息后,康熙帝非常愤怒与不安,如何招抚青海和硕特则成为接下急需完成的重要工作。康熙帝称“众蒙古以第巴为达赖喇嘛传戒之人,皆缄口不敢议。朕曾以敕谕往责第巴,彼甚心服,具疏认罪,朕因宥之。嗣后第巴若改前行,敬奉班禅、达赖喇嘛则已;若仍怙恶不悛,朕不但不宽贷第巴,即其亲密之青海台吉等,朕亦不轻恕也”[9]。康熙帝简要地道出了青海与西藏的关系,即清朝若要招抚蒙古必先屈服第巴,若想屈服第巴又必以兵威慑青海和硕特。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令员外二郎保前往青海招抚青海和硕特,“臣身自甘州起程,……七月初八日,达什巴图尔等三十一台吉全到盟所,以檄文授之”,并以博硕克图济农与噶尔丹联姻之事威胁青海和硕特屈服[10]。清朝招抚青海和硕特之举,引起第巴桑结嘉措的恐慌,第巴先是向清廷奏报博硕克图济农与噶尔丹结姻之事,请求清廷“噶尔丹之女已嫁博硕克图济农之子,免送京师,不致夫妇离散”[11],紧接着则“谕青海诸首领,俱于正月二十八日在察罕托洛海地方会盟,缮修器械,可令尔(噶尔亶多尔济)属下人亦缮修器,务如期必到会盟之地”,对第巴的举动,清朝高度警戒,“第巴无故令青海诸台吉缮修器械,又约从来未与盟会之噶尔亶多尔济,其意叵测”[12]。于是,康熙帝加强招抚工作的力度,“近来皇上遣贤员携扎西巴图鲁台吉等之使者前往劝降携来,甚是,宜遵谕施行。是以遣臣等携扎西巴图鲁台吉之使者鄂木布等三人前往青海,传宣皇上恩旨,劝降青海台吉携来”[13]。清朝的招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十一月,顾实汗幼子达什巴图尔率青海诸台吉赴京师朝觐。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颁诏,敕封青海诸台吉,封达什巴图尔为亲王,土谢图戴青纳木札尔额尔德尼为贝勒,彭楚克为贝子等[14]。
招抚工作如此成功,这是康熙帝始未预料的,“前不知事之成与否,恐反起兵端,亦未可料,故未即发。今观阿喇布坦等奏疏,青海台吉皆愿降来朝。未向一兵一卒,尽收西部厄鲁特。此乃大喜之事,是以急报”[15]。然而,青海和硕特诸台吉是受清廷威胁而屈服的,与清朝的关系依然是若即若离,在涉及根本利益常以逃避的方式抵制清廷的要求。
二、准噶尔入侵西藏前青海和硕特内讧
前文述及,“达赖喇嘛殁已九年矣”的消息,立刻引发西藏政治“地震”。康熙帝得知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多年的消息后,深感被欺蒙,“夫本朝为达赖喇嘛护法之主,礼待六十余年,其没也,第巴理宜奏闻而第巴匿之,反惑众诱噶尔丹兴戎,第巴之罪大矣”[16],立遣使者向第巴桑结嘉措问责。此时的第巴桑结嘉措即知事实已公众于世,开始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护,清朝当时尚无条件直接过问西藏政务,无法深究桑结嘉措,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拉藏继承和硕特汗王之位,因不甘心汗权的旁落,与第巴展开了权力的争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拉藏汗擒获第巴并将其处死,“先是,达赖喇嘛身故,第巴匿其事,构使喀尔喀、厄鲁特互相仇杀,扰害生灵。又立假达赖喇嘛,以惑众人。且曾毒拉藏,因其未死,后复逐之。是以拉藏蓄恨兴兵,执第巴而杀之,陈奏假达赖喇嘛情由”[17]。拉藏汗处死第巴桑结嘉措,目的是恢复对西藏的统治。清朝得知拉藏汗擒杀第巴桑结嘉措后,传旨拉藏汗、青海诸台吉使者“今拉藏杀第巴后受阻,不知达赖喇嘛之实虚,不能裁决,所以奏请。今更改第巴给拉藏之成吉思汗之名,给予其父之达赖之号,送达赖喇嘛至此,朕观达赖喇嘛之实虚后,或立为察齐尔巴顿汗,或封为达赖喇嘛之处,观后决定”[18],要求将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押送赴京,拉藏汗迫于压力只好俯首从命,青海和硕特等颇为不满。更为重要的是,拉藏汗私自选立意希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严重触犯青海和硕特部的共同利益,从而引起西藏僧俗和青海和硕特的愤怒,一场围绕真假六世达赖喇嘛问题而展开的权力争夺拉开了序幕。
首先,拉藏汗与青海和硕特诸台吉之争。仓央嘉措被废事件发生后,青海和硕特首先向拉藏汗发难,“先是,拉藏汗立波克塔胡必尔汗为达赖喇嘛,青海众台吉等未辨虚实,彼此争论讦奏”,至是,康熙帝“命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众台吉之使人赴西藏看验”,拉都浑等回奏称,意希嘉措是真达赖喇嘛,“据云:前将假达赖喇嘛解京时,曾奉谕旨令寻真达赖喇嘛。今访闻得波克塔胡必尔汗系达赖喇嘛。亦不能信,又问班禅胡土克图,据云:波克塔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我始为之安置禅榻,非敢专擅”[19]。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清朝赐封意希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20]。但是,拉萨三大寺的上层喇嘛们对意希嘉措仍持不承认态度,他们根据仓央嘉措写的一首情歌:“羽毛洁白的仙鹤,请把翅膀借给我,不到远处的地方,到理塘去去就回”得到启示,既然他是“到理塘去去就回”,于是他们就在理塘寻找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结果找到了一个名叫格桑嘉措的儿童[21]。在理塘找到转世“灵童”的消息立刻引起拉藏汗的重视,遂派使者前往察看虚实。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正月,格桑嘉措的父亲索诺木达尔扎,因听说拉藏汗所派格敦和达吉加来理塘,恐有不测,带领格桑嘉措外出躲避,至7月,有关格桑嘉措为达赖喇嘛化身的说法传到康藏和青海和硕特诸台吉牧地[22]。青海和硕特诸台吉得此消息后,大家甚为高兴,并商定为了证实和缔结因缘,每位头人须派一名使者去确认[23]。值得注意的是,顾实汗幼子达什巴图尔临终时,向其子罗卜藏丹津及济农等人留下遗嘱:要不惜一切,尽快迎请理塘达赖喇嘛化身到青海。青海和硕特把理塘的格桑嘉措接到青海,视其为真达赖喇嘛,目的是以其对抗拉藏汗。自此,和硕特汗庭的内争愈演愈烈,一场以武力冲突势所难免。康熙五十五(1716年)年九月,拉藏汗向清朝奏参察罕丹津,“伏闻照封今世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恢复如初,裁断从中所出之其余呼毕勒罕为假,送来塔尔寺之温旨,又并赏整疋好缎十二匹,不胜喜悦。今戴青和硕齐竟谓圣主所封之达赖喇嘛为假,从前班禅所指是假,将巴尔喀木城之头领杀者杀,换者换,擒拿我等所立济农、达尔扎布二人,掠走赏给达赖欢台吉下贝勒色布腾扎勒之人。伊肆意妄为,无恶不作”[24],康熙帝一时难以确定对策,只好下旨将贝勒色布腾札勒纳贡人尽数给还,令其兄弟之际消除猜忌。
青海和硕特汗庭的内争,严重影响了清朝对局势的判断,也给青藏高原的稳定带来严重后果。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朝从俘获的准噶尔阿筹拉克、吹扎卜两人中得知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远征西藏,此时康熙帝的反映则是“以此观之,尔或欲侵戴青和硕齐、罗卜藏丹津,以引导策妄阿喇布坦之兵,亦未可定”,于是清朝下旨严重警告拉藏汗“尔诚受我主之封,食我主之禄,而侵我边疆之贝勒,我四川等处,所有三万兵丁,与贝勒戴青和硕齐,同在一处,又岂有坐视尔临诺木珲乌巴什穆鲁乌苏等处,侵青海之理乎。至彼时,我兵助戴青和硕齐,与尔交战,我虽有禁止之文,亦无及矣”[25]。至拉藏汗求救的奏报到来时,清朝完全陷入被动局面,一切都为时已晚。更有意思的是,拉藏汗在其求救的奏章中,再次提及他对青海诸台吉的疑虑,策妄阿拉布坦“五月十五日于达木地方与戴青和硕齐约定,公同夺攻克,以延请班禅额尔德尼”,拉藏汗的疑虑是否属实,康熙帝或许也无法判断,只能劝勉,“矧策妄旺喇布坦既然与尔为敌,即以前尔之青海兄弟与尔曾有些睦之处,亦系尔之骨肉,且朕诸多年来轸念固始汗,予以抚养,其亦断不会另起二心,为此尔切勿有疑虑”[26]。青海和硕特汗庭内部的不团结,自然加速其自身的衰亡。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四月,侍卫阿齐图向清廷奏报,准噶尔兵已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攻下拉萨,拉藏汗被围身亡[27]。准噶尔兵成功占领拉萨,也标志着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统治西藏75年历史的结束。
其次,青海和硕特左右翼内讧。青海和硕特左右翼诸台吉在前往迎请格桑嘉措父子时,也咨会清廷有关理塘出现五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的情况,“先经青海右翼贝勒戴青和硕齐、察汉丹津等奏称:里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请册封。其从前班禅胡土克图及拉藏汗题请安置禅榻之胡必尔汗是假”[28]。康熙帝接到报告后,“查得,去年,贝勒戴青和硕齐察干[罕]丹津等,具奏理塘地方出个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之处后,圣主洞鉴,以倘将伊留于青海地方,恐日后伊等兄弟内互相反目,肇生争战”[29]。清朝立即派侍卫阿齐图等人前往,试图迎接格桑嘉措入京师。此时,青海和硕特就是否将格桑嘉措送往清廷之事,彼此之间又发生分歧:
据青海左翼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台吉苏尔扎、右翼贝勒色布腾扎尔、盆苏克旺扎尔、台吉达彦等遣员来禀:先前,于会盟之地,我等五人因极力规劝我等众兄弟,应遵圣主之旨,将此呼毕勒罕送往口内。是以贝勒戴青和硕齐察干[罕]丹津等,以我等与伊等意向不和,视如仇敌。以其势观之,此呼毕勒罕断难送往口内,我等之意,除遵圣主之旨外,别无它言,是以遣员以我等身病为辞,告知停止前往。八月二十九日,于会盟之萨喇图地方,众台吉齐集后,奴才等详谕贝勒察干[罕]丹津等曰:奉圣主之旨:宗喀巴之庙亦属内地,距西宁近,察干[罕]丹津等既请求将此呼毕勒罕驻宗喀巴庙,即照伊等所请,送往宗喀巴庙暂驻可也。钦此。各等情后,据贝勒察干[罕]丹津等会议后告曰:圣主鸿慈,既降旨准照我等所请行,命呼毕勒罕驻宗喀巴庙,本应立即送宗喀巴庙,闻得,口内宗喀巴庙周围有出痘之事,患病这人甚多,照看二三月后,俟患病、出痘期间过后再送。等语。……而今察干[罕]丹津等又悔言,造作种种借口,声言小呼毕勒罕本年无前往之造化,拟来年秋季前往。等语。由此观之,此系因策妄喇布坦、察干[罕]丹津等互派使臣所致,与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并无关系。[30]
上述内容显示,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等一再迁延送格桑嘉措赴京,清朝显然看出其中别有隐情,“此系因策妄喇布坦、察干[罕]丹津等互派使臣所致,与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并无关系”。阿齐图等奏报传达了更重要的信息:青海和硕特不仅与拉藏汗争斗,其诸台吉之间也存在不和,左翼的阿拉布坦、鄂木布、苏尔扎、右翼色布腾扎尔、盆苏克旺扎尔、台吉达彦等明显倾向于清朝,与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等的利益发生抵触,“以我等与伊等意向不和,视如仇敌”。为迫使阿拉布坦等屈服,察罕丹津试图采用武力吞并不同政见的台吉,“贝勒察罕丹津等因去年胡必尔汗之事,贝勒阿喇布坦鄂木布、盆苏克汪扎尔,台吉达颜、苏尔扎等遵旨不与同心。今欲与罗卜藏丹津等盟誓,先攻取五家,将胡必尔汗送往西地”[31]。鉴于此情况,清朝令西宁、松潘驻军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追剿。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正月,迫于压力的察罕丹津针对贝勒阿拉布坦鄂木布等对其的奏参,向清朝上奏辩护称:“臣前觐天颜,荷蒙圣旨洪恩,迄今不贰。前我屡被族人讦奏,……札希巴图鲁王屡喻我奏请皇上,该新呼毕勒罕是真,故曾奏请,我等不敢违背圣旨而行。……今我青海兄弟诬告我归附策妄喇布坦。”对于察罕丹津的辩词,清廷则认为,关于格桑嘉措入京之事“时唯独察罕丹津抵制,始终推诿,谓呼毕勒罕无前去之造化。等情,不令起程。而今又以王札希巴图鲁为托辞”[32],下令察罕丹津即刻将呼毕勒罕送往塔尔寺,否则务必征剿。至闰三月,康熙帝再次下旨令青海左、右二翼台吉和睦,“复屡谕青海台吉等,若等始惧,于三月十五日,送呼毕勒罕至宗喀巴寺,但青海二翼台吉,今虽和睦,恐不能久,请令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达颜管理右翼事务,额尔德尼额尔克托鼐、阿喇卜坦、鄂木布管理左翼事务,再遣大臣同郎中长受、主事巴特玛至青海会盟,令其永远和睦”[33]。
青海和硕特迫于清朝的压力,最终将达赖喇嘛格桑嘉措送至塔尔寺,但这并不表示青海和硕特不会以某种借口抵制清廷的要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康熙帝接到拉藏汗求救的奏报后,下令“侍卫色楞、侍读学士查礼浑在西宁满洲兵内选二百名,绿旗兵内选二百名,及土司之兵一千,带至青海地方,会同青海王、台吉等商酌行事”[34]。清廷不曾想到的是,青海诸台吉仍以内部不和,不与清朝合作,“据王罗卜藏丹津等声称:前年准噶尔贼匪夺取藏时,我圣主为保护黄教众生,特派官兵,青海亦派兵丁会盟,计左右翼共派兵万名,等因,具奏在案,嗣因兄弟互相不和,未能派兵,至误军机”[35]。青海和硕特内部关系的复杂性,也使得清廷将领对察罕丹津等存有诸多的不信任。六月十七日,色楞向清廷报告,总督额伦特“奉旨差渣布往察罕丹津处,令伊(察罕丹津)遣人将准噶尔之兵诱来。俟所遣之人回信,然后进兵”[36],要求色楞按其计划等待察罕丹津消息后再行事,但色楞认为“策妄阿拉布坦、察罕丹津互约,征伐拉藏,立小呼毕勒罕,以察罕丹津为首驻扎之事,虽不稔知真伪,现所传布之语,不可谓甚无征象”[37]。于是,色楞“臣愚以为准噶尔残害西藏,彼处人民悬望我师如望云霓,岂能刻缓”,遂孤军深入。九月二十日,哈喇乌苏(黑河)战役打响,清军全军覆灭。青海和硕特蒙古的内讧,先是让准噶尔军队有机可乘占领拉萨,再则以内讧而贻误军机,造成清军首次远征在藏准噶尔军队失败[38],“策妄阿喇布坦之人,霸占藏地,毁其寺庙,散其番僧,青海台吉理应弃命忘身,奋勇致讨,乃伊等口称维持黄教,但无实心效力之人”[39]。
三、清朝收服青海和硕特联军进藏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康熙帝接到色楞远征西藏准噶尔失败的奏报后,立即召集大臣商讨再次远征的计划。十月十二日,康熙帝任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领兵远征在藏准噶尔军队。因事关重大,也放心不下青海和硕特的暧昧态度,令允禵等与青海和硕特诸台吉共同商议入藏之策。因“准噶尔、青海相互结亲年久,大将军王率兵出边,我等出兵多少,青海之若知,准噶尔之贼即可获闻”[40],到达西宁后,允禵的首要工作就是处理青海和硕特事务,拉拢与青海和硕特共同进藏。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五月十四日,允禵会见罗卜藏丹津等,并让青海和硕特举行会盟,商议出兵之事。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六月二十八日,察罕丹津奏称,罗卜藏丹津等阻其果莽喇嘛叩拜格桑嘉措,“札西巴图尔王在时,与敦莽喇嘛前代之先扎木苏不睦,留有遗言,不可与小呼毕勒罕和睦,故将谢圣主之恩,请王之安,一并停止”[41]。二十九日,罗卜藏丹津参奏察罕丹津,其内容如下:
前策妄阿喇布坦遣努和里为使,与老亲王、贝勒、贝子、公等共语:我等四厄鲁特自古以来患难与共,今一心一意而行,老亲王语:除大圣主慈恩外,我等并未同四厄鲁特同心协力,今不可与之同心协力。贝勒、贝子、公、众台吉均照老亲王与其交恶,似投汉人为妥。故如此言,仅我为之亲近,照策妄喇布坦语,凡言行迎合而行。等情寄信,遣返努和里。伊续遣之克图尔克依言称:努和里来时,我如此这般而言,今虽我在此处有备,尔等由彼处始取哈密。遣返时,达克巴喇嘛前来称,我等对尔等语,取哈密令兵启程,尔诸事有备,由我处取信。等语。其后又复遣克图尔克依,言先取哈密之事能成。今我同汉人既然近居,孤事难成,尔等自彼处派兵,前来西方,我亦从此处率兵前往,会合捕拉藏汗,取土伯特后,易于取汉地。等语。克图尔克依来后,特遣达克巴喇嘛来郡王戴青和硕齐前,圣主之大臣查问之时,谎称未来我处,而秘密返回,于是,大圣主遣派大军,而策妄喇布坦、郡王戴青和硕齐二人,堵截圣主大军,各自不能差人取信,不能于西方会师,故大圣主向西方遣使时,谕令我等青海王、贝勒、贝子、公、诸伯共同遣使,我等共遣可靠不失言之人,且郡王戴青和硕齐独差其婿阿喇布坦者,一则可靠,二则乃策妄喇布坦弟辈,伊感大圣主之恩宠少,而叛逆圣主,会同策妄喇布坦,商定一切言行等情。再思军旅之事若与此等人率兵而行,将会同征战之人,以我等为仇矣……郡王戴青和硕齐之品行,若往军中,则不可靠,若留于家,则可忧虑。[42]
上述内容显示,罗卜藏丹津历述察罕丹津与策妄阿拉布坦“通敌”合谋,先是商议“尔等自彼处派兵,前来西方,我亦从此处率兵前往,会合捕拉藏汗,取土伯特后,易于取汉地”,而后则“策妄喇布坦、郡王戴青和硕齐二人,堵截圣主大军,各自不能差人取信,不能于西方会师”,对于察罕丹津,罗卜藏丹津等认为“郡王戴青和硕齐之品行,若往军中,则不可靠,若留于家,则可忧虑”,故需请抚远大将军允禵出面处理。罗卜藏丹津为何在此时要参奏察罕丹津呢?对此,察罕丹津有自己的看法,七月初九日,察罕丹津奏报称:
先亲王札西巴图尔在时,爱我强于诸子,凡事均同我商议而行。嗣后亦如此,王罗卜藏丹津我等二人,凡事统一行之。因我贝子丹忠从中挑唆我等,如今,果莽喇嘛不叩拜小灵童,亦与我结仇外,与喇嘛并无敌,今若在罗卜藏丹津我等二人间如此挑拨,曼殊舍利大皇帝饬此大事况不能成,似违背和睦一心,一致行动之训谕。故此,伏请大将军王严责贝子丹忠如此劣迹。[43]
察罕丹津申辩称,与罗卜藏丹津关系不和是因受了丹忠的挑唆促使的。丹忠,察罕丹津侄子,曾因婚嫁问题与察罕丹津有矛盾。实际上,这只是其中的表象原因,其实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察罕丹津对罗卜藏丹津的地位构成威胁。康熙帝为实现与青海和硕特的联军进藏,曾许诺青海和硕特“约你们兄弟大力共征准贼,恢复你祖道法”[44],即恢复顾实汗时代青海和硕特对青海、西藏的统治。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九月,清朝封贝勒戴青和硕齐察罕丹津为多罗郡王[45],这引起了罗卜藏丹津的嫉恨,“查罕丹津仰蒙赐封郡王,恩施赏赉各样物件,交给西藏事务,罗布藏丹津心存妒嫉”[46]。
康熙帝深知,青海和硕特诸台吉内部不和,是徒有雄心而无实力,故而彼此内争、彷徨观望。为解决罗卜藏丹津与察罕丹津之争斗,康熙帝首先对丹忠、察罕丹津、罗卜藏丹津等给予教诲,“遂贼旺喇布坦暗中遣兵,取招地,毁尔等祖父顾实汗所立之黄教,侵土伯特之众,斩尔等骨肉拉藏汗,掳掠妇孺,特命我大军管辖,保护尔所有,清除逆贼,恢复尔等祖父顾实汗所立之黄教。尔等为进兵,往请训谕,圣主制止尔等兄弟内相互猜疑,和睦一体,一心图敌,尔等内若互相残杀,如何外以图敌?对尔等面训遣之”[47]。其次,允禵亲自迎请果莽喇嘛至西宁并加厚赏[48],以此拉拢察罕丹津。更重要的是,康熙帝给青海和硕特吃了定心丸。十二月二十三日,康熙帝指示“伊(青海和硕特)等倘以土伯特部教俱我祖辈固始汗所建,地方俱属我者,仰赖圣主大军宏威,获取地方。主子自远方前来之军,为何辛劳驻扎守招。我军理应镇守,仅我军镇守可也,伊(青海和硕特)等欲镇守,则也妥。以此,我大臣等著军士略少驻守而已。如今朕已下此谕,后日以朕未谕而翻悔则断然不可,朕于众前颁谕也”[49]。史料显示,谕旨中康熙帝希望青海和硕特蒙古继承祖业、镇守西藏[50],为表明他将恢复青海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权,“朕于众前颁谕”以表明其态度,并申明“后日以朕未谕而翻悔则断然不可”,康熙帝甚至对延信说“尔进兵平定西藏后,倘达赖喇嘛、青海之人未求留兵,大军全部撤回”[51]。
清朝通过政治诱导、武力威胁等将青海和硕特拉拢到远征西藏的队伍,完成了进藏前的重要工作。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正月,康熙帝命“抚远大将军允禵率前锋统领弘曙,移驻穆鲁斯乌苏、管理进藏军务粮饷。授都统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进藏”[52],授噶尔弼为定西将军,会同都统武格,从巴塘进发拉萨,与此同时,又令靖逆将军富宁安、征西将军祁里德分别从巴里坤、阿尔泰两路出兵,“袭击准噶尔边境之地,使贼人扰乱,可以相机行事”[53]。二月十六日,命封格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遣兵送往西藏[54]。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噶尔弼率领的南路清军,未遇准噶尔军任何抵抗,顺利进抵拉萨。由延信率领的北路清军,在当雄一带击败策零敦多布后,于九月八日率1 600人护送格桑嘉措向拉萨前进,九月十四日抵达拉萨,十五日,格桑嘉措在拉萨坐床。至是,清军胜利将在藏准噶尔军队驱逐出去,西藏正式纳入清朝的版图。
结 语
以上就围绕康熙末期清朝如何拉拢、利用青海和硕特蒙古实现“驱准保藏”事业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和探讨。1636年始,青海和硕特汗庭控制着青海、西藏及其周边藏区,成为蒙古诸部共同遵奉的格鲁派之护法者,是内陆亚洲一支重要政治势力。清廷自顺治朝始曾试图屈服或笼络青海和硕特,以待共同对抗准噶尔及喀尔喀,并顺势笼络蒙古诸部共同遵从的达赖喇嘛。对于清朝的笼络,青海和硕特一直若即若离。直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始的六世达赖喇嘛之争及之后的准噶尔远侵西藏事件的发生,清朝趋此时机,利用青海和硕特蒙古内部不和,采用政治引诱、武力威迫等手段使其屈服,并联合进军成功驱除西藏的准噶尔军队,代替青海和硕特汗庭成为达赖喇嘛的新护法者,控制西藏,将西藏纳入清朝的版图。
[1]宝音特古斯.十八世纪初期卫拉特、西藏、清朝关系研究——以“六世达赖喇嘛事件”为中心[D].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33-46.
[2]达力扎布.清太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史实考略[J].中国藏学,2008,(3):72-81.
[3]清太宗实录[Z].崇德七年冬十月已亥条.
[4]顺治帝令鄂木布卓里克图巴图鲁济农等出征喀尔喀之敕谕[A].齐木德道尔吉,吴元丰,萨那日松.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3辑)[Z].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90-92.
[5][6]齐木德道尔吉,巴根那.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Z].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729,790.
[7]刘锦.边境纠纷与清朝借助达赖喇嘛处理青海蒙古事务的开端[J].清史研究,2013,(1):95-103.
[8][10][16][25][3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Z].卷26,卷28,卷26,卷4,卷3.
[9][11][12][14][17][19][20][27][28][31][34][36][45][52][53]清圣祖实录[Z].卷287,卷180,卷182,卷187,卷227,卷236,卷241,卷278,卷263,卷266,卷277,卷279,卷281,卷287,卷287.
[13][15][18][24][26][29][30][32][37][40][42][43][47][48][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80,171-172,403,1141,1531-1532,1064,1063,1080-1081,1302,1379,1407-1408,1422,1408,1419,1442.
[21]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76.
[22]丹珠昂奔.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200-201.
[23]陈庆英等.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形象历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67.
[35][41][44][46]吴丰培.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Z].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42,52,261-263,245-246.
[38]赵珍.论康熙末年清军两次入藏的战略选择.[J].清史研究,2002,(4):98.
[39]柳陞祺.十八世纪初清政府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始末[A].柳陞祺藏学文集(上)[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161.
[50]邓锐龄.1720年率军入拉萨的清军将领——延信[A].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上)[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321.
[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8.1.
[54]平定准噶尔方略(康熙五十九年二月癸丑)[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