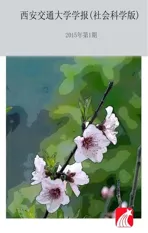上网影响个人的社会融合吗?——以陕西和广西为例
2015-02-15雷鸣
雷 鸣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710049)
使用互联网会影响个人的社会融合吗?用互联网语言来说,长期“泡”在网上会不会使人变得更“宅”?对于这一问题,媒体和大众凭借日常生活的印象更偏向给出肯定的回答。无论是“网虫”——“爱电脑胜过一切”,“屁股钉在椅子上,恨不得把电脑椅改装成便捷式马桶”①http://baike.baidu.com/view/6854.htm?fr=aladdin#1_1,还是“极客”——“些依靠计算机技术结合成的社会性人群”,“把大量社交时间花费在电脑网络上”②,都给人以离群索居或者遗世独立的印象。
仅凭漫画式的勾勒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全面地认识这个问题需要严格的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然而目前国内针对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大型社会调查较少,基于调查完成的学术论文更加稀缺,且大都聚焦在哪些因素影响个人的互联网使用上。例如祝建华、何舟的研究发现了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收入等因素对是否使用互联网会有影响[1]。郑嘉雯通过调查指出,受过良好教育、经济条件良好的城市年轻男性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使用互联网[2]。只有黄荣贵等人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3]。已有研究大多仅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没有给出深入的理论解释,也没有把这些因素纳入一个系统的解释框架中。
社会学家巴里·韦尔曼(Barry Wellman)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国际社会学界对互联网的研究经历了1990年代中期“臆想和轶事”般的分析,1990年代末期以来致力于记录互联网使用者和使用的增加,现在真正的分析应该以“更聚焦的理论驱动的计划”开始系统研究[4]。在这方面,巴里·韦尔曼、保罗·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伊斯特·哈吉泰(Eszter Hargittai)等西方社会学家都做出了有效的尝试[5-6],目前在关于互联网的社会学研究中形成了“数字不平等”、“虚拟社区”等较有影响力的理论框架[7]。如何扩大这些理论的解释力,如何更好地通过理论来解释中国居民相关的互联网使用现象,是国内研究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上网与个人社会融合的关系给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数据加以检验。
一、社会融合的概念与测量
(一)社会融合的三个层次:社会、群体、个人
社会融合是社会学诞生以后的经典研究论题之一,然而它的定义直到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没有明确的共识[8-10],这与概念本身指涉现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有关。笔者拟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社会-群体-个人”的三层次的理论框架,并将本文的研究聚焦在个人层次上。
社会学里的社会融合概念可以上溯到学科奠基人之一的迪尔凯姆,他在代表作《自杀论》中提出,较好的社会融合水平可以防止社会原因导致的自杀[11],这里的社会融合着眼的是作为整体的“社会”,而不是特定的团体或个人。我们可以把迪尔凯姆开创的社会融合研究视为在“社会”整体层次上的研究,这里的社会融合是一个宏观层次的概念,也可以译成“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
20世纪以来的社会学家逐渐把社会融合的研究对象明确到“群体”与“个人”的层次上,这些研究从个人与群体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融合,但不同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从“群体”出发,研究“群体对个人的吸引力”等内容;有的侧重从“个人”出发,研究“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中其他人的合作行为”等内容[12],这种社会融合概念也译作“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弗里德金在一篇总结性论文中肯定了这条研究路径,并进一步把社会融合定义为“使每个成员停留在群体里的强大力量的结果”[9]。这样,社会融合的内涵更加明确,测量也更具操作性。可以看出,它事实上是从层次不同但紧密相联的两个主体——群体和个人的角度来研究同一个社会过程。本文着重从个人角度出发,研究个人的社会融合现象。需要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上存在所谓“虚拟社区”[13],那么个人对虚拟社区的融合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融合。但是本文所说的社会融合,背景是与互联网无关的现实中的社会,或者说“线下”的社会。
另一方面,不管概念如何具体定义,也不管分析对象是群体还是个人,学者们对社会融合的测量一致集中在行为和态度两方面[9]——虽然在具体指标的选取上有差异。对个人层次的社会融合来说,学者们通常选取个人的群体参与行为或者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感作为具体指标,而群体层次的指标往往就是群体内个人指标的汇总,如个人行为或态度的平均值等[8]。对于本文研究的个人的社会融合情况,笔者也将从行为和态度两方面选取指标对其进行测量。
(二)个人社会融合的两个维度: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
上述国外的社会融合研究虽然都涉及到群体,但它们并未对群体性质做进一步细分,也就没有考察个人对不同性质群体的融合情况。诚然,部分研究——尤其是社会网与社会融合的研究会关注群体的结构——诸如群体规模、密度、是否存在强连带等等[14],但这些因素仅仅反映出部分群体指标的量的差异,并未意识到群体在质上的不同,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造成的不同。
中国人的社会融合情况可以用“差序格局”的模式来分析:对个人来说,社会群体没有明显的边界,以个人为中心,与他人的关系如水波纹般向外推出,距离越远,关系越薄[15]。每个人处在差序有别的群体中,对每个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不相同。按照“差序格局”的模式,构建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从家庭到整个社会的由内到外的个人所属社会群体的连续谱。理论上,这个连续谱越往外,个人对其认同感和归属感就越低,那么个人在不同群体中表现出的社会融合情况也会不一样。费孝通甚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15]。
尽管在差序格局概念的定义和中西社会的比较分析的准确程度上,学术界存在诸多不同见解,但许多学者认为,差序格局概念是中国本文社会发展出来的具有普适性的主要社会学概念,即使在现代中国社会仍具有很强的理论解释力[16]。研究个人的社会融合,理当考虑由差序格局带来的群体性质的差异造成的个人行为与态度的差异。差序格局在现实中的表现比较复杂,为了把握这种差异并初步揭示出相关规律,以下把个人所属群体划分为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这两种类型,分别考察个人对这两类群体的融合情况。
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是社会学划分群体类型的一对基本概念。初级群体一般是指类似家庭纽带关系的群体,成员之间面对面的互动更多,人们在初级群体中可以大量地自由交往,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与情感,也从中获得个人情感的满足。对中国人来说,个人从初级群体中获得的“人情”资源也会给个人带来实际利益的好处[17]。
次级群体是为了达到特殊目标而特别设计的群体,人们最熟悉的次级群体就是各种组织——工厂、学校、政府机构等等。次级群体在现代社会中很普遍,人们在次级群体中相对更少地展现个性与投入感情,更多的是从中获得个人利益的满足。
在依据差序格局划分的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群体的连续谱中,显然初级群体处于离个人更近的内层,次级群体处于离个人更远的外层,那么个人对这两类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应该是差序有别的。因此,个人对这两类群体的社会融合情况也应该是不一样的。下文将考虑个人在这两类不同群体中的表现,从而分析上网对个人社会融合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关于上网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它基于一个对基本事实的推论:电视的出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人们把原本用在听广播、看电影、看杂志的时间用来看电视了。那么,互联网的出现很可能会使历史重演,人们把原本花在其它社会生活上的时间用来上网了。这一观点就是迪马吉奥等人概括的“时间替代”(time replace)机制[18]。有许多研究证实了这一机制。比如,柯兰特等人通过一项在匹兹堡进行的追踪调查发现:上网会减少人们与家人的沟通,减少社会交往,增加人们的孤独感[19]。罗宾森等人通过一项跨国研究也发现上网会显著减少人们与家人的交谈和户外的社交活动[20]。聂和厄布林的一个大型调查也发现,使用互联网会减少人们线下的社会活动[21]。上述“时间替代”现象说明上网是不利于个人的社会融合的。
也有学者从其它角度对上述研究提出了质疑。林南就认为,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交流工具,人们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是可以扩展社会交往的[22]。罗宾森等人在另一项全国调查中发现,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交往具有积极作用[23]。纽曼等人则指出,不能简单地比较上网与不上网这两类群体,而忽略上网群体的内部差异。一个互联网使用的新手跟老网民的上网行为是很不一样的,新手由于经验和技术的限制而不会使用互联网实现与他人的社会联系[24]。还有一些研究发现上网会扩大人们的社会网、增强人们的普遍信任水平[25]。这些研究说明,上网对个人的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是比较复杂的,它也可以是有利于个人的社会融合的。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看似相反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也并非完全矛盾。本文将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综合以上研究的成果,建构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上网与社会融合关系的理论。
首先,互联网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它的确可以被用来促进人际交流,推动线下的社会交往,加强个人的社会融合。并且如前文所述,“重度”的互联网使用群体比“轻度”的互联网使用群体上网经验更丰富,技术更娴熟,也更会利用互联网实现人际互动,所以有:
假设1:上网会加强个人的社会融合,并且这一点在更多地使用互联网的群体身上表现得更明显。
其次,随着花费在网上的时间的增加,“时间替代”现象确实会出现,人们需要更合理地分配自己线下的时间,那么在对待不同群体时,行为上会做出一定的选择,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这种选择,既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为了阐释这一点,需要明确西方人和中国人看待不同社会群体的理念差异。
对西方人来说,社会整体文化氛围强调利益与规则的普适与公平,强调群体组织的成员资格与身份归属,尊重和认可蕴含在成员资格中的权、责、利,资源的获得和运作往往通过正式组织等次级群体来实现[26],因此,他们相对中国人来说会更加认同次级群体,而对初级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相对较弱。从前文引述的研究可以看出,互联网会有利于他们扩大社交规模,增强普遍信任水平,而减少与家人和邻居的交流。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上网相对更有可能增强他们对次级群体的融入。
中国社会的情况与西方不同,对中国人来说,从小就生活在“差序格局”的文化传统下,强调对人际圈层“内”与“外”的区别对待,因此会更加注重对初级群体的融入。并且如前文所述,中国人更有可能从初级群体中获得“人情”资源进而获得实际利益,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也应当更注重融入初级群体。因此,不论是受文化传统影响,还是出于实际利益考虑,中国人都应该是更认同初级群体,也更注重维持对初级群体的融合,所以有:
假设2:上网强化了个人对初级群体的融合,尤其对更多地使用互联网的群体来说,这种强化作用更明显。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2010年“中国西部社会变迁调查”(Chinese Survey of Social Change,简称CSSC)的数据,调查总体是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18岁以上城乡居民。本次调查根据各省非农人口比重将样本框中的县/区级单位划分为“城市层”单位和“农村层”单位,然后分别在每一层中根据人口数进行多阶段的PPS抽样,最终包括样本10946份。详细调查结果参见《中国西部调查报告》[27]。CSSC只在陕西和广西二省(区)对个人上网时间进行了调查,样本共计2145份(其中陕西为1146份,广西为999份),考虑到部分样本的变量有缺失值,最终进入模型的样本量为1906。
(一)社会融合指标
本文拟沿袭以往研究的思路,从个体的行为与态度两方面来测量个人的社会融合。从个体行为来看,个人与他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是一种典型的反映其社会融合情况的行为[28],社会交往活动越频繁,代表其社会融入程度越深。然而个人在社会中的社会交往活动形形色色,选取何种活动最具代表性呢?请客吃饭在中国是一种跨越不同地域和群体,最具广泛参与性的社会交往活动,是测量社会融合行为的最佳指标[29]。因此,本文采用请人就餐频率测量个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根据被访者对过去一年中请人就餐情况的回答,把它的频率按照从低到高都分为三类,依次是从不、较少、经常。如表1所示,样本中从不请人就餐的接近1/5,较少请人就餐的约占2/3,经常请人就餐的接近15%。
请人就餐这一行为可以用来测量社会交往活动,那么一起就餐的对象则可以用来测量社会交往的对象,它可以反映社会融合的群体类型。CSSC2010在调查被访者就餐情况的同时,也调查了被访者一起就餐的对象,具体来说,是让被访者回答一起就餐的人当中的熟人比例,本文认为该变量可用来测量人们社交对象中初级群体的比例。简单来说,与被访者一起就餐的人中,熟人比例高的意味着交往对象中被访者所属初级群体成员比例高,熟人比例低的意味着交往对象中被访者所属次级群体成员比例高。按此标准,本文把样本的交往对象中的熟人比例分为低、中、高三类,各占约40%、48%、12%。
另一方面,个体的态度也是衡量其社会融合的重要指标。弗里德金曾指出,对群体的归属感可以作为衡量个体社会融合程度的一个态度方面的指标[9]。本文采用这一概念来作为测量个体社会融合的态度指标。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出个人对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的态度,本研究分别选取了两个主观变量来测量个人对群体的归属感。
对周围的事情的态度可以反映个人对初级群体的归属感。调查测量了个人主观的对自身周围事情的态度,给出从1到5的5个分数,1为“很不感兴趣”,5为“很感兴趣”,由被访者自己判定。依据程度高低将这5个分值进行合并,分为弱、中、强三类,分别占到样本量的大约42%、19%、39%。
对本地发展的态度可以反映个人对次级群体的归属感。调查也测量了个人主观上对本地发展的态度,同样给出从1到5的5个分数,1为“很不愿尽力”,5为“很愿尽力”,也是由被访者自己判定。笔者依据程度高低也将这5个分值进行了合并,分为弱、中、强三类,分别占到样本量的大约10%、76%、14%。
(二)核心自变量
CSSC2010的调查询问了被访者每周上网的时间,单位为小时。前文指出,上网可以加深个人的社会融合,而且互联网的“重度”使用者和“轻度”使用者的社会融合情况也不一样。如表1所示,样本平均每周的上网时间接近5小时。另外,该变量的最小值是0,也就是完全不上网,最大值达到112小时,上网行为表现得非常频繁。这样,周上网时间这个变量就可以反映出从完全不上网到非常频繁地上网这一系列程度不断加深的行为对因变量的影响。

表1 变量的均值、百分比、标准差(样本量=1906)
(三)控制变量
诸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等特征,是社会学划分群体的基本标准,而这些基本特征都会影响个人的社会融合情况。因此,选择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五个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如表1所示,样本的平均年龄将近44岁,标准差接近15。样本中男性占55%,略多于女性。样本的婚姻状况包括已婚(含同居)与未婚(含离异、丧偶)两种情况,其中已婚者占80%多。本文用受教育年限来测量样本的受教育程度,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年多。本文的收入是指被访者的年总收入,样本的平均年收入为1.2万元。
四、模型结果分析
本文为了检验理论假设,分别建立了四个模型,因变量分别为个人的社会融合行为变化情况、社会融合对象中初级群体比例变化情况、个人对初级群体的归属感变化情况、个人对次级群体的归属感变化情况,依据前文所述的指标进行测量。由于以上四个因变量经过处理均为定序变量,所以笔者构建了四个ologit模型。所有模型的核心自变量均为每周上网时间,控制变量也相同。同时,在建模过程中对样本根据不同省份的居民人口比例进行了加权处理。结果见表2,其中,第1列报告的结果是自变量名称,第2列报告的结果是模型中自变量的系数,本文同时对各系数进行了显著性检验。下文将详细解释表2中的模型结果。

表2 上网时间对社会融合的影响
(一)上网与社会融合行为
在模型1中,自变量“周上网时间”的系数为正值,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这充分说明,个人的社会融合行为的发生频率与其上网时间成正比,上网确实会对个人的社会融合产生影响,上网会促进个人的社会融合行为,从而加深个人的社会融合。同时还可以看出,随着每周上网时间的延长,请客行为也愈加频繁,这说明,互联网的“重度”使用者和“轻度”使用者在行为表现上确有不同——越是更多地使用互联网,个人的社会融合行为就越频繁。这些结果都支持了假设1。由模型1初步可以证实,上网会对个人的社会融合产生正向影响。
(二)上网与个人对初级群体的融合行为
在模型2中,自变量“周上网时间”的系数也为正值,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可见,个人上网时间越长,一起就餐对象中的熟人比例就越高。前文中曾经解释过,这种熟人比例的提高意味着与初级群体中的成员交往程度在加深,个人对初级群体的融入程度相对在提高,上网对初级群体融合行为的强化作用得到了体现,假设2得到了部分证实。
(三)上网与个人对初级群体的归属感
社会融合不仅仅表现在行为上,也表现在态度上,模型3就是用来考察上网时间与个人对初级群体的归属感的关系,从态度上分析个人对初级群体的融合情况。它的自变量“周上网时间”的系数也为正值,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个人上网时间越长,越认同“只对周围的事情感兴趣”,也就是对初级群体的归属感越来越强。上网对初级群体融合态度的强化作用也得到了体现,进一步支持了假设2的结论。
(四)上网与个人对次级群体的归属感
不同于行为,人的态度可以表现为两重性,不同的态度可以共存于人的主观认知中。因此,个人对初级群体归属感的增强并不必然能推论出个人对次级群体归属感的变化情况。模型4专门考察了上网时间与个人对次级群体的归属感的关系,从态度上分析个人对次级群体的融合情况。它的自变量“周上网时间”的系数为负值,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个人上网时间越长,越不认同“愿意为本地发展尽力”,也就是对次级群体的归属感越来越弱。这从方面验证了上网对初级群体融合态度的强化作用,再一次支持了假设2的结论。
综合以上结果,上网会促进个人的社会融合行为,上网时间的延长会强化个人对初级群体的融合,这一点在行为和态度两方面都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从表2的结果也可以看出,年龄与个人社会融合行为的负相关效应非常明显;男性、已婚人员的社会融合行为更频繁;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对个人的社会融合均有正向影响。
五、总结
互联网在我国日益普及,其使用群体的规模也日益扩大,无论是发挥积极意义上的新兴人际沟通方式的作用,还是预防消极意义上的所谓“网瘾”,都需要我们对上网与社会融合的关系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本文聚焦于个人层次的社会融合,分析了互联网使用时间对个人的社会融合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上网对个人的社会融合确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上网程度的加深而加深。具体地说,上网会促进个人社会融合行为的增加,上网程度越深,社会融合行为增加地越明显。
第二,个人的上网行为对其所在的不同社会群体融合情况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本文把社会群体划分为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结果发现,随着上网时间延长,“时间替代”机制会发挥作用,人们将对融合对象做出选择,把有限的“线下”的时间更多地分配给某一类群体。本文着重指出,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群体归属感是一个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差序格局”结构,并且中国社会中人们也更多地依赖初级群体获得所需资源,所以,中国人在结构约束下(这里主要是时间约束)会更注重对初级群体的融合。由此可以推出,个人上网程度的加深会强化其融入初级群体的程度,本文从行为和态度两方面证实了这一点。这也提示我们,研究个人的行为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第三,前文虽然初步得出了结论,但却不能断定上网对社会融合的影响就一定是积极作用。社会网理论奠基人之一的格兰诺维特认为,与自己人际关系强度较低的人(往往是次级群体中的成员)的交往往往可以使个人获得异质性的稀缺资源,并带来收益[30]。同时,国内有关研究也表明,人们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之后,会倾向于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与外界建立相对更宽泛的联系,以谋求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对次级群体的社会融合,有其不能取代的作用,它可以代表一种更加深入的社会融合。上网在强化了个人对初期群体融入的同时,也就相使人弱化了对次级群体的融入,对这一点需要有清楚的认识。
本研究在得出以上结论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仅仅用上网时间来测量互联网使用行为,使得对上网影响个人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缺乏深入的探讨。弥补上述不足,是笔者后续研究的方向。
[1] 祝建华,何舟.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现状与前景:2000年京、穗、港比较研究[J].新闻大学,2002(夏):22-32.
[2] 郑嘉雯.中国“数码不平等”调查:互联网使用的社会与人口学特征[J].新闻大学,2012(6):10-19.
[3] 黄荣贵,骆天钰,桂勇.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一项基于上网活动的实证研究[J].江海学刊,2013(1):227-233.
[4] WELLMAN B.The three ages of internet studies:ten,five,and zero years ago[J].New Media and Society,2004,6(1):123-129.
[5]WELLMAN B,JANET S,DIMITRINA D,LAURA G,MILENA G,CAROLINE H.Computer networks as social networks:collaborative work,telework,and virtual community[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6,22:213-238.
[6] DIMAGGIO P,BART B.Make money surfing the web?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earnings of U.S.worker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8,73:227-250.
[7] 黄佩,杨伯溆,仝海威.数字鸿沟中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探讨:以学生家庭背景与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关系为例[J].青年研究,2008(7):16-23.
[8] BOLLEN KA,HOYLE RH.Perceived cohesion: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J].Social.Forces,1990,69:479-504.
[9] FRIEDKIN N.Social Cohes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4,30:409-425.
[10] MOODY J,WHITE DR.Structual cohesion and embeddedness:a hierarchical concept of social group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3,68:103-127.
[11] DURKHEIM E.Suicide[M].London:Routledge,1951.
[12] FESTINGER L,SCHACHTER S,BACK KW.Social Pressures in Informal Groups:A Study of Human Factors in Housing[M].New York:Harper,1950.
[13] WELLMAN B.Effects of mass media of communication[M]//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MA:Addison-Wesley,2001:77-195.
[14] BURT RS.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M].Cambridge,MA:Harvard Univ.Press,1992.
[15] 费孝通.差序格局[M]//费孝通.费孝通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16] 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31-142.
[17] BIAN Y J.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Indirect Ties,Network Bridges,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7,62:366-385.
[18]DIMAGGIO P,ESZTER H,RUSSELL N,JOHN PR.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1,27:307-336.
[19] KRAUT R,PATTERSON M,LUNDMARK V,KIESLER S,MUKOPHADHYAY T,SCHERLISW.Internet paradox:A so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Am.Psychol.1998,53:1011-31.
[20] ROBINSON P,GODBEY G.Time for Life.State College[M].PA:Penn State Univ.Press,1999:.
[21] NIE NH,LUTZ E.Internet and Society:A Preliminary Report[J].It&Society,2002,Summer:275-283.
[22] LIN N.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NY:Cambridge Univ.Press,2001:.
[23] ROBINSON JP,BARTH K,KOHUT A.Personal computers,mass media,and use of time[J].Soc.Sci.Computer Rev.1997,15:65-82.
[24] NEUMAN WR,O'DONNELL SR,SCHNEIDER SM.The Web's next wave:a field study of Internet diffusion and use patterns[M].Ms.,MIT Media Lab,1996:.
[25]HAMPTON K,WELLMAN B.Examining community in the digital neighborhood:early results from Canada's wired suburb[M]//Dig-ital Cities:Experiences,Technologie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Heidelberg,Germany:Springer-Verlag.2000:475-92.
[26] 边燕杰,郝明松.二重社会网络及其分布的中英比较[J].社会学研究,2013(2):78-97.
[27] 边燕杰等.中国西部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4.
[28] 边燕杰,肖阳.中英居民主观幸福感比较[J].社会学研究,2014(2):22-42.
[29] 边燕杰.中国城市中的关系资本与饮食社交[J].开放时代,2004(2):93-107.
[30] GRANOVTTER M.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1360-1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