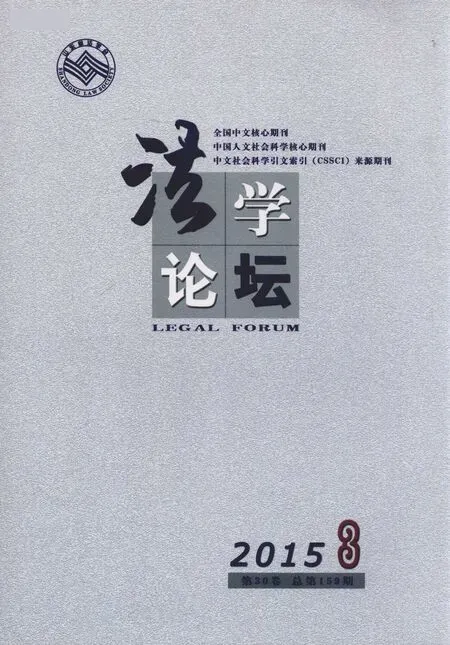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建构与法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2015-02-15钱锦宇
钱锦宇
(西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3)
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建构与法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钱锦宇
(西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3)
面对21世纪“新战国时代”的诸多挑战,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仍然是各国首要的政治主题。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离不开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法家思想文化的支撑。法家思想中“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义、“缘法而治、以法为教”的法治主义和“禁胜于身、立公弃私”的权力制约观等合理内核,能够助推“四个全面”这一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先秦法家思想在21世纪的复兴,绝不是未经批判地在当下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结构中嵌入先秦法家的全部观念和重述其所有的政治法律主张,而应当是对先秦法家思想进行批判性反思、提炼,进而实现三个转换,即由先秦法家的“弱民”转换为现代政治的“强民”;由先秦法家的“君主立法”转换为现代政治的民主立法、以宪护法;由先秦法家的“天道”转换为现代政治的人权。
新法家;新战国时代;国家治理;依法治国
从21世纪的国际局势来看,中国仍然处于一个“新战国时代”。在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看来,21世纪的国际关系,就是一个“国际无政府状态”。而“中国‘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生存的最好方式是取得亚洲地区霸权’……长远而言,美中将进行‘一场激烈的安全竞争’。”*[美]阿米塔伊·埃齐奥尼:《中美或有一战,其实只是提醒》,乔恒译,载于《环球时报》2015年3月31日。尽管米尔斯海默对中国和平崛起与发展的战略定位视而不见并妄加臆测,但是他关于当下的国际关系态势的判断,却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在这种以“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为特征的21世纪的“新战国时代”中,中国政治的主题和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并未改变,仍然是国家的政治生存和发展。这就需要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当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参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内生视角上看,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路径的中国政治治理现代性的建构,是中国剧烈社会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而从外生视角上看,中国政治治理现代性的建构,也是在以“一超多强”这种力量格局为特征的“新战国时代”中,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建构中国政治治理的现代性,并不是简单地把中国政治支配的关键词从传统的“统治”替换成时兴的“治理”,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话语和修辞的替换,而是需要建构一种能够在新时期国际竞争结构中支撑这种政治话语的思想文化和观念,以及一套相对完整的相关政治制度。
而当下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在21世纪的“新战国时代”中,支撑中国政治治理现代性建构的思想文化观念,除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扬儒家思想精髓和借鉴西方优秀思想观念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智识资源可供资用?这种(些)智识资源在当下又需要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相以支撑政治治理现代性的建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将首先分析在“新战国时代”中建构中国政治治理现代性,应当重视、重新提炼和转化先秦法家思想的原因,进而论述法家思想支撑中国政治治理现代性建构所必须的理论转出,并阐发法家思想的新内涵。
一、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及其当下意义
(一)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核
政治治理的现代化推进,需要思想文化方面的智识资源的支撑。习近平曾深刻地指出:“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201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此观点,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毫无疑问,“新战国时代”的政治现实,使得法家思想在21世纪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仍然具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法家思想的核心要旨就是通过“富(国)强(兵)”之道以实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那么,法家开出的实现“富强”之道是什么?就是“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义、“缘法而治、以法为教”的法治主义和“禁胜于身、立公弃私”的权力制约观。
首先,“富国强兵”是先秦法家思想中的核心战略目标。任何思想文化,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反映着时代的特征和实践的面相。春秋战国“强国务兼并,弱国务力守”*出自《商君书·开塞第七》。的时代特征,客观上需要一套能够使国家得以在剧烈政治竞争和军事斗争中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学说理论体系。面对这种社会需求,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以性善论为出发点,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政以德”、“以礼治国”的系统政治主张,并游说列国,期望能够以此救世,通过“礼制”和“正名”来重塑春秋战国的社会秩序,回复到“礼崩乐坏”之前的“礼治”之下的旧有政治利益格局。但是儒家“法先王”的因袭观念,以及“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观念,无法有效地把国家塑造成能够适应战国时代的以“优胜劣汰”和“弱肉强食”为原则的“丛林法则”。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家的思想核心是“退”,是恢复到“礼崩乐坏”之前“持之以义”的政治状态,把政治制度设计的重点放在了“明明德”和“化性起伪”上了,试图通过正名而使人安分守己、各守其道。相反,法家思想的核心就是“进”。从其起源时开始,法家思想就有着明确的战略定位,即富国强兵。如何谋求富国强兵,可以说是法家创建其政治思想和理论主张的一个不争的逻辑前提。唯有实现富国强兵,“持之以力”,国家才能在“丛林法则”的支配下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作为法家思想的奠基人,管仲就明确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癝。国多财则远者来,地僻举则民留处。仓癝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出自《管子·牧民》。因此,战国时代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国家富强。《韩非子》开篇所讨论的,也是富国强兵和存亡之道。而当下中国,在执政党提出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质内涵,就是国家富强兴盛、人民安居乐业。这种战略目标的定位,反映出执政党基于21世纪“新战国时代”的特征而做出的判断和选择,也体现出一切文明时代中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
其次,先秦法家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改革特征。儒家为了实现其政治思想所设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礼治”主义。要实现“礼治”,则需要“法先王”*出自《孟子·离娄上》。,要求统治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认为周礼是完美融会贯通天理与人情的最高规范。后世统治者必须以先王的成法为典范,遵守旧有制度,即所谓“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出自《诗·大雅·假乐》。然而这种保守的政治思想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战国时代诸国面临的生存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相反,实现国家富强这一战略定位,先秦法家无一不将其理论焦点集中于改革变法之上,并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理念。为了阻扰商鞅的改革,秦国保守派大臣甘龙指出:“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出自《商君书·更法第一》。则恐遭天下之人非议。而杜挚强调:“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出自《商君书·更法第一》。商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变过不必法古。”*同①。因此,古代君主都是“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同①。韩非子也认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出自《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应当“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在法家看来,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必须以政治现实为场域。政治情势变更,就必须随之改革变法,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出自《吕氏春秋·察今》。可见,在法家看来,只要能够强国利民,就可以不必因袭旧制陈规。在这种改革理念的指导下,法家游说于列国并直接推动政治改革。如管仲在齐国实施改革,建乡设邑、确立职业的世袭制、打破井田,承认私田的合法性、“禄贤能”以打破贵族对于官职的垄断,最终使齐国首先称霸于春秋。子产在郑国执理朝政时,最重要的改革就是铸刑书于鼎,开启了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打破了贵族对于法律的垄断。李悝以魏文侯相的身份主持改革,颁布“平籴法”,并“集诸国之法典,制法经六篇”,为后世中国的法典化奠定了基础。法家吴起在楚国为相,按照法家思想推行改革,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推行“强兵”政策,强调“明法审令”的法治。而商鞅则在秦国推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如在修改和补充《法经》的基础上颁布《秦律》、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取消世卿世禄制度、废除井田并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郡县制、按户征收税负等。改革变法的结果,则是使得秦国一跃成为当时最为强盛的国家。可以说,改革变法的理念贯穿于法家思想的整个体系,法家思想呈现着鲜明的改革品性。毫无疑问,在法家看来,改革变法是时代潮流,是推进富国强兵这一战略目标的根本动力。先秦法家的政治实践已经证明,以改革求发展,是适应战国时代的必然要求,而改革本身也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根本动力。
再次,法家对“法治主义”予以高度重视。由于儒家将周礼视为人类实施政治治理的最为经典的规则系统,因此儒家在设计其治国方略时,往往强调国家治理必须依据礼,建构了所谓“为国以礼”为核心、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内容的礼治主义。究其实质,礼实际上是通过正名来实现政治利益的分配及其秩序。在礼治主义的框架内,儒家提倡“以德为政”、“以德服人”,主张在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中,道德先于法律,统治者应当重视伦理道德的规范功能,实现“德主刑辅”、“以礼去刑”。然而,法家却提出以“缘法而治”、“一断于法”和“以法为教”的法治主义。管仲明确指出,但凡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在“威不两措,政不二门”的同时,实施“以法治国”。*出自《管子·明法》。因为,法律是“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是“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法家认为,法律的功能首先就在于“禁恶止乱”,“定纷止争”,通过赏功罚罪来实现“君臣上下”的政治统治秩序。因此,法家奉行“缘法而治”和“一断于法”的法治主义,视法律为公义的体现,主张法治破除私意。“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同⑥。可见,“以法治国”所要求的奉公法、废私意,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根本道路。韩非子深刻地指出:“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出自《韩非子·有度》。而在当下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已经上升到执政党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的高度。能否推进依法治国,不仅关系到改革能否得以顺利展开,关系到改革的红利能否惠及全体国民、防止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的制度性保障。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下的法治主义道路的建构。已有学者指出法家助推依法治国的可能性,即:“当下依法治国理念和实践,有必要更多地接续新法家的理路,因为当下依法治国与新法家的关怀、旨趣,具有很大的共通性。”*喻中:《新法家助推依法治国》,载《环球时报》2014年9月3日。
最后,法家主张对公权力予以制约。儒家倡导礼治主义,要求宗法等级的高低与掌握政治权力的多寡成正向关系;儒家遵循德治主义,要求塑造出能够克己复礼、躬身践行道德规则并以此实现道德教化的统治者。因此,在政治治理过程中,人的因素要比法的因素更为重要。孔子就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出自《论语·中庸》。荀子更进一步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出自《荀子·君道篇第十二》。荀子认为,从人类历史发展上看,“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出自《荀子·王制第九》。然而,法家则强调“治民无常,唯法为治”*出自《韩非子·心度》。君臣上下都必须遵守法律。一方面,“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出自《韩非子·饰邪第十九》。而“私心”本身正是乱法乱治的根源,因此,必须以法律这种“至公大正之制”来达到废除私心和私欲。“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出自《韩非子·诡使第四十五》。另一方面,虽然法家思想最终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可以超越于法律而肆意妄行。《管子》曰:“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出自《管子·法法》。慎道提出了“立公弃私”说,主张“君主必须按照代表‘公义’的法令行事,即‘不得背法而专制’”。*段秋关:《新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在慎道看来,法律代表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公义,而君主和人臣的个人利益称为私,公义大于私欲,因此,君主个人的私欲应当屈居于作为公义的法律之下。而法律的功能就在于规制和杜绝包括君主在内的个人私欲。唯有这样,国家才能得以大治。先秦法家为现代政治给出的启示是,对于统治者和统治者的代表,都需予以制约。确立法律的至上性地位,实现对法律的普遍遵守,以法律的形式来控制统治者及其代表的权力,使其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运行,是当下中国治国理政战略布局的关键点所在,也是统治者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而先秦法家的理论主张和政治实践,对于当下的中国政治治理现代性的建构而言,是具有巨大镜鉴意义的,值得深入发掘。
(二)助推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法家思想内核的当下意义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考察时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在2015年2月2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的开班仪式上,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是服务于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四个全面”的时代性,在于它是基于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富强、民主和文明的政治现实而提出;其现实性,则在于要推动解决中国当下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其正当性,则源自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和高度认同;其科学性,则在于它是执政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政治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制定,反映了推进我国政治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有效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又有助于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上永远不存在“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现代化在内的“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从历史传统出发,不能不从古典传统中汲取灵魂。”*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下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因此,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不仅需要有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思想体系的政治思想的指导,也需要有中国传统思想以资镜鉴。而法家思想的核心论题不仅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存在结构相似性,而且法家思想中的合理内核,能够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提供智识支持和历史镜鉴。
首先,先秦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87页。和“立公弃私”的法治观,能够为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智识支持和历史镜鉴。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法律具有绝对权威、至上地位和据此产生的支配性效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就是强调宪法和法律在社会治权结构中的绝对性支配地位,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宪法和法律为最终行动准绳。法治能否实现,关键是政府权威服从于法律的权威,任何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和社会团体和政党(包括执政党),都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任何公民(包括国家机关公职人员)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反对存在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行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柏拉图就曾在其晚年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在法律享有绝对权威这一点上,先秦法家思想和西方主流哲学是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的。先秦法家思想文化的核心主张,就是“以法治国”,“任法而治”。在先秦法家看来,法治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就内在地要求对统治权力必须予以必要的法律约束和控制。任何人,包括君主,都必须应当服从作为公义的法律,因为“令尊于君”,所以“不为君欲变其令”*出自《管子·法法》。,最终实现“立公弃私”。而当下执政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重申执政党的行动不能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强调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些主张都与法家的基本思想存在实质上的共通性。与此同时,法家强调法律的明确性、稳定性(商鞅指出“立法,必使明白易知”*出自《商君书·定分》。,韩非子强调法治必须“易见”、“易知”和“易为”*出自《韩非子·用人第二十七》。)和维护法律的统一(“法莫如一而固”*出自《韩非子·五蠹》。)等主张,对于当下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法治建设目标,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法家的改革发展观,能够为当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智识支持和历史镜鉴。改革发展是当下中国政治的首要主题。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和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动力。当下中国正在处于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着无限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国际地缘政治斗争日益复杂、国内地区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仍未彻底打破、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诸多约束、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及改革红利并未遍及全民等,都制约着中国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从而制约着“中国梦”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反思和重视先秦法家“不法古、不循今”、“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改革变法观。先秦法家的变法实践辨明,为了实现“国富”、“兵强”和“统一天下”的政治战略目标,必须凭借政治自信,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冲破思想观念和体制上的束缚,打破利益固化状态,全面深化改革。邓小平早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要以“三个有利于”来作为判断工作得失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政治判断,无疑符合并发展了先秦法家关于“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改革变法主张。而当下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也应该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先秦法家的改革观,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
二、21世纪法家思想复兴必需的创造性转换
需要注意的是,先秦法家思想在21世纪的复兴,绝不是未经批判地在当下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结构中嵌入先秦法家的全部观念和重述其所有的政治法律主张,而应当是对先秦法家思想进行批判性反思、提炼和转换。正如程燎原教授所言:“不仅力求完成对外来法的现代性思想的消化与融摄,而且试图展示‘中国式的法的现代性’的思想结构与理论原理。”*程燎原:《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载于《中国法学》2008年第05期。在中国当下的政治治理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以及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自我认同过程中,必须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揭示或发展出其中能够助推当下政治治理现代性建构的合理内涵。这种基于批判性继承的发展,就是“转换”。可见,“转换”蕴含着创造性发展的内涵和特征。而与时俱进正是法家思想的核心精神和品性。法家思想文化只有通过理论“转换”,才可能真正参与当下中国的政治文化认同、推动中国政治治理的现代化。
笔者认为,法家思想文化在21世纪的复兴,应当推动三个理念的转换。
(一)由先秦法家的“弱民”转换为现代政治的“强民”
在先秦法家看来,国家要得以大治,必须实现“法”(法律)、“势”(权力)和“术”(权谋)的统一。法家本质上是以君权为核心的一套维护君主统治利益的思想学说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主张就是维护“君臣上下”的统治秩序。法家认为,法律是统治臣民的首要工具,而法治要得以实现,君主必须“抱法处势”,垄断政治支配权力,通过权谋之术来实施统治,即所谓的“君尊则令行”。*出自《商君书·君臣第二十三》。君主统治臣民的两个基本方式,就是通过法律来“赏功”和“罚罪”。
之所以把通过法律实施的“赏功”和“罚罪”作为君主施行政治统治,是因为法家对于人性的解读。法家认为,人类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人的这种本性就表现为“好利恶害”、“好生恶死”、“好逸恶劳”、“好富恶贫”、“好贵恶贱”、“好赏恶罚”。“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出自《管子·形式解第六十四》。商鞅也指出:“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出自《商君书·错法第九》。而人的这种好恶本性,就是君主制定法律(实施赏罚)的依据。在法家看来,君主的法律要得以实施,进而维护其统治秩序和实现其统治利益,其途径就在于“弱民”。在商鞅的理论视域中,人民弱则国家强,“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则志强。”*出自《商君书·弱民第二十》。国家务必要使人民处于“辱”(卑贱)、“弱”(怯懦)和“贫”(贫困)的状态,只有这样,人民才会为了爵位和赏赐而去勇于征战,为了脱贫而努力农耕蓄牧,并敬畏政府、服从法令的权威。*“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参见《商君书·弱民第二十》。而一旦人民有私人的荣誉和财富,就会轻视官吏、鄙视封赏,不遵守法律和怯于征战。这就无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法家认为要使人民不断处于弱势状态,力图使人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而实现“弱民”的有效方式,就是以法治国。必须用刑罚来威慑人民守法,用封赏来激励人民作战。
与此不同的是,21世纪政治文明国家在推动其国家政治发展、实现其政治战略目的过程中,无不以“强民”为其必要条件和行动归宿。无论是西方的“社会契约”政治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都将“人民主权”和“多数人的统治”奉为基本政治理念,并承认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观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在民主政治理念的塑造下,国家和人民并不像先秦法家所认为的那样存在根本上的对立和消长关系,而是一种正向的互动关系。这种正向的互动关系更多的时候表现为民强则国强,国愈强则民愈强;民弱则国弱,国愈弱则民愈弱。而从英美国家的发展史和中国的近现代史来看,民强国强的这种关系,清晰可辨。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借鉴西方的主流民主理论,批判性吸收传统儒家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特征的民本学说,强调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根本上是实现“强民”,也要依赖于“强民”。而当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以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都为“强民”国家的缔造提供来自于传统文化的智识支持。
(二)由先秦法家的“君主立法”转换为现代政治的民主立法、以宪护法
尽管先秦法家认为要实现“垂法而治”,必须以法律的君臣共守为条件,尤其是君主本身必须遵守法律,因为法律是至公大正的制度,即使君主的私欲实现也不能超出法律的框架,而且“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主更需要以身作则服从于法律的权威,所谓“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出自《管子·法法第十六》。但是,在梁启超看来,先秦“法家最大缺点,在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换言之,先秦法家将规制万物的法律的制定权赋予了君主,这种立法权的归属,不仅是因为法家维护君主统治秩序和利益和必然要求,也是法家有关民智未开的理论假定使然。在法家看来,作为被统治者的人民犹如婴儿,“民智之不可用也,犹婴儿之心也……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出自《韩非子·显学篇第五十》。因此,在先秦法家看来,人民必须“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与此同时,君主循天道而立法,将法律“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予百姓者也”。*出自《韩非子·难三第三十八》。事实上,使人民无权参与立法,是法家实现政治统治的一个核心要求,这就是“务在弱民”。法家主张“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民之所乐民强”。*出自《商君书·弱民第二十》。因此,如果臣民享有立法权,则必然其所制定的法律符合民众的利益而为民所乐,则君主必定无法实现“政作民之所恶”所实现的“民弱”。正是因为如此,法家才强调君主享有立法大权。但是法家的理论主张存在一个内在逻辑错误:既然君主可以立法,则自然也可以废法,后世之君也可以废除前世君主的法律。这样一来,则法家主张“抱法以待,则千世治而一世乱”,就在逻辑上,也在事实上无法成立。*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可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由是观之,先秦法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设计出使法律必然得以实施的方案,即“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出自《管子·七法第六》。
而自近代以来,民主逐渐成为了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潮流。民主理念所力求塑造的,是一种以主权在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要义的政治支配模式。民主要求以人人平等为原则,主张所有人都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即通过选举人民的代表)参与国家的治权结构,共同决定国家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事务。无论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主张的“主权在民”和“民有、民治、民享”,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民主的理念。胡锦涛强调:“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习近平则深刻指出:“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始终牢记宗旨、牢记责任,自觉把行使权力的过程作为为人民服务的过程,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做到为民用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127页。在以人民为主体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民主立法,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立法平台,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在执政党的领导下使人民的意志转换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并以此为政治治理的根本性制度依据。从根子上消解先秦法家无法在立法问题上正本清源的难题。与此同时,仅强调从:“君主立法”换为“民主立法”,对于现代政治发展而言,并不能建构一套完善的法律治理体系。究其原因,就在于还需要创制一个制度,解决先秦法家“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的困境,使得“以法治国”这种治理模式成为必然的政治治理模式的。而西方国家成功的宪法实施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西方法治经验表明,需要从根本法的立场确立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保障“以法治国”的治理模式不受动摇。正是因为如此,习近平才高度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三)由先秦法家的“天道”转换为现代政治的人权
先秦法家在其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儒家的“正名定分”论、墨家的“一同天下”观,以及道家“法自然”而“无为”的主张,进而嬗变汇合为统一体系。*此观点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法家主张“垂法为治”,而凭以治世的法律,必须具备“刑德”。换言之,法律必须接受某些外在的道德性约束。先秦法家秉持道家的“法自然”观念,提出“循天道”而立法的主张。先秦法家的“天”出于老子“自然”之天,“人生于天地之间,与自然界形成一种适应和共处的关系,并称之为天道。”*段秋关:《新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法家将“天道”等同于“公理”,并视为法的本源,即“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乡,或以治国,或以治天下。”*出自《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而韩非子也认为:“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出自《韩非子·主道第五》。因此,在立法过程中,齐国的法家则主张“宪律、制度必法道”。*出自《管子·法法第十六》。其具体要求是:法律必须“立公弃私”和适应“四时”。“立公弃私”原则要求法律必须体现公义或公理,消解包括君主在内的人们的私欲,从而最终维护君主国家的最高统治利益。“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废天道,行私为,则子母相怨。”*出自《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而顺应“四时”的原则要求法律适应四季时令。法家秉承道家的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天地的大理,四时是阴阳的大经。“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出自《管子·四时第四十》。
人权是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尊严和权利,其核心就是自由、平等、公正与和谐。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来,洛克、杰弗逊等英美政治学家提出了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然法学说,认为国家起源于人们之间为了更好地保障自然权利而签订的政治契约。在这些自然权利,较为重要的自然权利有生命、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等权利,国家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然权利的实现。正是由于这些权利是人性的必然要求,因此多数西方政治学和法学流派都趋向于将人权视为法律中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认为国家制定的法律不能够违犯这种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否则就有可能失去法律的本性。尤其是二战以后,对于纳粹德国暴行的反思,使得这种思想更加具有道德力量。即使是坚持强调道德和法律相分离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在第二次世界战后经过与自然法学派的不断辩论,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法律的实效在于法律本身必须满足某些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其标志就是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H.L.A.哈特在其代表性作品《法律的概念》中对于“正义与道德”和“法律与道德”的论述。*参见[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9章。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出现了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伴随着这种全球化浪潮的,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即使是西方学者本身,对于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所包含的“文明一元论”也不无忧心。在他们看来,世界政治文明是多样化的,而“如果必须赋予全世界所有的人以‘人权’,那么,这就可能给那些热衷于专门推广欧洲文化的人开了绿灯,他们可能会不尊重其他文化而恣意孤行,而其他的文化对于美好的生活和公正的社会本来是自有看法的。”*[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页。因此,中国必须创造具有自己理论品性的人权思想和文化。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包容自由和平等的人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首先就是解决资本主义支配结构中人产生的异化问题。在资本所支配的社会结构中,人的本性被资本所褫夺而处于奴役的状态。马克思所谓的“羊吃人”,实际上是被资本所异化了的“羊”吃掉了被资本所异化了的“人”。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创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的联合体,是最高的社会理想和最终的理论奋斗目标。换言之,人性和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之所在。建构中国的人权思想和文化,必须坚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尤其是践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和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国家的“中国梦”之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与此同时,还必须批判性地继承儒家思想的精髓,吸收其民本思想和以“仁”为核心的文化观念。面对“人是什么”与“人应该如何生活”的终极论题,儒家基于人道主义而提出“仁”的观念。儒家“仁”的观念中高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内在地要求“把人当作人对待”。当然,也还需要批判性地反思和借鉴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西方政治哲学在人权问题上所取得的积极贡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量西学人权文化的“体”,裁中国人权文化的“衣”;不是以西方人权理论为唯一的和至上的标准,来考量、指导中国人权文化的建构。文明多元观念和多重现代性,要求反对“西方中西主义”和历史文化一元论所支撑的人权文化帝国主义对于远东政治文明的侵略。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西方政治文明成果,创造性地建构中国的人权思想和观念,使之“以人为本”和“尊重人权”不仅成为宪法原则,还要使这种宪法原则在立法过程中得以落实,为“强民”和“富民”奠定法制基础。
21世纪是充满新的国际竞争关系的“新战国时代”,“新战国时代”呼唤新法家的出现和先秦法家思想的复兴,以塑造一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民族精神。在这种新民族精神中,高扬着“自由”、“平等”、“公正”的理念,秉持着“诚信”、“友善”、“爱国”和“敬业”的观念,以塑造“富强”、“民主”、“法治”的国家状态,以及“文明”、“和谐”的社会状态。这,就是中国人的“中国梦”。
[责任编辑:吴 岩]
Subject:Constructing the Modernity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Legalists
Author & unit:QIAN Jinyu(Administrative Law School,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Xi’an Shannxi 710063, China)
With the fierce national competition in 21st century, China will face more and more challenges, and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re still the main political topic in the New Warring States Period. As the Ruling party in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ust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governance and promot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ity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ider, summarize and draw on the reasonable theories and arguments of the Legalists in ancient China. And it is needed to make three transformations: from “making people powerless” to “making people powerful”, from “legislation by monarch” to “legislation by the governed and protected by the constitution”, from “the Dao of heaven” to “human rights”.
new legalists; new warring states period; governance; modernity
2015-04-13
钱锦宇(1978-),男,云南昆明人,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法理学、人权法。
D911
A
1009-8003(2015)03-0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