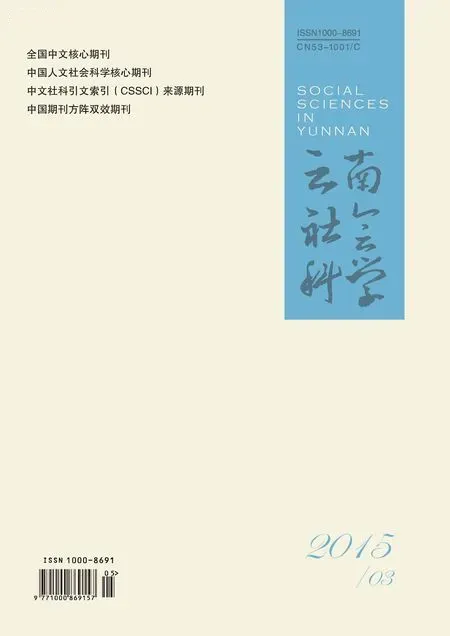从“天谴”到“科学”:灾难解释主题现代性嬗变刍议
2015-02-13
作为在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生存的物种,人类历史一直与各种自然灾难纠结在一起。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不同的时代对自然灾难的解释叙事也随之变化。传统社会对自然灾难的解释大多是“天谴说”。现代社会中,“天谴论”被“科学论”取代,主要是为了维护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发展自身的优先权。但需要反省唯“科学论”的负面效应,警惕“有组织不负责任”的短视与科学理性的自负,重视追究风险社会中活动者的责任。要避免单一的灾难决定论,需要建立“人人有责”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一、“天谴说”的传统工具意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治乱之说和自然灾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即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所谓“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的“天谴说”。先秦古籍中记载的灾异现象已比较丰富,如《诗经》中就记载,“荒政”中以周王为首进行救灾的应对措施。“天谴说”主要兴盛于东汉,究其客观原因为在东汉时期自然灾难的频率较高。其兴起的主观原因是自汉代以后兴盛的天人感应逻辑,这套逻辑认为天是宇宙的主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在上天控制的范围内,自然万物乃至社会历史变迁等都与天意有关。因此,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水、旱、虫、疫灾等各种自然灾难,统治阶级往往将之视为天命降灾,同时会将上天动怒谴告的起因归纳为“人祸”:灾异一般都预示了某种即将来临的社会(政治)变乱,而这种灾难也常常是上天对上位者疏怠政治事务的警告或惩戒。传统社会中,救灾主体主要是以君王为最高领导的国家行政力量。当国家遇见特别大的天谴灾难时,国家一般会采取一些措施,比较典型的是下罪己诏,即君王开展自我批评,希望上天息怒,恳求其不要因为他区区一人之过而殃及黎民。同时还会有一些弥灾类政治策略,如大赦、虑囚、求言以及实际的物资赈灾行动等。
在传统社会的灾难“天谴说”中,前现代社会中的自然还没有完全成为人理性认知力量的客体对象。自然被认为是一种凌驾于人的独立神格化力量,人们认为,它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变化具有模仿巫术的契合关系,即循时而变的自然是社会良性运作的镜像,反之则为恶兆。因此中国自周起即有专门司职保护自然资源的官职与相应的政令。如《周礼》卷四“地官司徒下”曰:“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窃木者有刑罚。林衡掌巡林麓之政令而平其守……若斩木材则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礼记》卷五“月令第六”也特别强调在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春秋繁露》卷十六“求雨第七十四”云:“无伐名木,无斩山林。”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人们认为自然的变动与社会的运作有着很大关系,因此,对自然本身的照顾、关切和保护成为国家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应该看到在这种天人感应的灾难诠释中,天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上下等级关系,更被理解为血缘伦理关系。确切地说,“天谴论”中天谴责的是一个人,即承天命而管理国家的天子。可以说,君王的合法性就源于他是天在人间的指定代理人。传统社会中的国之大事主要体现在战争与祭祀上,国家各级行政机构都有祭祀的义务,然而,唯有君王才是最高级别的祭司,即“灾难面前,周王需要以国家总代表的身份‘承担’灾难的责任和义务”①曹新宇:《传统中国社会的灾难信仰制度与秘密教门的灾难神话》,《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作为最高的、终极家长的威严或感召魅力是动员传统社会的关键整合力量,依照韦伯的说法就是领袖的“克里斯马”魅力。韦伯认为,合法的统治形式,即权威应该“建立在情感的或克里斯马的、传统的或理性的基础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出现的权威形式往往是‘克里斯马’或‘感召权威’类型”②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6页。。“克里斯马”是一种领袖人物的人格力量,它能够激发特定的大众对某个公众人物(政治领袖或军事统帅)的忠诚或情感。具有这种人格魅力的人,常常被认为具有某种超凡脱俗的力量或品质,所以这些人可被视为“天纵神才,这种权威也可以称为‘神授’权威”③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376~377页。。君王作为人间事物的第一承付者,其能力和义务均来源于他和上天的血缘关系,这种证据即“感生”的传说。即郑玄在《驳五经异义》中所言“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凡人都是父母所生,但是大贤或者受命的君王的诞生往往是神秘的,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如《诗经》之《商颂·玄鸟》《大雅·生民》中记载商、周始祖契与弃的诞生与“玄鸟”“大人之履”之间的神奇联系。这些神迹可以被视为原始领袖之所以高贵聪慧的原因所在。
因此,“天谴说”实乃是父子矛盾的一种仿像:各种自然灾难或者灾异现象是上天对君王这个“子”不肖不贤的警告,要解决灾难,唯有儿子亲自做些让父亲高兴的事情。所以,天子会自我检讨发布罪己诏,同时恩威并重地在君(臣)民关系上整顿一下(如大赦、虑囚、求言),将这种父子伦理关系依样复制到他与子民之间。传统中国社会是个典型的宗族社会,社会的整合依照家庭血缘建构起来,所谓“天地君亲师”的权威服从等级模式正是模仿血缘伦理的最好证明。“中国社会可谓以家族组织为其最基本单位的社会,相应地,中国的文化也以家族为其最基本的价值内容。”④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2页。大灾后的大赦、虑囚(即核实冤狱)等补救的方法体现了君王家长“恩”与“垂怜”的一面。这种天命-君王-子民由上至下家庭关系的模拟对于平息灾后的混乱与人民的心理痛苦是非常有效的。君王“克里斯马”的魅力与感召力之所以在传统社会的灾难观中如此重要,无非与传统社会心理中根深蒂固的神-国-家的同构观有关。当然,这种灾异负责制与“天谴论”的弊端也在于容易动摇政权的合法性,给政治异己力量以可乘之机:灾异“天谴说”是古代历史上一波波谶纬言论的根源之一,是各种政权合法性敌对力量兴起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双刃剑:现代灾难“科学论”
毋庸置疑,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都面临着自然灾难,所不同的是,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现代社会,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的认知逻辑中,天命-自然-人类共存在一个有机体系中,每一个部分的变化都与别的部分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前现代的灾难解释中,大多数自然灾难都可以被笼统地视为“人祸”,也可以被当成“人祸”来处理,这与其天人感应的世界观息息相关。随着人类对自身理性价值的重视以及科学知识的积累,“天人感应”逻辑渐渐去魅。在科学理性作为支撑性力量的现代认知范畴中,自然成为独立于主体以外的被认知客体,大自然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立于人类社会的系统,因此自然灾难可以被视为该系统非规律性的突发事件。因此,只要不是明显的人为灾难,如实在无法加诸到自然身上的核灾难、战争灾难、政治灾难等,对于一般以自然现象呈现的灾难,现代人首先将其归咎为自然界的异变。这类典型的灾难包括地震、海啸、旱灾、水灾、虫灾、瘟疫等。但是,问题恰恰在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在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介入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可以这样说,人口膨胀的现代社会中,一个纯净的、没有人类活动介入痕迹的自然环境少之又少。随着时代的变化,科学的反噬力不但增加了灾难的类型,如“科技灾难”“核灾难”等,同时,由于人类对自然改造的幅度以及力度的加大,使得显性的自然灾难与隐性的人为因素纠结在一起,难以区分。“研究灾难的学者发现,近些年来频仍发生的灾难,与人类社会片面追求发展有着某种正相关的关系,换句话说,原先可能不至于带来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某些自然现象,在今天显得严酷,而这类因自然或者人为的因素引起的灾难最近十多年来在发展中国家尤甚。究其原因,很可能与片面强调发展所导致的脆弱性累积有关。”①范可:《灾难的仪式意义与历史记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32页。因此,在“人为自然”中,全世界频发的水灾、旱灾、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难,与看上去和此无直接关联的城市化进程、水利工程、森林砍伐、植被破坏、野生动物的消亡、工业废气排放等人类社会行为有一定的关联性。“介入自然过程的社会或者物质行为,越来越频繁地引发出各种新型的危险,以及潜在或显在的灾难。”②Edited by Anthony Oliver-Smith and Susanna M.Hoffman Anthony Oliver-Smith:Culture and catastrophe: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Santa 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2002,p.33.虽然在很多科普类的宣传或者对日常生活的建议中,大众都能获知或者理解自然灾难与人类行为有一定的关系。但吊诡的是,一旦发生具体的自然灾难,几乎没有哪个宣传机构或者科研机构会真正关注人为因素在自然灾难中的具体责任,更为甚者对人为因素忽略不计。总之,传媒口径以及相关专家总在第一时间内将之解读为不羁的自然界的一次事故,并通过官方传媒途径将自然灾难分为两种主要的叙述主题:其一,给大众进行一次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知识的普及,如地震、海啸等是无法预测的地壳运动。而每次发生自然界的灾难以后,相关专家总会给大众传授一些深奥的专业术语。其二,针对受灾主体开出一些具体补救措施,如由专家介绍一些逃生技巧,以及灾后的心理疏导等。而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究竟在某一次具体的自然灾难中应该承担什么份额的责任、如何尽力探求出这种份额并从中得出教训等,现代自然灾难解释几乎都选择避而不谈。
三、科学专家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是人类理性力量的体现。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科学”“发展”的深信不疑也到达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深信,自然在终极意义上能被人类理性加以解读和控制。体现在对自然灾难的现代解释中表现为两点。其一,人们觉得,自然科学家总能找到自然灾难发生的源头。其二,科学不仅解释原因,同时也是补救的手段。对大多数自然灾难,官方往往将第一诠释权归于自然科学界,负责面向大众进行解释的是在官方媒体上出现的“科学”代言者——科学专家群体。
灾后专家群体的功能是人类理性的心理保护屏障。一般来说,自然灾难发生以后,专家群体总是与官方媒体对灾情的报道同步出现在大众面前。他们在第一时间的出现,其言论本身具有科学理性至上的图腾功能。专家负责用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向大众解读自然灾难的成因,无论如何,“科学论”对灾难中的人们来说总是一种安慰。因为即使人们目前无法完全控制自然,但是能运用自然科学原理解释灾难的成因仍然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秘密的根本性掌控。
然而,现代灾难“科学说”是一把双刃剑。面对自然界的灾难,虽然专家大多表现出客观冷静,并将自然界运作原理说得详实仔细。但是,现代社会中很多自然灾难,很可能还是人为风险造就的结果。何谓风险?风险“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各种风险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是与文明进程与现代化紧密相连的。这意味着,自然与传统不再具备控制人的力量,而是处在人的决定与人的行动的支配之下。夸张地说,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他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③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9页。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之处在于它是个与现代启蒙思想、科技力量相伴生成的风险社会,如果说传统社会的自然灾难以客观自然力量作为承付主体的话,那么20世纪晚期迄今,新技术无疑在很多自然界灾难中要承付一定的责任。因此,吉登斯指出现代风险景象之一是“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人类的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①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然而,一旦涉及具体的自然界灾难,上述这些值得思考和深究的关联就沦为理论空文。在官方媒体关于自然界灾难成因的解释中,追责自然与人为因果关系的专家体系往往集体失声。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家体系会在自然界灾难的开端肇始上就匮乏社会问责的能力。这种追问甚至提及的缺席有其深层含义:在某种意义上,“灾异天谴说”符合传统社会对政权合法性的要求,那么现代的“灾难科学论”则主要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发展的优先权。因此,自然界灾难的科学解释优先权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引导性的忽视、剔除灾难中人为因素的表现。退一步说,很多自然界的灾难因为目前科学认识能力有限(这一点是科学家群体自身也承认的现实),专家无法给出更多的解释,他们向大众传达这个看上去似乎无可奈何却又价值中立的信息,如我们对地球的预知能力有限,大地无情,只能依靠大众自己灾后的坚强和互助克服痛苦。在媒体构建的兼具科学智慧与人情悲悯的背景中,现代行政或者社会组织开足马力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围剿,如那些匆匆上马的大型人造工程对河流山川的巨大破坏,都成为被忽略的人为事实。媒体的抒情与专家的冷静共同建构了一个无人负责的自然界灾难,这也是现代风险社会“有组织不负责任”的特有症候,即:“相关责任主体尤其是各类组织,便会利用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来转嫁与推卸责任。”②林丹:《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4页。
诚然,对灾难起因的科学解释非常必要。需要提醒的是,由于人类对环境竭泽而渔的开发使得现代社会的人类整体共同面对比前现代社会更为危险的环境,“由于科技加速进步,生态危机出现。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变得成问题了。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称之为自然的问题,长期以来被归纳到工业化进程中去了,它变得危机重重。”③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第21页。
现代灾难的危险性就在于,虽然大众普遍认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如以前安全的自然环境中,但是人类行为卷涉而产生的“风险”在很多人看来还是一种“可能性灾难”④林丹:《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44页。,这种概率的大小,以及灾难真正发生后,人为因素到底如何计算或者衡量是非常困难的问题。于是,各种社会心理如侥幸、麻木应运而生,尤其因为量化技术上的难以操作以至于无法给出实际的数据,让各级行政机构或运作机制主体无视自身行为带来的环境或生态恶果。“没有什么‘他人’能够对此负责,或因此受到攻击或责备……现在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风险的巨大后果,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而且,没有哪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能够对他们负责,或能够被要求‘正确地安排’它们。”⑤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15页。正是这种“一切让数字、证据说话”的工具理性思维让人类对自然界的灾难“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并在掩耳盗铃中继续“发展”。在很多现代国家,虽然“风险在增长,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被改造为预防性的风险管理政策,甚至,哪种政治体系或政治制度能够承担这项任务还是不明确的。”⑥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第55页。比如,目前在中国城市中,威胁大多数人健康的雾霾问题,在实际治理工作中,由政府等行政机构组织专家抛出一个个“可能性”的原因,但是却始终无法确定责任主体。
四、结语:建设“复调灾难解释体系”成为必要
不同时代和社会类型要求我们有新型的思维范式。每一次具体的灾难解释都是特定社会建构的思想产品。“可以说风险是可以被社会所随意建构或界定。就此而言,掌握着建构和界定风险的权力的科学、法律和大众媒体等相关领域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⑦林丹:《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69页。因此,大众需要反省行政权力的短视与科学理性的自负。前现代社会中,一切灾难皆为人祸的论断是基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而当下的唯“科学论”自然灾难解释体系是建立在人类福利至上的短视发展观之上的。无数的灾难证据警告我们,人类的科技日渐强大并不是盲目干预自然进程的合法理由。即,当人类在夸耀我们“能”的时候,应该先考虑一下我们是否“可以”的问题。每一个物质进步或者人类福祉如果是以摧残自然本身运动规律作为代价的话,很可能福祉持续不了多久便会催生灾难。
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背景:科普知识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重视,而实际灾难的解释却有意忽视人为因素。在愈来愈严重的自然环境问题浮现的当下,人们仅仅问责具体的行政机构似乎是不够的。因为,当我们问责某个自然灾难与人为行为的关联度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在于大众问责者群体自赋了责任豁免权,即,灾难与问责者群体仿佛没有任何关联一样。在这个信息社会里,一旦灾难发生,大范围的大众问责者会僭越成为受害者代言人发问灾难事故中人为需要承担的责任。当然,这种问责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警醒的进步。但是,不要忘记的是,在人类前行的未来,每个责任者都可能最终是以个体的身份站在灾难面前。因此,在问责他人或者机构的同时,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更需要先反省问责自身:“我有没有参与制造灾难?”因为在风险弥漫的现代社会中,即使看上去现在我们离某个发生灾难的空间很远,尚能以清白者的身份问责相关行政机构、企业或者专家,但是不能确保,问责者的个体日常活动不是促成下一个灾难的蝴蝶效应。因此,建立完善的“人人问责、人人有责”的公共意识是抵御风险、克服灾难的重要前提。
这个公共心理机制的建立需要综合力量的整合与共同努力:国家行政权力、企业组织、具有独立能力且能全面思考的专家群体,以及公民意识日渐完善健康的大众。其中尤其要强调的是社会科学专家的作用,吉登斯在反省经典社会科学家的对现代社会的预见时最为短缺之处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生产力’拓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①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7页。在一个完善的灾难公共意识与警报系统中,社会科学不能再有缺席的理由。
身为栖身在地球上的脆弱物种,我们要敬畏、尊重大自然自身的运行规律;也不能忽略、推诿、掩盖人类过度开发行为的过失;我们要避免单一的灾难决定论,需要建设起复调的灾难解释体系。“把受灾原因完全归咎于制度或自然界会造成幼稚的决定论,会忽视人的能动作用,放弃追究社会活动者的责任。”②纳日碧力戈:《灾难的人类学辨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9期。简言之,建立起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的风险意识是当下风险社会中的必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