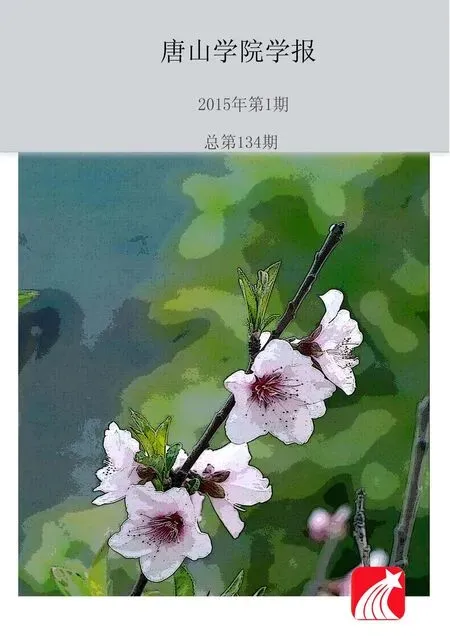改良派关于国民性及通过开明专制实现自由的争论——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2015-02-13周福振
周福振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南昌330003)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国民性较低,因而主张通过开明专制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后,再通过君主立宪以实现自由。在梁启超提出这一国民性问题后,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并具有革命倾向的蒋方震首先向他发出质问。蒋方震认为先有新民,再有新政府,再有新国家,从理论上讲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应该是先有新国家,才能有新民[1]。梁启超并没有认同他的思想,而是继续搞他的新民工作,新民在梁启超的心目中占了重要位置,以致于日本学者狭间直树认为梁启超“正是为了发表《新民说》才创办了《新民丛报》”[2]。到底是先有新民再有新国家,还是先有新国家再有新民,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得到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蒋方震认为先有新国家再有新民,则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要先解决国家体制的问题,而梁启超与之相反,则首先要解决中国国民性的问题。问题的争论也就由此产生了。从历史上看,革命派主张通过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就是要解决国家体制的问题,但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推翻了帝制,国家体制的问题解决了,而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当李大钊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时,李大钊认为中国先要解决国家体制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胡适所主张的建设“好人政府”,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但是新中国建立后,到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仍然较低。如果要首先解决国民性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承继梁启超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批判是激烈的,但是也没有解决问题。国家体制与国民性是密切相关的,如何破解它就像抽刀断水水更流一样,难以泾渭分明。如果有人告诉你,一方面要进行国家体制的改革,一方面要提高国民性,这话说得很有理,但是相当于没说。如果考虑到那些国民性低的人大部分是一些无权无势的人,恐怕就要从改革国家体制入手了;如果考虑到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都是从普通人中来的,那么就要从提高国民性入手了。但是如果综合起来考虑,当然是要从有权有势的人入手,那就是要首先改革国家体制。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说的“民”,胡适认为它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3]101。陈瑞志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认为梁启超“新民说”对其有较大的影响,一反思想界批评梁启超的倾向,指出梁启超的“新民说”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价值”[4]。这是对梁启超提倡“新民”的一个高度评价。然而,当梁启超在努力使自己的理论变得完善之时,它的不足之处反而暴露无遗。从表面上看,梁启超的思想非常有道理,但是他连自己人都没有说服。这说明梁启超的这种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改良派关于国民性引发的开明专制的争论
西方思想家认为“政府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梁启超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5]。于是,他在提倡新民的同时,广泛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黄遵宪和胡适对梁启超的这一点评价很高。黄遵宪说:“公所草《新民说》,若权利,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合群,皆吾腹中之所欲言,舌底笔下之所不能言,其精思伟论,吾敢宣布于众曰:贾、董无此识,韩、苏无此文也。”[6]贾、董指的是西汉的贾谊、董仲舒,韩、苏指唐朝的韩愈和宋朝的苏轼。这四个人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思想家,而且均以文才著称于世。黄遵宪却说这四个人都没有梁启超讲得好,表明他对梁启超的高度肯定。胡适也承认梁启超的《新民说》对他的巨大影响,指出:“《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的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3]105
梁启超一直在考虑自由在中国实现的问题,他在《新民说》中所讲的自由、自治、权利等思想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当他注意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原因在于地理环境所造成之时,他逐渐认为自由在中国不能扎根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国民性较低,人民程度之不逮。因此,梁启超提出中国人应该先通过实施开明专制提高国民性。然而,这引起了改良派内部的争论。与梁启超关系非常亲密的杨度对梁启超的这种思想表示了不满。杨度在《中国新报》第4号上发表了《致〈新民丛报〉记者》一文,认为梁启超用人民程度的不同反对革命党人的民主立宪是不合道理的。杨度指出,如果仅以人民程度为标准,那么英国和美国应该实行同样的政体,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种,而且美国也是由英国人跑到美洲而建立的国家,美国人的国民性也并不比英国人高,但是英国却实行君主立宪,美国却实行民主共和。再如,德国内部人种相同,但是德国统一之前,各邦却实行不一样的政体,有的实行共和制,有的实行君主制。杨度还特别指出,如果仅仅以人民程度而论,则英国和德国应该实行共和,而法国则应该实行君主立宪,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7]401。杨度确实举的是实实在在的例子,这就从国民性高低上否定了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性低,只能实行开明专制而不能实行自由的思想。
另外,梁启超认为汉人的国民性低,没有立国之资格,杨度则认为蒙、回、藏的国民程度更是不足以立宪,但是可以合满人与汉人组成一个共和国。在杨度看来,蒙、回、藏,无论为民主立宪还是君主立宪,人民程度都不高,但是立宪之后在宪法范围内,以特别制度行之,促其国民程度提高,然后使与汉、满同等,而收蒙、回同化之效。然而,杨度又认为汉人、满人,无论实行民主立宪还是君主立宪都可以,只是合满汉人民组成一个共和国,是有事势上之不可能而无程度上之不能[7]401-402。也就是说,杨度认为,中国人不能实行共和是事势上的原因,而不是国民性问题。
杨度通过分析,认为中国国民已达立宪之程度,这是与主张民主立宪者是一样的,但是杨度反对民主立宪,主张君主立宪,却与梁启超一致,杨度所持的根本原因是“国之情势”[7]401-402。这一点,杨度比梁启超要高明得多,以中国特殊情势论来反对民主立宪,可以塞革命党人学法国、美国实行共和的借口。但是,即使不用杨度说,各国情势不一样本身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因而当杨度可以拿中国特殊情势来反对革命党人时,清政府也照样会拿它来反对康梁的君主立宪。
康有为与梁启超在立宪方面具有一致性,但他主要也不是以人民程度为理由来反对共和。康有为通过观察欧美文明和中国文明,发现辛丑年之后(1901年为旧历辛丑年),人人提倡自由,三尺之童都以之为口头禅,却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康有为认为,中国之病弱非他,在不知讲物质之说而已,中国人缺的是物质。实际上,康有为的这种思想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而他认为魏源的思想“实未尝少行也”。康有为还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物质不强大,国家就难以强盛,如英国在欧洲列强中物质最为强大,所以英国最为强盛,而中国强调以农立国,导致物质落后。从此而论,康有为认为中国的失败不在于自由,而是在于物质[8]。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指出,物质只是外在之文明,主张从内在之文明入手,即文明的精神(又称风气),来改造国家[9]。梁启超受到了福泽谕吉的影响,才努力提倡改造国民的精神,而康有为却主张从物质入手,两者的出发点已经完全不同了,但都是为了使国家走向强盛。物质和精神都非常重要,但到底精神和物质哪一个更为重要,即使我们现代人仍在争论不休,没有一个统一答案。虽然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坚持物质和精神两手都要抓,但是在实践中明显是有偏颇的。然而,从历史上来看,日本明治维新从改造人的精神方面入手,确实使日本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为世界上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实现民族富强提供了先例。同时期的中国先从解决物质方面入手,也就是清政府的洋务运动,虽然曾使中国经济获得很大的发展,GDP长时期仍居世界第一,史称“同光中兴”,但是最终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命运。从此而论,人的精神也就是国民性应居物质之前。但是,如果考虑到印第安人的精神非常好,甚至善待那些跑到他们那里的欧洲殖民者,最后却败在了他们的坚船利炮之下,几乎被屠杀殆尽,也就是说,你的品德再高,国民性再好,如果没有先进的武器,面对手拿枪炮的敌人,恐怕也会感觉无能为力。实际上,从康有为和梁启超关于物质与精神的争论而言,它告诉了我们世界本身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悖论是时刻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从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来看,我们大力发展物质力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国民性却仍然非常低下。正是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八项规定、四风建设,目的是要提高中国人的国民性,但是最终能不能成功,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蒋智由也并不认同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从而提出了“宪胚”之说,认为立宪是一个从开始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梁启超则认为他所说的开明专制与蒋智由是一样的,造成不一致现象的原因是他持论喜走极端,以刺激一般人之脑识所致,因而他专门给蒋智由写信讨论这个问题。梁启超指出,他所认为的开明专制是立宪过渡、民选议院未成立之时代,相当于日本的太政官时代之政体,因而与蒋智由是“相反而相成”。后来,梁启超又指出与蒋智由是“全同而相成”[10]。
主张君主立宪的张君劢也不认同梁启超的思想。起初,张君劢在介绍英国自由主义者穆勒关于“代议制政府”的理论时,认为应该提高中国人的国民性之后再进行立宪。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张君劢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张君劢认为穆勒关于立宪国民的条件的学说是完美的,但是事实却不尽然,这是因为他认为如果等待中国人的国民性提高了再去实施立宪,恐怕中国永远也不能实现君主立宪。张君劢进而指出,中国人可以通过依赖少数先觉之士来主持实施立宪政治。他认为,世界上的大共和国在政治改革前后,都会依赖少数先觉之士,即使西方代议制度最发达之国,大多数人民仍暗愚如故。于是他提出实施立宪的两种方法:一是练习议政,以造就人民政治的习惯;二是统一舆论,以养成强有力之监督机关[11]。在这里,张君劢的思想与革命党人汪精卫等人认为的只要中国人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就能实行共和,以及孙中山的先知先觉理论有相一致之处。后来,胡绳也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他在《理性与自由》一书中指出“既然人的知识程度有高低,智慧年龄更不会没有长幼,当然就要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12]。
实际上,梁启超也曾经有寄希望于少数英雄的思想,但他还有一种担心,认为仅仅凭一二英雄难以实现全民自由。他指出,中国“岂无一二聪伟之士,其理想,其行谊,不让欧美之上流社会者,然仅恃此千万人中之一二人,遂可以立国乎?恃千万人中之一二人,以实行干涉主义以强其国,则可也,以千万人中之一二人为例,而遂曰全国人可以自由,不可也”[13]。恰恰是这一点,张君劢和革命党人都忽略了。
在人的天性方面,汪精卫与张君劢的思想具有一致性。汪精卫认为,凡为人类都有人权思想,不同之处在于程度之优劣,中国是专制国,是就国家经制而言,但是疾专制乐自由是人类之天性,因而中国人也一定具有此性。汪精卫并拿孟子的学说来说明,如果说中华民族无民权的组织则可,但不能说中国人不疾君权不乐自由,如孟子认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匹夫,闻诛匹夫纣,未闻弑君,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等等。在汪精卫看来,这是中华民族社会心理之宣言,也就是说君权之可疾,而自由之可乐,不待学说之修明,而后家喻户晓,但是由于中国人知恶专制而不知重民权,因而起事之初,咸抱帝制自为之心,以为自己将以仁易暴,不知其根本的思想正与所欲扑灭政府无殊,结果只能以暴易暴[14]。刘师培也曾将孟子的这句话与西方民约论相联系,认为孟子“限抑君权”,诸子不能及,要而论之,“孟子非以君为神圣不可侵犯者,不过视君为统治之机关”[15]。然而,汪精卫与张君劢的认识有一个最大不同。张君劢认为既然人天性疾专制乐自由,那么不用等国民性提高就可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而汪精卫则相信就是因为中国人疾专制乐自由,所以中国人能通过革命建立共和。从理论上讲,汪精卫的理念是有道理的,但是革命党在真正实践共和的时候却在宪政之前加了一个训政,由革命党训练人民走向宪政。这实际上是和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有一致性的。
毋庸置疑,改良派关于国民性争论中的基础和目标都是大家一致认可的。他们争论的基础有两个方面是一致的:一个是中国人的国民性较低,一个是中国人都痛恨专制、热爱自由。他们要实现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由,而实现自由的路径是通过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但是,从此而论,却导致了不同的见解,即如何实现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说,到底要不要经过开明专制来提高中国人的国民性作为其过渡?如果考虑到原始社会状态下的野蛮人都存在着民主自由,国民性确实与立宪、自由没有决定性关系;如果考虑到现在很多国家,如泰国、伊拉克,想实行民主自由,却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自由,国民性确实又与立宪、自由有决定性的关系;如果将各种情况综合起来看,国民性只是能不能实行立宪、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已,并不是其全部原因。所以,改良派关于国民性与开明专制、立宪及自由的争论,从不同方面来讲各有各的道理。他们之所以提出各种不同的理念,主要是因为他们对问题的认识以及关注现实的方面不同。实际上,梁启超提出通过开明专制提高中国人的国民性后,改良派也有一种担心,那就是开明专制能不能真正提高中国人的国民性呢?统治者实际上是不愿意提高国民性的,因为国民性提高之后,统治者就不容易进行统治了,统治者最喜欢服从的人,最喜欢奴隶。这也是改良派既支持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又反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言以蔽之,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到底是不是真的立宪?清政府在还没有实现立宪之前就已经灭亡,也就无法用实践来证明了。
二、改良派关于国民性引发的主渐还是主急的争论
一般而言,社会除弊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主渐,二是主急,二者各有优缺点。梁启超在介绍日本西村博士的思想时,形象地指明了这一点:“除弊宜以渐,若急除之,则溃裂四出,遂不可拯,此经世家之常言也。其言固非无理。虽然,若一概主渐而斥急,天下将皆自安于弊中而不觉悟,于是其弊益深厚,有不至国亡不止者。譬如病毒在身,以缓和之药治之,其病毒益浸蚀,身遂陨焉。若于彼时以快刀截断病源,虽复一时苦痛,遂可望全愈。今日亦有许多之事,宜用霹雳手段,不宜用缓慢手段者。余日望良政治家之快刀久矣。”[16]67也就是说,如果只采用主渐的手段,恐怕改良永远不会成功,所以改良也需要实行快刀斩乱麻式的主急方式。这两种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新民丛报》学人。
由于《新民丛报》学人内部在国民性问题上的争论,导致了他们在实践方式上采取了不同的路向。有些人认为主渐与主急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与国民性关系不大。因此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就有人明确提出要用主急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即:“吾国人于形质上、精神上有种种奴隶根性,积之数千年,非有狮子吼之说法,不足以震荡之而涤除之。”[17]而在《新民丛报》前期,《新民丛报》学人也是这样做的,特别是梁启超表现得尤为激进。但是,后来梁启超认为主渐还是主急虽然是一种手段,却与国民性有很大关系。如果国民性高实行主急的方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国民性不高再实行主急就会导致国家更加混乱,自由就更无从实现。所以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应该从开明专制入手,劝告政府实行开明专制以立宪,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独一无二之法门。虽然如此,梁启超也担心会被清政府所戏弄,所以仍主张与清政府进行斗争。
《新民丛报》学人中对于主急表现得尤为激烈的是黄与之。黄与之认为革命盛行于中国是由于“数千年来专制之淫威,有以激之使然,而满汉两族并棲于一国之下,其互相猜忌者,二百余年如一日”,“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脑蒂,其排满性之伏于其中者,遂不期而自发”,“此革命党之势力所以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但是不仅革命要流血,就是立宪政体“在今日文明诸国中,必流无量之血,掷无数之头颅,乃始得,此君民冲突之结果”[18]。这是黄与之看到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是英国人不惜生命努力争取的结果。虽然英国通过较为和平的“光荣革命”实现了君主立宪,但是在此之前他们仍然是通过革命将国王查理一世推向了断头台。
一些人认为日本立宪为无血之革命,黄与之则指出天下没有无代价之物,各国立宪也是如此,只不过是“所流之血有分量上之差异而已”。单纯看明治维新而言,日本确实是和平的改革,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前进行过倒幕运动却是付出了流血的代价,黄与之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从此而论,黄与之指出,如果清政府倡导预备立宪,而使中国国民能“安享参政上之权利”,则中国的立宪是“世界宪政史上之一创例,而日本之所不能得者,反以得之于吾国”。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黄与之认为政府藉口人民程度不能立宪,则永无立宪之期,现在国民对官制改革尤为失望,因此国民必须“自起而谋之”,而且中国的宪法“必不以日本之钦定宪法为满足,而更求所以进于日本”。黄与之又考虑到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指出,在中国当时的时势与人物,较之日本明治维新时,“皆勿及微特勿及而已,其时势之危险,其人材之消乏,有百倍于明治维新之时者,以日本之时势与人材仅得一钦定的宪法”,“吾国以百倍于日本之艰巨,又有满汉种族之感情,革命立宪之纷扰以为之障碍”。因此,黄与之认为,“果欲得一完满无缺之宪法”,“不可不出万死排万难,以吾人之血为代价而购得此宪法”[19]。也就是说,中国的立宪比日本还要付出更多的血的代价。从这里可以看出,黄与之的思路与革命派的思想有所接近。
从理论上讲,如果国民性高,可以采用主急的方式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良;如果国民性低,最好用主渐的方式进行改良,可以避免主急方式可能带来的混乱。但是,从实践上来看,问题要远远复杂得多。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希望用主渐的方式实施改良,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主渐的改良成功的机会并不多。这是因为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自愿放弃自己的一些权益。如李自成进攻北京时,崇祯帝让臣下拿出一百多万两银子救急,结果大家都说没钱,当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后,几天就拷打出了七千多万两白银。从此而论,既得利益者是不希望采用主急方式的,以求在改良中尽量保有其利益,而那些弱势群体因为没有多少利益可保,是喜欢主急方式的。梁启超等改良派亲自参加过戊戌变法,在其失败后,许多“好心人”指责他们太急了,应该实行渐进的改良。梁启超当时就直接回击这些人说,这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良好愿望而已,洋务运动就是采用主渐的改良方式最终遭到了失败,日本采用主急方式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所以中国积弊太多,不应采用主渐的方式,应该采用主急的改良[16]67。实际上,对于改良派而言,他们内心也是想通过主渐的改良方式实现君主立宪,从而实现中国人的自由,所以他们才会与孙中山革命派进行你死我活的论战,但是他们又看到清末立宪不急不慢的实施,才感觉到清政府实行主渐的改良可能是假的,不会成功,所以才会有黄与之这种提倡主急改革的人。从历史上看,采用主急方式成功的人都是有雄才伟略能够把握局势的人,如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主急式的变法成功了。如果领导者没有这种能力,最好实行主渐的方式,否则就会引起国家的混乱。
总之,改良派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人国民性低下,但是关于中国如何实施立宪以实现人民自由的思想却大相径庭。梁启超等人认为应该通过开明专制以实施立宪;张君劢等人认为不用通过开明专制,否则中国人永远不能立宪;杨度等人则认为实行什么样的政体与国民性无必然关系,而从中国情势来说应该实施君主立宪。另外,他们在选择实现自由的道路上,由于对国民性理解的不同产生了中国改良应该通过主渐还是主急方式的争论。这深刻地说明了认识问题较为容易,但是如何解决问题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想统一起来是太难了。但是不能因为难而不去解决它,实际上改良派的目标都是要实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它。然而,由于改良派一直没有掌握政权,也就无法用实践来检验其理论。现在同样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即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实施主渐还是主急式的改革,希望领导者能实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希望所有的中国人有一个共识,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去努力。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0]。
[1] 飞生.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J].浙江潮,1903(8):23-30.
[2] 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9.
[3] 胡适.四十自述[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
[4] 陈瑞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M].上海:上海书店,1936:171.
[5] 中国之新民.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N].新民丛报(第1号),1902-02-08.
[6] 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N].新民丛报(第24号),1903-01-13.
[7] 刘晴波.杨度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8] 蒋贵麟.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十五册[M].台北:宏业书局,1987:28-96.
[9]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
[10]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66-369.
[11] 立斋.论今后民党之进行[N].新民丛报(第95号),1907-11-06.
[12] 胡绳.理性与自由——文化思想批判论文集[M].上海:华夏书店,1949:32.
[13]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林志钧.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12.
[14] 扑满.革命横议[N].民报(第3号),1906-04-05.
[15] 刘师培.刘师培全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567.
[16] 西村博士自识录[N].新民丛报(第18号),1902-10-16.
[17] 绍介新著 ·仁学[N].新民丛报(第1号),1902-02-08.
[18] 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N].新民丛报(第92号),1906-11-30.
[19] 与之.日本之政党观[N].新民丛报(第87号),1906-09-18.
[20] 黄炎培.延安归来[M].重庆:国讯书店,194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