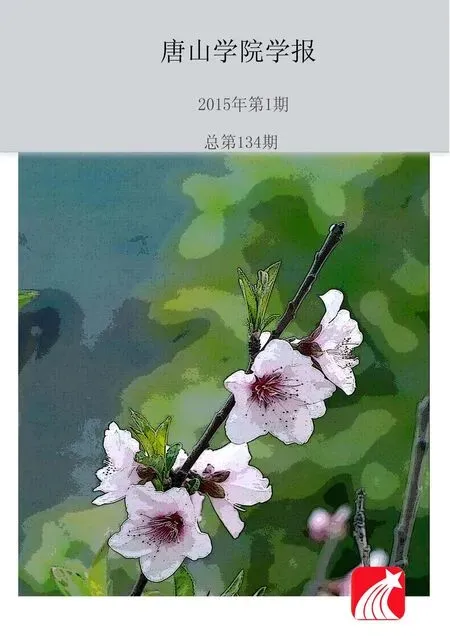论李大钊的尊严观
2015-02-13易明
易 明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172)
论李大钊的尊严观
易 明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172)
面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历史情景,中国人民受尽侵辱而毫无尊严的生存状态,李大钊尊严观开始萌发并不断发展,为中国人民追求尊严生存的斗争指明了历史方向。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尊严思想、马克思主义尊严思想和西方人权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李大钊尊严观,其关于肯定人的主体能动性,注重安定国家秩序,追求个人解放与自由,关注妇女尊严等方面的思考,对当代中国尊严建设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李大钊;尊严;主体性;个性解放与自由
一、李大钊尊严观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外有侵略、内有纷争,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的生存毫无尊严可言。救亡图存、御辱兴邦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重任和广大人民的最强呼声,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前赴后继地寻找摆脱奴役和压迫、实现尊严生存之道路。地主阶级开明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实业派与革命派先后尝试从不同途径寻找救国的道路,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随着各阶级和各阶层人士的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劳苦大众如何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学说,在中国经过激烈的论战,逐渐传播开来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尊严问题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系统的尊严理论。马克思主义尊严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的尊严的历史特征、社会基础、阶级实质和超越性追求,为人类正确认识尊严现象,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赢得自身尊严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一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尊严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尊严观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尊严观开始萌芽,李大钊的尊严观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大钊尊严观的思想基础来源于对中国传统尊严观念、近代西方的人权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尊严观的批判性继承和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尊严思想。以儒家尊严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尊严观念,重视和肯定人的价值,称颂和赞美人的气节,倡导并追求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主体以尊严。李大钊虽然早年就读新式学堂并东渡日本求学,但其思想依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弘扬人的主体性,主张通过稳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环境维护人的尊严,号召人们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来维护和实现人的尊严等方面均可以见到中国传统尊严思想的影子。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严思想构成了李大钊尊严观的最初思想来源。
近代西方人权思想是李大钊尊严观的又一思想来源。近代西方人权观念作为反封建、反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的武器提出来后日益成为国际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这些普遍被认同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等。人的高贵与尊严正是要通过人们能够平等、自由地享有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才能体现出来。李大钊曾赴日本留学,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因此李大钊接触到了大量的西方先进学说。例如,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在日本形成并非偶然,李大钊曾经的老师吉野作造发表《论民众的示威运动》等文章,阐发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其他老师如大山郁夫、美浓部达吉等,也都宣传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他们的思想对李大钊的影响很大。此外,章士钊于1914年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甲寅》月刊针对当时的《国权论》,以寻求“政治根本之精神”为方针,系统地宣传了“天赋人权”观念,李大钊通过投稿与章士钊相识,并且“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1],这些因素均对李大钊尊严观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尊严观是李大钊尊严观的核心思想来源。可以肯定的是,李大钊在日留学期间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有据可查的事实是,李大钊在日本主要受到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安部也正在该校任教。《早稻田大学百年史》这样记载:“李大钊曾在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学习,深受安部矶雄经济学的影响……”[2]日本学者森正夫认为:李大钊“把在东京时代以某种形式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藏在心中,一旦实现这种思想的外部条件成熟时,就将其作为自己思想的内在发展而开始确认这一理论”[3]。由此可见,对于当时急于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李大钊来说,马克思主义这一崭新的革命理论,其关于肯定和弘扬人的价值,倡导并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赞美和歌颂人的尊严的世界观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其拯救民族、解放人民的锐利思想武器。
二、李大钊尊严观的主要内容
(一)肯定人的主体能动性是人的尊严的基本标志
李大钊肯定并弘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赋予了人的尊严以人性基础。李大钊的革命思想始终贯穿一个“民”字,他早期就提出了“唯民主义”。1924年,李大钊在《百科小丛书》中列举了“民主(democracy)”当时的几种译法,有平民主义、民本主义、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唯民主义等,而李大钊则认为“‘平民主义’和‘唯民主义’及音译的‘德谟克拉西’损失原义的地方较少”[4]。
辛亥民主共和失败时,孙中山提出“训政”、梁启超提出“贤人政治”,而李大钊则提出了“民彝”思想,这是他早期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1916年,李大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同时将自己主编的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取名《民彝》。李大钊认为“民彝”就是要从“民”的主动性、主体性角度缔造共和的坚实根基。他强调要培养主体创造的能力,特别是广大青年更要自觉到“活泼泼之我”“特立独行之我”。“民彝”肯定并充分尊重人民的意志与愿望。
具体到“民彝”的历史作用,他反复论证了是群众势力、群众之意志、国民之思想等决定了人类历史进程,而并不是以往人们普遍认为的英雄、圣人决定历史和创造历史。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后,李大钊受唯物史观的影响,为自己的“民彝”思想找到了客观的物质的基础。“民彝”之所以必须受到重视和肯定,在于它是代表社会进步的经济力量,他依据唯物史观说明“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虽然坚信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历史的必然法则,是“历史的命令”,但他并没有放弃提倡人民的创造性和自觉性,他不断呼吁人民一定要有“阶级自觉”,不能坐等新境遇的到来而不去努力,真正的命运是由自己掌握的。这就将人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创造性放到了较高的位置,从而赋予了人的尊严以较为坚实的人性基础。
(二)强调统一稳定的国家秩序是人的尊严的政治保障
李大钊认为人的尊严的维护和实现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和政治保障,即统一的国家秩序。只有在统一的国家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人的生命才不会受到威胁,身体才不会遭到摧残,行动才不会受到限制,这些条件都是人的尊严得以维护和实现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将统一的国家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一美好愿望寄希望于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在他看来,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不仅扫除了“暴秦以后”两千多年来的“君祸”,还实现了共和民主政治。但令李大钊始料未及的是中华民国的运作过程却步履维艰、难如人意。其主要根源在于中华民国的存在暗含诸多危机,民国陷入危机的原因,李大钊着重指出了三个方面:不顾民众幸福,只为自己利益奔波的政党利己主义——“党私”;集政权、军权、财权于一身,企图维护割据体制的各省都督的利己主义——“省私”;通过煽动会党等引起民众反乱气氛的——“匪氛”。当然,这一时期李大钊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完全革命的,例如,他把依仗军事力量与袁世凯对抗的国民党系统的都督(安徽、江西、湖南、广东)严厉谴责为民国建设的障碍,指出“都督一日不裁,国权一日不振,民权一日不伸”,“虑地方分权,召国家分崩之福者,未之闻也”[5]。但是,李大钊担心国家内乱纷争对人的尊严的威胁却是不争的事实,他把避免内乱,维护国家统一视为实现人的尊严的前提与基础。
(三)主张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是人的尊严的基本标志
首先,李大钊认为在中国传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几乎人人尽丧自其为我”,他依据孔孟言论指出“孔孟亦何尝责人以必牺牲其自我之权威,而低首下心甘为其傀儡也哉”。面对“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的个性压抑状态,李大钊号召人的独立与解放,“近世文明之特质惟在解放,吾国以专制之余,凡其自体具有权威者,罔不遭君主之束缚,斯不独个人己也”[6]48。他用“解放”来概括近代文明基本特征。他认为20世纪是人的解放时代,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一个“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结合的新组织。对于如何达到未来社会的理想境界,他说:“现在世界进化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新组织。”[7]597-598因此,在李大钊看来,个性解放是走向大同世界必经环节,大同世界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又容纳并保护着每一个人的个性解放。
其次,李大钊高举人的尊严的伟大旗帜,真诚执着地追求个人自由。他强调个人自由与专制统治势不两立,“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6]175。所以,他坚决反对独裁统治和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在《自由与秩序》一文中,李大钊明确指出倡导自由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仅绝不矛盾,而且应当相互结合。在他看来,大同世界与个性解放结合必然涉及到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关系问题。李大钊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个人则是社会中的一分子。“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7]437-438李大钊还对体现个人自由的言论自由等进行了详细阐述。李大钊强调:“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性质,只有愚昧与虚伪是顶危险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行为。”[7]7言论自由对于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境界亦有重要意义。“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应能够容他真实没有矫揉造作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7]8所以,李大钊认为既然思想自由是禁止不了的,那么保障言论自由便是社会文明进步唯一途径,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思想言论自由不仅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更是人的尊严的重要体现和基本标志。
(四)重视妇女农民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尊严
尽管尊严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尺度,每个人都应平等享有尊严。但不可否认,由于种族、性别、阶级地位、经济条件、身体条件等因素的存在,人的尊严实际上存在着差别。例如,旧中国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实际上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李大钊尊严观的可贵之处,正是看到了这些群体的尊严缺失状态并对其给予了关注和思考,就她们如何摆脱无尊严的生活状态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
李大钊吸收和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妇女理论作为维护妇女群体尊严的有力武器。首先,李大钊高度重视妇女群体的尊严。李大钊认为妇女尊严代表了时代的呼声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8]9李大钊在《废娼问题》中更是明确指出这种现象的存在对妇女的尊严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废娼的第五个理由中他说:“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社会上有了娼妓,大失妇女在社会上人格的尊严。”[9]由此可见,李大钊对妇女群体的尊严问题高度关注,这成为李大钊妇女尊严思想的理论基石。
其次,李大钊反对歧视妇女并主张以法律保障妇女的尊严。他认为男人对于女人并无先天必然的优越感,而妇女对于健全男人的存在具有重要作用。“男子的气质,包含着专制的分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与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10]李大钊认为仅仅因为妇女的判断力弱就取消她们参政的权利是极其荒谬的,虽然旧中国的妇女在知识结构、文化法律等方面确实有不足,但造成这种状况并非全赖于妇女的本性,而大部分是由于社会对她们的歧视。对于妇女尊严的保护,李大钊主张通过法律途径来实现。例如,宪法应规定妇女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民法上应给予妇女财产权和行为权等,刑法上应禁止买卖妇女等,行政法上应使男女享平等为官之权利,应有同工同平等就业的权利等等。这些全面的权利显示了李大钊对于妇女尊严的深刻思考。
最后,李大钊号召妇女联合起来争取自身尊严的实现。他认为:“妇女要达到她们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8]9李大钊认为妇女力量的联合,有利于让事实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战胜男权统治。特别是处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李大钊认为更有必要团结和联合一切有着相似利益诉求的团体和流派,追求妇女解放道路上的大联合。他说:“欲为民权的运动,无论哪种团体,都须联络一致,宗教的、母权的、女权的、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可合而不可分,可聚而不可散,可通力合作而不可独立门户。”[8]174只有这样,才能打倒军阀,澄清政治,实现妇女的解放。对于妇女尊严实现的彻底办法,李大钊说:“一方面应合妇人全体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社会制度;一方面还应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社会制度。”[6]640
除了对妇女群体的尊严非常重视之外,李大钊还特别关心底层劳动人民的尊严问题,农民、童工等社会底层民众的尊严都是李大钊思考的内容。在《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章中,李大钊对民国建立以后人民的尊严不仅没有改善,甚至出现恶化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李大钊认为中国农村的农民构成中以自耕农、佃农及自耕农兼佃农为最多,这些农民在外货入侵、军阀横行面前生活日渐艰难,自耕农和佃农成为农民中最困苦的阶级,而农村中的佃农和雇工的经济地位则更为低下。李大钊强调佃农及雇工所受的压迫,比自耕农更甚,有些几乎决不能维持其生存,根本谈不到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李大钊还对我国境内外国工厂的童工毫无尊严的生活状态给予了极大关注。在《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中,李大钊揭露了外国资本家盘剥童工的罪恶:“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到极重的损伤,而以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之所致。……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很多的不过六岁的童工,在大工厂里做工,十二小时内,仅给他们一小时的功夫去吃饭。他们大多是站立着做工。……那些儿童们的衣食住,均极惨苦,而不得一钱。”[11]李大钊还将观察童工问题的视野扩展到了整个工人阶级。他在《劳动问题的祸源》一文中阐明了工人阶级生活无以安宁的祸源是工银制度、资本制度、工厂制度以及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12]。可见,李大钊对中国工人阶级毫无尊严的生活进行了客观全面的阐释,为寻找工人阶级的解放道路奠定了基础。
(五)重视人的基本的身体尊严
身体尊严是人们维持自身健康、安全存在的必要保障,它要求不能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人身安全和行动自由等。李大钊高度重视人的身体尊严,尤其强调尊重人民的基本的生命权和生存权。著名法学学者杜钢建指出:李大钊关于生命权生存权的论述反映出他的人权思想具有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双重性质,他关于生命权特别是自杀权的主张表现出他受到个人主义人权观影响,他关于生存权特别是劳动权休息权的主张表现出他受到社会主义人权观影响[13]142。首先,李大钊在国内较早探讨了自杀权这一关涉人的生命的权利。李大钊从人的权利角度出发,强调法律和社会既不应剥夺人的生命权,损害人的尊严,也不应禁止个人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我们应当承认一个人于不直接妨害社会,迷惑他人范围内,有自己处决他自己生命自由权。”[7]517这并不是说李大钊鼓励自杀,他赞同人的自杀主要是基于人们应以誓死之决心来改造当时社会,鉴于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状况,李大钊主张广大青年应该“拿出自杀决心,牺牲精神,反抗这颓废时代文明,履行这缺陷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生活”[13]143。
其次,李大钊高度重视人的生存权。生命权属于自由权范畴,而生存权则属于社会权范畴,生存权中又可划分出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团体行动权等等。受路易·勃朗等社会主义者思想的影响,李大钊着重从劳动权角度理解和阐释生存权,甚至有时他会将二者互为代替。例如,他说:“彼又以为人人均有劳动之权利(生存之权利),欲求生存必须劳动。”[7]593在接受马列主义以后,李大钊主张人人都应该成为劳动者,应该享有维持人的存在的劳动权利,要实现这种权利,必须建立“工人政治”,实行“工人统治”,“以劳工阶级统治,替代中产阶级少数政治”[7]594。这样,就实现了以劳动者和无产阶级为本位的无产阶级专政。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中劳动者超长工作时间下的无尊严生活状态,李大钊提出了批判,并依据现实提出了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维护劳工阶级尊严的“三八”主张,即工作八小时、修游八小时和休息八小时。李大钊认为通过休息和游玩,人们可以舒缓工作的疲倦并恢复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等,最终达到人体和精神的平衡协调发展。
三、李大钊尊严观的时代价值
李大钊尊严观的萌发和形成,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李大钊的尊严观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尊严生存的斗争指明了方向。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获得自身的尊严生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但这些努力和尝试在相当长时间内其实是盲目的,没有真正的革命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等,只是出于民族义愤和情绪宣泄并不能真正带来中华民族的解放。李大钊尊严观的适时出现,和其关于实现“工人统治”、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等思想,以及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尊严生存的科学描述和具体阐发,让黑暗中的中华民族找到了可以为之奋斗的光明目标。
李大钊尊严观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尊严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李大钊较早在国内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其诸多思想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李大钊尊严观的丰富内容也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尊严观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来源。例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人民大众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的肯定和支持,这与我们今天倡导“以人为本”的内在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对国家秩序统一和稳定的高度重视,成为我们今天为国家统一和社会的安定繁荣而奋斗的思想动力;李大钊对人的解放和自由的不懈求索,也正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旨归一以贯之的。
李大钊尊严观为当代中国尊严建设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李大钊尊严观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从宏观上论述了人的尊严的内涵、意义及其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对微观意义上人的尊严在实践中的保护进行了深入思考,如李大钊关于妇女群体权利的保护与实现的一系列思想,以及关于童工问题的深入思考,都对当代中国尊严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1]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史事综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96.
[2] 骆为龙.李大钊同志在日本留学的日子[N].北京日报,1982-06-28.
[3] 杨树升.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J].韩一德,刘多田,译.齐鲁学刊,1987(1):74-75.
[4] 李大钊.史学要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52.
[5] 李大钊.裁都督横议[J].言治(月刊),1913(3).
[6] 李大钊文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 李大钊文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 李大钊全集:第4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9] 李大钊.废娼问题[N].每周评论(第19号),1919-04-27(2).
[10] 李大钊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348.
[11] 李大钊.上海的童工问题[J].中国工人,1925(4).
[12] 李大钊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3.
[13] 杜钢建.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校:李高峰)
On Li Dazhao’s Theory of Dignity
YI Ming
(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enzhen 518172, China)
In modern times, the Chinese nation, poor and weak, suffered abuse, shame and lack of dignity and against such background Li Dazhao proposed and developed his theory of dignity, which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people’s pursuit of survival and dignity. The theory assimilated ideas about dignit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m and the Western thought about human rights.The ideas of human subjective initiative, the stability and order in the country, the pursuit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and freedom, the dignity of women are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gnity construction.
Li Dazhao; dignity; subjectivity; personality liberation and freedom
B17
A
1672-349X(2015)01-0023-05
10.16160/j.cnki.tsxyxb.2015.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