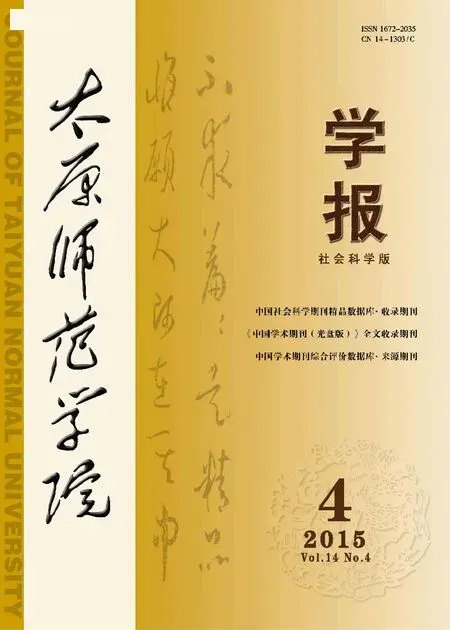晚明公安派的尊陶及文学史意义
2015-02-13邓富华
邓富华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晚明公安派的尊陶及文学史意义
邓富华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作为晚明文学的重要代表,公安派的尊陶颇值得注意。他们一反复古派对陶诗的贬抑态度,标举陶诗之“淡”是“真性灵”,将陶诗的文学史地位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尊陶,既是希望通过省察文学传统、重构文学审美理想来矫当时诗坛之弊端,同时也是回答在拟古思潮笼罩下文学如何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在更为广阔范围内向古代典范学习。
晚明文学;公安派;陶渊明;文学史
公安派是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以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兄弟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为湖北公安人而得名。这一文学流派的主要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人。在晚明文学领域,公安派可谓声势浩大。目前学界关于公安派的研究成果颇丰,不管是其诗歌还是小品文都有不少专门的论述与研讨,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未有学者深入探究公安派的尊陶倾向,也即他们为何要将陶诗作为典范而加以推尊。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秉持“取法乎上”的方法论原则,坚持古诗宗汉魏、近体法盛唐的拟古主张,致使一些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于已经在诗歌史上被赋予崇高地位的陶诗,前七子的领袖何景明提出“诗弱于陶”的诗学命题,开明代中期抑陶之端,后七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论调有所修正,但还是相对忽视陶诗的价值与地位。公安派作家则对陶渊明及其诗歌大力表彰,他们对陶渊明性格、人品及诗歌的解读也与前代迥异,对陶诗的典范意义与审美价值进行了再次体认。可以说,陶渊明在晚明文学中受到充分关注和高度重视与公安派的推尊是分不开的。本文即以公安派的陶诗接受为研究视角,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此期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以及文学主张,同时也是研究陶诗接受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一、对陶渊明人格性情的重新解读
对于陶渊明的人品,历来都有论述与推崇,尤其是耻事二姓,入宋之作只书甲子的气节,在明代继续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普遍认同。王祎说:“陶氏世为晋臣,义不事二姓,故托为之辞以去。”(《自建昌州还经行庐山下记》)[1]182张以宁则认为渊明是因不遇明主而辞归:“昔无刘豫州,隆中老诸葛。所以陶彭泽,归兴不可遏。”(《题海陵石仲铭所藏渊明归隐图》)[2]523而在公安派作家那里,陶渊明“耻事二姓”的一面被淡化,陶渊明更多的是作为追求“适性”生活的形象:
每看陶潜,非不欲官者,非不丑贫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故竟“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悔耳。(《汤义仍》)[3]215
在袁宏道看来,陶渊明归隐田园最重要的原因既不是“耻事二姓”,也不是未遇明主,而是其“好适之心”与“厌劳之心”,以至于“宁乞食而不悔”。也就是说,陶渊明辞官归田的选择是本着自己的心性来决定的,是“适性”的结果。为什么会有对陶渊明的这种解读呢?这与他们自己“适性”的人生体验有关。如袁宏道在万历二十三年任吴县知县,到任不数月就向友人诉说:“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沈广乘书》)[3]242不久辞官,其后再度入仕,后又辞官归里。其在仕隐之间的这种选择,正是其追求“自适”生活的反映,他曾说:“鹦鹉不爱金笼而爱陇山者,桎其体也;雕鸠之鸟,不死于荒榛野草而死于稻粱者,违其性也。异类犹知自适,可以人而桎梏于衣冠,豢养于禄食邪?则亦可嗤之甚矣。”(《冯秀才其盛》)[3]480,这与陶渊明将官场比作“樊笼”是一个意思。江盈科也感叹为官之苦,说“官套笼人类缚鸡”(《同张幼于诸君游荷花荡》之七)[4]174,不愿意“笑面人前假,攒眉背后真”(《书怀》之一),希望回归“官至不束带”(《自述》)、“快活似仙人”(《自述》)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由此可见,他们对陶渊明的解读是有选择性的,主要是从渊明厌恶官场而归于自然的角度来看待。
对于渊明之归隐,袁宗道在《读渊明传》中也有详细的阐说:
人固好逸,亦复恶饥,未有厚于四肢,而薄于口者。渊明夷犹柳下,高卧窗前,身则逸矣,瓶无储粟,三旬九食,其如口何哉?今考其终始,一为州祭酒,再参建威军,三令彭泽,与世人奔走禄仕,以餍馋吻者等耳。观其自荐之辞曰:“聊欲弦歌,为三径资。”及得公田,亟命种秫,以求一醉,由此观之,渊明岂以藜藿为清,恶肉食而逃之哉?疎粗之骨,不堪拜起;慵惰之性,不惯簿书。虽欲不归而贫,贫而饿,不可得也。……然则渊明者,但可谓之审缓急,识重轻,见事透彻,去就瞥脱者耳。[5]292-293
他认为陶渊明出仕奔走本是为解决生活问题,是人之常情,与“奔走禄仕”的世人并无不同,但是“疏粗之骨不堪拜起,慵惰之性不惯簿书”,以至于辞官归里,过着“执杖耘丘,持钵乞食”的生活,虽然穷苦潦倒一些,但不至有性命之忧,假如久居官场反而可能丧身失命。这种对陶渊明出仕的解读无疑是大胆的,那就是陶渊明首先是一个人,一个需要靠物质来维持生存的人,并非生来就是清高孤傲的,可以说在追求物质生活方面与常人无异。但陶渊明终究是陶渊明,辞官归田,正是“见事透彻,去就瞥脱”的高明之处,这种处事方式也并非一般“禀性孤洁”所能为,而是缘于其对生活有透彻的感悟,所以中郎有诗云:“彭泽去官非为酒,漆园曳尾岂无才。”(《偶成》)[3]28也即陶渊明“超人万倍”之处在于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能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违自己的心性,所以袁宗道不认同萧统等人将陶渊明视为“恶嚣就静、厌华乐澹”之人,换言之,陶渊明是不能仅仅定义为“隐逸诗人”的。他们对陶渊明的这种认识,还表现在对陶渊明“狂”的阐释:
嗟乎,世无孔子,天下谁复思狂,而狂者之嘐嘐不顾,颇见刺于乡愿,世人右乡愿而左狂,则狂之不用常多而用常少。以生观之,若晋之陶潜,唐之李白,其识趣皆可大用,而世特无能用之者。世以若人为骚坛曲社之狂,初无意于用世也,故卒不用,而孰知无意于用者,乃其所以大用也。渊明之气似巽而实高,似和而实不恭,是故耻于见督邮,而不耻于为丐,其狂可见也。天下知其为耻于折腰之人,而不知其为耻事二姓之人,其狂不可见也。(《第五问》)[3]1519-1520
袁宏道对历来将陶渊明仅仅视作诗人与隐士表示不满,认为渊明与李白等人是用世之才,不能只作“骚人”观,为他们不能为用感到惋惜,提出了“无意于用者乃其所以大用”的新观点。另一方面,他认为“渊明之气似巽而实高,似和而实不恭”,这是一种“狂”气质,渊明之狂不仅在于清高自傲,更在于能于死生之际,“坦焉若倦鸟之投枝”,这与“不耻于为丐”一样,是一种超人的胆识,所以他说渊明是“亢而潜者”。袁中道则认为“陶潜之可仕而不物,以其性刚耳。”(《听雨堂记》)[6]530可以说,他们对渊明个性中“狂”的一面的解读,突破了单纯从耻事二姓的立场对之所作的简单化理解倾向,更多地看到陶渊明在当时的环境下所作出的人生选择时的复杂心理:“夫以阮籍、陶潜之达,而于生死之际,无以自解,不得已寄之于酒。”(《四牡歌序》)[6]453相应的,表面上平淡自然的陶诗正因寄托了诗人丰富的情感而更具深厚的内涵。
二、陶诗之“淡”与“文之真性灵”
陶诗“用平淡朴素的语言,表现出从肺腑中流出的真实感情,遂在文学史上放出一道异彩。”[7]108自然平淡的陶诗自唐宋以来对后世文人影响甚巨,但在此前,陶诗并不受到文坛的推崇。刘勰撰《文心雕龙》就不曾论及陶渊明,钱锺书说:“晋代人才,略备于《文心雕龙·才略》篇,三张、二陆、潘、左、刘、郭之徒,无不标其名字,加以品题,而独遗渊明。”[8]90钟嵘的《诗品》也只把渊明列为中品,所以钱锺书说刘勰、钟嵘都不是陶渊明的知音。陶诗在南北朝未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追求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的审美风尚格格不入,也即与当时的文学风气有关,“当时崇尚的是说理的玄言诗,渊明却还是用诗来反映他亲身感受的生活,来抒情言志;当时崇尚雕琢辞藻,渊明却用最朴实的语言来表达真挚的感情,构成平淡朴素的风格,含有深厚的情味”[7]104-105。陶诗平和冲淡的风格到了宋代得到高度评价与推崇。宋诗的“开山祖师”[9]22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梅尧臣《宛陵集》卷四十六),十分推尊陶诗,把平淡的诗风看成是创作的最高境界。
陶渊明在明初诗坛得到进一步的推崇与认同,宋濂《与章秀才论诗书》称:“独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虽出于太冲、景阳,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远韵,殆犹太羹充铡,不假盐醯,而至味自存者也。”(程敏政《明文衡》卷二十五)充分肯定陶诗已越过建安而远承《诗经》、楚辞。但明代前后七子掀起复古文学运动,提出古诗宗汉魏,近体法盛唐,对六朝诗歌大都持否定态度,对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多有贬抑,如李梦阳说:“大抵六朝之调悽宛,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章园饯会诗引》)[10]516得出了六朝诗歌靡弱的结论,自然是包含陶诗在内。何景明更是提出“诗弱于陶”(《与李空同论诗书》,何景明《大复集》卷三十二)的命题,胡应麟则说:“仲默称曹、刘、阮、陆,而不取陶、谢。陶,阮之变而淡也,唐古之滥觞也;谢,陆之增而华也,唐律之先兆也。”[11]74他们从师法“正体”的立场出发,将“变而淡”的陶诗摒弃于典范之外,可见他们并不欣赏陶诗之平淡自然。公安派则对陶诗有很高的评价,江盈科认为:“若晋魏六朝,则趋于软媚。纵有美才秀笔,终是风骨脆弱。惟曹氏父子,不乏横槊跃马之气;陶渊明超然尘外,独辟一家。盖人非六朝之人,故诗亦非六朝之诗。”[4]705袁宏道极力推崇陶诗之“淡”,且在《叙呙氏家绳集》提出陶诗之“淡”是“真性灵”:
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浓者不复薄,甘者不复辛,唯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风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虽有顾、吴,不能设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东野、长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极,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学,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3]1519-1520
袁宏道不但肯定“淡”所具有的审美价值,而且将“淡”的审美范畴引入“性灵说”之中,提出“淡”是“文之真性灵”,将“淡”的境界提升到诗歌的甚至是文学的审美制高点上。具体而言,“淡”就像“风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既然“淡”是“不可造”的,也即是不假雕饰的,那么诗歌之“淡”就是一种自然本色的表达。这种“淡之至”的境界,只有“元亮以之”,而孟郊与贾岛他们虽然也追求“淡”,但“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极”,可见他们是有意为之,非出自然,所以形成了“寒瘦”的风格,没有达到自然浑成的境界。白居易与苏轼“一累于理,一累于学”,都“非淡之本色”。显然,袁宏道所谓“淡”的诗歌审美范畴是与“自抒性灵”相联系的,此之“淡”是摒除闻见道理、直抒其情的一种审美理想。比较而言,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虽也较推崇陶诗的自然,但他认为陶诗之“淡”是一种锻炼之“工”的结果:“渊明托旨冲淡,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入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12]43显然与公安派所强调的真情自然抒发是大不相同的;而公安派把陶诗作为审美理想的典范而形成的尚“淡”的美学追求,不但丰富了“性灵说”的内涵,也是对复古派文学主张的反拨。
三、“陶公有诗趣”
“趣”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审美范畴之一。关于“趣”的理论,影响最大的当属严羽的“兴趣说”,而宋人在理学思潮的影响下,“理趣”又成为了诗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到了晚明,“趣”作为诗歌审美的重要范畴,被公安派着力标举。袁宏道《叙陈正甫 <会心集 >》就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3]463并认为:“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3]463-464袁宏道论“趣”主要是继承了李贽的“童心说”,摒弃了“道理闻见”的影响,认为“趣”是与“学问”对立的,是“得之自然”的。他更是将“趣”提到诗歌审美理想的高度:“夫诗以趣为主”(《西京稿序》)[3]1485,可见“趣”也是公安派的审美追求之一。那么,谁是“诗趣”之代表与典范呢?
袁宏道说:“仆尝谓六朝无诗,陶公有诗趣,谢公有诗料,余子碌碌无足观者。”(《与李龙湖》)[3]750将陶诗与“趣”紧密联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公安派所定义的陶诗之“趣”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趣”,陶诗之“趣”,首先是一种“恬澹之趣”(《程晋侯诗序》)[6]471的意境;其次,“趣”还与“真诗”相为表里。江盈科在论及“真诗”时提到了“趣”,他认为:“夫为诗者,若系真诗,虽不尽佳,亦必有趣。若出于假,非必不佳,即佳亦自无趣。”[4]43在江盈科看来,“趣”与“真诗”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真”,才有“趣”;而这个真,也即自然,不矫饰,不雕琢,既是内容之真,也是形式之真。他还曾在《舟中忆家》一诗中说“诗求得趣何论体”[4]128,足见“趣”在诗歌审美中的重要性。江氏在评价陆符卿之诗时,便以陶诗为参照,其中“趣”是最为重要的标准:
抑余谓先生之诗似靖节有说焉:盖诗有调有趣,调在诗之中,有目者所共见;若夫趣,则既在诗之中,又在诗之外,非深于诗者不能辨。故夫以调似靖节者,凡效陶之辈皆能之,如优孟学叔敖,衣冠笑貌俨然似也,然不可谓真叔敖也。若先生之似靖节,殊不在调,直以趣似。以趣似者,如湘灵之于帝妃,洛神之于甄后,形骸不具,而神情则固浑然无二矣。(《陆符卿诗集引》)[4]290
他提出的“趣”是“既在诗之中,又在诗之外”,看似说得玄妙,其实通过他将“调”与“趣”对举,可以见出他所谓的“调”是指诗歌的声调格律等形式方面的因素,而“趣”则是诗歌所蕴含的“神情”,所以“趣”不是“字模句拟”可得的,因此江盈科说:“余观陶靖节诗冲淡潇洒,妙在格律之外。六朝诸名士诗非不工,要于不求工而令工者引以为不及,则靖节一人而已。”(《陆符卿诗集引》)[4]289这里的“格律之外”就是诗之“趣”,也是不求工而能自工的高明之处。
四、公安派诗歌创作对陶诗之接受
陶渊明任真适性开田园一派,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公安派的作家,无论是袁宗道的闲情逸兴,还是袁宏道的懒于仕宦,他们崇尚自然本真的思想无疑是受到陶渊明的重要影响。陶渊明诗歌天然本色的语言,不假雕饰、恬淡自然的文学风格,也对公安派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袁宏道就创作了《桃源咏》四十余首,曹蕃评论“其诗语翩翩欲仙”[3]1698,此外,诗中常借渊明以明志,如《乞归不得》云:“不放陶潜去,空陈李密情。”[3]118《偶成》曰:“稽叔终疑傲,陶潜总任真。只因图事简,不敢恨家贫。宦邸为欢少,乡书报死频。弥天都是网,何处有闲身。”[3]123曾和韵陶诗,有《桃花源和靖节韵》,希望“长驱入仙林,遍觅心所契”[3]1015-1016。袁宗道的《咏怀》诗将自己与渊明对照,表达对闲适生活的向往:“矫矫陶彭泽,飘飘赋归田。六月北窗下,五柳衡门前。有巾将漉酒,有琴慵上弦。老死无储粟,扣门语可怜。……伊余慕古人,冉冉迫中年。局蹐忽已久,未得一日欢。幸有祖父庐,兼之江郭田。虽缺声伎奉,不乏腐儒餐。为白非所望,为陶谅难堪。揣分得所处,将处陶白间。”[5]7江盈科的创作也都平易明畅,他多次强调“诗从偶得不须敲”(《闲坐》),“信手题诗不忍删”(《春日睡起思归》),袁中道评其诗“多信心为之,或伤率意,至其佳处,清新绝伦”(《江进之传》)[6]727,而陶望龄的诗歌“为陶为柳……,啸吟烟云,超如也。”(《歇庵集序》,黄汝亨《寓林集》卷三)他还钟情于拟陶诗,有《病士拟陶七章》、《拟陶二首》等。
需要指出的是,公安派的学陶,不是句模字拟,而是重视其韵致神情,中郎就说:“今之学陶者,率如响榻,其勾画是也,而韵致非,故不类。”[3]1103可见,他们不仅有对陶诗理论上的阐释与高度评价,而且在创作上也接受了陶诗的熏陶,将“尊陶”落实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去。
五、公安派尊陶的文学史意义
由于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拟古风尚长期雄踞文坛,晚明以袁宏道为领袖的公安派力图扭转文风,举起革新大旗。袁宏道《叙小修诗》云:“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歩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3]118公安派秉持“代有文学”的发展观念,反对以时代先后作为判别文学优劣的标准,鲜明地指出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独特创造与价值。在这样的一种标准之下,他们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狭隘拟古主张,与此相联系,他们必然要肯定前此被复古派所贬抑的一些杰出作家。就整个六朝诗歌而言,公安派不是没有微词,但他们所不满的主要是“六朝骈丽饤饾之习”(《雪涛阁集序》)[3]710,在对古代典型的学习方面,他们要比七子派更加通融,袁中道就说:“读佳诗力能扛鼎,……但愿熟看六朝、初盛中唐诗,要令云烟花鸟灿烂牙颊,乃为妙耳。”(《答秦中罗解元》)[6]1053认为六朝诗歌也是应该认真学习的;而江盈科更是说:“陶渊明超然尘外,独辟一家,盖人非六朝之人,故诗亦非六朝之诗。”[4]705将陶渊明的文学地位突出于六朝之上,这与前后七子对陶诗的贬抑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11]58的情形之下,七子派提出文综秦汉,诗法汉魏、盛唐,但取法对象过于狭隘,且重模拟,并不能推陈出新。公安派对陶诗的充分肯定,实际上也是在回答拟古风气笼罩之下文学如何继续发展的一个问题,即应当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向古代典范学习。
其次,公安派希望通过对文学传统的反思与文学典范的确立来矫正当时诗坛之弊端。袁中道就指出:“诗之为道,绘素已耳。三代而上,绘即是素;三代而下,以绘参素。……近日文藻日繁,所少者非绘也,素也。”(《于少府诗序》)[6]471而“真能即素成绘者,其惟陶靖节乎?”(《程晋侯诗序》)[6]470所以他说“今晋侯迹大类于陶,皆得恬淡之趣者也。故其诗深厚隽永,可以救世之靡靡浮夸者焉,予所以乐为述也。”[6]471不难看出,袁中道认为当时的诗坛存在“文藻日繁”之弊,就必须要以“素”来矫正,而陶诗正是“即素成绘”最佳的典范,这也是他们着力标举陶诗,以之作为典范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江盈科《敝箧集叙》引用袁宏道语云:“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3]1685因此,他们提出“善论诗者,问其诗之真不真,不问其诗之唐不唐,盛不盛。”[4]699作诗先要求“真”。公安派以为“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你自己胸中流出”(《答李元善》)[3]786,这样的作品才是真诗、真文,而“陶靖节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而真率自然,则自为一源。”[13]306陶诗理所当然地成为公安派所提倡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想典范,故他们着意标举陶诗,这首先是基于他们自身所秉持的文学观念。
最后,需要对公安派从“崇苏”到“尊陶”的诗学进路作一些说明。公安派有较为明显的宗宋倾向,尤推苏轼,袁中道诗文集就名为《白苏斋类集》,袁宏道则称东坡为“诗之神”(《与李龙湖》)[3]750。而苏轼最为企慕的正是陶渊明,他说“渊明吾所师”(《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和东方有一士》诗后自注),先后和陶诗达百余首。东坡后期平淡而富于理趣的诗风也受到陶诗影响,李泽厚说:“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14]163可以说,陶诗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的确立与苏轼的推尊是分不开的。公安派则对陶诗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将平淡自然的陶诗提升到“真性灵”的高度,这无疑是对陶诗典范意义与审美价值的再次肯定与体认。
另一方面,公安派虽然提倡“独抒性灵”,反对拟古,但他们并不是彻底地否定向古代典型学习,而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要让自己的文学主张得到认同,也不能无所依傍,所以他们也在梳理文学传统,希望在文学传统中寻求切合自己主张的典范,以便获得理论与创作上的支撑。他们将陶诗之“淡”推尊为“真性灵”,又说“诗以趣为主”、“陶诗有诗趣”,无疑将陶诗作为他们“性灵”诗学的代言人。尽管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有抑陶的倾向,但陶渊明是唐宋以来公认的文学大家,其人格气节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这也是为什么何景明提出“诗弱于陶”之后立即遭到诸多质疑的原因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安派的“尊陶”,也是他们在反思文学传统、重建文学审美理想来抗衡复古派的过程中,为了宣扬自身文学主张与扩大流派影响的一种策略。
[1]王祎.王忠文集(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26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张以宁.翠屏集(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26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江盈科.江盈科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8.
[5]袁宗道.白苏斋类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周振甫.陶渊明和他的诗赋[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8]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9]刘克庄.后村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李梦阳.空同集(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62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1]胡应麟.诗薮(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刻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王世贞.艺苑卮言[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13]许学夷.诗源辩体(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崇祯刻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1672-2035(2015)04-0075-05
K206.2
A
2015-01-28
邓富华(1979-),男,四川苍溪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 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