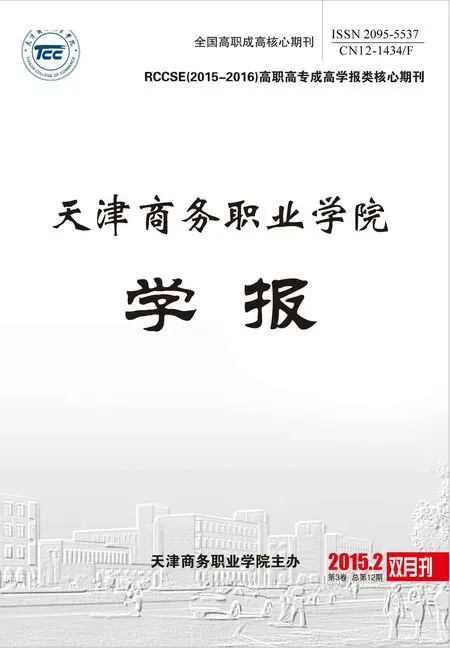王国维的学术三变
2015-02-12王晓蕾
王晓蕾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驻马店463000
一、国维生平——悲观的性格
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祖籍河南开封,他的父亲王乃誉经商,家境还算小康,但他自幼体弱多病,四岁丧母,造成了其一生孤僻又自卑的性格,他在《三十自序》(一)中也说到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他六岁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十六岁考取秀才,之后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都失败了。二十二岁来到上海,在《时务报》做书记、校对,后来结识了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一个人——罗振玉。于罗振玉东文学习社学习日文,戊戌变法失败后继续在东文社边工边读,跟随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学习西方文化知识。1902年赴日本留学学习物理,后因足疾返国,1903年后在江苏南通师范讲授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一家到日本,从事经史小学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1916年回国,为哈同办《学术丛刊》,任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22年任北大教授,1923年任溥仪“南书房行走”,1925年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其一生,大多颠沛流离,依靠罗振玉的接济生活,五十之年丧子,又与好友断绝关系,自卑忧郁的性格使他多愁善感,又具有诗人的忧郁气质,为了追求人生之理想,解决人生之问题,专心在学术上实践他的人生理想,在学术上的一变再变也正是他始终追求人生理想的体现。
二、“知”与“情”的矛盾——从哲学到文学
作为一个传统文人,王国维以遗老自居,但是实际上他对于政治不大关心,在日本学习期间也并不像那些爱国志士义愤填膺,他更像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的学者,他所追求更多的是自己的理想的实现,即追寻“人生之问题”的解答,他在《三十自序》中说道:“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宇宙之变化,人事之错综,日夜相迫于前,而要求吾人之解释,不得其解,则心不宁。叔本华谓人为行而上学之动物,洵不诳也。哲学实对此要求,而与吾人以解释。”在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之际,王国维接触到西方哲学。后于日本学习物理,翻译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仪神释。”对于哲学的热爱实际上是希望以求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重构,以实现精神价值的追求,发扬中国之学术。叔本华的哲学为他打开了这样一条中西贯通的道路,他曾经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陋儒可决也”。他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待中西方文化,认为中西文化有其相通的地方,可以共同繁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即开,互相推助。”怀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梦想,他潜心在哲学著作里一呆就是三、四年。他的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同时忧郁的性格使他更为敏感,一旦接触到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则更加深了他的忧郁。一直到1904年的春天,王国维皆与叔本华为伴,自称“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王国维是个知情兼胜的人,他自己也曾分析到自己的性格:“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也。”“立论虽全在叔氏之脚地,然于第四章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他指出西方形而上的哲学确是能够给人以思辨的力量,但是他更认为魏源所介绍的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更为可信,而他之后从事史学研究也是按照实证主义的精神来实现的。王国维主动从以纯粹思辨、诉诸理性的西方哲学中撤退出来,而转向中国诉诸感性、悟性的传统文化中来,对于西方哲学的怀疑以及性格的矛盾导致他又转向了文学的研究,从事诗的创作。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知情兼胜的人,在感性感悟的同时又不失理性分析,所以在文学理论,尤其是诗词理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1906年辑《人间词话甲稿》,第二年又辑成《人间词话乙稿》。不同于前人的词话,可谓是一本中国总结式的诗词评论,尤其对于“境界”理论的提出,使他成为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者,而“境界”也可以说是他所追求的人生之理想境界。他为我们描述了三种人生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宴同叔)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三变)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此第三境界也。”“境界”的蕴意要比“意境”更有外延,“意境”单指文学之境界,而“境界”则将“意境”泛化,是人生的理想,生命的原则,以及自我实现和肯定的途径,包含了作者生命存在价值的指向,是他人生理想的最高追求,而王国维的治学途径和这人生三境界也是一致的,于日本求学,经历苦闷与彷徨,最后终于确认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所在。
三、“可爱”与“可信”的融合——从文学到经史考据
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一家随罗振玉到日本避难,在日本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到罗振玉的大云书库,丰富的藏书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历史典籍,为他从事经史考据打下了坚实基础,有人认为王国维钻到故纸堆里是为了躲避现实,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也是当时历史环境所迫,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对“人生之问题”的追解,于哲学,于文学,都不能满足他的理想,那么几千年前的文物这些看起来与现实社会相去甚远的东西就能实现他的理想了么?他也曾经指出“是以欧战之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大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礼。”(《政学异同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使他又回到经史考据上来。
王国维所追求的是“可爱”与“可信”之间的统一,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支撑点,于这“可爱”的中国传统中求得“可信”,落实到整个中国社会,便是社会理想的重构,人文精神价值的实现,王国维认为:“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思古之情”使他回到中国传统中去,“求新之念”使他又用新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眼中,中国哲学的最高形式也就是政治道德在社会中的体现,这种哲学是“可信”的哲学,他理想中的社会是“德治”的社会,王国维曾经说过:“……此六者,皆周而始有定制,皆周所以治天下之术,而其本原在德治。”怀着这样人文精神价值的探索,王国维终于写成了让他名声远播的论文——《殷周制度考》。“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王国维认为周的传子制度是进步的,可以稳定社会,做到息事宁人,“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间不免有争位之事,特如传弟既尽之后,则嗣立者当为兄之子欤?弟之子欤?以理论之,自当立兄之子;以事实语之,则所立者往往为弟之子。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而周人传子之制,正为救此弊而设也。”(《殷周制度考》)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所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积淀莫不是这样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制度是基础,在此制度之中实际上所蕴含的是中国最传统的人文精神,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实现人生的理想。
郭湛波说,王国维继考证学之续,由古籍至古器物,然后至甲骨文,而甲骨文‘适为中国社会史之据’。对于史学上的贡献,王国维超越了乾嘉学派,开一代之新风,他的“二重证据法”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辉煌的道路,对此陈寅恪有高度的评价,他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写道:“评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其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眼晕考等是也。”其二,是以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传统文化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史》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是也”。其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剧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并且进一步提出:“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尽符合,要皆足以转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
而事实证明了陈寅恪对于王国维的评价。近一个世纪以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我国经史考据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沿用至今,这样严谨的治学作风正是王国维对于“可信”的追求,于自己的人生理想的实现找到确凿的依据。他进入到经史考据的研究中,也是自我的一种回归,也是对自我、对本民族精神价值的确认,也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以及传统文化建构找到了依据和支点,所以,王国维在学术领域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学术的推进,也是其人生的自我实践,更为整个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于当今之世确立新的制度、新的价值体系,是对过去的突破,也是对未来的开拓。西方哲学并不能解决王国维的人生之问题,同样也不能解决中国之问题,中国并不缺少形而上的哲学,只是中国的哲学更关注于人生,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化无形于有形,是“可爱”与“可信”的完美结合,为人生问题的解答,王国维至此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从哲学到文学,再由文学到经史考据,王国维的学术之路也是他追求人生理想,解决“人生之问题”的道路,他企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来实现社会体制的健全,但其实现人文精神传承的愿望还是破灭了,“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际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其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金明馆丛稿二编》)王国维就是这样一个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欲求中国精神发扬光大的人,但实际上,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得王国维在学术上所做的努力并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实现。但他的学术思想是永存的。
[1]刘烜.王国维评传[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2]王国维.静安文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