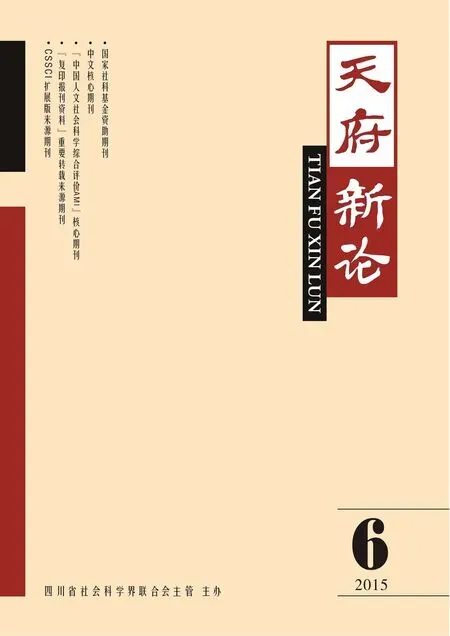18至20世纪初缅甸的滇商会馆及其经济影响
2015-02-12马晓粉
马晓粉
18至20世纪初缅甸的滇商会馆及其经济影响
马晓粉
自“蜀身毒道”开辟以来,云南就与缅甸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18至20世纪初,滇商积极活跃在这条商道上,并在缅甸伊洛瓦底江沿线多个城镇建立起商人组织——云南会馆,以严密的组织性和高度的互助性在缅甸开展商业活动。这使得滇商整体实力增强,贸易迅速拓展;促进了滇缅贸易的繁荣,密切了中缅国际区域市场的联系;带动了缅甸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云南边疆、缅甸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滇商会馆;互助平台;滇缅贸易;国际区域市场
有关专家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张骞曾在大夏国见到蜀布和邛竹杖的相关记载考证,早在汉代,中国西南地区就已开辟出一条自成都经过云南大理、保山、腾冲到达缅甸,再从缅甸到印度的商道,〔1〕学者将其称为“蜀身毒道”、“贝币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这条商道的开辟,直接将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缅甸、泰国、印度等地区市场联系起来。其中,云南与缅甸领土相接壤,经济联系也最为紧密。18世纪以后,滇缅贸易繁荣程度达到历史高峰,期间入缅经商的滇商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在缅甸结成利益联盟——商人会馆,以团体方式开展其在缅甸的贸易活动。
商人会馆最早出现于明,兴盛于清,至清末中国商会成立后,逐渐淡出经济史舞台。它是中国同乡商人以地缘为纽带或同业商人以业缘为纽带,以祀神、聚会和推进业务为目的而建立的民间经济组织。它将祠庙建筑与商人组织办公地合二为一,形成“馆庙合一”的组建特色;并将“天人合一”、“乡情”或“业缘”等传统文化因素融入到组织内部管理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商人会馆不仅是中国商人国内贸易拓展中普遍采用的组织方式,也是中国商人外海贸易拓展中普遍采用的组织方式。缅甸滇商会馆(云南会馆)就是滇省商人在缅甸开拓贸易时建立的商人经济组织,它对滇商贸易拓展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前,学界对中国国内商人会馆的关注较多,成果丰硕;而对海外中国商人会馆的研究较少。王日根〔2〕、闫彩琴〔3〕、谭志词〔4〕、野泽知弘〔5〕几位学者分别对新加坡、越南、柬埔寨地区的中国商人会馆进行了研究,但尚未出现对缅甸滇商会馆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18至20世纪初的滇商会馆进行研究,揭示滇商组织在滇商贸易拓展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为今天“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缅甸滇商会馆发展概况
由于“馆庙合一”是商人会馆组织的一大组建特色,故民间多以会馆建筑群主体建筑的名称来指代会馆,会馆“庙”、“宫”、“寺”等主体建筑的建立,也标志着该商人会馆组织的成立。滇商会馆,俗称“观音寺”、“关圣寿台”或“土地祠”等,这些祠庙建筑在缅甸的建立,表明滇商已在该地建立了商人组织,而会馆的迁移、发展历程则反映了滇商经济组织的迁移、发展历程。
(一)18世纪以前
自汉代“博南古道”开辟以后,中国历代文献中均有关于云南永昌(今保山地区)市场出售来自东南亚、南亚诸国货物的记载,其中玉石、棉木等商品则来自缅甸。相对于云南与缅甸互市的悠久历史,文献关于滇商入缅经商的历史记载则晚至明代(大约为16世纪)才出现,当时数万名来自云南“三宣六尉”的滇商已在缅甸大明街(今八莫)从事商业贸易活动。〔6〕但其人数和经济影响力有限,目前尚未发现18世纪以前缅甸存在滇商会馆的资料,说明在此之前缅甸没有滇商会馆组织。
(二)18、19世纪滇商会馆的建立
18至19世纪中叶,中国海禁未开,滇缅陆路(博南古道)成为中缅印区域市场联系互动的主要通道。滇商凭借地缘优势,大量涌入缅甸经商。据中国官方的一份奏报记载,当时“腾越州和顺乡一带民人”在缅甸贸易者较多,〔7〕实际上,除了腾越州(今腾冲)商人以外,滇省大理、鹤庆等地的商人也有不少在缅甸经商的。由于滇缅商道实际上是狭窄的山道,交通运输几乎靠畜力完成,故入缅贸易的滇商大多是一队马帮,由一位或几位大商人(货主),数十上百匹骡马以及赶马人,还有其他跟随马帮入缅的小商贩组成,他们于每年雨季过后自云南驮运商品入缅甸八莫销售,次年收购缅甸商品回国,周而复始。
随着滇商贸易在缅甸的顺利推进,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在缅甸客居,或就地售卖货物,或在商道沿途开客栈、货栈为滇商提供服务。这样,缅甸的滇商既有季节性行商,也有定居坐商,为便于行商、坐贾之间相互联系、互相帮助,滇商联合起来结成利益联盟,在伊洛瓦底流域的首都瓦城以及新街(八莫)、金多堰建立了滇商经济组织——云南会馆。
缅甸首都瓦城是滇商聚集的重要商业城市,滇侨所称的瓦城实际上包括古都阿瓦、阿摩罗布罗(今洞缪)和曼德勒,①1783年以前阿瓦是缅甸首都,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缅王迁都阿瓦北郊的阿摩罗补罗,然仍属于阿瓦辖区;1859年(咸丰九年),缅敏同王再次北迁都城至曼德勒,华侨则延称此两地为瓦城。滇商在后两地均建有商人会馆,其中阿摩罗布罗(今洞缪)滇商会馆始建时间最早,规模最大。
阿摩罗布罗(今洞缪)滇商会馆建于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位于汉人街,以寺为馆,以馆为滇商组织。据《重修观音寺功德小引》〔8〕载:“瓦城观音寺者,溯自乾隆三十八年汉并秦凯后,继以两国修睦,商人渐进……斯时地广人稀,建立斯寺”。1773年中缅战争结束后,两国商业贸易逐渐恢复,滇商陆续到此贸易,修建了云南会馆“观音寺”。此时的滇商会馆规模并不大,“只供石胎佛像菩萨一尊”,“已觉室小殿窄”。数年后,阿摩罗布罗(今洞缪)的滇商会馆组织人数越聚越多,滇商贸易商品数量剧增,规模逐渐扩大。
1815年(嘉庆十五年),洞缪滇商会馆被大火焚毁,“一经祝融,殿宇菩萨概行被毁”,会员随即重修;1829年(道光九年),会馆“经装焊山门”,不料山门被焚毁,“速修补建”;1837年(道光十七年)云南回乱波及缅甸,滇商会馆被焚,次年重修,并于1846(道光二十六)竣工。〔9〕自1815年至1846年,短短31年间洞缪滇商会馆三度遭受火灾,三度重修,尽管前两次重修规模并未扩大,但其维修速度非常快。1837年滇商会馆彻底被焚,会员协商后决定重修并扩大会馆规模,“翕同垫告缅王讨要后地,幸蒙赐给得地十有余丈,……而暗备地价向各地主善买,已费银千余金矣”。〔10〕新落成的会馆规模宏伟,庄严华丽,由照壁、山门、正殿、配殿、客厅、两厢、客厢、天井、僧房、厨房等建筑组成,历时八载,耗资(一元改银)银数千金,彰显了滇商组织强大的经济实力。
1859年(咸丰九年),缅敏同王将都城从阿摩罗布罗(今洞缪)北迁至曼德勒,滇商又在新都曼德勒修建了会馆,是为新馆。据《重修瓦城云南会馆序》〔11〕载:“继后缅王迁都瓦城(曼德勒),吾滇客缅先达为增新建会馆乃向缅王申请,获赐汉人街中心地基,平敞宽阔,即现有之馆址也”。曼德勒滇商会馆坐落于汉人街中心地段,市肆栉比,万商云集,乃商业繁华区,会馆由山门牌坊、戏台、两厢、正殿、两天井、大厅、客堂、厨房、仓库等建筑组成,装饰华丽、规模雄伟、美轮美奂。值得一提的是,该馆是由滇侨商人尹蓉倡修的,其时任缅王经济事务顾问,在缅商以及滇商中威望较高,他出面向缅王讨要了汉人街中心地基并牵头出资修建曼德勒云南会馆。据说,当时云南会馆奠基所需木材由缅王钦赐随山砍伐,石匠、木工由国内剑川、鹤庆、丽江聘请,〔12〕会馆建立后初成为“腾冲会馆”,后更名为“迤西会馆”。
除了商业大都市瓦城以外,滇商还在伊洛瓦底江重要商业港口新街(今八莫)修建了滇商会馆。新街(今八莫)是滇商入缅到达的第一站,距蛮暮数十里,位于伊洛瓦底江上游东岸,乃大盈江入金沙江之口,伊洛瓦底江自此以下可以通航,地当水陆要冲。新街(八莫)滇商会馆,俗称“关汉寿行台”或“关圣庙”,建于1806年(嘉庆十一年)。新街滇商会馆规模虽然不及首都瓦城云南会馆那般宏伟,但在当地建筑中堪称宏大,1871年(同治十年)中国使缅大臣王芝曾称,新街滇商“以关汉寿行台为会馆,楼台廊阁壮丽”;〔13〕1879年(光绪五年)黄楙材路过新街(八莫)亦称滇商“建关圣庙为会馆,回廊戏台,规模宏敞”,〔14〕王、黄二人所述“关汉寿行台”、“关圣庙”为同一建筑,就是滇商所建会馆。
此外,在阿摩罗布罗(今洞缪)通向曼德勒之间的金多堰修有一所滇侨于明代所建的“土地祠”。其始建之初,乃滇侨供奉土地神之祠,19世纪滇商势力扩大之后,在此成立会馆组织,借土地祠为会馆。据《洞缪观音寺修葺始末》碑刻记载:“迨至缅王们董(敏同)时代迁都瓦城,侨商旋随迁移,复经吾滇先辈筹建瓦城云南会馆……斯时由瓦城云南同乡推举管事,兼管瓦城云南会馆、洞缪观音寺、金多堰土地祠三处事务,……每年于佛诞节日按例输值分别于该三址,举行庆祝,沿袭至今将百年”,〔15〕由此可知,金多堰“土地祠”实际上起着云南会馆的作用。
(三)20世纪以后滇商会馆的演变
20世纪早期,滇缅陆路贸易逐渐受中国海上贸易、红河水陆贸易、滇越铁路贸易的排挤,其繁荣程度不及18、19世纪,滇商在缅甸各地的会馆依然维持运转,但未扩建或新增。后来,随着国内商会的成立以及各类会馆的演变,缅甸滇商会馆逐渐演变为“云南同乡会”。
二、缅甸滇商会馆的主要功能
滇商翻越崇山峻岭到缅甸是为了求富,但却不惜重金在伊洛瓦底江各商业港口繁华之区兴建会馆祠庙,这似乎与他们追求经济利益的初衷相矛盾。实则不然,这些会馆在滇商贸易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其一,滇商会馆为在缅甸滇商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联系和互助平台,有助于滇商在商业竞争中取得胜利。滇缅边境相连,然自然环境恶劣,交通条件差,滇商需越过滇缅边境的崇山峻岭方可到达新街(八莫),陆路交通实际上是高山中间的一条狭窄小路,只可徒步或依靠马力行进。从新街(八莫)而下的水陆亦非一路顺风,正所谓“到八莫,又焦着,过水乘舟,怕的是,船又小,木头腐朽;又焦着,投江边,遇着漂流”,〔16〕路途上的艰难险阻可见一斑。尽管18世纪以后的滇商是以马帮或商帮集体入缅贸易,但是,马帮或商帮只是同乡人之间较为松散的群体,他们之间可以存在利益联系,也可以不存在利益联系,“制度性弱,系统性差,且没有固定的联络、互助平台”。〔17〕滇商所从事的长途贩运贸易,运输距离长、运输商品量大,而运输条件恶劣,运输周期较长,如果滇商仅以马帮或商帮形式开展季节性往返贸易,不仅贸易成本较大,还存在信息过期导致商品滞销的风险。如果国内、缅甸滇商能够相互协作,将商品的收购、运输、销售有机分工、链接起来,不仅能够降低经营风险和成本,也能使整个贸易链良性循环。当滇商在滇缅贸易不断拓展时,这种互助协作越显重要,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固定的、有制度、有体系的经济组织,来配合他们完成在当地贸易活动。
于是,滇商采用当时国内地域商人普遍采用的组织方式——会馆作为其在缅甸的利益联盟,他们在已有马帮、商帮基础上联合滇籍(或为某一府州、或为全省)同乡行商、坐贾一起在缅甸重要港口建立了会馆,形成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性的地域性利益集团,集团成员仅为滇籍商人,共通的语言、习俗、乡情、亲情使他们之间能够很快建立起互助关系,它能够帮助个体商人克服困难,在竞争中获胜。
这种互助性体现在信息共享以及商品的购、运、销方面。商业信息对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不过古代商人所面临的信息流通环境较差,信息闭塞、流通较慢,而且商人在异国经商语言不通、异地商人的排斥等因素都使得商人获取信息的难度较大。滇商建立会馆后,缅甸沿江流域各地商人之间建立起系统的信息交流平台,除了会馆内部成员常规的商业信息交流、传递之外,他们还通过会馆重要聚会,将各地会馆成员聚集到一起,进一步增强各港口商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助。如,1846年(道光二十六)洞缪云南会馆新建落成典礼上,来自八莫的马锅头、缅甸各地的丝商、各商号都聚集于云南会馆,〔18〕可以推测,在这样的聚会中马锅头、丝商、玉石商等必定会互通信息,丝商、玉石商可向马锅头获取商品流向、流量等信息,马锅头亦可以向丝商等招揽生意。商品的购、运、销互助是缅甸滇商会馆的最重要、最突出功能,各港口的云南会馆之间是相互联系、互助、合作的。滇商从中国贩运货物入缅,先到八莫,再通过八莫云南会馆商人组织分销、运输至缅京,货物到缅京后又由京都云南会馆商人组织销售。这样,不仅能够避免滇商与缅甸交易中缅商出尔反尔拒绝支付货款的现象,还能使滇商贩运的商品流通顺畅,缩小资金周转周期,提升了滇商的竞争力。
其二,滇商会馆有助于商人规范贸易秩序、争取合法权益,维护在缅滇商利益。滇商在缅甸经商,不仅会面临缅甸本土商人的竞争,甚至是不平等竞争,还会面临来自缅甸政府的责难或苛刻。如,18世纪一位中国商人罗立请求缅甸地方官员允许他在南巴村(八莫地区)建一座跨越太平江(伊洛瓦底江)的桥梁,以便贸易能够顺畅进行,缅甸地方官员因罗立态度不好将其逮捕,当他被释放回到八莫时发现自己的货物少了许多,于是向缅甸地方政府提出赔偿要求却被拒绝。〔19〕再如,一对大约有二千匹马组成的中国商队在缅甸与缅商做生意,缅商却不肯支付滇商货款。〔20〕故,良好的经营环境以及贸易秩序对滇商至关重要,他们无法获得来自国内清政府的外交保护,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争取他们在缅甸的合法权益。
滇商会馆建立后,它通过各种渠道或方式与缅甸政府结成友好关系,争取政府对滇商贸易的支持。比如,会馆举办重要庆祝或聚会互动时,宴请政府官员出席,增进滇商与缅甸官员的交流、沟通,以一种轻松方式进行磋商,或请求官员给予贸易优惠,或与官员沟通贸易行情,以期获得政府官员的支持和庇护,维护滇商合法权益。事实证明,缅甸滇商会馆确实与缅甸各级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洞缪云南会馆、曼德勒云南会馆修建时均向缅王讨要或赐予商业区土地修建会馆;1846年洞缪云南会馆竣工开馆典礼上,缅甸税务官(蕴们)、中国事务官(德禄蕴们)、各地头人孟宾斗等参与会馆捐款。〔21〕
尽管缅甸滇商会馆碑刻或文献资料并未记录下缅甸官员给予滇商的商业优惠政策,但是,从同时期外国人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窥到一些信息。1836年,英国人布莱尔记录到:去年(1835年)韩莱①英国官员,1835年出使缅甸,希望缅甸官方支持英国官员调查缅甸通往中国的道路。“离开阿瓦不久以后,即有自阿瓦来的中国商人代表团觐见明塔吉亲王,抗议韩莱的使命”,“这是因为他们恐怕丧失掉他们长期以来执掌的阿瓦北部贸易的专利以及琥珀、青玉出产的专利”。〔22〕1836年,滇商已经在缅甸洞缪建立起商人会馆组织,而且是洞缪唯一的滇商组织,故笔者认为布莱尔所指“中国商人代表团”就是滇商会馆组织派出的商人。他们觐见亲王的目的是为了抗议韩莱的使命,以维护滇商在缅甸贸易专利。
当然,在滇商会馆组织内部,会馆可通过制定规则、约定俗成、集体商议的方式来规范滇商所从事的行业规则。如,滇商在八莫云南会馆“关帝庙”内设立了“丝花公会”,毋庸置疑其目的是为了处理丝花贸易相关事务。再如,洞缪滇商会馆《重修观音寺功德小引》碑刻记载,该馆向丝花、京广杂货行抽收厘金,抽收比率由会馆商议决定。〔23〕这则资料也向我们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滇商会馆组织下附设丝花、京广杂货行,受会馆组织统一管理和领导。
其三,会馆有助于提升滇商的凝聚力和竞争力。滇商会馆“馆庙合一”的建筑格局是有一定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的,它不仅是供奉神灵或先哲的圣殿,也是商人在异乡的精神家园。祠庙的设置和建立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强商人组织的内部凝聚力,提升滇商的整体竞争力。
缅甸洞缪、曼德勒、八莫滇商会馆的正殿分别供奉观音、关公、孔圣诸神、先哲,这些神是背井离乡的滇商心中的保护神。观音(观世音菩萨),是佛教中慈悲和智慧的象征,他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只要供奉者诚挚称念“观音菩萨”,并向其许愿,就能得到观音的帮助,获得救赎、实现愿望,滇商供奉观音希望随时随地获得观音的援助和庇护。关公,乃三国时期著名将领关羽,中国各朝官方将其视为忠义的化身,并奉于各种封号,清代朝廷奉其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在民间,关公不仅是忠义、诚信的化身,也是民众信仰的“救世主”、“武财神”,受到各地商人的供奉。滇商供奉“关帝”不仅由于他武艺超群,能够救苦救难,忠义诚信;还由于他是“财神”,能够招财进宝,从而保佑滇商经营活动大吉大利,财源滚滚。滇商供奉这些神灵,借助神灵的“神性”消除心中的恐惧和不安,使他们感到有神灵的庇护,其经营活动就能顺利进行,保证贸易成员的稳定性和贸易活动的持续性。
此外,滇商会馆还设有厢房、客厅、仓库、施棺会、养病院等,〔24〕给予同乡帮助。如,阿摩罗布罗(洞缪)云南会馆于1846年新建时设立的“客厢”,即供往来滇商住宿之用。新街(八莫)云南会馆“关圣行台”也为商人以及华侨提供住宿,光绪年间黄楙材路过新街便居住在该馆,“抵新街,寓于关帝庙”,〔25〕会馆能为往来中国官员提供住宿,必然会为滇商提供住宿服务,滇商携带的货物亦可随身寄存于馆内。施棺会、养病院则给予贫困滇籍商人、工人各种帮助,使他们能更好地投入贸易活动中。滇商会馆的这些祀神、宴会、慈善等活动增进了同乡商人之间的友谊,增强了滇商团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三、缅甸滇商会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缅甸滇商会馆的建立,使滇商成为具有严密组织性的商业队伍,他们以缅甸各地会馆为贸易链接中心,在滇缅以及缅甸沿江流域地区从事商业活动,对中缅区域经济的联系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推动了滇商缅甸贸易的拓展。缅甸滇商会馆建立以前,滇商大多从事季节性贩运贸易,他们以“三百至四百头牛,或以两千匹小马在中国及八莫间运送丝绸及其他货品”,①〔英〕安徒生博士在《进八莫云南西部远征队报告》中引布莱尔《缅甸年代记译文》。见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连载之二),《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1期。滇商的作用似乎仅限于往来于腾冲和八莫之间“运送”商品,资本实力、社会影响力有限。1773年后,越来越多的滇商“鱼贯而入,客货渐次宏通”,〔26〕他们联合在首都近郊洞缪建立了会馆,标志着缅甸滇商从松散的马帮、小商帮发展成为一个有制度、有体系的商业团体。滇商会馆将单个滇商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整合起来,增进会员商人之间的联系、互助、合作,使滇商群体资本实力增强,为滇商贸易的拓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会馆通过举办宴会活动、私人社会关系等渠道,与缅甸王室、各级官员结成友好关系,提升了滇商群体声誉和社会影响力,为滇商贸易的拓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滇商在缅甸首都瓦城的贸易日益繁荣,经营项目包括丝、棉、玉石、纺织、京广杂货等行业,不少商人还在此开始了商号或分号,洞缪逐渐发展成为滇商缅甸贸易的聚散中心。
随着滇商资本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他们于1806年、1859年前后在八莫、曼德勒、金多堰建立了会馆,从而将整个伊洛瓦底江上游贸易链接起来,并在沿途开辟了大小商埠50余个,“轮船停泊,装卸货客之大埠二十三个,小埠二十九个”,②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四,光绪十八年四月十一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512~513页。此据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15-1316页。主导着伊洛瓦底江上游各商埠贸易的发展。
其次,促进了滇缅贸易的繁荣,加强了中缅国际区域市场的联系。滇商掌控沿江上游各港口后,他们贩运的商品能够顺利进出各港,并在各港实现运、销、售一体化,刺激着滇缅贸易的不断发展和繁荣。资料显示,18至20世纪初滇商会馆整合下的滇缅贸易主要是丝绵贸易,1773年洞缪滇商会馆组建时其成员大多是经营丝、绵(棉花)贸易的商人,“商人渐进,丝绵往来,裕国通商”,〔27〕此后,这两项贸易一直成为滇商会馆组织的重要业务。滇商在洞缪和八莫滇商会馆内专设了“丝花行会”,负责丝、棉花交易事务,从而将中缅丝绵贸易发展推到历史高峰。有学者评估,19世纪20年代缅甸每年输入云南的棉花货值超过20万英镑,重量不下500万公斤,〔28〕这相当于19世纪初滇缅贸易总额(30-40万英镑〔29〕)的66.67%-50%; 19世纪晚期,仅滇商会馆会员永茂祥号每年运销缅甸的丝就达二千担左右。〔30〕除丝绵之外,中国所产铜、锡、铝、金、银等有色金属矿以及丝、熟丝、绒、鞋、纸等日用百货以及缅甸所产棉花、玉石、宝石、雀毛、鹿角等商品也是滇商会馆组织的贸易项目,商品结构多元,贸易总额不断上升,至19世纪中叶,双边贸易额从初期的30-40万镑上升到50万英镑。〔31〕
再次,加强了中国四川、云南等地市场与缅甸八莫、洞缪、曼德勒区域市场的联系和互动。在滇商会馆组织的链接下,缅甸滇商通过在国内修建的云南会馆取得联系、互助,他们收购云南市场上剩余的铜、锡矿产,还收购中国川、赣、楚等地商人从内地市场贩来的丝、熟丝、京广杂货等商品到缅甸八莫、猛拱、瓦城销售;在缅甸,滇商会馆组织会员商人从缅甸各地收购棉花、雀羽、鹿角或收购、开采宝石矿运回云南,棉花主要分销至云南各地市场,宝石、雀羽、黑漆等则由国内滇商会馆或其他内地商人会馆组织贩运至滇、川、湖广、粤地市场销售。这样,不仅实现了云南市场与缅甸市场的直接联系和互动,还实现了中国内地市场与缅甸各地市场的联系和互动,这种联系、互动随着滇缅贸易的繁荣而日益加强。滇商贸易缅甸市场上的商品,有一部分经滇商、印度商等国商人“从仰光出口,经过加尔各答而往亚洲西部及欧洲”,〔32〕尽管这些出口商品的数量远不及销售到缅甸市场上的商品数量,但它却成为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互动的一种方式。
复次,带动了缅甸纺织业、采矿业的发展。滇商会馆不仅协助滇籍贩运、销售商将缅甸棉花、玉石等商品运销至中国销售,而且还协助滇商在缅甸发展纺织、棉花种植和宝石开采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滇商会馆组织的最大特性就是能够为会员商人提供来自同行以及社会各界的联系和互助。滇商为了打开丝商品在缅甸的销售市场,在曼德勒地区开设纺织作坊,利用中国国内的纺织技术,通过会馆组织招募滇籍工人,运用中国丝纺织出“缅布”,再将成品“缅布”通过会馆组织分销到缅甸各地。运销售、纺织商、经销商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占领了缅甸纺织品市场,使滇商纺织业兴盛起来,也使曼德勒发展成缅甸重要的纺织品工业区,至今如此。在棉花种植、宝石开采行业,滇商依然利用会馆组织的联系和互动平台,利用滇商资本、中国技术、同籍工匠或工人组织种植或开采,再将产品专销给同籍商人或直接运销到中国,使缅甸宝石开采业和棉花种植业有了很大发展。
综上所论,18至20世纪期间,滇商在缅甸沿江各港口城镇兴建了滇商会馆,使分散的滇商结成一个组织严密的利益联盟,将云南——缅甸伊洛瓦底江贸易链接起来。滇商整体实力增强,贸易链接畅通,贸易规模拓展,促进了滇缅贸易的繁荣,加强中国与缅甸市场的联系和互动,带动了缅甸纺织业、采矿业和棉花种植业的发展,为云南边疆和缅甸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现今,缅甸云南会馆演变为云南同乡会,会员们依然秉承先贤们创立会馆之初衷,为从事两国商业贸易的滇籍商人提供联系和帮助。
〔1〕李俊.西南丝绸之路与云南贝币的流通〔J〕.云南文物,1994,(38).
〔2〕王日根.中国会馆史〔M〕.东方出版中心,2007.
〔3〕闫彩琴.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越南华人会馆初探〔J〕.兰台世界,2012,(6).
〔4〕谭志词.越南河内历史上的关公庙与华侨华人〔J〕.南洋问题研究,2005,(2).
〔5〕〔日〕野泽知弘.柬埔寨的华人社会——从潮州会馆和陈氏宗亲会看华人社团的国际化〔J〕.南洋问题研究,2011,(3).
〔6〕〔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M〕.中华书局,1985.6.
〔7〕乾隆三十三年九月“谕军机大臣等、阿里衮等奏”〔A〕.清高宗实录〔C〕.中华书局,1987.卷818.
〔8〕〔9〕〔10〕〔18〕〔21〕〔23〕〔26〕〔27〕重修观音寺功德小引〔A〕.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C〕.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11〕〔24〕重修瓦城云南会馆序〔A〕.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C〕.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12〕缅甸云南同乡会.缅甸云南会馆史略〔Z〕.内部印刷资料,2007.
〔13〕王芝.海客日潭〔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卷1.
〔14〕〔25〕黄楙材.西輶日记〔M〕.光绪十二年(1886年)刻本.
〔15〕洞缪观音寺修葺始末〔A〕.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C〕.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16〕佚名.阳温暾小引〔Z〕.腾冲和顺手抄本.
〔17〕马晓粉.清代云南的商人会馆及其经济影响〔J〕.思想战线,2014,(5).
〔19〕〔20〕〔22〕〔32〕〔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连载之二)〔J〕.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1).
〔28〕〔29〕〔英〕克劳福.阿瓦宫廷某大使日记Journal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Ava〔A〕.贺圣达.缅甸史〔C〕.人民出版社,1992.214.
〔30〕腾冲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Z〕.1991.24,29.
〔31〕Dorothy woodman,The making of Burma,London:The cresset press,1962,p.173.
(责任编辑:谢莲碧)
F1
A
1004-0633(2015)06-155-6
2015-10-08
马晓粉,历史学博士,曲靖师范学院铜商文化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史、云南地方史。云南曲靖65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