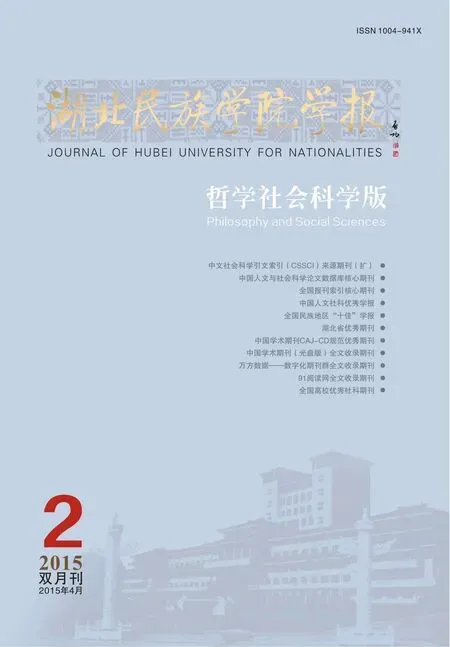“文”“章”学的意义诠释
2015-02-10金春岚
金春岚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200237)
“文”“章”学的意义诠释
金春岚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200237)
回顾我国几千年的文章学的基本理念,“文”、“章”与“文章”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义。究其根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文人正是通过“文”来获得社会存在的基本价值,来与人沟通,来实现与社会的“共存”的意义。通过文章达到“公器”的要求,于是产生“大我”,最终实现了为“文”之人的“外王内圣”的价值理性。
文;章;文章学;意义
一、 文章学中“文”之涵义
“文”之生态涵义首先体现在其字面意义上,是一种贯穿和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共存的“礼仪”和“仪式”,这是生态学中人与周围环境和谐的最高境界。
文,《说文解字》解释为“错画也。” 而《易·系辞》解释为:“物相杂,故曰文。”《周礼·天官·典丝》“供其丝纩组文之物。”到了《礼·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而《尚书序》:“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说文》序中:“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卽谓之字。”《古今通论》中说:“仓颉造书,形立谓之文,声具谓之字。”《易·乾卦文言疏》:“文谓文饰。” 《论语》:“小人之过也,必文。”到了汉代,《史记·谥法》“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①《康熙字典》477页第01页。所以“文”的意义发展基本是中国古文字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最早的意义“事物错综所造成的纹理或形象”、“装饰”等,到“记录语言的符号”,“用文字记下来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华、辞采”等,再到“礼节、仪式”等等,无不显示“文”的意义发展是文章学和古文字学发展的重要线索。
而“章”的概念则渗透了文章组织及结构概念。章,意断曰章。《说文解字》释为:“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也有“采”的意思。《书·皋陶谟》“五服五章哉。” 古语同“彰”,彰明。如《易·垢卦》“品物咸章”。汉扬雄《法言》中提出的一切言说必须“章明正道,唯圣人能明此道,因此要征圣,而圣人之心见诸五经,所以征圣必须明经。”也有“篇章”的意思。如《诗疏》“诗有章句,总义包体,所以明情也。”后来有“条也,程也”的意思。如《史记·高祖纪》“约法三章”。章的字面意义也有“又大林木曰章”。如《史记·货殖传》中“千章金材”。《尔雅·释山疏》又解释“山形上平者名章”。所以“章”的意思从字面上的从“花纹,文采”、“佩带的身上的标志”等发展到“条目,规程”、“奏本”等。《易经·艮》“言朽序”;“不成章则不达”,言语、文字需经巧妙的组合、结构,才能使人乐于接受。东汉末荀悦说:“章成谓之文”(《申鉴》),使用了结构(后谓之“章法”)、条理之义。在文章学上从“歌曲诗文的段落”发展为“章节、章句、乐章、章回体”等等。 “章”在文章学上表示“意断为章”即划分言语表达的标识。从《诗经》时代起,古代诗歌就是分章的,多个章就可以构成篇,相当于现代“段”的概念。如《周南关雎》就是五章四句。后来的诗歌不分章,章篇合并为一,统称篇章。从最初的“乐竟为一章”到《书疏》曰:“成事成文曰章”及《汉书》的“约法三章”到《文心雕龙·章句》篇时,“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至此,“章”的形式意义则完全体现。
就“文章”一词而言,其出现较早,意义经历了泛指到专指,逐步深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人文”生态理念逐步深化的过程,是指写作者对生存环境的深刻理解和积极参与的过程。如《史记 ·儒林传》记公孙弘语曰:“文章尔稚,训辞深厚。”这是将当时盛行的“辞章之学”纳入“文章”范畴。东汉时期,以“文章”泛指诗赋、散文等所有文章体裁或者书写形式,班固在《汉书》中或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或“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在《汉书·艺文志》中,则称凡著书于书帛者为文章。到了曹丕时代:“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随着文章的概念被大家所认可,“文章学”的说法也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可,只是定义不一。祝尚书认为文章学也就是宋人所称的“笔法学”:“文章学就是解决诸如文章如何认题立意,以及它的间架结构、声律音韵、造语下字、行文技法等等‘知之’方面的问题。”更多的则把文章学理解为一门学科,是关于文章的形成、创作、鉴赏的系统研究,如张寿康《文章学论略》认为,文章学的内容有源流论、类别论、要素论、过程论、章法论、技法论、阅读论、修饰论、文风论、风格论等。王凯符《古代文章学概论》认为文章学的科学体系至少包括:“文道论”、“修养论”、“写作论”、“文体论”、“风格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够全面,因为正如吴承学所说:“‘文章学’是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概念,有明显的历史色彩,而且同一时代的不同理论家、同一理论家在不同文本语境中都可能出现不同的表述。”
秦汉之前,人们所使用的“文”这一概念,含义比较广泛。孔子经常所讲到的“文”,是文章在内的文化学术的总称。*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1页。文章学中的“文”应该是个意义指向变窄的概念。从先秦时代起,“文”是广义的文化观念,包含典籍制度、文化修养、文艺学问的诸个方面。《论语》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天之将丧斯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等等。孔子四科十贤中:“文学:子游、子夏”,《荀子》也说:“人之于文学也,尤玉之于琢磨也。” 王充在《论衡· 超奇》中说:“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紲,表著清心,以明己之必能为之也。”可以说是继承了孔子关于“文”的思想。到后来随着“文学”的独立门户,“文”的概念日趋缩小。晚清刘师培总结说:“故三代之时,凡可靓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谓之文。就事物言,则典籍篇文,礼法为文,文字亦为文。就物象言,则光融者为文,华丽者亦为文。就应封言,则直言为言,论难为语,修辞者始为文。文也者,别乎鄙词俚语者也。”所以说,如果说“中国人的第一罪恶,就是太文了!”*林同济,论文人(上)选自雷海宗等《文化形态史观》,业强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第117页。这类论断有合理性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由此得到更加荒谬之论断:没有典籍篇文或者礼法文字的国度才算是文明之国度吧。
也有学者“认为古人关于‘文’的观念是出自‘和’”*陈良运著,中国古代文章学三辨。选自《跨世纪论学文存》,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20页。,但是从下文的论述将可以看出,中国文章学的价值理性是一种终极“人文”关怀,正如《易经》所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方面通过个人实现‘大我’而‘浑然与天地同体’,一方面又以自身为原则要求介入现实以现实的行动来呈现这终极性的价值。……”*刘文勇博士论文:价值理性与中国文论,2002年,四川大学。如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说:“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通过使文章达到“公器”的要求来表达“大我”,最终实现为“文”之人的“外王内圣”的价值理性,而这种理性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理念。
二、文章的社会功能是文人的价值取向所在
远古是“诗、乐、舞”一体的时代,《诗经》中的“德音不暇”要求心平德和才能使音乐尽善尽美,这其实是对乐者的要求。到《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里的“文”可以理解为礼乐文化传统,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符合传统礼乐要求的文人。而《左传》也云“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这里都强调了“文”与为“文”之人的关系。到了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 “修辞立其诚”等概念中有些词如“文质彬彬”“诚意”等到了现代被用到了形容人的方面,应该并非偶然。而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实已经把写文章这件事或者为文者的作为和价值放在了极高的地位上。当然他在后文中也强调了通过文章来实现政治抱负和理想的要求。到了《史记》时代“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更加显示对为文之人的要求。而王充《论衡·超奇》中提及“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即能独抒己见,“极—冥之深”才能被称为文人。”而隋唐之后,“文”的政教作用则更加得到了强调。杨炯《王勃集序》中:“君之生也,含章是托。”而唐权德興《醉说》提出“岂止文也,以宏诸立身。”他认为著文与修身道理一致。韩愈《答李翊书》提出写古文的三阶段,学习与修身始终紧密相关的。后来的“文如其人”更是把文人和其文作划上等号。如清代学者何绍基所言:“移其所以为人者,发见于语言文字。”明王世贞则更加直接,在他的《文章九命》所谓的“知遇、传诵、證先、贫困、偃蹇、嫌忌、刑辱、夭折、无后”等文章的九命无疑是对著“文”之人的命运的评价。
另外,众所周知的是,“文”学所记载的主要是人的行为,以行为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人的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所以“文”往往通过表达“人”的情感来约束“人”的行为;文章学的“文”,即为“文”之法,不仅对“文章”成为“公器”有技艺上的标准,也有社会价值的标准存在。如周亮工在《书影》中提及:“宋景濂云:‘扬沙走石,飘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诡诞不经,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间濮上,危絃促管,纵使五音繁会,而淫靡过度者,非文也;情缘愤怒,辞专讥讪,怨尤勃兴,和顺不足也,非文也;纵横捭阖,饰非助邪,而务以欺人也,非文也;枯瘠苦涩,棘喉滞吻,读之不复可句也,非文也;瘦词隐语,杂以诙谐者,非文也;事类失伦,序类勿谨,黄钟与瓦釜并陈,春秾与夏枯并出,杂乱无章,刺眯人目者 ,非文也;臭腐塌茸,厌厌不振,如下俚衣装,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类不能偏举。必也旋转如乾坤,辉映如日月,阖闢如阴阳,变化如风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国家,小之为天下国家用,始可言文。’”*王水照《历代文话》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此外,“文以载道”被唐宋许多学者提出,如唐李汉在《昌黎先生文集序》提出“文者贯道之器也。”宋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其中“道”的意义有许多不同,如比较宽泛的认识认为文承载明善恶、辩是非的作用(如毕仲游“文章盖美恶之车舆也”),也有以儒家内圣之学来理解,即以人形体之身,得天地之秀,显太极阴阳之理(即“道”、“诚”)(周敦颐《太极图·易说》)。但是不管以何种角度阐述,都是基于通过文章来实现为“文”之人的社会价值和功用的。而正如Mühlhaüsler创造的一个术语—“共生境”(covironment),这个术语原本表现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共生关系(Mühlhaüsler,2001),也可以指代文章学对与文章与社会的共生关系。
三、文章学中“风骨论”“神气说”等体现“人”的主体特性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意为皮肤,华发为冠冕。”《文心雕龙·风骨》也有云:“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 ‘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文心雕龙·养气》论: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文心雕龙·神思》曰:“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所有这些,可以发现为“文”的要求和标准是借助对人的生理及心理的譬喻来达到的。
孟子首创的“养气”之说,到后来“气”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主体论范畴,内涵经过历代文论家的阐释而趋于丰满。学者们普遍认同“气”的三种诠释角度:先验的或者经验的获得,如《文心雕龙·体性》中“气有刚柔”;从人格角度理解,“气”是一种道德涵养为中心的人格培养或者整体的精神气质。如孟子的“浩然之气”,还有苏轼赞李白《李太白碑阴记》以“士以气为主”;韩愈有强烈的“道统”的意识,他提出“气盛言宜”说以引人向道,认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以水之浮物为喻,说明正气充盈,则文章自然能写得好。而要做到“气盛”关键在于充实根基,加强修养:“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埃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他在《答李翊书》还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指示修养的具体门径:“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
而元代杨维帧《赵氏诗录序》提出“评诗之品无异人品”成为文学批判史的重要命题。他说:“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 后来明代诗论家胡应麟《诗薮》称“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
在《文荃》中关于文章体段的这样的结构:

如图所示,把文章的结构与人体相譬喻,是非常明晰,对于初学者而言,学习和理解则非常容易了。明代大学者唐顺之也认为:“文章家绳墨布置,奇正转摺,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间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者,不足以舆此。*王水照《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61页。另外更为出名的则是“文脉”“意脉”说。杨载《诗法家数》论古诗要法,说:“凡作古诗,体格、句法俱要苍古,且先立大意,铺叙既定,然后下笔,则文脉贯通,意无断续,整然可观。”*杨载:《诗法家数》,中华书局排印本《历代诗话》第726页,1981年。“语篇亦可称之为一种自足完满、文脉绵长丰满并呈线性延展的持续语际表达流。文脉之性质于此得以确认,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将文脉之‘眉目筋骨’称作中国传统修辞学的‘顶针回环’抑或‘语际文法’亦无不可。”(傅勇林,2001)所谓意脉连贯正是方东树“语不接而意接,血脉贯续”,李涂“务要十句百句只如一句,贯穿意脉。”比如“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张炎,1963)所以,“文脉”“意脉”的概念一方面强调意脉起主导作用,意脉驾驭语言文字,使之上下连贯构成语脉;同时这上下连贯的语言,前呼后应,贯串全文,形成文脉,使整篇文章首尾圆合,文章流畅,气势如潮。另外一方面与人的“脉”为比喻的对象,也显示了文章的连贯性与“人”的血脉连贯性一致,流畅贯通,生机勃勃。
四、文章学中的作文之法论体现生态语言对作者的创造性要求
对于为“文”之法,历代文论中基本倾向于:法须有,但无定法。如《荆溪林下偶谈》认为“为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同①《文辩》:“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无,大体须有。’”*同①,第1150页。
由此可见,为文之法非常重要,但是在历代文论中较少论述,如果理解了古代“文”的“人文”性意义,那么理解文章学“法无定法”的概念则容易许多。
原因何在?
首先,人有相似基本构成,但外观构成却千姿百态,而格式相当于人的基本构成,虽然重要,但是却不是形成外在特点和审美外观的重要因素。如元代倪士毅《作义要诀》中所述:“宏齊曹氏泾曰:‘作文各自有体,或简或祥,或雄健或稳妥,不可以一律论,盖文气随人资禀,清浊厚薄,所赋不同,则文辞随之。然未有无法度而可以言文者。法度者何?有开必有合,有唤必有应;首尾当照应,抑扬当相发,血脉宜串,精神宜壮。如人一身,自首至足,缺一不可,则是一篇之中,逐段逐节,逐字逐句,皆不可以不密也。’”如清代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中所说:“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严。夫具五官,备四体,而后成为人。其形质配合乖互,则贵贱妍丑分焉。然未有能一一指其成式者也。”
另外,“法无定法”体现作文过程中所需要的创造性。明代庄元臣在《论学须知》中认为:“大抵体制有古今,轨辙无先后,善学者师其轨辙,不善学者师其体制。*同①,第2211页。北宋江西诗派吕本中提出其诗学核心概念“活法”,虽然禅学和理学提供了其思想的来源,如宋代禅师宗杲曾在《大慧语录卷十四》说:“夫参学者,须参活句,莫参死句……”,而理学朱熹在《戊申对事》说“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吕本中的观点结合了黄庭坚对初学者要求,如矜言法调,强调准绳和定法,及苏轼的强调立意,不拘定法结合起来,形成自然为上的“人文”特性的诗学法则。而创造性的要求无疑是人本的,无疑是立足于“人”的主体情境的。如明代著名僧人憨山德清所云:“文者,心之章也。学者不达心体,强以陈言逗凑,是可为文乎?须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盖天盖地。”也如清末大学者刘熙载所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文,经纬天地者也,其道惟阴阳刚柔可以该之。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一阖一闢谓之变。然则文法之变,可知已矣。 叙事之笔,须备五行四时之气。”
五、小结
正如前文所述,文章学的根本是一种“人文”的关怀,自古以来,为“文”之学地位极高,如曹丕所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如明代大学士宋濂所说:“吾之所谓文者,天生之,地载之,圣人宣之,本建则其末治,禮著则其用章,斯所谓秉阴阳之大化,正三纲而齐六纪也。亘宇宙之始终,类万物而周八极者也。呜呼!非知经天纬地之文者,烏足以语此!”然而,精通为“文”之道更是难上加难,如《文章精义》有云:“人皆曰文章天下之公器,然必具眼目识见高者,而后能语其精义之精。”究其根本,为文之人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观及对社会的贡献的真正达到是非常困难的,这正如雅斯贝尔斯把“生存的交往”(existentielle Kommunikation)称之为真正的交往,因为生存交往是通向生存的最佳途径。这种交往不是生存之间的沉默的相互融合,而是“爱的斗争”(1ibender Kampf),是对抗,也就是为了使他人开放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在他人的失败中自己的生存也不得不沉寂下来。相反,这种斗争是“既证明自己,又证明他人的斗争,因而也是为了他人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人同他人一起实现自身存在。”在文章学的生态理念中,文人需要通过为“文”来获得社会存在的基本价值,来与人沟通,来实现与社会的“共存”的意义。
[1] (宋)张炎.词源·杂沦[M]//词源注.夏承焘,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点校本.
[2] (明)宋濂.曾助教文集序[M]//宋濂全集·芝园前集(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3] (清)何绍基.使黔草自序[M]//东洲草堂文钞,同治六年长沙刻本.
[4]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 (清)刘熙载.艺概·经义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 (清)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M]//宁武南氏校印本.刘申叔先生遗書·左盦集(卷八).
[7] 李涂.文章精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 德清.示陈生资甫[M]//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三).
[9] 韩愈.答李翊书[M]//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一).
[10] 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1] 傅勇林.文脉、意脉与语篇阐释——Halliday与刘熙载篇章理论之比较研究[M]//张后尘,胡壮麟.99中国外语博士论坛.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12] 黄知常,舒解生.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13] 祝尚书.对文章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D]//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届中国古代文章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
[14] 张寿康.文章学论略[J].北京师院学报,1986(4).
[15] 王凯符,等.古代文章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16] 吴承学.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
[17] MUHLHAUSLER P.Talking about environmental issures[M]//FILL A,MUHLHAUSLER P.The ecolinguistic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1.
责任编辑:王飞霞
2014-12-20
2013年华东理工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立项研究项目资助。
金春岚(1976- ),女,浙江绍兴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英汉对比和翻译。
H319
A
1004-941(2015)02-00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