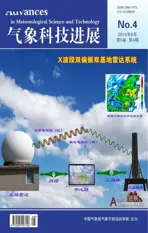台风定强技术及业务应用
—— 以Dvorak技术为例
2015-02-08许映龙张玲向纯怡
许映龙 张玲 向纯怡
(1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1;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 210044;3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 100081)
台风定强技术及业务应用
—— 以Dvorak技术为例
许映龙1,2,3 张玲3 向纯怡3
(1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1;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 210044;3 国家气象中心,北京 100081)
回顾了台风业务定强Dvorak技术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我国台风业务定强技术流程改进的必要性,简要介绍了世界气象组织推荐使用的1984年版本的基于BD增强红外云图的Dvorak台风业务定强分析技术流程以及中央气象台在2012—2013年开展的业务试验及应用情况,最后对Dvorak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及业务分析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业务试验及应用的结果表明:Dvorak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中央气象台台风业务定强的精度和客观技术支撑能力,而且也增强了我国台风业务定强数据与国际上其他台风业务中心的可比性。与中国气象局台风最佳路径资料对比检验表明,中央气象台台风业务定强平均精度由2011年的1.9m/s 优化至2013年的1.3m/s,提高近32%;针对2013年中央气象台和日本气象厅所确定的共511个台风现时强度指数(CI)对比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两者确定的CI指数基本一致,总体相差在±1.0之间,这种差异与两者进行Dvorak技术分析时所使用的卫星资料(MTSAT或FY2系列)不一致有关,同时也与预报员的实际分析经验有关。
台风,强度估计,Dvorak技术,业务应用,局限性
Keywrds:typhoon, intensity estimation, Dvorak technique, operational application, limitation
0 引言
台风生成于热带或副热带洋面,而海洋是常规观测的盲区,地面雷达探测距离有限,气象卫星则具有观测范围广、观测时次多等特点,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气象卫星投入业务运行以来,卫星云图就成为对台风进行全天候监测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对远海台风的监测。在台风业务预报实践中,台风定位定强是制作台风预报和发布预警的第一步,定位定强精度不仅会影响台风路径和强度预报的质量,而且也会影响到其所带来的狂风、暴雨和风暴潮预报的质量[1]。卫星图像作为台风定位定强最常用的资料,在台风业务预报实践中的应用一直是广大业务科研工作人员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这方面早期的研究工作包括20世纪60年代Sadler[2]、Fett[3]、Fritz等[4]和Hubert等[5]利用卫星云图估计台风强度的初步尝试,但由于当时卫星探测技术的局限,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6]。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Dvorak在多年预报经验及气象侦察飞机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基于当时可见光(VIS)和红外(IR)云图的台风云型特征与台风强度的统计关系,并逐渐发展出一套基于卫星图像台风云型特征的台风强度估计技术[7-12]。经过多年业务实践,该技术已成为世界上最成熟的利用卫星云图确定台风强度的方法,是缺少飞机探测条件下确定台风强度的世界通用标准[6,13-16],并于1987年为世界气象组织推荐使用[1,14]。
初始版本的Dvorak技术通过对可见光云图的识别和实际预报经验,总结出台风强度与其云型变化之间的关系,并重点关注台风云型本身(包括眼区和眼壁)特征和外围螺旋云带特征,将上述两部分云系特征分析得到的T指数之和定义为台风现时强度指数(CI),用于描述台风强度,CI指数变化范围从1~8,以0.5为变化单位,CI越大,表示台风强度越强。但初始版本的Dvorak技术只依赖于可见光云图,因此无法实现全天候监测,而且估测精度也不高[17-18]。此后,随着气象卫星探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卫星红外成像技术的发展,Dvorak技术开始引入红外云图分析,以使该技术应用于夜间台风的监测。期间,Dvorak技术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改进。1984年,Dvorak从强调台风云型结构匹配与简单的发展和衰减模型转为注重分析台风云型特征,如弯曲云带螺旋度、低层环流中心与深对流之间的距离、中心密闭云区云顶亮温和范围、眼区及周围环境的亮温等,并对一个热带对流云团在什么情况开始进行Dvorak分析做了明确的规定[11];1995年,Dvorak细化了最终强度指数在台风发展和消亡阶段的限定规则和约束条件,并对具体应用做了详细解释[12]。
Dvorak技术设计的初衷是针对北大西洋飓风。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青藏高原和西太平洋暖池使得台风强度变化不同于北大西洋,且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台风云顶亮温相对较低,直接应用Dvorak技术将产生一定偏差[17-19];另外,Dvorak分析流程较为复杂,预报员经验丰富与否决定着最后的分析精度。因此1980年卫星云图联合分析组[20]和方宗义等[21]对Dvorak技术进行了简化,总结出与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强度变化相关的云型特征,包括:环流中心与密蔽云区的相对位置、眼的形状、大小和清晰度、中心密蔽云区范围大小和螺旋云带特征等,台风总强度指数定义为环流中心特征数、中心强对流密闭云区特征数与螺旋云带带状特征数之和。在此基础上,中央气象台建立起了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定强分析流程,在台风业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22-23]。简化后的方法操作简单,但主要适用于40m/s以下的台风,40m/s以上的台风只能定性地判定为40~60m/s,且分析精度取决于预报员的经验[24-26]。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江吉喜[27]、范蕙君等[26,28]又先后对Dvorak方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进。江吉喜[27]基本沿用了Dvorak分析的基本思路,采用4级BD增强(白、浅灰、深灰和黑)红外图像对Dvorak技术进行了简化,并将同心双眼墙台风纳入分析流程。范蕙君等[26,28]则针对卫星云图联合分析组和方宗义等[21]的方法进行了改进和优化,增加了眼的形状、直径和亮温、中心密蔽云区最低云顶亮温和面积、螺旋云带最低云顶亮温和条数以及结构紧密度等与台风强度变化相关的因子,使之适用于各种不同强度的台风,较卫星云图联合分析组和方宗义等[21]的方法有了较明显的改进,并实现了人机交互,但对55m/s以上的台风分析误差仍较大,且易低估台风强度[24-26,28-29]。由于种种原因,江吉喜[27]、范蕙君等[26,28]的改进工作并没有真正纳入中央气象台的台风业务定强分析流程中。直到2012年之前,中央气象台的台风业务定强流程仍然采用卫星云图联合分析组和方宗义等[21]简化后的方法[1,22-23]。
2011年4月11—16日在美国夏威夷召开了世界气象组织第二届国际台风最佳路径资料气候管理会议(International Best Track Archive for Climate Stewardship Meeting,IBTrACS)和台风卫星分析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Workshop Satellite Analysis of Tropical Cyclones),中央气象台和上海台风研究所的相关业务研究人员参加了该次会议。会上包括中央气象台在内的世界各大台风业务中心分别展示了Dvorak技术在台风业务定强中的应用情况,除中国以外的业务中心均采用1984年版的Dvorak技术流程,而中央气象台的台风业务定强流程则采用卫星云图联合分析组和方宗义等[21]简化后的方法,与国际上通行的Dvorak技术分析流程存在较大的差异[30-31]。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分析流程过于简化,且没有采用红外BD增强卫星云图进行分析,分析流程仅宏观地考虑了台风云型特征,而没有细致考虑台风眼区周围云顶亮温、眼区亮温等与台风强度变化相关的因子,也没有考虑Dvorak分析的一系列限制规则和约束条件,分析随意性较大、精度低,与国际上其他业务中心定强结果的可比性差。
因此,无论从参与国际交流的角度,还是从提高我国台风业务定强的精度以及为台风气候变化趋势研究提供可靠数据来看,均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的台风业务定强流程进行规范和完善,以实现我国台风业务定强流程与国际其他业务中心的接轨,增加我国台风定强数据与国际其他业务中心的可比性,提升我国在国际台风界的地位以及我国台风最佳路径数据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为了使业务人员尽快掌握世界气象组织推荐使用的1984年版Dvorak台风业务定强分析流程,中央气象台于2012年2月22—29日和2013年8月4—17日分别邀请了香港天文台的陈世倜和美国关岛大学的Mark Lander进行了专题培训和现场指导,培训内容包括:台风卫星SWAP分析平台的功能和操作,业务定位所用资料、技术流程规范及Dvorak业务定强分析流程等,为中央气象台台风业务定强流程改进提供了充分的技术准备。
1 Dvorak技术分析的基本方法
在卫星云图上,台风强度是台风云型结构多种特征的综合反映[6]。这些特征包括:台风环流中心与强对流云区的距离、中心强对流云区范围、外围螺旋云带以及台风眼区周围云顶亮温、眼区亮温等方面。Dvorak技术是在假定台风云型特征变化与台风某一发展阶段和一定强度相对应的基础上,通过对卫星云图上的台风云型特征进行提取和分析,得到用于表征台风强度的台风现时强度指数(CI),然后由观测统计得到的CI与台风中心最大风速的经验关系,得到台风近中心最大风速,再由台风中心最低海平面气压与台风中心最大风速的风压统计关系来确定台风中心最低海平面气压。Dvorak技术能够反映台风强度变化的关键在于其包含了影响台风强度变化的动力和热力因子[6],动力因子包括:台风云系的组织程度和深对流偏离台风中心的距离等,它们分别反映了台风涡度的大小和高低空环境风场水平风速垂直切变的大小;热力因子则包括:不同的台风云型分类和台风眼区亮温等方面,它们分别反映了台风对流发展的强度和台风内核发展的强度。Dvorak技术分析流程如图1所示[11,16,32-33]。
在1984年版的Dvorak技术分析流程中,Dvorak规定了台风业务定强的具体分析流程及分析中必须遵守的一系列限定规则和约束条件。下面仅介绍目前国际上最通行的基于该版本的采用BD增强红外云图的台风业务定强分析技术流程,具体分析流程和步骤如下。
1.1 热带扰动分析启动条件
确定一个热带扰动系统是否可以开始进行Dvorak技术分析,一般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①该系统持续了12h以上;②该系统在直径小于等于2.5个纬距范围内的云系中心(Cloud System Center)已经持续了6h以上;③有一个宽度大于1.5个纬距的浓密而冷的(BD增强红外云图上的亮温值低于-31℃)密闭云区,该密闭云区与系统中心的距离不超过2个纬距。对于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热带扰动的初始T指数定义为1.0或1.5。上述条件将保证一个初始热带扰动在未来有足够且稳定发展的深对流云团,在合适的环境场条件下,可预报该系统在未来24~36h发展为台风(即最终强度指数FT达到2.5以上);若初始涡旋没有发展,则在初始的T指数后面加负号表示。
1.2 确定台风云系中心
确定台风云系中心(Cloud System Center,CSC),对分析台风云型特征,特别是对切变型和嵌入中心型是非常重要的。在确定台风云系中心时要考虑云型的整体结构,在有可见光时应注意分析云顶的中小尺度特征,如上冲云顶;红外图像上应注意分析冷云区中明显的暖点,同时要考虑系统移动的连续性及与预报的一致性。对切变型云系,除了确定系统中心外,还应尽可能找到其低层环流中心;对弯曲云带型云系,有两种确定云系中心的方法:①先确定弯曲云带的轴线,将轴线的终点(图2a的A点)与少云区契形的极点(图2a的B点)的连线中点作为系统中心;②将几条螺旋云带的共同曲率中心作为系统中心(图2b)[33]。确定系统中心位置后,预报员可根据当前台风的云型特征,选择对应的云型特征分析方法,进行资料T指数分析。
1.3 确定资料T指数
Dvorak根据台风云型特征将台风云型分为六类:①弯曲云带型(Curved Band),适用于VIS和IR,包括适用于VIS的弯曲云带眼型(Banding Eye);②切变型(Shear),适用于VIS和IR;③眼型(Eye),适用于VIS和IR;④中心密闭云区型(Central Dense Overcast,CDO),仅适用于VIS;⑤嵌入中心型(Embedded Center),仅适用于IR;⑥中心冷云盖型(Central Cold Cover, CCC),适用于VIS和IR。Dvorak根据台风强度的发展规律和实际预报经验,针对台风不同云型类型给出了相对应的强度指数模型(图3),同时针对台风不同云型类型给出了具体的分析流程和一系列分析调整和限制规则,包括眼和螺旋云带带状特征调整规则以及眼型、嵌入中心型和中心冷云盖型分析的限制规则等,具体分析流程如图1所示。在业务定强分析中,预报员可以根据当前台风的云型特征,采用对应云型特征的分析流程,得到适合当前台风云型特征的台风资料T指数(Data T Number,DT)。
1.4 确定模式期望指数
台风模式期望指数(Model Expected T- Number,MET)定义为台风过云24h强度变化趋势与该台风24h前的最终强度指数(FT)之和。在Dvorak分析流程中,Dvorak将台风强度变化趋势分为发展(D)、减弱(W)和无明显变化(S)三类,台风过云24h的强度变化趋势可通过将当前卫星图像与24h前的图像相比较而获得。若与24h前的情况相比,围绕台风中心的密闭云区增多增厚、云系结构更为密实,或者眼区更为清晰,则表示台风强度处在发展中,相反则表示台风处于减弱中;若云系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则表示台风强度无明显变化。
此外,Dvorak还根据台风强度变化的剧烈程度将发展和减弱趋势再分为快速发展/减弱(D+/W+)、正常发展/减弱(D/W)和缓慢发展/减弱(D-/W-)等六类,并给出了台风强度发展的模式期望指数变化曲线(图4)[9]。在Dvorak业务定强分析中,预报员可根据台风24h的强度变化趋势分析结果,结合该台风24h前的FT,确定台风当前的MET。具体的确定规则为:①若为快速发展(减弱),以24h前的FT加上(减云)1.5作为当前的MET;②若为正常发展(减弱),则在24h前的FT加上(减云)1.0作为当前的MET;③若为缓慢发展(减弱),则在24h前的FT加上(减云)0.5作为当前的MET;④若强度无明显变化时,则以24h前的FT作为当前的MET(表1)。

表1 MET指数的确定规则
1.5 确定云型指数
台风云型指数(Pattern T Number, PT)主要是在需要对MET进行调整时使用的,它将当前台风的云型特征与Dvorak事先给定的台风云系型态(表2)比对而得。在比对前,需根据1.4节中分析的MET,选择与MET数值对应的一栏或左右相邻的两栏与当前台风的云型特征比对,然后选择与其匹配最好的云系型态对应的云型指数作为当前台风的PT。即,若当前台风云型特征与MET数值对应一栏相邻的右(左)栏的云系型态更为匹配时,则在MET数值上加上(减云)0.5作为当前台风的PT。此外,在进行比对时,若匹配的云系型态的阴影部分为白色或更冷时,可再加上0.5作为当前台风的PT。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台风云型特征明显地强于或弱于MET数值所对应的云系型态时,PT才可以与MET取不同的数值。

表2 红外BD增强云图上不同云型指数对应的台风云系型态
1.6 确定最终强度指数(Final T Number,FT)
在第1.3~1.5小节中分析的DT、MET和PT的基础上,应用给定的限定规则和约束条件,确定台风FT。具体的限定规则和约束条件包括:①台风云型特征清晰时,直接使用DT作为FT;②台风云型特征不清晰,但云型可识别时,使用PT作为FT;③当台风云型特征不清晰且云型难识别时,使用MET作为FT;④热带云团首次定强分析时的FT必须为1.0或者1.5;⑤台风最初发展的48h内,由于对流云团存在日变化,FT不能在晚上减弱,在实际分析中规定为20时至次日05时,也即可看到可见光云图之前,但白天分析时,FT可以出现减弱的情况;⑥热带云团首次定强分析FT为1.0以后的24h内,FT必须≤2.5;⑦当FT<4.0时,6h的变化量不能超过0.5;⑧当FT≥4.0时,6h变化不能超过1.0,12h变化不能超过1.5,18h变化不能超过2.0,24h变化不能超过2.5;⑨FT必须在(MET-1.0)到(MET+1.0)之间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Dvorak技术是假定台风特定的云型特征与台风强度发展的特定阶段存在对应关系,根据典型台风的统计关系而建立的,因此有时并不能完全反映所有台风强度变化的真实情况。对一些快速增强的台风,有时其强度变化往往超过上述限定,严格使用Dvorak限定规则和约束条件可能导致对其强度突变的误判,低估其强度,这时可以打破Dvorak规则的限定,但打破Dvorak规则需慎之又慎,且只有在台风云型结构特征清晰、变化特别明显时才能使用。
1.7 确定现时强度指数
台风现时强度指数(Current Intensity Number, CI)是基于第1.6小节中分析的FT,根据给定的限定规则和约束条件而确定的指数,它是Dvorak技术的最终强度分析产品,直接与台风当前的强度状况相对应。给定的限定规则和约束条件是为了保证CI不会因为云型结构指数虚高而定得过强;而在减弱阶段,台风低层风场往往会维持一段时间,因此CI也应保持相应的时间。具体的限定规则和约束条件包括:①台风发展阶段,CI应与FT一致;②台风减弱阶段,CI应高于FT,实际分析时,台风减弱的最初12h内,CI保持不变,之后保持较FT高0.5或1.0;③台风再次发展时,FT未增至CI前,CI应保持不变。
需要指出的是,每次业务定强分析后,需根据卫星图像演变对先前分析结果进行检查。当先前分析出现误差时,需及时修正先前的CI,以保证为后续分析提供可靠的MET,且这种修正有时可能会改变业务定强分析的结果。
1.8 确定台风中心风速和气压
Dvorak技术并不是对台风风场和气压场的直接观测,它仅给出了用于表征台风强度的CI。为了直观地了解台风的强度状况,还需将反映台风强度的CI指数与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速和中心最低海平面气压联系起来。在实际业务定强分析中,通常是由CI指数与台风中心最大风速的经验关系来确定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而中心最低海平面气压则是通过应用台风风压关系得到的。
台风风压关系是一种基于历史观测资料得到的台风中心风速与气压之间的统计关系,就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而言,我国和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一直沿用Atkinson等在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1947—1974年76个西北太平洋台风实测的平均风速和海平面气压资料建立的风压统计关系[34-35],日本则采用Koba等[36-38]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根据1981—1986年50个西北太平洋台风实测资料所建立的风压统计关系,两者在对台风以上强度的风压关系中存在较大的差异[39-42]。Atkinson等建立的风压关系至今仍被列入联合国亚太经社会(ESCAP)和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的台风业务手册中[16]与我国的台风业务与服务规定和气象卫星业务产品释用手册中[23,34](表3)。然而,在不同海域,台风生成发展的地理区域和环境条件不同,Dvorak分析时所采用的风压关系存在明显的差异[42]。为此,燕芳杰等[43]基于1975—1985年美国飞机观测资料对Atkinson等建立的风压关系进行了纬度和季节订正,但订正后的关系仍是1min平均持续风速的风压关系,且由于种种原因,也未被纳入中央气象台的台风业务定强流程分析中[23,34]。Atkinson等建立的风压关系形式具体如下:
式中,Pc为中心海平面气压,单位为hPa;Vmax为中心1min平均风速,单位为kt。
正是由于我国台风业务定强分析中采用的风压关系为台风中心1min平均持续风速的风压关系,这明显与我国台风等级标准(GB/T19201-2006)[44]的台风强度定义不相一致,因此,在实际台风业务定强分析中,最终确定的台风中心风速和中心最低气压,还需根据预报员的实际经验进行适当的主观修订。

表3 CI与台风中心最大风速和海平面气压的对应关系[23,34]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Dvorak台风业务定强分析时所采用的台风风压关系,不仅是影响其分析精度和可信性的一个重要因素[42,45-55],而且也是进行全球台风强度长期趋势变化评估时,影响台风强度气候资料均一性的一个关键因素[56-64]。然而,国际上不同台风业务中心用来定义台风强度的平均风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日本、菲律宾、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大多数受台风影响的国家或地区采用的是10min平均风速,美国采用的是1min平均风速,印度采用的是3min平均风速,我国采用的则是2min平均风速[39-42,44,65],因此,国际上不同台风业务中心进行Dvorak台风业务定强分析时所采用的风压关系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不同台风业务中心针对同一台风的强度估计分析结果也会出现较大的差异,这需要在台风实际业务预报中加以考虑。
2 Dvorak分析技术的业务应用
根据Dvorak分析流程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图1),中央气象台于2012年3月建立了基于世界气象组织推荐使用的Dvorak技术(1984年版)的台风业务定强分析流程,并开展了业务试验,包括CSC、DT、MET、PT、FT和CI以及台风未来24h强度趋势预报等具体分析流程(图5)。为方便预报员分析使用,还将Dvorak台风定强分析流程制作成工作卡片(表略)。在开展了近1年的业务试验后,中央气象台于2013年正式开展了基于Dvorak技术的台风定强业务应用,期间还邀请了美国关岛大学的Mark Lander教授再次就Dvorak业务定强分析技术进行专题培训和现场业务指导。在业务试验及应用中,中央气象台对满足Dvorak分析条件的热带扰动云团及编号台风,在进入48h警戒线[34]之前每天进行4次定强业务分析,进入48h警戒线后每天进行8次定强业务分析,具体操作时间参见表4。

表4 中央气象台Dvorak实时业务操作时间
台风业务定强流程的改进及业务应用的结果表明,Dvorak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中央气象台台风业务定强的精度和客观技术支撑能力,而且对深入认识台风的结构变化也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年轻预报员把握台风强度发展变化和提高卫星云图的综合应用能力作用明显。通过与中国气象局年度台风最佳路径的强度资料对比检验表明,2013年中央气象台台风平均业务定强精度由2011年的1.9m/s优化至1.3m/s,提高了近32%。同时,Dvorak技术的业务应用还增强了我国台风业务定强数据与国际上其他台风业务中心的可比性,具体从2013年共511个样本的检验情况来看,中央气象台确定的CI指数与日本气象厅基本一致,但对台风以下强度的CI指数分析结果,中央气象台较日本气象厅偏大的样本偏多明显,而对台风以上强度,两者CI基本一致,且样本数相差不大。两者CI总体相差在±1.0之间,这种差异与两者进行Dvorak技术分析时所使用的卫星资料(MTSAT或FY2系列)不一致有关,同时也与预报员的实际分析经验有关(图6)。
下面结合2012—2013年业务试验及应用中的具体台风个例,简要介绍应用Dvorak业务定强技术的具体情况及效果。
2.1 Dvorak技术可为台风业务定强提供技术支撑
由于缺乏海洋观测资料,在实际台风业务定强分析中,往往很难准确地给出台风的实际强度。Dvorak技术将台风云型结构特征变化与台风一定发展阶段的强度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由卫星云图结构特征分析台风的动力和热力结构、定量给出表征台风强度的CI指数的技术手段。目前,Dvorak技术分析得到的CI指数已成为中央气象台台风业务定强分析的主要技术参考指标,尤其在台风快速增强阶段。
回顾中央气象台过云的台风定强分析业务工作,可以发现,由于当时没有采用BD增强红外云图,而采用普通红外云图(BW)和简化分析流程,进行台风强度分析。在BW红外云图上,预报员仅靠肉眼和主观经验很难定量识别台风在不同时次云型特征的细致差别,因此当时的业务定强分析流程和结果均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即对40m/s以上的台风只能定性地判定为40~60m/s[24-26],且往往明显低估台风的强度。如针对2008年0802号超强台风“威马逊”的业务定强分析,中央气象台实时业务定强分析中仅将“威马逊”确定为强台风,中心最大风速为45m/s,直至年度台风最佳路径审定后,才将其修订为超强台风,中心最大风速为55m/s(图7)。从当时的BD增强红外云图的演变看,“威马逊”在2008年5月10日08时至12日02时云型特征变化明显,中心密闭云区(图8中白色区域)经历了由不规则—密实对称—范围缩小—最后消失的变化过程,眼区则经历了由模糊不规则—清晰规则—眼区放大—眼区减弱的变化过程(图8a~8d),“威马逊”云型结构特征的明显变化反映了在此期间其强度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当时中央气象台仅从普通的BW红外云图进行简单分析(图8e~8h),很难识别和捕捉到台风云型结构特征的这种细致差别和变化,10日08和20时、11日08和20时分析的CI指数一直维持5.0不变,业务定强则一直保持45m/s不变;而当时日本气象厅分析的CI指数则分别为6.0、7.0、7.0和5.5,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分别为6.5、7.0、7.0和5.0。其中10日20时和11日08时“威马逊”眼区清晰、中心密闭云区密实对称,日本和美国分析的CI指数均为7.0。由于日本的台风强度定义为10min平均风速,美国为1min平均风速[39-42,65],所以虽然日本和美国的台风业务定强结果在数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均很好地反映了“威马逊”强度出现的这种明显变化,而中央气象台的业务定强结果则看不到“威马逊”强度明显变化的趋势,只是在年度台风最佳路径审定修订后,才体现了“威马逊”强度明显变化的这种趋势(图7)。
在中央气象台采用1984年版Dvorak技术进行台风业务定强分析流程改进之后,由于分析中采用了BD增强红外图像,并细致考虑了台风不同云型特征的分析标准及一系列限定规则和约束条件,规范化的Dvorak分析在准确及时把握台风强度的变化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可为准确把握台风的快速增强及强台风以上台风强度的准确确定提供客观参考依据。
下面给出中央气象台针对2012年1214号强台风“天秤”(图9a)和1224号超强台风“宝霞”(图9b)以及2013年1311号超强台风“尤特”(图9c)和1330号超强台风“海燕”(图9d)的业务定强结果与CI指数的比较,可以看出Dvorak分析结果较好地反映了它们的强度变化趋势,且CI指数的变化基本与中央气象台业务定强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天秤”向我国台湾东南部靠近时,Dvorak分析可见其中心附近深对流密闭云区明显发展,且面积显著增大,由部分白色的对流云区(图10a)演变为呈环状的白色对流云区,且出现了清晰的眼区(图10e),CI指数由8月20日08时的4.0增至20时的5.5,业务定强也由33m/ s增强至45m/s。“宝霞”在登陆菲律宾南部后,眼区填塞(图10b),进入南海后,受其北侧强高层辐散流出气流的影响,再次增强,中心附近深对流密闭云区再次出现清晰的眼区(图10f),CI指数由12月7日08时的4.0增强至20时的6.0,业务定强则由33m/s增强至50m/s。在“尤特”快速增强阶段,Dvorak分析可见其中心密闭云区迅速发展增厚、范围扩大的过程,且出现清晰的眼区(图10c和10g),CI指数由8月10日02时的2.5迅速增强至11日20时的7.0,业务定强则由18m/s增强至60m/s。“海燕”在向菲律宾中部靠近时,Dvorak分析可见其云型结构特征的迅速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心密闭云区迅速发展增厚、面积显著增大,且在密闭云区之外还表现出较强的螺旋云带特征(Banding Feature)(图10d和10h),眼区亮温高达18.3℃,眼区周围呈现为冷黑灰(Cold Dark Grey, CDG)的环状,平均亮温低达-82.9℃,而冷中灰(Cold Medium Grey, CMG)的环状最小宽度也达150km,CI指数则由11月5日20时的4.5增强至7日20时的8.0,业务定强也由35m/s增强至75m/s。可见,Dvorak技术确实可为台风实时定强业务提供较为客观的技术支撑,尤其是在台风的快速增强阶段。
此外,在Dvorak业务定强分析过程中,预报员可以通过台风在卫星云图上的云型特征变化来直观地了解和把握台风当前的强度和结构状况。同时,通过对比连续若干时次的台风云型结构,预报员还可以把握台风强度变化过程中其结构演变的特征和变化,从而有助于预报员对由台风结构变化导致的强度变化有更为直观和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年轻预报员建立台风强度变化概念模型、积累预报分析经验很有帮助。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Dvorak技术虽然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台风强度估计技术,但该技术在台风云型特征的识别上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对弱台风的云型结构特征识别上,不同的预报员针对同一台风同一时刻的业务定强分析可能会有不同的分析结果,但从业务试验及应用的实际效果来看,由于在弱台风期间,CI指数数值小,分析的差异不会太明显,因此,这在总体上并不影响Dvorak业务定强分析的精度,而且随着预报员对Dvorak技术的理解和应用熟练程度的提高,这种分析的差异将会逐渐减小。
2.2 Dvorak技术的局限性
虽然Dvorak技术包含了与台风强度发展变化相关的环境动力和热力两类因子,但由于Dvorak技术是在假定台风特定的云型特征与台风强度变化发展的特定阶段存在对应关系的前提下,根据典型台风的统计关系而建立的,因此Dvorak技术并不能完全反映所有台风强度变化的真实情况,其技术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6]。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一些小尺度的台风(Midget Typhoon),由于环绕台风中心的深对流冷云区最小宽度往往达不到Dvorak限定规则中对相应色阶的深对流冷云区的最小宽度要求,严格按照Dvorak限定规则进行分析,常会产生一定的偏差,低估其强度。
2)Dvorak技术的一系列限制规则和约束条件对台风强度突变的考虑存在不足,Dvorak规定:当FT<4.0时,其6h的变化量不能超过0.5;当FT≥4.0时,其6h变化量不能超过1.0,12h变化量不能超过1.5,18h变化量不能超过2.0,24h变化量不能超过2.5。但一些快速增强台风的强度变化往往超过上述限定,因此当台风云型结构特征清晰、变化特征特别明显,可打破Dvorak规则和约束的限制,但需审慎为之。
3)对于一些由季风低压发展而来的尺度较大的台风,其中心附近由于缺少深对流,Dvorak分析也常会低估其强度。
4)对于一些移速较快的台风,由于环境风场的叠加和作用,常会造成台风破坏力的加强,而这时的Dvorak分析也常会低估其强度。
5)对于同时具有斜压性和正压性特征的温带气旋,特别是变性中(后)台风,Dvorak分析也会由于系统中心附近缺乏持续的深对流云区而造成对其强度的低估。
6)对一些临近登陆的台风,由于台风中心附近对流云系较为松散,Dvorak分析也常会低估其强度,而这些台风往往在海岸地形向岸风的作用下,观测到的地面风速却会非常大。如2012年1211号强台风海葵”(图11a)和2013年1323号强台风“菲特”在靠近华东沿海时(图11b),在可见光云图上,“海葵”和“菲特”均呈现典型的台风结构(图略),中心密闭云区完整,且在红外BD增强云图上,两者也呈现出完整典型的台风结构,但眼区模糊,眼区边界也不清楚,黑色(Black)或白色(White)的深对流云区未形成环状,很难根据眼型来确定其DT指数,而即使根据眼型来确定其DT指数,也因为环绕台风中心的深对流冷云区的最小宽度达不到Dvorak对相应色阶的深对流冷云区的最小宽度要求,因此Dvorak分析的“海葵”和“菲特”的DT指数均较小,CI指数只能定到4.0,也即只能达到台风强度的下限(33m/s)。而“海葵”和“菲特”在靠近华东期间,地面观测的多个沿岸及海岛测站地面风速却出现持续增大,并出现了14级以上的平均持续风速。“海葵”期间,浙江东矶和大陈观测到的最大平均风速分别达46.9m/s(15级)和39.4m/s(13级);而在“菲特”期间,浙江石坪和南麂观测到的最大平均风速则分别达59.7m/s(17级)和50.7m/s(15级)。因此,中央气象台对“海葵”和“菲特”的实时业务定强一直维持着强台风强度,直至其分别登陆浙江象山和福建沙埕。Tang等[66]根据浙江宁波凉帽山370m铁塔观测资料的分析也证实了中央气象台对“海葵”的实时业务定强结果的合理性。以上分析表明,对一些中心附近云系较为松散、且临近登陆的台风,Dvorak技术业务定强分析结果有时会出现较大的偏差,这时需综合分析各种观测资料,进行及时订正。
3 小结与讨论
1)Dvorak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成熟和最具操作性的台风业务定强分析技术手段,为世界各大台风业务中心广泛采用。本文回顾了Dvorak技术的发展历程、简要介绍了目前国际上最通行的1984年版本的基于BD增强红外云图的Dvorak台风业务定强分析技术流程以及中央气象台在2012—2013年开展的业务试验及应用情况。业务试验及应用的结果表明:虽然Dvorak技术在台风云型特征的识别分析方面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弱台风的云型结构特征识别上,但从业务实践的实际效果来看,这在总体上并不影响Dvorak业务定强分析的精度,因此,Dvorak技术分析得到的台风现时强度指数(CI指数)可以作为中央气象台台风实时业务定强分析的主要技术参考指标,为台风业务实时定强分析提供客观技术依据,特别是对一些高影响的极端台风事件(如1013号超强台风“鲇鱼”和1330号超强台风“海燕”)和快速增强台风的强度监测分析。
2)Dvorak技术的业务应用不仅提高了我国台风业务定强分析的精度和客观技术支撑能力,而且对深入认识台风的结构变化也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年轻预报员把握台风强度发展变化和提高卫星云图的综合应用能力作用明显;同时Dvorak技术的业务应用还实现了我国台风业务定强分析流程与国际其他台风业务中心分析流程的接轨,增强了我国台风业务定强数据与国际上其他台风业务中心的可比性。与中国气象局台风最佳路径资料对比检验表明,中央气象台台风平均业务定强精度由2011年的1.9m/s优化至2013年的1.3m/s,提高近32%;针对2013年中央气象台和日本气象厅所确定的共511个CI指数对比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两者确定的CI指数基本一致,但对台风以下强度的CI指数分析结果,中央气象台较日本气象厅偏大的样本偏多明显,而对台风以上强度,两者CI基本一致,且样本数相差不大。两者总体相差在±1.0之间,这种差异与两者进行Dvorak技术分析时所使用的卫星资料(MTSAT或FY2系列)不一致有关,同时也与预报员的实际分析经验有关。
3)Dvorak技术并不是对台风风场和气压场的直接观测,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卫星图像估计台风强度的统计方法,并不能完全反映所有台风强度变化的真实情况,因此其技术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了解决Dvorak技术在实际台风业务定强分析中存在的局限性,综合应用极轨气象卫星微波遥感、雷达、沿岸及海岛地面气象观测站或飞机观测等多种资料来对Dvorak分析结果进行有益的补充分析是非常必要的,且综合应用各种探测资料得到的台风业务定强分析结果往往更为合理,并更接近地面实际观测的风速。
4)Dvorak技术分析中采用的台风风压关系,是影响台风业务定强分析精度和可信性以及台风强度气候资料均一性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由于目前还没有建立适用于将台风强度定义为2min平均风速的台风风压关系,Dvorak分析中采用仍然是1min平均风速的风压关系,因此,在台风实时业务定强分析中,仍需预报员对Dvorak定强分析结果做适当的主观修订。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风风压关系的建立工作至今尚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不仅将影响我国台风业务定强分析的精度,而且也将影响我国台风最佳路径数据在国际上的认知度和可信度。
[1]矫梅燕. 现代天气业务(上).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10.
[2]Sadler J C. Tropical cyclones of the Eastern North Pacifc as revealed by TIROS observations. J Appl Meteor, 1964, 3: 347-366.
[3]Fett R W. Life cycle of Tropical Cyclone Judy as revealed by ESSA II and NIMBUS II. Mon Wea Rev, 1966, 94: 605–610.
[4]Fritz S, Hubert L F, Timchalk A. Some inferences from satellite pictures of tropical disturbances. Mon Wea Rev, 1966, 94: 231–236.
[5]Hubert L F, Timchalk A. Estimating hurricane wind speeds from satellite pictures. Mon Wea Rev, 1969, 97: 382–383.
[6]Velden C, Harper B, Wells F, et al. The Dvorak tropical cyclone intensity estimation technique: A satellite-based method that has endured for over 30 years. Bull Amer Meteor Soc, 2006, 87: 1195–1210.
[7]Dvorak V F. A technique for the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of tropical cyclone intensities from satellite pictures. NOAA Tech Memo NESS 36, 1972.
[8]Dvorak V F. A technique for the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of tropical cyclone intensities from satellite pictures. NOAA Tech Memo NESS 45, 1973.
[9]Dvorak V F. Tropical cyclone intensity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from satellite imagery. Mon Wea Rev, 1975, 103: 420–462.
[10]Dvorak V F. Tropical cyclone intensity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from satellite visible or enhanced infrared imagery. NOAA National Environmental Satellite Service, Applications Laboratory Training Notes, 1982.
[11]Dvorak V F. Tropical cyclone intensity analysis using satellite data. NOAA Tech Report NESDIS 11, 1984.
[12]Dvorak V F. Tropical clouds and cloud systems observed in satellite imagery: Tropical cyclones. Workbook Vol.2, 1995.
[13]McBride J L, Holland G J.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ing: A worldwide summary of techniques and verifcation statistics. Bull Amer Met Soc, 1987, 68: 1230-1238.
[14]世界气象组织(WMO). 全球热带气旋预报指南. 裘国庆, 方维模, 等译. 北京: 气象出版社, 1995.
[15]John A. Knaff, Daniel P B, Courtney J, et al. An evaluation of Dvorak technique-based tropical cyclone intensity estimates. Wea Forecasting, 2010, 25: 1362-1379.
[16]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Tropical Cyclone Programme Report No. TCP-23: Typhoon Committee Operational Manual: Meteorological Component 2014 Edition, WMO/TD-No.196, 2014.
[17] 刘喆, 朱元竞, 李万彪, 等. 气象卫星资料在估测热带气旋强度方向的应用进展.热带气象学报, 2008, 24(5): 550-556.
[18] 刘喆, 王新, 李万彪, 等. Dvorak技术估测热带气旋强度研究进展.气象科技, 2007, 35(4): 453-457.
[19]Guard C P, Carr L E, Wells F H, et al. Joint Typhoon Warning Center and the challenges of multibasin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ing. Wea Forecasting, 1995, 7: 328–352.
[20]卫星云图联合分析组. 用卫星云图分析预报台风的方法(上). 气象, 1980, 6(9): 24-26.
[21]方宗义, 周连翔. 用地球同步气象卫星红外云图估计热带气旋的强度. 气象学报, 1980, 38(2): 150-159.
[22]王志烈, 费亮编. 台风预报手册. 北京: 气象出版社, 1987.
[23]董超华. 气象卫星业务产品释用手册. 北京: 气象出版社, 1999.
[24]范蕙君, 李修芳, 燕芳杰, 等. 确定台风强度方法的改进. 气象, 1990, 16(8): 10-14.
[25]李修芳, 范蕙君, 燕芳杰, 等. 用增强显示云图确定热带气旋强度的方法. 应用气象学报, 1993, 4(3): 10-14.
[26]范蕙君, 李修芳, 燕芳杰, 等. 用数字云图确定热带气旋强度的原理和方法. 大气科学, 1996, 20(4): 439-444.
[27]江吉喜. 增强显示红外卫星云图在热带气旋分析中的应用. 气象学报, 1986, 44(4): 482-487.
[28]范蕙君, 李修芳, 燕芳杰, 等. 用数字云图确定热带气旋强度方法的检验和应用. 应用气象学报, 1996, 7(1): 113-117.
[29]燕芳杰, 范蕙君, 李修芳, 等. 用数字云图确定热带气旋强度的人机对话系统. 气象, 1995, 21(11): 30-32.
[30]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The Final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atellite Analysis of Tropical Cyclones, 2011.
[31]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Tropical Cyclone Programme Report No. TCP-52: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atellite Analysis of Tropical Cyclones, 2011.
[32]Paul McCrone. Dvorak Guide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 mccrones.com/tropical/dvorak/.
[33]郭炜, 卢乃锰, 孙冬联, 等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培训教材: 卫星观测的热带云和云系. 北京: 气象出版社, 1996.
[34]中国气象局. 台风业务和服务规定(第四次修订版).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12.
[35]Atkinson G D, Holliday C R. Tropical cyclone minimum sea level pressure/maximum sustained wind relationship for the western north pacifc. Mon Wea Rev, 1977, 105: 421-427.
[36]Koba H, Osano S, Hagiwara T, et al. Determination of intensity of typhoons passing through the Philippine islands (in Japanese). J Meteor Res, 1989, 41: 157–162.
[37]Koba H, Hagiwara T, Osano S, et 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 Number from Dvorak's technique and minimum sea level pressure or maximum wind speed of tropical cyclones (in Japanese). J Meteor Res, 1990, 42(2): 59–67.
[38]Koba H, Hagiwara T, Osano S, et al. Akashi.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 Number and minimum sea level pressure/maximum wind speed of tropical cyclones. Geophysical Magazine, 1991, 44(1): 15-25.
[39]Osano S. Improvement of tropical cyclone analysis with satellite data. The 22nd session of ESCAP/WMO Typhoon Committee, Japan, 1989.
[40]Kamahori H, Yamazaki N, Mannoji N, et al. Variability in intense tropical cyclone days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c. SOLA, 2006, 2: 104-107.
[41]Nakazawa T, Hoshino S. Intercomparison of Dvorak parameters in the tropical cyclone datasets over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SOLA, 2009, 5: 33-36.
[42]Harper B. A. Tropical cyclone parameter estimation in the Australian region: Wind–pressure relationships and related issues for engineering planning and design. A discussion paper. Systems Engineering Australia Pty Ltd (SEA) for Woodside Energy Ltd, 2002.
[43]燕方杰, 范永祥. 西北太平洋台风近中心最大风速与中心最低海平面气压的统计相关. 气象科技, 1994, (1): 56-59.
[4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台风等级GB/T19201-2006.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6.
[45]Guard C P, Lander M A. A wind–pressure relationship for midget TCs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c. 1996 Annual Tropical Cyclone Report of Joint Typhoon Warning Center, 1996.
[46]Callaghan J, Smith R 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face wind speeds and central pressure in tropical cyclones. Aust Meteorological Magazine, 1998, 47: 191-202.
[47]许映龙. 重新审视台风业务中的风压关系. 第14届全国热带气旋科学讨论会, 2007.
[48]Knaff J A, Zehr R M. Reexamination of tropical cyclone wind–pressure relationships. Wea Forecasting, 2007, 22: 71–88.
[49]Shyamnath V. Comments on “Reexamination of Tropical Cyclone Wind–Pressure Relationship”. Wea Forecasting, 2008, 23: 758–761.
[50]Harper B A, Stroud S A, McCormack M, et al. A review of historical tropical cyclone intensity in North-western Australia and implications for climate change trend analysis. Aust Meteor Mag, 2008, 57: 121-141.
[51]Greg H. A Revised Hurricane Pressure-Wind Model. Mon Wea Rev, 2008, 136: 3432–3445.
[52]Knaf J A, Zehr R M. Reply to Comments on "Reexamination of Tropical Cyclone Wind-Pressure Relationship". Wea Forecasting, 2008, 23: 762-770.
[53]Courtney J, Knaf JA. Adapting the Knaf and Zehr wind-pressure relationship for operational use in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 centres. Aust Meteor Ocea J . 2009, 58(3): 167-179.
[54]Kieu C Q, Chen H, Zhang D L.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essurewind relationship in intense tropical cyclones. Wea Forecasting, 2010, 25: 895-907.
[55]Knaf J A, Harper B A. Tropical cyclone surface wind structure and wind-pressure relationships. WMO 7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ropical Cyclones, 2010.
[56]Knapp K R, Kruk M C,. Levinson D H, et al.The International Best Track Archive for Climate Stewardship (IBTrACS): Unifying tropical cyclone best track data. Bull Amer Meteor Soc, 2010, 91: 363-376.
[57]Landsea C W, Anderson C, Charles N, et al. The Atlantic hurricane database reanalysis project: Documentation for 1851–1910 alterations and additions to the HURDAT database. Hurricanes and Typho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lumbia: Columbia UnivPress, 2004.
[58]Webster P J, Holland G J, Curry J A, et al. Changes in tropical cyclone number, duration, and intensity in a warming environment. Science, 2005, 309: 1844–1846.
[59]Brown D P, Franklin J L, Landsea CW. A fresh look at tropical cyclone pressure-wind relationships using recent reconnaissancebased best track data (1998–2005). Preprints, 27th AMS Conference on Hurricanes and Tropical Meteorology, Monterey, CA, April 2006.
[60]Weber H C. On the pressure–wind relationship in tropical cyclones. Preprints, 27th Conf. on Hurricanes and Tropical Meteorology, Monterey, CA, 2007.
[61]Kossin J P, Knapp K R, Vimont D J, et al. A globally consistent reanalysis of hurricane variability and trend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7, 34: p6.
[62]Kruk M C, Knapp K R, Levinson D H, et al. Data stewardship of global tropical cyclone best tracks. Preprints, 28th Conf on Hurricanes and Tropical Meteorology, Orlando, FL, 2008.
[63]Michael K C, Knapp K R, Levinson D H. A technique for combining global tropical cyclone best track data. J Atmos Oceanic Technol, 2010, 27: 680–692.
[64]Kenneth K R., Kruk M C. quantifying interagency diferences in tropical cyclone best-track wind speed estimates. Mon Wea Rev, 2010, 138: 1459–1473.
[65]Harper B A, Kepert J D, Ginger JD. Guidelines for converting between various wind averaging periods in tropical cyclone conditions.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TCP Sub-Project Report, WMO/TD-No.1555, 2010.
[66]Tang Jie, Wu Dan. Intensity identifcation of typhoon haikui (1211) during the landing stage. Trop Cycl Res Rev, 2013, 2(1): 25-34.
Typhoon Intensity Estimation Technique and Its Operational Application: With Example of Dvorak Technique
Xu Yinglong1,2,3, Zhang Ling3, Xiang Chunyi3
(1 Chinese Academy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s of CMA, Beijing 100081 2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3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re of CMA, Beijing 100081)
The history of operational typhoon intensity estimation based on Dvorak technique is reviewed and 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the operational flow of typhoon intensity estimation in China i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n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method and flow of Dvorak technique (1984 Edition) based on BD enhanced infrared satellite image and recommended by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and the effect of its operational tests and application in Central Meteorological Office (CMO) of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CMA) in 2012 and 2013. Finally, the limitation of Dvorak technique and some problems in operational analysis a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of the operational tests and application show that Dvorak technique not only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operational typhoon intensity estimation and the objective technical support capabilities in CMO/CMA, but also enhances the comparability of the operational typhoon intensity estimation data given by CMO/CMA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al typhoon centers. And the comparative verification resutls, based on the CMA typhoon best track data, show that the average accuracy of operational typhoon intensity estimation of CMO increased to 1.3 m/s in 2013 from 1.9 m/s in 2011, increased by nearly 32%;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total 511 comparative samples in 2013 indicate that the current typhoon intensity index (CI) given by CMO and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JMA) are almost consistent, and there is an overall difference of ±1.0 between their CI indices.The difference is related to the satellite data (MTSAT or FY2 series) using in Dvorak analysis and the operational analysis experience of the forecasters.
10.3969/j.issn.2095-1973.2015.04.003
2013年12月3日;
2014年6月12日
许映龙(1968—),Email: xuyl@cma.gov.cn
资助信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5066和41175063);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GYHY200906002和GYHY201106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