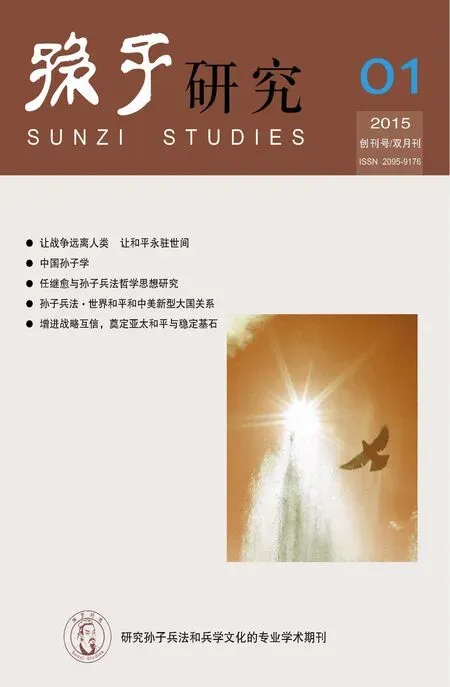《吴越春秋》孙武“辟隐深居”说刍议..
2015-02-07陆允昌
陆允昌
《吴越春秋》孙武“辟隐深居”说刍议..
陆允昌
本文通过《吴越春秋》与《左传》《史记》相关史书的比较分析及对《吴越春秋》作者赵晔的研究,对古兵家孙武当年曾否在苏州“辟隐深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吴越春秋》 孙武 辟隐深居
齐人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史记》语)之前,是否已在吴地“辟隐深居”?当今国内兵学界、文史界人士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不同见识,但以肯定者居多,而持“肯定说”者无一例外援引《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传云:
(阖闾)三年(前512年),吴将欲伐楚,未行。伍子胥、伯嚭相谓曰:“吾等为王养士,画其策谋,有利于国,而王故伐楚,出其令,托而无兴师之意,奈何?”有顷,吴王问子胥、伯嚭曰:“寡人欲出兵,于二子何如?”子胥、伯嚭对曰:“臣愿用命。”吴王内计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灭而已,登台向南风而啸,有顷而叹,群臣莫有晓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荐孙子于王。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鉴辩,知孙子可以折冲销敌。乃一旦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细察此言,最值得关注之处在于:伍子胥“七荐孙子”,缘于他与伯嚭(楚人,因受迫害奔吴)二人在吴王阖闾欲出兵伐楚表示“臣愿用命”时,阖闾却产生“内计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灭而已”的反常行为,从而引出“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荐孙子于王”,以至于作者赵晔推出孙武是“吴人”及“辟隐深居”的事。显然,阖闾的“内计”与子胥的“荐孙子”之间存在“因”与“果”的关系。
一
《吴越春秋》此一记载是否可信?要害在于“因”与“果”是否紧密契合。这就需要作切实的论证。笔者依据《左传》和《史记》的记载,先就吴、楚二国关系作一简要交代。
早在东周以前,地处南方的楚、吴、越三国向被中原诸国鄙视为“蛮夷”。三国间相安无事,一度还结为盟友。《左传·宣公八年》(前601年)记有“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据《左传·成公七年》(前584年),楚国巫臣因其族人被朝廷卿大夫子重、子反残杀并瓜分他们的家产,愤而投向晋国,发誓报仇。由于楚、晋两国长期不睦,互相侵伐,巫臣入晋后即“请使于吴”,企图联合吴国,攻伐楚国。对此“晋侯许之”。其时,吴国正在崛起,出于与楚国争霸的需要,吴王寿梦欣然接受晋国“以两之一卒(30辆战车)适吴,舍偏两之一(士卒25名)焉,与其射御(驾车者和射手)。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并重用狐庸(巫臣之子)“使为‘行人’(外交官)”。是年,“吴始伐楚,伐巢(今安徽巢县东北),伐徐(今安徽泗县北)。子重奔命”。吴、楚两国从此反目。自后,“马陵之会,吴入州来(今安徽凤台县境),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中原诸国)”(引号内文字均引自《左传》)。
从寿梦称“王”到阖闾弑僚自立之前的七十年间,吴、楚二国先后发生战事十次,互有胜负,规模虽不大,但彼此积怨加深。《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公子光(阖闾,下同)于吴王僚二年(前525年)、八年(前519年)、九年(前518年)曾三次奉命伐楚。吴王僚五年(前522年)伍子胥因楚平王听信谗言杀其父、兄,历尽艰辛,亡命奔吴,欲“借力以雪父之耻”(《史记》语)。入吴之初,子胥就向吴王僚建议举兵伐楚。王僚“知之,欲为兴师复仇”。而在场的公子光(阖闾,下同)早有觊觎君位之心,深恐子胥的建议得到王僚的赞同而害其谋,于是出谗言,以子胥建议伐楚是出于“报私仇”为由,进行挑拨,致使伐楚一事被取消。子胥看出公子光有“内志”,转而投靠于他。
《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有此记载:
子胥之(至)吴。……公子光闻之,私喜曰:“吾闻楚杀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复父之仇,来入于吴。”阴欲养之。市吏于是与子胥俱入,见王。……王僚知之,欲为兴师复仇。公子〔光〕谋杀王僚,恐子胥前亲于王而害其谋,因谗:“伍胥之谏伐楚者,非为吴也,但欲自复私仇耳!王无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子胥退耕于野,求勇士荐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专诸。
由于得到伍子胥的鼎力相助,公子光于吴王僚十二年(前515年)弑僚自立。事成后,阖闾聘伍子胥为“行人”,执掌吴国内政、外交,君臣相依,形同一人。以此而论,三年后,阖闾何以对子胥和伯嚭二人表示伐楚“臣愿用命”时突然变卦,对“二子”心生疑虑?这于情理不合。可见,《吴越春秋》所记的上述文字,明显存在抵牾之处!
再以《左传·昭公三十年》(前512年)所记作一验证:
吴子(阖闾)问于伍员(子胥)曰:“初而(尔,你)言伐楚者,余知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如何?”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肆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左传》的记载说明,伍子胥奔吴之初建议吴王僚举兵伐楚,在场公子光是“知其可也”,只因怀有弑僚自立的阴谋,故在王僚面前谗言,力劝“王无用之”。当子胥知道公子光“欲害王僚”,转而投向他,为其出谋划策。阖闾三年(前512年),在与子胥商议伐楚时,阖闾终于吐露衷肠,告诉子胥“初而言伐楚者,余知其可也”,提出“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如何”?子胥立即献伐楚之策“三师以肆”。“阖闾从之”。阖闾四年(前511年),《左传》载:
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楚沈尹戌帅师救潜,吴师还。楚师迁潜于南冈(今安徽六安县北)而还。吴师围弦。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
这进一步说明阖闾对于“伐楚”,不仅与子胥一致,而且对子胥提出的“三师以肆”的战术,言听计从。君臣无隙,又何来“内计”此类疑虑、揣度之心?
同一年(前512),同一事(君臣商议伐楚),同一作者(赵晔),《吴越春秋》)竟然出现二种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的不同记载。无论从“内证”,还是“外证”,是《左传》可信?还是《吴越春秋》可信?这是不辨自明的。
《吴越春秋》是一部记载春秋末期吴、越两国相争史事的著作。学界公认,其书的要点皆取自《左传》《史记》《国语》,但叙述的情状却并不一致。例如,上述三部古籍恰恰都没有子胥“七荐孙子”以及孙子 “辟隐深居”的事。
二
对于一些学者认为孙武在“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前,早已在吴地“辟隐深居”的说法,苏州大学陆振岳教授先后发表《孙武由齐入吴曾否隐居考析》和《“辟隐深居”考——再论孙武入吴隐居说不可信》,认为:“‘辟隐深居’或者与此相似的记载,既不见于先秦典籍的《左传》、《国语》等,也不见于汉代撰写的《史记》,连宋代撰成的《新唐书》,其《宰相世系表三下》的‘孙氏’述及孙武的身世,也不载隐居的事。这样问题就来了,成书年代比《左传》约晚550年,比《史记》约晚150多年、距离事发已近600年的《吴越春秋》这一独家记载的孤证是否可信?就成为‘隐居说’成立与否的关键。”他的看法是:“《吴越春秋》所说阖闾对子胥伐楚复私仇的疑虑,以及由此而引出‘荐孙子于王’,完全是作者赵晔臆想出来的。这就是说,这个‘因’是不存在的。因此,由这个‘因’而导致‘七荐孙子’,并引出孙武‘辟隐深居’的‘果’,也就失去了前提,‘隐居说’自然就不能成立。”
对陆振岳先生所议,苏州科技学院的戈先生以“不能贬低《吴越春秋》的史料价值”为由,撰文提出质疑和批评。说:
孙武至吴地隐居著述兵法,最早提出此说的是《吴越春秋》。有人为了否定孙子隐居于吴的事实而竭力否定《吴越春秋》的史学价值,这是不公允的。……孙子隐居于吴地,由伍子胥而受知于吴王阖闾。《吴越春秋》之说,是对《史记》“孙子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的补充,并与同时代写作的史书《汉书》相一致。
笔者以为,戈先生的这段文字有三处需要拨正:
一是《吴越春秋》只说“辟隐深居”,并无“至吴地隐居著述兵法”之说,这显然是戈先生自己添加所为。二是《吴越春秋》之说是对《史记》的补充。这是“与史无据”的臆说。三是说与《汉书》相一致,此言差矣。《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其中《刑法志》中的原文是:
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擒)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从连横,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
书中并无记有孙武“辟隐深居”之事,更未言明孙武于何地“垂著篇籍”,又何以说与“《汉书》相一致呢”?戈氏接着说:
有人为了否定“孙武隐居”,把《吴越春秋》贬为“问题不少”的野
史。我认为,《吴越春秋》是中国最
早的地方史著之一,具有可靠的史
料价值。《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
作。……其所作多采自当地史乘与民
间传闻,是记载吴越遗事的地方史,
故含有不少真实成分。他所记孙武
“辟隐深居”说,当亦是真实可靠,
因而获得明杨循吉《(嘉靖)吴邑志》、
牛若麟《(崇祯)吴县志》、冯桂芬《(同
治)苏州府志》的赞同而著之于书。
《吴越春秋》的史料不能贬低,它所
载的“孙武入吴隐居”说应该肯定。
笔者以为,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此话未免偏颇。
客观地说,《吴越春秋》自问世以来,历来的古典目录学者、文献学者既肯定它“在记事方面有独到之处”,同时也指出此书存在“史实错乱”、“年代混淆”、“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等问题。学界人士公认它是一部杂合正史、传说、想象几方面材料敷演汇集而成的历史小说。《隋书·经籍志》称:“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自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主编清《四库全书》的纪昀等人认为,《吴越春秋》“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属于小说家言”。《白话吴越春秋》一书的译者黄仁生先生在“序言”中直言:“它实际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言长篇历史小说。”这些评价是确当的。而把此书说成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史著之一,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显然有违史实。
在此,不妨以《左传》《史记》《吴越春秋》三书对同一事(从“子胥入吴”到“退耕于野”)的“表述”作一对比。
《左传·昭公二十年》载:
员(子胥)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吴王僚)。公子光曰:“是宗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从也。”员曰:“彼将有他志,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见专设诸(专诸)焉,而耕于鄙。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
(员至于吴)伍子胥说吴王僚曰:“楚可破也。愿复遣公子光。”公子光谓吴王曰:“彼伍胥父兄为戮于楚,而劝王伐楚者,欲以自报其仇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退而与太子建(楚国公子)之子胜耕于野。
《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载:
子胥之(至)吴,乃被发佯狂,跣足涂面,行乞于市。市人观,罔有识者。翌日,吴市吏善相者见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尝见斯人也。非异国之亡人乎?”乃白吴王僚。具陈其状,王宜召之。王僚曰:“与之俱入。”公子光问之,私喜曰:“吾闻楚杀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复父之仇,来入于吴。”阴欲养之。市吏于是与子胥俱入见王。王僚怪其状伟,身长一丈,腰十围,眉见一尺。王僚与语三日,辞无复者。王曰:“贤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语语,遂有勇壮之气,稍道其仇,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为兴师复仇。公子〔光〕谋杀王僚,恐子胥前亲于王而害其谋,因谗:“伍胥之谏伐楚者,非为吴也,但欲自复私仇耳!王无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入见王僚,曰:“臣闻诸侯不为匹夫兴师用兵于比国。”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诸侯专为政,非以意救急后兴师,今大王践国制威,为匹夫兴兵,其义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吴王乃止。子胥退耕于野,求勇士荐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专诸。
三书所述之事完全相同,但遣词用语,《左传》《史记》叙事简洁,文字凝练,绝无虚幻造作之言。《吴越春秋》则庞杂得多,尤其是书中的曲折情节和人物形象及对话,明显出自赵晔的想象和发挥,使本来平常的事变成充满吸引力的动人故事。联系书中所云“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以及充斥“梦签占卜”之言,使《吴越春秋》一书成为今人所说的“既有历史意义上的野史,也有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当代知名学者周谷城先生担纲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把《吴越春秋》归入“杂史”之列。《吴越春秋全译》的译注者张觉先生在“序言”中直言:“当然,作者对体例的构思虽然很好,但在具体的记载中却往往有年代错乱的情况,有些事迹也明显有违史实。我们虽然基本上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但它毕竟是一部杂史,如果毫无鉴别地采用其中的记述来研究当时的历史,那显然也是不适当的。这是我们在利用其中的史料时应加注意的。”在此,笔者再就《吴越春秋》所记孙武事迹,择其要点,从史料学的角度作一番阐释。
三
第一,《吴越春秋》称孙武是“吴人”,明显与古籍记载不合。
具体来说:
1.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见吴王》孙武在吴王阖闾面前自称“外臣”不合。“外臣”一词,是古代列国大夫和士对别国君主的自称。《国语·贿免卫侯》:“自是晋聘于鲁,加于诸侯一等;爵同,厚其好货。卫侯闻其臧文仲之为也,使纳赂焉。辞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说的是晋人曾执卫侯“归之于周”,卫侯后来得释,知道是鲁国大夫臧文仲所谏。卫侯不忘此恩,遣使赠礼答谢。臧文仲一再推辞,遂说了上面的话。这里的“外臣”,是臧文仲对卫侯的自称。又,《仪礼·士相见礼》曰:“凡自称于君……他国之人,则曰外臣。”足见孙武非“吴人”。
2.与《史记》所称不合。《史记》明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此处的“齐”,当指“齐国”,说明孙武的里籍是“齐”而非“吴”。
3.与《越绝书》称“吴王客、齐孙武”更是相悖。“吴王客”,清楚地表明孙武是吴国的“客卿”。所谓“客卿”,即古代在别国做官的外籍人。如:《史记·范睢列传》,记范睢是魏国人,辩士出身,后来“羁旅入秦”,秦王“拜范睢为客卿,谋兵事”。至于《汉书》称“吴孙武”(见《古今人表》),并对其时存世的孙武、孙膑两人的《兵法》分别冠以“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和“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是因孙武、孙膑古代都被尊称“孙子”,《汉书》称孙武为“吴孙子”,称孙膑为“齐孙子”,用意在于区分两部《兵法》而已。
由此可知,《吴越春秋》称孙武是“吴人”,显然是赵晔的揣度,故为后世史家所不取。
第二,《吴越春秋》称吴军攻入楚都,“阖闾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伯嚭亦妻子常、司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与《左传》所记完全相反。
《左传·定公四年》(前506年)记:“庚辰,吴入郢(楚都),以班处宫。子山(阖闾子)处令尹之宫。夫概王(阖闾弟)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处”的一个义项是“住所”。其意是:吴军攻入楚国都城后,按照官位高下,君、臣分别住进楚国君、臣的宫室或住所。子山住进楚国令尹(执掌楚国军政重任)囊瓦的住所,但被夫概看中,欲行夺占。子山惧怕,只得退出。赵晔却把《左传》的“以班处宫”,敷演成阖闾、子胥、孙武、伯嚭等吴国君臣夺人之妻,奸淫被占领下的楚国君臣妻室!
第三,《吴越春秋》称:“孙武曰,吾以吴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戳其尸,亦已足矣”。这也与史实不符。
(吴)阖闾九年(前506年),吴国面对20万楚军,以3万之众取得“五战入郢”、“昭王出奔”、楚国险遭灭亡的重大军事胜利。中原各诸侯国为之震动。此次吴、楚决战,伍子胥、孙武、伯嚭、夫概等人功不可没,但“西破强楚”的统帅是吴王阖闾,作为“吴王客”的孙武岂能僭称“吾以吴干戈西破楚”?至于“屠墓”、“戮尸”事,先秦以来传说纷纭:一说有其事;一说无其事。早于《史记》的《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王〕之坟三百”。先秦成书的《春秋谷梁传》《淮南子·泰族训》以及东汉时成书的《越绝书》,均从此说。这说明伍子胥并没有“掘墓鞭尸三百”,而仅是“鞭坟三百”。无论是鞭“尸”,还是鞭“坟”,都只能说是《吴越春秋》作者赵晔此言在于彰显伍子胥因楚平王听信谗言、将其父、兄杀戮后的复仇心态。这与孙武何干?孙武岂能如《吴越春秋》所说,越俎代庖,把功劳归于自己?
对于《吴越春秋》的史料价值,固然不能一概否定,但仅从上述数点,能说《吴越春秋》所云完全可信吗?
四
关于赵晔,《后汉书·儒林传》有传,全文如下: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
从《儒林传》中可以窥见,赵晔的长项在于“诗”,而不在于“史”,如今有人称赵晔是“东汉史学家”,显然言过其实。
至于赵晔的“辟隐深居”说在“地方志”中的记载,也有必要在此作一辨析。
苏州自唐至民国的一千五百年间,先后编就并现存于世的府、县《方志》有十三部,其中确有三部采录《吴越春秋》孙武“辟隐深居”一说。如明嘉靖《昊邑志》卷七《人物》载:
孙武,吴人也,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吴王阖闾将伐楚,伍员乃荐武于阖闾。阖闾乃召武,问以兵法。
明崇祯《吴县志》卷四十二《人物》载:
孙武者,齐人也,《吴越春秋》作吴人。善于兵法,避隐深居,人莫知之。吴王阖闾将伐楚,伍员乃荐武。武以兵法见于阖闾。
清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四《杂记一》载:
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鉴辩,知孙子可以折冲销敌,乃一旦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
上述三部《方志》的内容和遣词用语,与《吴越春秋》雷同。由此可以肯定,三“志”所记并不是新材料。这是《方志》记叙的特点,以网罗地方文献为能事,没有什么可以深文周纳的。问题在于《方志》所记或所录是否真实?倘使是不可信的,即使重复百遍千遍,又有什么意义呢!况且,苏州尚存其余十部府、县《方志》,如〔唐〕陆广微《吴地记》、〔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和范成大《吴郡志》、〔明〕卢熊《〔洪武〕苏州府志》和王鏊《〔正德〕姑苏志》、〔清〕卢腾龙、宁云鹏《〔康熙〕苏州府志》、习寯《〔乾隆〕苏州府志》、姜顺蛟《〔乾隆〕吴县志》、石韫玉《〔道光〕苏州府志》、以及曹允源、李根源《〔民国〕吴县志》,都没有采录《吴越春秋》所云孙武“辟隐深居”之事。
此外,苏州尚存五部穹窿山志(记):清康熙年间的《穹窿山志》、民国时期惠心可《穹窿山志》、李标《穹窿山志》、李根源《穹窿小记》和《穹窿山志残稿》,也都没有记载孙武的片言只语,更不用说孙武在所谓苏州穹窿山“辟隐深居”、“著述兵法”的事了。
(责任编辑:李兴斌)
Discussion on Sun Wu Living in Seclusion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Wu and Yue State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ut forward his own view on whether Sun Wu lived in seclusion in Suzhou with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Wu and Yue States, Zuo Zhuan and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and study on Zhao Ye, the author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Wu and Yue States.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Wu and Yue States; Sun Wu; living in seclusion
K85
A
2095-9176(2015)01-0104-07
2013-12-1
陆允昌,原苏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