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2015-02-03罗拱北
罗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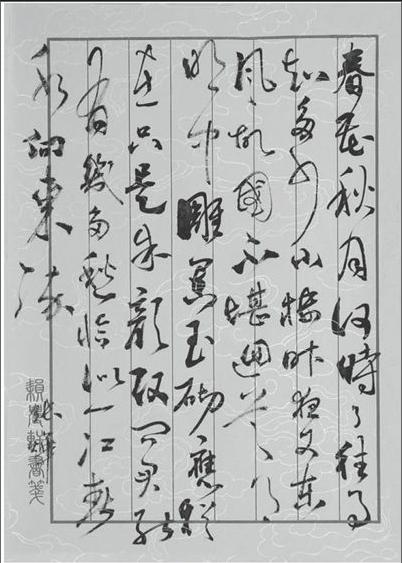
近一段时间,我总是梦见老屋。
老屋是我老家的房子,它的年龄应该比我还大,因为自我记事的时候起,它就在现在这个位置,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至今应该超过四十年了吧。老屋是四川最为常见的三合院,没有什么明显的特点,要说与别家略有不同之处,就是院坝边上有两棵树。一棵是桃树,从根部开始就分为两个丫杈,那桃树长得很高很高,其中一枝竟然都伸到房背上去了。一棵是梨树,长得枝繁叶茂。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那些桃子和梨子是如何安慰了一个乡下少年狂野的心,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大约是在端午前后,那些布满了绒毛的桃子就从层层叠叠的叶子间露出了头,仿佛还在向我们一群小孩子眨眼。尽管大人一再厉声呵斥我们果子没有成熟不许偷吃,但是我们哪里受得了这个诱惑。大人在屋里时,我们装得若无其事,趁大人出坡劳动,我们就干起小偷的勾当。在几个孩子当中,我年龄最大,手脚敏捷,顺着树干爬到房背上去偷摘桃子更是我的拿手本事。说来很怪,也许房背上的桃子与其他枝条上的桃子并无两样,但我就是觉得比其他桃子大、比其他桃子好吃。我象猴子一样爬到树上,再抓着枝条从树上轻轻地下到房背上,然后悄悄坐在浓密的叶子背后。没有成熟的桃子,青色的表面布满了绒毛,但是这难不住我,摘了桃子,我撩起衣角几下就把它擦得光光溜溜,狼吞虎咽塞入嘴里,尽管那桃子还没长出甜味。吃上几个后,我再在衣服裤子兜兜里塞上几个,顺着树干溜下来,把桃子分给弟弟妹妹和邻家的小孩。大人发现后刚开始骂得挺凶,但是随着树上的桃子越来越少,骂声也就日渐稀少下来。待一树桃子只剩下枝叶的时候,我们又把目光转向了那些青皮的梨子……大人每年都没有见到果子长大,倒是我们一天天越来越大。家里的房子不够住了,祖爷决定把桃树砍了,在院子边上又加盖了两间瓦屋。那棵梨树无疑是幸运的,直到现在,依然在春天开出雪白的花朵,夏天则挂满了黄澄澄的果实。
这座白墙青瓦的老屋,留存着我温馨的记忆,也留着我揪心的牵挂。
我家原来是四世同堂的,那时一大家子十几口人住在一起,祖爷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是一家之主,他的威严让全家人感到惧怕。父亲是老大,据母亲说有了我之后,祖爷就将老屋东头两间房子分给父亲,让父亲分家另过,后来陆续又有了我的妹妹和弟弟,而祖爷、爷爷则拖着尚未成家的二爸和五个姑姑住在老屋的西头。虽然是一大家人,但由于生活都很拮据,除了过年,其余时间是从不在一起吃饭的,甚至有时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彼此之间还吵吵闹闹。我的祖婆却是一个无比慈爱的老太太,她不仅从不参与大人之间的吵闹,还对我们姊妹三个在幼年时期给予了无限怜爱。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她终年穿着一件深蓝的长衫,头缠一条黑色的丝帕。由于长年患病,她浑身瘦得皮包骨头,那青筋毕露的手里经常拎着一个取暖用的烘笼,而且罩在长衫下面,她的身子微微佝偻,面容却经常带笑,看不出她有多么痛苦。那时我们家孩子多,粮食经常不够吃,当我们家快断顿的时候,祖婆便偷偷地给我们舀半碗米,裹在长衫里给我们拿过来,以解母亲的燃眉之急。她长年吃中药,为了缓解口苦,祖爷给她备了些白糖,她却舍不得全吃了,而是一点一点藏起来,等我们饿了的时候,她悄悄地给我们泡水喝。有一次我家做饭的时候正好没了盐,我自告奋勇端着一个瓷杯去找祖婆借盐。祖婆给我装了满满一杯,我端着杯子兴冲冲地往家跑,却忘了四川的土墙房子门槛都是很高的,三四岁的孩子一步根本迈步过去,我一跤跌倒,把杯子甩了个粉碎。母亲又气又急,几巴掌打在我屁股上——要知道七十年代的农村买一斤盐也不容易。我还没哭祖婆却哭得眼泪婆娑的,她一边赶紧跑来拉我一边数落母亲,“一杯子盐撒了就撒了,你还打娃!”然后又找了一个杯子装了盐交给母亲。等我现在有能力为祖婆买糖的时候,她已经过世多年,只剩下她单薄的背影、一头白发和我深深的叹息!
还有我的小姑,她大约比我大三四岁的样子。有一年冬天天气奇寒,老屋旁边的一个冬水田结了厚厚的冰。她偷偷地背着我去滑冰,她那时也是小孩子,根本不会想到四川的冬天即使再冷冰也是不结实的,哪里承受得起两个小孩加在一起的重量,结果没走几步,“扑哧”一声全掉到了冰窟窿里,吓得她哇哇大哭。大人听到哭声,才赶紧把我们拉上来。
但是这些都不是我牵挂老屋的主要原因,关键是我的父母至今还住在老屋。随着年岁的更迭,家里的老人相继去世,二爸十几年前就搬到了离老屋不远的镇上,我们姊妹三个都在城里买了房子,原来热热闹闹的老屋如今就剩下父母在那里居住了,一下子竟显得无比空落和寂寥。经历多年的风雨,老屋已经老了,房背上不仅长了一片片苔藓,而且有的地方檩条断裂,一到雨天就开始漏水,虽然还不至于象杜甫那间“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茅屋那般凄惨,但是我毕竟担心父母的安全,尤其是当我所在的城市下雨的时候,我总要给打个父母电话回去,问问老家是否也在下雨,尽管父母说一切安全,我还是要反复叮咛他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有雨的夜晚不要睡得太死,白天要到房子四周转转,看看有无破损的地方,我的心里似乎有一片瓦一直在悬着,老是感觉只要一下雨它就有可能掉下去伤着父母。前年父亲身体一直不好,大姑打电话叫我们把父母接到城里,不要再在老房子里住了。我与父母商量,父亲坚决不同意,说是身体还好,还可以种几年庄稼。我估计父母一方面是怕给我们增添负担,另一方面也许是他们已不愿离开居住惯了老屋。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如今他们已经步入老年的行列,他们在老屋里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他们需要的农具以及伺候惯了的鸡鸭牛猪,他们是这里的主人,而到了城里,认不得一个人,找不到回家的路,让他们换一个环境,无异于把一棵老树连根拔起而让它去适应新的水土,那对他们而言实在是太陌生也太痛苦了。我想帮父母把老屋翻修一下,把那些朽了的檩条和破了的瓦片给换一换,可是这些年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已经找不到木工和烧瓦的师傅了。我也想过在镇上给父母买两间房子,至少让他们住着放心,但是这个想法也没有得到他们同意。在父母眼里,老屋不仅仅只是一座可以居住的房子,而是他们生命和生活的圆心,老屋的周围有一条条小路,伸向他们成天在上面劳作的土地,伸向长满柴禾的山坡,伸向水井,伸向与山外连接的大路,他们就象蜘蛛,在自己精心编织的这张网上进退自如,如果把他们搬离了圆心,他们也就失去了依靠,他们的根也就失去了生生不息的滋养。为了不伤着父母的根系,我们姊妹几乎年年春节都要回去,帮父母把老屋修修补补,以便让父母能够住得舒心一些,也让我在远方能够少点愧疚和担忧。夜晚,睡在老屋的床上,风嗖嗖地从门缝里灌进来,仿佛整座房子都在吱吱作响,忽明忽暗的灯光把斑驳的墙面照得光怪陆离,我怎么也睡不着,一位位亲人的影子和过去的事情象电影一样从脑子里一一掠过,那些在小时候怨恨过或是喜欢过的亲人,此刻都让我感觉那么亲切和怀恋。
直到今天,我时时陷于纠结之中,不知该如何对待老屋。它就象一个尖锐的楔子,深深地扎在我的内心,让我伤痛,也让我快乐,让我纠结,也让我踏实。它也许更象一个锚,用一根看不见的链子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即使我飘得再远,飞得再高,而最后都要回到那个原点。我想,如果有一天老屋真正人去楼空,我也就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