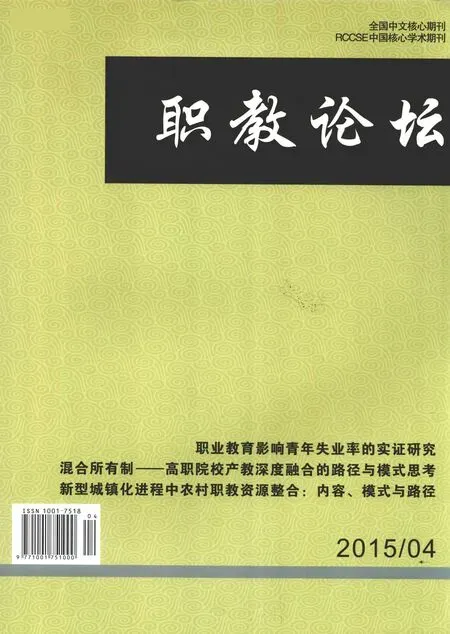农村职业教育杂谈之二20世纪初期我国乡村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
2015-02-01
一
尽管说农村一词是近代社会的产物,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不断身份强化的结果,但是,既然它成为了大众术语,也就没有必要回到乡村词汇上去,这也是整组文章还是叫做农村职业教育杂谈的原因。无论用什么词汇表达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事物。
农村职业教育问题是目前我国存在的现实情况,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所谓历史问题是指他既是历史发展带来的结果,也是今后发展的起点与基础。历史发展的结果有时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有时也是可以避免一些发展误区得到更好的结果,当然,历史是没有办法重现和改变的,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但是,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是可以避免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犯同样的错误,因此,梳理历史也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总的来讲,我国的农村职业教育是从近代开始的,也可以说是伴随着近代实业教育的发展而开始的,尽管这一现象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清末,但20世纪初期的大规模乡村教育运动更具有典型性。当时的乡村教育运动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历史的经验还是历史的教训,就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梳理,因为它对目前农村职业教育还产生着影响。
对20世纪乡村教育的梳理,首先需要对乡村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进行简要的回顾。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兴办新式学堂,诏书中提到“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在之后的几年时间内,各省均开始兴办新式学堂。但由于政府经费短缺,不少地方的新式学堂大都由当地乡坤兴办,譬如,张謇从1903年到1920年期间,在通海地区先后开办了小学315所,中学若干所,师范学校3所,专科学校6所,大学一所[1]。但是,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建立的新式学校并未在农村发展起来。究其原因是很多的,然而从中国的现代发展历史中不难看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改革是在遭遇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之后被迫进行的自救式改革,这种改革是外铄的而不是内发的,改革的方向是在落后挨打之后急切地向西方学习,按照西方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设计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系。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土社会,孕育于农业社会,这样新旧教育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新教育打破了乡村原有的文化生态模式,在新旧教育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乡村读书人纷纷离去,剩下的普通农民大多没有能力送孩子进入新式学堂,农村的整体文化水平陡然下降。由于兴办新教育的成本比较高,农民由此增加了很多的捐税,原本就穷苦不堪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以上种种原因导致新教育在当时乡村的推行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并不被农民所认可。同时,我国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下,战乱频仍,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列强入侵。政治体系的紊乱导致水利失修,自然灾害频繁,再加上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沉重的战争损耗,致使农村的经济和生产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殖民化的商品浪潮中,分散的小农经济抵抗不了国际市场的冲击,农民纷纷破产,中国的农村以空前的速度被拖向破败的边缘。
二
在这种背景下,一批仁人志士将目光投向了农村,他们怀着“拯救乡村、复兴中国”的梦想,希望通过推行乡村教育来改变整个农村破败的状况。在乡村教育运动中他们甚至开创了多个流派,如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别,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派等等。乡村教育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黄炎培先生指出,乡村教育要急农民之所急,苦农民之所苦,他们认为当时农民之苦是“贫第一,病次之,至于教育乃是有饭吃以后之事,先富之,后教之”,他还强调我们“只须把有利的事实,给人家看,不怕人家不照办”,所以黄炎培在指导徐公桥乡村教育运动时提出的方针是“富政教合一”。晏阳初在《农村运动的使命》一文中提及“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2],在定县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当时的农村存在四大问题,分别是“愚”、“穷”、“弱”、“私”,要复兴民族,振兴国家,“首当建设农村,首当建设农村的人”。他希望通过“平民教育加乡村改造”,实现“除文盲、做新民”的目的。梁漱溟认为导致农村破败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西洋文化之后而导致的农村社会文化的失调,农村社会伦理本位的破坏。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社会是以乡村为本的社会,80%的人口住在乡村,过着乡村生活,农业是中国的主要产业,是中国的国命所寄,它的状况的好坏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从事其他建设的根本前提。而西洋各国都是工业国家,皆以都市为本,他们的文化是一种都市文明。故此,他强调乡村教育应该立足于农村、农业,“重建一新社会组织结构”,“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结构。陶行知在1926年《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疾呼“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完全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繁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有荒田不知开垦,有荒田不知造林……遇了水草水害而不知预防。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像这种教育,大家还高唱着要教育普及,真是痴人说梦。其实这种教育决不能普及,也不应该普及。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3]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具体说就是 “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陶行知在1927年《再论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又指出,“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便成为空洞的教育”。
在此指导思想下,一大批仁人志士在当时的农村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农村教育的改革探索。在黄炎培的领导下,中华职教社在徐公桥实施了“划区施教”的农村职业教育方案,施教者以教育为先导,兼顾该区域的经济、交通、卫生、治安等问题,统筹解决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实验区举办了义务教育、成人教育(教学内容以生产教育为主,重点普及农事教导,训练农业技术)、健康卫生教育、改良农事、养成农民自治能力等事业。晏阳初为了解决农村的“愚”、“穷”、“弱”、“私”四大问题,在定县采取了“四大教育”举措: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包括农民生计训练、合作组织制度、植物生产改进和动物生产改进)攻穷、以卫生教育攻弱、以公民教育攻私,并采用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家庭式教育“三大方式”推行。梁漱溟指导下的邹平乡村教育实际上是以教育为主要手段,重建乡村社会新秩序。他提出新的乡村文化礼俗应是在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邹平乡村教育通过设立村学、乡学、乡农学校来实现“乡约”的补充改造。乡农教育的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此,还包括进行农业改良、倡导农业合作事业、推行农民自卫训练等等,但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儒家伦理道德和“人生态度”的教育和陶冶。乡农教育的教育对象包括一村或一乡中男女老少等众人。陶行知认为“师范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方法”,将改造乡村的重任寄托在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的身上。1927年3月,陶行知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晓庄师范学校是按照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开设的,晓庄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乡村人们儿童所敬爱的导师”,这种导师应该具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健康的体魄、艺术的兴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陶行知挑选了南京北郊崂山脚下的荒坡作为校址,选取田园200亩作为学生耕种土地,有大片的荒山供学生造林,并在附近农村设立几所中心学校和小学,供学生教学实习所用,晓庄师范学校与中小学校的关系为:中心学校是主,晓庄师范是附,晓庄师范根据中心学校的要求设置课程,中心学校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另外,招生时看重农事经验,培养过程中课程设计以乡村生活为中心,实行教学做合一,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打破学校的围墙,开展各种联村活动。非常可惜的是,1930年,晓庄学校遭当局查封,被迫停办,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乡村教育家们在进行乡村教育调试和改革的过程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理念和方法不同,但是在乡村教育的定位上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教育与农业、农村相结合的路子,强调教育内容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农村改造相结合。无论是晏阳初的“民族再造”,还是梁漱溟的“文化再造”,无论是陶行知的“生活再造”,还是黄炎培的“职业改造”,都体现出通过教育改造农村的用意。[4]
但是乡村教育的种种模式最终并没有改变当时农村破败的状况。以定县为例,1931年比1929年借债户数增加了78%,借债次数增加了117%,借债总额增加了133%,1934年借债户达到46000户,占全县总户数的67%。农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1929年前定县的乞丐很少,到1933年冬增至3000人,1933年冬定县吃不起盐的人约占人口总数的20%,1931年因还不起债而被债主没收家产的不过50户左右,1933年达到2000户之多;农民流离:1930年前每年约在700人左右,1934年前3个月就超过了15000人。[5]事实上,各个实验区在乡村建设基本结束交付地方政府的时候,不仅发展农村经济的目标没有实现,仅仅普及学龄儿童教育这一目标也大多没有实现,1935年统计,定县全县6-12岁学龄儿童520000人,失学者占60%,其中男童入学者占65%,失学者占35%,女童入学者占16%,失学者占84%。1935年时仍有10650名失学儿童,其失学儿童人数比在校儿童人数还多606名。在成年农民扫盲教育这一方面,到1934年,73%的青年妇女仍是文盲。[6]上述情况说明,仅完成适龄儿童的教育普及目标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成年农民的教育目标、发展农村经济的目标更成为了镜中花、水中月。定县在所有实验区中实验的时间最长(1926—1937年),投入的资金和人力最多,晏阳初通过海外募捐和众多的留学归国的洋博士下乡解决了定县的经费和师资问题,为定县实验打造了一支豪华战舰,即便这样,定县在交付地方时尚且如此,其他实验区就更不用说了。
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这还得回到乡村教育的起因,乡村教育运动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教育改良拯救破败的农村,这种对教育功能的定位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乡村教育家们在探寻当时农村破败的原因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梁漱溟深感中国农村破败完全是盲目学习西洋文化造成的。晏阳初认为当时中国农村所有的问题是“人的改造”,只要通过教育改变了农村人“愚、穷、弱、私”四大问题,就可以拯救整个农村。黄炎培认为通过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就能拯救破败的农村。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的,导致农村破败的原因是复杂且多方面的。一方面,西方列强向中国大量倾销农产品,对中国实施经济侵略,致使农村生产濒临破产。另一方面,民国成立以后地方政权在管理上的混乱无序和长期的军阀混战而导致的地租剥削、税赋压榨和高利贷剥削,无疑对破败的农村是雪上加霜,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对农村、农业造成的巨大打击,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破败。然而,乡村教育运动家们却片面地将乡村破败归因于农民素质的低下和农村教育的落后。他们指出“中国不必亡,亡不亡全在教育界。教育界可以支配中国,支配前途,改造社会”。这种观点明显是有悖于社会现实的,错在过分夸大了教育的功能。仅仅通过教育改良、提高农民素质是难以解决中国农村破败问题的。教育尽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并不是游离于社会系统之外的,教育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这就决定了教育的功能不是万能的。教育功能只能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许可的范围内才能生效。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功能也不是无限的,它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也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当时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之下所产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也就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自耕农的比例大幅度的减少,土地呈现高度集中的状况。据1931年对江西兴国的调查,不满人口总数6%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80%;占人口总数20%的中农占有土地15%;占人口总数74%的贫农雇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占有土地仅为5%。[7]故此,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没有变革的前提下,希望通过教育变革来解决社会问题,无疑是缘木求鱼。
乡村教育运动的另一个起缘是为了解决工业化、城市化取向的新式教育在当时的农村难以推行的问题,为了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同,乡村教育对新式教育进行了调试,并最终选择了教育与农业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改革尽管预示着中国教育近代化从最初的向西方教育的邯郸学步逐渐转向了走向理性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农村的教育发展道路。但是他们的改革方向更多的是关注如何适应农村、农民的需要,表现出了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教育规律,即教育结构的变革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社会产业结构变革与发展的影响。既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孕育出来的传统文化难以抵挡工业文明的侵蚀,那么变革就不可阻挡。乡村教育的定位就不能仅仅为孕育传统文化的农业、农村服务。况且在他们进行的有限的面向农村、农业的改革方面,也没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各个乡村教育实验区都将教育的方向定位在农村现有物事的改造与发展上,希望通过改进农业生产方式、推广农作新技术、改良农产品品种,推动农业发展。譬如,徐公桥实验区就曾经积极推广新农具、推广的新农具包括大小马力发动机、碾米机、散播机、中耕机等,但是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农村并不具备推行农业机械化的基础,甚至到上世纪6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仍然是基础的耕种的技术。即使有新品种的推行,由于土地分配不均、西方列强通过农产品倾销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下跌,再加上我国仍然是靠天吃饭,根本无法满足新品种所需的成长、灌溉条件。所有这些原因导致农民对改良农业积极性不高,改良农业的成效也极其有限。
从社会大背景看,当时的社会产业结构已经开始转变,民族工业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1840年始,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以后,民族工业蹒跚起步,中国经济开始被动地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行工业化转型。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后,民族工业获得了高速发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譬如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卷烟业、造纸业、电力、机器业、造船业、建筑业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各类工业的发展急需大量的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技术工人,甚至有些行业如机械工业、建筑、造船等还需有较高水平的技术工人。乡村教育要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更好的出路应该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为农业经济培养人才的同时,为工业经济发展服务,这样才能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真正促进农村的发展。并且农村人口的离村已成必然,在人口聚集区的农村已经难以养活当地的农民,土地已经无法承载他们的生存,这一时期,华北地区大量的农民纷纷离开了自己久居的村庄外出谋生,譬如1933年冀鲁豫三省各有100万人以上的农民离村,其中流向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城市为数最多,其次就是东北地区,历史上著名的闯关东即是对这一现象的描述,据史料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华北离村农民奔赴东北者络绎不绝,蔚然成势。尤其在1927年至1929年,内地人口前往东北三省者呈一高潮,每年均达到百万人左右。[8]
诚然,导致乡村教育最终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由于当时政权更迭频仍、战乱不断导致乡村教育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力量的支持、缺少大批能够落地生根的乡村教育家和实干家、缺少经费支持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但其办学方向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乡村教育还是有历史贡献的,成功的地方并不是原来乡村教育家们所设计的教育与农业相结合的方向,它的贡献在于推动了师范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为农村基础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农村基础文化教育的发展。实际上,当时有些仁人志士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任何职业教育都是不可能建立在一个低素质的人口基础之上的,普遍提高适龄人口的基本素质才是农村教育的关键。所以,在乡村教育运动的后期,陶行知就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他认为大面积的普及基础文化教育对国家的建设才是最重要的。抗战期间,陶行知克服种种困难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建立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的学生日后大多都成为了新中国各行各业的建设人才。所以,从整体上来说,20世纪乡村教育的失败是毫无疑问的,它终像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乡村教育家们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对日后的中国基础教育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基础教育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真所谓无意插柳柳成荫。
[1]陈钦.北洋大时代——大师们的理想国[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8.
[2][5][6][7]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38,523,487-488,1.
[3]陶行知全集(第1卷)[A].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85.
[4]周志毅.传统、理想与现实的变奏——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变迁[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2):42.
[8]朱汉国,王印焕.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的离村与社会变动[J].史学月刊,2001(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