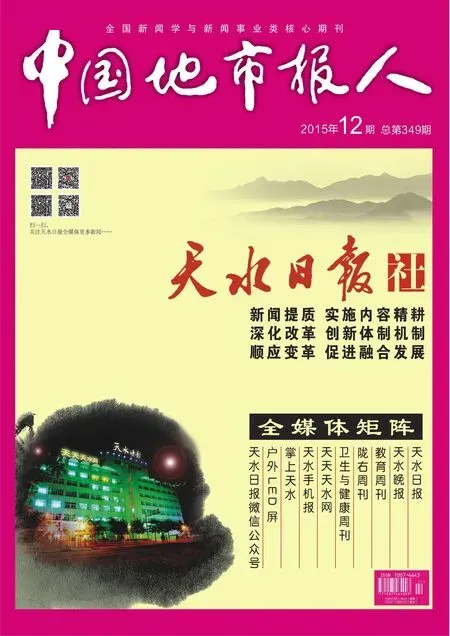感悟与思考
——新闻工作30年随感
2015-01-30马继锋
□马继锋
(赤峰日报社,内蒙古赤峰024000)
感悟与思考
——新闻工作30年随感
□马继锋
(赤峰日报社,内蒙古赤峰024000)
笔者从事新闻工作已整整30年,虽然尚未退休,仍在一线工作,但总结往昔黄金岁月,反思半生职业生涯的念头时时萦绕在心。自己工作的单位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市级报社,不曾经历国家级媒体对历史转折的思考、大是大非的激辩、国内外战争的目击,却也经历和记录了改革开放、思想嬗变、经济振兴、社会变革在一个地区的演变,以及一个普通媒体人的奋斗与追求,困惑与思考,功过与得失。
回顾与梦想
为什么能从事一份职业整整30年却没有转行?很多人经常这样问我。我回答说是因为兴趣和爱好。从小学起,就喜爱和擅长写作文,爱读“闲书”,崇拜作家和记者。上大学专业是哲学,却对枯燥的理论毫无兴趣。大学期间发表了几篇文学作品,在全省曾引起不小的轰动。于是坚定了长久以来立下的志向,将兴趣做职业,毕业后当一名记者或作家。
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市政府当秘书,尚未适应复杂的官场和刻板的公文写作,一年多后我要求去了报社工作。
当时正是崇尚知识的时代,也正是作家、记者、媒体最风光、受尊崇的年代,其优越感、成就感甚至在官员之上。一位如今已是副市长的朋友对我说,自己毕业后想去当记者,报社不要,只好去中专当老师。我说,假如你去了报社,可能不会有今天的社会地位。
有很多事足以证明当年记者、媒体的社会地位。市委书记市长下基层检查工作,记者与领导行同车、食同桌。记者出外采访,领导亲自接待,认真接受采访,一些单位甚至把记者请上主席台。凡开大会,记者不到不开会,尤其是摄像、摄影记者似乎比领导都重要。几乎所有的部门单位领导都以上报纸、上电视为荣,发表后会组织职工阅读、收看。无论到哪,出示记者证,人们会高看一眼,脸上充满羡慕和尊重。
自进入报社以后,我便感受到这里学习氛围浓厚、人际关系融洽、工作环境宽松,每个人的爱好、特长、追求都能得到包容和尊重。在漫长的30年职业生涯里,这种环境一直伴随我从稚嫩走向成熟,尽管有机会却一直不曾“跳槽”离开。这里聚集了全市各类精英人才,包括文学、诗歌、美术、书法、摄影,大家以文为友、以文为业、以文为生,相互学习,相互竞争,佳作频频,人才辈出。既培养出多位自治区有影响的作家、画家、书法家,也先后走出几十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大家以记者自豪,以职业为荣。
我在报社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也尽享报纸改革开放后大繁荣、大发展的所有黄金岁月。小报改大报、铅印变胶印、报纸扩版、彩色印刷、报业集团成立、报业大厦落成使用。我自己成长进步最快、获奖作品最多也正值这个时期。
最先感到新闻行业“寒意”的或许是从记者的“无冕之王”光环渐渐褪去的时候,或许是媒体的真实性离人们渐行渐远的时候。过度的商品化、市场化使一些媒体一度迷失了方向,虚假新闻、有偿新闻、虚假广告使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受到损害。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纸媒报道新闻的速度落后于新媒体,新闻深度日渐式微。伴随新媒体迅速崛起的是传统媒体的日益萎缩,有人感叹:纸媒正成为夕阳产业。
2014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日益显现,地级纸媒广告及其他经营收入遇到前所未有的“寒冬”,全国同行业也境况相似。直接原因看似是经济拖累和新媒体冲击,但此前多年的积弊及媒体人的自我伤害早已为今日的衰落留下了隐患。如形式多样的有偿新闻,舆论监督的弱化,报纸内容的陈旧、呆板,新闻人才的匮乏,传阅率、权威性、公信力日渐下降等。媒体人最直观的感受是:记者及媒体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力明显下降,不仅体现在记者随领导下基层调研被安排与司机同桌吃饭,而且记者进行采访报道屡遭冷落或拒绝。若是批评报道,稿件未写完即被“封杀”。
纸媒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困境,媒体人对造成这种境况的客观原因分析透彻,但对自身原因反思不够,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上。
感悟与思考
和现在比,30年前的记者就像“土八路”。当时,固定电话尚未普及,传真机几乎没有,交通也不发达,记者下乡采访,有时坐长途班车,到偏远村镇,有时骑马、坐驴车,甚至步行,但许多好新闻作品都是靠一双泥腿从基层跑出来的。
当年采访,记者只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现在的记者是“武装到牙齿”,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交通是采访车、私家车、高速公路,活动时间和空间大大缩短,信息传递及时快捷。但是,记者真正沉在基层采访的反而少了,很多素材靠电子邮件、微信、电话等,缺少原汁原味、生动感人的精品和力作。
30年前,办报的条件、设备、手段非常落后,但新闻精品多,每年引发社会反响乃至轰动的作品层出不穷,因为有一支勤勉敬业、业务精湛的新闻队伍。
如今,办报条件、设备、手段堪称现代化。但报纸的内容和质量远不及形式,过去是小报,如今早已改成大报,版面也增加了几倍,但亮点少,精品少,轰动一时的作品更是一年鲜有,新闻队伍空前庞大,但人才严重不足。报纸的发行量大了,但传阅率大不如前,影响力也日渐式微。
30年里,办报最难的不是技术改造、机构改革、经营创收,而是舆论监督。哪一任总编辑都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以此增加报纸的公信力、可读性,但都未能如愿。原因只有一个,上级领导不喜欢舆论监督,或只是表现在口头上、讲话中而已。
如今,报纸最难的已不再是舆论监督,是找亮点、报成绩,由于经济不断下行,各行各业交出的业绩不够亮丽,寻找新的“成绩显著”、“实现新跨越”类素材让记者大伤脑筋,最佳办法是同一新闻分不同角度、侧面、形式轮番重复报道。
30年今昔对比,与新闻业由上升转为下行相吻合的是,人才队伍明显萎缩。正因为当年新闻业的无限荣耀,报社聚集了大批对新闻有理想、有追求、有成果的人才,如今这批人或升迁、或调离、或退休,而新人又大都是经过考公务员、热门机关单位筛选后考录的,许多不是因为爱好和兴趣,而是因为所学专业或需要一份职业。他们学历高,智商高,但专业热情和能力亟待提高。前两年,报社拿出几个免试指标去名校招录研究生,竟然无人报名。
因为临近退休之年,所以笔者总在想:30年我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有多少作品到如今仍有价值或传于后人?30年,我写过的消息、评论、通讯、报告文学、散文难以计数,自以为有价值的尚留有少量报纸,其余的成了废纸。时政消息、社论,时效性最强,生命力最短,因为大多是领导调研、会议等。往往是,同一项工作,领导第二年讲话,或更换了新的领导,内容大相径庭。这一年生态立市,过些年又工业立市。每一任领导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思路。至于刚报道过的领导一夜间变成了腐败分子,同级媒体总是保持沉默,曝光是上级媒体的任务。
由于从上世纪90年代起承担过多年政法报道,写过的侦破通讯、报告文学至今仍有可读性。原因不仅是这些案例情节惊险曲折,而是案例的真实性,很少有记者的粉饰和加工,因而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最具保存价值、也是最能体现成就感的是人物报道。不论是消息、通讯还是报告文学,凡是写各条战线有血有肉、倾注真情实感写出的人物,都会在读者中留下深刻而长久的印象,尤其是他们的大部分在媒体长期关注、宣传下,都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突出业绩,并逐渐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始终与记者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作为一名记者,写批评报道既能体现勇气和责任感,也能考量眼力和笔力的功底。在几十年能够保存下来的作品中,一些批评报道能够引起领导和读者关注,并最终促使问题得到处理或解决,心中的成就感远远超过省级新闻奖。
当年,很多人选择当记者的初衷是推动社会进步、揭露社会丑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新闻理想、个人价值。时至今日,除了职称、职务晋升、作品获奖,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梦想与现实到底有多大距离?怎样唤起记者的职业荣耀感?对这些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
2015年初,我收到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纪念章,不是表彰我作品获奖,而是为新闻事业工作了30年。不敢与官居高位的同学比,就是与同属专业技术系列的医生、律师、建筑设计师、金融业的同学比,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也相差巨大。很多年前,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事业成功,事业中既包含职务升迁,也包括经商致富,还包括其他事业。后来,成功的标准分为两个:要么做官,要么发财,其他成功属于精神层面。
整整30年,从最初的理想一路走来,途中有过诱惑、有过迷茫、有过懈怠……但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毕竟,我亲身经历了新闻业最美好的年代。
(本栏编辑:高秉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