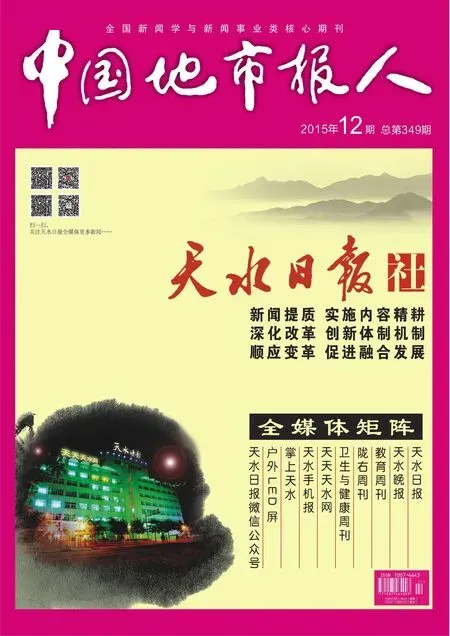在“走转改”中感受和留住乡愁——关于地市媒体在“乡愁报道”中的责任与优势
2015-01-30邱隆洪徐贤礼
□邱隆洪 徐贤礼
(京江晚报,江苏 镇江 212001)
央视播放的纪录片《记住乡愁》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得益于电视这种记录的形式,我们得以在家里“走进”一个又一个远离我们的小村庄——这些微小的角落即使是在当地,也几乎处于被遗忘的边缘了。
“我们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使世界像会飞的魔毯似的重放出来。”①这句话原本被麦克卢汉用来形容电影,不过,用在如今的电视上同样合适——纪录片更是一个真实世界的记录。但是,仅仅是记录,与观众的乡愁无关。
对于笔者这些异地的观众,《记住乡愁》里记录的家乡是他乡。他乡之愁不属于自己。这部纪录片给笔者的启示有两个:一是既然乡愁有地域和经历的限制、一地之人有一地的乡愁,那么别人的乡村只能激起好奇心,而不是乡愁的认同;二是在留住乡愁方面,当地媒体有天然的优势和责任。
留住乡愁,少不了感知地方风物
需要说明的是,乡愁是需要认同的。一个北方人其实难以理解一个南方人的生活习俗,即使在一省之内的居民,共同点当然有很多,但也有差距,有些差距甚至是巨大的。当然,如果乡愁是共同一致的也就没有魅力,也不存在“留住”的问题。可以说,乡愁源于差异。
从新闻得知,纪录片《记住乡愁》曾经向全球征集主题歌歌词。从入围的作品来看,四合院、小石桥、白沙鸥、塞北雪……这些歌词中的内容所能代表的,往往也是作者自己的乡愁。尽管思想的感情相似,但化为具体的形象却有区别。
而想要激起乡愁让人认同,少不了需要感知地方风物。一个人的乡愁,只有在看到属于他自己的“小石桥、白沙鸥”时,才能激发出来。
从这种差异性来说,当一个观众面对一集以乡愁为主题的纪录片,是获得认同感还是仅仅如麦克卢汉所说的是获得“魔力四溢的消费品即梦幻”②,关键在于其本人与纪录片所记录的村庄的距离——越远越偏向于后者。而我们更希望获得的结果是前者。
留住乡愁,地市媒体有责任也有优势
很显然,追求更多的认同和记录真实的乡愁之间是存在一定矛盾的。
就媒体这个表达者本身来说,想要完全地诠释每一类、每一个地域的人的乡愁而不流于浮光掠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表达者有自己的乡愁,其最擅长表达的也只有这一种。
既然表达者(这往往是一群媒体从业者组成的集体,他们大多来自同一地域。当然,城市越大从业者的来源越复杂,而在地市级媒体当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往往只擅长于表达一种乡愁,那么,地市级或者县级媒体就是留住当地乡愁的最佳选择。
在笔者从业的媒体,采编人员来自本地的占80%以上,如果不是近年来自外地的从业者增加,这个比例可能更高。这些从业者在激起受众的乡愁方面具有亲缘优势和地缘优势:家在农村或亲戚在农村,离农村、离基层更近。其实,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人都有自己的故乡记忆。
受众的优势则是另一方面。地市级媒体以当地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他们本就是这些人群当中的一员。在信息的传播上,他们可以做到更精确的传播。可以说,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优势,地市媒体也有责任承担这样的任务。人已老去而乡愁无处寄托——如今的社会变化发展之快,是所有人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甚至是从前无法想象到的。当记忆中的“小石桥、白沙鸥”不再,乡愁也就无处寄托。
如上文所述,地方媒体了解乡愁寄托在何处,因此也清楚如何留住这些乡愁的寄托之所。对于地市级媒体的从业者,作为目标的“小石桥、白沙鸥”是了然于胸的。那么,用好这种优势,在最短的时间、用最高的效率作出能留住乡愁的努力,也就成了地市媒体及其从业者不容推辞的责任。
换个角度来说,受众也乐于见到媒体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在传统媒体遇到发展的压力的背景下,写下自己的乡愁也是每一个地市级媒体在内容上做出特色的途径之一。在纸上读出乡愁,对于读者来说,这样的亲切感是不需要多加说明的——在信息传播日益快速的背景下,媒体内容的雷同是很容易出现的,要想区别的话,这是一个好的角度。
所以,从自身发展的角度,地市级媒体有责任留住乡愁。这是为读者,为社会,也是为自身。
留住乡愁,离不开“走转改”实践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③
“村庄原始风貌”正是乡愁的产生和寄托之处。可以说,乡愁在乡间、在基层。乡间、基层也正是媒体人和他们的乡愁的来处。要寻找和留住乡愁,自然要“往来处去”。
2011年初,笔者采写了稿件《记忆中的麻油香回来了》,关注的是一个老品牌的辉煌、合资、消失、回归历程。和那些树、湖、房一样,一个老品牌也能是乡愁的寄托。
完成了这篇稿件的采写之后,笔者得到一个认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寄托。如果不是距离很近,这样的差异对媒体人来说也是很难把握的。作为一个1984年注册的品牌,甘露麻油的记忆是属于一个特定年龄段的人群的。这篇稿件唤醒的也正是这一群人的记忆。如上文所述,这群人大多生活在本地。稿件刊发之后,共鸣最多的也是这一人群。一些读者反映说,当这一个品牌重回市场,沉睡的记忆被唤醒,亲切感自然而然地出现。“这是我们当地人自己的品牌。”一位老年读者称,这样的感情“外人”理解不了。
这篇稿件的产生恰好是一次“往基层去”的发掘过程。线索是笔者在走访当地企业的过程当中发现的。当时,这个商标新的持有人刚刚找到了新厂房,默默挣扎多年后成为江苏省著名商标——相比之前的荣誉,这只能算是新的出发点,也是需要媒体关注的时候。
可以说,留住乡愁,离不开“走转改”实践。如上文所说,乡愁来自基层,要抓住真正的乡愁寄托也需要回到基层。
可以一说的是,笔者工作的《京江晚报》近年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寻找那些“乡愁的寄托”。我们关注传统手工制作的月饼、关注城市里为数不多和新发现的古井、关注一条路上的老梧桐树的去留、关注民间传说……这些都寄托着一群人的乡愁。■
注释:
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7第一版324页
②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7第一版331页
③《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2013.12.14,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