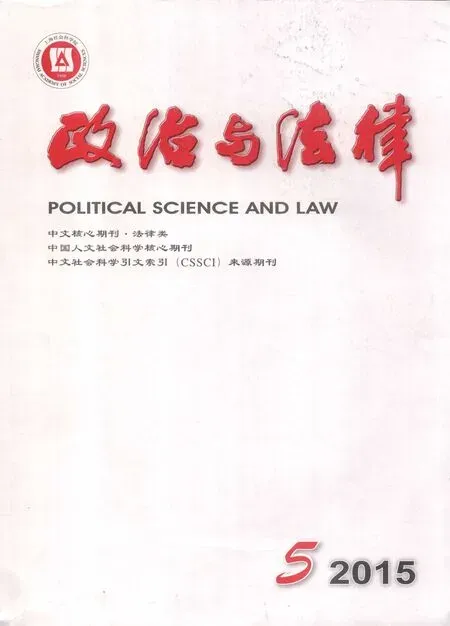地方法治建设评价体系实证分析*——以余杭、昆明两地为例
2015-01-30易卫中
易卫中
(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南京215800)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提出后,各地的依法治省(市)工作也相继展开。与此同时,法治建设评价从以前依附于目标责任制下的单项绩效考核步入全方位的地方实践阶段。2007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正式公布了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之后,地方法治建设的评价活动跨入了新的阶段,各地法治建设评价实践的探索如火如荼。2011年,第一个省会城市法治指数——“昆明法治指数”也正式对外公布。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这意味着将更加重视法治建设评价的研究,地方法治建设评价实践活动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笔者选择我国内地正式对外发布过法治指数的余杭、昆明两地进行考察,其代表性强,也可比较客观地分析当前法治地方指标体系实际运行中出现的各种情况,为今后的地方法治评价建设研究及实践活动提供借鉴。
一、余杭、昆明法治指数出台的背景
余杭法治指数是我国内地第一个地方法治指数。2005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区政府提出了建设法治城区的目标,随后明确了“法治余杭”建设的具体要求,并依据这些目标要求,余杭区成立了专门的区法治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法治余杭评估体系的建设。同时,该区聘请了专门的法律专家参与其中的具体工作。经专家论证过的《“法治余杭”量化评估体系》在2007年出台,同年发表了首个余杭法治指数,分值为71.6,成为我国内地第一个正式对外发布的地方法治指数。
昆明法治指数是内地第一个正式公布的市级(省会城市)法治指数。昆明市以《中共昆明市委关于推进依法治市建设法治昆明的实施意见》、《建设法治昆明工作规划(2009-2014)》为具体指导思想,组建了专门的昆明市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并聘请了由“专家+职能部门法治建设骨干”组成的21人课题组,具体从事法治昆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工作。2010年9月,“昆明市发布了《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随后聘请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团队具体负责实施了首次法治评测工作,并于2011年正式发布首个昆明法治指数,分值为72.96”,①《昆明市首次发布“昆明法治指数”:得分72.96》,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04/25/c_123034624.htm,2013年11月19日访问。成为内地首个正式对外发布法治指数的城市(省会城市)。
二、余杭与昆明两地法治评价体系的比较
(一)余杭、昆明两地法治评价体系的相同性
余杭、昆明是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对外发布法治指数的两个地区,虽然两者地理位置以及行政级别存在差异,但是法治评价体系却存在一些共同之处。
1.法治评估主要目标相同
无论是《法治余杭的量化评估体系》,还是《法治昆明综合评价体系》,其测评的结果都是向社会发布的本地区具体的法治指数。当然,“法治指数本身并非单纯的一个数字,而是蕴含了一种社会法治发展的理念、一个动态体系的系统性工程。因此,法治地方建设评估体系首先需要确定评价的目标”。②付子堂:《地方法治建设评估机制的全面探索》,《法制日报》2012年8月8日。余杭、昆明两地的法治评估的主要目标都是建立一套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法治评价体系,并以此为标准客观评估当地法治发展状况与成效,从而促使各部门更好地依法规范和约束当地各项公权力,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从而达到提升当地法治化水平的最终目标。
2.法治评估指标设计上的一致性
从设计的程序来看,两地区的指标体系从设计到正式提出都经历了长达几年的时间。无论是我国余杭地区的法治指数设计,还是昆明市法治指数的设计,都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经过调研、讨论(包括引入专家的讨论)、民意调查、反复论证等程序,才提出的科学体系,贯彻了全面、真实、客观的实际要求。两地的法治指标体系在指标的设计上体现了中国特色,如对依法执政、民主政治、法制宣传教育等问题都有所反映和揭示。两地法治指标体系的设计突出了引导性,两地法治指数除了反映一个时间段内法治运行情况外,更侧重于通过客观、科学的测量和评价规范法治行为活动,整体提高法治化水平。
3.法治评估计算方法上具有一致性
昆明和余杭法治指数计算上都运用了加权平均法,“即先计算出每位评估主体对每个指标的评价分值,这一分值等于该指标权重得分与指标等级得分的乘积。然后,运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每位评估主体对所有评估指标评价的总和,即为该专家对评估区域法治总体水平的量化评价。基于每位专家的法治水平评价,在去掉最高分与最低分的基础上合计出最终的法治指数”。③钱弘道:《余杭法治指数的实验》,《中国司法》2008年第9 期。
4.法治评估都注重公众对法治的主观感受
杭州市余杭区、昆明市所研究设计的法治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均包含对人民的满意度调查,考察与了解公众对法治建设状况的评价与主观观感。例如,在昆明的法治综合评价体系中专门列出了“公众评价性指标和公众体验性指标”等考察公众主观感受的二级指标,这一侧重点使得法治地方建设评估可以尽可能地反映民众的需求。通过对公众主观观感的评估,以评价当地的法治指数,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世界各国注重人权保障的大趋势使然,它的好处在于有利于对人的自身价值的深层次关注,促进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增强公众的幸福感;也有利于政府知晓法治的各项制度是否真正为民所设、制度的效果是否为民所认可,由此了解民众的实际法治需求,并可作为今后法治改革的依据。
5.法治评价指标体系的运行都是政府主导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发展得益于党和政府的主导、推动,即党和政府主导下的法治演进模式。法治地方建设评估体系的构建,同样离不开党的大力推动和倡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上述余杭、昆明等地法治评价的运行模式,也遵循这种自上而下的法治发展模式。虽然两地的法治评估植入了较多的民意因素,吸收了普通民众的意见,其中昆明市的首次法治评测工作还是以整体委托给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团队具体负责的形式来实施的,但是两地的法治评估均由当地党委政府组织发起,并委托有关学术机构具体承担,学术机构在具体的评估活动中体现了明显的服务于政府的政策导向,独立性受限。可以说,地方党委政府是法治地方建设评估体系运行的主要推动力。
它们的具体做法是,地方党委政府依照中央精神先成立法治建设领导办公室,通过法治建设规划纲要,然后,在法治建设领导小组或办公室的领导下,开始地方法治建设的评价体系的评估工作。如昆明市在《法治昆明综合评价体系》出台之前,先由中共昆明市委法治昆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起草了《关于推进依法治市建设法治昆明工作规划(2009-2014)》,随后在市委法治昆明建设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始法治昆明综合评估体系的工作。“余杭的指标体系则是完全根据2006年《中共余杭区委关于建设法治余杭的意见》中所提出的9 个总体目标而设置的。因此,法治地方建设评估指数体系的设计更多的是政府主导,大多属于一种‘自我评估’。同时,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评估能否顺利进行,既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也有赖于政府各部门的支持和配合。”④朱未易:《地方法治建设绩效测评体系构建的实践性探索——以余杭、成都和香港等地区法治建设为例的分析》,《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 期。
(二)余杭、昆明两地法治评价体系的差异性
1.法治评估指标体系不统一
通过对余杭、昆明两地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考察可知,“余杭侧重量化分析技术,同时不忽略定性研究方法,体现了主观判断与客观数据的结合。在客观数据的获取上,余杭的数据信息除了政府依法行政等方面的数据外,还包括了党委依法执政的数据”,⑤参见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 期。而昆明的则侧重于定量分析,定性的分析较少,如“二级指标下社会安全细分五个三级指标,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万人交通事故死亡数;万人拥有警察数;年一审公诉案件数;亿元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⑥参见:《法治昆明综合评价体系首次测评指标及方法》,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4/24/14105538_0.shtml,2014年3月8日访问。这些全部是可以被量化的。尽管法治具有区域性的特点,立足于区域的具体情况设计的评估指标体系更有利于考察本区域的法治建设状况,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出台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存在指标体系不统一的问题,尤其是在细微的考核指标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法治评估标准的不统一弱化了法治量化评估的横向对比功能,不利于全国法治建设的统一协调发展。各地区仅可在时间维度进行纵向对比,考察本地区的法治建设的现状以及发展情况。此外,法治评估指标体系不统一、考察的侧重点不统一,各地所得出的法治指数则不可在同一层面上考察,也就无法起到激励与鞭策的作用。”⑦谷小娟:《法治建设量化评估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1年度硕士论文,第35 页。
2.具体指标选择的侧重点及指标权重有所不同
余杭和昆明法治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的选择上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共性之外,其具体的指标设计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如《法治昆明综合评价体系》的具体指标包括规范立法,并突出了公众评价指标和公众体验性指标。而余杭法治指数就没有设计此类指标,因为余杭区作为杭州市下属的一个区,其没有地方立法权,所以法治余杭指标体系上没有关于立法的评价指标。对于公众评价性指标和公众体验性指标没有像昆明指标体系那样单独列出,而是分散在其他的指标之下,作为具体的评价标准表达出来。
此外,余杭区的法治指数结合自身的特点,将民主政治完善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在“健全监督体制,提高监督效能”具体指标上提到了“加强人民政协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监督;完善举报网络,健全举报制度,加强信访工作,进一步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切实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加强舆论监督;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为监督的重点对象,坚决查处各种违纪违法案件,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⑧资料来源于余杭法制网,http://www.yhfz.cn/newsshow.aspx?artid=2711,2009年2月6日访问。而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在提到法律监督时,具体指标设计上也只有“人大监督和司法监督”。这说明,余杭、昆明两地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指标选择上存在不同。可以说,不同地区的法治指数关注的法治侧重点不同,直接导致了在具体指标选择上存在一些差异。
值得注意的还有,同样的指标在不同的法治指标体系中具有不同的权重。昆明法治指数、余杭指数根据对当地法治化进程影响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有些相同的指标,在两地的指标体系中具有不同的权重。
3.评估方法存在差异
“余杭的法治指数通过纵横交错的评估方法得出余杭总体的法治指数,即从高到低纵向深化和横向展开对各政府机关部门逐个评估方法,使评估体系既能得出反映余杭整体法治状况的总指标,又能对政府各具体部门的绩效具体考核,还能具体落实到乡以下的基层政权机关的量化考核。”⑨同前注③,钱弘道文昆明的法治指数是采用综合评价方法,“是对昆明法治状态的一种整体性描述,没有再细分到政府的具体部门。具体评价方法上,由3 个评估组别(内部组、外部组和专家组)分别进行独立评价打分,最后加权计算获得平均值。对‘公众评价性指标’——‘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指数’则直接引用全国性评价数据;‘公众体验性指标’——社会安全感指数、对昆明法治环境的满意指数的独立的问卷调查——委托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完成”。⑩同前注⑥。
三、余杭、昆明两地法治建设评估体系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知,两地在法治建设评估体系建设中,都认识到法治指标体系可以检验一段时期内,法治变化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影响,在指标体系的设计过程中也开始注意指标体系横向上的可比性,注重地方特色;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重视专家的作用以及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这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较明显的作用,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之处。
(一)地方法治评价理论研究滞后导致地方法治指标体系设计不够准确
在世界法治量化的浪潮冲击之下,我国各地踊跃进行法治量化的实践,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却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直接影响到法治指标体系设计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文化传统上的独特环境,法治量化的诸多问题未能从理论上予以厘清,对法治地方建设评价的目标、价值取向、评价主体、评价对象等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较为零碎的状态。理论研究的滞后,使法治指标体系的设计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法治指数和法治建设评估指标体系不作区分。“法治指数是对既有法治状况的量化,其作为一个精准的实证调研数据,应该是在一个法治基本比较完善而且法治正常运转的语境下,对于法治可能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偏差进行‘数据纠偏’。而事实上,我国整体上还处在一个非法治国的时代,‘非法治事件’到处可见,地方的‘法治指数’更像是一件华而不实的盛装。”⑪参见《“法治指数”无法衡量所有现状》,http://www.legaldaily.com.cn/shyf/content/2008-04/08/content_829142.htm,2014年3月7日访问。相反,“法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则是在法治不健全不完善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量化的数字评价来促进法治的建设,可以通过一国局部地方的层层推进,从而最终实现国家的法治。此外,考虑到法治的统一性,‘地方法治’概念本身就具有争议。”⑫屈茂辉、匡凯:《社会指标运动中法治评价的演进》,《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3 期。因此,我国目前各地所提出的法治指数,应该定位为法治建设评价体系较为妥当。
第二,法治地方建设评价指数与法治政府评价指数不作区分。法治政府评价是对政府是否依法行政方面的评价,是法治地方建设评价的一个方面,但是有些地方将法治政府评价体系等同于法治地方建设评价体系。法治的核心无疑是依法行政,但不等同于依法行政。遗憾的是,在理论上,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未能很好地将两者区分开来。如钱弘道教授等撰写的《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就混合运用了这两种评估体系,其在文中提到的深圳市的法治指标体系,其实就是《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⑬同前注⑤,参见钱弘道等文。
在法治评估实践上,则表现为注重依法行政的考察。与国外的法治指数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法治指数相比较而言,我国大陆各地区进行的法治量化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或法治指数研究注重对政府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构建进行重点评估。如在余杭法治指数中包含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的指标,依据余杭区2007-2111年法治指数,该项指标的权重得分在9 项一级指标中居于前三位。无论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普通民众均认为该项指标在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昆明市发布的《法治昆明综合评价体系》中二级指标“依法行政”权重得分为23 分,在所有的二级指标中居于第一位。
政府的行政执法活动容易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较大程度的直接影响,这就使得行政行为依法行使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法治地方建设评估侧重“依法行政”说明地方党委政府认识到法治政府的构建、政府依法行政对于整个社会法治运行的重要性,也表明地方法治建设过程中对政府依法行政提出较高的要求。然而,这种过分注重依法行政的指标设计,容易导致将法治等同于依法行政,将地方法治评价混同于地方法治政府评估,这不利于法治建设的发展。同时,一些反映民生、环境保护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的指标则付诸阙如。
(二)指标体系内容和结构上存在缺陷
第一,将不属于法治内容的指标也纳入评估。如在余杭、昆明两地都将民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传统上不属于法治或者与法治并立的内容作为评估的重要指标。例如,余杭法治指数第一项内容就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包括了“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积极开展文明城市(城区)创建,以开展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活动为载体,不断完善以村、社区民主选举制度、村务工作规则,深化村(居)务公开;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加强各种所有制企业工会组织建设,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⑭资料来源于余杭法制网,http://www.yhfz.cn/newsshow.aspx?artid=2711,2009年2月6日访问。昆明市的法治综合评估体系也有专门的二级指标“民主政治”,在此下面包括“民众参与选举成效;政治协商成效;基层民主建设水平”三个三级指标。⑮同前注⑥。
第二,有些法治地方指标没有考虑到地方的实际情况,如有的地方立法没有地方立法权限,也将地方立法列入考核的指标体系之中,设置这样的指标因没有考核对象而形同虚设。
第三,与国外法治指数比较,有些公认的重要指标缺位。“与国际上比较公认的世界法治指数相比较,我们法治地方建设指标缺少了有限权力指标、腐败遏制指标以及基本权利指标。”⑯参见张宝生、郑飞:《世界法治指数对中国法治评估的借鉴意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6 期。这些指标在余杭、昆明的法治评价体系同样缺位。
(三)法治评估主体单一、缺少中立性
法律至上,政府的权力、责任受到法律约束与规制,这是法治社会的真谛。要达到此目的,仅有表面的形式是不够的。政府在行使其职能过程中是否依法办事、政府为公众服务的效率直接关系到人们权益的保障水平,法治评估指数正是社会实践中法律对政府权力和责任监督力度的形象反映。因此,在法治建设评估指标体系中,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及政府依法办事的能力的考核就成了首要的目标。为达到此目标,法治评估量化应该由独立的第三方组织或单位作为评估机构,而由政府以“自我评估”方式进行的话,政府就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之嫌。
上文提到,我国法治地方评估体系实行的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即由党和政府主导,服从其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法治意识、民主参与、社会冲突等方面,我国市民社会还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通过各地方党委和政府组织布署、积极推进的自上而下的法治发展模式也比较符合我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这样的运行模式,虽然在理念上仍然摆脱不了工作分解和工作布置的思维框架,但是毕竟已经在尝试着用一种标准和尺度来衡量地方法治建设工作的推动状况以及地方部门法治建设的进步程度。从发展观的视角看,从过去地方法治建设推动的单向性工作思路,到法治地方建设的主观评价体系的构建,的确是一种进步和提升”。⑰同前注④,朱未易文。
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这种模式下存在的隐忧。正如有学者指出:“政府主导下的法治地方建设评估,法治指数容易成为各级政府‘秀政绩’的新的战场,尤其是法治指数的设计掌握在政府自己手中的时候,法治指数能否真的实现表象与实质的统一就变得更为让人怀疑。法治指数的设计和推进是为了推进法治建设的发展与完善,并且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和途径。如果将法治指数视为评估和衡量法治建设好坏的唯一标准并上升为政府绩效的考核指标,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全国性的法治运动‘大跃进’,那么最终留给社会的只是法治的表象,而丢失了法治的实质。”⑱侯学宾、姚建宗:《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法律科学》2013年第5 期。
余杭、昆明两地的法治指数评估工作组虽然吸纳了专家学者的参与,但是专家组是由政府自己聘请,政府提供经费,很难想象专家组能够违背政府意志设计法治指标,即使专家组能坚持己见,政府是否采纳、认同也是存在较大疑问的。此外,政府主导评估工作的官方性与主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基于数据搜集、分析者的个人偏好不同所致,定量分析中‘玩弄数据’的空间本来就不可避免,在我国政府主导下的法治建设评估中这种情况同样不可避免,甚至会更加明显。”⑲同前注⑱,侯学宾、姚建宗文。公众对评价结果的公正性与可信度的怀疑就在情理之中。评估结果既缺乏公信力,也很难反映地方的真实法治水平。因此,注重评估主体中立性的建构,将是今后我国法治建设评估工作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四、对地方法治建设评价体系的反思
毋庸置疑,地方法治指标体系的设计作为量化法治的实践工具,其重要性正在被不断的提升。为了避免现有法治评价指标体系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今后的地方法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建构过程中应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应明确地方法治建设评价指标的设计目标。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应抛弃以往重形式较少关注实际的做法,在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方案的顶层设计时,就必须要明确地方法治建设评估的目标,并依照此目标来指导具体指标的设计。例如,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要体现法律价值的目标。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就要考虑如何把与法治息息相关的价值,例如“公正”、“正当”、“应当”、“良善”等,通过一系列的指标体系予以体现,并通过有效的计算加以直观的界定。当然,在具体设计的指标数值中,要注意防止不合理的量化指标走向设计目标的反面。有学者甚至指出“法治指标追求实效性,容易造成唯指标主义和追求‘工程进度’的法治功利主义”。⑳尹奎杰:《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能”与“不能”——对法治概念和地方法治评估体系的理论反思》,《长白学刊》2014年第2 期。例如我国推行的法院结案率指标,在实践中却被法院异化为限制立案的理由,各地法院为提高结案率,每年都会集中一段时间不受理新案件,甚至对已受理的案件,在审限到来之时,要当事人撤诉后,再去重新起诉。这种不符合法治建设目标的指标设计既达不到确保司法权依法运行的作用,也不能很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相反通过人为的方式轻易地实现而成为扰民的指标。
第二,内容上要协调好法治的基本目标与法治的地方特色的关系。“约束公权、保障私权”始终是法治的精髓。法治的基本目标在于控权与维权,既使国家的权力得到制约,又能有效维护社会公民权利。因此,建立地方法治指标体系在内容上要包含能体现上述精髓的具体指标。同时,为了促进法治在地方的推进和实现,地方法治指标体系的具体设计中要体现法治的地方特色,应该注意与地方经济发展、地域文化风俗习惯的衔接,吸收地方法治建设中有益的成分。因此,在法治地方建设评价体系设计过程中,指标的设计、指标的量化和细化、指标权重的设置、数据的搜集方法等都要注意协调好两者的关系,而不能相互否定彼此。
第三,强化地方法治评估主体的中立性。目前,地方法治评价体系都是采用政府主导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虽然也吸收了政府之外的专家参与评估,但是其组织与经费都来源于政府,专家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因此,专家组的中立程度是不够的。因此,为了提高地方法治评估结果的可信度,这一问题应在今后的地方法治建设评估体系中优先解决,逐步从政府主导型的地方法治建设评估模式过渡到社会推进型的法治建设评估模式,评估过程中吸收不同主体参与评估,提升地方法治评估主体的中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