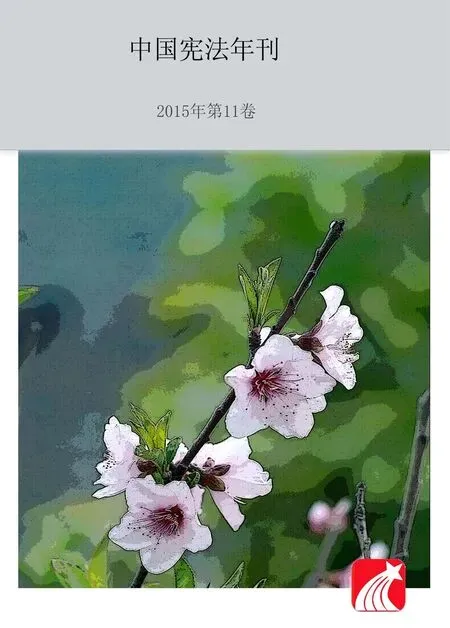互联网条件下对我国《宪法》第35条的解释
2015-01-30陈道英
陈道英
互联网条件下对我国《宪法》第35条的解释
陈道英∗
我国《宪法》第35条(以下简称第35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但是第35条的表述非常简单,只是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而并未对言论自由能否进行限制,如果能够限制其界限何在等问题作出任何规定。具体来说,如果要将第35条予以适用,那么释宪者①尽管我国宪法将宪法解释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但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非我国唯一的宪法解释主体,法院的合宪性解释也是属于宪法解释的,而法院的合宪性解释并未为宪法所排除。因此在谈及我国的宪法解释主体时,笔者使用的是“释宪者”这一术语。在本文语境下,“释宪者”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法院。关于法院的合宪性解释构成宪法解释以及法院的宪法解释权并未为宪法所排除的观点,参见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至少应明确如下3个问题:(1)第35条所说的“言论”指的是什么?(2)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在哪里?(3)第35条的效力范围,也就是第35条的法律效力是仅及于公民—国家之间,还是同时及于公民—公民之间?尽管传统的言论自由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但是一旦将第35条适用于互联网的语境下,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也将发生变化。因为互联网所带来的绝不仅仅只是技术上的革新,它实际上是造就了一个与传统空间截然不同的“高维度空间”,②喻国明:“基于互联网逻辑的媒体发展趋势”,载《人民日报》2015年4月19日。因此,在互联网条件下对第35条进行解释时就不能直接套用传统的理论,而必须寻找独立的、适应于互联网架构的理论。
从我国的宪法解释实践来看,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对第35条作出过正式的宪法解释,因此,第35条的解释主要体现在各级法院判决的言论自由案件中。而在互联网领域,我国法院审理过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言论自由案件主要包括:“金山安全公司诉周鸿祎微博言论名誉侵权案”(以下简称周鸿祎案)、①“微博第一案二审判决生效 微博言论有了法律尺子”,资料来源http://www.zhtv.com/tech/201109/ 120401.htm l。关于这一案件的分析,参见陈道英:“微博言论自由之法律规制——从‘微博第一案’谈开去”,载谢佑平主编:《司法评论》(第4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余丽诉新浪公司案”(以下简称余丽案)②杜强强:“论民法任意性规范的合宪性解释——以余丽诉新浪公司案为切入点”,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以及“方是民与崔永元名誉权纠纷案”(以下简称方是民案)等。由于在方是民案中法院对网络言论自由做出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并且上述几个案件在主要精神和原则上不存在本质区别,故而本文将主要以“方是民”案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资料来源 http://weibo.com/3927469685/Co9ygCr87?type=comment#-rnd1435721228773。为分析材料来展开论述。而从方是民案的判决书来看,法院在网络条件下对第35条的解释上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1)强调网络言论自由对推动民主的特殊价值,由此认为对于涉及公共议题的言论应给予特殊保护;(2)在确定言论自由的边界时,强调应持谨慎、宽容的态度,并倾向于适用利益衡量的方法,但对于如何进行利益衡量尚未能提出具体的方法;(3)认为第35条在私人间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
上文曾提出,互联网条件下解释第35条主要需要解决3个问题:(1)什么是“言论”;(2)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3)第35条的效力范围。然而方是民案判决书仅涉及后两个问题,并且与周鸿祎案一样,花费了较大篇幅来论述言论自由的意义和价值。乍看上去似乎宪法解释实践与理论分析无法互相对应,然而仔细分析即可发现:(1)法院之所以会花费较大篇幅论述言论自由的意义和价值,是因为它对于确定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2)对第35条的“言论”一词含义以及言论自由法律界限的回答实际上同属对第35条的解释基准④“宪法解释基准”是由东南大学汪进元教授提出来的,笔者在这里借用了这个概念。本文所说的解释基准指的是对释宪者解释宪法的具体行为发生指导作用的准则和规则。它比原则和精神更为具体,能够直接对宪法解释活动予以指导。的内容。两厢结合,可以得出结论,在互联网条件下解释第35条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1)互联网条件下对第35条进行解释的原则(价值);(2)互联网条件下对第35条的解释基准;(3)互联网条件下第35条的效力范围。本文就将依此展开论述。
一、解释原则:保障民主文化
所谓宪法解释的原则,就是贯穿于宪法解释活动的始终,指导并督促其科学、合理运作的基本准则或原理。⑤章志远:“略论宪法解释的基本原则”,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1期。尽管对于宪法解释原则的具体内容存在各种争议,但是宪法解释原则最基本的意义是在于防止宪法解释权的滥用,其功能在于对释宪者提供一种立场和价值判断上的宏观约束与指引并使之能达成共识。因此,具体的宪法条款的解释除了应遵从符合宪法基本原则、不背离宪法规范的字面含义、以保障人性尊严为其终极价值追求等一般性解释原则外,还可能需要以遵循特定的价值拘束,将其作为自己的解释原则。具体到对第35条的解释,这种具体的价值拘束通常被认为是促进民主政治。这一观点,笔者称其为民主政治论。
民主政治论最早是由美国的米克尔约翰提出的。他认为言论自由实际上所保障的是人们参与自治(self-government)的权利,①Meiklejohn,“The First Amendment Is an Absolute”,1961Sup.Ct.Rev.245,pp.255-257.因此言论自由保护的是“每一个公民都要参与公共讨论”。②[美]米克尔约翰著:《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自此之后,对“公共讨论”和民主政治的强调构成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讨论的主旋律。例如,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布伦南大法官在论证不实陈述仍有可能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时作为核心观点加以强调的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在于保护公民对公共事务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 (uninhibited,robust,and w ide-open)的辩论。③New York Times v.Sullivan,376 U.S.254,270(1964).而即使是作为米克尔约翰观点修正者的费斯和波斯特,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颠覆了米克尔约翰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上的理论设定,其最终的落脚点也仍然在于促进公共辩论的品质,④[美]欧文·M.费斯著:《言论自由的反讽》,刘掣、殷莹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在于促进民主正当性。⑤[美]罗伯特·波斯特著:《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左亦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事实上,正如波斯特所指出的,他们与米克尔约翰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对民主理解上的差异。⑥同上书,第21页。尽管美国学者就言论自由的价值提出过各种观点,但是从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审查标准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民主政治论在美国具有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所不及的。同时,德国宪法法院以及学术界也是赞同民主政治论的。⑦何永红著:《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审查》,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从我国宪法学界来看,虽然民主政治论不能说占据了通说地位,但也同样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持。例如,杜钢建教授早在1993年论述言论自由时就指出言论自由的价值在于推动思想的解放、打破思想僵化、真实体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以及集思广益以做出科学决策。⑧杜钢建:“首要人权与言论自由”,载《法学》1993年第1期。其后,不少中青年学者,包括欧爱民教授、马岭教授、何永红教授等也都持类似观点。⑨欧爱民:“修正的思想市场理论与言论的双轨保护”,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马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及其法律保护”,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1期;何永红:《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审查》,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论及网络言论自由的论文几乎都是从网络,特别是社交媒体对于民主和舆论监督的促进作用展开论述的。①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闫斌:“网络言论自由权宪政价值初探”,载《理论月刊》2013年第4期;郑燕:“网民的自由与边界——关于微博公共领域中言论自由的反思”,载《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1期;张小罗:“网络媒体:公众参与的新平台”,载《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7期。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的是,不少持综合价值说的学者实际上也认同“民主”构成言论自由的一项重要价值。民主政治论在我国之所以能够占据重要地位,除了与其他国家相似的原因外,我国宪法学的通说将言论自由划归为政治自由无疑也为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增加了分量。
然而,可惜的是,尽管民主政治论对于传统领域的言论自由可能是适用的,但它对于互联网条件下的言论自由却是不适用的。耶鲁大学的巴尔金教授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巴尔金教授提出,互联网所代表的数字技术虽然与传统技术并不存在绝对的割裂,但它却使言论自由某些以往不被注意的因素得到了放大和强调,而这一变化直接要求重塑言论自由理论以适应互联网的客观要求。③Jack M.Balkin,“Digital Speech and Democratic Culture:A Theory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79N.Y.U.L.REV.1(2004),pp.2,31.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大众传媒时代,言论自由领域中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受众的言论自由与传媒集团的资本控制之间的矛盾。而民主政治论正为政府解决这一矛盾、规制大众传媒提供了重要的正当理由。④Ibid.,pp.28-29.因而民主政治论才得以在20世纪,尤其是21世纪兴起,并且以“平等”为最主要的关注点。但是互联网时代,言论自由则发生了重要变化: (1)话题及表达方式极度多样化;(2)创造性超前;(3)对已有素材的改造和创新[即后文将详细谈到的“就地取材”(glomm ing on)];(4)互联网言论是参与的、互动的;(5)互联网言论的上述特性使其允许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到文化和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这又进一步地丰富了我们人格的形成。基于此,必须得到强调的一点是:言论自由构成了社会交换、社会参与和自我形成的交互式循环的一个组成部分。⑤Ibid.,pp.31-32.与此相对照,民主政治论的不足就凸显出来了。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于政治问题和公共议题讨论的强调超过对其他话题的强调;第二,贬低大众文化的价值;第三,贬低自由和个人自治对于言论自由的意义和作用。①Jack M.Balkin,“Digital Speech and Democratic Culture:A Theory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79N.Y.U.L.REV.1(2004),p.30.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认识到,互联网从诞生之初就展现出的惊人的创造力和前进力源于每个普通人平等、自由的参与;另一方面,互联网提供的技术架构也极大地扩展了每个人参与文化构建、发展和传播的可能性。因此,无差别的开放性才是互联网的生命之源。基于此,一种仅以政府和民主协商为中心构建的言论自由理论对于互联网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以最为广泛意义上的民主——文化层面上的民主——为基础来构建网络言论自由理论。②Ibid.,p.32.
基于以上分析,巴尔金教授认为,网络言论自由应以保障民主文化为价值拘束。③Jack M.Balkin,“The Declaration and the Prom ise of a Democratic Culture”(1999),Faculty Scholarship Series.Paper 258,http://digitalcommons.law.yale.edu/fss-papers/258;Jack M.Balkin,“Digital Speech and Democratic Culture:A Theory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79N.Y.U.L.REV.1(2004);Jack M.Balkin,“Old School/New School Speech Regulation”,127 Harv.L.Rev.2296(2014).巴尔金教授所说的民主文化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每一个普通人,而不仅仅是政治精英,得以公平地参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参与构成其自身及其所属的共同体和子共同体之思想和意义的发展,而作为其结果的意义之形成又反过来型塑了每个人的人格。民主文化较民主政治在外延上更为广泛,更注重过程而非结果。④Jack M.Balkin,“Digital Speech and Democratic Culture:A Theory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79N.Y.U.L.REV.1(2004),pp.3-4,32;Jack M.Balkin,“How Rights Change:Freedom of Speech in the Digital Era”,26Sydney Law Review1,2(2004).这一观点,笔者称其为民主文化论。
尽管巴尔金教授的民主文化论是针对美国的情况提出的,但是在对我国国情进行分析之后,可以认为这一学说同样适用于我国。首先,作为其最基本的特征,互联网的这种无差别的开放性与广泛的参与性在中国也是同样存在的。这一特性同样也是互联网在中国能够获得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其次,互联网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对它的理解绝不应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在对互联网的分析上,我们经常强调的就是它对于加强公民政治参与、构建公民与政府沟通渠道的积极作用,是它在公共事务上舆论形成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理解无疑是狭隘的。互联网不仅仅在政治舆论形成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更多的是在“人”的形成上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不仅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是网民表达其对于公共事务的观点的平台,它同时也是新文化的创造与传播的媒介,是加深与扩大人际交往的工具和途径,是技术发展的加速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简言之,它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私人事务等多层次、多方位内容的“高纬度空间”。①CNNIC的调查统计显示,个人对互联网的使用按照使用率的降序排列主要包括即时通信、信息搜索、网络新闻、网络娱乐(包括音乐、视频和游戏)、网络购物、网络支付等功能。参见《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年1月),第43~44页。互联网的多样性由此可见一斑。在互联网条件下对第35条进行解释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最后,民主文化论能够为我国的《宪法》文本所包容。在《宪法》序言为我国确立的建设目标中,从来没有把政治建设作为唯一的内容,而是明确规定:“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同时,在第2条中,在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同时,规定“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说明我国《宪法》对于由人民所构成的这一共同体的认识同样也是饱满的、多层次、多角度的,而绝非单一维度的认识。这就为我们借鉴民主文化论提供了坚实基础。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赞同巴尔金教授的主张,认为我们在互联网条件下对第35条进行解释时应以促进民主文化为原则。当然,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避免对巴尔金的民主文化理论产生误解,或以偏概全,用“‘文化中心主义’去取代‘政治中心主义’”。②左亦鲁:“告别‘街头发言者’——美国网络言论自由二十年”,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我们应该抓住的是民主文化理论的精髓,那就是对普通人平等参与的强调。
二、解释基准:无差别地适用比例原则
正如引言所述,解释原则将直接影响到解释基准的选择。在民主政治论下,由于言论与民主政治存在直接的联系,因此,政治言论(公共言论)得到了极大强调,它被认为是言论自由保护的核心,受到了最高程度的保护(适用严格审查基准)。而其他类型的言论,如商业言论、无意义的言论(nonsense)等,则被认为是不具有价值或是低价值的言论,只能适用中度审查基准,甚至宽松审查基准。我国法院虽然并未直接阐明适用分层理论和对于政治言论(公共言论)应该适用更严格的审查基准,但是从判决书的具体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法院的确接受了分层理论。在方是民案中,法院做出了这样的论断:对于“涉及公共议题、公共利益的言论”应该“留下相对宽松的自由空间”。换言之,法院认为对于公共言论应该提供更高程度的保护,这也就意味着对其应适用更为严格的审查基准。至于其他言论,受到保护的程度自然相对而言将更低一些。实际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周鸿祎案中就曾做出过这样的表述:微博言论之所以应予宽容对待,乃是在于它是“沟通思想、分享快乐和思考的交流平台”,而被告周鸿祎是将其作为营销平台,故而在判断其言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上应予严格对待。③陈道英:“微博言论自由之法律规制——从‘微博第一案’谈开去”,载谢佑平主编:《司法评论》(第4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193页。
然而,一旦我们试图以民主文化为原则来构建互联网条件下对第35条的解释基准,政治言论(公共言论)的这种特殊地位就不复存在了。
在民主文化论看来,互联网条件下的言论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就是因为互联网为每个普通人都提供了均等的参与文化之型塑的机会,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够进行创作和再创作,可以借由“绕道而行”(routing around)和“就地取材”(glomm ing on),①Jack M.Balkin,“Digital Speech and Democratic Culture:A Theory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79N.Y.U.L.REV.1(2004),pp.9-13.另可参见左亦鲁:“告别‘街头发言者’——美国网络言论自由二十年”,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在传统媒体塑造的文化之上创造出一种新的互联网文化。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使每个普通人参与文化塑造的行为都具有了意义,每个人的声音都有了“被听见”和对他人产生影响的可能。而反过来,这种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民主文化又将对作为其构成分子的个人产生影响。简言之,对于民主文化而言,重要的不再是政治观点的碰撞,不是在公共事务上通过有质量的商谈达致获得多数人认可的观点,而是“普通人以其自由意志平等参与”本身。换言之,在民主文化论看来,关键之处并不是“每件值得说的事情都可以说出来”,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说话”。②米克尔约翰曾经说过:“关键之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说话,而是每件值得说的事情都可以说出来。”参见[美]米克尔约翰著:《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任何促进这种民主文化的言论,任何真正体现“普通人的平等参与”和构成其实质内容的言论,不论是否政治言论,不论其议题是否公共事务,都具有同等的价值,都应受到宪法的同等保护。
嘎绒每天早上8点来到营业部,有些时候还早一些,从来不迟到。他来早了,便守在后门边和莽子说话:你一定看见小偷了,快给我说说是谁?看到甲洛洛走近,嘎绒笑笑,也学会了用汉人的方式打招呼:吃饭了吗?甲洛洛没好气地回应:一天只知道吃,又不是猪。嘎绒坏笑:我们的生活比猪有趣多了。这时西西来了,穿着从不离身的黑藏服,围着暗红围巾。还没等她走近,嘎绒便让出自己屁股下的木桩。西西正眼也没看他们,盯着莽子:昨晚冷了吗?嘎绒抢着回答:昨晚的确有点冷。甲洛洛张开的嘴还没出声,西西扭头:我在问莽子。甲洛洛赶紧把嘴闭上,嘎绒的脸上浮起一层红。
上文曾经提到过,互联网之“新”正在于它将传统言论自由的某些特征予以了强调和放大,而这些被放大了的特征之一就是言论所涵盖话题的多样性。虽然话题的多样性是传统言论自由也具有的特征,但是在传统条件下,这一特征并不明显。各种分散性的话题绝大多数只能在小范围(熟人圈)内传播,其影响力对于社会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传统条件下,张三看了一部不满意的电视剧,最多只能私底下抱怨两句,而无法形成有影响力的舆论。真正能够形成舆论并对共同体产生影响的,最主要的就是以政治言论为代表的公共言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言论自由理论才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政治言论上。
然而在互联网条件下,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了。在互联网条件下,每一个微弱的声音都获得了“被听见”和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因此话题的多样性得到了极大放大和强调。同样是张三看了一部不满意的电视剧,在互联网条件下,他就可能通过微博、微信、豆瓣等途径发表自己对于电视剧的看法,可能到该电视剧的主演、编剧、导演以及制作方的官方微博下进行评论。此时他的观点就不再是只能在小圈子里传播,而是在理论上拥有了被传播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的可能性。相应地,他也就具有了对这部电视剧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总的说来,网络言论固然包括政治言论和公共议题,但它同时也包括大量的闲言碎语、家长里短、心灵鸡汤;而这些言论对于民主文化同样具有推动作用。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14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渗透率最高的即时通讯工具(如QQ、微信)用户的主要用途是聊天或者是关注朋友圈,①“2014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资料来源https://www.cnnic.net.cn/hlw fzyj/hlwxzbg/ 201408/P020140822379356612744.pdf。渗透率第二的社交网站②本报告提及的“社交网站”是指狭隘的社交网站概念,即与Facebook形态和功能类似、基于用户线下社交关系而诞生、旨在为用户提供一个沟通交流平台的社交网站,在中国这类网站主要包括QQ空间、朋友网、人人网、开心网、豆瓣网等。参见“2014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资料来源https://www.cnnic.net.cn/hlw fzyj/hlwxzbg/201408/P020140822379356612744.pdf。使用较多的功能则依次为上传照片、发布/更新状态、发布日志/日记/评论。③“2014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资料来源https://www.cnnic.net.cn/hlw fzyj/hlwxzbg/ 201408/P020140822379356612744.pdf。而即使是关注新闻/热点话题这一功能使用率最高的新浪微博用户,④这一比例高达80.3%,参见“2014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资料来源https://www.cnnic.net.cn/hlw fzyj/hlwxzbg/201408/P020140822379356612744.pdf。其关注点也并非总是集中在政治言论(公共言论)上。例如,2015年6月21日9:59新浪微博热搜前3名就分别是:“(1)赵丽颖 新闻当事人;(2)广场舞大妈终于输了;(3)雪梨 王思聪。”⑤资料来源http://s.weibo.com/top/summary?Refer=top-hot&topnav=1&wvr=6。对于网民而言,他们固然关心香港政改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他们同样关心豆腐和蜂蜜能不能同时吃、即将上映的电影到底好不好看。而这一事实并不会削弱互联网言论自由所要促进的民主文化;相反,它正是民主文化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体现。我们每个人正是在这些看似不重要的意见的表达和交换中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同时每一个人的参与又共同形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与子文化。
因此,当我们以保障民主文化为原则来解释第35条时,应该对所有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不区分性质、不区分内容地给予同等保护。
而具体到解释基准的选择,从方是民案等的判决来看,我国法院只是明确了对网络言论自由案件应适用利益衡量的方法,而并未确定明确具体的解释基准。早在周鸿祎案中,法院就已经表明了司法权对待网络言论自由的基本态度:“对微博上人们的言论是否受言论自由的保障、是否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不当伤害,也应进行法益衡量,综合考量发言人的具体身份、所发布言论的具体内容、相关语境、受众的具体情况、言论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具体后果等加以判断。”⑥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一中民终字第09328号。如果说周鸿祎案只是提出了利益衡量的方法并予以了粗糙的运用,那么方是民案就是将利益衡量的方法在中国目前的客观条件下运用到了可谓“精致”的地步。首先,法院表明“本案双方的争议虽由‘转基因’这一公共议题引发,但这并不意味着由公共议题引发的恶意人身攻击也可以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因为此类言论“不具有任何价值,反而会产生对他人权益、社会利益的伤害”。其次,法院指出,在认定具体微博是否构成侵权时综合考虑的事项包括:相关微博发布的背景和具体内容、微博言论的相对随意性和率性的特点、言论的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的区分、当事人主观上是否有侵权恶意、公众人物人格权保护的适当克减和发言时较高的注意义务标准、言论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程度等。随后,法院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对涉案的微博逐条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是否构成侵权分别得出了结论。例如,对于部分微博中方是民使用“骂街”、“暗箱操作”等用语的情形,法院考虑到双方在微博上展开口水战的具体情景,认定为或属调侃,或属质疑批评,虽有一定贬义,但并未达到恶意侮辱、诽谤的程度。
然而纵观整部判决书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法院的判决已然可称精致,但是其所运用的方法却仍然只是粗糙的利益衡量——因为法官在利益衡量的过程中并未适用任何确定的审查基准,而只是以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为引导。这种利益衡量的结果将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于第35条的实施,同时对于与之相衡量的另一方利益——在方是民案中是对名誉权的保护,都是不利的。
在言论自由的解释基准上,有两个选项可供我们选择,即美国的三重基准论与德国的比例原则。根据美国的三重基准论,对于公共言论基于言论内容的限制应适用严格审查基准,对于非公共言论和对公共言论基于时间、地点、方式的限制则应适用中度审查基准或合理性审查基准。其中,严格审查基准是言论自由上最重要的审查基准,它要求法院审查:(1)政府限制言论自由是否出于紧迫的、重大的公共利益,且并非以限制言论自由为目的;(2)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手段是否经过严格的剪裁(closely tailored),是否是对言论自由侵害最小的限制手段;(3)政府所采取的限制手段与其所声称要保护的公共利益之间是否存在紧密的、实质性的联系。①Richard Fallon,“Strict Judicial Scrutiny”,54UCLA L.Rev.1267,1268(2007).实际上,Fallon认为严格审查基准有3个版本,但是在学术论文中出现最多的是本文正文中提到的这个版本。并且适用严格审查基准意味着法官将适用违宪性推定。而德国的比例原则并非专为言论自由打造的解释基准,而是一项具有普遍性的宪法原则。②有关比例原则及其与严格审查基准的区别,参见Alec Stone Sweet and Jud Mathews,“Proportionality Balancing and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2008),Faculty Scholarship Series Paper 14;资料来源 http:// digitalcommons.law.yale.edu/fss-papers/14;杨登杰:“执中行权的宪法比例原则——兼与美国多元审查基准比较”,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比例原则首先要求法官确认国家行为是否限制、干预了基本权利,在得出肯定回答之后,法官应进一步追问国家行为的目的与目的本身的正当性,此为比例原则的预备阶段。一旦确认国家行为目的的正当性,法官即应依次审查:(1)作为手段的国家行为是否适合于实现其目的(适合性原则);(2)国家在所有对目的实现相同有效的手段中,是否选择了最温和的、对基本权利限制最少的,甚至不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必要性原则);(3)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与由此得以实现的目的之间是否有合理的、适度的、成比例的、相称的、平衡的关系(狭义的比例原则)。③杨登杰:“执中行权的宪法比例原则——兼与美国多元审查基准比较”,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
三重基准论与比例原则同为利益衡量的具体方法,两者之间自然不无相似之处,但是其区别也是同样明显的:(1)三重基准论以言论的类型化为基础,而比例原则“虽然可以容纳一定程度的类型化”,但却“并非以类型化为依归”,而是以“追求动态合理平衡”为最终依归。①杨登杰:“执中行权的宪法比例原则——兼与美国多元审查基准比较”,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2)三重基准论蕴含司法机关应对政治机关抱持谦抑的理念,而比例原则却认同司法机关可以作为政策制定者出场。②Alec Stone Sweet and Jud Mathews,“Proportionality Balancing and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2008),Faculty Scholarship Series Paper,p.4.(3)相应地,比例原则与三重基准论相比与新宪政论更为契合。③Ibid.,p.62.(4)有学者认为,三重基准论更为机械和死板,而比例原则更为灵活,因为它实际上“是一套论证框架或程序,要求人们通过这套框架或程序,详尽考量具体个案中所有相关因素与法益的分量”,“具体脉络中的适合、必要与适度”是其“最高判准”。④杨登杰:“执中行权的宪法比例原则——兼与美国多元审查基准比较”,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当然,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何永红著:《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审查》,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151页。(5)三重基准论认可言论自由为一种优越的(preferred)自由,⑤Richard Fallon,“Strict Judicial Scrutiny”,54UCLA L.Rev.pp.1287-1290.而比例原则却认为“只有在个案的具体脉络中,才能对基本权利与相冲突的其他法益谁较重要、谁应优先的问题做出完整而最终的回答”。⑥杨登杰:“执中行权的宪法比例原则——兼与美国多元审查基准比较”,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
对应于上述区别,在我们做出解释基准的选择时,尤其应该考虑到我国如下特点: (1)相比于美国与日本的司法理念,我国的司法权更倾向于强调司法能动而非司法谦抑的立场;⑦郑戈:“有自尊的高贵司法传统拒绝普世的整容术——在《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网上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资料来源http://www.aisixiang.com/data/92335.htm l。(2)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国家角色的理解上,与近代立宪主义有所不同;(3)我国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是以人性尊严为价值统领,⑧汪进元著:《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言论自由在我国的基本权利体系中并不占据优越地位。将这两种解释基准与上述特点一一对照即可发现,比例原则对于我国而言是一种更优选择。当然,考虑到比例原则内涵的丰富性及其灵活性,它对法官素质的要求也可能更高。
具体来说,法官在网络言论自由案件中运用比例原则对第35条进行解释和适用应依照如下步骤进行:(1)确认国家行为是否限制、干预了言论自由。这就涉及对“言论”的界定。从目的解释的角度出发,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制宪者制定第35条是为了对所有的言论一视同仁地提供宪法上的保护;因为某些言论的确会严重侵犯他人权益,破坏社会秩序或危及国家安全。在这里,制宪者必然蕴含了一定的价值选择,只有与此价值相吻合的言论才属于第35条保护的对象。结合上文有关第35条解释原则的分析,具体到互联网语境,应该认为只有确实有利于促进民主文化的言论才属于第35条所说的“言论”。据此,淫秽言论、侮辱言论、诽谤言论、挑衅言论等均应被排除在“言论”之外。(2)确认国家行为的目的与目的本身的正当性。(3)考察作为手段的国家行为是否适合于实现其目的。(4)考察国家行为是否符合必要性原则。(5)考察国家行为是否符合狭义比例原则。而在上述步骤中对立法事实进行审查时,不论涉案的是否为政治言论/公共言论,法官都应同样进行强力审查。①有关强力审查,参见何永红著:《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审查》,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9页。
三、效力范围:对第三人间接效力
如同本文开篇所介绍的,包括方是民案在内的网络言论自由案件均表明了我国法院的这样一种态度:承认第35条在私人间具有直接效力。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周鸿祎案、余丽案和方是民案的双方当事人均是平等主体的私人,例如,方是民案的双方当事人即作为私人的方是民(方舟子)与崔永元。但是法院在判决书中均毫不犹豫地将言论自由作为了利益衡量中的一方利益,这也就表示法院认为公民得向第三人主张言论自由。那么,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呢?换言之,第35条的效力范围是否包括私人间法律关系?
尽管宪法条款效力范围的问题在其他基本权利条款也存在,②宪法对第三人间接效力理论出现的时代背景是古典宪法的认识与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之间的矛盾,而在我国引发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直接起因却是私法领域中大量立法空白的存在。因此,笔者认为,宪法在私人间是否能产生效力对我国而言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具有紧迫性的问题;真正具有紧迫性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宪法的司法适用性。但第35条的效力范围问题之解决尤其具有紧迫性。因为ISP/ICP为网络言论自由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因此,网络用户能否主张ISP/ICP侵犯其言论自由就成为释宪者必须问答的一个问题。由此,在互联网条件下第35条的效力范围问题也就被放大为了在第35条的解释和适用上无法回避的一个常态问题。
实际上,宪法在私人间效力的问题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拒不承认宪法能够在私人间产生效力的国家在互联网法律规制中都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巴尔金教授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巴尔金教授指出,在美国,由于网络的基本架构是由私人公司所有的,因此,可以说服务商所代表的私权力(private power)与政府所代表的公权力共同左右了互联网的发展走向。③Jack M.Balkin,“The First Amendment is an Information Policy”,41Hofstra L.Rev.1,7-8(2012).正因如此,所以互联网时代政府规制的“新思路”(new school)极大地依赖的就是私人(服务商)与政府的合作;而基于网络架构的特征,政府赖以迫使私人与其合作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要求或者威胁服务商就用户的言论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此时则必然随之发生附属审查。④Jack M.Balkin,“Old School/New School Speech Regulation”,127Harv.L.Rev.7,9(2014).所谓附属审查,就是当私主体A需对另一方私主体B的言论承担法律责任,从而使得A对B的言论具有了一定的控制权力时所发生的私人言论审查形式。为了避免责任,A非常可能罔顾B的言论对B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而其进行过度审查。另外,巴尔金教授认为,服务商的附属审查实际上是由政府的压力而实施的,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Jack M.Balkin,“Free Speech and Hostile Environments”,99Colum.L.Rev.2295,2299(1999).同时,由于互联网资源掌握在大公司的手中,这些公司出于利益驱动本来就倾向于控制网络上的言论,使其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①Jack M.Balkin,“Digital Speech and Democratic Culture:A Theory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79N.Y.U.L.REV.1(2004),pp.22-26.由此,私人(服务商)就成为互联网条件下对言论自由最大的威胁。②Jack M.Balkin,“The Future of Free Expression in a Digital Age”,36Pepp.L.Rev.427,431,436(2009).但是,巴尔金教授对此开出的药方并非引入第三人间接效力理论,而是强调由政治部门制定符合第一修正案和民主文化价值要求的“政策”。Jack M.Balkin,“Digital Speech and Democratic Culture:A Theory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79N.Y.U.L.REV.1(2004),pp.47-49.
莱斯格教授在《代码2.0》中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了这一问题。他不止一次忧心忡忡地指出,在网络时代,对言论自由的威胁除了来自政府之外,还有可能来自私人(服务商);而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被认为只能适用于政府行为,因此,美国宪法对于这一情况无能为力,这样来自私人的威胁就可能是更加危险的。③[美]劳伦斯·莱斯格著:《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第298页、第343~344页。莱斯格教授不无羡慕地提到了德国基本法的第三人间接效力理论,在这一理论之下不需要将私人行为转换为政府行为即可适用宪法,因此上述问题对德国而言不成为其问题。④同上书,第343~344页。相比而言,美国宪法在互联网条件下的局限性就非常明显了,而这一局限性很难说是值得坚持的,因为“只有在政府是唯一的规制者的世界里,将宪法权力局限于政府行为上才有一些意义。当规制模式多样化时,我们就没有理由去限制宪法价值所能达到的范围了”。⑤同上书,第298页。
正如学者们再三指出的,互联网条件下言论自由最大的转变就在于它由“用户—政府”的双方关系转变为了“用户—服务商—政府”的三方关系。⑥陈道英:“我国网络空间中的言论自由”,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10期;左亦鲁:“告别‘街头发言者’——美国网络言论自由二十年”,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作为言论自由链条上的中间一环,服务商必然会与用户的言论自由发生各种纠葛;同时,基于同样的理由,政府在网络言论规制上也必将极大地依赖ISP和ICP,⑦陈道英:“ICP对用户言论的法律责任——以表达自由为视角”,载《交大法学》2015年第1期。而这势必导致附属审查。因此,第35条在私人间究竟具有怎样的效力就成为现实所提出的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虽然我国互联网的物理架构并不存在私人所有的问题,但我国的ISP同样是企业,同时,ICP中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如新浪、腾讯、网易等,是私人企业。当它们涉嫌侵犯用户言论自由的时候,我们同样会面临宪法在私人间适用的问题。而这样的情况几乎无时无刻不发生在网络空间中。对于ISP而言,限制某些域名的接入和访问、限制用户带宽、收取高额宽带使用资费等行为都有可能构成对用户言论自由的侵犯;而对于ICP而言,无论是要求用户实名注册,还是删除或屏蔽用户发布的帖子、对用户实施暂时性禁言(“关小黑屋”)以及封ID等措施,也都同样可能构成对用户言论自由的侵犯。同时,还需要注意到的是,服务商以外的私人也具有侵犯他人言论自由的可能性。①例如,微博主删除他人在自己微博里发表的评论,或者张三主张李四的言论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或隐私权等)而要求删除李四言论等情况。因此,第35条在私人间具有何种效力已经成为互联网条件下解释和适用这一条款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如上所述,我国法院在第35条效力范围上的态度是认可其在私人间具有直接效力。然而,以上观点只能涵盖方是民案之类仅涉及网络用户之间法律争议的情形。对于真正构成互联网条件下第35条范围问题的重点——用户与ISP/ICP的法律争议能否适用第35条,法院的态度却是不置可否。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9年7月13日发文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因网络管理而引发的民事、行政纠纷“不予受理”,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互联网管理案件立案审查工作的通知》。在2014年6月1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查立案若干问题的解答》(四)中仍然规定:“互联网管理引发的纠纷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在立案审查时要坚持慎立慎裁原则,并在第一时间逐级报告省高院立案一庭;同时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法委支持,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当事人的工作,不得擅自对外表态。”所以直至目前法院都未受理过此类案件,更谈不上回答第35条效力范围的问题了。③目前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中只有余丽案属于由服务商引起的网络言论自由案件。虽然余丽案同样适用了直接效力说,但由于它仅为个案,因此笔者认为它不具有代表性。回避受理,一方面使网民的言论自由无法获得司法救济;另一方面还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诉权。在我国已经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的今天,回避受理显然不应再作为我们应对这一问题的方式而存在。然而,适用直接效力说也是同样不足取的。从我国的宪法文本来看,只有第36条、第40条、第41条中出现了“任何人”或“任何个人”的用语。这也就意味着,只有上述条款是能够在私人间直接发生法律效力的。其他条款,包括第35条都只能在公民—国家间发生直接法律效力。一方面,法院在方是民案等网络言论自由案件中直接适用第35条的做法显然与宪法条款的规定相抵触。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完全没有考虑到宪法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法院随意适用直接效力说不仅从理论上来看是行不通的,而且从实践上来说还会产生将宪法庸俗化的后果。④关于我国不应适用直接效力说的理由,参见任丹丽、陈道英著:《宪法与民法的沟通机制研究——以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188页。
笔者认为,较为可行的做法就是承认宪法对第三人的间接效力。首先,无论从我国的宪法文本出发,还是从我国的宪法理念出发,承认宪法对第三人具有间接效力都是具有可行性的。⑤任丹丽、陈道英著:《宪法与民法的沟通机制研究——以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页以下。其次,从实践层面来看,虽然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并未得到承认,但是对于网络言论自由案件适用宪法对第三人间接效力理论却并非完全不可行的——因为宪法对第三人间接效力从本质上而言并不是宪法的司法适用,而是法院对法律进行的合宪性解释,而由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却是完全能够被我国的宪法制度所包容的。⑥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
落脚到互联网条件下第35条的效力范围问题,笔者认为,在考虑到服务商与普通私人之间区别的基础上,可做如下回答:(1)对于用户—服务商的私人间法律争议,宜承认第35条的间接效力,即对于服务商涉嫌侵犯用户言论自由的案件,宜通过对民法概括性条款的合宪性解释(第35条在私人间的间接效力)达到对用户言论自由予以司法救济的目的;(2)对于用户—用户的私人间法律争议,则应谨慎承认第35条的间接效力,尽量将其作为普通民事案件而在法律层面解决。
∗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2014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把握互联网‘最大变量’核心问题研究”(编号:14ZD003)、2015年度中国法学会重点专项课题“中国基本权利规范的宪法解释基准研究”[编号:CLS(2015)ZDZX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