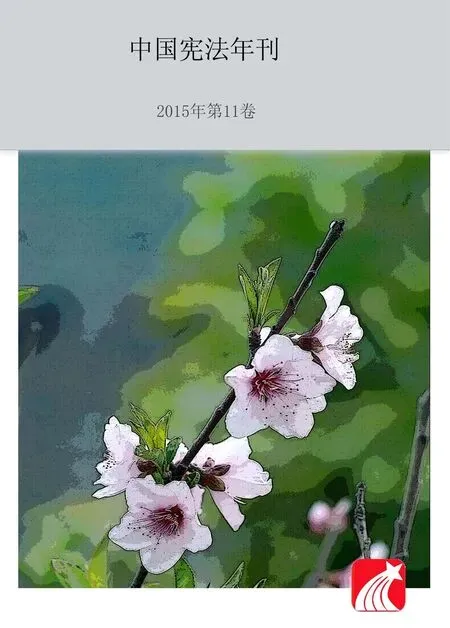论宪法惯例的规范性
2015-01-30何永红
何永红
论宪法惯例的规范性
何永红∗
现代宪法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它“缜密且统一地规范政治统治的建构和运作”,这不仅要求国家权力通过宪法产生,而且还有一个刚性条件,即“只有当宪法的调整范围与国家权力的活动范围完全一致的时候,它才能实现其对政治统治进行彻底法律化的诉求”。①[德]迪特儿·格林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宪法惯例作为对宪法性法律规则的补充,就性质而言,也具有规范性的特点。惯例和法律虽然在概念上有明确区分,但它们起作用的方式是相似的,而且具有许多共同的特性,这就使得法院和立法机关在恰当的时候把惯例转化成法律成为可能。
简言之,宪法惯例作为一种社会规则,不仅仅是对实然状态的描述,而且也是对政治行为的规范,具有宪法文本般的规范性和约束力。②就此而言,那些超出宪法调整范围的最高国家权力,在其实践中所形成的惯例就一定不是现代宪法意义上的宪法惯例。这就是我们区分宪法惯例与政治惯例的标准。参见何永红:“中国宪法惯例问题辨析”,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1期。在此前提下,若要对某些可疑的宪法惯例进行认证,就必须首先让它们在理论上通过“规范性”的检验,否则,这些所谓的惯例就只是一些“习惯性的做法”或“已有的做法”而已,并不构成真正的宪法惯例。然而,宪法惯例与习惯性做法之间的区别何在?宪法惯例具有哪些内容,以及更重要的,宪法惯例的约束力体现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宪法惯例是否为政治行为人施加了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靠什么保障实施?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作为宪法准则的宪法惯例
宪法惯例是英国人的发明,最先对其进行理论总结的是英国宪法学家戴雪。然而,在戴雪之前,已有大量关于宪法惯例的论述。戴雪本人在《英宪精义》初版(1885年)前言中承认,他的研究得益于同时代的宪法史学者弗里曼。弗里曼在“成文法”和“惯例性宪法”之间所作的区分,激发戴雪去探寻“为何宪法默契尽管不是法律却仍然得到遵守”这一问题的答案。③当然,在弗里曼之前,我们还能列出一长串的人物,如洛克、布莱克斯通、伯克哈勒姆等。按照弗里曼的说法,直至17世纪末,宪法和法律间划分不出界限,君主特权、议会特权、属民的自由权均奠定在制定法与普通法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有一整套政治道德,一整套指导公共人士的戒律准则。这些东西在任何制定法或普通法里都是找不到的,但是他们在实践中几乎与体现在《大宪章》或《民权请愿书》中的原则一样神圣。简言之,在我们成文法律旁边,生长出一部不成文的或惯例性的宪法。当英国人说某公共人物的行为合宪或违宪,其含义完全不同于说此人的行为合法或违法。”①The Grow th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3rd ed.,revised 1876),p.109.
弗里曼给出的例子包括:首相失去下议院的信任时必须辞职或要求解散下院,内阁和首相应保持统一立场,以及各部部长对议会的整体责任。弗里曼的贡献在于,他在书中把违反能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包括制定法和普通法)与违反非法律的规则明确区分。
戴雪于1885年出版《英宪精义》时,正好与弗里曼是同事。戴雪接受了弗里曼对“惯例性准则”的叙述,并且将这些非法律的规则命名为“宪法中的惯例”,或者今天的通用称呼“宪法惯例”。但戴雪比弗里曼懂得更多法律知识:“如果首相建议设立500名上议院贵族代表,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大法官法庭不会发出强制令以限制这一设立行为。如果首相因一次不信任案而应辞去职务,那么王座分庭肯定不会发出令状责问他为何仍任首相。”②Dicey,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London:Macm illan,1915,p.19.
安森的《宪法中的法律与习惯》(第1卷)在戴雪《英宪精义》出版1年之后问世(即1886年)。他赞扬同事戴雪对英国宪法的解释,但不打算照搬戴雪的方法。他的《宪法中的法律与习惯》(第1卷)的内容仅限于有关议会的问题:“思考我所描述的程序有多少是法律、又有多少是习惯,这是很有趣的。我所用的‘法律’这一术语不仅包括制定法,也包括一系列有时被称为议会法的、确为普通法组成部分的规则;而‘习惯’这一术语则指代这些惯例:违背它们不会影响议会程序有效性,也不会影响公共的或个人的权利。”③SirWilliam R.Anson,ed.The Law and Custom of the Constitution,1886,pp.67-69.
但是,安森把他所谓的“习惯”与那些“不重要的仪式”进行了区分。后者如选举议长的仪式、女王对议长当选人的批准等。在该卷最后,安森讨论了议会对行政机关的控制,他说这是超出法律的领域的,并沿用戴雪的说法,称其为一种惯例,其约束力最终取决于法律。④Ibid.,pp.319-321.《宪法中的法律与习惯》(第2卷)出版于1892年,内容是关于君主的。安森指出,18世纪的部长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意味着可能会受弹劾;与之相反,现在的部长责任则是向公共舆论负责,意味着可能会失去其职位。⑤Ibid.,p.112.
若干年后,宪法史家梅特兰谈到内阁时强调,研究法律规则很有必要补充研究“我们宪法中的习惯或惯例”。①[英]梅特兰著:《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此书材料来源于梅特兰生前的讲演,即1887年至1888年间在剑桥大学所作的演讲,梅特兰说这些成果受益于斯塔布斯、戴雪、安森等人近期的著作。另外,他称“自己正置身于一些显然不是法律规则的规则中,它们也许可被称为宪政道德,或者宪法性的习俗或惯例”。②[英]梅特兰著:《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页。在另一处,梅特兰再次说道,这些非法律规则“有时被称为宪政道德,或宪法实践、宪法习惯、宪法惯例,或者还可以被称为宪法性共识”。③同上书,第339页。
很显然,梅特兰接受了法律和宪法惯例之间的区分,尽管他并没有给后者取一个恰当的名称。真正让“宪法惯例”这一名称固定并传播开来的,还是戴雪在《英宪精义》中的著名区分,他说宪法中有两套完全不同的规则:
第一套规则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它们都是由法院强制实施的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宪法”,以示区别,可将其统称为“宪法性法律”(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第二套规则是由惯例、默契、习惯或常规组成的,尽管它们也可以调整握有最高权力的几个成员、全体部长或其他官员的行为,但因为不是由法院强制实施的规则,所以实际上根本不是法律。同样,为了以示区分,宪法的这部分内容可称为“宪法惯例”(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或宪法道德。④Dicey,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London:Macm illan,1915,p.23.
宪法惯例虽然不能得到法院的强制执行,但是按照戴雪的分析,对惯例的违反最终将导致对法律的违反。换言之,宪法惯例作为一种宪法准则,其最终约束力间接体现在法律制裁中。
二、宪法惯例的甄别及其类型化
英国的政府制度以惯例为基础——英国内阁本身就是惯例而非法律的产物,责任制政府的整个运行都建立在惯例基础上,但是对于惯例的内容和范围却很难精确界定,从历史上看,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是一个古老的民主国家,堆积了大量惯例,有些很难与传统做法或只是用法区别开来”。⑤[英]波格丹诺著:《新英国宪法》,李松锋译,李树忠校,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页。从逻辑上看,“我们认为是一项惯例和我们认为应当是一项惯例之间并不总是易于区分”。⑥同上书,第295页。加之宪法惯例的内容本身就很抽象,有时很难对其含义进行解释。所以,宪法惯例的甄别着实成为问题。
前述戴雪的理论并没有对何为宪法惯例作出解释,就性质而言,戴雪实质上是把宪法惯例定位于一种道德原则。这的确反映了对于惯例运作及执行的传统理解。尽管有一些惯例有明确的实施者,如首相或者总督,但许多惯例的确是由公众舆论的法庭来调整的。这一定位的最大困难是,它无法对何为宪法惯例的具体甄别提供指引。
关于惯例的甄别问题,最正统的学说是詹宁斯提供的,我们可称其为“詹宁斯标准”。他说,在辨识何为宪法惯例时,需要提出三个问题:“第一,这些先例是什么;第二,先例的参与者是否相信他们受着某一规则的约束;第三,该规则的存在有理由吗?”①[英]W.I.詹宁斯著:《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2页。单一的先例和好的理由足以建立一项规则。反之,若没有一个明确的历史先例,则不会有相应惯例的建立。后来的法学家,如尤金·福西特别赞同这一观点:“一个没有对应先例支持的宪法惯例就如同一座缺少任何基础的房屋……毫无疑问,必须至少要有一个先例。如果没有先例,就没有宪法惯例。”②Forsey,“The court and the 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1984)33UNB Law Journal,p.34.虽然詹宁斯标准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关于先例问题。
有学者评论说:“依赖于历史先例有点像借助星星航行。在晴朗的天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老天不会总是如此乐于助人。天空可能会整个被云团笼罩,或者大片的天空被覆盖。”③Andrew Heard,“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The Heart of the Living Constitution”,(2012)6Journal of Parliamentary and Political Law319,p.321.也就是说,当有先例存在而且能够分辨哪个先例与我们的宪法运行有关时,这一要素非常有作用。但关键问题是,历史先例可能完全丢失,或者是来自过去的时代,或者与别的先例相矛盾。所以,詹宁斯标准只对“那些从连续的政治实践中发展而来的惯例最有效果”,④Ibid.因为惯例有可能产生于政治参与者的政治协议,而有些惯例也是那些不连续的、陈旧的,或正在消失的先例的产物。
其次,关于参与者的信念问题。
这里的问题是,识别政治参与者的信念是非常困难的。根据詹宁斯的理论,我们需要去询问先例中的参与者是否认为他们被某项规则约束。但很显然,政治家的信念很难把握,往往难以找到对他们信念的清晰可靠陈述。另外,随着宪法共识的变化,政治人物的信念会随时间推移而产生巨大变化。因此,19世纪政治人物的观点与21世纪早期政治人物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最后,关于规则的理由。
相对而言,在詹宁斯标准中,这一要素的问题是最少的。尽管詹宁斯并没有解释他用“理由”表达的含义,但很明显,在詹宁斯这里,“理由”是在指一项原则而非一种简单的偏好。
如果没有内含的理由,先例就仅仅是传统做法而已。逻辑上讲,第三个要素必须与政治家认为他们受某项规则约束的信念联系在一起。政治家仅仅说“我感到有义务这么做”是不够的,没有内在的理由,这项义务可能仅仅是遵循传统或政策偏好。
总之,詹宁斯标准的确可以有效辨识许多惯例。正如赫德教授所言:“如果先例清楚,所有政治人物对于受规则约束做出了相应表态,并且有原则性理由这样做,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存在一个已经确立的惯例。如果先例和参与者是当下的,那这一切将更加顺利。”①Andrew Heard,“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The Heart of the Living Constitution”,(2012)6Journal of Parliamentary and Political Law319,p.328.然而,在缺少先例或先例模糊的情况下,这一标准会失败。另外,政治家不是法官,不会总是对他们的选择和行为提供详细、连贯、坦白而真实的说明。因此,詹宁斯的标准只是部分起作用。
当代宪法学家杰弗里·马歇尔评论说,惯例似乎产生于常规做法或协议之外的某种事务,它的形成可能是以某个公认的、赋予惯例正当理由的政府原则为基础的。比如,“尽管很少有人对以下惯例规则进行准确阐述,但它却是英国宪政体制中最明显也是最没有争议的惯例,即议会不会压迫性地或者专横地行使其无限的立法主权。这是一个依托于宪政原则和法治规则,模糊但是被明确接受的惯例规则”。②Geoffrey Marshall,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The Rulesand Forms ofPolitical Accountabil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9.对惯例的这一解释,比詹宁斯标准要合理得多。因为对政治家的信念要求,实际上是将惯例规则降为是对政治参与者内在道德的义务限定。随着更大的宪法共同体对当前政治参与者道德义务的建构,宪法惯例事实上以一种批判道德体系在运作。换言之,惯例是宪法中的“批判道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或社会学上的调查就不可能发现惯例,因为说惯例的存在是一个规范性表述,而非对事实问题的复杂描述。”③[英]波格丹诺著:《新英国宪法》,李松锋译,李树忠校,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页。
这样,根据宪法惯例本身的规范化程度之不同,可以将惯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具有根本性的,譬如,政府在下院不信任投票中失败时就必须辞职。第二类如内阁责任,虽然也具有根本性,但随着政治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其内涵可能会发生变化。第三类就不那么具有根本性,例如,皇室家族成员不能发表有党派倾向的言论。但是,由于没有类似于法院对法律规则的解释,所以惯例的具体内容往往不明确,其结论通常取决于政治变化。
三、宪法惯例的规范内容
尽管宪法惯例是英国宪法的重要渊源,但是并非只有不成文宪法国家才有宪法惯例。成文宪法国家如美国也具有典型的宪法惯例。④对美国宪法惯例的研究,参见 James G.Wilson,“American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The Judicially Unenforceable Rules Tat Combine With Judicial Doctrine and Public Opinion to Regulate Political Behavior”,(1992)40Buffalo Law Review645。相对而言,成文宪法国家可能更不能容忍惯例的不确定性,所以,其中有些国家把宪法惯例明确记载下来,即让惯例形式化。典型者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1985年澳大利亚专门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名为“宪法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由联邦和各州的政府代表组成,代表各个党派,试图对澳大利亚宪法中的惯例进行甄别。其报告列举了34项惯例。①David Wood,C.J.G.Sampford,“Codification of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in Australia”,P.L.1987,Summer,231-24.该文附录中详细列明了34项澳大利亚宪法惯例,同时也列明了31项《1983年不被承认和宣布的惯例》。这些惯例解决了女王的关于澳大利亚宪法权力的行使问题,联邦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和运作问题,总督任命和解职大臣的权力问题和他的权力范围问题,如议会、立法和全民公决等。试举数例。②David Wood,C.J.G.Sampford,“Codification of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in Australia”,P.L.1987,Summer,239-241.
第一,关于联邦宪法赋予女王的权力。
“第二条:女王直接接受英联邦部长建议。”
第二,关于总督的任命。
“第三条:澳大利亚首相就总督任命问题向女王及其大臣进行非正式咨询,然后女王在澳首相的正式建议下对总督予以任命。联合王国大臣不涉及任命问题。”
第三,关于澳大利亚女王和总督各自的地位。
“第十一条:总督行使宪法赋予他的权力时,女王不能干预,女王亦不能自己行使这些权力。”
第四,关于行政委员会的组成。
“第十四条:首相和财务大臣必须是众议院的成员,并且不得是参议院成员。”
第五,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运作。
“第十五条:行政委员会不是一个审议机构,它通过某部长批准后的书面意见来给总督提出正式建议。”
第六,关于总督行使的其他权力。
“第二十九条:总督根据相关大臣的建议,根据宪法第56条的规定行使对拨款目的的建议权。”
第七,关于议会和选举。
第八,关于司法独立。
“第三十四条:法官履行其司法职责时,不受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干预。”
澳大利亚的宪法会议对宪法惯例进行汇编之后,在宪法理论界引起了广泛争议。③Ibid.,237.这一汇编看起来像是立法和审判权的混合物。这与中世纪立法的做法有某种相似性,其任务最初被视为宣布现行法而非重新立法。但是现行权力的性质却不清晰。
最关键的问题是,宪法会议承认和宣布惯例的正当性何在?存在任何关于这种宣布(如自治会议)的先例吗?被承认和宣布的惯例规则的本质是什么?它们是否是一种德沃金式的原则,还是戴雪所说的“实证道德”抑或马歇尔的“批判道德”?
可见,“人们不能夸大惯例成文化可能带来的清晰度。惯例的表述将会是非常抽象,其解释有可能仍然存在争议……判断什么可算作一项惯例不是纯粹的知识判断和法律裁决,而实质上是一个政治行为,将惯例写进宪法并不会改变这种根本性难题”。①[英]波格丹诺著:《新英国宪法》,李松锋译,李树忠校,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页。惯例争议问题之解决,关键不在于能否成文化或写入宪法,而在于政治力量的较量,或者说取决于公共舆论或者前述“批判道德”。
上述澳大利亚宪法惯例的例证说明,大多数宪法惯例是对公权力施加义务的规则。“对于科予义务的惯例之遵守,不需要用一般性的理由来解释,其实只用指出,当这些惯例被遵守(而非违反、拒绝或者改变)时,会被认为是在创立有效的义务规则。”②Geoffrey Marshall,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The Rules and Forms ofPolitical Accountabil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10.正如Jaconelli所言,宪法惯例这个术语是被用来限制那些拥有宪法性意义而不仅仅只是政治意义的社会规则。宪法惯例作为一种社会规则,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根本特征:规范性和不可由法院强制执行。宪法惯例所具备的“宪法性”特征,使它们所起的作用与成文宪法的作用相似,即在政府机构和政党之间分配权力。③Joseph Jaconelli,“The nature of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1999)19Legal Studies24,pp.45-46.
四、宪法惯例的约束力问题
既然宪法惯例具有规范性,并且具有与成文宪法一样的作用,那么尚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回答,即宪法惯例的约束力体现在何处?换言之,靠什么保证宪法惯例的实施?
他16年坚持学术援藏,不畏艰险盘点世界屋脊的植物家底,寻找生物进化的真实轨迹。从藏北高原到喜马拉雅山区,从阿里无人区到波涛汹涌的雅鲁藏布江江畔,到处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粒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宪法学史上有两种经典理论来回答这一问题:一是戴雪的“法律制裁论”;二是詹宁斯的“承认理论”。
众所周知,戴雪在惯例和法律之间做出了明确区分,其区分依据是“法院能否强制执行(enforce)”,或者说,司法上是否具有可适用性(justiciability)。一般公认为,宪法惯例在法院的判案过程中,不能作为直接依据引用——很显然,法律之所以称为法律,是可以作为判案依据的。所以,戴雪的宪法惯例学说是建立在惯例和法律的明确区分基础上的。这样,戴雪就必须回答:作为在性质上与法律不同的惯例,其约束力体现在什么地方?
戴雪首先反驳了两种常见的观点:一是弹劾制;④戴雪说:“这个观点站不住脚,不然我们就可以说,这些惯例根本不是默示协议,而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故其唯一的特点在于,它们一旦被违反,只有一所特别法院即议会高等法院才能处罚。”参见《英宪精义》第15章。二是舆论。关于舆论的力量,我们在此必须多解释两句,因为“靠舆论保证宪法惯例的实施”符合大多人对惯例效力的看法。戴雪在下述这段话中作了有力的反驳:
公众舆论赋予政治生活中公认的行为准则以效力,这个说法倒也正确,但仍有一个缺陷,即如果不作进一步解释,它只不过是在重述我们正要解决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公众舆论表面看来,完全能够具有一种约束力,迫使宪法惯例得到遵守?显然,不能回答说,因为这些惯例是由公众舆论来强制实施的。①Dicey,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London:Macmillan,1915,Charter 15.
所以,要回答惯例的约束力问题,就必须寻找一种不同于“弹劾”和“舆论”的力量,戴雪的答案是:
法律的力量。政治伦理中所通行的那些信条,最初可能是由于恐惧弹劾而确立的,公众舆论肯定也对其施加了影响,但是,能够束缚住那些大胆的政治冒险家,让他们不得不遵守宪法的根本原则以及蕴含这些原则的惯例,其中的约束力正在于:这些原则和惯例一旦被违反,几乎就直接让犯事者陷入与国法及法院相冲突的境地。②Ibid.
为此,戴雪举了一个他认为最为确定的惯例规则来加以说明:一是“议会必须每年召开一次”。戴雪说,“如果该惯例打破了,其结果将会是没有机会通过必须每年通过一次的立法事务:军事法和财政法。因此,若不通过军事法,常备军的存在就是非法的;若不通过财政法,大部分的税收将不能以合法名义征收,同时每一个负责收税的政府官员将会使自己面临起诉的境遇”。③Ibid.,p.447.简言之,戴雪认为,惯例是靠一种间接的法律力量来强制的。
其实,这里真正的障碍是《权利法案》(1689年)的第6条,即除经议会同意外,平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者维持常备军,皆属违法。虽然在理论上,议会可以连这第6条也加以修改掉,但该条文不可修改或废除本身就是一个惯例。换言之,第6条应被视为根本法,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惯例。所以,按照Jaconelli的说法:“要求国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的惯例被违反之后,其后果不是(如戴雪所主张的那样)违反法律,而是因为违反深层次的惯例:应将第6条视为根本法。”①Joseph Jaconelli,“Do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Bind?”,Cambridge Law Journal64,1:149-176.
再者,《权利法案》第4条②“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中可适用的条款并没有暗示每年(或者甚至是经常)都需要议会授权。戴雪的论证因此没能支持他关于宪法惯例具有间接强制力的理论,即便在他引用的并不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范围之内。
再来看詹宁斯的“承认理论”。
詹宁斯在许多问题上都对戴雪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包括法律与惯例的区分,以及惯例的约束力问题。詹宁斯说:“戴雪论点的谬误主要在于法律是实施的……对政府或大臣违法行为的法律救济办法之所以起作用,并不因为它得到了实施,而是因为得到了遵守。”③[英]W.I.詹宁斯著:《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8~89页。就此而言,法律和惯例之间没有实质区别:“惯例就像任何宪法的大多数基本规则那样,主要依赖于普遍的默认。成文宪法之所以是法并非是由于某人制定了它,而是因为它得到了承认。”④同上书,第80页。21世纪Barber的论点与此类似,他说惯例和法律间的区分只是个程度问题,它们起作用的方式是相似的,而且具有许多共同的特性,这就使得法院和立法机关在恰当的时候把惯例转化成法律成为可能。See N.W.Barber.“Laws and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Law Quarterly Review,Vol.125,2009:294-309.在这里,詹宁斯的思路似乎与后来哈特对“承认规则”的界定颇为相近,即无论什么规则,之所以得到遵守,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官员和民众予以普遍承认这一事实。
可见,詹宁斯把法律和惯例视为相同的。但是,一方面,长期被人们遵守或认同的社会规则(作为与法律相对的概念)并不必然产生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另一方面,法律规则中的权利和义务若是长期被人忽略,在没有被正式法律修改废除之前,仍然不能说它就已经变成一种道德规则。简言之,法律和惯例在概念上需要做出明确区分。其实,詹宁斯本人也是承认法律规则和惯例之间的区分的。因为詹宁斯本人也坦承,法律和惯例的区别还是具有技术上的重要性。当他说到“法律规则是通过法院的判决正式表达或正式阐明的,而惯例则产生于习惯,而习惯何时成为或不再成为惯例,则很难把握”⑤[英]W.I.詹宁斯著:《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0页。时,他和戴雪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大。
所以说,宪法惯例所具有的约束力,都建立在某种不同于法律义务的基础之上。这样,我们就回到了戴雪所提出的经典问题上:既然惯例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规则,那么惯例的约束力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
实质上,对宪法惯例约束力的探寻,不能停留于惯例的内容,而要聚焦于宪法惯例产生的方式中。我们通常认为,宪法惯例本质上是遵循惯例的各方的一种共识,但更准确地说,惯例应该是双方或各方的一种合意,用戴雪经常用的一个词便是一种“默示协议”(understandings),意即“惯例的实质在于缔约行为产生的一系列相协调的行动与期望。在这种互惠行为与相互克制的体系中,我们可能洞见约束力的基础”。①Joseph Jaconelli,“Do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Bind?”,Cambridge Law Journal64,1:149-176.休谟在《人性论》中把这种情况描写得非常透彻:我发现,让别人占有他的财物对我是有利的,假如他也同样地对待我。他感觉到,调整他的行为对他也同样有利。当这种共同的利益感互相表示出来,并为双方所了解时,便产生了一种适当的决心和行为。这中间虽然没有承诺的介入,但可以恰当地称为我们之间的惯例或协议;因为我们每一方的行为都参照了对方的行为,而且做出那些行为时,也假定对方要作出某种行为。两个人开船划桨,是依据一种协议或惯例行事的,虽然他们彼此从未达成任何承诺。关于财务占有稳定性的规则虽说是逐渐出现的,并且经历了缓慢的进程,通过我们一再体验到破坏该规则带来的不便,才获得效力,但不能据此否定它起源于人类惯例。②[英]休谟著:《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30页。译文有改动。
休谟的观点简要归纳就是,一方接受宪法惯例加诸的限制的同时,希望并期待相关的另一方也接受同样的限制。如果借用合同法中的术语来说,就是那些想从对方契约义务的履行中获利的人,必须自身也接受该契约所加诸的负担。这就是宪法惯例义务的基础。
五、结语
按照戴雪的说法,宪法惯例主要是规范遗留下来的国王特权。王权的存在要早于下院权力。自诺曼征服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王权其实具有主权的诸多特征。“特权”一词是用来称谓国王原初权力部分被剥夺之后手中依然留有的那份权力。也就是说,用来称谓国王随时都掌控于手中的残存下来的裁量权(开始由国王本人行使,后来由“国王的臣仆”即内阁大臣行使)。我们还可以断定,宪法惯例主要是一些规定特权应如何行使以及按何种精神行使的规范。换句话说,对于可根据君主特权依法作出的诸如宣布战争与和平之类的行为,究竟应该如何行使,取决于宪法惯例的要求。
简单地说,当主权者由国王变成“王在议会”之后,国王的大部分特权问题得以解决,但是国王手中仍然残留大量特权(在性质上等于裁量权),对这些自由裁量权的调整,构成宪法惯例的主要内容。①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英国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国王特权?这就涉及宪法典或立宪时刻问题。按照波格丹诺的说法,“英国仍然是不成文宪法,主要是因为从来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宪法时刻’,并且,这是因为联合王国的核心地带——英格兰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感觉。几乎不可能找出一个固定的日期,标志着英格兰开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参见[英]波格丹诺著:《新英国宪法》,李松锋译,李树忠校,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如果英国历史上或将来出现一个立宪时刻,换言之,出现一个制定宪法典的机会,完全可以推测,目前由宪法惯例调整的规范,会被整合进成文宪法中,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博格丹诺在讨论英国未来的宪法典时,有大量的篇幅在讨论宪法惯例问题。参见[英]波格丹诺著:《新英国宪法》,李松锋译,李树忠校,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9章。在这个意义上,惯例的产生一开始就依附于大量的成文的、明确的宪法性法律基础之上。因此较之法律,惯例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而且惯例主要也是一种科予义务型的规则(本来的讨论也主要是从科予义务型的规则角度来进行的)。
宪法惯例规范本质上类似于一种默示契约的规范,但由于没有一个中立的裁判机构对是否违反宪法惯例进行裁断,所以宪法惯例就其实质而言,需要“自我监督实施”。这就对政治行为人,具体而言,对各党派的政治家提出了较高要求,他们在政治行动中,必须具有非常清醒的自我意识和政治德性: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正在促进一项社会规则的形成,并努力去维持这项规则的存在。当然,这并非一个单纯的自律问题,因为一方的举动,必然会影响另一方的行为:我们之间虽然没有明确的承诺或协议,但我恰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其前提是希望你也恰当履行相应的义务;否则,惯例规则便不复存在。
∗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得到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宪法惯例规范研究》(14XFX016)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