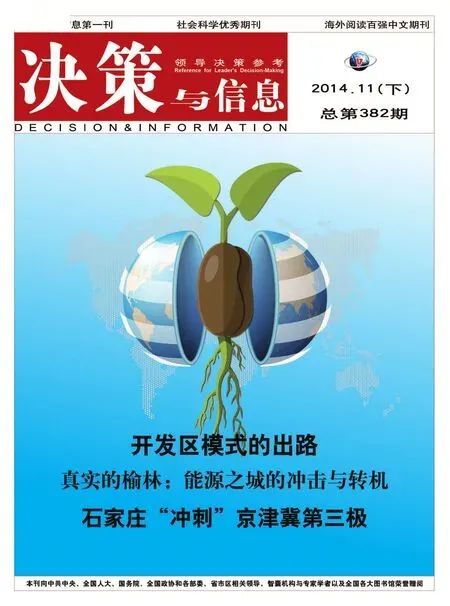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探讨
2014-12-13卢升鸿
卢升鸿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430079
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探讨
卢升鸿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430079
《公司法》虽然明文规定了社会责任承担的条款,但是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学者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对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是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存在争议,这就造成我们无法对《公司法》的条文的内涵进行正确的理解,也无法确定该条文是否具有强制的效力,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公司社会责任;道德义务;法律义务;强制性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
所谓公司社会责任,指的是“公司不仅对股东负有责任,而且应对股东之外的雇员、债权人、供应商、客户、社区以及公共利益负有责任”。美国学界的认识是: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董事作为公司各类利害关系人的信托受托人,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以履行公司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显然“股东之外的雇员、债权人、供应商、客户、社区以及公共利益”以及“员工及家人、社区甚至社会的整体”等概念主要是和“利益相关者”相联系或是指向这一概念的,另外一些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还提及这种类型的责任还包括保护自然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内容。
然而,何为“利益相关者”则是值得予以明确化的概念范畴。最宽泛的解释是能够影响公司目标实现的以及能够被公司实现目标的行为所影响的所有个人和群体。但是概念界定得过于宽泛则被用来指称的范围可能变得漫无边际,有可能会将公司其他类型的责任也划归为公司社会责任之中,使得“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逐步变成一个口袋性质的定义,从而逐渐模糊这一概念的真正内涵甚至是退化概念的核心所求。
因为《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做了规定,所以有学者就认为“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已在我国获得了强行法上的依据”,笔者认为,不能仅仅依据法律条文明文予以规定了就认为是强行法的规定,还必须具体分析。
笔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中的“责任”并非通常意义上我们所指称的“责任”。在通常意义上,责任指的就是法律责任,即“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坏予以赔偿、强制履行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而在这里公司社会责任其实更多地指的是公司应当承当的社会义务,而不是违反了该义务所要承当的不利后果,这种后果其实是公司违反这种“社会义务”的后果,也就是公司违反“社会责任”的责任。
二、法律责任抑或道德责任
《公司法》第5条1款规定公司要承担社会责任,对于这一义务是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不无争议。其实,国外的研究也曾经历过道德论和法律论的争议和认识上的演变。“美国学者早期对公司社会责任定义的讨论侧重于道德伦理的层次,之后转向法律层次。”而对我们国家来说,由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还是比较新的事物,所以虽然《公司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其予以了规定,但是由于缺少实施细则,所以很难在实践中得以落实,尤其在现实的中国更是如此,更多地像是口号性和宣示性的规定,连作为公司法的基本原则都比较勉强。
在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相关规定究竟属于法律上的责任还是道德上的责任,学者间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观点。而且即使认定公司社会责任为法律责任,学者对《公司法》第5条是否可以作为一项裁判规范也有不同的意见,有观点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条款只是一项法律原则,不是裁判规范”,也有学者撰文阐释公司法的这一规定虽然是关于公司社会责任承担的原则规定,但是却既是裁判规范,又是行为规范。在我国法学界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以下争议:
第一,学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在认识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有学者通过“分析道德化社会责任在伦理基础上和经济效益上与公司法基本理念的冲突”,进而“可以得出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公司社会责任概念即法律化的社会责任概念”。也有学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一种柔性社会义务,属于伦理层次,不能作为法律责任强制实施”。还有观点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既包括法律性质的责任,又包括道德层面的责任。可以这样说,目前我国商法学界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第二,学者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有分歧。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我国学者意见不一,认识也不一。公司社会责任是一个外来的概念,最初起源于美国,我国引进该概念后引发学界讨论。有学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还有学者将公司社会责任界定为“公司应对股东这一利益群体以外的,与公司发生各种联系的其他相关利益群体和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负有的一定责任。”
第三,学者对于公司社会责任具体包含的内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为不同的学者对于公司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所以对于公司社会责任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也没能形成一致的认定。这是由于学者对于社会责任是什么的不同理解致使其对公司社会责任包含内容的不同理解。刘俊海教授将社会责任的内容设定为保护“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等”。
随着我国公司法学界对于公司法社会责任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学界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逐步深入,相应的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有学者从中国的传统道德和独特的道德环境入手,分析中国历史传统形成的道德观念对于公司社会责任所能提供的道德支撑,试图揭示公司社会责任的道德义务性,并论证建构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及其实现路径的“本土资源”。“公司社会责任”是一个外来概念,国内法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略显不足,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问题论证不够充分。
三、公司社会责任内容的实证考察
对于企业或者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不同的学者似乎有不太相同的认识,可以说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范围大小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很难有完全相同的划定。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我国《公司法》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有地方的规范性文件如《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则有相关的规定,该指引规定了企业社会责任是指银行业机构对其股东、员工、金融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该指引所称的“利益相关者”主要的是指股东、员工、金融消费者、周围社区人员等。另外《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规定了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求中央企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利益相关者和环境负责,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协调统一。”
不同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界定大小不一,但大体上都包括了“改善劳工工作和生存状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针对社区的义务”以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被纳入到社会责任中的责任,大致分为两类:“法律明确规定的责任”和“法律予以倡导性规定的责任”,前者就是法律责任,后者指的是道德责任。前者如针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责任,在我国就有《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再如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责任有《消费者权益保护费》、《产品质量法》等法律的规定,一方面把这些“责任”认定为“公司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又说“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新概念,是“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新事物”是否有矛盾,这种认定是否合适都不无疑问。另外一些所谓的“责任”更多的是倡导性的规定,这类义务只视作道义的义务。因为无论是刑法还是行政上的处罚,以及民商事的赔偿都必须以法律有明确规定为前提。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社会责任”也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没有强制执行力。
四、结论
分析判断公司社会责任到底是法律责任还是道德责任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公司社会责任到底包括什么内容。第二,公司社会责任的不履行是否会带来强制性的后果。
法律与道德在概念上看似是清晰的,但是两者并没有切实地在各自的界限和范围内发挥影响,而这将给我们的司法实践造成重大影响。道德过分侵入法律的势力范围,法律干涉不道德但是没有违反法律的行为,这些都是造成法律道德模糊的重要原因,更要值得警惕的是不正当的法律干涉可能借助道德的外衣作为掩护,实施侵害法律主体权利的行为。笔者认为,应当明确法律和道德各自的调整范围,法律不应该干预道德范畴的行为,法律只调整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我们的实际情况是道德过多的切入到法律的领域内。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对于道德的要求非常重视,但是却缺乏了依法律治理的传统。而这种不明确性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在公司社会责任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和研究工作。
实际上道德和法律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工具,都可以在各自领域内发挥功能。因此,需要重视制度的设计,以期各种社会规则都能有用武之地。
认清这点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并认清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和理清其具体内容是有帮助的。
《公司法》虽然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强调,但只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发出了一个道德号召,并未设定一项真正的“社会义务”,更谈不上所谓的“法律责任”。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义务是有其特定的法律规则结构的,也就是“假设-处理-制裁”或者类似的结构,但是《公司法》上的“公司社会责任条款”显然不具备这样一种完整的结构,这种条款的效力在我们看来就类似于“公民看到火情要及时向火警做出报告”之类的“倡导性条款”,无法构成真正的“法律义务”。我们主张不要让类似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条款和所谓的“法律责任”降临到司法实践中,至少是目前的司法实践。
有些研究人员抱怨“在公司实践中,社会责任却像‘无牙的老虎’——虽形似威猛,却对公司具体行动缺乏有效控制,尤其是未对公司微观商业决策形成有效的预先约束。竞相发布的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异变为一种新型的企业广告”。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责任也只能作为“无牙的老虎”来发挥其作用,至少不应该发挥超越能力范围的作用。《公司法》的规定无法消除学者间在这一问题研究上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和争议,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地进行研究和探讨。
[1]史际春,肖竹,冯辉.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义务、道德责任及其他[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2]李建伟.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与实现机制建构——以董事的信义义务为视角[J].清华法学,2010年第2期.
[3]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第1版.
[4]孙磊.我国环境警察制度构建研究[D].黑龙江:黑龙江大学,2010.
[5]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6]周友苏,宁全红.公司社会责任本土资源考察[J].北方法学,2010.1.
[7](台)杨政学.企业伦理——伦理教育与社会责任[M].台北:全华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7月第2版.
[8]罗培新.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司法裁判困境及若干解决思路[J].法学,2007年第12期.
[9]杰里米·边沁.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M].程立显,宇文利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10]朱明月.公司社会责任之反思[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1]赵万一,朱明月.伦理责任抑或法律责任——对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重新审视[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2]蒋大兴.公司社会责任如何成为“有牙的老虎”—— 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之设计[J].清华法学,2009年第4期.
卢升鸿:出生年:1986年,性别:男,籍贯:广东省揭阳市,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12级),研究方向:经济法学,单位名称:华中师范大学,所在城市:武汉,邮编: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