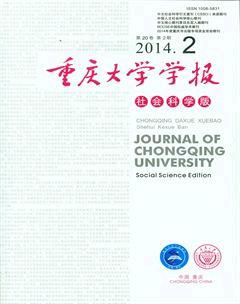社会学视野下域外少年司法社会控制的路径分析
2014-12-05侯东亮
侯东亮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河南郑州 450002)
回首少年司法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其主线具体表现为在福利和惩罚之间钟摆式的往复震荡,而钟摆的中点指向的是社会控制的考量。无论域外各国采取何种模式处遇少年触法者,以社会学为进路的研究更能兼顾或满足少年问题本质,因为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构需要考量“社会需求或其他政经制度等因素影响,少年司法在刑事和福利的两极化基础理念间调整其对策”[1]279。
一、少年司法中社会控制概念的引入
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从社会学法学的视角关注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在他看来,法律秩序就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通过法律实现权力行使的组织和系统化,从而达到社会有序化目标的社会控制过程。换言之,“法律是最显著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2]10-26。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针对19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大变迁时期的诸多问题,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的激增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在此背景下,罗斯认为社会藉由社会控制这一新的社会机制维持原有的社会秩序,并通过社会控制整合社会力量才能达致一个理性的社会。罗斯认为社会控制是一种民主与理性的控制,不同于过去所谓的强权压制型的控制,而是通过诸多的社会制度诸如信仰、法律、教育、习惯、社会暗示、宗教和艺术等手段维系社会的整体性[3]68-228。
美国犯罪学家赫希(Travis Hirschi)接受了涂尔干的观点,把犯罪或偏差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社会控制力太弱的缘故,并提出了人与社会联结的四个社会联结键(social bond)理论。在他看来,少年犯罪原因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少年犯罪人个体控制机制断裂或失灵,二是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社会控制建立在经验共识的基础上人类作出的政治选择。不断涌现的少年犯罪恰恰体现了社会控制机能的缺乏。刑事司法作为一个社会领域,从内在属性而言,刑事司法要在正当程序、人权保障和责任承担之间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从社会外部环境和政策而言,各个国家在犯罪和惩罚、社会福利等认识方面存在着差异。从文化背景分析,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法律文化深刻根植于不同国家精神体系之中。面对城市化、工业化、贫穷、少年犯罪浪潮等诸多社会问题,不同国家的政策选择更趋多样化。加之,青少年触法行为产生原因的复杂性,达致社会控制的目的势必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反映到司法领域,其内在地呈现出通过福利、惩罚或社会机构协作等多种途径教导、说服或规训少年触法者。
二、社会控制的不同路径
在法社会学领域研究颇有建树的唐纳德.J.布莱克教授认为,除了法律本身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控制”之外,还有其他的多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并且在它们之间法律的量的变化与其他的社会控制的量的变化呈现出反比关系。社会控制是社会生活的标准面貌,或者说是对社会越轨行为以及人们对社会越轨行为作出反应的行为的定义。正式的社会控制一般适用于较大的社会事件,正式控制的强制性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者法律直接授权。但在实践中很难在正式的社会控制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适用范围,而很多的矛盾冲突的解决的形式表现为正式的社会控制机构凭借非正式的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人们对社会越轨行为作出的反应主要包括四种社会控制:刑事控制、赔偿控制、治疗控制和和解控制[4]2-8。
(一)通过福利的少年控制
1.英美福利原型[1]280-298下的少年控制
“所有的社会控制应有助于人类福利”[3]317,总体说来,从英美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直至20世纪60年代,在国家亲权思想和个别化思想主导下,少年司法制度以保护教养为目的防范少年犯罪或反社会的行为。由此可体现出少年司法的保护、福利和教育的特征,虽历经数十年,但基本没有脱离福利原型模式。少年法院凭借公权力的运作维护和增进少年福利,为少年触法者创造积极的教育成长环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少年法庭往往被列入社会福利机构的范围,多数少年法院变成了社会福利工作者的活动领域[5]62-63。也可以说,在此福利原型的模式下,少年法制的发展在于“拯救我们的孩子”,在这种少年保护的理念下保障少年能够得到适当的保护教育。但从另一角度而言,这种从物质和精神角度关怀误入歧途的孩子的措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对无人抚养、被遗弃或被虐待儿童少年的控制,从而排除儿童、少年的触法行为的可能性。简言之,社会控制体现了社会制度安排的社会担当,社会福利施加于特定的人群,比如少年触法者,其功能就在于抚慰处于弱势地位的阶层从而防止社会动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在少年法院运动所倡导的思想浸润下,美国少年司法福利化程度达到了巅峰,福利化社会控制的机制才得以创建。1899年少年法院法规定的少年司法干预的目的是康复而不是惩罚。为体现这一理念,美国建立了管护制度(probation)。该法第6条规定少年法院有权选任管护人,被选任为管护人者其身份属于少年法院的职员。管护人同时还具有四项职责:一是根据少年法院的要求,对触法少年进行调查;二是在案件审理时代表少年利益出席法庭;三是根据法官要求向法官提供情况和帮助;四是按照法院指示在审理前或审理后负责照管少年。在延期审理的情况下,管护人负责照管触法少年,亦有权准许少年在家管护或者经少年法庭授权安置触法少年于适当家庭,孩子应当定期向管护人汇报情况;法庭有权把孩子交由教养学校或工艺劳作学校[5]60-61。管护制度在于凭借大量的社会福利机构的参与创制一个中间措施,管护人为代表的社会福利机构的介入取代了传统的检察官或律师的身影。
在少年法院的管辖权方面,16岁以下的少年触法行为(delinquency)不被视为犯罪(crime),少年触法和少年被忽视或被虐待事件的管辖权均由福利趋向的少年法庭享有。只有特殊的暴力少年或严重的少年犯罪才由刑事法庭审理。《少年法院法》第12条规定了少年教养机构设置代理人的问题,代理人负责调查从教养机构中假释少年的家庭情况,以便向法院报告该家庭对孩子是否合适。代理人还负责协助从少年教养机构释放或假释的孩子寻找合适的就业机会,同时还应当负责这些孩子在假释期间的监督[6]88-89。由此可见,少年法院甚至演变成为社会福利工作机构,其实质目的在于通过社会福利机构强化亲权监护的功能,从而完成了对少年触法者的控制。
2.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下的少年控制
近年来,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赢得了世人的赞誉和钦佩,社会稳定、消除贫困、收入相对平等和相对较少暴力犯罪,其各种福利国家机构运行也取得瞩目的成就。究其原因,福利模式下的社会政策建构了国家富强的基础。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福利模式的理念是基于集体福祉的公共责任和通过社会权利的机构化从而使得福利成为每一个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同时,社会保障制度起到了“社会减震器”的功能,它有效地防止经济危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伤害,并且能够保障其免受刑事司法的伤害[7]。
第一,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四国监禁率和犯罪率比较。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福利国家的模式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社会政策,这种社会政策的优势在于能够取得社会平等和社会公众信任,逐步减少惩罚的刑事政策,使之能够有可能发展出监禁刑的替代措施。从而能够减少政治方面的干预,消弭刑事政策严罚的趋向。研究表明,监禁率高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体现国家犯罪状况,但是,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也即是说,监禁率的高低和刑罚政策的严重程度、福利提供的范围、收入的不平等、政治结构和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8]。
结合图1所示,从整体上看,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四国1950-2005年犯罪率变化情况和监禁率的变化情况呈现出相互背离的趋势,它们的波动更多应当体现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错作用[9]179-181。半个世纪以来,瑞典、挪威和丹麦的监禁率都维持在40~70人/百万人口的水平。而芬兰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芬兰的监禁率是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的四倍左右。20世纪70年代的芬兰,监禁率仍然维持在120人/十万人口的监禁比例,其比例仍然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最高的。时间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并且芬兰1990年的青少年和成年人的监禁率出现了历史最低。

图1 1950-2005年北欧四国监禁率和犯罪率图
芬兰的犯罪率由1950年每10万人中将近2 000人的比例一路攀升,到21世纪的开局几年,犯罪率基本维持在7 000人/十万人口的比例。而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犯罪率整体的趋势呈现出上升通道,瑞典和丹麦两国的犯罪率在1991年分别到达历史较高点的11 000人/十万人口和10 000人/十万人口的犯罪比例。
其实,从整体而言,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有着相似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面临着相似的犯罪率的变化趋势,但各国之间采取了不同的刑事政策,各国在监禁率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尤其对芬兰而言,监禁率自1950年以来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与之相反,芬兰的犯罪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上呈现出上升状态。对芬兰这一监禁率和犯罪率整体变化趋势相互背离的态势,印证了犯罪学中的有关理论,犯罪和对犯罪人的监禁是彼此独立的两个问题,它们的变化趋势反映了自身的规律。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德国法学家李斯特一语道出了社会政策和刑事政策的关系。作为社会政策的福利政策和刑事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通过监禁措施将犯罪人予以控制抑或是通过福利的手段支持、矫治犯罪人同样都能够达到相同的社会效果。欧洲国家富有福利政策的历史,目前,欧洲国家日益吸收并发展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福利制度。就目前的发展趋势而言,北欧福利国家依然通过高就业和低贫困保持着其广泛的福利政策[10]。换言之,在福利国家,由于福利的投入,严重的犯罪却较少出现,犯罪率呈现较低态势,对犯罪嫌疑人适用监禁措施也表现得较为克制。
我们以社会福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指标,可以得出社会福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监禁率之间的反比例关系①芬兰犯罪学家Tapio Lappi-seppälä在其《 Trust,Welfare and Political Economy:Cros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penal severity》一文中的观点。他还通过分析得出收入不平等和监禁率之间的关系在1987年其相关性几乎为零,但在此后的时间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强。。瑞典、芬兰、丹麦等国国内生产总值在社会福利部门的投入高而监禁率低[7]。显然,在较高的福利水平背后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福利事业投入的加大,也即是说,社会随着国家对学校、家庭和社会福利机构比监狱等监禁场所投入的加大将会变得更为完善。如此一来,社会福利法在对于触法青少年采取的保护措施将会得到更广泛的适用,而适用监禁措施的可能被减少到最低的限度(表1)。

表1 2005-2006年被监禁的少年(15~17岁)在所有被监禁的犯罪人中所占比例
第二,社会福利机构主导少年司法。1982年瑞典社会福利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变早期所采取的镇压和社会保护的思想而采取基于青少年需要的思想。其反映了一直以来学术界与实务界存在的一种争论[11]92:是采取以福利为导向的少年司法,还是采取以正式刑事司法为导向控制少年犯罪、减少少年犯罪?在1902年,瑞典通过立法赋予社会福利机构提供处遇替代刑罚措施。至此之后,社会福利系统和少年刑事司法系统的合作共同承担了少年违法行为的控制。瑞典1998年社会福利法(Social Services Act 1998)和2003年强制照管法(Compulsory Care Act 2003)的目标是在于对受虐待或被遗弃儿童以及少年犯罪和其他社会问题提供保护、帮助和支持。但在此语境下的社会福利途径主要体现以照管为主导的少年控制,主要体现在当地社会福利委员会根据社会福利法的规定对儿童和家庭采取照管措施。简言之,瑞典少年司法福利的模式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把15至17岁的少年触法者交由社会福利体系处理。
芬兰的儿童保护工作与瑞典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芬兰儿童福利工作通过各种以儿童为中心的项目起到干预改善儿童福利的功能。另一方面,芬兰少年司法系统既包括作为市政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儿童保护系统又包括司法系统。通过刑事责任年龄立法规定,15岁以下儿童仅可以适用管护和保护措施。而18周岁以前的少年时代,少年被赋予了儿童保护措施来完成对其违法行为或者反社会行为的社会控制。即使对其适用刑事程序也与18周岁至20周岁的青少年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略有不同。同时,管护、照顾未成年人的监管责任主要属于社会福利部门,而不是刑事司法机关。
2004年,为了协调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资源介入儿童福利的的状况,挪威中央政府直接负责儿童福利工作,虽然对于儿童提供必要帮助的基本责任最终必须还是由各市具体负责实施但中央政府牵头负责少年儿童福利工作有利于加强这一正式社会控制机制。另外,根据挪威《儿童福利法》规定,各个市应当设立一个儿童福利管理部门,由该部门负责人代表其履行法定的义务。在实践中,儿童福利部门多体现为学校、日托机构、学校心理服务中心和文化娱乐中心等机构的联合。显然,儿童福利机构在给予少年儿童帮助方面注意加强公共机构和自发组织的合作,从而使得少年儿童的利益得到保障。也即是说,少年儿童的成长对于社会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部门都有责任在少年儿童的教育和培养阶段发挥作用,他们应当密切配合为处于困境中的儿童提供福利服务和加强服务措施。社会资源的投入以及社会福利部门处理少年儿童的案件的增加也有力地证明了社会福利部门的预防性工作和帮助性措施在少年儿童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中,社会福利措施主要包括预防措施和事后的帮助措施[12]183-193:儿童福利服务首先应当维护家庭的完整,预防措施可以减少福利机构安置少年儿童的数量,使得家庭发挥其在教育和引导少年儿童方面的基础作用,从而有效地预防被忽视、被虐待少年儿童以及其违法行为;在事后的帮助措施中主要体现为自愿安置和非自愿安置。根据《儿童福利法》的规定,自愿安置是指由于父母生病或其他原因,儿童暂时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情况下,父母可以经与儿童福利中心商议后自愿作出书面决定,将少年安置于家庭之外。但当少年儿童在被虐待、被忽视或者无法接受适当治疗的情况下也可经过郡社会福利委员会发布照管令对少年实施非自愿的家外安置。这种非自愿的安置措施主要包括寄养措施和居住照管。根据法律的规定,寄养家庭的选择首先应当在家庭内部或家庭的社会关系中遴选。郡社会福利委员会的寄养令在作出两年后应当重新审查儿童返还自己家庭的可能性。
与刑事司法处理少年的数量相比,福利机构对少年安置的数量上占了绝大部分,从而使得福利机构在处理少年违法或福利问题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违法少年违法或需要帮助的少年绝大部分处在社会福利部门的控制之下。近年来,虽然社会福利部门安置违法少年的作用受到了质疑,因为有人提出社会福利部门的广泛运用隔离了被安置少年的正常的社会生活,并使其反倒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适应人为设计的环境,结果导致了攻击性行为的上升。但整体而言,被安置少年在社会福利机构提供的服务中能够受到益处,不同安置措施的作用能够满足不同被安置少年的需要。
(二)通过惩罚的少年控制
正如庞德所言:“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在当前的社会中,我们主要依靠的是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我们力图通过有秩序的和系统的适应能力,来调整和安排行为。”[2]10就世界范围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起依靠惩罚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究其原因,这种变化是源于社会、经济领域问题层出不穷,犯罪和安全已经成为社会难题,尤其是近年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社会“反恐”政策的实施,整个社会面临着社会控制的危机。一般而言,惩罚作为社会控制的有力支撑力量,支持着社会控制机制的建构,也有力防止“逃逸”社会控制的可能。但少年司法存在着逐步被泛政治化的趋向,“满足少年需要”的原则也受到侵蚀转而向“社会安全”方向转变。美国、英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在少年法的研究方面几乎都一边倒地趋向于惩罚思想的回归。英国儿童法律中心及少年国际保护运动报告的立足点在于“世界各国的少年司法政策压倒性采用了惩罚性的思想”[13],也即是说其侵蚀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思想而转而对少年违法者采取强硬的态度。但这此严罚思想的社会背景之下,惩罚应当作为一种功能体系的综合体,其模式化和组织化的特性融合了包括法律、家庭、教育、宗教等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使得各种社会力量整合为回应社会需求的社会制度。
1.监禁率的变化
在福柯看来,20世纪的人类社会没有沿着启蒙运动的理念兑现承诺,而是在社会趋于复杂的情势下发展了更为复杂的社会控制机制。这些复杂的社会控制机制在表面上表现为法律、政府、警察、军队、学校、医院等强制性的体制。于是,社会演变为“景观社会”[14]219-256,公民个人生活在一个超级全景监狱,先进的电子技术和大众传媒发展成了现代的监视系统。犯罪学家科恩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社会控制的视觉》一书,也敏锐地洞察出社会控制机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的变化。科恩提出中央集权和官僚机构在控制系统中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伴随着专业人员和专家的不断参与导致社会控制的影响力增强,不拘泥于形式主义的控制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社会控制的能力和范围[15]。于是,大量非监禁的替代措施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与监禁刑罚控制机制复合控制之网,非正式的社区控制和监禁刑罚等正式的社会控制使得社会控制的机制无处不在,国家强调社会秩序的问题,社会控制的欲望和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监狱和警察等国家强制力量也得到了发展,而非正式的社区控制或非监禁的替代措施所呈现出另一种社会控制的形式,具体表现为社会机构参与到社会控制。
20世纪主流的犯罪学家和大多数的政治家认为福利国家会有效遏制犯罪和惩罚的需求。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犯罪率居高不下严重侵蚀着公众对现有司法模式的信心。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大规模监禁率的趋势越来越表现为对福利的限制。在美国,少年触法者的监禁率在20世纪90年代增加了43%,在2006年对少年触法者的监禁人数已经达到105 600人。截至2005年,仍有18个州继续允许对16~17岁严重的少年触法者适用死刑。大多数的州仍然保留对严重的少年触法者保留终身监禁不得适用死刑的权力。但美国少年司法也面临着种族问题的困境。以2005年为例,2 225名被监禁的少年中有60%属于非洲裔美国人。
相对于1899年少年法院创设之初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思想,当下的美国少年司法系统更加关注对少年触法者的惩罚,越来越多的少年触法者被转送到成人刑事法院。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美国15岁以下的儿童因持枪凶杀案件而被害的死亡率是其他国家的16倍。不可否认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惩罚思想的回归影响范围至深,但各州面临的不同的经济、道德压力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英国尤其是英格兰、威尔士,自1993年以来青少年安全中心拘留的儿童数量已经增加了一倍。在2002年7月,英国政府公布了“所有人的正义”(Justice for All)的白皮书,它确定了英国在三个领域改革导向[16]:一是根据被害人利益调整刑事司法制度之需要;二是要为检察官、警察提供更多的使犯罪接受审判的途径;三是要将对反社会行为、严重毒品和暴力犯罪采取严厉行动。从而使得刑事司法领域体现为犯罪人接受审判、司法效率的提高和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平衡。在此思想的影响下,西欧国家过去近30年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由福利干预模式向成人刑事司法靠拢,而凭借成人刑事司法程序完成对少年控制,其必然转而追求程序正义。诚如荣格尔-塔斯教授(Junger-Tas)所说:许多国家的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采取了更为压制的措施,但效果并不一定有效[17].513-517。
在世界范围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研究中心对青少年监禁率的统计数字堪称最准确的青少年监禁比例②实践中监禁率的研究存在着困境:一是各国对少年触法者被监禁的数据公开程度存在着差异;二是各国法律对儿童、少年、青少年的年龄规定不同;三是各国统计方法和统计工具不统一。。许多国家存在着对青少年适用措施的倾向。美国对青少年触法行为转而实行严罚的思想,其相应地大量适用管护措施。欧洲国家如英格兰、威尔士、德国等也实行严罚的政策,具体实践表现为广泛适用管护对青少年违法行为实行控制。通常情况下,青少年监禁的统计数据明显排除了那些基于福利或保护的思想而予以户外管护的青少年,比如,芬兰和瑞典广泛存在的拘留中心、精神治疗室、训练学校、社区之家等可以在违背父母意愿的情况下对青少年适用管护措施。于是,芬兰堪称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最低的少年羁押率,但在其背后其实隐藏着基于福利系统而对青少年广泛采取适用社区之家、精神治疗室等管护措施[18]。从另一角度而言,芬兰、瑞典的福利系统内完成了对青少年违法行为的控制,而不用诉诸刑事法律或者刑事羁押手段。
长期以来,困扰少年司法的议题是对少年犯罪采取“福利”抑或是采取“刑事犯罪”的态度。一系列的研究也强化了这一疑问:羁押率是否能够或者应当成为检测惩罚的因素。对于监禁率和犯罪率的关系,欧洲委员会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监禁率的高低并不能必然决定犯罪率高低,反之亦然。不同国家对于少年犯罪率增长的态度更多是一种主权国家在处理国家事务时的政治选择和社会公众对犯罪率的交错反应,反映到司法领域就体现为国家在处理青少年犯罪问题上的政策和模式的选择。汉斯·冯·霍费尔(Hanns Von Hofer)教授在2003年对芬兰、瑞典和荷兰的监禁率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作为北欧的三个国家,芬兰、瑞典和荷兰具有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相似的犯罪趋势。但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2000年时三个国家的监禁率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体现了国家具体的政治选择:面对少年犯罪的增加各个国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19]。
2.刑罚福利主义的思想
大卫·嘎兰德(David Garland)作为当今最杰出的犯罪学家之一,其提出“刑罚福利主义”的思想,该理论提出的背景是当代西方社会对古典犯罪学的复兴和21世纪不同法学理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认为惩罚的措施应当作为康复需要的干预,而不是消极的报复性惩罚,其作为一种新的严罚思想的体现,其实质仍然是对犯罪者的社会控制。监禁的功能一方面体现为对犯罪人的惩罚和矫正,从另一方面来看,监禁能够在物理上起到阻隔空间的作用,通过监禁从而把犯罪人与社会相对隔离。根据康复思想,监禁的适用只能是万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从而最低限度地减少监禁对社会安全和个人正常生活的干预,及早使得被监禁人融入社会。欧洲社会保持着福利国家的传统,随着其重点加强福利系统的投入,监禁率相应地也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如今的福利模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主要的体现是保障措施的加强和监禁率的增加。于是“安全福利国家”似乎是更为准确的词汇。
大卫·嘎兰德(David Garland)认为,后现代刑罚的主要特点体现为犯罪控制处于精神分裂的复杂境地。具体而言,国家承担着多重的社会角色——福利和惩罚的代理人:既是刑罚革新的力量又是严罚思想的代理人,其一方面承担着犯罪控制的责任,同时又承担着对犯罪人照管的义务。由此可见,英美后现代的社会控制策略建构在犯罪和惩罚、福利和安全基础之上,是整合不同要素连锁结构的新策略。但是,与二战后的刑事政策形成宣明对比的是,目前的刑事政策的变化转向凭借社区矫正犯罪、康复违法者、创设不定期刑等独特的方案解决犯罪问题。“并不是犯罪已经变化,而是社会在变化,社会变革的程度已经达到了足以重新建构犯罪学的理论、社会公共政策和犯罪文化的意义”[20]28-48。也即是说,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促使我们倚重社会控制特别是犯罪控制,因为国家、企业和个人在试图解决多变的经济和文化问题方面势必涉及到广泛的社会控制和个人自由扩张的结合。
大卫·嘎兰德(David Garland)认为,新的犯罪控制政策作为经济社会变迁的重要结果,目前更多体现为这种政策的工具性价值。在实践中,这一政策的选择表现为在社区合作的适应性控制策略和国家对罪犯的强制控制策略的选择。具体而言,当犯罪率居高不下成为常态时,康复的思想就会受到质疑,而且刑罚和福利思想的综合也难以保障公众免于犯罪风险[20]141。大卫·嘎兰德认为,与刑罚福利主义的思想相比,当代犯罪控制政策能够通过惩罚性制裁和形式正义、受害者的回归和犯罪问题的政治化予以表现。
(三)通过协作的少年控制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惩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存在着“弥散性”。以美国少年司法为例,少年感化院适用相同的规训手段来对待少年触法者和困境少年,而没有在这一制度设计中给予区别对待。“所谓的治疗和矫治,仍然是建立在传统刑罚的基础上,其对罪犯的处遇,依然与昔日之刑罚并无二致”[21]79。在矫正论者看来,犯罪是一种疾病,罪犯是病人,惩罚体现了治疗的过程和手段。于是,“教育改造”、“社会矫正”、“刑罚替代措施”、“处遇”、“社会复归”等一系列词汇不断出现。从犯罪学的视野而言,其怀着新的目的性和合理性,也即是追求通过社会手段获得犯罪控制的目的颠覆了传统惩罚的价值合理性。也正是这种弥散性的特点模糊了刑事惩罚、家庭教育、社会福利的界限,也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技术性的手段。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李茂生在1997年提出了“同心圆结构”[22]140-142理论。“同心圆结构”建构出不同层面的空间,这些不同层面的空间构筑了围绕少年的外部社会环境和相对独立运作的少年司法系统。通过建构不同层面的空间为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的介入提供了不同的途径,于是,家庭、学校、社会福利机构和司法机构处于多层次的社会控制之下。“多机构参与,是指由主要的社会机构进行的有计划的、相互协调配合的处理犯罪和社会不良问题的模式。在工业社会中,社会控制的本质问题就是多机构参与”[23]。
1.扩大中的社会控制网络
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社会学方面的理论就是社群主义,其宗旨在于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可资凭借的途径在于强化社会化网络。基于严罚思想下国家主导型的打击犯罪的模式已经在实践领域遭到失败,在社群理论的支持下,犯罪预防领域的政策也作出了调整。国家权力开始分散给社会化组织,由社会化组织建构的分散的社会化网络主导社会控制。英国政府在1984年发布了一份关于犯罪预防的报告,其内容就是确立多机构协作预防犯罪。七年后,英国政府又发布了《内政部犯罪预防常务会议关于“使社区更安全”的报告:地方政府参与多机构协作犯罪预防模式计划》(又称为摩尔根报告),其主导思想是通过强调社区安全,增强社会化的犯罪预防措施,提高多机构之间协调[24]111-116。“邻里守望”、“警民同心”、“街头监督”等单项的行动计划更是鼓励了民众参与,使得社区安全演变成为社会公共行动,使得社会民众和犯罪控制机构之间不断联系和合作,建构了一条严密的控制网络[20]124-127。在英格兰、威尔士,自上而下的YOB和富有专业化、职业化特色的YOT以及一些社会组织的设置,为少年司法模式的建构在组织机构层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标本。其核心在于以YOB为主导的官方机构和以YOT为主导的社会化专业机构相互合作,凝聚国家、社会力量,协调警务部门、社会福利部门、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和一些自愿机构等关键的部门,整合社会资源实现预防少年触法行为。缓刑局的成立以及在同社区的互动关系中监督改造少年犯罪人都体现了英国少年司法协作模式的特点。斯坦利·科恩教授认为,分散化的犯罪预防模式或者其他非制度化的犯罪预防模式在无形中扩展了社会控制的网络,社会控制网络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为监禁措施提供了有力的补充[25]44。犯罪少年只是在扩大的社会控制之网中接受着较监禁措施更为精细的矫治过程,有利于把触法少年置于社会控制之下。
2.控制责任的分担
社会控制的早期表现较为混乱,有权者阶层垄断了立法和司法从而可以凭借通过所谓立法和司法达到犯罪控制的目的,于是,社会控制更多体现为通过严酷刑罚惩罚普通民众。警察组织的出现体现了国家统治的权威,意味着国家专业犯罪控制组织的形成。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社会凸显出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面临着犯罪率激增的情势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国家无法达到有效地完成社会控制的任务。因此,国家开始延伸国家机构的触角将犯罪控制的责任转移到被害人和社会大众,而不是由国家机构垄断[20]124-127。其具体表现为政府致力于非监禁刑的创设,并鼓励使用这些替代的措施。把监狱作为解决越轨行为的一种方式,把社会控制的责任转移给社区承担。各国通过预算加大对少年犯罪控制的投入,鼓励和实施以社区为基础的少年犯罪控制策略。于是,犯罪控制的界限开始模糊并逐渐呈现出去职业化、去专业化的趋势,警察、检察官、法院以及监狱等机构亦非垄断犯罪控制的责任,而产生了社会福利部门,社区参与犯罪控制、担当社会责任的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核心观念在于通过责任的承担,减少犯罪的可能性。
大卫·嘎兰德(David Garland)认为,在19世纪的晚期,刑罚和控制的策略更趋理性化,惩罚褪去了“机构营运者”、“痛苦传达者”的外衣,转向以惩罚、福利对话协商基础上的“现代惩罚”[26]381-384。但这一刑罚和控制策略的理性化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犯罪控制机能的弱化,而是通过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坐标网络的建构,对于越轨者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给予相应处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消逝,其实只不过是改变了国家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形式,转而由各个社会机构间接行使,而在实践效果上却增强了国家在社会控制系统中的力量。这种转变不是凭借主权国家威慑和强力制裁,而是协调、组织其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完成社会控制的任务。于是,犯罪控制责任在此得以分散,其结果是社会控制网的扩张(net-widening)[20]128。透过这种责任分散的思维方式,社会控制更借助于社区预防项目的推行,转变警察等国家机构被动的事后预防的传统方式,转而强化与警察等国家机构的合作致力于事前预防,从而使得少年触法等社会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惩罚和福利贯穿着少年司法演进的历程,呈现出了钟摆式的政策选择。正如许多其他西方福利国家对触法少年处理的发展趋势开始脱离福利途径,转而强调控制、惩罚和报应。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带来了对犯罪行为惩罚的优先权而忽略或牺牲少年需要,进而强调罪责刑相适应和刑事责任的概念,基于犯罪而干预而不是基于对儿童的需要而干预。在近代世界,我们力图通过有秩序的和系统的适应能力调整和安排社会冲突和社会行为。于是,我们开始转变传统上依靠政治组织的强力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机制,通过福利、惩罚和协作路径,实现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社会秩序这一法律基本价值实现的功能。
[1]施慧玲.少年非行防治对策之新福利法制观//家庭、法律、福利国家——现代亲属身份法论文集[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1.
[2]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是法律的任务[M].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E.A.罗斯.社会控制[M].秦志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唐纳德.J.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M].唐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5]康树华,赵可.国外青少年犯罪及对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姚建龙.超越刑事司法——美国少年司法史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7]SONJA SNACKEN.Factors of criminalization:A european comparative approach[EB/OL].[2011-09-20].http//lodel.irevues.inist.fr/crimprev/index.php?id=183.
[8]TAPIO LAPPI0SEPPäLä.Penal policy and prisoner rates in Scandinavia:Cros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penal severity[EB/OL].[2011-11-20].http://helda.helsinki.fi/bitstream/handle/10138/15877/Lappi-Sepp%C3%A4l%C3%A4.pdf?sequence=1.
[9]TAPIO LAPPI0SEPPäLä.Finland:A model of tolerance?//John Munice and Barry Goldson.Comparative Youth Justice[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6.
[10]ESSNER SE,ROSENFELD R.Political constraintof themarketand levels of criminalhomicide:a cross-national application of institutional-anomie theory[J].Society Forces,1997,75(4).
[11]HOLLANDER A,TÄRNFALK M.Juvenile crime and the justice system in Sweden[M]//MALCOLM HILL,ANDREW LOCKYERr.Fred StoneYouth Justice and Child Protection.London: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2006.
[12]贺颖清.福利与权利:挪威儿童福利的法律保障[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13]Children’s Legal Centre//Y Care International.Youth justice in action:Campaign report[R].London:Y Care International,2006.
[1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5]普拉蒂·约翰.批判社会学与刑罚性社会——一些新的社会控制视觉[J].李晓明,译,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3):121-125.
[16]陈光中,郑旭.追求刑事诉讼价值的平衡[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1):41-47.
[17]JUNGER-TAS J.Trends in International Juvenile Justice:What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Josine Junger-Tas and Scott.H.Decker.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Juvenile Justice[R].Netherlands:Springer,2006.
[18]PITTS J,KUULA T.Incarcerating young people:An Anglo-Finnish comparison[J].Youth Justice,2005,5(3).
[19]HANNSVon HOFER.Prison populations as political constructs:The case of Finland[J].Journal of Scandinavian Studies in Criminology and Crime Prevention,2003,4(1).
[20]GARLAND D.The Culture of control: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1]林山田.刑罚学[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3.
[22]黄玉清,林启树,林金铃.对少年触法行为性质分析模式之实务研究[J].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刊,2005.
[23]YONG J.Left realism and the priorties of crime Control//COWELL D,STENSON K.The Politics of Crime Control[M].London:Sage,1991.
[24]戈登·休斯.解读犯罪预防——社会控制、风险与后现代[M].刘晓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25]COHN.visions of social control[M].Cambridge:Polity,1985.
[26]大卫·葛兰.惩罚与现代社会[M].刘宗为,译.北京:商周出版,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