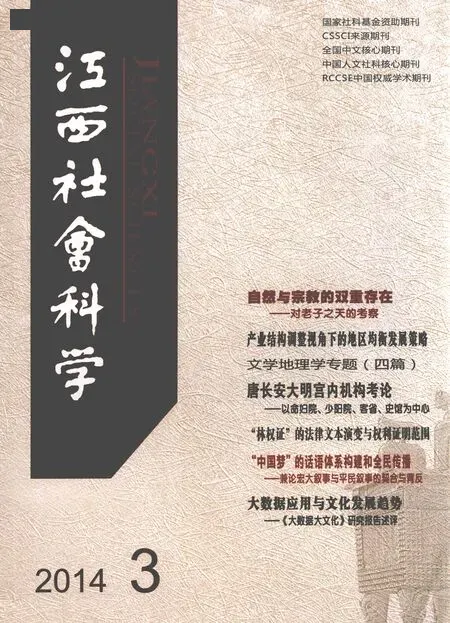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江流儿”及其原型
2014-12-04彭岚嘉孙胜杰
■彭岚嘉 孙胜杰
神话凝聚了民族文化、心理和宇宙、历史意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根”,渗透到文学、音乐、建筑、绘画等各个方面。作家或艺术家的创作往往取自或包含着神话中不断出现的主题、象征和人物。弗莱说:“神话乃是文学构思的一个极端。”[1](P171)神话精神已经渗透到艺术身体的最深处。
弗莱认为“神话即原型”,所谓“原型”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2](P96),是一种典型的、原初性的、反复出现的、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的意象、象征、主题或人物模式。“文艺作品或文化现象中的神话及其模式,与原始意象有着同样的意义和功能,是显现人类深层心理与现实行为的特殊中介,是沟通原始精神与现实情感之间的桥梁。”[3](P114)因此,从原始深层的传统文化中寻求它的当代状态,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是可能而且必要的。通常伟大的文学都会与神话原型和神话观念紧密相关,甚至神话原型和神话观念还会影响或者掌控着文化整体的发展,通过将远古与现实联系起来的原型,可深入发掘出当代文学或文化的潜在意蕴。
一
“江流儿”的神话,多出现在分布广泛的英雄传奇中。如,后稷被弃于寒冰而不死,重生以后成为周人的始祖;徐偃王卵生,被抛弃于水滨,被犬衔起后成为一代人王。藏族的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以及满族始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传说也是一个“江流儿”。另外还有彝族的“夜郎竹王”和“淌来儿”的故事,都是“江流儿”。
《西游记》中的唐僧被看作典型的“江流儿”。他的身世传说有研究者认为其原型应来自于异生神话“漂流婴儿”伊尹。[4]传说伊尹是在河流中靠浮他母亲化作的桑木才存活下来,长大后成为商汤时期的贤臣,受殷人爱戴,死后被尊奉为神人而受祭祀。唐僧也是出生后被放在木板上抛入河流中,被寺院长老救起,赐予他“江流”的名字,法名玄奘。唐僧在寺院中长大,虔心向佛,最终历尽艰险,取得真经,修成正果。
“江流儿”源于古老神话,世代流传。梅列金斯基说:“综观文学领域的神话主义,居于首要地位的观念是确信:原初的神话原型以种种‘面貌’周而复始、循环不已,文学和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以独特的方式更迭递嬗。”[5](P2)作为潜意识层面的“江流儿”原型已经成为一种“种族记忆”留存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并化作一种巨大的心理潜能,影响着人们以后的心理和行为。上自远古神话,下及后世小说,以至民间故事,“江流儿”原型在中国文学史上总是或隐或显地不断“重现”。
“江流儿”故事有固定的模式:孩子出生后,因为种种不得已的理由被抛弃于河流,最后被人捡拾,长大成人后往往成就一番事业等。关于产生“江流儿”故事的原因,很多学者都探讨过,但仍然莫衷一是。胡万川在《中国的江流儿故事》中总结出多个原因:1.古代的试婴习俗;2.人类“生育过程”的象征反映;3.生子礼仪的展示;4.来自上古时期宇宙初创,洪水神话的残存记忆与模仿,以及从心理分析角度认为,是人格中“自我”成长、父子对峙关系的象征等。[6](P237)
“江流儿”故事追根溯源是很困难的,而且从当代文学的角度来探究“江流儿”原型,其问题的重点应该是这一类故事反复出现,在当今的文学中呈现的意义是怎样的。
“江流儿”的神话的核心在于“江流儿”顽强的生命意志和历经苦难的坚毅精神。因为他们从母体脱离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要面对生存的威胁,而且生而孤独,学会面对一切生活苦厄,找寻新的重生命运。伊尹经历世间各种磨难后才从一个奴隶到辅佐商汤的重臣;唐僧取经成功,成为圣僧,途中也经历了无数险阻等。这些人物的性格并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他们身上的坚毅和顽强精神积淀在人类的意识深处,也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故事中的“江流儿”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生,抛弃的原因如何,最后都会成为某一领域的重要的人这一点是相同的。“江流儿”出身的孩子经过一番不平凡的努力成为有成就的“英雄”。“江流儿”原型精神带给我们的是积极向上的精神激励,这种已经植根于民族精神血脉中的集体无意识,在历代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如鲁迅所说的,神话“实为文章之渊源”[7](P12)。
二
原型是过去记忆的复现、回忆,但在不同的时代、地域,原型有着极强的生成力。王一川说:“与其说原型是一种胚胎,不如说原型是子宫,它只是孕育着什么,而不是像胚胎那样预示着什么。被孕育的东西就等同于子宫,它自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和本性。”[8](P144)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原型“既是一种规范,又是一种开放的空地,毋宁说它永远是一片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空地,诗人们耕耘其上可以各得其所”[8](P144)。所以,原型的这种独特的生命力与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现实社会问题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神话作为产生于原始初民的最初的文学形式,在以后的进程中则作为种族记留存于人类的潜意识中,并作为文学创作的灵感积淀。“神话是一种不明显的隐喻的艺术”[1](P171),当文学作品中有神话原型出现时,它要向读者传达的信息不仅仅是作品表层的意思,而是要通过对人类历史文化积淀的翻动来唤起当代人心中悠久、丰富、博大的经验。“在神话中,我们看到的是孤立的文学结构原则,在现实主义那里看到的是同样的结构原则被纳入似乎真实可信的前后联系之中。不过,现实主义的虚构中所出现的神话结构要使人信以为真就会涉及某些技巧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所用的手法则可统一命名为‘置换变形’”[1](P171)。任何传统如果要成为有意义的传统,途径是和当代生活发生联系,传统的活力要依赖当代精神才能被激活,“原型”的意义也只能在这种情境下才能呈现或置换,即原型的置换和意义生成要靠现实的文化力量的推动。
“置换变形”有两种倾向:一方面是“使神话朝着人的方向置换变形”;另一方面是“朝着理想化的方向使内容程式化”[1](P171)。“江流儿”原型在当代的置换变形是朝着人的方向,人们在“江流儿”原型中看到的不再是崇高的英雄,有着“英雄”性格的“江流儿”已经失去往昔崇高而走向平凡沉沦,这就是“江流儿”原型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置换变形。
苏童《河岸》中我的父亲是个“江流儿”。女烈士邓少香最后执行任务遇难后,遗孤被枪杀她的宪兵放到了河边上。婴孩还在箩筐里,本来以为会被好捡拾孩子的船民捡起,可是夜里河上涨起一大片晚潮,冲走了箩筐。“一只漂流的箩筐延续了邓少香的传奇,随波逐流,顺河而下……最后,箩筐漂到河下游马桥镇附近,钻到渔民封老四的渔网里去”。[9](P9)封老四拿过箩筐,发现“在箩筐的底部,一条大鲤鱼用闪亮的脊背顶开了一堆水葫芦,跳起来,跳到河里不见了”,父亲就是“怀抱水草坐在鲤鱼背上的婴孩”。[9](P10)
新中国成立后,封老四活了很多年,他在马桥镇的孤儿院指认了我父亲就是当年他捡到的箩筐中的那个婴孩,这样,马桥镇孤儿院里最脏最讨人嫌的男孩小轩,成了烈士邓少香的儿子。
大家公认库文轩是烈士邓少香的儿子,所以一块革命烈属的红牌子在我家门上挂了很多年,凭着它,父亲当上了油坊镇的书记,住上了镇上条件好的房子,娶到了镇上有美貌有才华的播音员乔丽敏当老婆,过着可以呼风唤雨的令人羡慕的生活。可是这样的好时光并没有过多久,有一年夏天从地区派来了一个神秘的工作组,这其实是一个烈士遗孤鉴定小组,专门调查库文轩的烈士后代的身份。结果,父亲当年的“出身成了悬案”,他“成了来历不明的人”,他需要赎罪,于是带着我“到向阳船队,也许不是下放,不是贬逐,是被归类了”[9](P43)。从此,他们父子俩就在河上生活了十三年,库文轩再也不愿回到岸上。
作为“江流儿”原型的库文轩隐喻着历史的变化,他的形象以及经历印着那个时代的影子,是历史年代的象征。“江流儿”的身份——烈士邓少香的后代,让他有权有势,成了镇上人人羡慕的有成就的人,可以说这是“江流儿”的归宿,成为“英雄”。可是库文轩虽然形式上是一个“江流儿”,但他少了“江流儿”的内容,他并没有经过苦难拼搏,而是凭着上一辈的荣耀,这使得他烈士后代的身份一旦遭到质疑后,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不见,最后回归河流母体时,也只是“英雄”被流放。
另外,库文轩回到河流上生活,最后自绝于岸上世界,这也暗示了当时岸上世界的荒诞。库文轩始终执着于自己的烈士身份,这种执着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观念强加在他身上的,他被历史左右,丧失了正常人的判断力。所以当他的身份被质疑后,他只能选择回归于河流母体,因为岸上母亲 (这里的母亲角色不管是邓少香还是乔丽敏)消失或失散,父亲的灵魂和肉体就会四处游荡,这也暗示出河流对生命的滋养,岸上的荒诞历史对人有着巨大的改变力量,这本身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无奈和逃避。
“英雄”面对权力世界感到彷徨和绝望,权力失去也就意味着一无所有,再辉煌的生活都会成为“空屁”。我是“江流儿”的后代,是一个平凡普通人,面对权力世界更加被动,无法选择地跟随父亲漂泊在河流上。如果父亲“英雄”的一面仅表现在情欲上,“我”连最基本的情欲也受到了压抑,面对岸上的爱情只能默默观望。“江流儿”在当代已经没有英雄的印迹,随着放置作为父亲身份权力象征的纪念碑棋亭变成公路后,父亲的生命也被毁灭。作家对“文革”那个年代的书写是带着一定的批判的,一个思想正常的人生活在不正常的年代,思想也会变得不正常起来。库文轩对烈士身份超常的执着认同,最后宁可不要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这种象征权力的身份,这样的叙述让我们感到时代对人的控制,它的控制力量巨大到足以使正常人失去理智。最后父亲驮着纪念碑跳进河里的行为,刚好印证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和历史特点,这样的批判在文本中虽然不明显,但通过“江流儿”的神话原型隐喻在文本对人对事的书写中。作者通过“江流儿”原型的置换变形,回顾了那一段荒诞的历史,其中也暗含着作者对于历史书写的批判中有反思的态度,给后人以启示、警醒。
通过“江流儿”的形象,作家除了对历史的批判反思,还有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10](P2),在不同的领域谈论现代性,对其含义的理解也不相同。通常来说,它与现代化相关,是一种独特的、非人格化的、物质层面上的、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商业规则的完善、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等内容。换一种说法:“就是现代同过去的断裂:制度的断裂、观念的断裂、生活的断裂、技术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现代之所以是现代的,正是因为它同过去截然不同,它扭断了历史进程并使之往一个新的方向——我们所说的现代的方向发展。”[11](P28)“现代性”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所引发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正如韩少功所说,全球化、一体化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实现现代化和反思现代性这双重的挤压,正在承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各方面的变化和震荡,每个人在这个大漩涡里寻求精神的救助”[12](P213)。黄佩华作为桂西北土生土长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利用其“江流儿”的神话原型来表现对“现代性”的思考。中篇小说《涉过红水》中的巴桑是一个“江流儿”。巴桑的父亲曾经是桂西北有名的地头蛇,虽然担任着保安团长,其实和当地的两股烟匪势力形成三足鼎立。后来因为内奸的出卖,在一场剿灭两股烟匪的战斗中全家被血洗。当时巴桑抱着一截木头滚进了涛声如雷的红河,被河水冲到野猪窝才保住了性命。红河不但救了他的生命,而且还给他带来了家人——他的妻子、儿子和儿媳妇。有一年,巴桑在红河边救回了合社,她因为生过的八个孩子都死了而绝望跳河,被巴桑救起后,两人结合,很快生下了儿子鲁维。鲁维健康长大成人。多年以后,巴桑又在河中救起因家庭遭难而绝望跳河的板央,不久板央嫁给鲁维,生了三个孩子。野猪窝三面环山,一面傍水,一块小小的空地生活着巴桑一家三代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巴桑从年轻的小伙子到年老衰弱的老人,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捞在红河上游被流水冲下来的遇难者的尸体,然后重新命名、埋葬,而且每年都会给亡灵祭祀、修墓。
这样重复的事情,他做了许多年,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听说要修建红河水电站,这一带的河谷和他生活的野猪窝都要被淹没,巴桑变得无比忙碌,他忙着把亡灵装进罐子,转移到山的高处,直到河水涨到淹没了他的家,他搬运完最后一个亡灵的瓷坛,和妻子合社才相偎在高地的岩洞里,怆然地看着红河水淹没了他赖以生存的野猪窝。
关于这篇小说的意义,黄佩华在散文《我的桂西北》中曾经有一段话说明:“数年前,我曾经写过一个叫《涉过红水》的小说,文中的主人公都是以这个河段的几个村子的名字取的。现在,当年的这些村子都被水淹没了,他们永远消失在水里了。或许,在许多年后,这些真正意义上的村子只能在小说里找到它们的模样了。”[13]作品中的巴桑、合社、鲁维、板央既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也是即将消逝的村庄,无论这些名字还是人都有着神秘的魅力,让人一直在寻觅它的意义。最后巴桑与合社的家园终于被河水淹没了,这也暗示出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和对桂西北生活在河边的人们情感的打击,更显示了作者对转型社会中人类生态家园问题的思考和对精神家园的忧虑。“因为大坝蓄水的缘故,红河的原貌被改变了,一些村庄被淹没了,原先在河谷里生活的人们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土地。不仅红河如此,就连水流不丰落差不大的驮娘河,也被无数的水泥大坝拦截成了若干节,借用当地人的形容,有些河段甚至蚂蚁也能过得河去,河床只剩下干白的卵石了。……那些没有任何工业污染的小溪小河流正逐渐被人们忘却,山坡的草地上飘舞的塑料包装袋和路旁遗弃的各种塑料瓶子,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域。”[14]显然现代化进程带来了物质利益,却荒芜了人类的精神家园。
《红河湾上的孤屋》中的老人也是一个“江流儿”,他的故事因为坎坷而神秘,因为辛酸而传奇。老人本是憨厚的山民,被表哥龙老八设计陷害,推进红河想要淹死他,但是老人凭着红河上的漂浮物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他住树洞,吃着没有滋味的食物,过着最原始的生活。残酷的生存环境和不幸的遭遇并没有泯灭他原本善良的天性,最终还是在湍急的河流中把有着和自己相同遭遇的“她”打捞上来,自己却葬身红河。这个小说不但让我们看到了蛮荒时代原始朴素生活方式的残酷孤独,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在这个缺乏英雄的年代,从老人身上散发出英雄的气息。
黄佩华通过对红河的“江流儿”的书写,作品展现出了执着顽强的生命意志和英雄气,他无意于批判社会或反思历史,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在努力地适应社会,接受现代文明。他们是家园的留守者,是“现代社会的闯入者、陌生人,在社会的夹缝里求生存,他们的社会意识还处于较为蒙昧的状态,无法成为社会反思的承担者或时代精神的代言人”[15]。这些曾经英雄般的“江流儿”不再是安于自然的族群,时代进入20世纪,必然要不可避免地走进现代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主动或被动、积极或消极地践行着优胜劣汰的生存规则。
黄佩华这两个红河题材小说和当时中国文坛现代化潮流的主流叙事是明显疏离的,甚至在“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进程中反其道而行之,塑造、发展了神话原型“江流儿”的形象,以此来表现作家自身的另一种情怀,即对将逝去的生活形态的挽悼,做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寻根。但他也忧虑地指出:“当作家们还在迷恋高地上的原生态与淳厚古朴之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如果我们只是乐此不疲地充当地理原貌和民俗风情的忠实记录者和见证者,那么文学与人们心灵的距离将会越拉越远。”[14]可见,尽管黄佩华对桂西北乡村是满怀激情在书写,但他并没有沉迷其中,他是通过小说中“江流儿”人物思索着如何让桂西北走出衰落,在现代化文明改变生存状态的同时,怎样构建他们的精神家园、生态家园。这是作者的焦虑,也是所有处在现代化转型期的人们的焦虑。
原型是“一些联想群”,作为“可交际的单位”,“它们是复杂可变化的”,而且随着时代文化背景的改变而变化、丰富。[1](P157-158)对神话原型的“复活”,也不能是简单的重复再现,而是要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中重新激活。弗莱提出原型的“置换变形”,原型通过置换变形才能沟通现代与远古之间的联系,才能负载不同时代人的精神与情感体验,同时也使这一原型不断丰富而且更具有历史感。“江流儿”原型也正是在这种古已有之的模式基础上,在当代文学中被不断更新、激活、发展,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下发生了变异,增加了新的内涵,即作者对时代、社会、文化的思考。原型置换变形这一结构特征使“江流儿”原型拥有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和吸引力,让我们在相同的原始思维的模式下发现不同的文化蕴涵,让我们更直接、更深刻地重新认识“江流儿”原型的既抽象具体又稳定多变的文学基因。
[1](加)弗莱.神话批评-原型理论[A].神话-原型批评[C].叶舒宪,编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
[2](瑞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A].神话-原型批评[C].叶舒宪,编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
[3]程金城.原型批判与重释[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4]王振星.唐僧“江流儿”身世的原型与流变[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5](俄)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M].魏庆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胡万川.中国的江流儿故事[A].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传说故事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8]王一川.意义的瞬间生成[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
[9]苏童.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10]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A].汪晖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1]汪民安.现代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2]韩少功.文学的根[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
[13]黄佩华.我的桂西北[A].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黄佩华卷[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14]黄佩华.我的高地情结——兼谈桂西北叙事[N].文艺报,2011-04-20.
[15]黄伟林.从自然到社会——论黄佩华小说《红水河三部曲》[J].民族文学研究,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