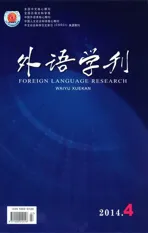诺斯洛普·弗莱的预表思想研究
2014-12-04侯铁军
侯铁军
(景德镇陶瓷学院,景德镇 333403;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
诺斯洛普·弗莱的预表思想研究
侯铁军
(景德镇陶瓷学院,景德镇 333403;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
诺斯洛普·弗莱的预表思想与原型批评相混淆,带有循环论的特征,被视为一种思维模式与修辞手法。虽然偏离了正统的基督教释经学,否定了《旧约·圣经》的历史性,但弗莱的预表思想遵循了其一贯的总体批评观,拓展了《圣经》预表法的阐释维度,为诠释西方文学、文化和政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弗莱的预表思想;原型批评;循环论;思维模式与修辞手法
1 引言
诺斯洛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的前言和致谢部分,向读者解释了这本书的源起。在撰写完研究布莱克的专著《可怕的对称》后,弗莱“决心用其从布莱克那里学来的文学象征主义和《圣经》预表法①的原则来分析另一位诗人”,即斯宾塞。但在开始研究斯宾塞的《仙后》时,他却发现自己的研究“还没开始,便结束了”,因为“为斯宾塞而做的引言变成了有关寓意理论的引言,而这一理论又固执地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Northrop 1990:iii)。于是,弗莱便着手研究这一更大的理论框架,而这一转向的成果就是《批评的解剖》——一本开启了文学批评作为独立学科的皇皇巨著。
尽管在研究方向和内容方面有所转向,但弗莱仍对预表法念念不忘。他不仅在《批评的解剖》的开篇处,哀悼它已成了一门“早已死亡”的语言(弗莱 2006:19),而且还不时地见缝插针,向读者宣讲他的预表思想。时光荏苒,弗莱内心深处的这一预表情结却日久弥坚。时隔25年之后,在他的另一巨著《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中,弗莱花了近乎四分之一的篇幅探讨预表法,以了多年的夙愿。在此书中,弗莱将预表法放置在全书的正中心,并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探讨它。
梁工指出,“弗莱所寻求的乃是为之【预表法】恢复声誉”,但由于其个人思想和经历的复杂性,“这又使他对基督教传统预表法的重建更趋复杂化”(梁工 2011:3),因而也引起了不少质疑和批评。正如梁工所言,弗莱对预表法进行隐喻式发散性研究,将神学、圣经阐释学、比较圣经研究、古希腊思想乃至现代政治思想囊括其中,十分复杂,甚至时常自相矛盾,以至被希伯来圣经专家罗伯特·奥尔特批评为“武断”、“牵强”、“十足的误导”(Alter 2002:18)。因此,简单地将弗莱的预表思想置于某一批评体系下(如神话——原型批评),都有削足适履、泛泛而谈之嫌。本文从“弗莱预表思想的原型底色”、“弗莱预表思想的循环论特征”以及“作为思维模式与修辞手法的弗莱预表思想”3个方面探讨弗莱的预表思想,认为它虽然偏离了正统的基督教释经学,否定了希伯来圣经的历史性,但它遵循了弗莱一贯的总体批评观,拓展了《圣经》预表法的阐释维度,为诠释西方文学、文化和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2 原型批评与《圣经》预表法的名与实
在文学批评史上,尽管弗莱不愿被称为原型批评的开创者,但学界总是将其与原型批评相联系,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在弗莱的批评实践中,又总是隐含着几分预表法的影子。因而,在分析弗莱的预表思想之前,我们首先应对原型批评与《圣经》预表法的内涵和外延有所了解,为本文的论述奠定基础。
原型(archetype)由希腊文 arche(原初)和 typos(形式)组合而成,“在古希腊起初指模子或人工制品的最初形式”。柏拉图曾使用此词,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念世界中的原型所创造的。荣格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原型,认为它是“反复发生的领悟的典型模式,是种族代代相传的基本原型意象”(张中载 2006:827, 828),是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弗莱借鉴了这一定义,但去除了其心理人类学层次的含义,从总体文学观的角度,把原型定义为“一种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形象”,是“可供人们交流的单位”(弗莱 2006:142)。
在原型批评的视角下,文学作品中各式各样的意象、细节、情结和人物(类型)都被视为某些原型的置换变型,因而从本质上而言,原型(archetype)与类型(type)的关系便与柏拉图主义的二元论如出一辙:在时间上,原型在先,具有本源性、先在性和规定性的地位;而类型在后,是派生性、从属性的。原型是类型的实体,类型是原型的影子。类型只分有原型的某些特质,其本身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则可被忽略。
圣经预表法(typology)一词源自希腊词根typos,意为“印记(imprint)、记号(mark)、痕迹(trace)、肖像(effigy)、楷模(example)、模范(model)、样式(type)。typos一词后来被翻译为拉丁文figura(形象),进而又被翻译成英文type”(Aichele 1995:62)。因而,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typology是有关形象、模样、典范、类型的学问或方法。但它到底是有关什么形象、模样、典范、类型的学问或方法呢?艾布拉姆斯对它的内涵与外延做了较好的概括:“用预表的(typological)或形象的(figural)模式来解读《圣经》是由使徒保罗开始的,然后为早期教父所发展,他们将希伯来经文中的历史、预言和律法纳入到基督教经文的叙述和教义之中。圣奥古斯丁曾道出了它的原则所在:‘《旧约》隐匿着《新约》,《新约》显现了《旧约》’。在预表法中,《旧约》中的主要人物、行动和事件被视为‘形象’(figurae)(拉丁文figura),它们均具有历史性,但同时,它们还预示着(prefigure)《新约》中的人物、行动和事件,而且前者在某些层面、功能或关系上与后者相似。通常,《旧约》中的形象被称为‘类型’(types),而它们在《新约》中的对应物则被称为对型(antitypes)。《旧约》中的形象或类型被视为更高真理的预言或许诺,后者根据一个计划在《新约》中‘实现’。这个计划永恒地处在上帝的意念之中,但它仅在被一段时间间隔开来的《旧约》和《新约》中向人类显现”(艾布拉姆斯等 2010:162)。
上述定义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囊括了预表法的发起者(保罗)和用途(解读《圣经》经文),界定了《旧约》中的类型与《新约》的对型之间的相互关系:前者预示和表征了后者,后者是对前者的应验和实现,及其等级次序:类型虽在时间上先于对型出现,但相对类型而言,对型是更高的真理,抑或类型的完满形式。因而前者是次要的,从属性的,而后者才是本源的,规定性的。强调了类型和对型的历史性:都是真实的历史人、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时空间隔,并将它的终极原因或原动力归结为上帝永恒的计划。
3 弗莱预表思想的原型底色
在弗莱看来,《圣经》呈现出“首尾呼应的一致性及体系完整的史诗结构”(弗莱2006:484),而这一结构特色应归功于《圣经》预表法(弗莱 1998:113)。但在用预表的方法诠释《圣经》时,弗莱却多次指出,《旧约》中的类型,如亚伯的死与他自己献给上帝的祭品都是一致的,以至于“在《圣经》中,总是把大海与一种海怪(leviathan)联系在一起,又将这种海怪与巴比伦和埃及的暴君统治视为一码事”(弗莱2006:214)。
对于弗莱的上述解读,希伯来圣经学者罗伯特·奥尔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认为弗莱的预表解读混淆了原型批评与预表法的区别。弗莱显著地使用“预表法”与“原型”作为批评术语,在《伟大的代码》中明显的是,《旧约》中类型与《新约》中对型之间的象征对等为他提供了模式,即一种所有文学中相同原型的不同表现之间的象征对等模式。这样一种简单的对等使得“海、海怪及约拿登岸的外国岛屿都是同一个地方,意指同一样东西”。如此一来,“当每个人物都被融化入某个原型时,人物的具体个性和人物间的特殊关系便灰飞烟灭了”,并指责弗莱的解读显得“武断”,“有时则牵强附会”且“时常是十足的误导”(Alter 2002:9-19)②。
原型批评以原型理论为基础,以结构主义方法为手段,将原本纷繁复杂的文学视为原型的置换变形(或类型)。虽然它丰富了文学批评的视角和方法,但却抹杀了具体文学作品意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圣经》预表法则强调类型的历史性,即强调它的真实性和特殊性,不将他/它们化约为对型的毫无个性的置换变形。更为重要的是,在预表法中,“唯有类型有效时(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大卫),其对型才有效”(Reiter 1969:563)。类型预表着对型,如果前者的历史性受到抹煞的话,那么后者的历史性也就岌岌可危了,这样一来,耶稣这个终极对型的历史性就会受到质疑,而这与预表法的初衷以及基督教的根本教义相悖逆。
强调类型的历史性有着重要的政治和种族意义。在批评弗莱时,奥尔特认为,“他复兴了基督教替代主义的一种形式,将希伯来《圣经》从它们富于个性的变动不居的复杂性中抽离了出来”(Alter 2002:21)。基督教替代主义是反犹主义的一个支流,认为《新约》已废除了《旧约》,并声称上帝和犹太人所立的约定已不再有效,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中,外邦人已经取代了犹太人。这一反犹思潮在使徒保罗那里便已初见端倪,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暗潮汹涌,至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时更是愈演愈烈。在1899年的德国,便有一股基督教替代主义势力,他们质疑《旧约》的历史性,要求“完全废弃基督教中的犹太元素”,而在这表面的宗教神学争议中,暗涌的正是来势汹汹的反犹主义大潮和种族灭绝的滔天罪恶(Dawson 2001:1)。面对种族和宗教的双重危机,德籍犹太裔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曾借助语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批评方法,为希伯来《圣经》和犹太民族正名。当时正流亡于伊斯坦布尔的他,写下了著名的“形象”(Figura)一文和巨著《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试图用预表法来调和旧、新约之间的关系,强调《旧约》的历史性,反对将《旧约》的类型看成共时性的“寓意”和“象征”,努力将它从人们对犹太教的憎恨中拯救出来。
虽然没有亲历纳粹反犹罪行的暴虐,但民族和宗教意识强烈的奥尔特却拒绝奥尔巴赫似的调和,走上了一条更为独立的道路。他反对将希伯来《圣经》④降格为《新约》的陪衬(旧约与新约这两个名称就是佐证),极力凸显希伯来《圣经》中具体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维度,并通过翻译希伯来《圣经》并撰写《圣经的叙事艺术》等著作,揭示它内蕴丰富的文学特性,从而捍卫它乃至犹太教的特性和独立性。这样一种使命担当,使得奥尔特对基督教替代主义异常敏感,因而当他在弗莱的解读中捕捉到一点蛛丝马迹时,便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
4 弗莱预表思想的循环论特征
在《圣经》预表法中,《旧约》中的类型预表着《新约》中的对型,两者间相隔了一定的时空。虽然类型与对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相对于类型而言,对型是一种“更高的真理”。换言之,类型(影子)是对型的不完满表征,而对型(实体)是对类型的完满实现。因而,从类型到对型的发展呈历史的、线性的、水平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又与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一致。《圣经》以《创世纪》始,记述了宇宙和人类历史的开端,以《启示录》终,预言人类历史的终结,处于期间的是以以色列民族为代表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因而其“时间应当称为线性时间……不存在周而复始的循环”(梁工 2006:226)。
除了横向的线性发展趋势外,《圣经》预表法还与“一个神圣的秩序有着直接的垂直关系”(Auerbach 1984:72)。从人的视角来看,《旧约》的类型与《新约》的对型不处于同一时空平面之上,没有任何关联。“只有把两件事与上帝天意垂直联系起来,它们之间才有关联。”(奥尔巴赫 2002:83) 换言之,之所以类型与对型成横向的线性发展关系,就是因为它们内在暗含了与神意相连的垂直纵向关系。如果要用一个意象来指代上述联系,象征基督教的十字架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它一横一纵的结构正好与预表法的水平发展与垂直联系呈同一态势,而悬挂其上的耶稣基督——这个最伟大的对型——则是连接这一纵一横的粘合剂。
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建构了从古至今文学的总体走向:即从神话到传奇、高模仿、低模仿及反讽,最后回归神话,这种循环论的倾向在他的预表思想中亦有所反映。在《伟大的代码》中,他认为“我们所说的预表法就是神话反复不断的一种特殊形式”(弗莱 1998:118)。对此,王宁总结道,“弗莱依循自己熟悉的循环式、周期性或戏剧性结构,带领读者穿过预表法的车轮的静止点直取本书的核心部分”(王宁 1998:6)。
弗莱曾指出,“‘狡猾’的蛇能够通过蜕皮来更新它的活力,成为客观世界自然循环的象征。”(弗莱 1998:148),而“咬尾蛇将自己的尾巴咬在口中,使圆形与蛇身联系起来”(弗莱2006:213),因而,用咬尾蛇的意象来概括弗莱预表思想的循环倾向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实际上,《伟大的代码》这本书的框架便很好地体现了咬尾蛇这一意象。本书各章节的顺序依次为语言1、神话1、暗喻1、预表法1、预表法2、暗喻2、神话2、语言2,总共探讨4个方面:语言、神话、暗喻与预表法,而其中的每一个内容又被分为1和 2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关系有如预表法的类型和对型:1在某些层面、功能或关系上与2相似,2相对于1而言则是更高的真理。本书以语言1开始,以语言2结束,最终这一对类型与对型尾首相连,循环往复。
弗莱的诠释偏离了正统释经学,用带有循环特征的预表思想取代了圣经预表法的横向线性发展和神人垂直相连的纵向维度,从本质上而言,这也与原型批评密切相关。原型批评将原本纷繁复杂的具体文学现象(类型)视为原型的置换变形,这些类型在不同的文本中、不同的时空中反复出现,但它们的意义最终还得追溯回原型之中,才能被理解和诠释。换言之,文本的意义(原型)早已被预设,尔后所出现的各种意义的置换变形(类型)唯有被放置在早先的原型下观照,才能显现出自己的终极意义。原型不断投射出类型,类型则永远地回望原型,此二者的关系本就暗含了循环的倾向,这也是弗莱预表思想之所以被打上循环论烙印的深层次原因。
5 作为思维模式与修辞手法的预表思想
虽然弗莱从小就反感在解读《圣经》时过于拘泥于它的字面意义(饶静 2008:6),但作为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的他并不反对《圣经》的字面意义,更没有奥尔特所谓的“基督教替代主义”的反犹倾向。之所以弗莱的预表思想偏离了正统的基督教预表法并带有浓厚的原型色彩及其循环论特征,是因为弗莱的初衷并不是为了用预表法来更好地了解《圣经》中隐而不宣的上帝旨意,而是希望借此来开创一种总体批评观。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曾提出“往后退”(standing back)的观点来开展总体批评。往后退,与批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仅不会被对象的细枝末节所缠绕,还能高屋建瓴,从生成背景、文化传统和原型结构等方面更好地把握阐释对象。同样,在运用预表的方法阐释《圣经》时,弗莱与《圣经》预表法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他不断地往后退,将它“当作一种思维模式,而且也把它看做是一种修辞手法”。在这样的阐释预设下,弗莱自然会扩大《圣经》预表法的阐释范围,将《旧约》中人、事、物(类型)与《新约》中耶稣基督(对型)之间的预示和实现关系拓展开来,使得“以色列人”乃至“《旧约》中的一切成为《新约》事件的类型或预兆”,“《新约》中的事件构成了《旧约》中类型所预示的现实‘对型’”(弗莱 1998:120,112)。
总体批评观的磅礴气势和远大视野使得弗莱一直不断地往后退,最终他走出了神学与文学的疆界,进入到意识形态和政治之中。他认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修辞方法的预表法,对当今世界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16世纪的清教徒们,正是借助预表的思维方式和修辞手法,将“罗马教会”看做娼妓,把教皇视为反基督。此外,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也有几分预表的架势,“因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所作的预言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实现了”,甚至就连希特勒也受到这一思维模式和修辞方法的影响,“这个极其卑劣的暴君的唯一真正身份是他极认真地扮演了反基督的角色”。这些据弗莱看来,“可能就是预表法留给人类的遗产”(弗莱 1998:113,114,131)。
弗莱的预表思想之所以能有如此的张力是由于《圣经》预表法本身的互文性和开放性特点的内因使然。预表法所具有的独特诠释特性使《圣经》中原本时空分隔的类型与对型互相呼应,互相指涉,使得它们呈现出互文的特性。预表法的对型通过“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等方式(陈永国 2006:72),与类型建立互文关系,并将后者纳入到自己的框架中来观照,向它扩散自己的影响。这样一来,《圣经》文本在预表法的互文过程中便处于一种“生产”状态:《旧约》成了《新约》的“原材料”,一种可写文本,《新约》则通过使用、转化、扩展,甚至改写等方式对其加工,使其产生出新的意义。
预表法的互文性破除了类型与对型的阻隔,削弱了类型的自主和自足性,使它不再是原作者业已完成了的意义的载体,而是呈开放态势,永远地指向他者。这一“他者”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是类型永远缺乏的一部分,是次要的、边缘的类型所反映的首位的、中心的对型。没有对型这一“他者”,类型的意义永远处于不完善的悬置状态,因而它从产生之日起便在等待这个“他者”对自己的填充和完善。
然而,由于神意的隐秘和不可知性,为类型填充“他者”的工作就主要依靠释经者的解读,而释经者在用预表的方法阐释《圣经》时,又难免会受到自己思想意识中的某些“先结构”的影响,他们所持有的宗教、政治等立场往往会预设出某种类型或对型。弗莱的预表思想正是受到其总体批评观这一“先结构”的影响。借助预表法的互文性和他者性,弗莱将预表法视为一种思维模式和修辞手法,冲破了圣经释经学的清规戒律,把《圣经》纳入到西方文化、文学和政治的恢宏视野中来审视,极大地拓展了预表法的阐释维度。
6 结束语
尽管弗莱的预表思想偏离了正统的圣经预表法,但他却为我们理解和诠释西方文学、文化和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清教徒认为,克伦威尔领导的政府预示着千禧年的到来,荷兰也曾一度被视为新的希望之乡,美洲清教徒们则把《圣经》预表法“重新引入了激进的历史因素”(Bercovitch 1999:207)。他们将自己定义成上帝的选民,把《圣经》中的地理、人物和事件与美利坚的地理、民众和事件相联系,把前者视为后者的类型,将后者视为前者的对型。对此,艾利奥特曾有过精彩的论述:“预表法得到更自由、更广泛地运用,进入了一个更为精妙的语言体系,使得诠释者能在现今的事件中发现《圣经》的预兆。这样一来,清教徒跨越大西洋的航行就成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对型;新英格兰殖民地则变为基督再临迎接千禧年的新锡安”(Elliott 1988:34)。这些人之所以能言之凿凿,大义凛然,正是因为他们像弗莱一样,拓展了圣经预表法的阐释范围,杜撰出一套修辞话语和符号象征,以“上帝选民”的身份自居,为自己的俗世利益提供了神圣的合法性辩护。
至今,这一思维方式和修辞手法仍潜伏在美利坚民族的集体有意识和无意识之中:惠特曼宣称美利坚是“新的以色列”,约翰·沙利文为美国的领土扩张而高举“显然天命”,从克林顿所倡导的“新的契约”到延续今日的“美国例外论”,都可依稀看到弗莱式预表思想的身影。有关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深层原因及其意义和影响,笔者将另行著文分析。
注释
① Typology一词,在国内学界还没有统一的汉译名称。有的把它译成 “预示论”(《解剖》),有的则译成“类型学”(《代码》)。据艾布拉姆斯的释义(见正文),typo-logy是阐释有关旧、《新约·圣经》中的形象、事物、事件的预示与应念之关系的一种释经学方法,因而,本文采用了《圣经》阐释学中的“预表法”这一更加符合其含义的译名。为便于行文,作者将本文中引用的其他译本或论文的不同译名,统一改成了预表法。
② 本引文的中文译文参考了梁工教授的论文“试议弗莱原型批评的缺失之处”中的译文。
③ 中世纪盛行的一种释经法,将《旧约·圣经》中的所有事物的意义划分成4个层面:字面意义(literal)、寓意意义(allegorical)、道德或比喻意义(moral or tropological)以及神秘意义(anagogical)。
④ 希伯来《圣经》与基督教《旧约·圣经》的内容基本上一样,然而奥尔特为强调希伯来的特性,使用的是希伯来《圣经》这一称谓。
埃里希·奥尔巴赫. 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艾布拉姆斯等. 文学术语汇编[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陈永国. 互文性[A],赵一凡. 西方文论关键词[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梁 工. 《圣经》叙事艺术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梁 工. 试议弗莱原型批评的缺失之处[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诺斯洛普·弗莱. 批评的解剖[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诺斯洛普·弗莱. 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饶 静. 太初有言——诺思洛普·弗莱研究[D]. 复旦大学, 2008.
王 宁. 中文版序言[Z]. 诺斯洛普·弗莱. 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张中载. 原型批评[A]. 赵一凡. 西方文论关键词[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Aichele, G. & Gary A.PhillipsIntertextualityandBible[M]. Atlanta: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995.
Auerbach, E.ScenesfromtheDramaofEuropeanLiteratur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Bercovitch, S., et al.TheCambridgeHistoryofAmericanLi-teratu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Dawson, J. D.ChristianFiguralReadingandtheFashioningofIdentity[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Elliott, E., et al.ColumbiaLiter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Northrop, F.AnatomyofCriticism:FourEssay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Reiter, R. E. On Biblical Typolog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J].CollegeEnglish, 1969 (7).
Alter, R. Northrop Frye Between Archetype And Typology[A]. In J. M. Kee(ed.).NorthropFryeandtheAfterlifeoftheWord[C]. Atlanta: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2.
【责任编辑王松鹤】
AStudyofNorthropFrye’sTypologicalThought
Hou Tie-jun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Jingdezhen 333403,China;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Featured with the cyclical tendency, Northrop Frye’s typological thought i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archetypal criticism and regarded as a mode of thought and of rhetoric. Although Frye’s typological thought has deviated away from the orthodoxical Christian exegetics and has leaded to the denial of the historicity of theOldTestamentofBible, it accords with his overarching view of criticism, has extended the interpretative scope of biblical typology,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interpreting Wes-ter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politics.
Frye’s typological thought; archetypal criticism; cyclical tendency; mode of thought and of rhetoric
I106
A
1000-0100(2014)04-0142-5
2013-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