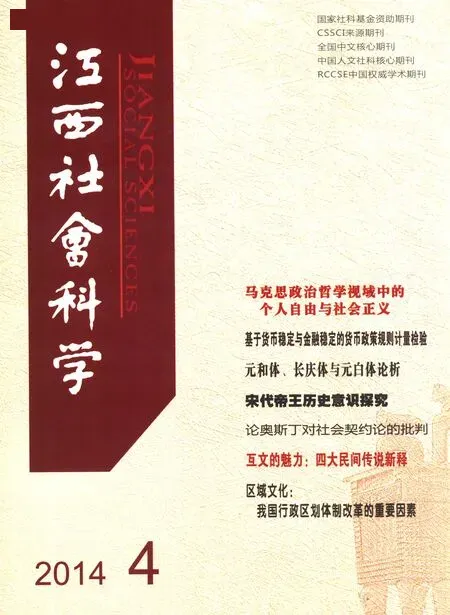翻译文学:民族视野下的世界文学景观
2014-12-04李卫华
■李卫华
随着全球交往的日益频繁与深入,穿越于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文学翻译,已成为学界新的研究热点。但翻译文学长久以来的尴尬处境——无论是在源语国文学还是目的语国文学中,都处于不被关注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翻译文学到底是外国文学还是本土文学,抑或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学界尚未有定论。如果将翻译文学视为相对独立的场域,这种独立性从何而来?它又是怎样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学界对此也缺乏深入探讨。本文认为翻译文学自主性受到外部权力场域、本土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的制约,但自身的逻辑发展和建构才是确立翻译文学场域的关键,翻译文学由此表现出相对于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的“双重拒绝”,但其同时也表现出兼具两者某些特点的“双重结构”,翻译文学是世界文学从文学理想成为审美现实的“流通模式”和“阅读模式”,它事实上就是民族视野下的世界文学景观。
一
对于参与翻译文学归属问题论争的各方而言,在承认翻译文学场域相对独立性这一点上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谢天振一再强调“一个相对独立的翻译文学的存在”[1],强调翻译文学“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2]。刘耘华也同意“我们的确应该给翻译文学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的地位”[3],王向远也认为要“确认‘翻译文学’的独立的、本体的价值”[4]。但这种独立性从何而来,各方缺乏必要的理论论证。场域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5],即场域主要通过自己内在的发展机制加以构建,具有相对于外在环境的自主性。翻译文学场域的自主性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作为“元场域”的权力场等外部条件的制约:从十七年时期苏联文学翻译的兴盛,而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尤其是现当代作品,则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而基本不予翻译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场域的隐性操控;“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隐性操控成为直接的干预,翻译文学的每一部(篇)作品从确定选题、组织翻译到最终的发行方式,每一步骤都处于意识形态的制控之下。权力场域对翻译文学场域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本土文学场域的发展状况对翻译文学的选择、译介与接受有着深层制约性。进入新时期,西方现代文学的大量翻译,虽然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禁区”和“毒草”论的反驳,但更主要的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契合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界要求突破单一观念与模式,进行艺术探索与创新的需要与渴望。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思想内容、文学手法的确与才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的中国人的文学接受视野、审美视野相差甚远,要使西方现代文学为读者接受,新时期初期的翻译文学采取了以下翻译策略:在内容与认识价值上,翻译文学力图避免源语作品的内容、思想与译入语文化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力求归化;从形式而言,翻译文学接受源语文本在艺术手法、创作方式上与译入语文学的差异,强调对现代派技艺的借鉴,即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以异化为主。可见,本土文学场域深刻影响了翻译文学的形态、性质、价值和意义,成为制约翻译文学场域自主发展的又一重要外部因素。
以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翻译学场域(学科)对翻译文学场域也颇具重要意义。诚然学界对是否将翻译确认为一个独立场域还颇有争论,但翻译专门杂志的诞生、翻译专业会议的不断召开、大型工具书的问世以及翻译学成为高校学位专业,标志着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自主场域和独立学科。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学位点的设立,标志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场域,在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体制中获得了合法地位。翻译学独立场域的获得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使得人们对文学翻译的过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具体指导着翻译家的文学翻译实践,并促使人们对翻译文学自身的定位、性质和发展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在一个以内在分析为优先次第的自主性原则导引下,权力场域、本土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虽与翻译文学场域关联颇深,但外部的影响总是要被转译为场域的内在逻辑,外部影响来源也总是要以场域的结构和动力作为中介,“只有当构成某种文学或艺术指令的特定法则,既建立在从社会范围加以控制的环境的客观结构中,又建立在寓于这个环境的人的精神结构中,这个环境中的人从这方面来看,倾向于自然而然地接受处于它的功能的内在逻辑中的指令”[6]。因而翻译文学自身的逻辑发展与逻辑建构才是确立翻译文学自主场域的关键。
自主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专家团体的兴起,翻译文学的自主发展也离不开文学翻译家、翻译文学理论研究者和翻译文学批评家(外国文学研究者)等专家们的努力,他们逐步发展、传播出自己特定的机构化、专业化的利益,并随之产生重新译解、阐释外在要求的能力。新时期以来对翻译文学进行本体论思考的学术著作及翻译文学史的撰写,正体现了专家团体对本场域的理论化、系统化思考,也成为翻译文学自主场域形成的重要标志。对自身历史的细微体查也意味着对自身主体性的确认。
另外,诸如《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和《译林》等翻译文学期刊为翻译文学场域提供了具有实体意义的、切实可感的翻译文学文本,营构了翻译文学得以公开出版的阵地。翻译文学期刊也为翻译文学场域内部的交流提供了一方园地,如1998至2000年,著名翻译理论家许钧在《译林》上主持“翻译漫谈”栏目,通过访谈方式,与许多翻译家就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的各方面展开对话。国内学界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长期存在着隔阂,这样一个栏目无疑对双方增进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专家团体的兴起及专业刊物的出现,标志着翻译文学场域自主的原则已转化为场的逻辑固有的客观机制,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场域内部各种因素的配置和作用之中。
二
翻译文学自主性的确认也使得其体现出对于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的“双重拒绝”,当然,通过拒绝从属于两极位置来确定自我身份也是场域自主性获得的重要表现。“双重拒绝”可简单表述如下:我拒绝(厌恶)X,但我并非不拒绝(厌恶)X的对立者。“X”可以是某个观点、某种运动、某个场域……“双重拒绝在从政治到严格意义上的美学的所有生活领域都存在”[6],翻译文学不属于外国文学,不属于本土文学,正是这种决然的不从属于任何领域的拒绝确立了场域独立自主的性质。虽然参与翻译文学归属问题讨论的各方承认翻译文学相对独立的事实,但也都从各自的立足点和侧重点出发,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做了或此或彼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张南峰的《从多元系统的观点看翻译文学的“国籍”》、高玉的《论翻译文学的“二重性”》虽一定程度上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承认翻译文学的“双重国籍”或“二重性”,但也是“虽摆脱了二元对立,却没有摆脱二元论”。[7]将翻译文学归属于民族文学主要是从外部的历史事实出发,认为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的交换,更是两种文化的交往,而且这种交往活动最终必须转换为一种文化的内部活动;将翻译文学视为外国文学则主要是从文本内部的审美结构出发,认为外国文学是翻译文学的源泉和根本,没有外国文学文本,哪有翻译文学文本?没有原作者的创作,哪有译者的再创作?两者都具有一定的合理内核,但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外国文学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它只是外国文学“来世的生命”,它与外国文学在语言样态、文本环境和文本接受等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翻译文学也不是民族文学,它并非对本民族自身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独特表述和艺术编码,而是其他民族生活和心理状况的真实写照。
场域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在翻译文学内部的美学分析与外部的社会分析间寻求沟通,从而摒弃认识论上传统的二元对立,超越结构与历史的割裂。翻译文学场域与外国文学、民族文学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翻译文学来源于外国文学又在民族文学语境中发挥作用,同时具备两者的某些特点,亦即具备“双重结构”,它处于两者之间且兼具两者的某些因素。翻译文学这种兼具源语文学和目的语文学特点的“双重结构”体现在文学活动的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的每一要素之中。
从作家身份来看,翻译文学事实上有两个作者,原作者和译作者,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一部译作,并非译者独立拥有,而是原作者与译者共有,译者与原作者一样发挥了创造性的作用。从文本性质来看,翻译文学文本在情节、内容上源于源语文学,而在语言及形式表达上有赖于目的语文学,正如有学者所言:“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主要是质的联系、内容的联系,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主要是文的联系、形式的联系。”[7]从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来看,虽然翻译文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目的语国的本土读者,从阅读、理解到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在目的语国的语境和经验范围内运作,但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不经阅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赋予了作品无穷的意义,翻译文学使得原作品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传播到各民族的读者中去,源语文学的读者和翻译文学的读者一起建构并丰富了作品的意义。外国文学文本是异域文化语境中作家的精神表述及艺术编码,其迁移、旅行到其他文化、民族时,除了表面的语言指涉、情节结构等借翻译得到准确传达外,语言背后具有丰富历史内涵和文化意义的文化符码、观念体系,大多不能进行表层的直接迁移,而是在与本土的观念体系进行深层次的碰撞后,借着文化误读的方式得以曲折呈现。也就是说翻译文学是跨越两种文化、两个“世界”的书写。
三
翻译文学场域“双重结构”的特点为翻译文学的最终定位确立了基础。笔者将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视野下的世界文学景观①,这充分考虑了本土文学、本土语境对翻译文学的选择与接受的深层制约,也考虑到了翻译文学源于外国文学这一事实性基础。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对大部分中国作家来说,“世界文学语境实际上是根据中国的文学文化需要作了选择、剔除的一种自我选择的‘中国化’的语境,即翻译文学营造的世界文学语境,它与自在状态的世界文学语境在广度上要狭小”[8]。世界文学概念最少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无论是宏观意义上全面地、综合地、整体地指称全球所有国家的文学;还是指全人类文学史上获取世界性声誉的第一流、顶级作家的作品,亦即“伟大的”、“经典的”作品;或是歌德所憧憬的“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的充盈着乐观的普世主义的文学“大同世界”[9],在任何一个层面上,“世界文学”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客观的、有效的和现实的存在。那么,我们怎样在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来理解世界文学的概念呢?笔者认为,翻译在建构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的世界文学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角色,正是翻译的中介,一些原本仅具有国别/民族文学特征的文学作品成为世界文学,也正是翻译的介入,使得世界文学从一种“乌托邦想象”成为一种“审美现实”。[10]
达罗姆什在论述世界文学是如何通过生产、翻译和流通而形成时,对世界文学进行了这样的界定:一,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简略折射;二,世界文学是翻译中有所增值的作品;三,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超然地去接触我们时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种模式,即一种“流通模式”或“阅读模式”。[11]詹明信同样认为,世界文学“指的是知识界网络本身,指的是思想、理论的相互关联的新的模式”,这种新的模式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更加理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异域文化与文学,要求我们在了解异域文学或其他环境里发生的思想、审美事件时,也必须深入理解造成这些事件的环境本身,而并不是把文化活动从它们各自的语境中孤立出来,投入到“绝对”的领域中去。“‘世界文学’的含义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它意味着当我们同别国知识分子交谈时,本地知识分子和国外知识分子不过是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的媒介。”[12]一部作品要成为世界文学,需要经历两个程序,首先是要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其次是要流通、旅行到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更大的语境中。翻译能使作品跨越多种界限,在尽可能多的人群中传播,是世界文学流通模式和阅读模式的基础。将世界文学视为一种流通模式,已经内在地考虑到了“世界文学”是对民族文学的折射,其本身也是在不同的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形成的,不应脱离具体的民族文学和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来谈世界文学。作为阅读模式的世界文学是指世界文学作品来源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翻译为我们提供了阅读的可能,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阅读的都是世界文学经典作品的译本,它让我们克服了自身语言的障碍,去接触广泛的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学成果,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的译本——也就是目的语的翻译文学成为事实上的民族视野下的世界文学景观。
在文学文本的异域旅行过程中,即“世界——作家——原著——译者——译著——读者”的链状关系中,翻译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流通模式和阅读模式的意义为其获得独立于源语文学(外国文学)和目的语文学(中国文学)的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更为重要的是,翻译文学使得世界文学从一种乌托邦理想成为一种审美现实,翻译文学就是民族视野下的世界文学景观。当然,我们应在文学文本的这样一个旅行范式中进一步思考翻译与流通的辩证关系,翻译文学的价值意义及其本体理论,更积极地将翻译问题纳入世界文学研究视野中。
注释:
①在新时期中国文学语境中,学界有将“世界文学”等同于“外国文学”的倾向和做法,这在逻辑上有含混之处,但考虑到事实与习惯,笔者在这里还是采用了“世界文学”这一术语。
[1]谢天振.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J].中国翻译,1992,(1).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3]刘耘华.文化视域中的翻译文学研究[J].外国语,1997,(2).
[4]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Bourdieu,P.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3:162.
[6](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7]宋学智.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8]查明建.从互文性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兼论影响研究[J].中国比较文学,2000,(2).
[9](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0]王宁.“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J].探索与争鸣,2010,(7).
[11]David 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281.
[12](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