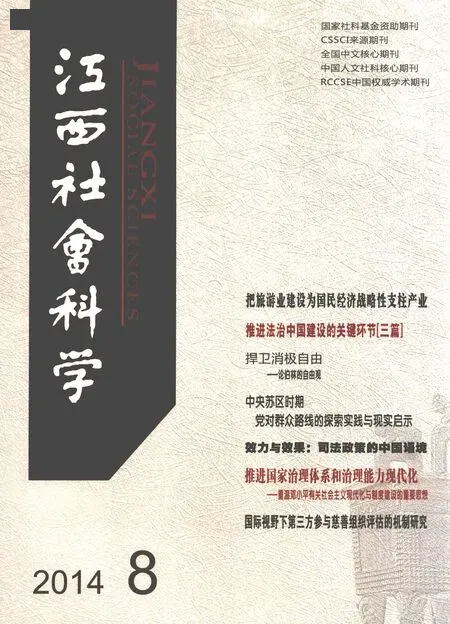都市写作的困境——以晚生代作家的创作转型为例
2014-12-03叶祝弟
■叶祝弟
在20世纪末的文坛上,晚生代作家已经广为人们所关注。所谓晚生代作家,主要是指20世纪60年代出生,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群体。关于晚生代一词的由来,陈晓明在其主编的晚生代丛书的前言中提及这件事情,在描述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思潮中,他首用这个概念,用以命名85新潮之后的小说家,后来这一名称用来指20世纪90年代之后登上文坛的更为年轻的作家,如韩东、邱华栋、朱文、林白、陈染、毕飞宇等,还有一些评论家将卫慧、棉棉、魏微等一批70后的作家也囊括在内。虽然文坛对这批作家的命名是斑驳而模糊的,评论家们试图用各种时间性的词语,命名这批写作风格存在差异的作家,但是总体相似的文学背景和文学理念,使得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某种共性。在创作上,他们的作品可以被概括为个人化写作、对宏大叙事的逃离;在精神气质上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反抗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现存的文学秩序。总体来说,晚生代作家的创作表现在直面当下的现实生活,以个人化写作姿态关注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强调创作的个体性和自我意识。[1]
然而,以标榜个人化写作和都市欲望生活写作为价值立场的晚生代作家,在凸显个人生存的本相的时候,却往往是以虚化历史维度和收缩社会视角为代价的,文学中理应被反应的社会问题和时代命题,便悬置在文学之外,而难以进入个人化写作的视野。这种写作视野的天然缺陷,反应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普遍缺乏广泛的生活题材和写作对象,无法对生活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普遍缺乏对生活能力的把握,建立不起宏阔的文学追求和宏大的叙事气象。这种创作的颓势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关注,有些批评家看到晚生代作家正在陷入创作的画地为牢中,许多晚生代作家的反抗性正在明显萎缩;如有的批评家认为,“我们有理由期待一种清晰的、透明的历史感的写作”。正是在这种不满与期待的复杂心境中,在21世纪初,晚生代作家中的一批中坚开始了创作的转型,比如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韩东的《扎根》、毕飞宇的《平原》、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作品,将目光从人们喜爱的都市空间转向热气腾腾的乡村,写作风格也呈现了别样的气象,对这些作品的分析和总结,有利于窥出晚生代作家群体的创作的新变,也有利于蠡测当前都市创作的问题和走向。
一
从一开始,在都市里从事写作的晚生代作家们,选择了一种拒绝与主流话语合作的边缘者的姿态。出于对中心意识形态的恐惧,他们选择了边缘性的位置,扛起个人化写作的大旗,在经验和立场上力图成为独特个性的“那个个人”。晚生代作家的都市小说里,出现了一大批游离于主流的小人物,他们是都市的流浪者和遗弃者。晚生代作家塑造了都市里漂的一代,并以此为隐喻,传达出晚生代作家在既定的社会秩序里面的残缺感和边缘感。
第一,边缘立场。陈染、林白、海男、韩东、朱文等一批作家,似乎一登上舞台就在个人化的生活经验、日常化的生活气息中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他们自认为是“时代的孤儿”(东西)。这种身份的自觉,使得他们天生以与生活平行或者低于生活的姿态进行写作。
这种边缘化的立场是晚生代作家能够安身立命的真正的要素。他们从中心退回内心,从集体书写退回个体言说,挖掘个体一己的经验,在日常生活状态中言说,使他们的小说有了新的美学意味和生命意味。晚生代作家无一例外地流露出回到个人内心写作的愿望。如有人认为“内心是作品的长相”(毕飞宇);有人认为,“如果不从自己最深切的这种痛感入手,那么我觉得这种写作就没有意义”(韩东);“我的全部作品都来自我的生命”(林白),正是这样的立场,他们获得了比前代作家更加自由的表述空间,使得他们所提倡的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个人化写作得以大行其道。
第二,边缘人物。晚生代作家塑造了一大批生活在时代边缘的人物,她们要么是同性恋者,如倪拗拗和禾寡妇(《私人生活》)、二帕和意萍(《瓶中之水》);要么是自恋、恋父者,如《子弹穿过苹果》、《回廊之椅》中的朱凉、《无处告别》中的黛二小姐;要么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无业游民,三个百无聊赖的朋友(《三人行》)。他们的小说里充斥着失意的诗人、自命不凡的天才、招摇过街的骗子、深夜不归的酒鬼以及毫无羞耻之心的妓女和嫖客。
第三,边缘心态。通读晚生代作家早期的作品,似乎所有的作品里面都散发出那种压抑、猥琐、迷惘、狂放的气息,这些人物的精神永远在流浪。在路上奔跑,是他们的人生状态,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从一个卧室到另一个卧室,在这些不同的场景中他们疲于奔波,灵魂无处安家。
人格的裂变是他们的普遍的心理状态,几乎所有的人物内心都是分裂的,他们在生活的缝隙中生存,他们挣扎在爱与痛的边缘,他们默默体验着孤独的苦酒。传统的英雄或者枭雄与他们都没有关系,他们只不过是正常人中的一个,只是比正常人要坏一些,要迟钝一些,要暧昧一些;匪夷所思是他们的行动状态,他们总是在恐惧和怀疑中生存,他们对世界充满了不信任,道德的冲突和阵痛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那么自然,那么栩栩如生。这是一种典型的颓废心态,正如魏微所说,“人们丧失了理想,然而内心是慌张的,在这个太平盛世里,我们失去了内心的平和,这是个无依无靠的时代,与前后都断裂了,成了时间之外的一个独立,人都是小人,也是无依无靠的,简陋,可怜。”
鲁羊的中篇《九三年的后半夜》,可以被看作是晚生代作家眼中的时代图像和背景。九三年应该是一个时间的隐喻,旧的秩序正在被破坏,新的秩序还没有形成,晚生代处在这个黑夜和黎明交替的夹缝中。这样的后半夜,就是这样一种时刻,“人类或仅仅是个人的真正境遇在此刻显示出来。无家可归者在此处更加无家可归了。狂欢达到了高潮,并且开始疲乏;街头巷尾站出来许多面孔和嘴巴。他们纷纷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并且我比你更流氓”,在这样一个无所适从的时代,我,苏轼(戏仿了宋朝的大知识分子),在一个大草垛上无所适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无法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了一个漂泊的人。
与苏轼同样出于尴尬地位的,还有朱文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小丁,拖着残缺的身躯在城市的边缘游走,整天无所事事,一种刻骨铭心的无聊感威逼着他。为了消除无聊,他不得不做出各种无聊的事情,编造各种无聊的故事去抵抗无聊。在《我爱美元》中,他和父亲大肆谈性,性成了生活唯一的目标;在《五毛钟的旅程》中,打电话消磨无聊的时间,他们甚至兴奋地以诋毁自己为乐,称自己为“垃圾”。
第四,边缘语言。与晚生代作家笔下的边缘人物相呼应的,晚生代作家的语言也是一种典型的边缘语言。在晚生代作家那里,语言呈现出粗糙、质朴的形态,既没有形式上的刻意创新,也没有艺术上的雕琢。方言、口语和生活语言泥沙俱下,在晚生代作家的笔下活灵活现,呈现着爆炸而又粗鄙的一面。在朱文的小说中,总是回荡着一种粗野的激情。欲望的狂欢与粗鄙的语言纽结在一起,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挑战一切、颠覆一切的意味,流露出都市边缘人的率真和下层人的流氓气。
林白在《我的全部作品都来自于我的生命》中写道:“我80 年写诗过来的,我想尝试一种粗砾、有点脏,但很生动的语言风格,多塞几个他妈的进去。”
到了《万物花开》、《石榴树上结樱桃》、《平原》、《妇女闲聊录》,都市边缘人退场,或者回到农村,原来在晚生代笔下被遗弃的乡下人,开始占据了文本的中心位置。
《万物花开》通过一个脑子里长瘤的大头的独特视角,观察活跃在乡村里的人物:杀猪的二皮叔、赚钱的王大钱、跳开放舞的女孩、偷情如家常便饭的乡村男女。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禾三叔(可以和村里的任何一个女人睡觉);乡间的、城市的顺口溜、民谣在这里交汇;贫穷、懒惰、生育、死亡都在他们身上呈现出狂欢的精神。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由自在的状态,他们生生死死。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保持了一定的宽容,对于发廊女三躲把性当成谋生的手段,三丫、四丫用肉体换取男人的钱财的行为,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谴责。
王榨的乡村人,不仅对人类保持着宽容的态度,而且对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满怀敬畏。大头与一头叫妞儿的母牛的结合,完成了性的启蒙,他小小的年纪就看透生死——“瘤子既使我通向死亡,也使我通向自由,它是我的双刃剑。”
二皮叔杀猪是给猪放生,让猪重新获得做人的权力。二皮叔对生死有特别的理解,性和死亡连在了一起,死亡是新生命的开始。在王榨人看来,“万物平等,万物有灵”,连茄子花、豆角花,也因为丰腴茂盛而有性的象征。
在《妇女闲聊录》中,王榨人另类是天生的,另类就是他们自由自在、最本真的状态。他们并没有像城市的叙述者那样蔑视农村、蔑视一切。他们笑看人生,在他们看来,苦难并不被认为是苦难,乡村也不再神奇和浪漫,但是他们按照自然而然的本相生活,浑身上下洋溢着狂欢的力量。
在扉页中,林白说:“无论如何,我就是大头。”在后记里,林白又说:“原先,我小说中的某种女人消失了,她们曾经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艾,也性感,也优雅,也魅惑,但现在她们不见了。”正如有学者指出:“那些潮湿的沙街、月光、青苔、镜像、冷艳绝伦的女人,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肥沃的土地、牲畜、花朵、瘤子,狂野恣肆的乡民。青瓷般幽冷孤寂的林白世界,转而充斥着浓郁的泥土气息。……王榨乡村及其万物生灵的鲜活,阅读中我们心灵的震颤,确证了林白生活在别处的意义。”[2]
二
当下写作,相对于过去时写作,它是一种现在时的写作,是晚生代作品的叙事背景。晚生代作家对当下生活日常状态保持持久的兴趣和热情,他们通过个人的视角写正在发生着变化的人和城市的关系。他们的欲望化叙事,一方面表达的是都市人在城市化过程中所享受到的某种自由,另一方面又流露了某种失控。他们潜入日常生活,感受日常生活的庸常、无聊、无力。
林白、韩东、东西的很多作品都是面向当下的现在时的写作,而不是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对历史有着狂热的迷恋。这种现在时写作有着自身的必然性。90 年代人们普遍对历史表示了某种冷淡,对与历史相对应的宏大叙事表示了嘲讽和不屑。作家们对社会的历程作非历史化的处理,他们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个人经验进行创作,用身体感悟外在的世界,用感性的语言描摹外在的世界。依靠感官而不是大脑写作,使得他们的作品热衷于表现某些转瞬即逝的感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让晚生代作家们更加倾心表象化、平面化的世界描述。
表面上看,林白是擅长用过去时写作的作家。她关于广西北流的故事的讲述很多就是用回忆的笔触来展开的。林白的小说不是以故事取胜,而是以那些暧昧不清的混沌诡异的意象营造的氛围取胜。在回忆中,故乡的沙街总是以一种若有若无的面目出现,呈现出斑驳不清的模态。她通过回忆,营造了一个“美丽动人、欲望勺勺、命运叵测的女人们”的世界。这些女人在沙街狰狞血腥的透着死亡和腐烂的空气中挣扎、毁灭。林白对这些女人投去的是悲悯的目光,并且不时要跳出来对这些女人指手画脚,她通过这些女人的塑造,“意在对女性隐秘、苦难经验反思和现实中女性欲望重新唤醒”。林白对她的女人们是一种爱怜的心态,同时又是居高临下的,她通过那些无所畏惧、在高低之间尖叫着飞翔的女体;通过美丽潮湿的雨季,赋予她的女子独特的女性个人气质。李莴、姚琼、冼小英无不是生机勃勃而神秘莫测地生活着。
这些女人诡秘的内心世界传达的正是身居异乡的林白的个人生命体验。她们虽然身在北流,但是与林白的个人现实世界是同构的。在漆黑诡异的黑夜,林白通过回望北流沙街来塑造另一个现时的自我,以驱逐孤单灵魂的束缚。她通过自说自话实现自我的拯救。当然林白是非常清醒的,这种回望的姿态并不能解救自我,靠陷入自我的想象、做虚幻的梦来拯救自己,其结果只能陷入更深的梦境中无法自拔。
在《妇女闲聊录》中,林白摆脱了过去自我回望的那种叙事方式,林白学会了倾听,她成了一个虔诚的聆听者。她记下了中年妇女木珍的口述,进行了一次拯救自我、解放自我的行动。这是另一种回望式的写作,与林白以前的封闭式的回望式写作不同。如果说以前的回望写作是为了对现实生活的逃避,那么现在的这种回望式写作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热情的驱动。回望写作是一种双重思维的写作,一方面写作者有着丰富的当下经验,另一方面带着这些经验再回望逝去的那些经历,就有了一种别样的色彩和韵味。
《妇女闲聊录》创作了一种闲聊体。《万物花开》是林白的写作由“个人化”全新风格的过渡,《妇女闲聊录》无论题材还是形式,都展示了林白从未有过的风格。书中以第一人称,散碎而又鲜活地还原了农村妇女“木珍”的生活记忆,看似零乱而口语化,却具有一种平静中的文字力量。
当叙述人处于一种闲聊的状况时,她的内心不会受到来自现实的压力,她可以把现实的任何烦心的东西抛到一边,全心全意陷入东拉西扯的闲聊中。她的这种回忆,因为有了距离而获得了别样的体验。木珍“回望”的不是属于一个妇女的个人内心小世界。她展示的是一幅中国乡村的典型的全景图,是一个农家妇女个人的历史、家庭的历史、自己所生长的乡村风土人情世故。在木珍的眼里,通过她的回忆,乡下的那些风物都拥有无限的温情。她可以原谅一切,她可以容忍任何的困境,她甚至对自己的情敌冬梅也是充满了某种理解和热爱。
木珍鲜活的记忆带给了林白别样的生命触动,木珍的那种几乎是超脱了个人情感纠葛的人生态度影响了林白,让林白感触很深,走出了房间,找到了都市写作和乡土写作的关系,评论家多有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中,人们对都市写作和乡村写作存在的误解也影响了晚生代作家的创作转型。
三
在现代化的版图上,城市意味着文明,意味改变命运的机会,更意味着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和现代化的生活形态。进入大都市成了人们普遍的梦想。但是当他们通过考试、上大学、工作来到城市,他们便像候鸟一样迁徙到城市,或者归隐到某个单位,或者自愿远离现有体制的控制,采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进行创作。农村的经验在他们身上烙下了深深的脚印。当他们以闯入者的身份来到城市,因为没有城市底层的经验和记忆,他们的写作题材很容易狭隘在酒吧、高级场所这样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地方,或者城市边缘地带、地下场所这些同样是与普通的城市居民隔膜的地方。
在晚生代作家的作品里,几乎都是都市公共空间的场景,并施展想象。对一个城市的弄堂——一个城市最基本的单位结构,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描写。根本原因就在于以经验化写作的晚生代作家,没有城市生活的天生的经验,丧失了言说的可能性。比如在林白的作品中,主人公总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自怨自艾。
犹如自言自语一样。这样的写作方式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比如交流和理解的问题,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在自己的空间里过着童话镜子里一般的生活,这种幽闭的生活只能导致人生更大的虚无,对外界生活的拒绝,也就意味着个人的沦丧。
晚生代在城市是没有根的,他们没有深厚的城市底蕴。他们是在城市想象城市。他们只能在都市的边缘从事生存和都市的双重漂泊。比如,林白90 年代来到北京,她的前期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北京创作的,然而却没有一部作品是反映北京的现实生活的,反而到了北京,在她的作品中主人公总是回望家乡北流。北京,虽然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政治中心体现为权力意志,权力跟文化结合以后,往往就会构成一种很特殊的文化圈。但林白基本上是排除在这样一个文化权力机制以外的作家。
另一个原因,在于晚生代作家并没有找到真正讲述的都市语言。随着方言的溃退,以及文字的演变,都市作为一个另面的“风景”被发现了。《子夜》等一大批都市小说的面世,标志着中国的都市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学长了一副极不对称的体格——乡土小说四肢发达,都市叙事头脑简单。造成这样的结果,不仅仅与作家的价值立场有关——我们是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度,我们一直以为农业文明代表着正义和诗意,代表美和善,而都市文明是恶之花,代表着狡诈、欺骗、虚伪和万恶——还与我们的都市经验表达的方式的贫乏有关,相对于发达的乡村书写体系,我们无法找到适合都市书写的方式。
一直以来,中国的作家认为都市只适合用精雕细凿的文字(欧化语言,白话文) 来表达,而对用声音为主的都市方言视而不见。甚至他们认为都市只存在着公共语言,而方言只存在于边远的乡村。其实不然,事实上,在中国任何一个都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方言,这些方言产生于弄堂里巷,产生于瓦肆会馆,流传在市井小民之间,他们是鲜活的,他们上不了厅堂,但是就像河边的水草一样,生命力旺盛,相对于普通话为代表的文字,它们才最大限度地承载了一个都市的记忆。
然而在现代性的思维模式下,都市方言也被压抑了。我们总认为雄伟的高楼、时尚的酒吧(对应的是普通话为主的文字) 才是都市,那些或隐或藏的里弄 (对应的是方言为主的声音) 不是都市。我们的作家总以为只有规范的文字才是表达生活的最有效的手段,却对都市里的方言没有多加注意。他们在表达都市经验的时候,放弃了对都市方言的采用,而钟情于干巴巴的文字。尽管他们殚精竭虑,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无奈植根于农耕文明之上的古典诗词对电话、电梯等现代词汇一筹莫展,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对市民生活的描摹方面却又是手足无措,他们一片茫然,于是他们开始怀乡,他们逃到对乡村的书写中去。中国都市书写的失败,我认为根本的原因不在于价值观立场的偏见——如把都市描绘成为诱惑、沉沦、幼稚、虚伪的人间地狱,而是表达方式出了根本的问题——都市书写中文字中心主义代替了语言中心主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一直存在贬低城市、抬高乡村的文学创作传统。从茅盾的《子夜》到周再复《上海早晨》,城市几乎等同于堕落、恶魔,而农村则象征着诗意、温情。中国一直存在现实主义创作的传统,而乡村生活中的苦难生活场景,风俗人情中的伦理观念,更容易产生深层的历史感。在当下社会,随着城乡交流的逐渐扩大,农村社会的各种传统道德的瓦解更容易被发掘和书写。在都市写作中,文字中心主义的写作理念是对语言中心主义的戕害,事实上这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都市书写的失败后,一大批中年作家错误地以为写都市是没有出路的,写乡村才能复活真实的经验世界。这种思维逻辑也同样影响了一大批晚生代作家——这些都市之子。他们最初以写都市闻名,尖叫着飞翔于文坛。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的都市书写是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深入到都市的方言中去观察生活,表达生活。
这一批晚生代作家其实是虚伪的都市之子,他们并不是天然的都市人,他们的血脉里残留着乡村的思维因子。这一批作家大多童年生活在农村,通过读书考上大学进入都市的经历,注定了不可能用彻底的都市思维去观察都市,去深入都市的肌理进行考察。他们要么用出生地方言(农耕文化) 的逻辑来观察都市,得出一个欲望、虚伪、做作的都市;要么用普通话的经验逻辑来描述城市,进而遮蔽了那些生活在里巷弄堂的都市生活经验。他们的这种“隔”的身份割断了他们与都市的最深刻的经验连接的可能,从而得出一个片面的、不成功的都市印象。在都市写作失败之后,他们最终又不约而同地逃向了对乡村经验的书写,逃回到那个最初最熟悉的世界里。
晚生代作家均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城市的失望和恐惧。其他的晚生代作家,表示出对乡村的迷恋,视乡村为自己的精神纽带,如东西:“随着三伯的过世,田氏家族中父辈的最后一双眼睛从我的身上消失,也就是摸过我脑袋,看着我长大的那一代田家人已经全部入土,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和故乡就切断联系呢?”这种逻辑的后果是,中国的都市文学一直处于被压抑被丑化的状态。因此,一个作家如果要复活出鲜活的都市经验,就必须转移自己的视线——从那些会堂、广场、酒吧、游乐厅等公共性的领域转向,转到里弄、亭子间、闺房等都市最私密性的场合——用声音(都市方言)而不是用文字(普通话标准语)来描述。其实,好的文学图景不是都市写作和乡村写作谁高尚谁低劣的问题,而应该是都市写作和乡村写作共同发展的状态。可惜的是,大多数的晚生代作家都不可能熟练操作两种题材的写作。
[1]张凤琴.大陆新生代小说创作研究述评[J].理论与创作,2004,(6).
[2]丛坤赤,俞春玲.对《万物花开》意义与叙事立场的一种解读[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