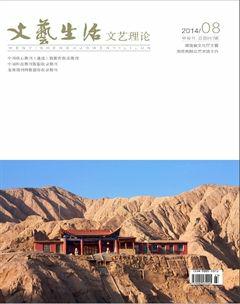浅析《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技巧
2014-11-28李萌
李萌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浅析《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技巧
李萌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的一场喷空。作者成熟运用了诸多叙事技巧,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独特的个性特征,包含了丰富的可读性。本文重在对小说的叙事分析。
一句顶一万句;叙事;刘震云
小说以杨百顺和牛爱国为主角,通过对人物、情节的调配,以近似而又不同于离乡-返乡的模式写出了人的心灵孤独。
小说是全知模式的,但又以限制式叙述开展。作者以“讲述”控制了历史背景和故事发展。不同于宏大叙事,小说尽力去除历史背景,使中国式孤独具有了普遍性;同时,小说也没有完全去历史,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的间隔是人所共知的断层,作者留白,将传统中国与具有现代性的人物对比,展现了心灵的孤独。尽管淡化了背景,凸显了具有永恒性的乡土氛围,但老詹、省长、总理衙门等词,造成了陌生化效果,使读者得以定位时间,这是作者对历史间隔的掌控。
刘震云没有滥用全知叙事,只在必要的情节前释放信息,张弛有度,加上在人物心理间的自由穿梭,使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也得以凸显。叙事角度不断转换,不同人物的声音共存,但都掌控在叙事主体下,各有差异,却和谐一致。老詹便是一例,他本是一个启蒙者,然而与老贾和吴摩西的对话解构了这一身份,将其转变为孤独者形象,成为了中国式孤独的典型。张力就在于,他带着崇高的使命感来传教,如果他的孤独一说出口,便解构了自己的身份。欲建教堂而不得的执念混合着他想以发展信徒证明自己的渴望,慢慢成为心魔,成为了“恶魔的私语”。对“信仰”的执念,使他过分关注“语言”,至于连经都讲不明白。上帝告诉他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却没有告诉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反倒是老贾更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这曲儿里说的苦,就是主要救的呀。”
又拍着桌子正色说:
“这就是主存在的理由!”
接着感叹瞎老贾弹出了主的心。又摇头感叹,一个能懂主的心的人,为啥还不信主呢?便想让瞎老贾信主。没想到瞎老贾说:
“既然我都知道他的心了,为啥还信他呢?”
老贾直面问题,取消了形式来直面本质。老詹临死前“恶魔的私语”,代表老詹对自身境遇的反思和领悟,与杨百顺“不杀人就放火”观照、对话,但道路仍是老贾式的。小说没有为孤独找到出路,老贾就是作者能诠释的最高意义。
小说人物众多,却有统一性,这得益于一个个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小故事。得益于作者对时间刻度的把握,这些小故事串在一起,促进了情节发展,烘托了中心人物的情感。
作者大量运用预叙和重复。预叙便是对信息的释放。去除支线来看主线,其实是一个普通的故事。看似不相干的支线使情节变化有了内在缘由。支线故事是小说的血肉,一个个扁平的形象,使杨百顺得以丰满。在主人公做出每一步转变时,作者都说出一个不相干的原因,吊起读者胃口,使支线的插入不显突兀。作者在高潮时笔锋一转,道出事件与主线的关系,又回到主线。支线主线的反差越大,在收回时就越跌宕起伏。重复不是相似事件的重复,而是不同故事指涉同一主题,每个支线因特殊性却“陌生化”,加深了主题,这得益于作者对乡土题材的搜奇罗怪。内容要素的丰富性被统一在叙事下,成功揭示了更为隐蔽、深刻的主题。尤其是主线结构的重复,即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可视作同一种“离乡”或同一种“归乡”,“乡”是故乡,也是心灵之乡。
出延津记以杨摩西更名罗长礼结束,回延津记则直接从几十年后开始,以“间隔”的手法调配叙事时间,中间的空缺只在最后透露出来,省去了诸多笔墨,读者对吴摩西的理解也产生了多样性。但间隔和重复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出延津记以一种扩散的姿态将杨百顺的故事扩展开来,当读者的期待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百流归一,故事终止。回延津记也一样,新人物出场,重新扩散,到最后才找到一些联系呼应前文。过大的间隔是一种冒险,处理不当会使小说变成独立的两篇:当读者充满对杨摩西命运的期待往下看,却只能看到一个讲述者油嘴滑舌故伎重演时,难免脱离语境,产生厌倦,使得后面的新故事不再鲜活。
小说的语言特点与主题相近:“绕”,但这种拉家常式贴近生活直白露骨的语言却逻辑严谨有因有果。“是……也不是……也不是”之类的叙述语链构成的语段及语篇,与情节和主题有统一性。每一层所指和能指都有个较大差异,但是每一层所指都印证了下一层的能指,而每一层的能指又与上一层的所指联系在一起,层层递进,推进了主题。不光是绕,对“虚”的喜好,与杨百顺的改名也都有逻辑关系,表达了乡土中国人的精神困境:人们不愁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这都是已发生和必然发生的,重要的是不知道心灵的去处。这种迷失也更多显现在社会层面。吴摩西找巧玲,牛爱国找章楚红,本不必要,也是一种对社会偏见的超越,但又亡羊补牢。吴摩西改名罗长礼也一样———改名前,他一直有着对虚的追求,并不执着于“名”,却在社会中处于失名状态。当他选择了一个务虚者的名字找到了社会地位坐标时,他又进入了彻底的失语状态。“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罗长礼从此过起了以后。而全书的结尾,似乎又留给了读者另一种丰富性:
宋解放:“还没找到庞丽娜和老尚吗?”
牛爱国:“不,得找。”
和吴摩西一样,牛爱国洞悉了社会与人的语言关系,踏上了寻找章楚红,寻找以后的道路。这可能是又一次无力的反抗,但这又何尝不包含了一种更好的可能呢?
总体看来,作者对叙事模式的运用已非常成熟,小说既饶舌又逻辑清晰,既指涉心灵又大气磅礴,既有跌宕起伏又具有现实普遍意义,产生了丰富的多义性和可重读性。
I206
A
1005-5312(2014)23-0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