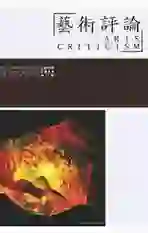诗人与校园
2014-11-17吴思敬
在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公寓的窗外,有一株高大的白杨树。白天,浓密的枝叶为诗人遮蔽住阳光,晚上风动树叶的飒飒声则给诗人带来诗意的联想。几乎每位驻校诗人都被这株高大的白杨触发了诗情。十年了,随着白杨树年轮的扩大,它迎来和送走了一位位驻校诗人,成了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的一个美好见证。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的建立,要回溯到 2002年。那一年《诗刊》社设立了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这是个面向年轻诗人的有重要影响的奖项,获奖诗人年龄限制在 40岁以下,评奖采取读者推荐与专家结合的方式,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最终根据专家背靠背的评分,确定获奖者。 2003年,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评出了江非等三位获奖诗人。此时这个奖项已颁发了两届,《诗刊》在探讨怎样把“华人青年诗人奖”办得更深入人心,即不是评出获奖诗人、颁了奖就了事,而是如何切实地关心、爱护这些获奖诗人,让他们能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像有些植物一样,开花之后便枯萎。此时他们把眼光投射到了刚刚诞生不久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上。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唯一的以诗歌研究为中心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地除去要对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诗歌作品及其相关理论形态进行基础性研究之外,也要承担诗歌教育与传播等面向现实的任务,以充分利用中国诗歌这一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提高国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2003年底,《诗刊》社主编叶延滨、编辑部主任林莽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副主任吴思敬做了沟通,探讨让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得者进入高校,为学校加强诗歌教育,也为获奖诗人自身的提高形成双赢局面的可能。
获奖诗人用什么名义进校呢?此时国内还没有可以参照的样本,西方国家则有过“桂冠诗人 ”、“驻校诗人 ”等名号。“桂冠诗人 ”是由英国王室给资深的大诗人的荣誉称号,很明显,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得者都是年轻人,不具备“桂冠诗人 ”的影响与实力。“驻校诗人 ”在美国较为普遍,是大学教育与文学互补的一种方式,进驻学校的是罗伯特 ·弗罗斯特、布罗茨基这样的创作成就突出的大诗人,他们进入学校后,通常会给予教授称号,并可以带创造性写作方向的研究生。当然也有些驻校诗人以写作为主,不承担教学任务。这样一比较,显然“驻校诗人 ”这一称号有较大的包容量,也更有弹性。于是,《诗刊》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很快就达成了一致,在《诗刊》社每年评选出的“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得者中遴选一人,送到首都师范大学驻校,为期一年。
2004年9月,山东青年诗人江非,作为首届驻校诗人来到首都师范大学。自此又有路也、李小洛、李轻松、邰筐、阿毛、王夫刚、徐俊国、宋晓杰、杨方先后驻校,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确立起来,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
自从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活动公开报道以来,社会反响强烈。青年诗人,或毛遂自荐,或单位推荐,希望来首都师范大学驻校的非常踊跃。那么,让谁来驻校?讲人情,讲关系学,肯定不行;像高考一样,命题做文,一卷定终身,也未必妥当。而诗刊社的“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评选就恰恰提供了遴选驻校诗人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它提升了驻校的门槛,从根本上保证了驻校诗人的质量,也使驻校诗人遴选的公信度、透明度大为增强。叶延滨、林莽相继从《诗刊》退休后,《诗探索》接替《诗刊》继续举办一年一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评选,完全保留了《诗刊》时期形成的评奖原则,也使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的来源有了稳定的保障。
每年九月,随着新学年的开始,驻校诗人来首都师范大学报到。通常会有一个简朴的入校仪式,驻校诗人与诗歌研究中心的师生以及首都诗歌界及媒体的朋友见面,同时举行这位驻校诗人的作品朗诵会。驻校诗人均有充满深情的答辞,其中王夫刚、李小洛的答辞是有代表性的,表明了他们对驻校生活的理解与期待:“感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感谢你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生活的横断面和时光的林间小路给予我用来学习和交流,与其说这是奖掖一个曾经年轻的外省诗人,不如说是在物欲时代向曾经伟大而今饱受诟病的诗歌精神的顽强致敬”(王夫刚)。[1]“今天,来到北京、来到首师大,其实我是在接受着一个‘希望的召唤。因为我坚信,这个由前辈学人、老师共同构筑的 ‘希望就是未来,是历史,也是道路。而且,这条道路不仅通向了中国诗歌的远方,也在今天抵达了我的心灵。此时此刻它正和我左边的荣誉感,右边的羞怯感一起,教育,鞭策,并激励着我”(李小洛)。[2]
驻校诗人从走出校门,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早就希望有回到校园再学习、再充电的机会。首都师范大学则给他们提供了方便的学习、进修的条件。驻校诗人可以利用学校的现有资源,包括开通校园网、办理校园卡,学校的图书馆、诗歌中心的资料室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他们还利用首师大距离国家图书馆较近的条件,到国家图书馆去看书和查资料。杨方说:“我在首师大图书馆系统地阅读了一些这些方面的书籍,并且详细地做了五本厚厚的笔记。在我阅读的这些书中,有《穆旦译文集》,有拜伦的长诗《唐璜》,惠特曼的《草叶集》,弥尔顿的《失乐园》,辛波斯卡的《我曾这样寂寞地生活》,阿多尼斯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荷马的《伊利亚特》等,首师大图书馆找不到的书,我就去国家图书馆找。我要求自己每个月平均有七到十天的时间待在图书馆里看书。在这一年学习结束的时候,我整理了一下读书笔记,我总共读了五十四本书,可能还要多些,有些可能没有被记录。这其中不包括对杂志的阅读。 ”[3]应当说,这样的阅读量,是相当惊人了。驻校诗人还可以在首师大各学院任意选听感兴趣的课程与讲座,有的诗人除了听首师大教授的课程与讲座之外,还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旁听了他们喜欢的课程。
对驻校诗人而言,写作是他们驻校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安排诗人驻校,就是给他们创造一个安心写作的条件,尤其是那些来自基层的诗人,他们可以从繁忙的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心思在创作上。至于驻校诗人写什么,怎样写,学校不加任何干涉和限制,也没有数量和品种的要求,给他们充分的创作自由。每一位驻校诗人都非常珍惜这可贵的驻校机会,时间抓得非常紧,那棵白杨树下的驻校诗人公寓的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驻校诗人来这里之前,平时的创作,多是孤军奋战,很难有与评论界交流的机会。首都师范大学则给他们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门安排了资深教授与驻校诗人保持联系与交流,对其作品和创作方向提出批评与建议。与研究生的对话更是平等的、真诚的,青年学子们往往坦率地说出阅读驻校诗人作品时美的或不美的感受。在与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评论家与读者的交流中,在不同诗歌观念与诗学主张的碰撞中,诗人们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诗歌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有了新的感悟。
驻校诗人在校期间,还做了大量诗歌教育与普及方面的工作。他们给本科生开诗歌讲座,与研究生对话、座谈,参加并指导学生文学社团的活动。他们的到来,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因为以前同学们只是在报刊上、网络上了解诗人和他们的作品,现在诗人来到了身边,他们可以近距离地与诗人接触、交流,这种活生生的诗歌教育是他们过去难于感受到的。宋晓杰曾评论过当代大学生的写作:“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诗群,他们的技术和经验也许还没有多少,但有充足的知识贮备、才情和表达能力,有时会闪电一般击中我。我觉得这样的人确实不在少数。但能走多远,还需要许多诗之外的东西——比如,坚持、外力助推、有意识的自我提升等等都很重要。 ”[4]宋晓杰以她对当代大学生写作的深刻理解,与同学们平等地对话,审阅、修改他们的诗歌作品,并挑选其中的优秀作品推荐给诗歌刊物。正是在校园近距离地与学生的接触与互动中,驻校诗人们言传身教,在青年学子中播撒了诗歌的种子,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自觉的诗歌读者群,一些校园诗人也开始崭露头角。
驻校诗人立足于首都师范大学,除去可以利用学校自身的资源外,还可以大量运用北京的资源。北京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在地,驻校诗人可以参加中国作协及其所属的《诗刊》社、现代文学馆、鲁迅文学院等举办的诗歌活动。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作协立刻组织了赴震区慰问与采访团,当时就把驻校诗人邰筐吸收进去。邰筐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到了汶川,回来写了不少动人的诗作。此外,首师大还为驻校诗人提供与兄弟院校交流的机会。比如介绍李轻松、邰筐、徐俊国、王夫刚、宋晓杰等到北京语言大学同外国留学生座谈,为他们讲课,很受欢迎。这些汉语水平较高的留学生,很可能是未来的汉学家,他们和这一代作家接触后,对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对驻校诗人来说,最难忘的,恐怕就是在驻校结束的时候召开的有关自己诗歌创作的研讨会了。在通常情况下,为身居基层的年轻诗人开专门的创作研讨会,那是很难的。首都师范大学给驻校诗人结业时开的研讨会,是很正式的,有很高规格的,参加人除去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外,还特邀过包括谢冕、韩作荣、叶延滨、唐晓渡、张清华、王家新、西川、蓝蓝等在内的重要诗人和评论家。而且提前三个月就发出会议通知,把驻校诗人的作品发下去,让大家准备论文。开会前就编印好有关这位诗人的研究论文集。研讨会上,驻校诗人汇报驻校一年的体会与成绩,与会诗人与专家则对其一年的驻校生活及其创作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一本研讨会论文集,一次充满诗情与友谊的研讨会,对驻校诗人说,这是他驻校结束时收到的最为珍贵的礼物,诗人和专家们的意见,青年学子的热切期待,对他未来的创作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为驻校诗人提供的服务,应当说主要是在软件方面,也就是在精神、文化方面为他们的创作与学习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也要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最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一个住所,既是他们的卧室,也是他们的创作室。第一位驻校诗人江非驻校时,是与首都师范大学的访问学者合住一个房间,诗人没有独立的空间,对创作不方便。到第二位驻校诗人路也时,便在学校附近的北洼西里居民小区租了一套两居室,由路也与一位韩国博士生同住,每人都有一间独立的卧室兼工作室,条件要好些了。但住在校外,毕竟有许多不便之处,既然叫“驻校诗人 ”,还是以住在校内为好,既安全又方便。这样,从第三位驻校诗人李小洛起,便在首都师范大学家属宿舍区,为驻校诗人租了一套一居室房屋,客厅、卧室、厨卫等齐备。北京的房租年年在涨,最初是每年一万八,现在已是每年近四万了。租金是由首都师范大学来承担。驻校诗人给学生开讲座等,会给他们开讲课费。从 2013年开始,每月还给驻校诗人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当然,限于首都师范大学的财力,补贴有限,驻校诗人的生活主要还得依靠原单位的工资或其他来源。
当初《诗刊》社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提出驻校诗人设想的时候,希望能为学校加强诗歌教育,也为获奖诗人自身的提高形成双赢的局面。经过这十年来的实践,这双赢的局面应当说是实现了。
从驻校诗人方面说,通过一年的驻校生活,他们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自信,驻校的确成了他们诗歌创作道路上的加油站。驻校诗人的情况不同,像路也、阿毛、杨方等都上过大学,路也本人还是大学教师;有些诗人则没有上过大学。不管哪种情况,他们对一年的驻校生活,都是充满怀念与感恩的。杨方在离校的告别会上深情地说道:“对于这一年的学习,我无限热爱和留恋,我甚至希望驻校不是一年,而是三年,五年,甚或十年。不是我贪心,是因为在首师大每一个读书的日子都是那么明亮而饱满,我像一棵绿萝,拼命吸取水分和营养,然后不断从身体里长出身体,从绿叶里长出绿叶。这一年的学习帮我打开了视野和思路,学习也使我对自己的诗歌写作变得更加自信和坚持。无疑,这要感谢学校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安心学习的机会,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学校系统地安排了诗歌研讨、讲座、对话、访谈、诗歌朗诵和给学生上诗歌课等形式,建立了诗人与学院、评论家、国内外研究者的立体联系和深层互动。学校对服务诗歌的公益心和扶植诗人的赤子心,以及细致琐碎的工作中闪烁的诗歌良知和纯粹品质,让我感动。这些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事,都与诗歌有关,又超出了诗歌本身。因为这一年的学习,我对诗歌的感恩和敬畏与日俱增。 ”[5]没有上过大学的宋晓杰,则把一年的驻校生活,看成是对自己青春的一种补偿:“回想这段不寻常的时光,我愿意用新鲜和偏得来定义。因为我没读过大学,是诗歌给了我额外的补偿,把生命中缺少且我很在意的重要一环‘合上 了!虽然与具体的学业无涉,我也不能拿回首师大的一纸毕业证书,但是,生命意义上的修补和重构已然发生,必将影响到我今后的人生。虽然北京时而阴霾的天气令人不开心,像一个人云里雾里命运不知所终,但另一种字里行间的欢畅呼吸和自由游弋,也许令我终身受益。 ”[6]在思想上、艺术观念上受到启迪的同时,驻校诗人们也交出了丰硕的创作成果,有的诗人在离校的同时便出版了新的诗集,如阿毛的《变奏》、徐俊国的《燕子歇脚的地方》、宋晓杰的《忽然之间》、杨方的《骆驼羔一样的眼睛》。李轻松驻校期间写出了诗剧《向日葵》,并在小剧场演出,十分成功。有的诗人离校之后,获得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如李小洛、邰筐进入了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有的诗人则转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在他们眼里,驻校改变了命运。至于后来,他们所获取的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各种诗歌奖项和荣誉称号之多,就举不胜举了。
从首都师范大学学生的角度说,驻校诗人的到来,大大丰富了他们的文学生活,加深了对诗歌、对诗人的理解,在诗人与学子间架起了心与心之间的桥梁。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中,历届都有诗歌的爱好者,成立了“唳天诗社”,但未形成持续性的影响,一批骨干毕业了,就会消沉一个时期。此前,也有过诗人进校园,比如曾请西川等诗人给学生开过讲座,但都是一次性的,未形成制度和传统。驻校诗人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首师大学生的诗歌生活。不是一位,而是一连十位当下活跃的青年诗人就在你的身边,这对年轻的学子说,是何等的幸运!同学们不只看到了诗人头上的光圈,更看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诗人与学生的互动,朗诵会、对话会、研讨会、诗歌讲座层出不穷。诗人与学生亦师亦友,诗人给学生看稿,手把手地帮他们修改。正是在诗人的带动下,一股诗歌创作的潮流在学生中间潜滋暗长,一些学生不只是在校刊校报,而且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诗作,《诗刊》就曾为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创作开过专栏。
这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驻校诗人与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对研究生的培养与驻校诗人的提高之间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霍俊明是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他入学的时间大致与首都师范大学建立驻校诗人制度同时,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他与驻校诗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霍俊明与首届驻校诗人江非同属 “70后”,读博期间相识,因诗而成了好友。以致霍俊明在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 70后先锋诗歌》的序言中开篇即写道: “2007年1月22日,内蒙古额尔古纳的茫茫草原为皑皑白雪所覆盖。当江非把一册自己刚刚打印装订的诗歌小册子《纪念册》递给我的时候,我强烈感受到了诗歌在一代人手中的热度和分量。 从额尔古纳回来之后,江非为我们的这次相逢写的一首诗《额尔古纳逢霍俊明》成为我写作这本书的动力之一:‘你、真理,和我 /我们三个——说些什么 //大雪封住江山/大雪又洗劫史册 //岁月 /大于泪水 /寂寞 /如祖国”。可见驻校诗人江非在霍俊明心目中的地位。霍俊明与驻校诗人的交往与互动,直接促成了他的首部学术著作《尴尬的一代——中国 70后先锋诗歌》的诞生。这部书带有真切的现场感和原生态性质,为自己,也为包括驻校诗人在内的一代人的文学活动留下了历史见证。俊明为他的同龄人 ——70后诗人所写的这本书,标志着他已走出了学院式的研究模式,找到了一条适宜自己的学术道路。作为同龄人,他很容易就与 70后的诗人形成良好的互动,他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些诗人的脉搏的跳动,他能理解这些年轻人的血性与躁动不安,也能觉察出他们的局限与不足,从而写出了这代人清醒而困惑、守旧而背叛、沉默而张扬、单纯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以及“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尴尬处境。霍俊明毕业之后,继续关注驻校诗人。他与首都师大前后十位驻校诗人都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与这些诗人做了多次的深度访谈,在此基础上整理了十篇对话,并为每位诗人写了专论,成为研究驻校诗人的宝贵资料。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的十年实践,除去让驻校诗人与首师大的学生受惠外,还能够触发人们对文学人才培养及文学制度创新的联想。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不仅基于诗歌意识和表现形式的变革,也离不开文学人才的培养体系和相关文学制度的保障。中国古典诗歌的写作,建立在自然经济与小农经济的背景下,以私塾式、作坊式的教育为主要传承方式。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诗歌的发展与报刊媒介、新式学堂、文学社团等的出现,特别是文学制度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制度是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条件,也是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结果,文学审美意识变迁的背后,必有文学制度的参与和运作。文学制度制约和引导着文学发展,包含文学人才培养在内的健全的文学制度的建立,是文学健康发展的保障,也应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予以创新。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诗歌人才的培养,渠道是较为单一的,基本是在中国作家协会与地方作家协会系统内进行的。主要是靠作家协会系统的专业作家、合同作家制度,也包括中国作协及地方作协所办的文学讲习所、文学院,以及形形色色的不同主题的作家班等。这种体制具有“官办 ”色彩,而且由于作家协会力量有限,再加上各级作协普遍对小说家重视,成了如艾青当年批评的 “小说家协会”,能为青年诗人提供的服务与进修机会实际是很少的。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的建立,打破了由作家协会进行封闭式培养的传统思路,调动了教育部门的资源,把教育与诗歌、校园与诗人联系起来,突破了诗人封闭自足的私人空间,让诗人与诗歌进入社会的公共空间,既为莘莘学子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又为青年诗人的成长提供了一片沃土。当然,驻校诗人制度之所以能在首都师范大学坚持下来,是由于有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这样一个实体。这个条件不是一般有中文系的学校就能办到的,不仅需要稳定的经费的保障,而且应当有一支有相当实力的诗歌研究队伍,有一些热心驻校诗人事业的人士。驻校诗人制度是多元的,首都师范大学的驻校制度只是其中之一。实际上,每所大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建立自己的驻校诗人或驻校作家制度,通过不同的方式为教育与诗歌、教育与文学的结缘作出贡献。
驻校诗人制度是人才培养的制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看一种人才培养制度,十年是不够的。当下的驻校诗人制度的成效,近期也许还看不明显,重要的是要看远一些,当几十年以后,回顾这段诗歌史的时候,看看那些有影响的重要诗人有谁是曾经驻校,是由校园走出的,也许到那个时候,才能较为客观与准确地判断今天工作的价值。因此驻校诗人的工作,还是要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作为教育部门,主要是为驻校诗人与莘莘学子搭桥,做好细致认真的服务工作,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避免急功近利。此外,就驻校诗人制度在青年诗人中受欢迎的程度来讲,现有的驻校诗人的名额限制远远不能满足诗人的要求。因此,应鼓励更多的学校建立起驻校诗人或驻校作家制度,对于这种跨界的带有创新性质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行政部门应该鼓励并予以经费的支持。
当我编定这本《诗人与校园——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研究论集》,不禁感慨万千。十年,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史上不过是一瞬,但是在每个人的生命史中却是不能忽视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了。有幸的是,十年来我与驻校诗人携手走来,目睹了驻校诗人的风采与蓬勃的创造力,也亲身体验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为驻校诗人制度的建立付出的艰辛。驻校诗人王夫刚在离别首师大的时候说:“去年我来的时候,窗外的白杨树是绿的;今年告别的时候,窗外的白杨树依然绿着。从绿到绿,这绿已非那绿;从绿到绿,植物的哲学与人类的思考终将殊途同归作为驻校诗人的老邻居,白杨树进入诗歌是必然,成为驻校诗人的北京记忆之一也是必然”。[7]每当驻校诗人离校的时候,我也一样依依不舍,常会怅然若失地走到驻校诗人公寓前,仰望那棵高大的白杨树出神。这棵白杨树最接地气,却又挺拔俊朗,就像它送走的一位位驻校诗人。如今的白杨树,绿叶扶疏,在微风拂动下,发出飒飒的声响,似乎是在向下一个十年的驻校诗人发出热情的呼唤吧!
注释:
[1]王夫刚.愿诗歌与我们的灵魂朝夕相遇——在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驻校诗人入校仪式上的发言[A].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编.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王夫刚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集》 .2011.
[2]李小洛.以白云为师——在2006年度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入校仪式暨朗诵会上的致辞[A].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编.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李小洛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集.2007.[3][5]杨方.在首师大每一个明亮而饱满的日子里[A].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编.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杨方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集.2014.[4][6]霍俊明、宋晓杰.“只有我,是越来越旧的”——宋晓杰访谈[A].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编.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宋晓杰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
[7]霍俊明、王夫刚.向上的枝条,向下的落叶——王夫刚
访谈录[A].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编.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王夫刚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集.2011.
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