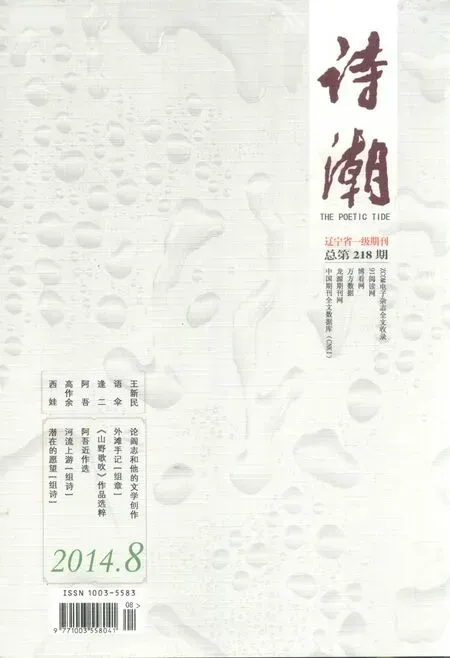“我翻遍了口袋找寻钥匙”
——语伞《外滩系列》析读
2014-11-17
“我翻遍了口袋找寻钥匙”
——语伞《外滩系列》析读
黄恩鹏
每个人都有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常人需要直接的理解,诗人需要隐喻的理解。方式不同,逻辑不同,抵达“隐秘中心”的悟觉不同。我在诸多文本细读中,已经谈到如小说文本那样,要设置诗文本的“隐秘中心”。围绕整个隐秘中心,来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然后再延及世界。在这方面,语伞做得不错。她的作品哲学思辨很强。这对一位女性散文诗人来说实属不易。她能从婉丽的抒写中超拔出来,进入庄子般的静悟中,真正体悟天地。无论高贵,还是卑微,都让文本活脱。她能从庸常的生活本态中,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东西。而《外滩系列》,则是借着一个漂移者的审视,来说“根与叶子”的关联。一切都是以探秘者的身份出现。上海的外滩,成了她的一种精神放脱的审视符号。这种审视符号,是借助者和寻找者的关系。一个外来者,感受现代社会大机器对个体人生的无情碾压。“落叶与落叶,在地面完成着一场场另类的相逢。”人人都是落叶,但并未归属自己的根系。这种巨大惆怅,是身在大都市的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果实最初的酸涩,已不可尝。”具体是如何在这个符号面前,让她认知现代社会与个人精神的关联或影响呢?“某些秘密的事物,正穿行于喧嚷的大街,比耳朵沉默”(《外滩:和声》),这种人生引导,以及“我翻遍了口袋找寻钥匙”的人生没有归宿感,如此强烈充斥文本。理解社会首先要被世界理解。从最初的天真性到感伤性的转变,有如棋弈,要预设下一步的走法,但你永远也不能准确判断“社会”这一强大对手的变招,它总是以巨大的动机左右你的预设路径。与社会对弈的人生,注定会让全身血迹斑斑。那里面包含着普遍的、激烈的人类感知的矛盾的一切。“在镜子里眺望我的人,复制下我的忐忑,转过身,挖掘体内的火焰。”外滩的映象,让人生的精神体系彻底展露。
可以说,外滩是一个大的精神场域。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图式层面的判断与粉墨,皆在此演绎。重组或敛藏,则需诗人的探究。有如哲人之间的对话,总希望能找到一个触角,触摸到对方的心灵世界。那个符号性的指向,早已根植内心,并开始延伸、放大,它所伸出的触角直到让你看到答案为止。但事实是,谁能看到这样的答案?在社会体系面前,一个个巨大的虫洞吸入了人生全部,无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背着祖辈遗训的人,在一幢脚手架支撑起的新大楼房旁和远方的孩子对话,他的手机屏幕上粘满了纯白的灰尘,他繁杂的神情,让人难以用肤浅的见识目测。”肉体与肉体的距离感,也是精神与精神的无法联结。诗人在写“人类的故事”,这个故事是那般的让生命不堪。在变幻莫测的社会面前,真相永远无法抵
达。距离感,让诗人有着巨大的感伤。一种难抑的人生漂泊。外滩,并不是她的最终归宿。身在,心却遥远得没有边际。一切天渊之别,与行色匆忙的人,与变化无常的时光。这种时间面前的构想,完全是博尔赫斯式的,以镜子、光、路、落叶,来暗示生命迷宫般的无常,以及错配的身份、复杂的故事、无望的路径,等等。博尔赫斯提醒我们,真实的主题和中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故事一页一页进展下去,直到它展示了宇宙的各种尺度。诗文本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往往隐藏无限的可能性。人的精神场域,在“外滩”呈现。它绝不是诗人个体的,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大家共有的。它属于时间的呈现。
语伞特别推崇的是萨尔瓦多·达利的《永恒的时间》(也叫《持续的记忆》),之所以能够保持魔力,是因为在记忆或时间面前,你永远无法让“真实性”得以证实。人必须接受一座延续了的、平滑如缎的海滩般的无限。那些被称作记忆的时间,在无限的可能性面前,永远是绵软的存在。时间嘲弄人生,也让这个世界变得空虚或沉寂。语伞的悟性极高,她能从达利的这幅名画中,看到一种虚无的人生存在。有如“外滩”这一境域里存在形役。“江水东流,当我作为俗世的影子,与外滩交换了眼神和思索,抬头望见星辰的须发,正以瀑布的形式,完成光明赋予的使命。”(《外滩,或者光》)永恒与变化,虚无与存在,有如画布上软塌塌的钟表,一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怅惘,不折不扣沉浸的幻想,通过精神的苦痛,一一展现。“光”是一个不确定的存在,更是变幻的喻象。极端与反叛,造就了现代主义般的厌恶和反抗情绪。“不可寻觅”“不可预见”有如外滩的明暗与远近。画面的变形、挪移、漂坠,泛人类的情感对于人生的浸透,有如斯多葛派的冷漠。而“外滩”又是有着游戏规则的,“镜子”内外的各自角色,“更多的被复制的人群,渴望在游戏中试探一个出口”。(《外滩,或者镜子》)“我纷繁的欲念跌入脑海、跌入黄浦江下游的东海,组合成一条大鱼。它游着游着,又张开巨蟒般的嘴巴,回头看我。”这种奇妙的梦幻,让我很容易与现代主义绘画联系在一起。比如亨利·卢梭。“黄浦江”“东海”是现实的广延性的存在,“大鱼”“巨蟒”则是幻思的存在。这种幻象提高了强迫性的梦境般的精神冲撞,是寂寞的游子能体验到的。它裂变成了境象的存在。“镜子”或“沙滩”在博尔赫斯小说中常常出现,人生游移不定、精神生命的易碎感,都是如此。实际是,现实生活无刻不存在魔幻。有时候魔幻却是真实的存在。它就在“我”的身边,天天上演。它驱使我改变脚下的路径。方向游移,心灵转向。而人性与可能性随时可以分裂。但无论怎样这些都是诗人看法。作为个体的人生,不要再为社会的动机而活。因为当你认知了社会动机时,整个人生就会改变。这是“镜子”的不确定性,更是“路”随时改正人行为所指。“我的血管,已被这个城市灌注了太多高贵的谎言。”(《外滩,或者路》)城是一个大规则的概念,它的虚假与挫伤精神性,让你无论来自何方,都将被改变。因为不改变就无法生存。那么,“路”又能给我们多少?路是改变人性图式的存在,行走的过程也是与许多驳杂的事物交错的回味过程。
渴望挣脱“城”的束缚跃然而出。因此诗人追问此时能否有庄子的超逸,或者有悉达多式的服膺自己内心的自由?如何摆脱外在的强制或随波逐流,或者除去束缚地活着?我想这对语伞这一个蜀人来说,极为艰难。她也只能在夜晚或在繁忙之后,借助于心灵的世界,独自找寻了。“我翻开书,返回商周,流浪在‘小雅’与‘大雅’之间。我的马匹,瞬时奔驰于云朵之上。”“天空与大地对应,我走遍自己,无数的影子在太阳下复活。”这个时代,依于内心活着却成了莫大的失落。《外滩,或者悬崖》也如此:城市有如悬崖,愈走愈窄。在走向空旷之时,仍然无法摆脱险阻。俗世的网就在周围临罩。“必须学会障眼法。必须在自我欺骗里把假象记得更牢。”一个迷茫者的心灵世界,让我听见并体悟到了。
幻梦式的思考是文本的基调。这当然与现实的理想无法实现相关。作为一个诗人,在现世生活得久了,肉身已经麻木,精神却打磨得厚重。纯粹的无意识的精神活动,被梦幻的无限力量牵引,正是诗人的一种释放、排解方式。那么,打破时空的限制,让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某种可能的情形之下,联结成丰富的梦想,也许只有诗人能够做到。在语言魅惑下,掩藏的是越来越沉重的复杂心境。拂去外表的灰暗,潜藏着的,是生命原初的光亮。诉诸于文本之中,便有了溪水的希冀。因为“没有一座山能拦得住小溪”(黄恩鹏语),这让她的人生充盈着光亮。双面的人生又有何不好?一切都是关联的,尽管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里,一切皆有可能发生。这需要人自身的调解。在严苛的现实面前,她清醒于现实,又沉睡于梦境。此种双重的人性本态,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