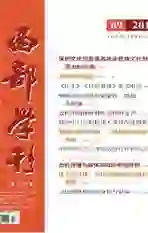《庄子》《吕氏春秋》重文研究
2014-10-23聂中庆
摘要:《庄子》乃庄子学派之文集,其中各篇形成的年代及作者都不尽相同。《庄子》中有许多章节的文字重出于《吕氏春秋》,而《吕氏春秋》形成的年代是确定的。因而理清《庄》、《吕》各篇谁是抄袭者,就可以推断《庄子》各篇是成于《吕览》之前还是之后,这对我们研究《庄子》的流变及各篇的真伪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庄子》;《吕氏春秋》;重文;年代
中图分类号:B223.5;B229.2 文献标识码:A
今传《庄子》三十三篇,是晋郭象编注的。《汉志》载“《庄子》五十二篇”,盖为刘向整理的本子。在刘向整理《庄子》之前,《庄子》当有不同的传本。《庄子》乃庄子学派之文集,此书成于何时已不可确考,书中各篇阐述的义理也不尽相同,当非一时一人之作。《庄子》中有些章节重出于先秦诸子,对这些重文进行细致的比勘,可以帮助我们理清《庄子》的流变,同时对我们甄别《庄子》各篇真伪也不无裨益。
《吕氏春秋》成书于前239年左右,书中有许多章节重出于《庄子》,其中包括《逍遥游》、《养生主》、《胠箧》、《天地》、《达生》、《山木》、《田子方》、《庚桑楚》、《徐无鬼》、《外物》、《让王》等。理清《庄》、《吕》各篇谁是抄袭者,我们就可以断定《庄》文各篇是成于《吕览》之前还是《吕览》之后,这对于我们推断《庄子》各篇形成的时间及作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让王》篇重出的文字较多,笔者拟另撰文进行专题研究。
一、《庄子·逍遥游》: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吕氏春秋·求人》:
昔者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劳乎?夫子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辞曰:“为天下之不治与?而既已治矣。自为与?啁焦巢于林,不过一枝;偃鼠饮于河,不过满腹。归已君乎!恶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颍水之阳,耕而食,终身无经天下之色。故贤主之于贤者也,物莫之妨;戚爱习故,不以害之;故贤者聚焉。贤者所聚,天地不坏,鬼神不害,人事不谋,此五常之本事也。
按:二文事迹略同而行文有别。《庄子》“日月”、“爝火”、“鹪鹩”《吕氏春秋》作“十日”、“焦火”、“啁焦”,无论是《吕》抄《庄》还是《庄》本《吕》,不当有此不同。且《庄》文比《吕》多出“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数句,《吕》比《庄》多出“遂之箕山之下……此五常之本事也”一段文字。我认为既不是《吕》抄《庄》也不是《庄》抄《吕》,而是二书各有所本。盖古代有尧让位于许由的传说,而其记述有所不同,《庄》、《吕》所因袭的应该不是同一文本。另外与《吕》文相比,《庄子》对所引用的文献可能有所修改,重点突出“圣人无名”之主张。而《吕》文意在申明“五常”之理,盖阴阳家所为。陈奇猷云:“此篇盖阴阳家者流之作也。篇中言‘贤者所聚,天地不坏,鬼神不害,人事不谋,此五常之本事也,其重视‘五常之理,正是阴阳家家法,此其明证。”[1] 1525
二、《庄子·养生主》: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吕氏春秋·精通》:
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见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磨研,顺其理,诚乎牛也。
按;《庄》“无非牛者”《吕》作“無非死牛者”;《庄》“全牛”《吕》作“生牛”;《庄》“新发于硎”《吕》作“新磨研”,二者差别较大,盖《吕》非袭用《庄》,《庄》亦非化用《吕》,庖丁解牛应是流传较广的故事,《吕》、《庄》应本自不同的传本,《庄》文很可能对流传的故事进行了再创作。王叔岷云:“陈昌齐《吕氏春秋正误》、陶鸿庆《读吕氏春秋札记》并谓‘生为‘全之讹。因‘全讹为‘生,后人又于上句‘无非下妄加‘死字,遂不成文理。窃以为《吕氏春秋》此文虽本於《庄子》,而有所改易,未必有误。惟施之于《庄子》此文,则诚不成文理。”[2]105陈奇猷云:“许维遹曰:刘先生校《庄子》曰:‘全字乃‘生字之误,‘牛者上敚‘死字,《吕览》可证。”[1]518王叔岷、刘文典认为《吕》“死牛”、“生牛”不误是有道理的。然王氏认为《吕》本于《庄》而有所改易,致使其文“不成文理”则未必可信。哪里有把原文改得“不成文理”的道理?实际上《吕》文所说的“生牛”、“死牛”即《庄》文所谓的“全牛”、“未尝见全牛”。“生牛”是指牛的外表,“死牛”是指牛的肌理,并非“不成文理”。《论衡·订鬼》:“宋之庖丁学解牛,三年不见生牛,所见皆死牛也。”《论衡》所引亦死生对文。
三、《庄子·胠箧》:
故跖之徒问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吕氏春秋·当务》: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
按:《庄》“何适而无有道邪”《吕》作“奚啻其有道也”,《淮南子·道应训》亦载此文,作“奚適其無道也”。依文意,当以《吕》文为正,意谓何止是有道,圣智仁义勇皆存焉。盖后人不知“适”、“啻”古通,而于文中误增“无”字,将此句理解成到哪去没有道呢?将原句清楚的递进关系理解成含糊其辞的何往而无道。抛开文意不论,如果作者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原文当作“何适而无道邪”,《庄》文中的“有”字显然多余,或谓《吕览》因《庄》而去其“无”,实不知《庄》文误增“无”字耳。王念孙云:“本作‘奚适其有道也,‘适与‘啻同。(《孟子·告子》篇:‘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秦策》:‘疑臣者不适三人。‘适并与‘啻同,《史记·甘茂传》作‘疑臣者不特三人。)言岂特有道而已哉!乃圣、勇、仁、义、智五者皆备也。后人不知适之读为啻,而误以为适齐、适楚之适,故改‘有为‘无耳。《庄子》本作‘何适其有道邪!适亦与啻同。今本作‘何适而无有道邪,‘而无二字亦后人所改,惟‘有字尚存。《吕氏春秋·当务篇》正作‘奚啻其有道也!”王叔岷云:“王说甚精,非浅人所能辨也。唯此句疑本作‘何适而有道邪,‘而犹‘其也。”[2]349我认为此句当以《吕》文为准,本作“奚啻其有道也”,《淮南》更“啻”为“适”,《庄子》更“奚啻”为“何适”,后人误解“适”字而误增“无”字。
《庄》“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吕》作“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吕》文为是。关内指室内,中藏指猜中室内所藏之物。句谓猜中室内所藏者为圣。《庄》文只言其猜,未言其中,猜者非圣,猜中者方为圣,故《吕》文义胜。《淮南》作“夫意而中藏者,圣也”,与《吕览》意同。陈奇猷云:“孙蜀丞先生曰:《庄子·胠箧篇》作‘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庄》书‘之字亦当作‘中。上‘中字读‘允执厥中之‘中,下‘中字读如‘臆测屡中之‘中,成疏可证。此盖缘后人于重叠之文记以‘、、,遂误作‘之,《吕氏》、《淮南》并不误也。”[1]615王叔岷云:“《抱朴子·辨问篇》引此文作‘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乃引大意。‘妄意而知人之藏亦即‘妄意中藏之意。又据《吕氏春秋·当务篇》作‘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则《庄子》此文或本作‘夫妄意室中中藏,圣也。‘之乃‘中之误,亦未可知。”[2]350
察文意,《胠箧》引此文以非圣,即所谓“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当务》此文在于阐明“辨(辩)若此不如无辨(辩)”,即盗跖以中藏为圣,入先为勇,后出为义,知时为智,分均为仁,其言虽辩却与儒家观念不符,故曰辩不如不辩。显然作者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批驳盗跖的,此文的作者不可能同意《胠箧》篇的非圣观念。因此我认为《吕览》袭用《庄子》的可能性很小。而《庄》文前有“故”字,当是引自他书。且《庄》文多误而《吕》文不误,亦可证明《吕》文非本自《庄》,《庄》文后出。
四、《庄子·天地》: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立而问焉,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敢问,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阖行邪?无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顾。
《吕氏春秋·长利》: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而问曰:“尧理天下,吾子立为诸侯,今至于我而辞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说,愉愉其如赤子。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后世之乱自此始。夫子盍行乎,无虑吾农事。”协而耰,遂不顾。夫为诸侯,名显荣,实佚乐,继嗣皆得其泽,伯成子高不待问而知之,然而辞为诸侯者,以禁后世之乱也。
按:《新序·节士》亦载此文。《吕》“辞诸侯”当作“辞为诸侯”,与上“立为诸侯”对文,《庄子》、《新序》皆作“辞为诸侯”。《吕》“故何也”当如《庄》作“其故何也”,脱“其”字。《庄》“刑自此立”《吕》作“利自此作”,盖原文赏罚、德刑对举,作“刑”为是,《新序》亦作“刑”。《吕》改“刑”为“利”是为了应和《长利》篇之主旨。据此,《吕》文有晚出迹象。
就内容而言,《庄》、《吕》、《新序》存在明显不同。《吕》“民不知怨,不知说,愉愉其如赤子”为《庄》、《新》所无;《庄》“无落吾事”《吕》作“无虑吾农事”,《新》作“无留吾事”;《庄》“俋俋乎耕而不顾”《吕》作“协而耰,遂不顾”,《新》作“耕而不顾”。又《新序》“(昔尧之治天下),举天下而传之他人,至无欲也,择贤而与之其位,至公也。以至无欲至公之行示天下”诸句为《庄》、《吕》所无,王叔岷云:“案《后汉书·冯衍传》注、《李固传》注引(昔尧治)‘天下下并有‘至公无私四字,《艺文类聚》三六、《御览》五〇九引嵇康《高士传》同。(《新序》‘尧之治天下下,亦有称尧至无欲、至公之文。)”[2]431可见《新序》所本既非《庄子》亦非《吕览》,而《庄》、《吕》亦当各有所本,至于《庄》、《吕》孰先孰后则难以断定。
五、《庄子·达生》:
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吕氏春秋·去尤》:
庄子曰:“以瓦殶者翔,以钩殶者战,以黄金殶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盖内掘。”
按:《吕》文明谓“庄子曰”,则其本自《庄子》无疑。察二文差别明显,盖非本自今本《庄子》。
六、《庄子·达生》:
田开之曰:“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
《吕氏春秋·必己》:
张毅好恭,门闾帷薄聚居众无不趋,舆隶棩媾小童无不敬,以定其身,不终其寿,内热而死。单豹好术,离俗弃尘,不食谷实,不衣芮温,身处山林岩堀,以全其生,不尽其年,而虎食之。
按:《庄》文为田开之与周威公之对话,情节完整。其中“鲁有单豹者”《吕》作“单豹好术”,张毅“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吕》作“不终其寿,内热而死”。《庄》文明确指出单豹的国籍以及张毅的寿数,可见《庄》文早出,《吕》文盖化用《庄》文。察其文,《吕》先张毅后单豹,表述也多有不同,盖古人引书有时单凭记忆,述其大概而已。
七、《庄子·达生》:
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以为文弗过也。使之钩百而反。颜阖遇之,入见曰:“稷之马将败。”公密而不应。少焉,果败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马力竭矣,而犹求焉,故曰败。”
《吕氏春秋·适威》:
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曰:“善”,以为造父不过也,使之钩百而少及焉。颜阖入见。庄公曰:“子遇东野稷乎?”对曰:“然。臣遇之。其马必败。”庄公曰:“将何败?”少顷,东野之马败而至。庄公召颜阖而问之曰:“子何以知其败也?”颜阖对曰:“夫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造父之御,无以过焉。乡臣遇之,犹求其马,臣是以知其败也。”
按:《庄》“以为文弗过也”《吕》作“以为造父不过也”,奚侗云:“本书‘父误作‘文,而挩一‘造字。”其说是。《庄》“使之钩百而反”《吕》作“使之钩百而少及焉”,盖《庄》“反”乃“及”之误,“反”上脱“少”字。章炳麟云:“百即今‘阡陌之‘陌字,‘钩百谓般旋陌上一周也。”少,少顷。及,到达,完成。谓马用很少的时间就能在阡陌上跑一圈,言其速也。比较二文,《庄》有晚出迹象。
八、《庄子·山木》: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
《吕氏春秋·必己》:
庄子行于山中,见木甚美,长大,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以不材得终其天年矣。”出于山,及邑,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具酒肉,令竖子为杀鴈飨之。竖子请曰:“其一鴈能鸣,一鴈不能鸣,请奚杀?”主人之公曰:“杀其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将何以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于材、不材之间。材、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则不然:无讶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禾为量,而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此神农、黄帝之所法。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成则毁,大则衰,廉则剉,尊则亏,直则骫,合则离,爱则隳,多智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
按:1、《庄》“夫子出于山”《吕》作“出于山”,无“夫子”为是。《经典释文》:“夫者,夫子,谓庄子也。本或即作夫子。”《释文》本无“子”字。王叔岷云:“无‘子字者是也。惟‘夫乃‘矣字之误,当属上绝句,上文‘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下,《御览》九五二所引,及《吕氏春秋·必己》篇并有‘矣字,是其明证。因‘矣误为‘夫,后人遂于‘夫下妄加‘子字,以之属下读,既称‘夫子,则此章易误为庄徒所述矣。《艺文类聚》九一、《意林》《御览》九一七、《事类赋》一九禽部二注引此皆无‘夫子二字,《吕氏春秋》同。”[2] 718
2、《庄》“舍于故人之家”《吕》作“及邑,舍故人之家”,后者为是。王叔岷云:“《艺文类聚》、《御览》、《事类赋》注引‘山下皆有‘及邑二字,《吕氏春秋》亦同。”又云:“《文选》卢子谅《赠刘琨》诗注、《艺文类聚》、《意林》、《御览》、《事类赋》注、《事文类聚》后集四六、《合璧事类别集》六六、《韵府群玉》一五引此皆无‘于字,《吕氏春秋》同。”[2]719
3、《庄》“命竖子杀雁而烹之”《吕》作“具酒肉,令竖子为杀鴈飨之”,后者为是。王叔岷云:“《御览》、《事类赋》注引‘喜下并有‘具酒肉三字,《吕氏春秋》同。《文选》注、《艺文类聚》、《御览》引‘命皆作‘令,‘鴈下无‘而字,《吕氏春秋》亦同。”[2]720《庄》文“烹”盖“享”之误。王念孙云:“享与飨通。《吕氏春秋·必己》篇作‘令竖子为杀鴈飨之,是其证也。”
4、《庄》“今主人之雁”《吕》作“主人之鴈”,无“今”为是。王叔岷云:“上文所言木与鴈,皆昨日之事,则‘主人之鴈上不当有‘今字,盖浅人妄加。《文选》注、《艺文类聚》、《意林》、《御览》、《事文类聚》、《合璧事类》、《韵府群玉》二及一五引皆无‘今字,《吕氏春秋》同。”[2] 720 《吕》文末之“胡可得而必”乃是对此篇首句“外物不可必”的呼应语,《必己》篇下文所记诸事之后亦有“外物岂可必哉”之评语,前后一贯。而《庄》文“胡可得而必乎哉”一句与前后皆无呼应,颇显突兀,其袭自《吕览》无疑。张恒寿云:“《必己》篇每引述一个例证之后,总要加几句论断,不应开首引了《山木》篇庄子故事后,偏没有一句解释,便直接提出第二个论证。所以《山木》篇这一段末尾的几句,一定是《吕览》的议论,而不是《山木》篇的原文。”[3]209
九、《庄子·田子方》:
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仲尼见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见温伯雪子久矣,见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
《吕氏春秋·精谕》:
孔子见温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贡曰:“夫子之欲见温伯雪子好矣,今也见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不可以容声矣。”故未见其人而知其志,见其人而心与志皆见,天符同也。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
按:《庄》“子路”《吕》作“子贡”,《御览》引作“子路问焉”,成玄英疏:“仲由怪之,是故起问。”盖本作“子路”。《庄》“吾子欲见温伯雪子久矣”《吕》作“夫子之欲见温伯雪子好矣”,陈奇猷校释引吴承仕云:“好读为孔。孔,甚也。”其说非是。即使此好可以读为孔,孔有甚义,甚矣也不能说成孔矣。《吕》文“好”盖“久”之误。
孔子见温伯雪子只是《庄子》“温伯雪子适齐”章的一小部分内容,盖因其有“目击而道存矣,不可以容声矣”的论述,故《吕览》的编者截取之以明“精谕”之理,并评论说“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庄》文无《吕》“不可以容声矣”后面的评语,可以证明不是《庄》抄《吕》而是《吕》袭《庄》。
十、《庄子·田子方》:
肩吾问于孙叔敖曰:“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吾始也疑子,今视子之鼻间栩栩然,子之用心独柰何?”孙叔敖曰:“吾何以过人哉!吾以其来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我何以过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将踌躇,方将四顾,何暇至乎人贵人贱哉!”
《吕氏春秋·知分》:
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达乎死生之分,则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与崔杼盟而不变其义;延陵季子,吴人愿以为王而不用;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忧;皆有所达也。有所达则物弗能惑。
按:《庄》是问答体,《吕》是论说体。《吕》通过“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忧”之事迹以明“知分”之理,并给予“有所达则物弗能惑”的评论。显然是《吕》袭用《庄》而不是《庄》袭《吕》,因为若是后者,《庄》文理当因袭《吕》文末的评语,且孙叔敖所说的一大段话也不可能是作者凭空编造的。另外《庄》文所阐述的是顺遂自然,与《吕》文所说的“达乎死生之分”有所不同。
十一、《庄子·庚桑楚》:
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吕氏春秋·有度》:
先王不能尽知,执一而万物治。使人不能执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缪,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缪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荡乎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清明,清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按:《吕》文有“故曰”二字,《庄》文没有,盖《吕》袭自《庄》。
十二、《庄子·徐无鬼》:
管仲有病,桓公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谓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管仲曰:“公谁欲与?”公曰:“鲍叔牙。”曰:“不可。其为人絜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治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公曰:“然则孰可?”对曰:“勿已,则隰朋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勿已,则隰朋可。”
《吕氏春秋·贵公》: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行私阿所爱,用竖刀而虫出于户。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饰服,私利而立公,贪戾而求王,舜弗能为。
《列子·力命》:
管夷吾鲍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处于齐。管夷吾事公子纠,鲍叔牙事公子小白。齐公族多宠,嫡庶并行。国人惧乱。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奔鲁,鲍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孙无知作乱,齐无君,二公子争入。管夷吾与小白战于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既立,胁鲁杀子纠,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鲍叔牙谓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国。”桓公曰:“我雠也,愿杀之。”鲍叔牙曰:“吾闻贤君无私怨,且人能为其主,亦必能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鲁归之,齐鲍叔牙郊迎,释其囚。桓公礼之,而位于高国之上,鲍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国政,号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尝叹曰:“吾少穷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大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此世称管鲍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实无善交,实无用能也。实无善交实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鲍叔非能举贤,不得不举;小白非能用雠,不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夷吾曰:“公谁欲欤?”白曰:“鲍叔牙可。”曰:“不可;其为人也,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理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小白曰:“然则孰可?”对曰:“勿已,则隰朋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谓之圣人,以财分人谓之贤人。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勿已,则隰朋可。”然则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
按:《列子·力命》篇亦载此文。比较三者重文部分,《吕》文表述多有不同,如其比《庄子》、《列子》多出“‘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诺”诸句,比《庄子》、《列子》少“使之治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诸句。盖此故事流传较广,流传的文本也不尽相同,《列子》、《庄子》属于同一传承系统,《吕览》则另有所本。
《庄》、《列》间谁是抄袭者?《列》讲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庄》只截取其中的片段来说明管仲举荐能出以公心,不徇私情。实际上是因为有了上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的记述,管仲荐人不徇私情方得以体现。也就是说,如果只读《庄》而不读《列》篇,我们对管仲荐人不徇私情就不会有深刻的领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列》此章乃有机之整体,非杂凑之作。而《庄》此段与前文“庄子送葬”及后文“吴王浮于江”皆无关联,《庄》截取自《列》盖无可疑。
第二,就两篇相重合的文字而言,《列》“及管夷吾有病”,《庄》作“管仲有病”。《列》此段文字承接上文,“及”字不可省;而《庄》将此句作为文章的开头,故有意将“及”字删除。又《列》称管仲为“管夷吾”,称桓公为“小白”,前后一贯;《庄》作“管仲”、“桓公”,此亦表明《列》非袭《庄》。
《列》“可不讳”《庄》作“可不谓”。“谓”当作“讳”,形近而误。奚侗云:“‘谓当作‘讳。《管子·戒》篇:‘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讳也,《小称》篇:‘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讳而不起此病也,《列子·力命》篇:‘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讳云,张湛注:‘言病之甚不可复讳而不言也。《吕览·贵公》篇:‘仲父之病溃甚,国人弗讳,文各小异而义则同,皆可为‘谓当作‘讳之证。”
《列》“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庄》作“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庄》“又”乃“人”之误。孙诒让云:“此‘又当为‘人。‘不比之人句断,言不得齿于人也。《列子·力命》篇云:‘……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吕氏春秋·贵公》篇:‘管仲曰: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高注:‘比,方也。并与此书同,可据以校正。”其说是。
《列》“上忘而下不叛”《庄》作“上忘而下畔”,《庄》脱“不”字。陆德明《庄子音义》:“言在上不自高,于下无背者也。”其所见本当有“无”字。宣颖《南华经解》:“《列子》作‘下不畔,此处漏一‘不字也。上忘者,不自矜其能,故在己上者与之相忘;下不畔者,泛爱众,故在己下者,不见德而亦不忍畔之。”
第三,《列》“则隰朋可”后有“然则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一段文字,《庄》无。此段文字乃上文“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鲍叔非能举贤,不得不举;小白非能用雠,不得不用”之呼应语,用以阐发作者之“命定”思想,不可或缺。《庄》删节上文亦必删去此段文字,否则便会有突兀之感。以上论证说明《庄》此段文字截取自《列子》,《吕》文则另有所本。
十三、《庄子·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
《吕氏春秋·必己》:
外物不可必,故龙逄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乎江,苌弘死,藏其血三年而为碧。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疑,曾子悲。
按:《吕氏春秋》皆以意名篇,一般开头即阐明主题。如《慎人》篇“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遇合》篇“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等。此《必己》篇亦然,开头即云“外物不可必”,下文举例以实之,可见此文是《庄》袭《吕》。另外文中“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等表述也与庄旨不符。张恒寿云:“‘人主一词,在《孟子》中还未出现,到了《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中才成为习用之词。这一词是战国后期对国君的称谓,和后世‘上、‘主上、‘皇上等词的意思相似,皆是臣僚属下尊事其主的称谓。在《庄子》书中早出可信的各篇之中,他对于统治者总表示山谷之人的疏远轻视态度,绝少采用这种称谓。”[3]268其说是。《庄子》中“人主”只出现过这一次,《孟子》没有出现过,《吕氏春秋》出现过82次。
综上,《逍遥游》、《养生主》重出文字《庄》、《吕》当各有所本;《胠箧》重出文字《庄》文晚出;《天地》重出文字《庄》、《吕》孰先孰后则难以断定;《达生》重出的前两段文字为《吕》抄在《庄》,第三段文字难以断定;《山木》重出文字为《庄》抄《吕》;《田子方》重出的两段文字为《吕》抄《庄》;《庚桑楚》重出文字为《吕》抄《庄》;《徐无鬼》重出文字为《庄》抄《列》,《吕》文另有所本;《外物》重出文字为《庄》抄《吕》。
参考文献:
[1]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王叔岷.庄子校诠[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张恒寿.庄子新探[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作者简介:聂中庆,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杨立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庄子》校释及篇章作者研究”(13FZW0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