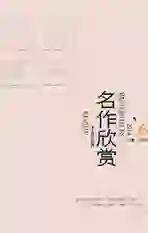“女英雄”形象与苏格兰的性别困境
2014-10-21石梅芳汪贻蒸
石梅芳 汪贻蒸
摘 要:瓦尔特·司各特在《密得洛西恩监狱》中通过珍妮·迪恩斯的形象来象征苏格兰坚韧、勤劳和救赎的善良品质。珍妮与司各特以往作品中的“女英雄”形象差异较大,表明司各特获得英格兰人民的同情和认可的决心。但是珍妮的形象弱化了男性地位,从而动摇了苏格兰独立的教会、司法体系的地位。为了维持联合主义的立场,司各特用珍妮的拯救之旅消解历史事件的政治意义,实则将苏格兰王国弱化到仅有优良品德而无政治实权的附属地位。
关键词:瓦尔特·司各特 《密得洛西恩监狱》 女英雄 苏格兰教会 司法体系
评论家通常将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的小说《威弗莱》《红酋罗伯》和《密得洛西恩监狱》视为三部曲。{1}在这些作品中,司各特均塑造了一些“英雄”形象来代表苏格兰民族性格中英勇无畏的一面。在前两部作品中,司各特一方面通过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的联姻表明其联合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他又从苏格兰所面临的社会结构与道德沦丧问题入手,质疑和批判了现代商业文明对高地文化的摧残。在联姻的基础上,司各特对苏格兰和英格兰在不列颠联合王国中的身份问题进行了设想。通过消解苏格兰民族性中存在的暴力反抗的政治因素,他将联合王国中的苏格兰拟人化为世俗婚姻中妻子的角色。但是由于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利地位,他所设想的联姻实际上陷入了将苏格兰贬低到附属地位的困境之中。
《密得洛西恩监狱》与《威弗莱》和《红酋罗伯》的区别在于,苏格兰的“英雄”从无畏的格伦奈仑、英勇的罗伯·罗伊变成了乡村姑娘珍妮。针对这种巨大的转变,评论家认为司各特的题材从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浪漫的传奇故事转向了普通民众及“私人生活的领域”{2};学者道格拉斯·吉福德认为“司各特选择珍妮·迪恩斯……来象征苏格兰的坚韧、体面和救赎的善良品质”{3}。但是,当苏格兰英雄由打家劫舍的“暴徒”变成虔信上帝、安分守己的姑娘,司各特所致力于塑造的“苏格兰”的民族身份是不是也将由此改写呢?
本文将以女主人公的角色塑造为切入点,分析“女英雄”珍妮的成长过程,寓意着对教会和法律在苏格兰王国中地位的弱化。这种弱化实则增强了苏格兰在联合王国中的从属地位,从另一个侧面深化了司各特的联合主义立场。
一、小说的政治寓意
小说《密得洛西恩监狱》有两条线索,一条是1736年发生在爱丁堡城的波蒂厄斯暴乱,另一条是农家少女艾菲·迪恩斯被判杀婴罪入狱。波蒂厄斯暴乱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源于苏格兰民间走私势力与英国政府的冲突,在民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被认为是“苏格兰自治与王权斗争”{4}的表现。这是1715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失败之后的一次重大事件,严重威胁到了“联合王国”,特别是伦敦政府的权威。
司各特的《密得洛西恩监狱》巧妙之处就在于,他将波蒂厄斯事件的线索与农村姑娘艾菲·迪恩斯被指控“杀婴”而面临死刑的线索交织起来。佃农之女艾菲·迪恩斯未婚产子,但婴儿去向不明,爱丁堡民事法庭根据推断法宣判她犯下“杀婴罪”。姐姐珍妮不肯做伪证来挽救妹妹,却决心步行到伦敦为妹妹求得赦免。经过重重艰难险阻之后,她如愿拿到了赦免令。这两条线索的连接点,就是逃亡的走私贩罗伯逊与被判杀婴的艾菲·迪恩斯之间的关系。司各特设计了一个情节——罗伯逊率众来到爱丁堡监狱,带走获得缓刑的波蒂厄斯;在监狱中他试图劝说已经被判死刑的情人艾菲逃走,却遭到拒绝。正是由于艾菲并未逃走,才最终产生了珍妮·迪恩斯的拯救之旅。最终,艾菲获得赦免,与罗伯逊(即乔治·斯汤顿)远走法国。但光鲜亮丽的斯汤顿夫妇始终受到往日所犯罪行的精神折磨,平凡的珍妮则获得了幸福稳定、儿女成群的家庭生活。
故事的结局很像一个传统的道德教化故事,却隐藏了作者的政治意图。他将艾菲和珍妮·迪恩斯与波蒂厄斯暴亂建立联系,实际上弱化了暴乱引起的政治危机——詹姆士党的阴谋、苏格兰长老会的激进行为等。在作品中,他摒弃波蒂厄斯暴乱的政治意义,将其简化为走私贩的报复行为,而非苏格兰民众对伦敦政府的敌意,有利于化解此次事件引发的伦敦与爱丁堡的矛盾和对立,最终强化联合王国的共同立场。同时,这个“养牛人的女儿”的“天路历程”也符合司各特一贯否定政治暴力和宗教狂热的立场。他认为要想赢得英格兰人民的尊重,必须表现苏格兰民众的美好品质。但是,平民姑娘珍妮·迪恩斯化身“女英雄”拯救妹妹的行为,却消解了民族独立性,实则削弱了苏格兰在联合王国中的平等地位。我们先来看珍妮作为一个女英雄的形象和意义。
二、非同寻常的女英雄
除了最终嫁给英雄、获得幸福的女性,司各特在作品中还塑造了很多“女英雄”的形象,比如海伦·麦戈瑞格、狄安娜(《红酋罗伯》)、弗洛娜·麦克伊沃(《威弗莱》)、明娜(《海盗》),几乎每部作品中都曾出现一个或多个类似的形象。詹妮·卡德尔曾总结说:“司各特作品中的一些女性……她们不是嫁给他笔下的英雄们的女人,而是自身表现出强烈的英雄气概,比如弗洛娜·麦克伊沃、梅格·梅瑞丽思和玛吉野火。另一种英雄品质则是《密得洛西恩监狱》中的珍妮·迪恩斯,她的高贵独立并非一种富有激情的表现力而是源自承诺。”{5}据卡德尔所言,司各特笔下的女英雄分为两类,一是有英雄气概的女性,另一种是没有英雄气概的女性。珍妮则属于没有“英雄气概”的那一类。
“英雄”“英气”和“英雄气概”(hero,heroic,heroism)都是以男性为标准确立的词汇,用以形容男性的勇敢气质。在司各特笔下,这些具有英雄气概的女英雄,多少都具有男性气质。加拿大学者伊娜·法里斯注意到了威弗莱系列小说中呈现出一个独特的特征,那就是对男女性别交换的兴趣。{6}如《红酋罗伯》中的海伦不但身着男性服装,外在特征更具有男性气质。她率领氏族的老弱妇孺抗击英国军队时所表现出的镇定自如、英勇无畏的精神气度,连罗伯本人也难以企及。同时,具有男性气质的女英雄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身份的边缘化,她们一般都游离于主流社会群体之外。如弗洛娜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事业,反对当权的汉诺威王朝;狄安娜也是一个“没有法定保护人的天主教徒”“全郡
最激烈的詹姆士党”{7}。这类女性角色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浪漫主义小说的最佳形象。
然而,珍妮·迪恩斯作为《密得洛西恩监狱》的女主角,迥异于光彩照人、激情洋溢的女英雄形象。她相貌普通、身材矮小,毫无动人之处,并且从未有任何机会和意图进行抗争。她出身卑微的佃农之家,接受清教教育,却仍属于主流群体,其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都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她坚定地相信汉诺威王朝会给她一个申辩的机会,认可远在伦敦的政府对苏格兰统治的合法性。因此,珍妮是司各特笔下的“女英雄”中的特例。非但如此,与司各特前两部作品中出现的“女英雄”相似的形象,在《密得洛西恩监狱》中被设立到珍妮的对立面,成了反英雄。如玛吉野火身着男装,面部特征线条坚硬,富有野性美,表现出一种“英雄气概”,可是她却疯疯癫癫;其母默多克森虽是英勇的高地将领的遗孀,如今已堕落到与强盗勾结谋财害命的地步,成了败坏苏格兰人名声的罪犯。非但如此,默多克森还绑架了珍妮,是妨碍她前往伦敦实现使命的反面因素。这表明,为了寻找和解的可能性,改变历史中两王国冲突、对立的一面,司各特只能放弃了他既爱又恨的边缘女英雄们。选择个性温和、忍耐的珍妮作为《密得洛西恩监狱》的主人公和“女英雄”,司各特淡化苏格兰与英格兰政治冲突的企图非常鲜明。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精神却随着珍妮的伦敦之旅而被削弱了。
三、珍妮的形象弱化了男性的地位
珍妮是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她成为女英雄的过程是在与父亲和恋人的对比中产生的。首先珍妮在审判中坚持忠于上帝的律法,“诚实”守信、不做伪证,冲击了父亲迪恩斯作为精神向导的权威;其次,恋人巴特勒病弱的身体与珍妮強健的身心形成鲜明的对比,弱化了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第三,她不畏惧斯汤顿的威胁,坚持相信伦敦政府的公正,消解了男性暴力的意义。最终,珍妮言出必行的行动力,进一步削弱了教条主义的迪恩斯、肉体虚弱的巴特勒和暴力犯罪的斯汤顿的男性特征,进而削弱了他们在苏格兰社会的象征性地位。
(一)父亲的形象
18至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父亲形象多被塑造成权威的形象。迪恩斯也不例外,他非但重视名节,更以狂热、坚定、高傲不屈的清教徒自居,因此是女儿珍妮的精神向导,也是她断然不肯做伪证的根源。但是,迪恩斯信仰的坚定性只存在于口头上,当女儿艾菲犯下通奸罪、杀婴罪面临死刑的时候,他又暗暗希望珍妮能上庭为艾菲做(伪)证,以挽救她的性命。这与珍妮坚决不肯做伪证,保持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形成鲜明的对比。老父亲面对艾菲被判死刑的结果昏厥过去,珍妮却下定决心步行去伦敦为妹妹求情。这两个不同的结果更表明,本该保护女儿的父亲精神脆弱、行动无力,他的权威性已经岌岌可危。
通常,父亲是女性在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刻提供指导性意见的关键角色。但是,珍妮在面临前往伦敦为妹妹求情这样重大的人生抉择的时刻,却决定不去征求父亲的意见。
珍妮对她父亲虽然孝顺,内心却觉得她父亲纵然正直而高尚,可是同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对于当此危机关头该采取怎样的措施不可能做出合理的判断。{8}
司各特对苏格兰历史上狂热的盟约派信徒的态度向来模棱两可,既敬重其信仰的坚定又忌惮其狂热造成的动荡局势。迪恩斯的角色与《清教徒》中的修墓老人类似,寓意了传统的终结。迪恩斯的清教徒立场与分裂、狂热、暴力的联系,是他被女儿视为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无法对形势做出合理判断的根本原因。司各特在提高珍妮的决策能力的同时,实际上削弱了父亲的权威和功能,将其贬低到象征性的地位——无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只能起到祝福、祈祷平安的作用。
(二)丈夫的形象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提到教育问题时曾指出,女性“被教导着像奴隶似的服从于父母,就为将来做婚姻的努力做好了准备”{9}。对当时的女性而言,未来的归宿和依靠只有一个,那就是婚姻和丈夫。但是,鲁本·巴特勒无论是作为恋人还是丈夫,都并未真正承担起保护妻子、养家糊口的责任。巴特勒的出场伴随着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关于法律、拉丁文、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对话,与迪恩斯吹嘘盟约派的教条一样,无法解决真正的现实问题——拯救艾菲。
司各特开始花费笔墨刻画巴特勒的形象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病弱形象——脸色苍白、身体瘦弱、多疑多虑,无法抗拒任何暴力威胁。尽管司各特不忘贬低珍妮的智力来衬托巴特勒的聪慧,但巴特勒的病弱形象显然是他刻意塑造的,以此突出珍妮健壮的体魄、坚韧的精神足以胜任将来的伦敦之行。在这里,性别角色的颠倒说明司各特决意将珍妮塑造成“苏格兰民族精神的代表”,必然要表现其坚韧、强壮、理智的优点。鉴于珍妮是个“传统的姑娘”,艾菲的杀婴罪危机到来之时,珍妮也立刻想到了两个男性,一位是父亲,另一位就是巴特勒。然而,老迪恩斯伤心病倒,鲁本·巴特勒则持续低烧,“要把身子拖到以劳役换取当天的面包的地方几乎都办不到。”他非但不能代替或陪伴珍妮前往伦敦,也不能给予任何经济上的支持,还要靠珍妮偷偷放下的几块钱生存。
巴特勒的无能为力与老迪恩斯类似,是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的弱化。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对苏格兰的现在与未来也无法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而只能作为“女英雄”珍妮的陪衬。
(三)反叛者的形象
与迪恩斯的清教信仰、巴特勒的病弱躯体不同,斯汤顿是激情驱使下完全失去道德观,不但损害了女性的肉体与精神,更是对苏格兰社会的稳定性产生极大危害的形象。司各特在波蒂厄斯暴乱的真实历史事件中增加了一个细节,即斯汤顿化妆成玛吉野火参与劫狱,试图救出艾菲。斯汤顿的第一次露面是男扮女装,是巴特勒眼中活跃积极的、雌雄莫辨的“女英雄”。但是,斯汤顿的“英雄”形象首先因他的装扮遭到解构,因为司各特作品中的英雄,罗伯(《红酋罗伯》)、弗格斯(《威弗莱》)等人都不会身着女装,性别身份的稳定性是其成为男性英雄的重要因素;其次,他们参与暴力反抗通常寻求的是高尚的目标——苏格兰独立。而斯汤顿却是一场非法骚乱的主角,一场“英雄”救美失败的主角,削弱了其成为英雄的可能性。在作品中,斯汤顿几乎从来不敢公开露面,也未能从劫狱行动中救走艾菲,甚至试图采用暴力威胁珍妮。相比之下,珍妮镇定自若、临危不惧,坚持前往伦敦为妹妹求情,并最终成功的一系列行为,将出身高贵、思想堕落的斯汤顿置于“假英雄”的境地。
珍妮在與生命中最重要的男性——父亲、丈夫、妹夫——的对比中,表现出一个女英雄的面貌,实则削弱了男性在苏格兰社会中的地位。与之相对应的,苏格兰相对较为独立的司法、教会的权威,就面临着女性的挑战。
四、女英雄弱化了教会和司法的地位
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组成联合王国之后,原本行使政府决策功能、象征苏格兰政治独立的议会被取缔,转而在英国议会中为苏格兰议员保留了一定数目的席位。苏格兰教会和苏格兰法律成为联合之后苏格兰王国重要的民族象征。然而,珍妮的伦敦之行,同时还意味着长老会和苏格兰法律在政治上的无能。当女性承担起教会和法律原本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将重要的民族特征(苏格兰教会和法律的独立地位)道德化了。
长老会曾经在苏格兰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联合以来,由于司法过多介入教会事务,苏格兰教会面临分裂。但也有学者认为,18世纪以来苏格兰的长老会顺应了联合的趋势,放弃了苏格兰的统治权。{10}《密得洛西恩监狱》中,司各特对此予以了形象的描绘。当伦敦政府强迫苏格兰牧师在布道前宣读镇压波蒂厄斯叛乱者的法令时,大家虽群情激奋地认为,“凡属公众礼拜方面的事情,只有教会大会才有绝对的权力做出规定;在苏格兰的教坛上,即使用上议院的大主教的名义来宣布什么,也等于承认主教统治制;而立法机关的禁令更无异于政府当局对长老会的jus divinum(神权)的干预”。面对国会法令的干预,苏格兰教会却并未真正做出有力或有效的应对。至少在司各特笔下,缺乏这些应对的例证。他反复强调老迪恩斯如何顽固、傲慢地在私人生活中自恃“最纯真的苏格兰教会的唯一代表”,实则讽刺了以迪恩斯为代表的清教徒的迂腐、可笑。父亲在珍妮的一生中原本是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的指导者,与教会在民众的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地位相当。父亲面对道德问题时表现出的缺陷(伪证)表明他已经失去了威信。无论是老迪恩斯个人面对女儿艾菲的问题,还是苏格兰教会面临伦敦政府法令,都表现出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伦敦政府最终取消高压政策的法令(牧师布道前宣读镇压法令),是珍妮向卡洛琳王后请求赦免妹妹时的一个附带后果(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珍妮承担了教会应该承担的拯救的职责,实际上削弱了教会的功能。但是,由于珍妮缺乏支持詹姆士党的女英雄的男性化特质,她的行为仅有道德意义。通过她的行为,《密得洛西恩监狱》将城市暴乱的社会问题转移到母性与姐妹情谊所面临的家庭危机上,隐喻了苏格兰长老会的“家庭化和女性化”,从而将信仰从政治领域转移到道德层面。{11}
而在苏格兰的司法体系中,也面临同样的危机。如波蒂厄斯犯下谋杀重罪却得到赦免,艾菲·迪恩斯的“杀婴罪”并无真凭实据,法官却仅凭推断法判其死刑,苏格兰的法律似乎陷入了无法代表公平正义、无法保证民众安全的泥沼。市政府官员的名字具有某种暗喻之意,市政官米德尔伯格,原文是Middleburgh,burgh在苏格兰语中是城镇之意,说明苏格兰政府的市政官走的是中间道路,并非为苏格兰民众谋福利;官员费尔斯克利夫则没有固定的立场,只靠在利益和权势之间迅速移动摇摆来实现“公平”(fair scrieve);负责法庭和警务的市检察官沙比特劳(Sharpitlaw)则代表“骗人的法律”(sharpie law)。苏格兰法庭无法查出艾菲杀婴背后的真相,更无法找到波蒂厄斯案件的真凶。因此,珍妮虽求得王后的赦免令从而救了妹妹一命,却将苏格兰法律的意义消解了。人们不由得对苏格兰法律和教会支撑下的苏格兰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提出质疑。从波蒂厄斯事件中,伦敦一方感受到君主权威受到威胁,从而对苏格兰实行了高压政策。珍妮的伦敦之行,实则是对君主权威的认同。珍妮依靠弱化苏格兰人的氏族观念、家族联系和政治倾向性才获得了官方的赦令。在英格兰,在卡洛琳王后面前,她仅是一位穿着苏格兰服饰的普通姑娘,诉说着妹妹的“可怜”、家人的“心碎”、犯罪者的“悲哀”、生者的“痛苦”。她的一句“杀害他(波蒂厄斯)的人一定会罪有应得”,将一场政治危机轻描淡写为普通的刑事案件。同时,苏格兰在波蒂厄斯事件之后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也通过珍妮的伦敦之行转化为纯粹的家庭问题。
五、结论
正如安德鲁·林肯所言,珍妮的英雄行为并不意味着司各特的小说向表现民主化的方向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她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她“不可能获得公共发言
权”{12}。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由于珍妮“她既非世俗的反叛者也非流浪者”,起不到激励人们寻找可被社会接受的、表达女性性别存在的途径的意义。同时,司各特也并未赋予珍妮·迪恩斯的英格兰之旅以成长的意义。在《威弗莱》和《红酋罗伯》中,英格兰青年威弗莱或奥斯巴尔迪斯顿的苏格兰之旅增强了他们的性别特征,使其最终转变为成熟的、富有英雄气概的男子汉。然而,苏格兰姑娘珍妮·迪恩斯的伦敦之行却不能强化她的英雄气概,当她回归家庭之后,立刻恢复了对父亲恭顺、对丈夫忠诚、勤劳顾家的传统女性面貌。只要女性尚处于社会结构的附属层面,其社会身份就不会提高到足以与男性比肩的“英雄”的地位。连公众发言权都没有的珍妮取代父亲、丈夫和妹夫而成为妹妹的拯救者,虽向英格兰的读者奉献了“勤劳朴实”的苏格兰民众的形象,强化了司各特的联合立场,实则消解了苏格兰教会、司法体系的地位,弱化了苏格兰在联合王国中的地位。
①③ GIFFORD, Douglas etc. ed. Scottish Literature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214, 216.
②{11} DUNCAN, Ian. Scotts Shadow: Novels in Romantic Edinburgh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41.
④ WILF, Steven. Laws Imagined Republic:Popular Politics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M].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6.
⑤ CALDER, Jenni. Heroes and Hero-makers: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Scottish Fiction[A]. The History of Scottish Literature. Vol.3: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 edited by Douglas Gifford. Aberdeen: Aberdeen University Press, 1988: 270.
⑥ FERRIS, Ina. The Achievement of Literary Authority: Gender, History, and the Waverley Novel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100-101.
⑦ [英]司各特. 紅酋罗伯[M].李民,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22.
⑧ [英]司各特. 密得洛西恩监狱[M].王楫,任大雄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279(下文所有引文分别出自本书,故不再另注)
⑨ [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M].王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01.
⑩ KIDD, Colin. Constructing a Civil Religion: Scots Presbyterians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State[A]. The Scottish Church and the Union Parliament [C]. ed. James Kirk. Edinburgh: Scottish Church History Society, 2000: 1-21.
{12} LINCOLN, Andrew. Concili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Unspeakable in The Heart of Mid-lothian [J]. Philological Quarterly 79, No. 1, Winter, 2000: 69-90.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市社科基金(TJWW11-2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3YJC752018)
作 者:石梅芳,文学博士,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
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汪贻蒸,文学硕士,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