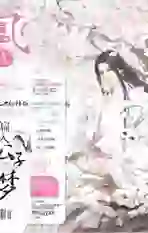风满青衫
2014-10-15莫卡
莫卡

楔子
时值深秋,白霜燃了红叶满树,一辆纱帘轻垂的马车停下,纱帘撩起,四个白衣侍从扶着一个女子下车,将小案酒器摆在红霞一样的枫树下。
小路尽头,一个青衣男子徐步走来,松绿色的长衫似乎也披了一层白霜,他走到女子身边停下,笑着问:“姑娘煮酒赏枫真是好兴致,不知在下能否讨一杯温酒?”
女子没有抬头,执起提梁壶,一丝细细匀称的酒线将白瓷杯注满,她反手拂开悠悠荡在半空的红叶,做了个请的手势,风雅又好看。
青衣男子欣喜走近,那女子却忽然拿起酒杯对着他猛地一泼,四个白衣侍从不知何时分散开来,加上坐在枫树下的女子,组成一个恰恰将青衣男子困在中间的五芒阵。
“收!”
青衣男子惊叫一声,五芒星光芒大涨成了一道结实的网,将他束住。他歪倒在地上仰天长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连这么漂亮的小姑娘都出了家当道姑满街抢男人!”
女子的食指和拇指卡住他的脖子,问他:“妖怪,你就是他们说的近日游荡在昆仑山下各个城池中的青衫客?”
“姑娘,仙姑,大仙!小的是菩提城里的好妖怪从来没害过人!穿青衫要是让您觉着不高兴,我还有红衫白衫黄衫紫衫!我以后再也不穿青衫了您放了小的好不好?”
女子眉头皱得更深,是哪个眼神不好的给她传话说那个青衫客满身仙风道骨,估计就是她要找的青衫剑仙?眼前这个男子眉眼轻佻妖气缭绕,简直就是在脸上写了“在下是妖怪”几个字。
她捏了个诀,身后的几个白衣侍从化作四张小小的纸人飘落在地上,每一张上面都写着“式神”。
“你,在本姑娘游历人间的这阵子,就给本姑娘当仆人吧,勤快刻苦些,本姑娘就考虑放了你。”
青衣男妖怪满脸苦大仇深,问她:“你不是有式神吗?”
“式神要耗损我的法术啊,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以前摔到过脑袋,记不得名字了。”
女子上下打量了他,想起妖怪一般是不肯将真实的名字告诉别人的,就道:“我叫作太阿,我没有剑,你也没有剑,那你得叫个有剑的名字,就叫,龙渊吧。”
那一年昆仑山巅,谁青衫玉隐,笑着对她说过一句相似的话:“为师没有剑,徒弟你也没有剑,咱们得起个有剑的名字,就叫,太阿吧。”
第一章
这一年,是仙门六百年来都不曾有过的热闹。
仙界千万山峰中的修仙门派,不约而同地大规模招收弟子,连向来闭门清修不理世俗的仙山昆仑,也在同一时间向三界广招弟子,所收新弟子人数之多,连闭关许久的首座弟子都不得不出关来亲自主持。
风满好奇地随着前往昆仑学艺的人群坐上船一样大小的巨蚌,漂过昆仑山下传说中不浮雀羽游鱼的弱水。
弱水正中长了一棵能预知战事名为风声木的神树,它的一半叶子为金石,金石长出则战事至;一半叶子是翠玉,每当金石代表的战事得到平息,就会长出一片相应的翠玉。此时,金石的叶子正无风而动,紧促地敲击着。
昆仑之上立刻流星般划出几位御剑而行的剑仙,悬浮在半空中仔细辨别了金石叶子生长的方向,便在众人的惊叹中御剑而去。
风满手脚并用,爬完了昆仑山三万七千四百五十六步的石阶,接过昆仑长老手中用来测试新弟子灵力所属的灵石,一道紫气猛地窜入灵石又迅速消失,那灵石便已在风满的掌心裂成了几瓣。
长胡子的长老笑开了一脸的褶子,乐颠颠地拉住风满不许别人和他抢徒弟。
风满后来才知道,别的弟子握着灵石,出现的都是代表了五行的青黄赤白黑,偏她是紫色的——剑气,这是修仙中极高的天分与灵根。
风满瞬间成了准备收徒的长老争抢的对象,直到挑选佩剑的那天,她推开藏剑阁的大门,刚一伸手,满屋子的弟子剑就纷纷震飞撞成一团,墙壁上挂着的名剑也嗡嗡长鸣躁动不安。
风满和一地佩剑的残骸被请到了巍峨空旷的昆仑殿里,昆仑的首座弟子淡漠地看着她说:“所有的长老都不肯收你做弟子,你虽然天分不错,整个昆仑,却没有一把属于你的剑。”
风满听得懵懵懂懂,低了头不好意思看那过于好看的脸,红着脸说:“没关系,我去隔壁山上学耍金刀,或者去隔壁的隔壁学流星锤都可以的。”
“哈哈哈,这便是那位传说中天分极高却被昆仑所有的佩剑嫌弃了的新弟子?师兄不如让她去我殿中,陪我抄经吧。”
殿门边不知何时站着一个人,身影修长,逆着昆仑的雪光山色,着一袭沾了雾气的松青色长衫,短发寸长刚刚及耳,瓷白脸上一双眸子如白瓷砚里新研开的浓墨。
这便是昆仑掌门的第二十个弟子,重墨。据说他曾是昆仑最有天分的剑师,藏剑阁中有一半的名剑出自他手,而他最骄傲的两柄剑,便是已成为传说的龙渊与太阿。他最喜欢的是太阿,太阿无形无迹,只以剑气存于天地之间,待天时、地利、人和三道归一,方现于世。六百年前三界与鬼族一战,重墨以太阿剑重创鬼族之王,鬼族兵败后,太阿化为剑气归于天地,重墨也从此不再执剑,六百年来每日只待在自己的殿内抄写整理经书文卷。
“二十,你居然舍得从你的屋子里出来了?好在你的龙渊剑被你沉在了天池水底,不然也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在那一对残骸里。”
重墨举起手里的小茶壶,严肃道:“你们到底是招了多少新弟子,连我殿中煮茶的小童都被拉去帮忙了。师兄,你要是再不给我个人煮茶,我就去效仿夸父,喝干一条河。”
首座弟子无奈而沉默地看他,他便径自走向风满,笑道:“近日龙渊日夜长吟,想是有故人旧梦终于拾得归途来归。”
她抬头看他,睁大了眼睛,只觉殿门外净白的雪景似成了一幅悬起的画卷,重墨便从那画卷的留白处走出,衣襟带风,玉石如削,一身风华。
第二章
风满在神游间便被转手给了重墨,回过神时已经认命地蹲在重墨殿中的小炉前给她这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师父煮茶。
“茶都要被你熬干了。”
耳边冷不防地响起重墨不满的声音,风满一惊,手忙脚乱地将茶壶取下来,又尖叫着把已经烧得通红的茶壶丢了出去。
重墨下意识地伸手接住迎面飞来的茶壶,“刺溜”一声皮肉烫焦的声响,灼热的触感立刻从手心传出。
他稳妥地将茶壶放在一边桌上,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被烫伤的手掌看了半晌,突然“啊”了一声,将手伸到风满面前说:“看,烫坏了。”
风满连连道歉,拿了药膏纱布为重墨上药包扎。
重墨看着她认真为他的手上药,无聊地问:“你为什么要到昆仑学艺?”
风满顿了顿,晃了晃脑袋道:“不知道为什么,上山之前的事都记不得了,好像我睡了好长的一个觉,一睁开眼就站在昆仑山脚下了。”
她甚至连名字都记不起,只因上山前,山下菩提城中算卦的老龟看着她说了一句“山雨欲来风满楼”,她便取了“风满”两个字做自己的名字。
风满紧张地抬头看重墨,以为他会不相信追问下去或者对她的来路不明心生怀疑,却见重墨用没受伤的另一只手支着下巴,靠在一边的小案上,浓墨般的眸子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那目光过于坦荡和专注,细看去又似乎若有所思意味深长,风满不由得有些无措起来,手脚都慌张得不知该怎么摆,脸上也莫名隐隐发烫。
她立刻转开话题,随口问道:“……师父,那个,那个,首座师叔怎么一直冷冰冰的不爱说话呢?”
“嗯?”
“我上昆仑之前,路过昆仑旁边的天什么城,他们也在招新弟子,人家的首座大师兄也是仪表英俊正气浩然,但是阳光灿烂地一笑花都开了,为了吸引我们入门还特意穿了弟子袍带着一众弟子跳舞呢。”
风满做了一个抹鼻血的动作,以表示对别人家的大师兄舞姿妖娆的膜拜。
“哦,那你怎么不去他们那儿做弟子呢?”
“我正准备去呢,谁知道大师兄跳舞跳到一半,一个长得可好看的少年红着一双眼拿着把剑就冲出来了,忒吓人了,我想着大概他们派的剑法练不好就容易走火入魔。”
重墨点点头,拿起桌上的残茶喝了一口,问自己新收的徒弟:“你来我这儿也有些日子了,想在为师这里学点什么呢?”
“长生不老容颜永驻可以吗?”
重墨摇头。
“点石成金呢?”
重墨还是摇头。
然后把自己刚被包好的手伸到风满面前,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说的那些都不实用,为师来教你些简单实用的,比如——这伤口自愈之术。”
他的手在风满眼前随意一晃,风满缠了半天的纱布便一圈一圈散开,露出重墨半点烫伤痕迹都没有的手。
“……”
风满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药粉和绷带,别过脸去,不忍看那个因为成功欺负了自己徒弟而笑得无比得意的男子。为何别人家的师父不是倾国倾城就是飘然若仙,她的师父却是个没长大的顽劣少年?
重墨喊住收拾完要离开的风满,按照规矩,上了昆仑之后,做师父的要给自己徒弟起一个俗家名字之外的称号,为修行之用。
重墨笑了笑,对风满道:“为师没有剑,徒弟你也没有剑,咱们得起个有剑的名字,就叫,太阿吧。”
第三章
“你,龙渊,把你那到处飘的长发给我束整齐了。”
抵死不肯交出真名只好接受女道姑赐名的男妖怪很不开心,闻言潇洒地甩了甩一头飘逸到凌乱的长发,痞痞地仰起头说:“大仙恕罪,小的生来不会绑头发,一直都是这么放荡不羁!”
太阿迟疑地问他:“你……不会束发?”
她伸出手,龙渊立刻捂脸跳开,叫道:“不许打脸啊,别以为你是神仙就能胡作非为,我们菩提城的妖怪头顶昆仑山,从来不害怕你们这些仗势欺人的!”
谁知太阿手里却拿了一把梳子,一根发带,小指一勾,龙渊身上的五芒星印便牵引着龙渊脸朝下扑到了太阿旁边。
光滑温润的象牙梳穿过龙渊墨色的长发,太阿记起,很多年前,曾有人唤她对着银河繁星,许一个愿望,她却没有来得及将愿望说出口。
孤身一人绝望找寻的这些年里,她都不敢去回想那个没说出口的愿望,此时却随着指尖缠绕的长发,被一点点扫去了岁月的尘屑,满月一般明亮温暖地从她的心海浮出。
第四章
那一日,是昆仑的拜师仪式,在自己名下收了弟子的昆仑长老和大弟子们,都要在大典上为自己的徒弟亲手束发,冠上昆仑弟子的白玉发冠,以示昆仑仙法师徒传承。
重墨在长长的队伍里,默默地摸出一把剪子,对着风满的头发就要“咔嚓”下去,却被旁边的首座师兄一把拍下,收走剪子,斥他“胡闹”。
风满对上自己师父眼中怜悯的神色,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果然到给她束发时,她感觉到自己的头发被扯掉了一撮又一撮,她的师父一边抻长了脖子看别人家的师父束发,一边在她耳边碎碎念:“徒弟,你不要怪师父,师父已经尽力了。看你师父我这一头的短发,就该知道我是个不会束发的。他们又不让我剪了你的……咦,不都是这么绕的吗?为啥就你的头发会一直掉下来呢?”
风满双手护头,痛苦地拧着眉头道“弟子有罪,不该长一头让师父束不好的长发……”
大殿上的众人看着着急,又因为这是师徒传袭之礼,不好用法术更不能由他人越俎代庖,一时间昆仑殿上下三千弟子就这么默默又焦灼地盯着那与长发斗争的师徒二人。
重墨忽然抓起风满的手,放到她的长发上,低声说:“来,为师握着你的手,你自己给自己绾,也算是把这白痴的仪式进行完了。”
那双手并不十分温暖宽厚,手心还有曾经握剑留下的薄薄的茧,就那么轻轻地覆盖在她的手背上,既让风满感觉到他在,又不会让她的手被限制了灵活,那契合好似手心薄茧,皆是记忆的深眠,因着重逢而浅醒——遥远的光影中,那是谁,在对着她欣慰浅笑,唤她“吾剑太阿”?
“太阿、太阿、太阿,为师渴了。”
风满“咚咚”地奔过去奉上新煮的茶,磨磨蹭蹭地抠着桌角在一边不肯走,直到重墨抬了眼看她,才弱弱地问:“师父,你能给我换一个名字吗?我是个女孩子,叫一把那么霸气的剑名,以后还怎么去见喜欢的人啊。”
而且简直跟中了邪似的,自从那天授徒大典上得了太阿这个名字,她天天晚上做梦都梦到自己变成那把紫气森森的古剑,有一个低沉的声音笑着叹息般唤她:“太阿,归来……”
那声音真实得就跟她师父在她耳边喊她似的……
风满一顿,怀疑地看着自己不靠谱的师父,对上他晶亮的一双眼,又觉得他虽然平日里看着像一个没心没肺的少年,倒也不至于无聊到半夜三更跑到徒弟耳朵边喊名字玩。
“喜欢的人?你喜欢谁,我的首座师兄?放肆!那是你的师叔!”
风满一惊,“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满心想说不是这样,却慌张得语无伦次,最后只是恳求师父别生气,请师父责罚。
半晌,才听到她师父的声音从厚厚的经卷中传出,他用探索天地玄妙的语气喃喃道:“一般情况下年轻的小徒弟不是都该看上自己的师父吗?不应该啊,怎么就我徒弟这么叛逆呢……”
风满跪了一会儿,见她师父再无他话而是已经专注于经文,才默默地爬起来,去殿外点燃了一盏青铜座莲花灯,用手小心护着灯芯,走回大殿深处。
此时早已夜深霜寒,她师父抄写经文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内殿靠着墙壁四面放着与殿顶齐高的檀木书架,垒满了泛黄的古经书卷。
重墨一身凝霜的松绿色长衫,端坐在书案前,那眼神沉静,是让人明了的专注和虔诚,仿若灵魂已经从墨染的笔尖流泻进抄写的经文中,整个人如烛光中凝成的一块琥珀,发着岁月磨出的微光,隽永而温柔。
风满笼着烛火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看他一字一字,看他连成一行,看他写满一张。
她曾经问过重墨,为何修仙的昆仑不用法术来做这样冗繁的事情。重墨告诉她,法术并不能做到真正的永恒——即便修仙,所谓的长生不老、容颜永驻也不过是暂时的,终有一日,他们会在沧海桑田中化为虚无。法术会随着他们的消散而消散,笔墨记载下来的东西却不会,它们比灵魂更坚定,比时光更长久。
她以凡人之身前来昆仑寻求高深的修仙之法,她的仙君师父却在教她怎么活得像一个世间的凡人。还理直气壮地问她:“你连一个凡人都做不好,还修什么仙?”
案边工整写满的纸已经堆成一座小山,重墨停笔收拾,转眸见着风满,惊讶地问她:“你一直站在边上拿手护着灯?”
他看向风满的眼神中,还有没退去的抄写经文时的虔诚专注。
风满点头,小声说:“弟子怕烛火在风中晃动,晃了师父的眼。”
重墨眸光灼灼,眼神复杂地看了风满半晌,叹气道:“你怎么能蠢成这样,昆仑的灯,用的都是南荒的不尽木做的灯芯,别说风吹,就是水泼都泼不灭。”
说着似乎是为了给自己的凡人徒弟长长见识,居然立起身,撑着桌面越过大半个身子,鼓起腮帮子对着风满手中的灯盏使劲吹了一口气。
风满只见重墨白瓷一样的脸突然贴近她,墨色的眸子只映着一簇烛火和一个小小的她,带着他气息的风刮在她的耳膜上,如击鼓一样。
她下意识地连退几步,脸上不受控制地烫起来,手一松,转身跑走了。
风满沿着月色跌跌撞撞跑出了重墨的宫殿,两只手捂在耳朵上直到如雷的心跳慢慢平静下来。
她有些迟疑地看着自己的双手,灯,呢?
第五章
不尽木,生于南荒火山,燃时暴风不熄,骤雨不灭。
此时的重墨宫殿,就被这不尽木的火焰点燃了满殿的经书纸张,在夜色之中烧得热热闹闹。
“师父!”
风满哑着嗓子嘶喊了一句,连滚带爬地往熊熊燃烧的大殿冲去,却在门口不小心被什么绊倒在地,也顾不得低头去看,站起来继续往殿里冲,却被人一把扯住了手臂,仔细一看,绊倒她的竟是脸被熏得乌黑的重墨。
“师父、师父……”
风满一头扎进重墨怀里放声大哭,被重墨嫌弃地用两根手指抵住她的额头推开:“要哭去找你喜欢的首座师叔哭去,为师这里没有你哭的地方。”
话虽说得薄情,手却还是伸了出来,在哭得打噎的风满背上轻轻拍了拍。
“嗝……师父,怎么办,你的经文……”
“愚蠢,为师不会用法术把它们转走吗?”
“那……嗝,你怎么不用法术把火灭了?”
“……为师是这昆仑山上的天才剑师,又不是负责烧炉生火的,怎么会学过灭火的法术。所以为师常常教导你,不要什么都依赖法术——笑什么笑,还哭不哭了,不哭就陪你师父我逃命去吧,那么大一座宫殿烧成了灰,你师父的师父会弄死我的。”
风满扶着他站起来,犯难地问:“可是我不会御剑,师父的剑也都收在剑阁中,我们也都没有坐骑。他们说昆仑山下那条弱水见什么淹什么,上山时坐的那个巨蚌平时都漂在四海之上,我们要怎么下山?”
重墨不理她,自顾自地往一处殿宇走去,拣了一间屋子扑上去挠着窗户的木格子喊:“三师兄!三师兄!快把你的剑穗借我过下弱水,我徒弟不小心把我的大殿烧了,师父会打死我们的!”
门打开,一个男子打着一个美人灯笼出来,腰间的剑上挂着一个浅绿色的剑穗,看了眼不远处火光冲天的殿宇,也不说话,朝山下走去。
重墨赶紧招呼因觉丢脸而使劲扯着他的衣角连头都抬不起来的徒弟,拽住自己师兄的剑穗跟上,据说那剑穗是弱水之妖的发丝所制,当年他三师兄落入弱水,全靠那剑穗相护,才能从水底安然无恙地浮上来。
在剑穗的庇护下,三人如履平地走过弱水,走进山脚下的菩提城。
一进城门,重墨师兄灯笼上的美人就从灯笼上飘了下来,吓得风满直往重墨身后躲,待那人和灯笼走得远了,才弱弱地问重墨:“师父,那个灯笼上绿色头发的是个妖怪吧?三师叔那个灯笼妖气好重,不对,这座城的妖气都好重,我觉得头晕……”
重墨见她脸色果然极差,想起她灵力中纯正的剑气,与这满城的妖气的确相冲。
重墨嘴角翘起说道:“这菩提城可是你最喜欢的首座师叔给他喜欢的姑娘建的妖怪城呢,怎么了,你不喜欢?”